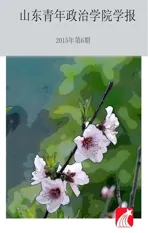都市青少年公益参与行为研究
——基于全国十大城市青少年公益活动的实证分析
2015-04-09徐圣龙
任 园,徐圣龙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083)
都市青少年公益参与行为研究
——基于全国十大城市青少年公益活动的实证分析
任 园,徐圣龙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083)
提升和改进都市青少年公益参与,一是要实现都市青少年群体对于公益推动的价值认同;二是获得与政府合作的资质和经验,搭建公益平台;三是创新公益方式,与青少年缩短距离,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积极参与;四是规范公益行为,这需要政府、公益组织、企业和相关公益参与者共同参与制定公益营销标准和协作规范;五是要及时评估公益绩效最主要是围绕青少年群体自身的特点展开分析,合理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公益和公道行为。
都市青少年;公益参与;组织;政府;社会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在经济发展之外,社会建设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益慈善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力量也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与许多后发国家一样,中国的公益事业也是自上而下启动的。不过,社会大众的参与无疑为公益事业的持续化、实效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优良的载体。而青少年群体在公益领域表现尤其抢眼。无论是在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还是在汶川、玉树地震等突发性自然灾害的救助行动中,无论是各种微公益活动,还是学校、社区、医院等场所奔走服务的公益性社团或组织,青少年都体现出了坚定、果敢、有为、担当的公益形象和青春力量,越来越为社会所认同和赞誉。
那么,就目前发展态势良好且代表未来中国公益事业发展重要趋势的都市青少年而言,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有:在中国转型时代的宏观背景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历程中,青少年的公益认知、公益行为和公益价值观状况如何?青少年如何进行公益活动,偏爱个体抑或组织、草根抑或官方?影响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因素有哪些?青少年公益参与面临哪些挑战和困境?如何让青少年的公益热情长期保鲜?未来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发展态势如何?本文尝试通过研究中国都市青少年公益行为的状况作出回答。
一、研究概述
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公益即是公共利益的简称,是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而公益行为是指提供满足公众福祉和利益的公共产品的活动。这里的公益活动,不仅仅指帮助弱势群体,还包括新兴的环保、保护动物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益活动。
本调查采用多阶段定比分层的方法进行,研究对象为全国十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武汉、西安、郑州、哈尔滨、沈阳)的9682名青少年,样本包含在校青少年、在职青年与社会青年三大群体。样本构成方面,在校青少年4831名(49.9%),在职青年3531名(36.5%),社会青年1320名(13.6%);男性50.3%,女性49.7%;本市户籍60.3%,非本市户籍39.7%;独生子女55.8%,非独生子女44.2%。
二、主要结论与原因分析
1.都市青少年个人素养与公益行为之间相关性显著
这里所指的个人素养主要考察了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家庭因素等变量,这些变量通过“只要有机会,我都愿意参与公益活动”调查项显示,P值均小于0.05,因此具有显著性,亦即公益参与意愿与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有显著的相关性。进一步分析发现,首先,就受教育程度而言,本科学历与专科高职学生年均公益参与频次居前,随后为高中生、研究生和初中及以下;其次,就经济状况而言,经济收入越高,公益参与意愿越强。与此同时,家庭经济状况与公益意愿的交叉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结论。绝大多数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当地上层水平的都市青少年都选择了“非常同意(53.1%)”和“比较同意(32.7%)”,而其他各阶层的青少年至多是“比较满意”,还有相当一部分认为“说不清楚”,另外,父母职业状况和受教育程度与青少年公益意愿的交叉分析也基本符合上述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包括本人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个人与家庭收入状况等个人要素是影响都市青少年公益参与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因素。这充分说明了经济状况和受教育水平是青少年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本,这两方面条件越好就意味着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优势,更有能力参与到包括公益活动在内的社会事务中,从而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也更容易获得持续参与的效能感。
这一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竞争愈发激烈,公民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所需的时间、精力和能力也受到极大的挑战。而社会公益行为的产生离不开有着良好生活素质公众的参与,这种良好生活素质包括了精神健康状况、生活幸福与满意指数等指标,要知道,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是难以唤起人们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和奉献的。其次,青少年公益参与的状况深刻反映了社会的良心与公民的素质,甚至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精神和有机状态。了解都市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避免现代社会的原子化状态,如何最大程度地调动青少年的公益参与积极性。
2.各公益参与平台所获褒贬不一,共青团与草根组织最受信任
在“通常喜欢以哪种途径参与公益活动”一项中,都市青少年就喜欢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单位或学校组织的公益活动”、“媒体倡导的公益活动”、“政府号召的公益活动”、“自己或家庭寻找帮助对象”及“NGO等社会组织发起的公益活动”。这与他们获知公益慈善活动信息一项的调查结果吻合。
但上述结论经由信任度一项检验后(0分表示一点都不信任,10分表示非常信任)可知,看似影响力甚广的官方组织其实不容乐观。都市青少年对各公益参与平台的信任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共青团组织(6.85分)、草根公益组织(5.99分)、官方公益组织(5.85分)以及半官方公益组织(5.75分),这充分说明了都市青少年公益参与与公益认同的不一致,而此状况如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势必会影响都市青少年的参与意愿与行动的持续化。另外一题的调查更可以佐证前述结论,在关于“影响您参与公益活动的最主要因素是何”一题中,“社会公益的透明度不足”仅次于“经济因素”排列第二。
总的来说,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虽然近年来民间公益组织大量涌现,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公益事业依然有着很强的国家动员特征。中国的“强国家”形态在社会自主性的增长过程中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因为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突出成就而使自身的合法性不断增强,政府在管理技术和技巧上也更加成熟和多样化。[1]事实上,政府应给予公益慈善事业更多的扶持,“对政府而言,更重要的不是亲自做公益,而是创造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提供优惠政策和措施等各种手段让公益组织和慈善事业自发成长。”[2]
其次,建立在强势国家的基础上,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却也导致公益慈善领域沾染了过重的“官方痕迹”和“组织色彩”。[3]这一因素使得公众对公益组织的信任产生了双向叠加危机效应,一方面,由于分配不公、官员贪腐等原因,民众将对官员、政府乃至社会的不信任感投射在官方或半官方公益组织上;另一方面,部分官方或半官方公益组织曝出的“善款丑闻”、“公益资金挪用”等事件成为民众对其不信任的重要来源,而这两方面对公众心态乃至价值认知是构成相互促进、相互叠加效应的。
最后,共青团作为党联系青年群体的桥梁和纽带,是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成立的,承担了部分政治职能,这是共青团不可回避的政治属性。但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家治理机制的调整,共青团积极顺应形势主动转型,在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方面不断创新,以适应青年自主化、个性化的时代特征,形成了覆盖面广、联系广泛的组织网络,并积累了丰富的青年工作经验,承袭了国家动员能力的传统资源,而在青少年公益参与的动员和组织方面更是拔得头筹,这些都是其得到广大都市青少年认同的重要因素。
3.民间组织地位较为弱势,动员能力亟待增强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民间公益组织在公益活动中无疑处于一个较为弱势的地位。例如,在获取公益慈善信息方面,被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学校团委、学生会等组织(27%),然后相对均匀地分布在自发的志愿者社团(14.4%)、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19.3%)、网络媒体和自媒体(18.9%)和同学、朋友等朋辈群(16.6%)。相比较而言,从各类民间组织方面获取公益慈善信息的仅占3.5%。另外,在公益参与渠道偏好上,青少年群体的参与偏好基本和获取公益信息来源一致。由此可以看出,民间组织不管是在公益信息传播能力,公益活动组织能力,以及公益影响力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间组织资源获取能力上的不足。民间公益组织不仅在获取经济资源方面远不及官方或半官方组织,在获取政策支持和法律保护方面也存在不足,亦即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缺乏。“我国现行法律将民间公益组织界定为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身份”,其中,“只有基金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其进入门槛太高,基本上民间公益组织够不着”,“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不例外地有业务主管单位的限制和不得在同一区域存在相同或类似组织存在的规定”,“大量民间公益组织就沦为第四类民间公益组织类型:志愿者组织,几乎没有什么独立地位和身份”。[4]
二是民间组织在公益信息传播能力上的缺陷。由于政策法律的限制和经济资源上的局限性,民间公益组织的确很难像官方或半官方组织那样,通过大型的新闻媒介或行政组织去传递公益信息,但其实,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发展与官方或半官方组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困境。另外,民间组织在新媒体应用能力上仍然乏力,调查发现,都市青少年群体通过网络媒体或自媒体获取公益信息仅占18.9%。
三是民间组织在组织建设方面的松散和非正式。官方组织或半官方组织的公益活动开展大多依赖于严密科学的组织结构支持,而民间组织强调自身的社会性,偏好自由和非正式的运作方式。事实上,民间公益组织并不必然要建设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但其需要形成基于公益理念的“核心—半核心—外围”的组织架构。
四是民间组织在品牌建设方面的忽视。对于官方组织或半官方组织而言,政府就是最大的信用和担保。而民间组织则需要通过自身的品牌建设来积累社会资本,吸引更多社会成员的参与。但民间组织的品牌建设与经营能力还有待提升,只重视项目运作而忽略品牌经营必然不利于其组织的良好发展,这也是改变民间组织弱势地位和动员能力欠缺的重要途径。
4.都市青少年公益认知与公益实践存在一定差距
调查显示,青少年群体在公益认知与具体的公益行为之间存在偏差,对于公益内涵的理解也较为狭隘。在对都市青少年参加公益活动频次的调查中,过去一年内一次也没有参加公益活动的占比26.9%,1-2次占47.3%,3-5次占18.7%。公益认同与公益实践在青少年群体中存在偏差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于公益内涵理解的狭窄。虽然绝大多数青少年都认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只要有机会,我都愿意参与公益活动”等理念,但是,公益理念不局限于这些普遍的流行观念,它也体现在青少年群体节俭、环保等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中。例如,大多数青少年表示其在日常行为中会出现“使用一次性筷子”、“不随手关灯”、“未自备购物袋”等行为。再如,以参与献血和接受志愿者培训为例,在校学生和社会在职青年,参与率都较低。在校学生中参与献血为3.8%、接受志愿者培训为6.0%,在职或社会青年有过献血经历为9.4%、接受志愿者培训为8.4%。因此,公益内涵缺乏细化,缺乏与日常生活习惯的关联,缺乏与道德的互动互补,这些都使得青少年群体存在高认知率、低参与率的问题。
二是对公益组织形象理解的定式。青少年群体对公益组织认同度低必然会导致公益参与度低。首先,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公益组织负面新闻使得青少年群体很难区分个别公益组织丑闻与公益组织整体之间的关系。其次,对官方和半官方公益组织形成了一定的刻板形象,“因为是政府和正式组织的号召、动员,所以一定程度上说青年们是被动参与青年志愿者服务的”,“这种被动的参与使得青年志愿者的主体性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并且,“这种组织形式社会认同程度不高”。[5]再次,民间公益组织发展得不成熟,未能在官方或半官方组织之外提供充分的公益实践空间。
三是公益实践受非公益因素的干扰。非公益因素对青少年群体公益行为的干扰,即在存在功利性条件下,公益参与率较高,反之则低。调查发现,在公益参与目的一项,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25.1%)占比最高,有志愿者经历的简历会比较好看(7.3%),可以获得荣誉和评奖加分(5.3%)等,相反,出于服务目的和价值诉求的占比并不高。这也就可以部分解释何以出现社会青年和在职青年的公益参与率低于在校学生的现象。另外,基于功利性动机的参与者也会影响其他个人,产生对公益实践的抵触行为。
5.所在城市是影响都市青少年公益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因素
影响都市青少年公益行为,除了个人素养、公益认知和公益组织要素外,“所在城市”作为外在环境因素也对都市青少年公益意愿和公益行为有着显著影响。调查显示,将所在城市变量与年度公益活动次数进行交叉分析,排名居前的城市为哈尔滨、天津和上海。按照选择“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者为标准,将“只要有机会,我都愿意参与公益活动”选项与所在城市变量交叉分析显示,排名前四的城市为哈尔滨(81.8%)、北京(79.0%)、郑州(77.4%)和天津(76.1%);将“捐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无论多少”与所在城市变量交叉分析显示,排名前四的城市为哈尔滨(91.6%)、郑州(89.9%)、武汉(89.4%)和西安(88.4%);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选项与所在城市变量交叉分析显示,排名前四的城市为哈尔滨(81.9%)、北京(81.5%)、天津(77.0%)和郑州(76.4%);将“我相信大多数公益活动的真实性”与所在城市变量交叉分析显示,排名前四的城市为北京(70.8%)、哈尔滨(69.1%)、上海(62.2%)和天津(60.5%);将“我愿意将公益当做职业乃至事业”与所在城市变量交叉分析显示,排名前四的城市为哈尔滨(56.7%)、北京(49.7%)、天津(49.3%)、上海(44.4%)。
上述结论可以看出,东部发达地区城市青少年对公益活动的信任度和投身公益事业的意愿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总体来说公益参与意愿和公益行为并未高出中西部城市。在十大城市中,哈尔滨的调查结果尤为引人注目,青少年无论是公益行为还是意愿都特别强烈,这应该与城市公益文化良好的发展状况有着重要关系。
一个城市的公益性文化也是该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居民在公共参与中所表现出的公德素质、文明行动是个体对社会的贡献,正是通过个体所结合成的相互支持和帮助的共同体,城市的和谐与持续发展才得以实现。而通过公益参与过程中所体现的人们之间较为密切、充满道德和情感色彩的社会关系,是推动社会互助互爱、和谐共处之人文环境形成的重要意涵。东部发达大城市由于融汇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梦想者、谋生者等多元群体,经济发展水平良好,人们的精神需求更为热切,但与此同时,更为复杂、疏离且充满风险的城市环境和异质化程度更高的社会关系,使得现代公益理念和社会合作意识更被大众所接受和践行,青少年更容易形塑基于集体生活的认同感、归属感、互助性和公益精神。相比东部城市,中西部城市的经济差距会导致不同城市公益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毕竟,城市公益文化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城市经济基础之上,因而哈尔滨的调查结果尤为引人深思。事实上,东部地区的城市应注意城市的综合实力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方面面,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中西部地区更应借鉴东部城市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力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均衡发展。
三、思考与建议
当代中国城市公益活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城市公益活动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具体到都市青少年公益活动,一方面,如何有效巩固既有公益活动机制及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围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何更好的发挥都市青少年公益活动的作用。通过调查研究,其存在提升和改进的可能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凝聚公益共识
凝聚公益共识是指实现都市青少年群体对于公益精神的价值认同,对于都市青少年而言,如何实现公益价值共识,需要理顺两对关系。
一是情感迸发与理性精神的关系。不管是对于公益观念的认同,还是对于公益活动的参与,都需要个体情感的支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个体感情的因素往往较重。公益活动离不开情感要素,但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又是不充分的,青少年群体尤其需要提升公益的理性能力,通过一些公益课程、公益讨论、公益培训等,可以很好的提高青少年群体在公益活动中的理性精神,实现情感迸发与理性精神的结合。
二是利他与自利的关系。自利不等于参与主体的功利。青少年群体参与公益活动,不仅是对特定社会群体或共同关注问题的帮助,也是对自身的一种锻炼和提高,这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自利”。因此,在公益价值的传播中,需要引入有关公益与青少年群体自身提高的关系,只是需要避免公益与功利的关联,以防误导青少年群体的公益观。
2.协同公益组织
“当前的中国社会仍是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相结合的模式,政府的活动和控制几乎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6]这使得公益组织容易出现部门化利益倾向。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草根公益组织由于快速发展,部分呈现出零散、重复和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既不利于公益活动的展开和公益目标的实现,也会对青少年群体的公益参与和自身成长造成不利影响。上述因素使得公益组织的协同、整合成为必要。针对青少年群体的自身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政府职能需要由“全能型”转向“服务型”,这是改变公益组织部门化利益倾向的根本所在。同时,社会公益组织与政府关系实现合作化、规范化、市场化,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获取资源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获得与政府合作的资质和经验”。[7]二是搭建公益平台。公益平台的搭建是协同社会公益组织的重要方式,它既包括半政府的公益组织,也包括各类非政府组织,甚至包括各类草根组织,为其合作、协调、整合提供充分的条件。公益平台的搭建是青少年群体公益参与的重要载体,既为其公益活动提供规范、广阔的平台,也避免了公益活动中各类混乱、不规范乃至非公益现象。三是打造公益品牌。虽然公益活动与企业营销本质上存在差异,但是,品牌建设却是吸引更多人参与公益活动的重要途径,尤其对处于时代潮流先锋的都市青少年群体而言。因此,公益组织协同的过程,也是公益品牌形成的过程。
3.创新公益方式
公益方式创新主要是指公益对象的选择、活动过程以及具体形式的改变、拓展和丰富。一方面,公益方式创新是公益发展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公益方式创新符合青少年群体偏好,同时,这也是吸引更多人参与公益的重要途经。
当前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公益方式创新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例如通讯媒介、信息传播媒介以及活动方式的多样化、个性化,但这并没有抓住创新与青少年群体的核心关联。青少年群体的公益创新应该以青少年为参与主体,实现自组织、自治理,改变在固有模式下的被动参与和负面激励,这里可以参考零点公司的“公益创新工作坊”。其在四个方面区别于现有方式:一是性质上的差异,工作坊的形式主要是发挥青年群体的主体性,每一个参与成员都需要主动提出自己的看法,通过协商达成计划,并负责实施,而不是被动接受任务;二是公益对象的选择,青少年自主选择对象群体或共同话题,并且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公益项目;三是公益活动参与过程和具体形式,允许各种技术创新和活动形式创新;四是公益活动的引导,工作坊形式并不和现有的公益形式相冲突,而是在其基础上,充分激发青少年群体的自主性,但这并不否定公益过程中的正确引导。
4、规范公益行为
规范公益行为主要是指公益活动过程中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它不仅针对不同的公益主体,同时也涵盖公益活动中各方参与者。首先,青少年群体作为公益活动参与者容易出现“不受约束、独立自主”的现象,这表明了青少年对“自主公益行为的渴望”[8]。但同时也反映了青少年乃至整个社会公益组织,都存在不规范、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其次,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公益营销活动中,公益与营销边界的模糊、泛化所导致的不规范行为,必然会引发相应的公益行为失范。
如何规范公益行为,从而为青少年群体的公益活动提供合理、合法的制度规范,这就要求:一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益组织之间的关系,政府既要提供充分的社会空间,变革现有合理而不合法的社会公益活动,也要为公益组织的合法运行提供制度保障,避免可能出现的逾矩行为;二是规范企业主体的公益活动和公益营销行为,建立一套企业公益营销遴选机制尤为必要,当然这需要政府、公益组织、企业和相关公益参与者共同参与制定公益营销标准和操作规范。
5.评估公益绩效
公益绩效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公益行为及其目标是否有效实现,二是通过改变哪些因素可以更好的发挥公益组织的功能作用。对于青少年群体的公益参与,绩效评估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首先,就公益活动与公益目标的关系而言,目标的制定和细化不可或缺。公益活动结束后,通过反馈和调查,可以很好的反映特定公益活动的绩效。其次,就影响公益活动的效用和功能发挥的因素而言,可以围绕青少年群体自身的特点展开分析。对于青少年,需要分析的方面包括心理、价值、偏好、个人资本以及补助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因素对公益绩效的影响。这里尤其需要注意非物质性受益因素,即个人资本项。虽然青少年群体参与公益活动一般不存在薪金项,但是,个人资本项间接等同于薪金项,因而这里存在公益活动与激励因素的关系。
四、结语
涂尔干认为,一个社会引以为荣的地方,不是因为它们最伟大、最富庶,而是因为它们最公平、组织得最好,具有最合理的道德结构。[9]托克维尔也说过,人民都知道社会的普遍繁荣对他们本身的幸福的影响,人民都习惯于把社会的繁荣看做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每个人都认为公共的财富也有他们的一份,并愿意为国家的富强而效劳。[10]在任何社会中,公益行为历来是民间社会的原动力,是一个国家社会秩序和文明进程的标志,而在当下急剧变迁的社会情境中,更是弥足珍贵。对上述这些议题的考察和追问,不仅有助于客观分析青少年公益状况,合理引导青少年公益参与和公益行为,有效促进社会建设和公益人文精神的形成,也是记录下中国社会力量成长和公民社会崛起的社会印迹。
注释:
①工作坊是指通过对参与人员、活动主题、时间和空间环境的精细化设计,使参与者围绕一个明确的需解决的问题,借助一定的工具,进行充分的讨论沟通和互动,最终拿出具体解决方案的一种研究和实施流程。公益创新工作坊是特指工作坊这一研究方式,在公益话题研究和公益解决方案设计和规划领域的延伸使用。参见陈馨:《公益创新的“势道术”》,载《市场研究》2011年第1期第29页。
[1][3]刘威.回归国家责任:公益慈善之资源动员与群众参与的新传统[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9).
[2]郑莉.“公益”时代遭遇诚信危机[N].工人日报,2011-03-27.
[4]崔巍,何超.论民间公益组织的法律地位[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6).
[5]昝玉林,昌灯圣.网络社会青年志愿者服务组织形式的发展[J].青年探索,2008,(2).
[6][7]虞谷民.政府与社会公益组织协同机制探析[J].党政论坛,2012,(8).
[8]陆霓.我国青少年自主公益行为参与现状[J].当代青年研究,2011,(7).
[9]涂尔干(渠东等译).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1.
[10]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70.
(责任编辑:赵广平)
Behavioral Study on Commonweal Participance of Urban Youth——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Urban Youths' Commonweal Participance of Top Ten Cities in China
REN Yuan, XU Sheng-long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China )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stimulate and improve the commonweal participance of youths who are in urban areas. First, deliver recognitions of values on promoting Commonweal of youths; second, i construct commonweal platforms after acquiring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ience of cooperating with government; third, innovate commonweal method for shortening distance between commonweal activities and youths and attracting more youths; fourth, regulate commonweal activities, which requires all the participants including governments, commonweal organizations, enterpris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engage in formulating marketing standards and cooperation specifications; last, assess the commonweal performance duly. The assessments should be carried on concentrating on youths' group characteristics for leading the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commonweal and impartiality activities.
Urban Youths; Commonweal Participance;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 Society
2015-10-0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人民团体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研究”(14YJC810010);201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中国都市青少年发展报告》项目资助
任园(1986-),女,讲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2014级博士生,主要从事共青团与社会组织方向的研究;徐圣龙(1988-),男,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2013级博士生,主要从事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
D432.63
A
1008-7605(2015)06-004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