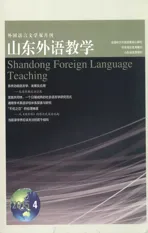“斯芬克斯的第三只手臂”——论《三臂人》中的身份危机与道德寓言
2015-04-08张连桥
张连桥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爱德华·阿尔比作品的《三臂人》是一部有关“道德失控”的寓言,剧中主角“第三只手臂”的出现与消失喻示着人类“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及其复杂性,展示出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剧本围绕着“他自己”因为“第三只手臂”先后所遭遇的一系列伦理变故而展开,讲述了人们面对某种畸形与奇观趋之若鹜的怪像,由此引发的价值扭曲与道德失控的局面。论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方法,紧扣剧中“第三只手臂”的出现这一核心伦理事件,剖析“他自己”的伦理遭遇与伦理选择的过程,探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剧中人物道德失衡及背后的伦理动因,以此窥见剧作家的伦理旨趣:通过书写极端的道德失控,寄寓人们对于理想道德法则的向往与正确伦理秩序的呼唤。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三臂人》;身份危机;道德寓言
DOI:10.16482/j.sdwy37-1026.2015-04-012
“斯芬克斯的第三只手臂”——论《三臂人》中的身份危机与道德寓言
张连桥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315211)
[摘要]爱德华·阿尔比作品的《三臂人》是一部有关“道德失控”的寓言,剧中主角“第三只手臂”的出现与消失喻示着人类“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及其复杂性,展示出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剧本围绕着“他自己”因为“第三只手臂”先后所遭遇的一系列伦理变故而展开,讲述了人们面对某种畸形与奇观趋之若鹜的怪像,由此引发的价值扭曲与道德失控的局面。论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方法,紧扣剧中“第三只手臂”的出现这一核心伦理事件,剖析“他自己”的伦理遭遇与伦理选择的过程,探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剧中人物道德失衡及背后的伦理动因,以此窥见剧作家的伦理旨趣:通过书写极端的道德失控,寄寓人们对于理想道德法则的向往与正确伦理秩序的呼唤。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三臂人》;身份危机;道德寓言
DOI:10.16482/j.sdwy37-1026.2015-04-012
收稿日期:2015-02-2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3&ZD128)和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爱德华·阿尔比戏剧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5NDJC072YB)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连桥(1982-),男,土家族,贵州沿河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伦理学批评和欧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献编号] 1002-2643(2015)04-0088-08
Abstract:Edward Albee’s The Man Who Had Three Arms is a fable about “losing control of morality”. The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third arm”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is play not only symbolize the existence of “Sphinx Factor” and its complexity but demonstrate the ethical conflicts between rational will and free will. The play expands around a series of ethical changes “Himself” has undergone because of “the third arm”, and narrates a strange spectacle that people have shown up when facing with some kind of deformities and wonders. The play describes the value distortion and moral tailspin caused by this spectacle. Taking the approach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third arm”, the core ethical event in the play. Through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ethical encounter and ethical choice of “Himself”,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thical motives behind the moral imbalance of characters, including “Himself”, in order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playwright’s ethical purport. By writing extreme condition about losing control of morality, Albee commits people about his yearning for the ideal moral law and calling for the correct ethical order.
The Third Arm of Sphinx:
On Identity Crisis and Moral Fable inTheManWhoHadThreeArms
ZHANG Lian-qi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Communi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TheManWhoHadThreeArms; identity crisis; moral fable
1.0引言
当代美国著名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Franklin Albee)在上世纪50年代末被当作美国“荒诞派”剧作家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其创作的戏剧人物常常“是现实观察和高度紧张的混合物,与此同时却又有着荒诞不经的夸张”(Hirsch,1978:6),“正如美国剧作家常常在一种明显安全的现实主义的渴望和实验的诱惑之间挣扎,因此在阿尔比作品中,我们看到一种介于现实主义和荒诞派戏剧之间的紧张关系”(Kauffmann,2005),此外,阿尔比戏剧通过表现“残酷、仇恨或是恶意损害着人类的自满情绪;野蛮的谩骂、荒谬的陈词滥调,或是在大难临头时的幽默态度刺激着观众,使人感到日常生活的凶暴”。(哈桑,1982:225)然而,在荣膺了1967年和1975年两次普利策戏剧大奖之后,他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创作的作品未被百老汇剧场追捧,阿尔比创作陷入低谷。加之阿尔比长期酗酒、放荡不羁,批评家对阿尔比这一阶段的作品更多的是持敌意的态度。尤其在1981年,阿尔比把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Lolita,1955)改编为剧本搬上舞台,引发诸多争议,甚至被认为是对纳博科夫小说“可怕的亵渎”(deplorable desecration)。(Way,1975)创作于1981年的《三臂人》(TheManWhoHadThreeArms)正是阿尔比创作低谷期的作品之一。实际上,阿尔比这一阶段的作品同样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阿尔比于1993年再次夺得普利策戏剧大奖,这也证明了阿尔比“从这段所谓的戏剧荒芜期受益匪浅”。(Bottoms,2005:7)
作为一部大胆创新的两幕剧,《三臂人》剧中角色均以代码命名:“他自己”(Himself)是此剧唯一的主人公,男主持人“男人”(Man)、女主持人“女人”(Woman)分别客串“他自己”人生历程中的多个角色,包括“他自己”的妻子、医生、领导、同事和“他自己”的经纪人等。剧中男主持人介绍了“男人对男人”(Man on Man)系列节目的由来和曾经在这档节目里做嘉宾的名单,接着引出主人公“他自己”的出场。戏剧围绕着“他自己”对自己传奇式人生的讲述而展开:“他自己”因突然拥有第三只手臂的风光生活早已成为过去,此次作为受邀嘉宾讲述自己的人生遭遇只为告诉他人他的成长经历、他拥有“第三只手臂”的过程、拥有“第三只手臂”之后的人生变故和“第三只手臂”逐渐消失之后的落魄与凄凉。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作品的价值一方面在于通过具体的事例对时代的道德进行歌颂与弘扬,另一方面在于揭示时代转变时期社会观念变化引发的种种道德问题”。(聂珍钊,2014:248)而道德问题历来探讨的是向善与向恶的问题,积极向善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些不道德可能会因此触犯法律,引发伦理混乱。《三臂人》正是这样一部有关道德寓言的故事:主人公“他自己”的“第三只手臂”恰恰喻示着人类“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因为“他自己”等人伦理意识的淡薄,在面对金钱、名利与地位的诱惑时,其“兽性因子”控制并主导了“人性因子”,利用“他自己”“第三只手臂”的“奇迹”,四处敛财,放弃了对于道德准则的坚守,成为金钱与利益的奴隶。本文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方法,紧扣剧中“第三只手臂”出现与消失的伦理事件,逐一分析“他自己”陷入身份危机后所遭受的诸多伦理变故,探究“他自己”身份危机背后的根源及其伦理选择的过程,进而分析《三臂人》内在的伦理思想。
2.0畸形的伦理身份与突发的伦理变故
在剧中,“他自己”作为节目的嘉宾,以充满冷静的、漠不关心的、讽刺的和诙谐的语言风格,讲述他的成长经历、婚后生活的林林总总,其间穿插着“他自己”与主持人之间的重复的、唠叨的和毫无意义的对话,包括两位主持人对“他自己”生活中所涉人物的“客串表演”。“他所探寻的新的戏剧语言,是其根深蒂固的本能的一部分,以此寻找处于现代经验的核心中的存在困惑的适当表达。”(Paolucci,1972:5)实际上,“他自己”的成长经历与生活细节十分普通,毫无亮点,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的人生经历:在一个普通的小镇,一对普通的夫妇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婴儿,之后这个婴儿开始成长,先后读小学、中学,终于如父母所愿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顺利留在了大城市。接着“他自己”又讲述了自己为何选择现在的妻子,因为现在的妻子比较传统,他喜欢传统一点的女孩,然后是恋爱、结婚、生子,之后他在大城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作为一家企业的高管,生活稳定且较为殷实。总之,“他自己”的一生都按照了他的设想而展开,无论是其童年生活,还是成年后的婚姻生活都相对稳定,正如“他自己”所说:
“他自己” 我的事业一路上升,可以说我的前途无量,妻子在我身边,小孩在我膝边蹒跚学步,充满喜悦、成就、安全感和可预测性……迅速的提升,长久富裕的顶峰,计划中的减速:简单的生活,简单的停止。然后。然后,这一切发生了,永远改变了我命运,创造了我,毁灭了我,成长了我。”(Albee,2005:160-161)①
然而,突然有一天,“他自己”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因为他发现自己突然间长出了“第三只手臂”。“第三只手臂”的出现成为“他自己”的人生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而且从此打破了平凡而可预测性的生活。
在过去平凡的生活里,“他自己”从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长出第三只手臂,这突然到来的“奇迹”(miracle)让他措手不及,也惊恐不已,让他更加恐慌的是,这第三只手臂有自己的“思想”,虽然长在“他自己”的身上,却并不能完全由“他自己”所控制。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样:这突来的第三只手臂“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全部的定义”。(P150)从此,“他自己”因有了第三只手臂被视为一个“怪物”(freak),他的伦理身份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他自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具有伦理意识的正常人而出现;另一方面却因为多了第三只手臂而变得不普通,这只手臂同原有手臂一样受到意识和知觉的支配,却又不完全受“他自己”所控制。因此,“他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畸形的身份”(deformed identity)。自从“他自己”有了第三只手臂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由此遭受诸多的伦理变故。
“他自己”由于多了“第三只手臂”而被当作格格不入的“怪物”,在单位里不仅被人嘲弄,最后还遭受解雇,理由是与一个长有第三只手臂的“怪物”一起共事会引起恐慌。失去工作的“他自己”,开始混迹街头,无所事事,然而各种账单几乎让他疯狂,不仅有抵押贷款、保险费、医疗费、学费、汽车费、食物费等,还有等待他“供养”的“第三只手臂”,此时的手臂还较小。之后,“他自己”在其表兄的推荐下,聘请一个退伍军人作为自己的经纪人。这个军人对“他自己”的“第三只手臂”进行包装与宣传,很快“他自己”便大红大紫,成为人们的追捧对象。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他自己”变得高兴,因为这第三只手臂不完全受他自己意志的控制。尤其到夜间的时候,这第三只手臂居然强制对“他自己”进行手淫,完全不顾其妻子的感受,而他却无法控制这第三只手臂,这让他的妻子终究难以忍受,带着孩子离开了他。至此,“他自己”因为突然拥有了第三只手臂而丢掉了工作、失去了妻儿,脱离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另一方面,经过经纪人和随行团队的策划与炒作,“他自己”从一个“怪物”摇身一变,成为轰动全国的“名人”,“他自己”伦理身份再次发生改变,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改变。
对“他自己”来说,鲜花、掌声、签名和留影等各种“名人生活”让他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然而,“他自己”同时成了人们满足猎奇心的“玩偶”(doll),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奇迹”。“他自己”的所有言行被经纪人和随行人操控着,连吃面包是先吃外面的皮还是先吃里面的心,都由别人来设计。可以这么说,“他自己”成为了满足人们好奇心的“丑角”:他以一个“玩偶”的形象供世人消遣、娱乐,“他自己”再次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自己”作为自我的个体伦理存在,有着对生活的追求与热爱;另一方面“他自己”作为他人的“玩偶”却没有了自我的存在感:“他为两股相互纠缠又彼此争夺的力撕扯着,使他无以自处也不知所终,只能任凭自己在一种带有深刻自戕性质的辩证法中扭曲、粉碎、分裂、挣扎。”(孙柏,2002:76)
在成为“名人”后“他自己”过得并不开心,相反无比沮丧。作为一个“名人”的“他自己”四处走穴,实际上只有着人的行为却没有人的思想和灵魂。正如剧中一个天主教牧师对“他自己”说:“你是大自然一个意外的产物。”(P151)在“他自己”被人们当成“玩偶”期间,因为在各个方面都被安排和被控制,一开始他经常一个人独自悄悄地哭泣,不但是为自己拥有“第三只手臂”而羞愧,更多地是为自己逐步失去了自我而悲戚。从这一点上来讲,“他自己”的伦理意识尚未完全丧失,但当他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他之后,“他自己”逐渐变得麻木和玩世不恭。正如“他自己”所说:“与此同时,在深层意义上来说,解脱。突然一切负担都离我而去,愧疚,恐惧……还有希望。不再有希望,也没有拯救与诅咒。”(P154)
此外,“他自己”全国巡回演讲的出场费最高的时候是每次2500美元,经济上的高收入并没有给他带来富裕的生活,相反,“他自己”出场费越高,他背负的债务就越多。自从“他自己”大爆料之后,“他自己”把孩子从学校接回到家里,高薪聘请教师单独辅导,昂贵的费用都是从经纪人手中支取;此后,“他自己”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又高薪雇佣一群私人保镖,这笔不菲的费用同样来自于经纪人的运作。毫不夸张的是,私人裁缝、厨师和私人医生等只有娱乐界明星们所享受到的贵宾待遇“他自己”都拥有。“他自己”的所有收入与经纪人团队五五分成,经纪人越来越有钱,“他自己”则因为开销过多而越来越穷。
最后,当“他自己”的第三只手臂开始逐渐变小、变短,直至消失的时候,经纪人团队和其他随行人员纷纷离开了他,社会也再次抛弃了他,然而因为成为“名人”期间开支过多,“他自己”背负了近三百万的巨额债务。尤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自己”受经纪人的蛊惑,专门为他的第三只手臂购买了两百五十万的保险费,以防有一天第三只手臂的消失或受损。面对巨额负债,“他自己”希望保险赔偿能够还清债务,结果保险公司告诉“他自己”,保险费的受益人是经纪人,而经纪人早已领走了这份保险赔偿。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2014:263)伦理身份的改变,会打破原有的伦理关系,进而引发伦理冲突。《三臂人》中矛盾的焦点就在于主人公“他自己”伦理身份的改变:“他自己”因为突然出现的“第三只手臂”而成为“不正常的人”。值得补充说明的是,“他自己”因为突然多了“第三只手臂”而改变了其伦理身份并不是“他自己”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作为一个受害者遭受这些伦理变故,这正是这出伦理悲剧的伦理结(ethical complex),直到“他自己”的“第三只手臂”消失,这一切才得以结束;然而,当“他自己”被社会抛弃之后,他并没有选择积极地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是选择了通过包装和炒作自己,利用“畸形的伦理身份”使得他成为他人满足好奇心的“玩物”,形成“名人效益”后获取不义之财,这一点却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伦理身份既是伦理选择的前提,实际上也是伦理选择的结果。
3.0扭曲的价值认同与缺席的道德约束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衡量伦理选择是不是道德的行为取决于伦理身份的不同。因为“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有时甚至是强制性约束,即通过伦理禁忌体现的约束”。(聂珍钊,2014:264)在《三臂人》中,“他自己”因为有了“第三只手臂”而被社会抛弃,在通过包装之后成为名噪一时的“名人”,然而“他自己”却没有发挥“名人”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实际上道德约束的力量在“他自己”身上已经不起作用,“他自己”所作所为只为敛财。人们纷纷追捧着“他自己”,把“他自己”视作这个世界的“英雄”,是“自耶稣受难后就没有过这样的故事”。(P182)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自己”对信仰早已放下,信仰生活已离他远去;作为“名人”的“他自己”没有给社会带来积极的效应,没有做出更广泛意义上的贡献,也没有对人们的精神价值有所提升,“他自己”之所以出名完全是因为他是一个拥有第三只手臂的“怪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没有炸开原子弹,我没有写过15行的四重奏,或者是拯救过国家。我长了该死的第三条手臂!这能有什么能耐呢?”(P148)
作为一个“怪物”,“他自己”却得到了人们的追捧和赞美,人们议论纷纷,争先恐后地抢购门票,以便“聆听”来自于一个奇迹般“伟人”的声音。“他自己”的经纪人先是举办了轰轰烈烈的记者招待会,之后举行盛大的游行,把“他自己”的第三只手臂当作世界上的“第八大奇迹”,“他自己”的“第三只手臂”高举美国国旗,一时引起巨大轰动。接着出版各种各样的小册子、画册、介绍资料和“他自己”的自传等。“他自己”的全国巡回演讲也十分受欢迎,并通过这种形式收取高额的门票,同时,每次活动都收取高额的赞助费。此外,“他自己”受邀去多个王室作演讲,接受总统的召见,参加东京的世界医学大会,成为各种杂志的封面人物等等。总之,“他自己”成为世界最出名的人物之一。“伦理选择是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不仅要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而且还需要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聂珍钊,2014:263)然而,成为所谓的“名人”与“英雄”,“他自己”并没有履行与之相应的伦理责任与义务,也没有在道德上树立榜样,相反,“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道德的,通过“第三只手臂”获取金钱、名誉和地位,这是一种不正当的致富方式,也是一种不正当的经济行为。
“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要对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进行历史的辩证的阐释,而且要坚持用现实的道德价值观对当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作出价值判断。”(聂珍钊,2006:9)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传统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颠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冲击着传统价值体系,诸如信仰价值危机、存在价值危机、生态价值危机等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却是传统的价值观及道德风尚的日趋衰落。”(刘建军,2005:255)人们对代表了传统美国精神和核心价值的那些政治人物或历史人物、科技人员、战争英雄等普遍持怀疑态度,人们对“名人”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对嬉皮士、娱乐明星、喜剧小丑等人物趋之若鹜,而人们所追求的“名人”身上并未体现出诸如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积极进取、富有开拓精神、充满信仰力量等积极向上的品质,相反,这些“名人”只是依靠一些搞怪、作秀来满足人们猎奇心理和窥视心理。一些被人们视为英雄的人物事实上却是“反英雄”(anti-hero)的,他们对传统新教伦理所要求的价值原则和道德戒律已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人们把一些怪诞事迹与耶稣受难相提并论实际上是亵渎了耶稣基督。因此,在宗教衰微的美国20世纪中叶,传统清教道德的约束力量受到享乐主义的现实体验的挑战,使各个层面的价值认同发生扭曲,传统的清教道德预设(moral presupposition)没有发挥作用,道德力量的缺席使得人们做出种种道德失衡的行为。
《三臂人》所凸显的正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评价(value evaluation)和道德约束(moral restraint)力量的缺席。人们纷纷追捧“三臂人”的背后,与社会价值评价标准的失衡是分不开的。这种价值评价的失衡,又与道德的约束力量的缺席分不开。《三臂人》所展现的价值评价标准的扭曲和道德约束力量的缺席,是与名誉、金钱和享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普遍盛行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又加速了这种扭曲和缺席,自我管理、社会舆论乃至社会心理、文化心理都深受影响。道德约束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功能在于道德力量会对人们一些不良的言行形成一定的规避作用。当“三臂人”被吹捧为“奇迹”而成为红极一时的“名人”时,这里折射出了“三臂人”作为名人的道德风险(moral risk),无论是“三臂人”身边的受益者、围观者,还是“他自己”,对名誉和金钱,乃至享乐,都是在这种价值评价的扭曲和道德约束的缺席的背景下所发生。“个体道德勇气的丧失原因在于公众需要一个英雄,尽管在这个英雄身上完全缺乏英雄的品质。”(Roudané,1987:178)我们是否应该把掌声和鲜花送给一个有“第三只手臂”的“怪物”?而前文所概述的围绕着“他自己”所包装和炒作的“奇迹”,正好与人们热衷名誉、骗取钱财、追求享乐的心理分不开。如此轰轰烈烈的包装和炒作,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经纪人团队、医生和围绕在“他自己”身边的人。
作为一个经纪人,他的道德预设应该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和保护当事人的名誉为前提,但事实恰恰相反,剧中的经纪人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想着充分利用“他自己”的“畸形”和人们的猎奇心理,采取各种措施让那些痴迷的观众不断掏出银子。即便到了后期,在“他自己”的第三只手臂开始变小并逐渐消失时,“他自己”的经纪人也只顾自己的利益,策划出了一次盛大的记者招待会,声称这是一次告别会,第三只手臂将告别人间,就像上帝要收回所有荣光一样。于是那些没有看过这只手臂的人们,再次争先恐后购买门票,以免错失目睹自耶稣基督受难以来所没有过的“奇迹”。之后经纪人团队从中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并在“他自己”的手臂彻底消失的时候,不见了踪影。
作为一个医生,他的道德预设是以救死扶伤为天职,把病人的病情控制在最早的阶段,或者以减轻病人的痛苦为前提,然而当“他自己”第一次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做出认真的检查,而是充满好奇和窥视心理,期待着“他自己”的“凸起”部位能长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出来,这样他的临床报告就有内容可写,于是他不断糊弄着“他自己”,让“他自己”过一个星期再来,错过了切除或治疗的最佳时期。这种职业操守的缺失,让“他自己”的第三只手臂不断长大。医生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多次欺骗“他自己”,最后出版了他的临床研究案例,还登上了畅销书榜首,为自己谋取名利。此外,围绕在“他自己”身边的裁缝和保镖等都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大量金钱。
而那些争先购买门票目睹“他自己”的第三只手臂的人们,和那些拥挤在报告厅聆听“他自己”的故事和奇迹的人们,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追捧“他自己”的“怪物个体”,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和窥视心理。此外,受“性开放运动”的影响,《三臂人》还讲述了“他自己”因为有了“第三只手臂”,很容易就得到妇女的青睐,他洞悉了这些妇女的心理,对这些妇女也来者不拒。这些妇女以能和有“第三只手臂”的男人分享性爱而倍感荣耀,这种开放、大胆的性爱观与美国传统清教道德影响下的性爱观大相径庭。
4.0“第三只手臂”:“斯芬克斯式的寓言”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过程中,通过分析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并探究这种变化与组合的根源与结果,能为充分理解文学作品的道德内涵提供参考视角。“斯芬克斯关于人的谜语实际上是一个怎样将人和兽区别开来的问题”(聂珍钊,2014:37),而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的存在喻示着人在伦理选择过程中有着善恶并存的现象。在《三臂人》中“他自己”因为有了“第三只手臂”而被当做“怪人”,但“他自己”到底是人还是兽并非取决于身体上有着完整的人的外形,因为“人同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因为人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够有效地控制兽性因子,从而使人成为有理性的人”。(聂珍钊,2011:6)在《三臂人》中,“他自己”作为一个伦理存在的人,来到舞台上,告诉人们他的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和这种所谓的“奇迹”对他自己的伤害,这时候“他自己”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反思体现了“他自己”作为一个伦理存在的个体,在社会中的合理存在。
在剧中,“他自己”因为突然有了第三只手臂而成为一个“畸形”的“怪物”,所以遭遇了诸如丢失工作、失去妻儿等种种伦理变故;“他自己”和经纪人团队通过暴露和包装这种“畸形”获得了空前的追捧,“他自己”享受着“超级明星”般的待遇,享尽了荣华富贵。当“他自己”的手臂逐渐消失,就像当初逐渐长出来的那样,跟随在“他自己”身边的人也纷纷弃他而去,“他自己”再次成为一个普通的人,而且负债累累,心灵空虚。在此,我们不禁追问:“他自己”的第三只手臂为何会长出来?人们追捧着“他自己”的“怪物形象”和这“第三只手臂”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第三只手臂”的逐渐消失?
在正常情况下,如“他自己”所讲述的一样,每个人都不曾想到自己会突然长出“第三只手臂”,人到中年也不可能再长出其它的肢体。如果“他自己”的“第三只手臂”是从娘胎里就带来的则另当别论,那是先天性的畸形;然而,后天长出“第三只手臂”来,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剧中“他自己”透露,大多数人都经历着和他一样平凡的人生历程,那些疯狂的人群因对“他自己”突然拥有“第三只手臂”的生活而充满种种好奇与向往,甚至对“他自己”一度风光无限的“名人生活”跟风模仿。在剧作家的精心策划下,这种对比效应能带给观众持续不断的冲击,同时诸如人们渴望奇迹的出现、人们面对琐碎生活的浮躁、人们对天才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渴望,也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心理。
人们盲目相信着“他自己”的“畸形”像耶稣受难一样伟大、一样不可思议、一样具有不可企及的道德精神,为目睹一次“他自己”的容颜和聆听一次“他自己”的故事而疯狂追捧,甚至把“他自己”当作神的再世而顶礼膜拜。《三臂人》所讲述的“他自己”受邀参加医学大会、参加总统的见面会、参加教皇主持的活动、对王室成员做演讲,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自己”的“奇迹”被与耶稣受难相提并论。20世纪的美国社会,宗教的衰微已成普遍现象,人们信仰力量的缺失和信仰对象的模糊化,使得新教传统社会所传颂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逐步被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所遮蔽。
“他自己”因为长出第三只手臂而发生人体局部“变异”,与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突然发生“变异”不一样的是,“他自己”发生“变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并非一觉醒来已彻底完成了“变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社会由于工业文明(industrial civilization)、技术文明(technology civilization)和理性文明(Civilization of Rational Mind)等多方面对人的约束和压抑,造成了对人体部分肢体或者部分功能的异化,这种异化恰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诸如一些技术工长期工作造成双目失明、长期在讲台上教学的教师导致咽喉病变,或者其它诸如耳朵、鼻子、或者味觉、视觉等在某方面发生变异,导致了人体部分的残疾或畸形一样。“他自己”长出第三只手臂也是不经意间发现后背有一个“凸起”(bump),但是往往人们对这种十分不明显的征兆视而不见。正如“他自己”在剧中所追忆的那样:
“他自己” 那是周日——还在那儿,既然没痛,也没有明显的发炎,我就没管。恩,看:我们从来不会完全把事情放一边。我是说,人们总是感觉到什么事比如这个凸起,但是会习惯,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决定,要是痛了或者是长大了,或发红了,或是很突然的,感到一阵本能的癌症的恐惧,我就会马上跑去看医生——否则,就不去。让它顺其自然——产生,治愈。(P171)
由此可见,“他自己”对这种“变异”是有一定的预感的,但他并不在意。现代社会里,由于受到环境污染,或者其它习以为然的事情所干扰,使得人们的身体发生某种变化,由最初的不在意并任其发展,最终导致结果的不可收拾。《三臂人》这种不经意间所发生的“变形”恰恰隐喻了现代社会里,深受各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欲望、环境变化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一开始大家都不以为意,或能接受,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这种变化已经不知不觉地麻木了人们的思想,甚至颠覆了人们原来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某种信念。“他自己”第三只手臂慢慢长出来,就如慢慢消失一样,作为人体的部分“变异”过程,正好象征了人们的欲望的产生过程,随着欲望的膨胀,人们对金钱、权力、地位和美色的需求变得不可收拾,直至最后丧失理性,造成悲剧。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把具有享乐主义、放荡不羁和游戏人生的道德规范称作为“消费伦理”(consumption ethic),“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享乐主义所控制,正是这种享乐主义颠覆了为社会提供道德根基的新教伦理”。(Bell,1976:84)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三臂人》主人公由于身体局部“变异”导致其身体的异常,被界定为“怪物”而不被社会接纳,只是悲剧发生的开始。随着“他自己”的经纪人对其包装和策划,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人,最终“他自己”也丧失了自己的伦理意识,成为一个不会思考、没有感情的“木偶”。“人性因子借助理性意志指导、约束和控制兽性因子中的自由意志,让人弃恶从善,避免兽性因子违背伦理。但是,一旦人身上失去了人性因子,自由意志没有了引导和约束,就会造成灵肉背离。”(聂珍钊,2011:10)在利用“他自己”的“变异”谋取巨额财富的过程中,无论是经纪人、医生,还是其他利用“他自己”的人们,无一例外也遭受到了某种“变异”,他们身上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已经被金钱所腐蚀,沦落为金钱的俘虏。此外,那些花费大把金钱以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和窥探心理的人,他们身上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力量逐渐缺失,沦落为没有自己的判断、没有自己的价值的“空心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的内心和“他自己”没有区别,他们身上的兽性因子主导并驱动了人性因子,成为了欲望的奴隶。
与此同时,“他自己”身体上的“变形”也给他心灵上带来了更为沉痛的伤害。一开始,人们对“他自己”的隔离、抛弃,使得他不被社会所接纳,不被社会所承认,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当“他自己”成为“名人”之后,受到人们的追捧,此时的他,一举一动都被设计、被安排,他原来所具有的自由、独立的个体,已不复存在,唯有按照经纪人和赞助商的要求,满足人们对“他自己”的那种期待,他的存在才有意义。“他自己”彻头彻尾成为了一个“空心人”,没有灵魂,也没有思想。“他自己”唯一的存在价值就是作为人们的“玩偶”。更具讽刺意义的是,《三臂人》的“他自己”在这种身体的“变形”过程中,没有反抗的能力,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反抗。这也告诉我们,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与伤害,往往是潜在的,是不可预知的;而且这种伤害发生之后,很快又被新的伤害所覆盖和遮蔽。当一个人被异化为“怪物”的时候,他的伦理意识也逐渐发生改变。
5.0结语
综上所述,《三臂人》围绕着主人公“自己”的演讲而展开,追忆着自己曾经拥有“第三只手臂”的风光生活和“第三只手臂”消失之后的落魄与凄凉。“第三只手臂”存在的时候,他的经纪人和那些围绕着他的手臂而大发横财的人们,充分利用着他的“畸形”,然而当他的第三只手臂消失之后,社会再次抛弃了他,人们也逐渐忘记了他。有趣的是,“他自己”伦理意识的变化伴随着“第三只手臂”的出现与消失而变化,在他拥有“第三只手臂”的时候,他在别人的操控下,逐渐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他的这种思考和反思能力随着手臂的逐步消失又逐渐找回。对于人们为何热衷于追捧“他自己”这样的一个“怪物”,主要原因还在于人们伦理意识的淡薄,其身上的兽性因子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影响下、在传统的道德精神和道德价值衰微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普遍缺乏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相反对金钱、名利和享乐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三臂人》告诉我们,当人们的猎奇心理发挥作用的时候,会把具有某种畸形的人当成具有影响的人物和时代的杰作,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掉人最基本的道德观念,而道德评价的失衡也象征着这个时代的“畸形”。
说到底,《三臂人》是一则有关“斯芬克斯的寓言”:“他自己”作为一个有着伦理存在的个体,当他面对突然的伦理变故与不幸遭遇时,由于伦理意识的淡薄,轻信他人的“大爆料”建议,导致其兽性因子未得到有效地控制和疏导,最终为了所谓的名誉、地位和金钱丧失了作为伦理存在的理性,沦落为一个行尸走肉的“玩偶”;而围绕着“他自己”“第三只手臂”的“奇观”,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们皆因为了满足私欲而集体陷入“道德失控”的泥潭不能自拔。《三臂人》通过书写这种极端的道德失衡,旨在呼吁人们对于理想道德法则的向往和伦理秩序的维护。
注释:
① 选自Edward Albee,TheCollectedPlaysofEdwardAlbee(Volume 3,1979-2003).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2005。有关《三臂人》的原文皆出自此书,以下随文只注明页码。
参考文献
[1] Albee, E.TheCollectedPlaysofEdwardAlbee(Volume3,1979-2003)[M].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2005.
[2] Bell, D.TheCulturalContradictionsofCapitalism[M]. New York: Basic Books,Inc, 1976.
[3] Bottoms, S.TheCambridgeCompaniontoEdwardAlbee[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Hirsch, F.Who’sAfraidofEdwardAlbee?[M]. Berkeley: Creative Arts Book Company, 1978.
[5]Kauffmann, S.LolitaUndone[J]. In S. Bottoms (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EdwardAlbee[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127.
[6] Paolucci, A.FromTensiontoTonic:ThePlaysofEdwardAlbee[M].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2.
[7] Roudané, M. C.UnderstandingEdwardAlbee[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7.
[8]Way, B. Albee and Absurd:TheAmericanDreamandTheZooStory[A]. In C. W. E. Bigsby (ed.).EdwardAlbee:ACollectionofCriticalEssays[C].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5.26.
[9] 伊哈布·哈桑. 当代美国文学:1945-1972[M]. 陆凡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10] 刘建军.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2006,(2):8-17.
[12]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 外国文学研究,2011,(6):1-13.
[13]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4] 孙柏. 丑角的复活:对西方戏剧文化的价值重估[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