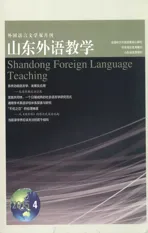伦理责任与“生活的乐趣”:海伦·阿尔文的伦理困境①
2015-04-08杨革新
杨革新
(华中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易卜生的《群鬼》在不足24小时的剧情中展现了一个家庭悲剧。该剧的核心伦理事件即海伦苦心修建的阿尔文上尉孤儿院化为灰烬,从法国回来的儿子欧士华变为白痴,而连接所有事件的却是早已死去10年的父亲阿尔文。父亲身体的缺场与其象征物的在场交替出现是整个剧情的伦理线,而孤儿院的大火既是剧情的高潮,也是对所有伦理结的解构。海伦的伦理困境既引领着人们对伦理责任与“生活的乐趣”的思考,又揭露了鬼一样的社会环境与制度对个人与家庭的毒害。
[关键词] 《群鬼》; 伦理线;伦理结;伦理责任;生活的乐趣;伦理困境 ① “生活的乐趣”是剧中欧士华与母亲海伦谈到自己巴黎生活时说出的一个,是《群鬼》潘家洵译本对“enjoy of life”的译文。本文以此作为标题的一部分,代表的是欧士华与其父阿尔文所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
Duty or “Enjoy of Life”: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of Helen Alvin
YANG Ge-x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
Key words: Ghosts; ethical line; ethical knot; duty; “enjoy of life”;ethical predicament
在易卜生的所有剧本中《群鬼》引起的骚动最大。它的演出对体面的中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受到了他们的谴责和禁止。当时整个北欧的剧院如同躲避瘟疫般地避开这个剧本,哥本哈根王室剧院还张贴出审检告示,认为“该剧以令人厌恶的变态病理现象作为剧情的首要主题, 暗中破坏了构成我们社会秩序的基本道德”。(海默尔,2007:257)甚至到了《群鬼》问世10年之后的1891年, 该剧在伦敦演出时, 有批评家竟然把它贬低为一部糟糕透顶的作品,一个令人反感卑劣的剧本。不可否认,《群鬼》的确是一部很有争议的作品,学界对该剧的解读也层出不穷,其中主要有四种观点很值得一提:其一,易卜生创作《群鬼》的目的是为了回应人们对《玩偶之家》中娜拉离家出走所引起的反对之声。海伦守着一个比海尔茂更糟的丈夫,不但没有出走反而以体面的方式掩盖着他们名存实亡的婚姻;其二,海伦和欧士华是生物世界的遗传法则和体面社会的惯例条令的牺牲品;其三,对于易卜生而言,遗传疾病是所有决定力量的象征,因此他力图以人类最强有力的母爱与之对抗;其四,一部分批评家认为该剧除了起到一种历史标记作用之外,其意义并不大。他们认为该剧虽然在当时看来可能具有革命性,但任何以痛苦和疾病作为戏剧冲突的剧本在今天看来都不具说服力。
以上这些观点早有批评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应。就笔者看来,这些解读多少带点误读或者没切中要害,因为他们虽对剧本做出了评价,但并没有挖掘出该剧深层次的冲突。目前已有的解读大多忽略了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人物 —— 已死多年的阿尔文上尉。这个缺场的人物其实才是该剧所有在场人物的核心。该剧所有伦理事件都因他而起,并因他导致悲剧收场。缺场的阿尔文以各种在场的形式左右着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他身体的缺场与其象征物的在场交替出现其实就是该剧隐藏的伦理线,本文试图以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术语中的伦理线为出发点,结合伦理结的解构来分析人物面临的伦理困境和造成人物悲剧的原因。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曾用“父亲的姓名”这个词语来表明父亲的权威与该词的力量,“父亲的姓名(Name-of-the-Father)既是权威的来源,又是权威的能指(Signifier),具有限制、规定的双重功能。”② 但在易卜生的家庭剧中人们却发现一种对丈夫和父亲角色的强烈质疑或抵制。这种质疑不仅针对男性人物个人,如《社会支柱》中的博尼克、《玩偶之家》中的海尔茂和《群鬼》中的阿尔文上校,它还针对这些人物所代表的社会和父权制。在《群鬼》中,真正的父亲阿尔文早已死去10年,但是他所代表的父亲权威却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左右着剧中人物的命运。父亲的缺场是预设的,是为了让剧中所有人物聚在一起;而在场是重构的,是为了推动剧情的发展和悲剧的产生。显性的缺场与隐性的在场交替出现构成了该剧的伦理线而贯穿始终。易卜生一方面以假父亲安格斯川的虚伪和谎言与真父亲阿尔文上尉的酗酒和好色表明父亲的形象和权威正一步一步被损毁,另一方面又以戏剧的方式展现已逝的父亲如何以在场的形式如孤儿院、烟斗和海伦力图战胜的父权制传统继续影响着剧中人物。这种缺场与在场的悖论既推动着剧情一步一步地发展又引领着人们对父亲身份的思考和悲剧成因的分析。
阿尔文上尉作为当时社会秩序的代表者,理应是个模范市民和造福社会的大善人,但是撕开其公众的面纱,展现出来的却是一个醉鬼和染上性病的好色之徒。他是一个病态的父亲,不仅身体上垮掉了,精神上也堕落了。他以父亲之名维护着父权社会的法律,但同时自己也是个法律的践踏者。他寻花问柳,逃避责任,勾搭自己的女仆并让她怀孕,从而让自己的家庭蒙羞。正因如此,阿尔文上尉失去了权威,成为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当他把丑事闹到家里来之后,海伦剥夺了他的权力,她不仅把儿子送走,还接管所有房产,这样他既失去了父亲的身份,也失去了家长的地位。可以说阿尔文在有生之年就已开始缺场于社会。
父亲的缺场不仅在于剧中没有出现阿尔文上尉的身影,而且还因为理想中的父亲或象征意义上的父亲从社会中消失。戏剧开场时阿尔文已死了10年,因为他一直被人们所纪念,因此成了社区穷人和失父者象征意义上的父亲。欧士华从国外回来是为了参加为纪念其父而建的孤儿院的落成典礼。正如比约恩·海默尔(Bjorn Hemmer)所言:“为纪念阿尔文上尉所建的孤儿院显然与阿尔文太太给儿子欧士华信中所虚构的父亲形象紧密相连。”(Hemmer,1994:84)海伦通过信件呈现给欧士华的父亲是一个重构的、理想的父亲,因此欧士华要纪念的父亲是一个虚幻的形象,并不是真正的阿尔文。当海伦准备告知有关其父的实情时,曼德牧师要她继续维护欧士华心中虚构父亲的形象。于是父亲就变成了一个概念,一个虚构的隐喻。与之相比,真正的阿尔文上尉却成了一个苍白的映象。然而海伦信中受尊敬的父亲形象与欧士华在巴黎亲眼所见的各色父亲却大相径庭。这些挪威的好父亲代表着阿尔文上尉的形象,却在远离自己受尊敬的地方去光顾巴黎的花花世界,沉醉于堕落中。这些离家的父亲显然在家道貌岸然,在外却放荡形骸。像阿尔文上尉一样,他们是当时法律的宣扬者,同时也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者。这种理想父亲与现实父亲之间的明显背离说明父亲这个词已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符号,根本无法表现任何所指,这样象征意义上的理想父亲也变成了缺场。
就欧士华而言,缺场的父亲隐藏在各种错觉层面;而从吕嘉娜的角度来看,站在她面前的父亲都是假的,而真正的父亲却隐而不见。母亲乔安娜收了钱而不得不隐瞒其生父的秘密,因而虚构了一个有钱的英国人做她的父亲,这同样也是一个幻觉。这个英国人完全缺场,因为他根本就不存在。当乔安娜告诉了安德斯川她的窘境后,他为了钱娶了她,从而获得了父亲的身份。安德斯川向曼德牧师谎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结婚后他父亲身份的合法性得到了教会的认可,但这种认可却基于一个虚构的故事。尽管安德斯川拥有父亲的权利,但他既不是吕嘉娜的父亲,也没有像一个好父亲一样对她。同时吕嘉娜也并不认可这种关系,反而追问牧师“要是真是一个值得敬重,够得上做我爸爸的人”她也愿意与之在一起。(易卜生,1995:223)③ 这暗示她并不介意“像一个女儿一样”与曼德住在一起。这既可以理解为她把曼德牧师看做了代理父亲,也可以理解为她可以以女儿的身份做他的情人。然而曼德牧师拒绝了这一身份,因而变成了吕嘉娜又一缺场的父亲。吕嘉娜的众多父亲角色再次把父亲这个概念降为一个空洞的符号,它时隐时现于众多靠不住和邪恶的父亲之中。缺场的父亲阿尔文上尉引出了一系列的假父亲形象,这些形象又进一步远离了真正的父亲,他们是虚构的、理想的、象征的,并且总是缺场。
阿尔文的缺场并不影响其鬼魂的在场,他是死去的鬼,而剧中的人物都是其在场的代言人,是活着的鬼。当欧士华叼着烟斗入场时,曼德牧师发现他简直就是阿尔文的再生,长得与之一模一样。欧士华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外貌也继承了他的疾病,还再现了他的罪孽,竭力去引诱吕嘉娜。阿尔文的儿子去引诱阿尔文的女儿暗示了兄妹乱伦和父辈的乱伦。曼德牧师执行了父权社会的法律,禁止乱伦的发生。他和海伦重现了对阿尔文与乔安娜的处理方式:把吕嘉娜送走或嫁人。这样缺场的父亲又以一种在场的形式左右着剧情。缺场的父亲同时也通过两个建筑物的形式得以再现,即阿尔文上尉孤儿院和阿尔文水手公寓。以阿尔文命名的孤儿院不仅刻上了他的名字,还象征着被父亲们丢下的孤儿。为了体现孤儿院的神圣性,尘世间的父亲并没有给它买保险,不幸的是,孤儿院被火烧了,这恰好证明神性父亲的缺场。随着孤儿院的毁掉,这个假定的父亲,虚构的大善人,以及父亲所代表的神圣的秩序也随之倒塌了。然而在孤儿院的灰烬中,安德斯川讹得了一大笔钱,并以阿尔文的名字开了一家水手公寓,其实质却是一家妓院。这样缺场父亲的高贵形象又转化为堕落之物,这种转化正好说明了父亲形象的进一步损毁与人物悲剧的加深。
缺场父亲在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父权式的话语模式。通过对死去丈夫的纪念,海伦试图摆脱父亲的姓名和已逝丈夫的权威对自己的影响。首先,她以一个忠爱丈夫的形象用丈夫阿尔文的名字和遗产进行捐赠;其次,她尽量不占有和获取一分一厘的遗产。然而海伦最后意识到尽管她已经以阿尔文上尉的名字建了一个孤儿院,她仍然无法逃脱他的控制,因为他已完全融入到她体内。阿尔文上尉在海伦血液和身体里的存在体现了更为深层的遗传特征,这远超过了欧士华所得性病的遗传性。这种围绕在海伦身边或存在于她体内的疾病和群鬼是一种话语,是一种由语言传承下来的父权统治的现实。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个母亲适应这个父亲的方式,还要关注她接受他表现其权威,换言之,表现其法律中父亲身份的话语和语言的方式”。(Lacan,1977:218)无论如何努力海伦意识到她始终无法摆脱群鬼或其已逝丈夫的影响。丈夫在世时,她极力维护其名声,死后也一直保护他的名声。海伦发现在她孤身一人的这些年月里,除了以一个男性的名义即一个理想父亲的形象存在之外,她根本无法获得自己的身份。她以丈夫的名字为无父无母的儿童所建的家其实可以看做是以缺场父亲的名字命名的一座教堂,它既为孤儿提供庇护所,也是自己得以解脱和赦免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海伦也是缺场父亲在场的代言人。
在戏剧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听到阿尔文上尉自己也是代表父权制话语的受害者。阿尔文对生活乐趣的追求导致他饮酒作乐,这破坏了他的家庭,也把他自己置于死地。由阿尔文所扮演的高贵父权制的上尉形象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上尉;同样,与海伦一起生活过的阿尔文的堕落形象也不是真正的阿尔文。因此真正的父亲和真正的阿尔文上尉其实陷入无法名状的过去与将来的迷雾中。人们可能认为,这个家庭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家长,有的只是一个衰败的传统,一系列鬼一样的父亲形象和代表鬼一样旧传统的话语模式。丈夫与妻子都陷入了自然欲望与他们生活其中的文化话语之间的矛盾中。因此通过父亲的缺场与在场这条伦理线串联起的剧中所有人物都是鬼,整部戏剧就是在死鬼和活鬼的冲突中达到高潮,这也是该剧用“群鬼”做标题的原因。可见“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分析作品,寻找和解构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线……是十分重要的”。(聂珍钊,2010:20)
《群鬼》在不足24小时的剧情中通过父亲的缺场与在场串联起所有伦理事件可谓结构巧妙。但按照当时流行的评价方法,该剧却因缺乏足够的剧情来支撑其观点而被认为瑕疵有余。这种观点最初源于萧伯纳,他认为该剧的主题和观点都不愧于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其技巧却明显不足。例如,如果仔细审视,我们会发现该剧缺乏真正的高潮。孤儿院在开张当日化为灰烬不是由戏剧对话自身发展而来,因而不利于人物角色完整性的表达。剧本结尾欧士华因从父亲遗传得来的梅毒病发而成白痴虽很具悲剧性,但这种疾病并不是剧中人物的行为所致,因而缺乏社会悲剧的意义。(Shaw,1979:152)这些评价最大的误区是忽略了隐藏在舞台背后缺场的父亲如何以在场的形式左右剧情的发展这条伦理线,如果我们结合这条伦理线来“对已经形成的伦理结进行解构”(聂珍钊,2010:20),则会发现该剧不仅高潮突出,而且悲剧氛围浓厚。
《群鬼》的主要伦理事件即以阿尔文上尉命名的孤儿院付之一炬,儿子欧士华变成白痴。剧中最大的节点并不在于遗传的影响,而在于父亲形象的重构与毁灭。父亲的身份与地位迫使海伦“逼着他做人,硬给他撑面子”。(P243) 阿尔文死后,她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并以他的名义兴办慈善事业,创办孤儿院,替他沽名钓誉。把儿子送往巴黎后,为了体面,她一直写信告诉儿子,说他父亲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为的是不让人知道我孩子的父亲是怎么一等人”。(P241) 后来,孤儿院修好了,“纪念碑”建成了,似乎并未受到阿尔文影响的欧士华也学成归来。一切看似美满,海伦似乎可以开始新生活了,高大完美的父亲形象似乎也可以美名永传。然而就在这时,大火熊熊燃起,烧掉了意欲永久掩盖一个丑陋形象的孤儿院。孤儿院的大火起到了解结作用,不仅解开了海伦一直隐瞒的秘密,还把剧中人物推向悲剧结尾。
大火是从哪儿开始的呢?火的象征最初出现在哪儿呢?火的引子在戏剧之初就已埋下:第一幕,欧士华一出场,嘴里就叼着个大烟斗,而父亲的这个烟斗极有可能导致了他的疾病:有天晚上,他醉醺醺地回家,兴高采烈地把欧士华放在腿上,开玩笑地把自己的烟斗给欧士华抽。欧士华当时只有四五岁,当场就感到恶心呕吐。也许梅毒就在这时从上尉的口腔溃疡中通过烟斗传给欧士华。这也是为什么欧士华一出场,嘴里就含着个烟斗的原因。从这一刻起,火的象征就一直燃到剧终,并演变成明亮的阳光。在戏剧的高潮,大火成了连接欧士华和海伦故事的节点。大火之前,剧情主要是对过去事件的回顾,展现的是剧中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建孤儿院的原因;大火之后,剧情主要是对当前问题的解决,展现的是海伦面对困境如何选择。大火解构了海伦虚构的理想父亲形象,把剧情从过去拉到现在,把父亲的高大形象(孤儿院)贬为堕落之物(水手公寓,即妓院),把才华横溢的儿子烧成白痴。孤儿院大火的意义并不在于大火本身,而是在于孤儿院本身。弗朗西斯·弗格森(Francis Fergusson)曾认为“《群鬼》的内在剧情是去控制阿尔文的遗产,即海伦为纪念丈夫而建的孤儿院,而孤儿院对海伦而言又是她与过去划清界限的标志”。(Fergusson,1953:161)如果孤儿院真象征着阿尔文的遗产,这些过去的鬼,那么海伦和欧士华看到熊熊大火时应该高兴不已,因为像石头一样压在他们心中的过去被搬开了,但结果大火却成了阿尔文家庭的不祥之兆,并演变成一场家庭悲剧。
为了进一步理解大火的解构功能,我们还“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聂珍钊,2010:19)在第二幕中,海伦了解到了欧士华的疾病。欧士华告诉她这病一定是在巴黎染上的,不过他还是喜欢巴黎的生活,相反对挪威的生活大加指责。他认为在挪威人们在生活中首先考虑的是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幸福,但生活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能从中得到身体上的快乐。但对海伦而言,她的整个生活就是责任、义务和牺牲,因此她大声惊呼:“生活的乐趣?那里面有救星吗?”(P270)欧士华所说的“生活的乐趣”对海伦不亚于一个警醒,她意识到自己没有给自己的婚姻生活带来任何快乐,她的清规戒律使得年轻的丈夫不得不到酒馆妓院寻欢作乐。她渐渐明白了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现在我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是我头一次明白,现在我可以说话(P272)。当海伦认识到自己信仰上的错误,并意识到感官上的生活也能给人拯救时,孤儿院的大火突然燃起来了—— 这是阿尔文的怒火,因海伦清教式的生活模式而受到压抑的欲火。他代表了欧士华所说的感官生活,它的突然爆发过度刺激了欧士华的大脑,从而导致了他的瘫痪。大火不仅是对海伦的谴责,它还解构了她一直信奉的牺牲观与义务观,把她推入了伦理困境之中。
在第三幕,欧士华说自己也在燃烧,他的头着火了,他的病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他的崩溃表面上是因为大火引起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紧张所致,实际原因却是其父的放荡生活。寻求感官上的享乐与刺激已经毁掉了阿尔文上尉,现在又导致了欧士华的脑瘫。他一直追求阳光下巴黎“生活的乐趣”,说自己没有太阳简直无法活下去。甚至连吕嘉纳,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一个充满生活乐趣的年轻姑娘,也是他想娶的对象。但当她知道他的病情后却宁愿去安德斯川的水手公寓做妓女,而这个水手公寓正是孤儿院的大火之后在曼德牧师默许的情况下修建的。这样大火不仅解构了孤儿院的秘密和海伦的生活信条,还解构了“生活的乐趣”这一生活方式的实质。他们追求的“生活的乐趣”最后堕落成了丑陋之物:阿尔文的孤儿院变成了妓院,他的女儿变成了妓女。因此,阿尔文的遗产只不过是一个堕落之物和疾病。就在欧士华大喊太阳之时,他的疾病已经开始折磨他的大脑了。他想去死,想着他的吗啡药片,但是他已经开始神经错乱了,这是全身瘫痪的先兆。他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并不一样,他嘴里喊着药片,但在他心里这些药片却变成象征着快乐生活的太阳。
孤儿院的大火烧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它还烧掉了群鬼脸上的面纱,它以解构的方式让所有角色原形毕露:海伦苦心经营的好父亲形象不仅化为灰烬,还演变成更为堕落的妓院;当初为了自己神圣的职业坚持相信上帝而反对阿尔文太太买火险的神性父亲曼德牧师,也露出了其虚伪的本质,竟然和卑鄙的假父亲安格斯川合伙做起了生意;一直被阿尔文太太视为亲生女儿的吕嘉纳也不顾欧士华的请求而选择离去,并决定用自己的青春去享受生活。孤儿院的那场大火,像一个炙热的太阳,照亮了漆黑的夜空,解构了整个伦理事件。大火产生的烟灰,洒落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最终,伪善的曼德牧师被安格斯川控制,继续伪善着;道德败坏的安德斯川即将经营起阿尔文水手公寓(妓院),吕嘉纳出去寻找“生活的乐趣”,欧士华失掉了所有的理想,海伦将面临痛苦的选择。
孤儿院的大火烧掉了海伦摆脱过去的希望,同时也让她陷入伦理困境之中:是追求“生活的乐趣”还是践行伦理责任?“生活的乐趣”是剧中阿尔文和欧士华一直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伦理责任却是海伦和曼德牧师一直坚守的人生信条。孤儿院的大火之后,海伦就在两种人生哲学之间饱受煎熬:她过去的牺牲观与现在的享受观。她现在关注的并不是如何与社会、教会和传统观念进行抗争,而是考虑如何在这两种人生哲学中做出选择。显然传统观念作为一种敌对势力一直压抑着整个情节,直到曼德牧师和安德斯川离开后,雾蒙蒙的天气变得明朗了,我们才明白整个争论的焦点其实一直围绕着义务与爱好,道德与享乐而展开。在戏剧的结尾,欧士华呼喊着结束自己痛苦的药丸,这对海伦是个伦理两难:如果海伦接受了欧士华的享乐主义哲学,她就应该给他药丸让他快乐地死去。如果海伦仍然坚持自己过去的牺牲观和义务观,她就应该全力去照顾他,即使他只是一具活着的僵尸。
其实海伦作为一个悲剧人物一直就生活在伦理困境之中。当她还是个年轻少女时,她对宗教非常虔诚,并且爱上了曼德牧师。然而她却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被迫嫁给了阿尔文上尉。婚后她对丈夫的越轨行为非常恶心,决定抛弃家庭责任和义务去投奔心仪的曼德牧师。因为害怕公众的舆论,牧师拒绝了她并以义务责任为由把她送回到丈夫身边。在随后的岁月里海伦渐渐明白当教会和社会都迫使她去与一个自己讨厌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时,一定是自己某些地方出现了问题。她开始改变自己的观念,承担起了生活之责。当发现丈夫把鬼闹到家里来了后,她接管了所有的房产,挑起了家庭重担,并忍住母子离别的痛苦把欧士华送到了国外,以免他受阿尔文的影响。多年以后,儿子从国外回家,她感到苦尽甘来,可以和过去再见了。但在与欧士华交谈的过程中,她却发现他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与她所想的一样。年轻时所受的教育告诉她没有牺牲就不会得到有价值的东西,而欧士华却信奉的是感官生活支撑着精神,生活的幸福在于身体的幸福。当从欧士华那里了解到人类的希望在于对生活全盘接受而不是带有宗教式的节制之后,她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多年以来她一直认为自己回到阿尔文身边是个天大的错误,但现在看来把充满激情的丈夫看作是一个恶心的动物是个更大的错误:是她把自己的丈夫从家里赶到了妓院酒馆。海伦现在开始变得开放了,她正试图去理解欧士华。当看到欧士华与吕嘉纳调情时,她甚至认为只要欧士华能在吕嘉纳身上找到幸福,她就准备容忍这种乱伦的行为。然而当曼德牧师问道:“你作为一个母亲怎么能允许你的……” 海伦却这样回答道:“我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P252)
海伦希望找到一种方式能同时满足自己相互矛盾的两种欲望:既想遵循社会强加在她头上的各种法律、传统和习俗,又想从各种规范中解脱出来。从剧情的开始,海伦就与《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不同,她不再反对传统习俗。她虽然认为传统习俗扼杀了个人的幸福,但她也承认传统习俗的重要一面:她渴望传统的母子关系。正是这种传统的母子关系才使得她不敢去追求自由。如果她理性地审视自己的婚姻,她也必须理性地去处理自己和欧士华的母子关系。在整个戏剧中她一直寻找着某个能解决这种矛盾的机会,但剧中并没给她提供这样的机会。每一个场景都是过去危机的重复。她告诉曼德牧师自己不幸福,但得到的回答仍是“义务”,只是以前是对丈夫阿尔文的义务,现在变成了对儿子欧士华的义务。当她发现欧士华与吕嘉纳在胡闹后,她也不得不像对待阿尔文上尉一样饶恕他们,以免被公众知道。后来尽管她认为并没有合适的理由去反对他们的关系,但她还是不允许他们违背传统禁忌去近亲结婚。他选择了维护传统的体面家庭,这种决定与当初送走吕嘉纳的母亲具有同样的目的。海伦只不过是重复了她过去的决定,因为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改变。年轻时她认为传统习俗与个人幸福绝对是相互矛盾的。现在年老了她更坚信这一点。她甚至有一种更强烈的感觉:她的任何决定要么是对社会的否定,要么是对自己的否定。
海伦的这种伦理困境其实是人的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相互较量的结果。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剧中海伦对伦理责任的遵守和维护则是其理性意志的体现,是人性因子发挥作用的结果。而阿尔文和欧士华一再追求的“生活的乐趣”其实是他们身上自由意志失控的表现,是兽性因子肆掠的结果。④“自由意志主要产生于人的动物性本能,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人的不同欲望,如性欲、食欲等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和心理动态。”(聂珍钊,2011:8)在自由意志的驱使下,强大的肉欲让人的理性意志无能为力。因此剧中阿尔文一心追求“生活的乐趣”,不顾家庭责任,任由自由意志驱使,在外寻花问柳,在家私通女仆,最后染上梅毒丢掉性命。欧士华追求“生活的乐趣”,相信生活的幸福即身体的幸福,因此在巴黎他就沾染上荒淫无度的毛病。就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原来我不应该跟朋友过那种快乐自在的日子。我的体力吃不消,因此我才害了病,这怨我自己不好!”(P265) 一回到家中他就看上了女佣人吕嘉纳,并对母亲说:“你看她多美!身段多漂亮,体格多健康。……她站在我面前,就好像张开了胳臂等着我一样。” ( P270)不断膨胀的兽性因子让欧士华完全忘记了吕嘉纳可能因为感染他的梅毒而终生痛苦。
海伦也曾任由自由意志驱使追求过“生活的乐趣”。年轻时她离家出走抛家弃子去投奔曼德牧师,她甚至准备接受欧士华的观点,容忍他的乱伦。但理性意志最终战胜了自由意志,她回到家中承担起了责任和义务,并阻止了欧士华的乱伦。海伦的困境不仅在于她要在这两种生活伦理中不断作出选择,更在于她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决定权,她的所有选择都被她所继承的传统所左右。例如她遵照母亲和姑姑的意愿与阿尔文上尉结婚,她离家后返回丈夫的身边,她对欧士华与吕嘉纳调情时的反应,她对曼德伪善的接受,她向欧士华隐瞒其父亲的真实面貌,她因欧士华对父亲生活的冷漠而产生的惊恐反应,还有戏剧结尾的问号,所有这些场景都证明海伦的自由理想和理性的诚实在实际生活中根本毫无用处。戏剧的结尾,海伦犹豫不决地摸寻着药丸,接着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即太阳神,也是神话中一个父亲的名字,在剧中即欧士华所说的“生活的乐趣”,这也是私生女吕嘉纳目前正准备去追寻的东西。但她的将来如何?易卜生虽没给出答案,但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其结局。“生活的乐趣”让欧士华的身体吃不消,让酗酒纵欲的阿尔文上尉丢掉了性命。吕嘉纳作为他的后代,“该家族的基因会一直延续到下一代,也许她会像她父亲一样因遗传病使其婚姻变成坟墓”(Templeton,1986:64),也许有可能幸免,只不过她具有讽刺性地回到了假父亲安德斯川的水手公寓显然只会让她堕落甚至丢掉性命。是坚持伦理责任还是选择“生活的乐趣”?戏剧最后的悲剧结尾和吕嘉纳的将来的命运其实为我们给出了答案。
太阳最后升起来了,这是剧本一开始就预设好的。随着过去的事件一件件曝光,随着剧情的冲突越来越尖锐,光亮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剧情在阴暗的傍晚和雨中拉开帷幕,在熊熊火光中达到高潮,又以太阳出来为整个剧情画上句号。阴暗的夜晚隐藏了缺场父亲的丑陋形象,在场的人物各个道貌岸然;熊熊大火烧掉了各自的面纱,呈现出高大的父权制与其代表者猥琐的本质,并引出了对伦理责任与“生活的乐趣”的思考;升起的太阳是否真能照亮每个人的前路?如果我们顺着缺场与在场这条伦理线去深挖父亲的隐喻与大火的象征,则不难发现升起的太阳只不过曝光了剧中人物悲剧的原因。阳光下的生活既有“生活的乐趣”也有伦理责任,它们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阿尔文和欧士华追求“生活的乐趣”丢掉了性命,但“生活的乐趣”的确让欧士华的巴黎生活充满激情。海伦遵循伦理责任维护了传统观念却仍然导致悲惨结局。因此该剧的悲剧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个人应如何用理性意志去控制自由意志的泛滥,还在于揭示了人们遵循的伦理制度是否合理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易卜生在强调了伦理责任的同时,让所有人物以悲剧收场也许是要说明只要鬼一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没有改变,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将继续存在。
注释:
DOI:10.16482/j.sdwy37-1026.2015-04-011
伦理责任与“生活的乐趣”:海伦·阿尔文的伦理困境①
杨革新
(华中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0)
[摘要]易卜生的《群鬼》在不足24小时的剧情中展现了一个家庭悲剧。该剧的核心伦理事件即海伦苦心修建的阿尔文上尉孤儿院化为灰烬,从法国回来的儿子欧士华变为白痴,而连接所有事件的却是早已死去10年的父亲阿尔文。父亲身体的缺场与其象征物的在场交替出现是整个剧情的伦理线,而孤儿院的大火既是剧情的高潮,也是对所有伦理结的解构。海伦的伦理困境既引领着人们对伦理责任与“生活的乐趣”的思考,又揭露了鬼一样的社会环境与制度对个人与家庭的毒害。
[关键词]《群鬼》; 伦理线;伦理结;伦理责任;生活的乐趣;伦理困境 ① “生活的乐趣”是剧中欧士华与母亲海伦谈到自己巴黎生活时说出的一个,是《群鬼》潘家洵译本对“enjoy of life”的译文。本文以此作为标题的一部分,代表的是欧士华与其父阿尔文所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
Duty or “Enjoy of Life”: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of Helen Alvin
YANG Ge-x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
Key words:Ghosts; ethical line; ethical knot; duty; “enjoy of life”;ethical predicament
1.0引言
在易卜生的所有剧本中《群鬼》引起的骚动最大。它的演出对体面的中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受到了他们的谴责和禁止。当时整个北欧的剧院如同躲避瘟疫般地避开这个剧本,哥本哈根王室剧院还张贴出审检告示,认为“该剧以令人厌恶的变态病理现象作为剧情的首要主题, 暗中破坏了构成我们社会秩序的基本道德”。(海默尔,2007:257)甚至到了《群鬼》问世10年之后的1891年, 该剧在伦敦演出时, 有批评家竟然把它贬低为一部糟糕透顶的作品,一个令人反感卑劣的剧本。不可否认,《群鬼》的确是一部很有争议的作品,学界对该剧的解读也层出不穷,其中主要有四种观点很值得一提:其一,易卜生创作《群鬼》的目的是为了回应人们对《玩偶之家》中娜拉离家出走所引起的反对之声。海伦守着一个比海尔茂更糟的丈夫,不但没有出走反而以体面的方式掩盖着他们名存实亡的婚姻;其二,海伦和欧士华是生物世界的遗传法则和体面社会的惯例条令的牺牲品;其三,对于易卜生而言,遗传疾病是所有决定力量的象征,因此他力图以人类最强有力的母爱与之对抗;其四,一部分批评家认为该剧除了起到一种历史标记作用之外,其意义并不大。他们认为该剧虽然在当时看来可能具有革命性,但任何以痛苦和疾病作为戏剧冲突的剧本在今天看来都不具说服力。
以上这些观点早有批评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应。就笔者看来,这些解读多少带点误读或者没切中要害,因为他们虽对剧本做出了评价,但并没有挖掘出该剧深层次的冲突。目前已有的解读大多忽略了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人物 —— 已死多年的阿尔文上尉。这个缺场的人物其实才是该剧所有在场人物的核心。该剧所有伦理事件都因他而起,并因他导致悲剧收场。缺场的阿尔文以各种在场的形式左右着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他身体的缺场与其象征物的在场交替出现其实就是该剧隐藏的伦理线,本文试图以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术语中的伦理线为出发点,结合伦理结的解构来分析人物面临的伦理困境和造成人物悲剧的原因。
2.0“父亲”的缺场与在场:《群鬼》的伦理线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曾用“父亲的姓名”这个词语来表明父亲的权威与该词的力量,“父亲的姓名(Name-of-the-Father)既是权威的来源,又是权威的能指(Signifier),具有限制、规定的双重功能。”②但在易卜生的家庭剧中人们却发现一种对丈夫和父亲角色的强烈质疑或抵制。这种质疑不仅针对男性人物个人,如《社会支柱》中的博尼克、《玩偶之家》中的海尔茂和《群鬼》中的阿尔文上校,它还针对这些人物所代表的社会和父权制。在《群鬼》中,真正的父亲阿尔文早已死去10年,但是他所代表的父亲权威却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左右着剧中人物的命运。父亲的缺场是预设的,是为了让剧中所有人物聚在一起;而在场是重构的,是为了推动剧情的发展和悲剧的产生。显性的缺场与隐性的在场交替出现构成了该剧的伦理线而贯穿始终。易卜生一方面以假父亲安格斯川的虚伪和谎言与真父亲阿尔文上尉的酗酒和好色表明父亲的形象和权威正一步一步被损毁,另一方面又以戏剧的方式展现已逝的父亲如何以在场的形式如孤儿院、烟斗和海伦力图战胜的父权制传统继续影响着剧中人物。这种缺场与在场的悖论既推动着剧情一步一步地发展又引领着人们对父亲身份的思考和悲剧成因的分析。
阿尔文上尉作为当时社会秩序的代表者,理应是个模范市民和造福社会的大善人,但是撕开其公众的面纱,展现出来的却是一个醉鬼和染上性病的好色之徒。他是一个病态的父亲,不仅身体上垮掉了,精神上也堕落了。他以父亲之名维护着父权社会的法律,但同时自己也是个法律的践踏者。他寻花问柳,逃避责任,勾搭自己的女仆并让她怀孕,从而让自己的家庭蒙羞。正因如此,阿尔文上尉失去了权威,成为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当他把丑事闹到家里来之后,海伦剥夺了他的权力,她不仅把儿子送走,还接管所有房产,这样他既失去了父亲的身份,也失去了家长的地位。可以说阿尔文在有生之年就已开始缺场于社会。
父亲的缺场不仅在于剧中没有出现阿尔文上尉的身影,而且还因为理想中的父亲或象征意义上的父亲从社会中消失。戏剧开场时阿尔文已死了10年,因为他一直被人们所纪念,因此成了社区穷人和失父者象征意义上的父亲。欧士华从国外回来是为了参加为纪念其父而建的孤儿院的落成典礼。正如比约恩·海默尔(Bjorn Hemmer)所言:“为纪念阿尔文上尉所建的孤儿院显然与阿尔文太太给儿子欧士华信中所虚构的父亲形象紧密相连。”(Hemmer,1994:84)海伦通过信件呈现给欧士华的父亲是一个重构的、理想的父亲,因此欧士华要纪念的父亲是一个虚幻的形象,并不是真正的阿尔文。当海伦准备告知有关其父的实情时,曼德牧师要她继续维护欧士华心中虚构父亲的形象。于是父亲就变成了一个概念,一个虚构的隐喻。与之相比,真正的阿尔文上尉却成了一个苍白的映象。然而海伦信中受尊敬的父亲形象与欧士华在巴黎亲眼所见的各色父亲却大相径庭。这些挪威的好父亲代表着阿尔文上尉的形象,却在远离自己受尊敬的地方去光顾巴黎的花花世界,沉醉于堕落中。这些离家的父亲显然在家道貌岸然,在外却放荡形骸。像阿尔文上尉一样,他们是当时法律的宣扬者,同时也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者。这种理想父亲与现实父亲之间的明显背离说明父亲这个词已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符号,根本无法表现任何所指,这样象征意义上的理想父亲也变成了缺场。
就欧士华而言,缺场的父亲隐藏在各种错觉层面;而从吕嘉娜的角度来看,站在她面前的父亲都是假的,而真正的父亲却隐而不见。母亲乔安娜收了钱而不得不隐瞒其生父的秘密,因而虚构了一个有钱的英国人做她的父亲,这同样也是一个幻觉。这个英国人完全缺场,因为他根本就不存在。当乔安娜告诉了安德斯川她的窘境后,他为了钱娶了她,从而获得了父亲的身份。安德斯川向曼德牧师谎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结婚后他父亲身份的合法性得到了教会的认可,但这种认可却基于一个虚构的故事。尽管安德斯川拥有父亲的权利,但他既不是吕嘉娜的父亲,也没有像一个好父亲一样对她。同时吕嘉娜也并不认可这种关系,反而追问牧师“要是真是一个值得敬重,够得上做我爸爸的人”她也愿意与之在一起。(易卜生,1995:223)③这暗示她并不介意“像一个女儿一样”与曼德住在一起。这既可以理解为她把曼德牧师看做了代理父亲,也可以理解为她可以以女儿的身份做他的情人。然而曼德牧师拒绝了这一身份,因而变成了吕嘉娜又一缺场的父亲。吕嘉娜的众多父亲角色再次把父亲这个概念降为一个空洞的符号,它时隐时现于众多靠不住和邪恶的父亲之中。缺场的父亲阿尔文上尉引出了一系列的假父亲形象,这些形象又进一步远离了真正的父亲,他们是虚构的、理想的、象征的,并且总是缺场。
阿尔文的缺场并不影响其鬼魂的在场,他是死去的鬼,而剧中的人物都是其在场的代言人,是活着的鬼。当欧士华叼着烟斗入场时,曼德牧师发现他简直就是阿尔文的再生,长得与之一模一样。欧士华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外貌也继承了他的疾病,还再现了他的罪孽,竭力去引诱吕嘉娜。阿尔文的儿子去引诱阿尔文的女儿暗示了兄妹乱伦和父辈的乱伦。曼德牧师执行了父权社会的法律,禁止乱伦的发生。他和海伦重现了对阿尔文与乔安娜的处理方式:把吕嘉娜送走或嫁人。这样缺场的父亲又以一种在场的形式左右着剧情。缺场的父亲同时也通过两个建筑物的形式得以再现,即阿尔文上尉孤儿院和阿尔文水手公寓。以阿尔文命名的孤儿院不仅刻上了他的名字,还象征着被父亲们丢下的孤儿。为了体现孤儿院的神圣性,尘世间的父亲并没有给它买保险,不幸的是,孤儿院被火烧了,这恰好证明神性父亲的缺场。随着孤儿院的毁掉,这个假定的父亲,虚构的大善人,以及父亲所代表的神圣的秩序也随之倒塌了。然而在孤儿院的灰烬中,安德斯川讹得了一大笔钱,并以阿尔文的名字开了一家水手公寓,其实质却是一家妓院。这样缺场父亲的高贵形象又转化为堕落之物,这种转化正好说明了父亲形象的进一步损毁与人物悲剧的加深。
缺场父亲在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父权式的话语模式。通过对死去丈夫的纪念,海伦试图摆脱父亲的姓名和已逝丈夫的权威对自己的影响。首先,她以一个忠爱丈夫的形象用丈夫阿尔文的名字和遗产进行捐赠;其次,她尽量不占有和获取一分一厘的遗产。然而海伦最后意识到尽管她已经以阿尔文上尉的名字建了一个孤儿院,她仍然无法逃脱他的控制,因为他已完全融入到她体内。阿尔文上尉在海伦血液和身体里的存在体现了更为深层的遗传特征,这远超过了欧士华所得性病的遗传性。这种围绕在海伦身边或存在于她体内的疾病和群鬼是一种话语,是一种由语言传承下来的父权统治的现实。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个母亲适应这个父亲的方式,还要关注她接受他表现其权威,换言之,表现其法律中父亲身份的话语和语言的方式”。(Lacan,1977:218)无论如何努力海伦意识到她始终无法摆脱群鬼或其已逝丈夫的影响。丈夫在世时,她极力维护其名声,死后也一直保护他的名声。海伦发现在她孤身一人的这些年月里,除了以一个男性的名义即一个理想父亲的形象存在之外,她根本无法获得自己的身份。她以丈夫的名字为无父无母的儿童所建的家其实可以看做是以缺场父亲的名字命名的一座教堂,它既为孤儿提供庇护所,也是自己得以解脱和赦免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海伦也是缺场父亲在场的代言人。
在戏剧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听到阿尔文上尉自己也是代表父权制话语的受害者。阿尔文对生活乐趣的追求导致他饮酒作乐,这破坏了他的家庭,也把他自己置于死地。由阿尔文所扮演的高贵父权制的上尉形象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上尉;同样,与海伦一起生活过的阿尔文的堕落形象也不是真正的阿尔文。因此真正的父亲和真正的阿尔文上尉其实陷入无法名状的过去与将来的迷雾中。人们可能认为,这个家庭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家长,有的只是一个衰败的传统,一系列鬼一样的父亲形象和代表鬼一样旧传统的话语模式。丈夫与妻子都陷入了自然欲望与他们生活其中的文化话语之间的矛盾中。因此通过父亲的缺场与在场这条伦理线串联起的剧中所有人物都是鬼,整部戏剧就是在死鬼和活鬼的冲突中达到高潮,这也是该剧用“群鬼”做标题的原因。可见“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分析作品,寻找和解构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线……是十分重要的”。(聂珍钊,2010:20)
3.0孤儿院的大火:伦理结的解构
《群鬼》在不足24小时的剧情中通过父亲的缺场与在场串联起所有伦理事件可谓结构巧妙。但按照当时流行的评价方法,该剧却因缺乏足够的剧情来支撑其观点而被认为瑕疵有余。这种观点最初源于萧伯纳,他认为该剧的主题和观点都不愧于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其技巧却明显不足。例如,如果仔细审视,我们会发现该剧缺乏真正的高潮。孤儿院在开张当日化为灰烬不是由戏剧对话自身发展而来,因而不利于人物角色完整性的表达。剧本结尾欧士华因从父亲遗传得来的梅毒病发而成白痴虽很具悲剧性,但这种疾病并不是剧中人物的行为所致,因而缺乏社会悲剧的意义。(Shaw,1979:152)这些评价最大的误区是忽略了隐藏在舞台背后缺场的父亲如何以在场的形式左右剧情的发展这条伦理线,如果我们结合这条伦理线来“对已经形成的伦理结进行解构”(聂珍钊,2010:20),则会发现该剧不仅高潮突出,而且悲剧氛围浓厚。
《群鬼》的主要伦理事件即以阿尔文上尉命名的孤儿院付之一炬,儿子欧士华变成白痴。剧中最大的节点并不在于遗传的影响,而在于父亲形象的重构与毁灭。父亲的身份与地位迫使海伦“逼着他做人,硬给他撑面子”。(P243) 阿尔文死后,她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并以他的名义兴办慈善事业,创办孤儿院,替他沽名钓誉。把儿子送往巴黎后,为了体面,她一直写信告诉儿子,说他父亲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为的是不让人知道我孩子的父亲是怎么一等人”。(P241) 后来,孤儿院修好了,“纪念碑”建成了,似乎并未受到阿尔文影响的欧士华也学成归来。一切看似美满,海伦似乎可以开始新生活了,高大完美的父亲形象似乎也可以美名永传。然而就在这时,大火熊熊燃起,烧掉了意欲永久掩盖一个丑陋形象的孤儿院。孤儿院的大火起到了解结作用,不仅解开了海伦一直隐瞒的秘密,还把剧中人物推向悲剧结尾。
大火是从哪儿开始的呢?火的象征最初出现在哪儿呢?火的引子在戏剧之初就已埋下:第一幕,欧士华一出场,嘴里就叼着个大烟斗,而父亲的这个烟斗极有可能导致了他的疾病:有天晚上,他醉醺醺地回家,兴高采烈地把欧士华放在腿上,开玩笑地把自己的烟斗给欧士华抽。欧士华当时只有四五岁,当场就感到恶心呕吐。也许梅毒就在这时从上尉的口腔溃疡中通过烟斗传给欧士华。这也是为什么欧士华一出场,嘴里就含着个烟斗的原因。从这一刻起,火的象征就一直燃到剧终,并演变成明亮的阳光。在戏剧的高潮,大火成了连接欧士华和海伦故事的节点。大火之前,剧情主要是对过去事件的回顾,展现的是剧中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建孤儿院的原因;大火之后,剧情主要是对当前问题的解决,展现的是海伦面对困境如何选择。大火解构了海伦虚构的理想父亲形象,把剧情从过去拉到现在,把父亲的高大形象(孤儿院)贬为堕落之物(水手公寓,即妓院),把才华横溢的儿子烧成白痴。孤儿院大火的意义并不在于大火本身,而是在于孤儿院本身。弗朗西斯·弗格森(Francis Fergusson)曾认为“《群鬼》的内在剧情是去控制阿尔文的遗产,即海伦为纪念丈夫而建的孤儿院,而孤儿院对海伦而言又是她与过去划清界限的标志”。(Fergusson,1953:161)如果孤儿院真象征着阿尔文的遗产,这些过去的鬼,那么海伦和欧士华看到熊熊大火时应该高兴不已,因为像石头一样压在他们心中的过去被搬开了,但结果大火却成了阿尔文家庭的不祥之兆,并演变成一场家庭悲剧。
为了进一步理解大火的解构功能,我们还“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聂珍钊,2010:19)在第二幕中,海伦了解到了欧士华的疾病。欧士华告诉她这病一定是在巴黎染上的,不过他还是喜欢巴黎的生活,相反对挪威的生活大加指责。他认为在挪威人们在生活中首先考虑的是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幸福,但生活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能从中得到身体上的快乐。但对海伦而言,她的整个生活就是责任、义务和牺牲,因此她大声惊呼:“生活的乐趣?那里面有救星吗?”(P270)欧士华所说的“生活的乐趣”对海伦不亚于一个警醒,她意识到自己没有给自己的婚姻生活带来任何快乐,她的清规戒律使得年轻的丈夫不得不到酒馆妓院寻欢作乐。她渐渐明白了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现在我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是我头一次明白,现在我可以说话(P272)。当海伦认识到自己信仰上的错误,并意识到感官上的生活也能给人拯救时,孤儿院的大火突然燃起来了—— 这是阿尔文的怒火,因海伦清教式的生活模式而受到压抑的欲火。他代表了欧士华所说的感官生活,它的突然爆发过度刺激了欧士华的大脑,从而导致了他的瘫痪。大火不仅是对海伦的谴责,它还解构了她一直信奉的牺牲观与义务观,把她推入了伦理困境之中。
在第三幕,欧士华说自己也在燃烧,他的头着火了,他的病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他的崩溃表面上是因为大火引起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紧张所致,实际原因却是其父的放荡生活。寻求感官上的享乐与刺激已经毁掉了阿尔文上尉,现在又导致了欧士华的脑瘫。他一直追求阳光下巴黎“生活的乐趣”,说自己没有太阳简直无法活下去。甚至连吕嘉纳,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一个充满生活乐趣的年轻姑娘,也是他想娶的对象。但当她知道他的病情后却宁愿去安德斯川的水手公寓做妓女,而这个水手公寓正是孤儿院的大火之后在曼德牧师默许的情况下修建的。这样大火不仅解构了孤儿院的秘密和海伦的生活信条,还解构了“生活的乐趣”这一生活方式的实质。他们追求的“生活的乐趣”最后堕落成了丑陋之物:阿尔文的孤儿院变成了妓院,他的女儿变成了妓女。因此,阿尔文的遗产只不过是一个堕落之物和疾病。就在欧士华大喊太阳之时,他的疾病已经开始折磨他的大脑了。他想去死,想着他的吗啡药片,但是他已经开始神经错乱了,这是全身瘫痪的先兆。他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并不一样,他嘴里喊着药片,但在他心里这些药片却变成象征着快乐生活的太阳。
孤儿院的大火烧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它还烧掉了群鬼脸上的面纱,它以解构的方式让所有角色原形毕露:海伦苦心经营的好父亲形象不仅化为灰烬,还演变成更为堕落的妓院;当初为了自己神圣的职业坚持相信上帝而反对阿尔文太太买火险的神性父亲曼德牧师,也露出了其虚伪的本质,竟然和卑鄙的假父亲安格斯川合伙做起了生意;一直被阿尔文太太视为亲生女儿的吕嘉纳也不顾欧士华的请求而选择离去,并决定用自己的青春去享受生活。孤儿院的那场大火,像一个炙热的太阳,照亮了漆黑的夜空,解构了整个伦理事件。大火产生的烟灰,洒落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最终,伪善的曼德牧师被安格斯川控制,继续伪善着;道德败坏的安德斯川即将经营起阿尔文水手公寓(妓院),吕嘉纳出去寻找“生活的乐趣”,欧士华失掉了所有的理想,海伦将面临痛苦的选择。
4.0伦理责任与“生活的乐趣”:海伦的伦理困境
孤儿院的大火烧掉了海伦摆脱过去的希望,同时也让她陷入伦理困境之中:是追求“生活的乐趣”还是践行伦理责任?“生活的乐趣”是剧中阿尔文和欧士华一直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伦理责任却是海伦和曼德牧师一直坚守的人生信条。孤儿院的大火之后,海伦就在两种人生哲学之间饱受煎熬:她过去的牺牲观与现在的享受观。她现在关注的并不是如何与社会、教会和传统观念进行抗争,而是考虑如何在这两种人生哲学中做出选择。显然传统观念作为一种敌对势力一直压抑着整个情节,直到曼德牧师和安德斯川离开后,雾蒙蒙的天气变得明朗了,我们才明白整个争论的焦点其实一直围绕着义务与爱好,道德与享乐而展开。在戏剧的结尾,欧士华呼喊着结束自己痛苦的药丸,这对海伦是个伦理两难:如果海伦接受了欧士华的享乐主义哲学,她就应该给他药丸让他快乐地死去。如果海伦仍然坚持自己过去的牺牲观和义务观,她就应该全力去照顾他,即使他只是一具活着的僵尸。
其实海伦作为一个悲剧人物一直就生活在伦理困境之中。当她还是个年轻少女时,她对宗教非常虔诚,并且爱上了曼德牧师。然而她却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被迫嫁给了阿尔文上尉。婚后她对丈夫的越轨行为非常恶心,决定抛弃家庭责任和义务去投奔心仪的曼德牧师。因为害怕公众的舆论,牧师拒绝了她并以义务责任为由把她送回到丈夫身边。在随后的岁月里海伦渐渐明白当教会和社会都迫使她去与一个自己讨厌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时,一定是自己某些地方出现了问题。她开始改变自己的观念,承担起了生活之责。当发现丈夫把鬼闹到家里来了后,她接管了所有的房产,挑起了家庭重担,并忍住母子离别的痛苦把欧士华送到了国外,以免他受阿尔文的影响。多年以后,儿子从国外回家,她感到苦尽甘来,可以和过去再见了。但在与欧士华交谈的过程中,她却发现他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与她所想的一样。年轻时所受的教育告诉她没有牺牲就不会得到有价值的东西,而欧士华却信奉的是感官生活支撑着精神,生活的幸福在于身体的幸福。当从欧士华那里了解到人类的希望在于对生活全盘接受而不是带有宗教式的节制之后,她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多年以来她一直认为自己回到阿尔文身边是个天大的错误,但现在看来把充满激情的丈夫看作是一个恶心的动物是个更大的错误:是她把自己的丈夫从家里赶到了妓院酒馆。海伦现在开始变得开放了,她正试图去理解欧士华。当看到欧士华与吕嘉纳调情时,她甚至认为只要欧士华能在吕嘉纳身上找到幸福,她就准备容忍这种乱伦的行为。然而当曼德牧师问道:“你作为一个母亲怎么能允许你的……” 海伦却这样回答道:“我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P252)
海伦希望找到一种方式能同时满足自己相互矛盾的两种欲望:既想遵循社会强加在她头上的各种法律、传统和习俗,又想从各种规范中解脱出来。从剧情的开始,海伦就与《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不同,她不再反对传统习俗。她虽然认为传统习俗扼杀了个人的幸福,但她也承认传统习俗的重要一面:她渴望传统的母子关系。正是这种传统的母子关系才使得她不敢去追求自由。如果她理性地审视自己的婚姻,她也必须理性地去处理自己和欧士华的母子关系。在整个戏剧中她一直寻找着某个能解决这种矛盾的机会,但剧中并没给她提供这样的机会。每一个场景都是过去危机的重复。她告诉曼德牧师自己不幸福,但得到的回答仍是“义务”,只是以前是对丈夫阿尔文的义务,现在变成了对儿子欧士华的义务。当她发现欧士华与吕嘉纳在胡闹后,她也不得不像对待阿尔文上尉一样饶恕他们,以免被公众知道。后来尽管她认为并没有合适的理由去反对他们的关系,但她还是不允许他们违背传统禁忌去近亲结婚。他选择了维护传统的体面家庭,这种决定与当初送走吕嘉纳的母亲具有同样的目的。海伦只不过是重复了她过去的决定,因为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改变。年轻时她认为传统习俗与个人幸福绝对是相互矛盾的。现在年老了她更坚信这一点。她甚至有一种更强烈的感觉:她的任何决定要么是对社会的否定,要么是对自己的否定。
海伦的这种伦理困境其实是人的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相互较量的结果。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剧中海伦对伦理责任的遵守和维护则是其理性意志的体现,是人性因子发挥作用的结果。而阿尔文和欧士华一再追求的“生活的乐趣”其实是他们身上自由意志失控的表现,是兽性因子肆掠的结果。④“自由意志主要产生于人的动物性本能,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人的不同欲望,如性欲、食欲等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和心理动态。”(聂珍钊,2011:8)在自由意志的驱使下,强大的肉欲让人的理性意志无能为力。因此剧中阿尔文一心追求“生活的乐趣”,不顾家庭责任,任由自由意志驱使,在外寻花问柳,在家私通女仆,最后染上梅毒丢掉性命。欧士华追求“生活的乐趣”,相信生活的幸福即身体的幸福,因此在巴黎他就沾染上荒淫无度的毛病。就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原来我不应该跟朋友过那种快乐自在的日子。我的体力吃不消,因此我才害了病,这怨我自己不好!”(P265) 一回到家中他就看上了女佣人吕嘉纳,并对母亲说:“你看她多美!身段多漂亮,体格多健康。……她站在我面前,就好像张开了胳臂等着我一样。” ( P270)不断膨胀的兽性因子让欧士华完全忘记了吕嘉纳可能因为感染他的梅毒而终生痛苦。
海伦也曾任由自由意志驱使追求过“生活的乐趣”。年轻时她离家出走抛家弃子去投奔曼德牧师,她甚至准备接受欧士华的观点,容忍他的乱伦。但理性意志最终战胜了自由意志,她回到家中承担起了责任和义务,并阻止了欧士华的乱伦。海伦的困境不仅在于她要在这两种生活伦理中不断作出选择,更在于她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决定权,她的所有选择都被她所继承的传统所左右。例如她遵照母亲和姑姑的意愿与阿尔文上尉结婚,她离家后返回丈夫的身边,她对欧士华与吕嘉纳调情时的反应,她对曼德伪善的接受,她向欧士华隐瞒其父亲的真实面貌,她因欧士华对父亲生活的冷漠而产生的惊恐反应,还有戏剧结尾的问号,所有这些场景都证明海伦的自由理想和理性的诚实在实际生活中根本毫无用处。戏剧的结尾,海伦犹豫不决地摸寻着药丸,接着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即太阳神,也是神话中一个父亲的名字,在剧中即欧士华所说的“生活的乐趣”,这也是私生女吕嘉纳目前正准备去追寻的东西。但她的将来如何?易卜生虽没给出答案,但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其结局。“生活的乐趣”让欧士华的身体吃不消,让酗酒纵欲的阿尔文上尉丢掉了性命。吕嘉纳作为他的后代,“该家族的基因会一直延续到下一代,也许她会像她父亲一样因遗传病使其婚姻变成坟墓”(Templeton,1986:64),也许有可能幸免,只不过她具有讽刺性地回到了假父亲安德斯川的水手公寓显然只会让她堕落甚至丢掉性命。是坚持伦理责任还是选择“生活的乐趣”?戏剧最后的悲剧结尾和吕嘉纳的将来的命运其实为我们给出了答案。
5.0结语
太阳最后升起来了,这是剧本一开始就预设好的。随着过去的事件一件件曝光,随着剧情的冲突越来越尖锐,光亮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剧情在阴暗的傍晚和雨中拉开帷幕,在熊熊火光中达到高潮,又以太阳出来为整个剧情画上句号。阴暗的夜晚隐藏了缺场父亲的丑陋形象,在场的人物各个道貌岸然;熊熊大火烧掉了各自的面纱,呈现出高大的父权制与其代表者猥琐的本质,并引出了对伦理责任与“生活的乐趣”的思考;升起的太阳是否真能照亮每个人的前路?如果我们顺着缺场与在场这条伦理线去深挖父亲的隐喻与大火的象征,则不难发现升起的太阳只不过曝光了剧中人物悲剧的原因。阳光下的生活既有“生活的乐趣”也有伦理责任,它们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阿尔文和欧士华追求“生活的乐趣”丢掉了性命,但“生活的乐趣”的确让欧士华的巴黎生活充满激情。海伦遵循伦理责任维护了传统观念却仍然导致悲惨结局。因此该剧的悲剧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个人应如何用理性意志去控制自由意志的泛滥,还在于揭示了人们遵循的伦理制度是否合理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易卜生在强调了伦理责任的同时,让所有人物以悲剧收场也许是要说明只要鬼一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没有改变,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将继续存在。
注释:
DOI:10.16482/j.sdwy37-1026.2015-04-011
收稿日期:2015-02-2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3&ZD128)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伦理批评的历时发展及其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2CWW00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项目支持(项目编号:201308420435)。
作者简介:杨革新(1973-),男,湖南临澧人,文学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献编号] 1002-2643(2015)04-0080-08
Abstract:Ghosts by Ibsen presents a family tragedy with a plot of no more than twenty four hours. The major ethical events of the play are the burning into ashes of the orphanage named as Alvin Captain and the turning into idiot of Oswald, the son. The dead father, however, absent or present in the play, is the ethical line stringing all the events. The flaming fire in orphanage climaxes the play and unties all of the ethical knots. Helen’s ethical predicament pushes people to ponder over the choice between duty and “enjoy of life” as well as the evil of social institutions which caused the family tragedy.
② 拉康曾在1957-1958年以LesFormationsdel’inconscient(《无意识的形成》)为题开设了一门研究生课程,其中有章节重点阐述了父亲和父亲的隐喻问题。本文有关父亲的观点与术语主要参考法国著名拉康研究学者若埃尔·多尔(Jo⊇l Dor)教授的著作《精神分析中的父亲及其作用》,参见 Jo⊇l Dor(2003)。
③ 本文所有剧本引文均来自亨利克·约翰·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五卷(1995)。以下引文只标页码,不再一一标出。
④ 本文所有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关的术语均来自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附录,参见聂珍钊(2014:247-282)。
参考文献
[1] Fergusson, F.TheIdeaofaTheater[M]. New York: Anchor Books Edition, 1953.
[2] Hemmer, B. Ibsen and the Realistic Problem Drama[A]. In J. McFarlane (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Ibsen[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66-88.
[3] Jo⊇l Dor.LePèreetsafonctionenpsychanalyse[M]. Editions érès, Ramonville Saint-Agne, 2003.
[4] Lacan, J.Ecrits:ASelection.Trans[M]. New York: Norton, 1977.
[5] Shaw, B.ShawandIbsen: “TheQuintessenceofIbsenism”andRelatedWriting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9.
[6] Templeton, J. Of This Time, of This Place: Mrs. Alving’sGhostsand the Shape of the Tragedy[J].PMLA, 1986,101(1):57-68.
[7] 比约恩·海默尔. 易卜生——艺术家之路[M]. 石琴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8]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 易卜生文集第五卷[M]. 潘家洵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9]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10]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 外国文学研究,2011,(6):1-13.
[11]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