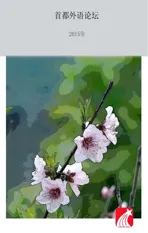彼得·凯里短篇小说中后殖民历史的建构
2015-04-08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张晓宁
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张晓宁
彼得·凯里短篇小说中后殖民历史的建构
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张晓宁
彼得·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代表作家之一,是后殖民文学界的先锋。他用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创建了多角度历史叙事性话语,从而完成了对澳大利亚在后殖民时期历史的建构。本文将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和后殖民主义角度论述凯里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如何集中体现文学对历史的阐释作用和对文化认同建构的能动作用。
彼得·凯里后殖民历史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
彼得·凯里的作品所建构的多元文化及各阶层社会意识形态的对话在后殖民主义角度来看是一种文化的碰撞、融合和杂交,以及如何顺应在世界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下建构文化身份的趋势。而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凯里实际上是通过多角度叙事的方式来重新构造历史。这种“重构”,不是简单的颠覆和否定,而是站在现代的角度通过阐释社会和政治秩序发展的规律和将参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各个元素融合起来,通过这种复杂又有序地交织,在文学语言和写作技巧的帮助下创建一种能动的历史叙事性话语。这种话语也将对文化的发展和建构起到积极的作用。
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提出,殖民文学能够发挥并加强文化霸权主义,因为帝国文化霸权通常是通过无形的表征层面进行的。①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页。以此类推,后殖民文学的创作也将成为对抗殖民文化的主要手段。以欧洲旅行叙述中的“东方主义”为例,西方人以自己的思维模式来“叙述”、“解读”自己看到的异族文化和东方世界。那些如马可波罗一般记录游历东方神秘古国的游记很大程度上会被看作是较为真实的历史,因为有笔者的亲身经历“为证”。但这其中显现出和构造出的“文化氛围”化的语言和文字还是体现了作者的文化倾向,从而铸造了帝国神话,使得文化帝国主义不断深化。
彼得·凯里对于后殖民历史的建构早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就有集中体现。
由于澳大利亚的历史原因,她在文化上与英美两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于二者在后殖民时期的关系,凯里在其早期短篇小说《美国梦》中就有所探讨和展示。文章中叙述了澳大利亚人在澳大利亚构建自己的美国梦,不仅通过人们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工建造的小镇去追求美国的生活方式展现了澳大利亚人对美国文化的崇拜和仰慕,同时小说的题目是“美国梦”,使读者不禁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化惋惜。独立后多元文化林立——土著文化、非白人移民文化、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后殖民世界的历史在凯里的作品中以多角度以及超现实主义手法呈现在读者面前。
凯里在作品当中让格里森筑墙,实际上自己也在“筑墙”,当地小镇的人通过墙换了个角度审视自己本身安逸且与世无争的生活,虽然知道自己现在所有并不是最好的,他们知道美国的经济发达,文化绚丽多姿。即便如此,身处看似封闭的环境中的这种对宗主国文化的羡慕只能深藏在人们的心中。通过对一些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近乎膜拜的珍惜——比如纸张和自行车来表现心中对作为文化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向往。然而,就在他们自娱自乐地“享受”着帝国主义文化潜在地同化的时候,一个名叫格里森的退休老人自购了两英亩的田地,并用墙隔绝了自己。对此觉得怪异的镇上的人曾想尽办法窥探墙里面的秘密,但谜底却一直到五年后格里森去世才真正揭开。格里森用那墙后的土地建造了一个小镇的微缩景观。它不仅精确地展示了小镇的格局,并且还有千姿百态、惟妙惟肖的人物。惊奇之余,小镇的人并没有感到分外的喜悦,反而恐惧将自己的微缩后的家示人,惧怕“屋顶”下面包含着自己不愿让别人看到的一面。凯里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在读者面前树立了一道墙,这道强迫使读者自己对作者的意图而感到模糊,会对格里森筑墙这个情节的设计有些迷惑不解,纵观小镇上的人对这个微缩景观的看法,以及外来的美国游客对这个“微缩小镇”产生极大兴趣,它为这个地区创造大笔的财富到底有什么意义?凯里无疑是希望他的读者能够反思,能够启发读者看到澳大利亚文化建构的无奈,能够让读者意识到在这其中体现出的后殖民时代澳大利亚人对自身文化的自卑心理,就如《美国梦》里体现的那样,在微缩景观建成之前,人们崇拜美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但因为身处山清水秀、远离大都市的小镇,人们只能单纯地做做“美国梦”,而对自己的生活和文化圈子有什么值得自己珍视和骄傲的东西,小镇的人们是茫然不知的。通过那道“神秘的”墙,他们平生第一次有了机会来跳出自己的圈子以“局外人”或“他者”的身份来审视和解构自己的文化环境。无疑,《美国梦》中经过格里森用墙来“解构”和“建构”的小镇一开始是让他们自己难堪的。他们是不愿意正视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文化自卑之余,美国游客的到来却又为这个微缩小镇,或进一步说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化提供了新的解构和建构框架。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承载者的到来和承认反而让这些人对代表自己文化的小镇自豪起来。充分显示了澳大利亚文化构建基础的脆弱性。也是在后殖民世界中构建文化身份所不能避免的。微缩小镇为成为了旅游景点。小镇的人对原本不以为然的文化特征产生了兴趣,甚至开始由衷地欣赏起自己的大好河山来。小镇人对自己文化的建构来自文化宗主国的“叙述”和解构和建构。这一点对于独立后想摆脱文化帝国主义,创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的民族或文化主体来说是非常讽刺的。作者凯里通过“筑墙”创建了一种具有模糊意义指向的隐喻。时而指向小镇里的澳大利亚人在构建文化身份时的无奈,让读者看到双重叙事角度下小镇里的人的截然不同的反映,通过他们在建构文化不同背景—— (筑墙前后)以及不同的文化心理来看所谓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叙事性和阐释性。
凯里的另一部短篇小说《克拉波斯》同样地借助文学的虚构性阐释了澳大利亚建立文化身份时的尴尬局面。只不过这次凯里利用超现实主义将“筑墙”改成了“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汽车电影院”。主人公克拉波斯因为汽车的轮胎被盗而不得不留在电影院里吃住,不得自由。虽然他靠梦想趋势变成了一部漂亮的美国福特汽车,但仍然无法逃脱用钢加固了的围墙。
凯里创造了离奇的情节,设法让读者联想到了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一些追求美国物质及文化标准的人,他们从生活方式上都想象美国人一样。虽然澳大利亚从它的创建历史来看,应该更视英国为宗主国,但为什么在它获得独立后反而对美国的文化更加崇尚的。原因在于,美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在经历着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激进的思想因为交通的便利和通讯的日益发达几乎传到了世界各地。英国的北爱尔兰共和派也是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多数澳大利亚的白人,特别是白人移民,他们认为自己祖辈的历史与美国的第一批移民非常相像。虽然17世纪初来到美国的清教徒不是流放犯,但他们都有逃脱本国政治迫害和宗教排挤的经历。而美国和澳大利亚成立的背景虽然不相同,但都是由英国的殖民地转换成了独立的国家。当然,美国的独立性随着他经济以及政治实力的增强要比澳大利亚强,因为澳大利亚到现在还是英联邦成员,并承认英国君主是英联邦的首领。美国的政治也是从多元化起家的,并随着移民种类不断增多和全世界范围的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也逐渐弱化了种族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美国的经济发达和强大为新一代澳大利亚人开创了一幅完美的蓝图。澳大利亚人甚至在潜意识当中会这样认为:今天在美国发生的一切,明天也会发生在澳大利亚。由此,美国的一切都为一些激进右翼人士,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所憧憬。当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起,澳大利亚人又看到了争取自由的机会,但此时已经有一些新一代的澳大利亚人看到这时的自由已不集中在摆脱英国的控制了,而是渐渐意识到自己本国文化受到美国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并受到了美国文化霸权的侵蚀。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一些文化特征也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澳大利亚本土文化,无论新一代澳大利亚人是否愿意承认,这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其实,拿澳大利亚的嬉皮士来说,他们就是一个美国文化在澳大利亚被本土化的活生生的例子。嬉皮士本来起源于美国,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等行为阐释手法来反霸权、反独裁、反战、反种族主义。他们从最开始的生活方式和言论的标新立异,到后期的激进的反战和对抗政府的活动,逐渐构建起了一种反对政府及文化霸权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观。澳大利亚的嬉皮士的产生当然要归功于新一代澳大利亚人对美国政治、经济、以及价值观的推崇。嬉皮士的反霸权精神深为澳大利亚本土的嬉皮士所应用。但随着美国文化的深入渗透,这些澳大利亚嬉皮士的反帝国主义意识使他们看到了他们曾经奉为自由“神灵”的文化宗主国却在后殖民时期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处在政治混乱和后殖民敏感时期的国家行使着军事、政治和文化霸权。于是,先前美好的“彩虹色肥皂泡”破灭了,于是澳大利亚的嬉皮士便把反霸权的矛头指向了美国,甚至是美国的嬉皮士也不再被他们像神一样地崇拜了。这在凯里的201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他的非法身份》 (又名《亡命天涯》)也有体现,澳大利亚当地对美国人,哪怕是嬉皮士和民权运动激进分子的追随者的黛尔在当地谋生的时候也一直不断排斥,甚至采取极端的行为杀死了黛尔和养子切的猫。如果说嬉皮士对美国嬉皮士的反感和排斥是澳大利亚人反抗美国文化霸权和帝国主义文化侵蚀趋于白热化的体现和叙述的话,那么早期的短篇小说《克波拉斯》就可以是一些包括凯里在内的受西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一些新派作家对读者的警示,通过作品的超现实主义的阐释来体现澳大利亚构建自身文化身份的无奈。作者凯里本身受嬉皮士文化影响比较深,同时在他在为一些文学作家和名人做广告的时候,又陆续接触到了一些后现代及现实主义作家。所以,在他心中的民族主义之火在他创作生涯之初就显露出来。之后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无论是叙述历史还是刻画当代的人物,不向文化霸权低头的信念一直在他的作品中通过阐释、叙事和隐语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一直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唤起人们对本族文化的热爱以及给予人们以启示——文化霸权无处不在,建立属于澳大利亚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帝国主义文化宗主国的影响和世界多元文化主义的大趋势的作用下,以及顺应后殖民文化研究中对于后殖民世界文化混杂将为最终发展方向的前提并不容易。而他也不断通过自己的作品进行辛勤的耕耘,希望通过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历史书写、叙述和阐释来推动和完成澳大利亚文化身份的建构,即既不完全排斥,也不甘于被同化。
在短篇小说《克拉波斯》中,凯里不仅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通过一种叙事体验和过程完成了对主人公克拉波斯的阐释和解构,并在阐释的过程中体现文学对于文化的能动性,即文学在言说者和创作者能动的叙事过程中对读者起到警示的作用,并对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提出指导。在新历史主义理论下,对克拉波斯的身材矮小、懦弱无能的表现,以及他追求一些非常美国化的东西的阐述——比如跟风去汽车影院看电影并在那里实施性爱——可以被看作是他掩盖内心弱小和无奈的表现。作者想表现出他想通过做最潮的事情来武装自己,甚至在被困在电影院中还幻想着自己已经变成了时髦绚丽、代表着美国经济及文化强大的V8福特车。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美梦破灭之后他仍然身陷囹圄,不能从汽车电影院里逃生,而除了福特车以外,所有那些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的物品,如用来加固电影院外强的钢筋都再一次发出这样的警示:如果文化建构永远要依附另一个文化霸权的承载者,那再强大的文化“外皮”都无法掩盖内心的弱小。更如文章中那个对情节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轮子”一样,凯里作为言说者希望传达这样一个隐喻意义:由于历史原因,美国文化对澳大利亚文化的影响就如同车轮对车的作用一般。轮子一旦被偷,车子就会瘫痪。由此看来,美国文化的霸权影响已经深深植入到澳大利亚文化当中,而继续任其就此发展将来的出路就只有变成文化附属国这个宿命。最终在建立文化身份和价值观的道路上无法冲出美国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束缚和牢笼。同时,小说中凯里也通过小说当中的政治隐喻。初步探讨了摆脱文化霸权和建立澳大利亚文化身份的方法,比如克拉波斯发现有些警察将一些车轮藏了起来。这里警察便是政府的代言人,凯里这个情节的设计就是要阐释政府在一些文化政治制度上的简单粗暴,其实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使澳大利亚本土文化的发展陷入瘫痪的状态。凯里在这里要传达的隐喻意义是:“抵抗美国的文化霸权不能简单一味地抵制和根除一切和美国有关的文化元素。那样会适得其反,甚至会使政府成了文化霸权的帮凶。”小说中克拉波斯和其他滞留在汽车电影院的澳大利亚人不就是因为车轮不见了才不得不成了“阶下囚”吗?换句话说,在警察藏轮胎这个情节上凯里还对澳大利亚的政治史做了阐释,澳大利亚的警察在殖民时期是非常腐败的,这在凯里后期的长篇著作《凯利帮真史》也有非常深刻的叙述。对政治史的重构和阐释使得政治隐喻意义表达得更加完整,文学对文化的能动作用更加得到突显。
除了《美国梦》和《克拉波斯》,凯里的多篇短篇小说都对人性、道德、政治和历史作了阐释性的描述,用于表现澳大利亚文化在后殖民世界构建文化身份的时候想要摆脱文化帝国主义霸权的无奈。同时运用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创建缥缈而虚幻的场景和情节,从而创建一种“模糊”的具有启发作用的隐喻环境和意义指向,从而赋予平凡事物不寻常的、非传统的隐喻意义。通过这种后解构主义的赋予语词和事物隐喻意向,完成后殖民主义下的多元文化的历史重构。另外,在叙事方式上,凯里在短篇小说中也进行了试验性的开发和实践,尝试在新历史主义下对历史的阐释以及文化身份的建构,从而充分体现用来阐释历史的文学文本其实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站在现在的角度对历史的进行的叙述并指导当代文化建构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