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故乡”及其精神隐秘
——从大陆看《复岛》
2015-04-05李云雷
李云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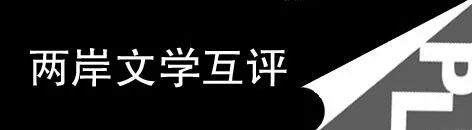
——从大陆看《复岛》
李云雷
台湾文学对于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陈映真、黄春明、王文兴、白先勇、张大春、骆以军等老一代作家,对于青年一代的创作,虽然也很有兴趣,但平常较少有机会阅读。之所以对台湾青年作家的创作感兴趣,其实也是想了解青年一代的情感结构与内心世界。可以说,陈映真等前辈作家虽然处在台湾,但他们的情感结构、问题意识、美学趣味与大陆作家并无太大的差异,台湾文学一九六○年代以降对西方现代主义极为推崇,大陆在一九八○年代以后也以相似的轨迹发展,台湾有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大陆也有关于寻根文学、新乡土文学的讨论。虽然这些文艺思潮在海峡两岸有着不同的思想、社会语境,但相似的主题与“问题域”却也显示出两岸文学的内在根脉相连之处,以及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对于青年一代作家而言,相互之间的精神交流却变得愈发困难,一方面在大众文化崛起的背景下,文学在海峡两岸都已处在了较为边缘的位置,已不再是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一九九○年代以后,台湾政治、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动也形塑了新一代青年复杂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对于这一时代变迁的隔膜,也让大陆读者很难切身体会到台湾青年作家的内心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读到王聪威的《复岛》,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可以触摸新一代台湾作家的情感褶皱,以及他们想象世界的方法。王聪威出生于一九七二年,他的《复岛》、《滨线女儿》出版于二○○八年,一般被视为台湾“新乡土派”的作品。此前他尚有《稍纵即逝的印象》、《中山北路行七摆》等作品,具有强烈的前卫风格,呈现出了不同的都市意象;此后在二○一二年,他则出版了长篇小说《师身》,以师生恋为题,探讨都市男女复杂的情欲问题。可见,即使在王聪威个人的创作历程中,《复岛》、《滨线女儿》也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有二,一是这两部作品写的都是“乡土”,二是在写法上作者并没有过多采用先锋性的现代派技巧,而更多的是平淡朴实的现实主义笔法。这与他此前此后的创作都颇为不同。在这两部作品中,《复岛》以四篇小说拼贴了对父系亲人的记忆,而《滨线女儿》则“写的是妈妈家乡哈玛星的故事,与写爸爸家乡旗后的《复岛》算是连作。”在这里,我想重点分析的是《复岛》中的四篇小说。
《复岛》由《奔丧》、《淡季》、《渡岛》、《返乡》四篇小说构成,除《渡岛》篇幅较长外,《奔丧》等三篇小说篇幅皆较短,意蕴也较为单纯,这四篇小说在人物、场景、情绪上相互交织但又各自独立,共同构成了一幅对父亲家乡的整体想象。南方朔先生在推荐序中指称此书为“地志风土作品”,强调该书的“地方性”特色,郝誉翔女士的推荐序则以“梦境与现实的交相渗透”为名,强调的是小说的写作方法,而作者本人则更重视“家族”的视角,在后记《家族境遇的形成》中详述了这一视角的“发现”。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一个访谈中表示,“我没有住过旗津一天,但我父亲、祖父在这里居住的痕迹,让旗津的一切与我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如作者所说,“这是我用文学重新建造的港口,用文字亲绘的地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乡土”是虚构出来的,而值得追问的则是,作者虚构的是一个怎样的“乡土”,为什么会虚构这样的“乡土”?
《复岛》写的是复岛一个王氏家族几代人的故事,第一代是日据时代的医师(爷爷),他娶了两房妻子,一房来自一户有钱的大户人家(奶奶,书中称为大阿妈),二房原先是大户人家的婢女,是奶奶的陪嫁,后来也嫁给了爷爷(书中称为小阿妈),书中主要写三代人的故事。《奔丧》写的是一个当兵的儿子(第二代)急急奔母丧的故事,故事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穿插,将不同时空中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交错出现,颇具张力。《淡季》则主要写“我”(第三代)对“小阿妈”的记忆,那是小阿妈在家族中的清冷地位,也是我随父亲去看她时的淡季岁月,是海边沙滩和局促房间的模糊回忆。《返乡》写的则是,“我”在病危的奶奶(大阿妈)病床前的思绪,故事在往昔的热闹岁月与如今的人事凋零中交错展开,在回忆中“我”看到了昔日健壮的大阿妈,也从“我”的想象中展开了大阿妈的情绪与意识流动,从不同角度再现了旧日的家庭场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时光流逝的沧桑与哀痛。
篇幅最长的《渡岛》,在结构与意蕴上也更为复杂,既有历史的兴衰与时代的变迁,也有现在时的场景,还有虚构与想象的传奇故事——祖父所经历的拆船业的兴旺与瓦解,大学生在海滩烧烤时遇到的事故,在海底复制一个岛屿的奇思妙想,一队送葬队伍的象征性意蕴,种种线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丰富复杂的文本。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王聪威在《复岛》所展现的是一个家族的片段历史,也是一个地方(旗津)的风俗志,更是对童年与记忆的重构,是小说家的想象与虚构。在台湾文学的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复岛》异于“乡土文学”的元素,一是作者更注重“个人化”的视角,而较少从社会化的视角切入历史与现实,比如相对于黄春明《苹果的滋味》、《儿子的大玩偶》等乡土文学经典作品,《复岛》没有直接介入社会问题的揭示与讨论,而是试图虚构一个地方性的家族故事,这或许显示了作者在当代都市生活中的无根感,以及在精神上重新寻根的努力;二是作者所讲述的方式并不是完全现实主义的,而是融入了现代主义的技巧与元素,这一方面显示了作者艺术修养的多元,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作者的问题意识的复杂,而这种复杂的问题难以由一种“透明”的现实主义所展现,或许只有现代派技巧能充分展现出其内在的皱褶与情绪,经由暗示、象征与时空交错,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与内心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写的虽然是“乡土”,但其着重点并不在于现实乡土问题的解析,而着重于以“乡土”抚慰都市中孤单而破碎的“现代人”的灵魂。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当代台湾乡村所遭遇到的最大问题,正如大陆乡村近些年来也遇到的一样,也是资本下乡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关系的重组,传统伦理—文明的解体,以及环境—生态问题等,在这方面,吴音宁所著的《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有着较为详细的历史梳理与现实剖析,林生祥及其“交工乐队”也有着艺术与社会运动中的“反抗”,但是《复岛》并没有触及现实中乡土所存在的问题,“乡土”在作者那里是一种抽象的存在,那里是他虚构中家族的血脉来源,也是他在都市生活中的“乡愁”,是他精神上的一种回归与超越。
我们还可以更详细地分析一下作者乡愁的指向。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乡愁的寄托之处是旗津(以及《滨线女儿》中的哈玛星),是高雄港附近的区域。如果我们以“乡土”与“本土”的思维框架来考察,那么可以看到,小说中的旗津所指代的无疑是“本土”——台湾本土的历史、传统与经验,但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这里的“本土”并不是指与大陆所并立的“台湾”,而更多具有“乡土”的本义——与都市经验相对的乡村经验、情感与记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九七○-一九八○年代年代所对立的“乡土”与“本土”论争,在新一代作家笔下已经有了新的融合与生成,在他们这里,乡土经验与本土记忆并不矛盾,而在新的问题结构中合二为一,成为对都市经验的一种审美反抗。
在这个意义上,新一代作家的“寻根”便具有与众不同的意义。在这里,作者寻找的不是固定在某一处的“根”,而是一种共通的前现代的经验,一种历史记忆与一种生活方式——大家族的聚合离散,人际关系中微妙的爱与疼痛,时光流转中的沧桑巨变。在这里,作者所面对和处理的不是台湾的“特殊经验”,而是现代中国整体在现代化转型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所谓台湾的“特殊经验”是指大陆来台作家所写的“寻根”作品,他们所寻的“根”在大陆,是在特殊历史境遇中对故土的记忆与眷恋。老一代作家姑不论,即使张大春的《聆听父亲》、骆以军的《远方》等,所追寻的根脉仍然在大陆,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两岸暌隔的历史回响。但是另一方面,大陆与台湾都处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那就是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巨大转型。两岸隔绝本身就是现代中国的痛苦经验,也是这一巨大转型中的后果之一。但相对于两岸隔离,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巨大跨越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痛感经验,这也是一个至今仍未完成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与内心世界逐渐瓦解,但一种新型的、属于“现代中国人”的情感与价值观念却没有建立起来。
在此种境遇下,对前现代中国乡村的眷恋与批判,便成为了“乡土文学”自诞生之初便具有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情感诉求。在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风波》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锋芒,而在《故乡》以及《朝花夕拾》诸篇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他对故乡人物与风土的温情与缱绻。在沈从文、萧红的笔下,我们看到的也是他们对乡村生活的留恋,以及对都市文明的讥讽。在现代中国文学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是与乡村和都市的对立同构的。在西学东渐的新文化视野中,乡村遗留了更多“旧文明”与传统文化。这种对立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在当代大陆青年作家的笔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对立”。但是与五四时期激烈地反传统不同,在当代青年的作品中,传统文化及其“载体”中国乡村,较多地呈现出了其美好温暖的一面。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巨大变化有关,在此种境遇下,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殊性便得到了重新关注与审视;另一方面,也与现代社会中孤独“个体”的生命体验相关,最近三十年,是中国大陆发生天翻地覆巨变的三十年,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化,让置身其中的“个体”经验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在这样一个时代,尤其是处于瞬息万变的现代都市,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不断“断裂”,很难形成相对稳固的内在“自我”,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孤独的“自我”处于一种不断聚合的碎片状态。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回到乡村与传统文化,寻找自我与家族的“根”,便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内在诉求之一。
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脉络与问题意识中,来理解王聪威和他的《复岛》。在《复岛》中,我们可以看到侯孝贤《童年往事》中淡淡的回忆与哀愁,那是小阿妈屋顶上的天窗,“倘若没有记错的话,是斜开着的,用根木棍顶着一片以四五条木条拼成的天窗,好像是有三扇左右,在下雨的时候,才会关上。在门的旁边,也有一扇相同的窗子,每一次敲门前,我总会习惯性地往窗子里瞄一下。”那是陪侍在大阿妈临危的病床前,从她的角度回忆往事,“杰仔找到了一个稍大的沙马洞,在没被海水泡到的地方捉了把干净白沙,慢慢将白沙均匀地洒进洞里。等到白沙满出洞口,便往下挖,……‘哇!’阿杰猛地跳起,一只难得一见的红黑混色粗壮沙马突然冲出沙堆四处乱窜。阿杰吓得拼命往后退,哗啦一声跌到海里去;我赶紧伸手拉他一把。”正是在这些细节中,“我”与小阿妈、大阿妈建立起了联系,也与家族、历史、地方建立起了联系,“我”不再是漂泊于都市中无根的“我”,而与这个世界建立起了稳固的血脉联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建立的这种联系是一种虚构的关系。前文我们已引述了作者“从未在旗津住过一天”的表述,在小说中也有相似的表达,在《淡季》中,“我拨打了一通电话给南方的家,问了爸爸,‘你记得小阿妈家吗?在港的工作船维修站对面那里?有一道白色石板阶梯往下走?’‘我不记得了。’他说,‘我不记得他们曾经住过那个地方?’……我在电话的另一端,没有提高声调或显露生气的声音,但几几乎快要哭出来了。毕竟那时候,爸爸是大人啊,我不过是个小孩,一定是记忆比较不好的,他这么说,我是的确会怀疑自己难道从未去过那里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此处不确定的叙述完全推翻了此前作者以扎实的细节建构起来的回忆场景,那些台阶、天窗、挖沙马的游戏成为了一种恍惚的记忆,甚至沙马这种动物是否存在也是一个疑问,“是否有可能根本没有沙马呢?倘若,那一整个淡季的存在都值得怀疑的话。或许确实如此,到目前为止我再也没有在别的沙滩上挖过沙马了。”对沙马的怀疑同样否定了记忆的可靠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的叙述技巧,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这样的叙述方式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人”的心灵状态——那种恍惚的、碎片的、不确定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复岛》的写作正是克服这一精神状态的努力,尽管作者所呈现的世界仍是恍惚的、不确定的,但至少那些细节已经落在了纸上,已经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即使故乡是虚无的,我们仍然需要虚构出一个故乡来——我想,这是“现代人”精神的一种归宿,也是我们面对世界与自我的一种选择。
(责任编辑 韩春燕)
李云雷,《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