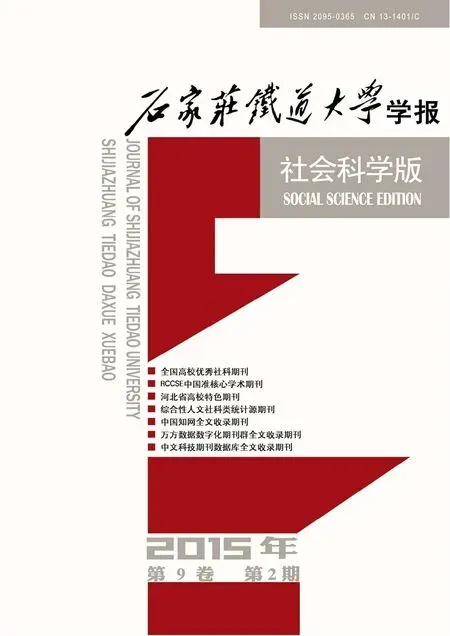论文学需要政治
2015-04-03刘江
刘 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广西柳州 545616)
人类至今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然而直至现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还没有完全厘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学术界和创作界的一些人,往往只注意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而忽视了文学表达和依附政治的需要,因而一些评论家和作家对政治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有的评论者认为,中国文学之所以和政治结合,只是某一阶级的政治对文学的劫持。而有的创作者,对那些与政治密切联系的作品不屑一顾。于是这里便出现一个问题:文学中的政治,就是政治所为吗?或者说,只是政治需要文学,而文学就不需要政治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一、文学需要政治的理由
(一)什么是“政治”?
要弄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必要先弄清什么是政治。在西方,“政治”一词来源于希腊,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荷马史诗》,最初的含义是“城堡”或“卫城”。后同土地、人民以及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被赋予“邦”或“国”的意义。此后又衍生出“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词。这时的“政治”,“就是指城邦中的城邦公民参与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1]在中国,先秦诸子也使用过“政治”一词。在许多情况下,是将“政”与“治”分开。“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秩序和法令”;“治”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指“实现安定的状态等”[1]。但随着社会的变幻,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于“政治”都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把政治说成是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的凯尔森;二是把政治视为权术和统治术,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和中国的韩非;三是把政治看作是“管理众人之事”,代表人物是中国的孙中山、英国的麦肯齐;四是把政治解释为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活动,是一种实现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活动,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戴维·伊斯顿;五是把政治等同于或归结为伦理道德,代表人物是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上述观点之外,马克思又把政治理解为“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2]41。列宁则认为 “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3]370。总之,“政治”的含义非常广泛。但无论怎么说,都无非是指国家、民族(族群)、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个人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文学需要政治”的理由阐释
在新时期里,我国学术界进行过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通过讨论,学界已经注意到了文艺本身具有某种不能为意识形态涵盖的特殊性,具体而言,即注意到了文艺的审美性,并试图将其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结合起来。”[4]这里,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并没有受到否定。当然,也没有特别提到政治意识形态。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中,政治意识形态应该是重要的方面。而眼下所要注意的问题是,文学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但政治需要文学,同时文学也需要政治。而文学对政治的需要,同时来自于文学本身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
1.文学对政治的内在需求
(1)遵从文学反映生活的原则。“艺术既是自主的又是社会形成的。”[5]355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内容所在。现实主义文学不用说,就是浪漫主义文学,也是借浪漫的想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而生活中缺少不了权力和道德,总是蕴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族群)与民族(族群)之间、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个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就离不开人们关于这些方面的思想意识。西方世界的民族歧视、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权力集团的腐败,都是突出的政治行为。西方有学者说:即使是家庭生活和疾病,甚至“身体行为”,其“一些基本方面,如走、站、坐等,都是社会结构。这些实践行为要求有官能性基础,但是官能性的潜力得以实施需要一个文化语境。”[6]92这“文化语境”中就有政治的因素,包括政治背景和时代环境,以及民族习俗、宗教精神和伦理道德等等。另一位西方学者则明确地指出:“今天”是“这样一个极易受到政治和企业生产意象的代理人操纵的社会”[7]88。还有一位西方学者又说:“社会仍以几种方式呈现在自主的艺术领域中;首先是作为美学表现的‘素材’……其次,作为斗争和解放的实际可能性的范围……”[8]265,他认为“斗争和解放”(也就是“政治”)是“社会”的一种“方式”。即使一些文学作品描写的是历史,而这“历史”,也是“作为过去的政治反映”[9]51。所以文学无论是反映现实还是反映历史,都难以和政治相离。其实,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生活,实际上都是由政治支撑的。要治疗非洲的埃博拉疾病,虽然医疗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技术,让其能够产生和应用的,还是政治。政治是社会生活支柱性的架构,也应该是文学支柱性的架构。如果说反映生活是文学的本质的话,那么文学表达政治,就与这本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如此,所以又有一位西方学者说:“‘小说的政治’并不是已经摆在那儿只等人去发现,而是得通过与文本对话产生出来”[10]84。——这里,不但认可了文学的政治内容,而且强调了读者解读政治的必要。
(2)遵从文学表现思想的原则。思想是文学的灵魂,无论古今,无论中外,文学都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载体,而思想情感之中往往缺少不了政治成分,所以政治的意识和情感是难以缺少的,需要在文学中反映出来。西方的现代派,他们的作品表达的即使是哲学上的思考,但内中往往也有政治的意味,如其代表作品卡夫卡的《变形记》,虽然从表面上看只是反映人与人间的冷漠和无情,表现人的异化,但实际上也是表现金钱社会的政治危机,其政治意味依然明显。
(3)遵从文学的主体性原则。文学的创作主体是人,而人是生活中的人。生活是很难离开政治的,所以创作者实际上都是政治中的人,特别是作为写作者的知识分子,他必然有自己的政治意识,并且有着借作品表达自己政治意识的主观需要。有些人似乎有意躲避政治,但其政治意识也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余秋雨写的“文化散文”,实际上和政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就是佐证[11]30。而另外一些人创作的所谓“纯文学”,其实也并没有脱离政党和道德的意识。至于抗战时期周作人醉心于描写花草虫鱼,那更是对祖国前途淡漠的表现,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政治”!这些都说明:表现政治意识,是创作者主观或客观的需要。
(4)遵从文学的服务性原则。文学具有服务功能。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总是要为某一阶级、民族(族群)、政党、利益集团的利益服务的。中国的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法国的巴黎公社文学,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自不用说,而“欧洲各国的启蒙文学”,其实就是“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战斗武器”[12]134来使用的;那些古典主义文学,当然也是以“拥护王权,崇尚理性”[12]113的政治理念,来为“宫廷”即封建阶级服务;至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却是为西方中小资产阶级服务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多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对贵族、大资产阶级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垄断非常不满,另一方面又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深为恐惧;因而他们揭露现实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企图通过改良现存社会的某些弊端恶习,以求建立一个中小资产阶级能以生存发展、无产阶级又不致起而反抗的‘理想’社会。”[12]232。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表达的,就是这些中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上述这些文学去进行这些政治性的“服务”,也就说明了文学对政治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些“服务”,那么这些文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同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5)遵从文学“内容重于形式”的创作原则。实际上,古今中外的文学都是内容重于形式的。恩格斯欣赏巴尔扎克的作品,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13]136,这无疑是首先从作品的内容着眼。列宁说“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14]175,其着眼点亦是如此。这是他们的审美原则,也是他们心目中的创作原则。其实西方学界也是这样认识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艺术……,它身上的艺术特质必须……从内容方面加以探讨。”[8]351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其声言重“文本”,但实际上还是先看内容,是在内容的前提下看重文本形式。难道存在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作品吗?一位西方学者说得好:“纯粹的美不可分割地与它最终是不纯粹的那种要求联系在一起……语言和美本身永远不可能完全自治。”[15]245
既然文学是内容重于形式,文学作品首先是因内容而存在,那么,内容在创作中就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内容就不可避免地牵扯到社会和政治。其实,政治不但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且是社会本质的体现。这是因为:自从人类脱离原始社会,特别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国家、民族(族群)、政党、利益集团,都是社会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建构,国家、民族(族群)、政党、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个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生活中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关系,中外社会的性质,就是按照这些关系来区分的。至于社会中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人格精神,也是由国家、民族(族群)、政党、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个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决定,或者是受它们所影响的。所以,文学要描写社会,要表现生活,其内容就必须反映这些关系,这才抓住了生活的本质,才有深刻性可言。如果否定文学描写这些关系的必要,那么文学的深刻性和重要性,也就足以置疑了。
(6)遵从文学叙事的美学原则。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诗所写的行动和思想感情可以美,即内容意义可以美。”[16]162的确,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美,是文学美的重要方面。而文学作品的美,是建立在“完美”和“理想”之上的。如果文学描写了理想的政治生活,表达了先进的政治意识,作品内容的美感也就随之产生。古今中外不少文学作品,正是描写了包含着政治内容的“理想”的社会生活,表达了先进的政治意识,因而获得了人们的喜爱。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名著,它们无论选择什么题材,都是在表达先进的政治情怀和感悟,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到文学对政治的需要。
2.文学对政治的外在需要
首先,文学需要政治提供其产生的社会条件。
世界上的各种文学,都是由社会条件(包括政治条件)所催生的。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环境,就给文学提供什么样的题材,触发作家什么样的写作动因,也就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有人说:“古希腊、罗马文学是奴隶社会的产物。”[12]11这话不错。恩格斯也说过:“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17]220这是从艺术(文学)产生的条件上,从正面说明古希腊和罗马文学对于社会政治条件的需要;而17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衰落的现象,意大利破败不堪,西班牙动荡不安,德意志四分五裂。由于这种政治局面,所以造成“17世纪欧洲各国的文学也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现象”[12]108,以致“未能产生出具有全欧意义的作品”[12]108,如果欧洲不是上述政治情况,就不至于有“这些国家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12]109,这却是从反面说明了文学的产生要以政治条件为基础;18世纪的启蒙文学,为了启蒙,为了使人民从封建意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就需要作品“不仅是反映生活,更主要的是评论生活、干预生活,宣扬他们的思想观点。”[12]134这说明文学的体式是由政治环境所催生的;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在资本主义确立、发展时期的产物”,[12]229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三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奋起反抗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社会,使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的历史条件,就不会有“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典型地再现社会风貌,深入解刨和努力揭示各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12]232。同时,也是因为当时社会的浑浊,造成作者们头脑中的一片迷茫,出于对政治的反感,西方的一些文学创作者,才在作品中显出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情态,这才出现了当时被认为新的创作流派的现代派文学。这些,却又说明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流派的产生,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条件和环境。
其次,文学需要政治的护卫和推动。
人类社会自从阶级产生以后,世界上的好些文学,实质上都是阶级文学,其存在和发展都要靠阶级的政治手段来护卫和推动。比如西方中世纪的教会文学,基督教会是把它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12]46来使用和护卫的;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存在,是宫廷在“成了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政治上集中统一”之后,对文学艺术“实现规范化”[12]113、予以保护的结果;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因为得到中小资产阶级的庇护和推动,才成了这一时期西欧“资产阶级文学的主要潮流”[12]236。当然,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工农兵文学。工农兵阶级完全是把它“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来使用,作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8]49来推动的。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后期,政治势力不知花了多少精力来培养作者、宣传作品,才使它显赫全国并走向世界。
放眼世界的文学,人们便会感到:整部世界文学史,实际上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史:它既阐释着“政治需要文学”,同时也阐释着“文学需要政治”。由此又证明:“文学需要政治”,不但是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
二、关于“文学需要政治”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文学需要政治”的中国文学传统,和当今一些人对它的排斥
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史看,“文学需要政治”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学传统。先秦时代,需要“百家争鸣”的政治环境提供创作的条件,才会有展示各种思想观点的诸子散文,和《诗经》的“风、雅、颂”的多种形态的诗歌;唐宋古文需要“文以载道”(这“道”含有封建性的人文性、民族性和爱国性的意蕴),才会有唐诗宋词和唐宋散文的人文性和爱国情怀,我们可以看看,无论李白杜甫的诗、陆游的词,还是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都是具有爱国情怀和封建道德意义的作品。同时,也正是清朝的衰落,才为曹雪芹作品提供了题材。也正因为他的《红楼梦》表现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衰落,表达了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政治意识,才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名著。可以说,五四之前所流传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表达政治倾向的文学。
出现于20世纪我国“五四”时期的好些文学作品,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4)、《孔乙己》(1919.3)、《药》(1919.4)、《故乡》(1921.1)、《阿 Q正传》(1921.12)等等作品,可谓之启蒙文学。虽然鲁迅的写作目的是揭示“国民性弱点”,即“揭出病苦”。而“揭出病苦”,是为着“引起疗救的注意”[19]6,但如果只从文化着眼,是达不到真正的启蒙目的的。所以鲁迅总是把作品的人物和故事放在清朝封建社会和辛亥革命的历史环境里,表明这“国民性弱点”即“病苦”,是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由此也说明国民必须去除政治上的蒙昧。正因如此,作品才有深刻的意蕴,才有厚重之感。如果这“启蒙”只是在文化上,没有政治上的目标,那么这启蒙就显得目光短浅。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表现出的是文学对政治理性的渴求,这是拥抱政治的文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20世纪4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后期的工农兵文学,都是阶级文学。而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他们所进行的并不是“个人写作”,而是“阶级写作”[20]56,作品是直接宣传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政策的,“它虽然有重要的文学失误,但不可否认也做出了重要的艺术贡献”[21]106。这一文学表现出文学对政治的依附,是以政治为指令的文学。
这些都证明了“文学需要政治”的确是中国文学的传统。然而这一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之后,开始受到质疑以至排斥。一些人执意从事“反其道而行之”的“纯文学”的创作,一些人在创作以搞笑为目的、没有政治和道德意识的小品和相声;在学术界,早就有人讥讽工农兵文学是“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22]67。而在近年,更是有人因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指责《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23]5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政治的最高境界是政治信仰。“政治信仰是意识形态的主导成分之一”[24]27,它不但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理想,同时也影响着一个人的文学观念。当今我国创作界和学术界,有一些人正是失却了政治的信仰,才产生了他们对政治的淡漠。这不但压抑了他们表达政治意识的欲望,并且促成了他们对政治的反感。
(二)关于文学所需要的政治环境和正确的政治方向
上面说过,文学需要政治提供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当然,好的文学,需要政治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只有具备宽容的政治氛围,坚决去除行政对文学的管控,大力开展文学批评和文学讨论,我们的文学事业才能繁荣发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作家们还得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18]69在阶级社会特别是在战争的年代里,这话有相当的准确性。在当下不提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们可以不提文学的阶级性,但要提文学的人民性。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因此,任何国家提出文学“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是没有错的。坚持文学的人民性,这是我们文学正确的方向。只有具有人民性的作品,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作品才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中外能够留存下来的名著,都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不具有人民性的作品,是会被历史抛弃的。因此,即使是在西方,一些清醒的学者也说:“知识分子必须尽快回到人民中间为他空着的位置上。”[8]274
(三)关于表达政治的样式的多样化
说“文学需要政治”,就要思考该怎样表现政治。在中外文学史上,存在两种表现政治的样式:一种是直接展现政治斗争的过程和场面,另一种是描写非政治斗争场景而间接表达作家的政治意识。前一种谓之政治斗争文学,后一种谓之政治倾向文学。以往的中国文学以及西方文学,所呈现的就是这两种样式。作为政治斗争文学的我国建国前和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的工农兵文学,绝大多数作品按照一种规范去描写政治斗争的过程,结果造成文学作品的类型化和趋同化,严重影响了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但其中也有例外,这就是艾青和孙犁,前者以自己的“私情”(对人民的感激之情)来对接“为工农兵”的大方向,后者在“为工农兵”的大方向下,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照日常生活)和审美理想(追求真善美)来构思作品,所以他们的诗歌和小说在工农兵文学中别开生面,受到广大读者特别的欢迎和喜爱。同样,同是政治倾向文学,巴尔扎克专事于描写“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点的资产者,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发家史”[25]128,体现出作者眼光的犀利和笔力的深邃;屠格涅夫的《罗亭》则着力塑造作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多余的人”的形象,表现“作者对罗亭们的悲剧命运十分惋惜”[25]210,散发出沉重的艺术气息;而易卜生却是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剧”中,“揭发了资产阶级的伪善和守旧”[25]245,嘲讽的意味浓厚…… 因此,一位西方学者说:“人们有时希望更加尊重事物的复杂性。”[26]306的确如此,文学的描写对象即生活是复杂多样的,因而文学表达政治的样式也应该是复杂多样的。
西方一位评论家的这句话值得人们思考:“艺术品只有作为自主的作品,才能在政治上达到目的。”[8]285政治倾向文学如此,政治斗争文学亦然。自主性是必须的,而“自主”,就是“把社会责任与最大限度的个人独创性结合起来。”[27]339独创性,也只有独创性,才是“文学表达政治”的多样性的保证。
(四)关于不同的思想感悟
同是描写政治,同是表达政治意识,还是可以有不同的具体的思想感悟的。比如西方,同是从政治上批判资产阶级,司汤达通过于连“个人奋斗、孤芳自赏、远离人民,最终走上一条依附统治阶级的可耻道路”这一故事,表现出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认识;巴尔扎克通过老葛朗台绝不让女儿去爱一个破了产的查理(《欧也妮·葛朗台》)、塞西儿在婚事中感兴趣的只是对方的财产(《邦斯舅舅》)这些人物和情节,表现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散发着铜臭味”[12]275的感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则通过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者的海尔茂“不允许妻子娜拉在家庭生活中有任何发言权,一切由他摆布和决定”[12]446这一生活情态,表现出作家对资产阶级不平等家庭关系的认识,以及需要“解放妇女,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12]443的思想……
如同一位理论家所说:“社会主义作家、艺术家的责任是巨大的。他们为完成这个责任,要靠党把他们看成人,看成思想独立的人。”[27]341而思想独立,就要表达出个人独特的思想感悟,这是必须的。
(五)关于审察政治的眼光和表达政治的角度
“文学需要政治”,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而“要怎样描写政治”,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从中外文学史看,选择审察政治的眼光和表现政治生活的角度至为关键。问世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这一政治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三里湾》和《创业史》,前者采用的是政治视角,中者采用的是生活视角,而后者采用的是则是文化视角。结果,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就大不相同:前者停留在政治的层面,失却了深刻和厚重,只能成为“具有感染力的政治宣传品”;中者给人以亲切感,是一部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而后者则给人以文化的厚重感和历史感,算得上艺术含量高的文学作品。我们说“文学需要政治”,绝非是要创作者停留在政治的层面上,而是要有文化的眼光,即从文化的视角来审察和描写政治,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政治,要在作品中表现出:政治不只是“政治”,更是一种“文化”。这才是对“文学需要政治”的正确理解。
[1]王波.什么是政治[EB//OL].(2008-07-25).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dPoGfmJ7BLOCYHe FOL2y9Rih3ZwHwRYTGUPFXk-pcMI0brVh95aqYX z7x4eb6ian1zFVZsPeIwWKtNSP5zYyFfNPJ-gkDN-voiVu1lSD9Zm.
[2]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
[3]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C]//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70.
[4]朱立元.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概况的调查报告[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73.
[5][德]泰·阿多尔诺.美学理论[C]//陆梅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355.
[6]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C]//王逢振.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92.
[7][美]保罗·鲍威.文学批评在后现代世界中的作用[C]//王逢振.2002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88.
[8][德]赫.·马尔库塞.美学方面[C]//陆梅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265.
[9][加]琳达·哈钦.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C]//王逢振.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51
[10][加]莱思·芬德利.另一种观点:后现代主义与对抗历史[C]//王逢振.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84.
[11]刘江.对政治的惧怕和躲避——余秋雨文化散文论析[J].淮阴工学院学报,2014:26-30.
[12]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
[1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C]//北京大学中文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36.
[14]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C]//北京大学中文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75.
[1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C]//王逢振.2002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245.
[16]朱光潜.西方美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2.
[17]恩格斯.反杜林论[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20.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9]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C]//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20]刘江.文学社会学视域中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论[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4):55-59.
[21]刘江.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工农兵文学——对工农兵文学的总体评说[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103-108.
[22]董之林.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06(4):66-69.
[23]王彬彬.《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J].当代作家评论,2010(3):56-59.
[24]井中雪.论政治信仰[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27-30.
[25]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欧洲文学史(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6][奥]恩·费歇尔.现代艺术的真实问题[C]// 陆梅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306.
[27][奥]恩·费歇尔.艺术与思想的上层建筑[C]//陆梅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