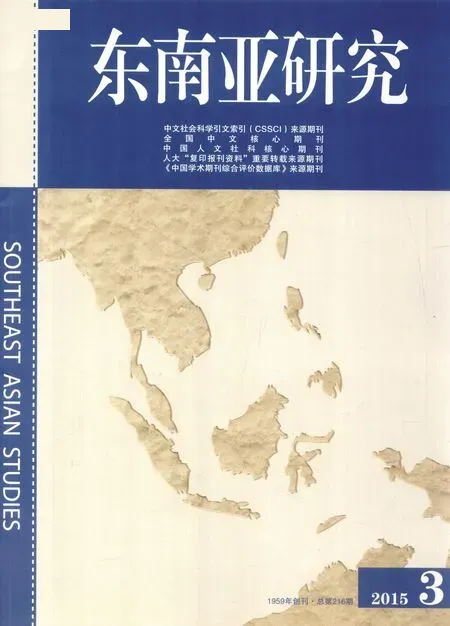19 世纪中叶赴美合同制华工与赊单制华工的比较
2015-03-30曹雨
曹 雨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广州510630)
随着19 世纪奴隶贸易的逐步废除,在奴隶制基础上建立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受到巨大的挑战,除了部分奴隶转化为受薪的雇佣工人以外,殖民地官员和奴隶主们被迫寻找新的廉价劳动力来替代奴隶,以维系经济体系的正常运作。由于亚洲国家有着非常丰厚的劳动力资源,欧洲殖民者们开始着眼于将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用来补充殖民地的劳工。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劳务契约移民被大量地输送到加勒比海殖民地和其他一些原先并未使用非洲奴工的殖民地。劳务契约移民的具体数字很难考证,因为大多数接收这些移民的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完整的资料记录这些劳工移民,对契约劳工的定义有时也是模糊的,而且这些劳工是自愿还是被迫签订契约则更是难以考据。但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契约劳工的工期与奴隶制不同,并非终身制。从1830 到1930年,大约有3000 万印度人成为契约劳工,其中有2400 万人最终回到了印度。从中国征募的契约劳工人数大致与印度相当,但是中国劳工中的女性人数更少。从整体数字来看,未回到故土的印度契约劳工大约为500 万,而中国劳工大约有700 万[1]。
在英语学术界,契约劳工一般被称为Indenture Labor,但在19 世纪中后期的英语国家通常也将他们称为Coolie。Coolie 一词最早见于官方文书是在美国1862年的《反苦力法》(Anti-Coolie Act),中文译为“苦力”,粤语称为“咕喱”。在当时语境下这一词语带有贬义,如19 世纪70年代美国加州排华风潮中经常以这一词语形容廉价的中国劳工,强调他们对白人形成威胁和带来不平等竞争。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此词来自印地语的“kuli”,原意和中文的“短工”相近[2]。在19 世纪,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劳工经常被泛称为“Coolie”。
一 契约华工及其分类
关于契约华工的研究,在20 世纪80年代以前,受国内政治左倾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学者在讨论契约华工问题时过于强调“猪仔”,认为契约华工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劳动力的主要方式”, “契约华工事实上已变成难于脱身的奴隶”[3]。猪仔贸易在美洲大陆仅限于古巴、秘鲁、夏威夷群岛、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牙买加。中国到美洲“猪仔”贸易活动的猖獗时间大约有27年左右,即1847年古巴首次有华工登陆,到1874年澳门全面禁止“猪仔馆”。20 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已经将非自愿的“猪仔”与大致上自愿的契约华工进行了区分,主要依据是华工出洋方式的历史分期演变,如王启民在《契约华工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就认为把“猪仔”与契约华工等同是不精确的,“猪仔”是契约华工中的一类,契约华工还有其它类型[4]。吴凤斌在《有关契约劳工的几个问题》中已经提出契约华工出洋的方式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以“猪仔”概称华工是不合适的,应予以区分[5]。
对“猪仔”一词的滥用既无视契约华工自愿出洋的史实,也掩盖了南方沿海地区在接触西方国家后社会经济层面出现的积极变化。实际上很多契约华工并不是悲惨的奴隶,而是具有探索精神的移民先驱,广东省也并非单纯遭受西方势力荼毒的地区,而是主动向近代化社会探索发展的地区。
吴凤斌将契约华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近乎奴隶制的契约华工,其二为债奴制的契约华工,其三为雇佣制的契约华工,但文章中也出现了“赊单苦力”这样的提法[6]。彭家礼在《中国大百科》的“契约华工”词条中称美国的赊单制也属于苦力[7];陆国骏在《美洲华侨史话》一书中也称赊单工为“隐蔽的劳役奴隶”,认为他们同其它地区的契约华工一样[8]。冈瑟·巴斯 (Gunther Barth)在《苦涩的力量》一文中也强调当时美国所盛行的赊单制与别的劳务合同制度并无二致,甚至离奴隶制也相去不远[9]。大卫·格兰森(David Galenson)在《美国契约劳工制的兴亡》一文中首次指出赴美华工并非一般的契约劳工,但不确定华工是否能够在还清债务之后成为自由人,也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够自由地选择雇主。但他同时也提到大多数当代美国学者认为这些华工仍然受到强制劳务合同的有效制约,只不过由于《反苦力法》的限制,不能明文写下强制的合约条款[10]。美国学者的这种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前驻华公使熙华德(George F.Seward)所撰的《中国移民:社会经济方面》一书。席沃猜测当时的华工中仍存在某种密约规定了强制的劳动期限,但由于《反苦力法》的限制而没有明文记载下来[11]。后世的美国学者基本继承了席沃的观点,如夏洛特·埃里克森(Charlotte Erickson)的《美国工业与欧洲移民》一文持有同样的观点[12]。艾莫·山德梅耶尔(Elmer Clarence Sandmeyer)在他著名的《加州排华运动》一书中也认为当时旧金山华人六大公司(Chinese Six Companies)①“六大公司”成立于1854年,当时华侨在加州成立之会馆已有6 所,遂联同主办洋务,1862年易名为“中华公所”。隐瞒了引进华工时的真实契约条款[13]。但即便是在席沃所处的1881年,也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赴美华工受到违背《反苦力法》的强制性合同的约束。笔者认为美国学者的这种猜测很可能来自于对华工的刻板印象,而在中文的资料中也没有发现可以证明华工与债主之间存在强制雇佣关系的合同。
在许多记叙或论述华工出洋历史的文献中,非自愿的“猪仔”贸易和自愿的契约劳工的区分通常是明确的,但对于自愿的契约劳工中的赊单制和劳务合同制则没有明确的划分,中文论著中往往通称为“苦力”。而在英文论著中,则多认为华工的赊单制只是为了规避美国的《反苦力法》而做的表面文章,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是带有强制劳动规定的,华工的人身自由仍然受到债主的限制。乔治·席沃、艾莫·山德梅耶尔、夏洛特·埃里克森、冈瑟·巴斯的文章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仅有大卫·格兰森认为尚无明确的证据证明华工受到强制劳务合同的制约,赊单制若真如其条款所规定,则并不属于劳务契约范畴,但缺乏记录证明赊单制的条款是否真实有效。
实际上,根据美国1862年的《反苦力法》,“苦力”的定义是债务合同与为期超过一年的劳务合同捆绑情况下的契约劳工,所以赊单制华工并不在此限,因此赊单制应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出洋务工情况,不应与劳务合同制混同,更不应被称为“苦力”。值得注意的是赊单制在19 世纪末期的广东实践的过程中,催生了带有金融信贷性质的商行,完全独立于劳务经纪。因此笔者认为自愿出洋务工所签订的劳务合同和赊单合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出洋方式,有必要作明确的区分。
赊单制发端的时间难以考证,可以明确的是18 世纪末到19 世纪中在英属马来亚地区即已流行,由于在船票票面上注明船费赊欠故称“赊单”[14]。但马来亚华人劳工借贷船费的合同与劳务合同是否有关联则尚不明确。中文“赊单”一词强调赊欠,而英文的对应词汇“Credit-Ticket”则强调信贷,中英文表述稍有偏差,本文中提及“赊单”一词偏重英文表述的含义,即强调其信贷特征。
本文主要讨论美国本土和夏威夷群岛①1898年美国正式将夏威夷群岛并入美国领土,1893年前为夏威夷王国,1894 至1898年期间为夏威夷共和国。的契约华工,对契约华工的类型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所以本文分析重点是契约华工中的合同制类型和赊单制类型的比较。合同制劳工盛行于当时英属和荷属亚洲殖民地以及夏威夷,在美国也有过实践。合同制劳工是自愿出洋,且签订了一定期限的务工合同,并由雇主代付旅费,在合同期限内人身自由受限制,但完成合同后即成为自由身。美国的合同制劳工往往会毁约逃跑,对雇主不利。赊单制劳工也是自愿出洋,由一些组织或个人代付旅费出洋,也有些人筹款自付旅费出洋,出洋后自由务工,偿清债务后由旧金山华人六大公司或其他华人组织开出放行纸,可以自由选择留在国外或是回国。
二 合同制华工:债务合同与劳务合同绑定的劳工
合同制劳工作为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契约劳工的一种,在许多文献中经常与赊单劳工并称为契约劳工,但实际操作上与赊单劳工有明显的不同,其契约条款的执行带有强制性质,劳工不能按照其个人意愿更换雇主。合同制劳工的契约条款并不基于信用,而是基于对劳工的人身控制,劳工出洋的债务合同与务工劳动合同是有连带关系的。债务合同与务工劳务合同之间是否有连带关系或者是否可以相互转嫁,可以说是赊单制与合同制的最根本区别。从带有人身限制的角度说,合同制劳工与卖猪仔有共同之处。但是合同制劳工是劳工自愿签订的,并不是受掳掠或是欺骗而被迫签订的,所以又与卖猪仔有明显的不同。从赴美华工的案例来看,这种性质的合同往往难以保障雇主的权益。
在早期广东人赴美的经历中,尤其在19 世纪40年代后期和19 世纪50年代,确有一些人以合同制劳工的形式来到美国。1848年3月6日,查尔斯·季乐派 (Charles V.Gillespie)在给托马斯·拉金(Thomas Larkin)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他引进中国合同制劳工的经历:“我喜欢的项目是把中国移民引进这个国家,不论他们是商人、农民还是佣人,也不论数量。他们本愿在一定期限内出售他们的劳力,以支付他们跨太平洋的旅费……我从中国带来的15 个劳工,本来受两年合约的限制,上岸后没多久就开始抵制合约,分别自找活计,没有人愿意管这种事。”[15]1852年,州参议员乔治·廷格雷(George B.Tingley)在加州立法院提案讨论让强制执行合同成为可能,中国劳工可以固定薪资签订少于十年的劳工合同,此议案由于受到极大的舆论阻力而未获通过。1852 后的数年中,一些中国社团和公司采用合同制劳工的形式来引进劳工,但都由于无法强制执行合同,因劳工毁约而遭受经济损失,因此合同制劳工这种形式在加州无法继续。
合同制劳工在加州不能有效施行的原因有三:一是加州的自由气氛使得限制劳工的人身自由既不合法也不可能。在美国南北严重对立的大历史背景下,加州社会对于任何接近奴役的制度都保持高度警惕的态度,任何使得加州向奴隶制靠近的举措都不太可能实施。二是当时加州劳动力亟缺,加州大部分就业岗位的工资都高于美国东部各州,有些岗位甚至可以拿到三倍于东部相同岗位的工资,对于合同制华工来说,毁约的代价小而报酬高。三是赴美的华工经济条件较好,基本上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大多来自于广东省最发达的三邑和四邑地区,要这些人忍气吞声地接受强制劳务合同是比较困难的。
合同制劳工在夏威夷群岛的实施要较美国更为顺利和广泛,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即在开设农场后不久从事过劳工经纪。孙眉的墓志铭这样写道:“未几以道川公命归娶,乃于故里复有移民事务所之设,一时应者风驰景从,更租轮舶以资还往。于是群岛皆辟……”[16]孙眉归国娶妻大约在1875年前后,因此其移民事务所应该大约同时设立。需要注意的是,夏威夷直到1898年才并入美国,成为美国领土,因此,此时在夏威夷的华工贸易严格来说并不能算作美国华工历史的一部分。夏威夷群岛处于热带,甘蔗种植和稻米种植是极具利润的投资,而这两种种植园都需要大批劳工,由于其劳动之艰辛,强制性合同便有存在的必要。在当时的夏威夷,引进华工最多的企业是香山人陈芳所设立的芳植记,在1852年至1876年期间,招募了1800 名华工,其中大部分进入了他的甘蔗种植园工作[17]。夏威夷群岛合同制劳工能够维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夏威夷政府乐见华商引进华工,不但合法而且还鼓励,与加州的情况迥异。另一个原因是夏威夷群岛的经济比较单一,劳工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因此不太可能违约。在1898年夏威夷并入美国后,美国1882年的排华法案适用地域延伸到夏威夷,阻断了华人向夏威夷移民的进程。
三 赊单制华工:拥有较大自由度的劳工
19 世纪中叶赴美华工主力来自广东珠三角地区,即以广府人为主,主流的出洋方式是赊单劳工制(Credit-Ticket System),而非卖猪仔和合同制劳工。在淘金潮的早期,确有极少的合同制劳工来到美国,但由于加州对合同制劳工的强力反对,强制性劳工合同也无法在美国执行,这种赴美方式无法继续进行,因此这部分人不应当被视作苦力,尽管当时很多媒体和排华人士仍然称呼华工为苦力。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美国船只运载苦力劳工的法令[18],但需注意夏威夷当时并未并入美国领土,不在此法令管辖范围内。赴美华工以赊单劳工为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广府人在移民目的地选择上的优越地位,比之经常被卖作“猪仔”的客家人,他们能以赊单劳工的身份前往生活和劳动条件较好的加州。以赊单制方式输入华工的地方除了加州以外,还有夏威夷、英属哥伦比亚(加拿大卑诗省)和澳大利亚。
赊单制劳工体系在加州的实践,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从旧金山华人六大公司在1862年针对《反苦力法》辩论过程中的指责而发表的自辩声明来看,至少在1853年以后赊单劳工成为了赴美华工的主流[19],但在1862年之前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强制性的合同劳工在1862年前仍为合法。1862年4月26日通过的《反苦力法》主要针对带有强制性质合同制的中国劳工,使得原本盛行的带有人身限制的合同制劳工在美国成为非法[20]。这就使得当时在加州引进华工的经纪人必须采用赊单制来输入华工。赊单劳工所签订的合同并不规定劳务期限,只要还清债务即为自由身,可归国,亦可留在当地。当时旧金山的华人六大公司负责核实劳工是否清偿债务,并发出放行纸。劳工经纪一般会预先为华工支付旅费,横跨太平洋的旅费大约为50 美元,另加约20 美元的其他杂费。华工赴美之后每月偿还债务,并支付利息,具体支付的数额不等,但其中应存在高利贷的情况,从某些个案来看劳工支付的本息总额可达200 美元[21]。
从赊单制劳工体系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广府人劳工在中国至少具备一定程度的家产和财富,或者有富裕的宗亲为之担保,否则基于资产和信用的赊单出洋方式无法对他们产生约束力。赊单制的约束力还体现在归国船票上,由于经纪人与轮船公司达成协议,没有放行纸的华工是不能登船回国的。在美国铁路建设期间,工资的发放往往要经过华人工头,而这些工头通常由六大公司派出,因此他们往往在给华工发放工资前便预先扣除了应还的赊单本息。另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家冈瑟·巴斯也认为华人社团和在华的宗亲势力有可能对华工本人或其家人施以暴力威胁,但这种猜测尚缺乏证据。冈瑟·巴斯认为赊单劳工体系的执行仍然带有某种强迫性质,因此“仍是一种露骨的奴工贸易”[22]。但芝加哥大学的大卫·格兰森则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他认为冈瑟·巴斯主观地夸大了赊单体系中的强制因素,他认为“虽然赊单体系下的华工并非是完全自由的移民,但这种体系仍然给予了华工相当大的选择权力,并且从一开始便是自愿的”[23]。
赊单制劳工说到底是一种信贷行为,基于债务人的偿还能力和他的信用担保而得以运行,在美国华人中这种出洋方式是最为盛行的。从人道层面上来说,这种出洋方式给予移民最大的自由和尊严,他不再被限定于要为谁工作,虽然在还款和归国的自由上受到限制,但与卖猪仔和合同制劳工相比,其文明程度较高,当然也需要有成熟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资本运作给予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广府人出洋的这种方式恰恰证明他们自由的个性和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他们是投机者和冒险者,是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9 世纪的广府地区并不是饥寒交迫的落后地区,而是受到西方经济深刻影响的、充满市场活力的地区。
结论
契约华工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出洋方式各有不同,但总体来说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成分,所以后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往往将其与奴隶劳工体制并称。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出洋,可以肯定的是,华工在出洋之前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其所往目的地的具体情况,在信息的获取上与雇主和放贷人相比是不对称的,而当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后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人身限制,且不能自由地返回故乡。就算是在务工和生活条件最好的美国,虽然受到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保护,华工们仍然受到来自雇主、华人会馆和放贷人的三重剥削。契约劳工制度的存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种植园对劳动力有着不断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奴隶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中止,由此笔者认为契约劳工制是介于奴工制和现代劳工制之间的一种过渡。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美国社会环境的推动下契约劳工制出现的变化,从带有强制性的劳工合同制到拥有较大自由度的赊单制,从人身被控制的劳工合同到带有信贷性质的赊单制。而19 世纪中期的广东省作为契约华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也体现出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经济活动频繁的珠三角地区有着广泛的对外贸易经验,身处这一地区的广府人对于外界的了解较多,很多人自愿前往外国工作,美洲和大洋洲又存在着对劳工的巨大需求,各种劳工经纪以及连带的担保、金融机构应运而生。例如香港的“金山庄”,他们一方面从事劳工经纪和担保业务,另一方面也进行跨太平洋贸易:自办货物、代客买卖、从事汇兑业务。从这个角度来看,赊单劳工体系也催动了珠三角地区华商金融信贷体系的发展。与赊单制相比,合同劳工制由于其对劳工人身的限制,在经济上对连带产业的发展并没有明显的催动。我们可以从19 世纪末期这两种出洋方式的此消彼长上看出,华工逐渐摆脱人身控制而转向基于信贷的契约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出珠三角核心地区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上逐步带动周边地区以至于广东省内其它地区的发展模式。在中西交流的历史上,作为中国率先接触西方的地区,广东社会在应对西方全球殖民贸易体系时表现出自我的调节和完善,并逐步发展出一套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方法,也充分体现在劳工出洋方式的演变上。
【注 释】
[1]Russell King,The Atlas of Human Migration:Global Patterns of People on the Move,Earthscan,2010,pp.33 -35.
[2]Encyclopedia Britannica,“Coolie”,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136194/coolie,2015-01-02.
[3]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历史研究》1963年第1 期。
[4]王启民:《契约华工制的历史分期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 期。
[5]吴凤斌:《有关契约华工的几个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9年第2 期。
[6]吴凤斌:《契约华工演变浅析》,《南洋问题研究》1986年第4 期。
[7]彭家礼:《契约华工》,中国大百科,http://ecph.cnki.net/,2015 -01 -02。
[8]陆国骏:《美洲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9 页。
[9]Gunther Barth,“Bitter Strength: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1850 -1870”,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Vol.45,No.4,1966,pp.354 -357.
[10]David Galenson,“The Rise and Fall of Indentured Servitude in the Americas:An Economic Analysis”,Engerman,S.L.ed.,Trad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00 -1850,Cheltenham,U.K.:Elgar,1996,pp.31 -56.
[11]George F.Seward,Chinese Immigration in Its Social and Economical Aspect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81,p.138.
[12]Charlotte Erickson,“American Industry and the European Immigrant,1860 -1885”,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27,No.1,1961,pp.120 -122.
[13]Elmer Clarence Sandmeyer,The Ani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p.14.
[14]同[6]。
[15]Thomas O.Larkin,The Larkin Papers Vol.VII,1847-1848,George P.Hammond e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0,pp.167 -169.
[16]汪兆铭:《孙眉墓表》,1935年4月。
[17]周南京: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0 页。
[18]H.Russell Conwell,Why and How the Chinese Emigrate,Boston,1871,pp.103 -106.
[19]National Archives,“Teaching with Documents:Affidavit and Flyers from the Chinese Boycott Case”,http://www.archives.gov/education/lessons/chinese-boycott/,2015-04 -26.
[20]David Northrup,Indentured Labor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1834-192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05.
[21]M.Lucy Cohen,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A People Without History,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4,p.28.
[22]Gunther Barth,“Bitter Strength: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1850 -1870”,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1966,Vol.45,No.4,pp.354 -357.
[23]Patricia Cloud & David W.Galenson,“Chinese Immigration and Contract Labor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1987,Vol.24,No.1,pp.2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