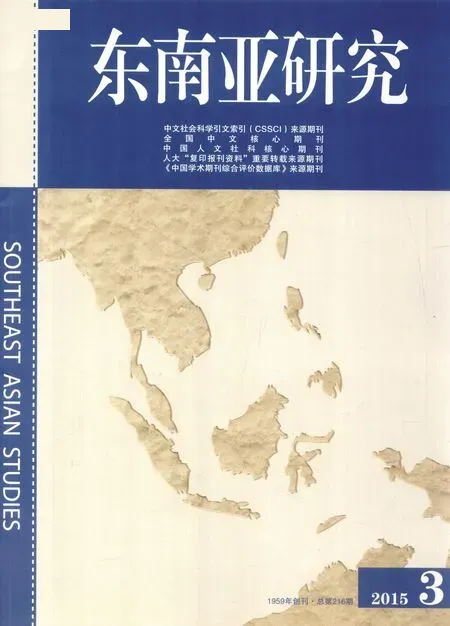印度尼西亚与南海海上安全机制建设
2015-06-17郑先武
李 峰 郑先武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南京210093;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南京210093)
后冷战时代,南海海上安全机制建设是南海相关国家塑造区域安全地位的战略重点。同时,印尼也不断谋求进而巩固着其作为东南亚区域大国的地位,并在建构区域安全机制的过程中试图成为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的核心。由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所具有的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与东盟方式等特点,以及域外大国在东南亚高度渗透的现实,东盟安全机制、域外大国主导的安全机制就构成了东南亚区域安全机制的两个主要方面,已有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两方面进行独立或关联的分析①代表性研究如刘相骏:《冷战后东盟安全机制的初步分析》,《当代亚太》2004年第12 期;王磊、郑先武:《国家间协调与区域安全治理》,《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4 期;李文良:《东盟安全机制及其特点探究》,《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2 期;龚迎春:《日本与多边海上安全机制的构建》,《当代亚太》2006年第7 期;蔡鹏鸿:《试析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6 期;滕桂青:《南中国海问题的外部因素及其对区域安全机制的影响》,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等等。,而对印尼在海上安全机制中的作用的学术研究尚属欠缺。本文基于案例研究“经验力度与检验数量最大化”的原则,通过对“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the Workshops on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以下简称“南海研讨会”)这一典型案例的剖析,揭示了印尼在谋求并巩固自身区域大国地位的进程中,以本国主导的海上安全机制建设来建构东南亚区域安全机制的一种路径。
一 南海海上安全机制建设与印尼的角色分析
南海具有跨区域的地缘政治及区域主义特征,又因其居世界海域之首的战略意义、地缘政治与经济价值[1],南海地区业已汇集了域内国家、周边国家、主要大国及其他海上航道使用国等全球众多国家的利益;相关各方在此又面临着非法捕捞、海上贩毒、海盗、海上武装抢劫、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20 世纪90年代后激化的南海主权争端则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所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南海因此成为全球安全威胁最复杂的海域以及安全机制的云集之地。这些海上安全机制因新区域主义下经济、安全与发展的密不可分,以及区域与全球的紧密联系而呈现出综合性与开放性等特征[2],糅合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指涉主权与海权、战略与安全、理论与实践等诸多方面[3]。南海海上安全机制因安全主客体、安全威胁、安全实现途径等界定标准的不同而纷繁复杂(见表1)。南海海上安全机制,按安全指涉对象性质的不同,主要包括全球安全机制、东盟安全机制、域内次区域双边安全机制、跨区域多边安全机制等四大类。按功能与目的的不同,可区分为安全保障机制与冲突管理机制两大类,其中后者包含冲突预防与冲突解决两大层面②以往南海海上安全机制的冲突管理功能主要侧重冲突预防,近年来,冲突解决的功能也逐渐被强化,典型的案例就是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兴起与发展,体现在从1996年《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到2004年《东盟促进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再到2010年《东盟宪章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的演进中,详见孙志煜《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兴起、演进与启示》,《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6 期。。按威胁性质的不同,可区分为传统安全机制与非传统安全机制。按行为主体的不同,可区分为政府间安全机制(“第一轨道”)、非官方安全机制(“第二轨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轨半”机制。按所涉领域及其特征不同,可大致区分为单一的法律规范、军事合作机制、技术合作机制、政治合作与协商机制等。相关海上安全机制具体表现为对话、规范、条约、国际组织等。鉴于此,本文对“南海海上安全机制”采取一种宽泛的界定,其“海上”意指一国领海以外的海域;其“安全”是实现“深化”与“拓宽”的“综合安全”③有关“安全”的定义参见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68 页。。海上安全机制即旨在使南海及邻接周边免于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系列条约、规范、制度等的统称。需要指出的是,海上安保(Maritime Safety)虽属于非传统安全机制范畴,但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海上安全机制之列④海上安保(Maritime Safety)意指船只、港口设施、近海设施的所有者、操作者及管理者以及其他海洋组织或海洋公司为防范未发生的及(或)最小化已发生的因船只质量问题、船员资质不达标或误操作引发的海上灾难或事故所采取的措施,如《国际船舶与港口设施安全准则》(ISPS)、《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等。详见Barry Desker,“Re-thinking the safety of navigation in the Malacca Strait”,in Kwa Chong Guan & John K.Skogan eds.,Maritime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London:Routledge,2007,pp.27 -38.。

表1 南海主要海上安全机制界定

(续上表)
作为南海地区的主要传统安全威胁,南海主权争端凸显于后冷战时期。这一时期域外大国主导的域外安全秩序对区域安全秩序的覆盖降级为渗透。与此同时,区域大国在区域整体安全秩序中的作用也因新区域主义的综合性、开放性、区域间性等核心特征而凸显,印尼逐渐在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中起到核心作用[4]。因而,南海争端凸显于印尼谋求区域大国、通联区域内外、统一区域秩序内外建构的关键时期。又因安全是区域秩序的核心,作为安全实现途径的安全机制的地位也就不言自明。南海主权争端因而成为印尼建构区域安全机制的核心关切。然而,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南海海上安全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安全威胁的界定及对策分析上,少数从安全机制视角探究南海问题的研究也主要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其应对。如蔡鹏鸿对美国主导的南海海上安全机制、跨区域多边合作安全机制等进行了分析①参见蔡鹏鸿《试析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6 期。;吴士存与邹克渊对南海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应对机制作了论述②参见Shicun Wu & Keyuan Zou eds.,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Regional Impl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shgate,2009.;乔舒亚·霍(Joshua H.Ho)分析了南海的海上航道安全机制③参见Joshua H.Ho,“The Security of Sea Lanes in Southeast Asia”,Asian Survey,Vol.46,No.4,2006,pp.558 -574;Joshua H.Ho,“Enhancing Safety,Security,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ingapore: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Vol.40,No.2,2009,pp.233 -247.。对于南海主权争端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争端本身的分析上,即落脚于对各方声索及其依据的分析论证、现状述评及解决路径等方面④有关南海争端本身论述的著作极为丰富,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Sam Bateman&Ralf Emmers eds.,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Sea:Towards a Cooperative Management Regime,Routledge,2009;Ralf Emmers,Geopolitics and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Routledge,2010;曹云华、鞠海龙主编《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1—2012)》,时事出版社,2012年;Wu Shicun,Solving Dispute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Chinese Perspective,Chandos Publishing,2013;曹云华、鞠海龙主编《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2—2013)》,时事出版社,2013年;吴士存:《南海争端的由来与发展》(修订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对印尼与南海海上安全的研究则主要是对印尼南海安全政策的阐释、对印尼在南海争端中调节作用的分析以及印尼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争端解决的历史研究等,常书对印尼南海政策的演变以及通过“南海研讨会”调解南海争端的作用进行了梳理①常书:《印度尼西亚南海政策的演变》,《国际资料信息》2011年第10 期。;鞠海龙在梳理印尼的安全政策史的基础上,分析了印尼在确保地区安全这一总纲上展现出的防止域外大国介入地区安全、与域内具有共同利益国家合作应对南海问题,同时逐步强化自身安全能力建设、展开适度安全合作的安全政策脉络②鞠海龙:《印度尼西亚海上安全政策及其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3 期。。因而,对印尼与南海安全机制建设的学术研究尚显不足。
本文以区域大国印尼对南海海上安全机制的建构为研究中心,并将安全机制置于区域安全秩序的范畴内。区域秩序建构指的是区域大国在实践中获得并保持这一区域身份从而建构区域秩序的过程,即它(们)基于本国的区域优势实力,在实践中协同国内政治、自我对区域秩序的目标、区域伙伴的态度及因应以及域外大国的认可和影响四者间关系,从而实现从区域内、外双向建构区域秩序。其中,区域秩序内部建构指的是,区域大国通过帝国(empire)、霸权(hegemony)与领导(leadership)等战略③“帝国”战略下,占支配地位的区域大国以自利为目的,以军事威慑甚至武力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与维持区域秩序的方式;“霸权”战略下,区域大国以自利为优先目标,兼顾区域共同利益,它可以恩威并施,因而又区分为仁慈霸权与强制霸权;“领导”战略下,区域大国以实现区域共同利益为首要目标,并通过合作方式加以实现,因行动倡导者的不同分为领导者发起型与追随者发起型。见Sandra Destradi,“Empire,Hegemony,and Leadership:Developing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Powers”,GIGA Working Paper,No.79,2008;Sandra Destradi,“Regional powers and their strategies:Empire,hegemony,and leadership”,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6,October 2010,pp.903 -930.,为区域提供多边机制、经济援助等国际公共产品;在作为核心的安全层面,区域大国通过发挥领导力(leadership)、管理力(custodianship)与保护力(protection),为区域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从而塑造区域安全秩序。具体而言, “领导力”意指区域大国诱使成员间合作以形成特定安全政策,实现共同目标;“管理力”意指区域大国积极管控业已生成的区域安全秩序,并维持其稳定;“保护力”意指区域大国确保区域安全秩序免受外来威胁。区域秩序的外部建构则指的是,区域大国通过自身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包括通过跨区域的安全合作重点建设区域安全管理力与保护力,从外部推动区域秩序的建构,同时也获得域外大国对本国区域大国身份的认可的过程。外部建构主要涉及“管理力”与“保护力”。安全机制则是上述三种安全能力共同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及实现途径,即安全机制是安全秩序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
印尼这种通联区域安全机制内外建构的地位体现在其所参与的东盟安全机制及独立主持的多边安全机制中。东盟安全机制意指确保东盟成员国之间实现国家安全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和规范”[5]。就结构而言,它包含内向与外向两部分,即东盟成员国间的安全机制以及旨在确保区域安全稳定的跨区域安全联系;就决策程序或运行模式而言,内向安全机制主要基于国家间协调的东盟方式,外向安全机制主要依靠大国平衡[6];就功能而言,它具有安全保障和冲突管理两大功能。印尼对东盟方式与大国平衡的产生与运作产生了关键作用,但又尚未在东盟外向安全机制中起领导作用。本文认为,印尼独立主持的多边安全机制是实践其安全战略、安全政策、区域主义和大国角色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其中的跨区域安全机制对印尼弥补自己在东盟外向安全机制中领导力不足有着重要作用。这种跨区域安全机制的典型就是印尼发起的“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国内外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南海研讨会”进程及其作用的述评上,对其作用的分析也主要针对南海争端本身④代表性研究参见张良福:《历次“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非正式讨论会述评》,《国际政治研究》1995年第1 期;Hasjim Djalal,“Indonesi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nitiative”,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Vol.32,No.2,2001,pp.97 -103;Hasjim Djalal,“The South China Sea:The long road towards peace and cooperation”,in Sam Bateman & Ralf Emmers eds.,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Sea:Towards a cooperative management regime,Routledge,2009,pp.175 -188;Yann-Huei Song,“The South China Sea Workshop Process and Taiwan's Participation”,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Vol.41,No.3,2010,pp.253 -269;常书:《印度尼西亚南海政策的演变》,《国际资料信息》2011年第10 期。。
本文以安全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指出,印尼主办的这一“第二轨道”机制本身综合了印尼的国家安全观、区域安全观以及南海争端特征,是其海上安全政策的实践过程与结果,构成了东南亚海上安全机制的协同补充,同时发挥着作为区域大国的印尼建构区域安全机制乃至秩序进程中的协同补充作用。文章以下部分即通过对印尼区域主义、海上安全政策、“南海研讨会”之间关联的分析,论证这种协同补充作用。
二 印尼的海上安全政策与南海争端
东南亚区域秩序的国家间特性决定了其区域安全机制建构中行为主体以国家间协调为主的主要特征,以国家为主所开展的区域安全互动建构了区域安全机制的主要方面。而“第二轨道”因具有传播社会化观念,参与制订合作规范,帮助培育集体认同和区域制度建设,促进安全共同体建设等的作用[7],对推动区域安全机制建构具有辅助功能。“第一轨道”与“第二轨道”是安全区域主义的主要构成。相关行为体的安全政策既是上述两大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亦是结果。一国的安全政策则通常由存在性安全威胁、安全主体对存在性威胁的感知以及安全主体的应对能力所塑造[8]。安全政策决定安全机制的产生与发展,后者同时又是前者的实施手段之一[9]。
海洋历来是印尼安危所系。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的严峻现实促使印尼重视海洋安全中的非传统安全层面。东南亚长期存在的海洋领土纷争使得印尼在谋求区域大国的进程中一直致力于化解与邻国的海洋争端,并时常在域内海洋争端中扮演调解者角色。20 世纪90年代后南海主权争端的凸显,则为印尼这个非声索国提供了谋求和强化区域大国地位的良机。调解域内国家与周边大国之间的南海领土主权争端,可以帮助印尼从安全管理力与保护力层面重点塑造本国区域大国身份中的安全能力,进而提高域内国家对其区域大国地位的认可。同时,南海及东南亚关键的战略地位、破碎的地缘政治特征使得该地区一直是域外大国竞相争逐的焦点,域外干涉与影响被印尼感知为本国及东南亚面临的又一重大安全威胁。存在性安全威胁来源的多元化、印尼国内社会破碎易损的特点以及决策者与决策集团对此类威胁的认知,促使海上安全成为印尼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决定了海上安全历来都从属于印尼区域主义与区域安全观[10]。从苏加诺“有指导的民主”到苏哈托的“新秩序”,再到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化,两次深刻的国内政治变革带来了印尼对外战略的转向,但印尼的对外政策也呈现明显的继承性,突出表现在其区域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中。苏加诺时期,印尼确立了“独立与积极”的外交理念,并在区域主义进程中将谋求区域大国地位与推动区域自主并行;虽然苏哈托任内印尼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但谋求区域大国地位与区域自主的基本理念在后苏哈托时代依旧延续了下来[11]。印尼先后通过实施从强制霸权到仁慈霸权再到区域领导的区域战略,意图谋求域内国家对本国作为区域大国的认可。而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化改革赋予了印尼外交决策的民主化以及外交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
如今,印尼的海上安全政策虽尚未形成体系,但也轮廓渐全,政策的延续性也脉络清晰。正如时任印尼国防部国防战略司总司长丹迪·苏森托(Dadi Susanto)曾指出的:“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安全内涵主要包括四大方面,它们分别是,为了实现国家综合安全目标,主要针对外部威胁而制定的地区防务战略;为了确保印度尼西亚国内安全,主要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等非传统安全内容制定的国家安全预防战略;为了保障公共安全而推行的防务改革战略以及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受侵犯而制定的防务赋权战略……印尼愿意在东盟地区论坛(ARF)的平台上,积极参与并推动亚洲发展‘信任建立机制’(CBM)、‘预防性外交机制’(PD)、‘冲突协调仲裁机制’ (CR)。”[12]印尼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明确表示将继承“独立与积极”的外交理念以及苏西洛任内确定的海上安全政策框架。他在竞选时的主张表明,加强海洋外交与建设海洋强国将是印尼接下来承担区域大国责任、彰显区域大国形象的主要途径之一,为此印尼将加快解决印尼边界问题,缓解大国之间在海洋上的敌对局势,并致力于推动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13]。所以,海上安全机制建设是印尼安全政策的固有内容。
在南海争端上,虽然印尼长期呈现一种暧昧的态度,但当南海争端凸显后,也积极主动担当南海争端调解者的角色。其中具首倡性、意在提升话语权的“南海研讨会”这一“第二轨道”机制可以提升印尼的区域安全管理力与保护力,影响东盟地区论坛、东盟等区域、跨区域组织内的安全议题走向,并强化印尼在相关组织内的领导地位,塑造其在区域与全球的和平大国形象等。拉尔夫·埃莫斯(Ralf Emmers)曾指出,南沙主权之争的烈度在21世纪头10年中相较于20 世纪90年代已明显降级,他将局势趋缓背后的成因总结为: (1)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的定位从“修正主义国家”变为“维持现状国家”; (2)中国在南海军力投送的减弱;(3)越南加入东盟强化了东南亚的联合与制衡能力;(4)相关声索国对各自国内民族主义的有效压制;(5)南海地区预期原油储量的下降; (6)美国对(直接)介入区域争端尚保持克制态度[14]。
本文进一步指出,后苏哈托时代印尼重拾区域大国身份并担当南海争端调解者角色是另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主要原因。正如鞠海龙教授所概括的,南海问题之于印尼有两大主要意义,一是鉴于自身安全防御能力不足而造成的主权所辖海域及战略航道的安全问题;二是南海问题长期存在而造成的潜在地区冲突问题。对于前者,印尼在完善自身防御能力的同时反对域外大国干预马六甲海峡;对于后者,则是通过主导“南海研讨会”等准官方论坛来施加影响力,推动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南海主权 争议 信 任 机 制[15]。哈 斯 吉 姆· 贾 拉 勒(Hasjim Djalal)指出,印尼管控南海潜在冲突的理念是:合作比对抗好,协商合作比准备斗争好。为达此目的,印尼主导的“南海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通过对话与沟通推动有关方面的互谅;二是通过营造尽可能有利的环境而鼓励有关方面寻求问题的解决;三是发展技术层面的具体合作,让每一方都愿意参与其中且应当有所作为[16]。因而就安全政策而言,印尼实践着对包括南海问题在内的东南亚秉持维持均势与区域自主并行的安全战略;以构建“东盟安全共同体”为政策取向;以建构安全规则、规范与制度为实施重点,尤其是多边安全框架;在已有实践中通过对安全行为准则、安全机制、信任建立措施三管齐下以实现上述目标。印尼主导“南海研讨会”是这种政策框架的直接体现。
三 “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进程梳理
“南海研讨会”是印尼针对南海争端而创设的,旨在通过信任建立措施来调解南海争端,迄今仍是唯一一个由南海争端六国七方共同参与的年度论坛[17]。“南海研讨会”由印尼前大使哈斯吉姆·贾拉勒发起,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第123 条对“闭海或半闭海”的规定为国际法基础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九部分“闭海或半闭海”下第123 条规定: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为此目的,这些国家应尽力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a)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b)协调行使和履行其在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方面的权利和义务;(c)协调其科学研究政策,并在适当情形下在该地区进行联合的科学研究方案;(d)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其他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其合作以推行本条的规定。详见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law/sea/los/article9.shtml,2015年1月25日。,通过非官方合作推动南海声索国间的合作与和解。“南海研讨会”秉持以下基本原则:(1)非正式原则。鉴于南海的敏感性,相关各方的政府官员须以私人身份赴会。 (2)非制度化原则。不设立永久的、组织化的秘书处,以分设于温哥华与雅加达的“南中国海非正式工作组”(The South China Sea Informal Working Group)暂行秘书处职能,主要负责会议筹备事宜。 (3)非国际化原则。为避免南海争端的国际化,主议程仅限于东盟十国及台海两岸,非南海相关国家或其他区域及全球组织的专业人士及志愿者可以参与业已制定的议程的实施。(4)循序渐进原则。为推动和解与合作,由简入繁地开展合作。贾拉勒指出, “南海研讨会”的主要目标有:寻求各方都能参与的合作领域以管控潜在冲突,发展信任建立措施以营造有利于争端解决的氛围,通过对话交换意见以促进互谅[18]。“南海研讨会”的主要架构包括:一是自1990年起每年在印尼各地举行的讨论会(workshops)。二是技术工作组会议(Technical Working Group Meeting-TWG Meeting),迄今为止已建立了五个技术组:海洋科学技术工作组(TWG on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海洋环境保护技术工作组(TWG on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航行、运输与通讯安全技术工作组(TWG on Safety of Navigation,Shipping and Communication),资源评估技术工作组(TWG on Resources Assessment),法律事项技术工作组(TWG on Legal Matters)。三是专家组会议(Group of Experts Meeting)。本文将迄今为止“南海研讨会”的发展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0年初至1992年上半年的初创期。该阶段主要通过举办第一届与第二届“南海研讨会”,以单一的讨论会创设了“南海研讨会”的初步架构,推动“南海研讨会”超越东盟,囊括中国,进入区域间层次;确立了合作的基本原则。1990年1月,印尼在巴厘岛试验性地举办了首届非正式的“南海研讨会”。与会国仅限于当时的东盟成员国,讨论范围包括领土主权争端、政治及安全议题、海洋科学研究与环境保护、航行安全、资源管理、合作机制建设以及非东盟成员国参与研讨会的问题等。印尼外长阿拉塔斯(Ali Alatas)声称印尼要做一个“诚实的掮客”。1991年7月,第二届“南海研讨会”在印尼万隆举行。与会方超越东盟范围,包括当时的东盟成员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中华台北身份与会)、越南、老挝等,阿拉塔斯在开幕致辞中进一步提出以合作共赢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讨论会最终确定了南海合作的“万隆六原则”,即(1)各方对领土和司法管辖权声索不应存有偏见,在此基础上探索在南海合作的空间; (2)此类合作可以包括:促进航行与通讯安全、打击海盗和武装抢劫、促进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保护和维持海洋环境、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打击海上贩毒。 (3)在领土声索重叠的区域,相关国家(地区)应考虑基于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包括信息交流与共同开发。 (4)南海的任何领土和司法管辖权争议应通过对话、协商等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5)不应使用武力来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之争。 (6)敦促争端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复杂化[19]。
第二阶段为1992年下半年至1996年的成型期。该阶段主要通过先后建立五个技术工作组,拓展并完善了“南海研讨会”的架构,确定了合作的具体领域,并开始试验性地由“协同国”(coordinator countries)牵头落实具体的合作项目。此外,最为关键的是确立了“南海研讨会”作为“第二轨道”的存在形式。1992年7月,第三届讨论会在印尼日惹召开, “万隆六原则”再次被确认;并决定建立资源评估和海洋科学研究两个技术工作组,以深入研究具体合作议题;会议还否决了设立秘书处的提议。次年两个技术工作组进入正式运行阶段。1993年8月,第四届研讨会在印尼泗水召开,讨论的重点落在业已成立的技术工作组范畴内,并决定通过“协同国”牵头专门议题的研究与合作;技术工作组数量也得到扩充,海洋环境保护技术工作组、法律事项技术工作组分别得以建立,还评估了建立航行、运输与通讯技术工作组的可行性。此外,“南海研讨会”还决定欢迎非南海周边国家与国际组织参与共同商定的计划草案的实施。会后发表的会议声明再次敦促各国保持克制态度,呼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在各国间建立信任,确认“南海研讨会”官方化尚为时过早,等等[20]。但1994年10月在印尼武吉丁宜举行的第五届讨论会上,阿拉塔斯再次建议成立秘书处,并邀请南中国海以外的国家、全球和地区组织参与具体合作项目,尤其是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遭到了与会中方人士的反对。1995年10月,第六届讨论会召开期间,在领土、管辖权、政治、安全等议题与技术合作事项中,与会方的兴趣与意愿明显偏向技术合作,截至当时海洋科学技术工作组的成效也最为明显[21]。
第三阶段为1996年底至2001年初的合作磨合期。此阶段的“南海研讨会”确定了以信任建立措施为施力方向,不再直接关注政治与领土主权等议题,而是通过试验性实施共同计划来推动合作。同时“南海研讨会”也遭遇了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1996年12月,第七届讨论会在印尼巴淡岛召开,此次讨论会的议题集中在探讨技术合作事项、共同商议确定的议项的实施以及南海行为准则(the code of conduct)等方面。1999年第十届讨论会在印尼茂物举行,“南海研讨会”突破性地同意在没有争议的印尼阿南巴斯群岛 (Anambas Islands)附近开展南海生物多样性联合调查活动(Anambas Exercise)这一试验性勘探。但就在2001年初,加拿大政府停止了对“南海研讨会”的经费支持,“南海研讨会”的前景堪忧[22]。
第四阶段为2001年3月至今的稳定发展期。“南海研讨会”再次确认会议“信任建立措施”的性质,并获得了持续稳定的财政支持,随着技术性合作的深入开展,其预防性外交特征逐渐凸显。在2001年初加拿大政府终止经费支持后,2001年3月第十一届讨论会在印尼珍加连举行。会议重申了继续推动“南海研讨会”的决心,再次确认了非正式、非制度、非国际化、循序渐进等基本原则及“第二轨道”的存在方式,重点致力于信任建立,并一致同意增开一次特别会议以力促继续合作。该年8月,特别会议在雅加达召开,会议肯定了业已进行的试验性勘探对推动合作与和解的重要性,再次强调“第二轨道”,建议避免探讨争议性、政治性及易导致分裂的议题,并特别建议筹措更多智库的建立与运行,提议设立一个由东南亚研究中心(Pusat Studi Asia Tenggara)执行的特别基金。“南海研讨会”得以成功挺过财政危机。2002年的第十二届讨论会确定阿南巴斯群岛附近的南海生物多样性联合调查活动所需经费通过与会方捐赠的方式来筹集,试验性勘探得以成功落实[23]。2003年9月,第十三届讨论会在印尼棉兰举行,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巴拉望生物多样性勘探计划” (Palawan Biodiversity Expedition Plan)的可行性,此举将作为对此前阿南巴斯群岛勘探的延续与深入;讨论了由中国、印尼及菲律宾分别牵头协同“数据信息交换与网络建设”、 “海平面与海潮监测项目”和“海洋生态系统监测培训计划”的研究与实施;还进一步讨论了特别基金的设立问题。2004年特别基金正式成立。2004年9月与2005年10月,中国分别在海南和天津召开了数据交换与网络建设的会议。“协同国”牵头的合作得到了第十五届“南海研讨会”的高度肯定[24]。2008年11月,第十八届讨论会在印尼万鸦老举行,台海两岸首次同意在下一届“南海研讨会”召开前共同提交一份提案。2009年11月在印尼孟加锡举行的第十九届讨论会通过了两岸联合提出的举办“海洋教育培训”的项目建议[25],该项目为期2年,分别由台湾与大陆于2010年和2011年出资举办。这被视为南海信任建立与合作的一个新里程碑。自此,中国与“南海研讨会”的互动更趋积极,2012年与2013年,中国南海研究院与印度尼西亚东南亚研究中心签署谅解备忘录,成功联合举办这两年的“南海研讨会”[26]。
四 “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与印尼海上安全机制建设
“南海研讨会”业已显现出明显的区域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首先体现在信任建立措施的框架内。其一,“南海研讨会”所秉持的非正式、非制度化、非国际化与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已得到与会各方学界及官方的肯定,尤其与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基本契合。相关各方的肯定是“南海研讨会”信任建立措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区域间性质是其价值实现的关键。其二,“南海研讨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法律与政策协调以及海洋科学研究信息与数据交换等诸多方面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具体合作,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海洋科学与海上能源及资源合作被认为是南海共同开发的关键突破口[27]。这些合作以利益共享为基础,带有明显的区域间性质,这将为今后可能的南海共同开发奠定组织基础,积累模式经验[28]。其三,作为多边架构的“南海研讨会”对推动双边对话与合作,促成正式的双边行为准则产生了实际影响。如中越在“南海研讨会”内的对话推动了《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的签署。越南与印尼在“南海研讨会”内的对话则影响了两国在纳土纳群岛以北大陆架的划界[29]。
“南海研讨会”的另一大区域影响力表现在其与其他南海海上安全机制的协同补充效应上,这种协同补充既是内容上的,也是程序上的。此外,这种协同补充对于印尼在东盟框架内外塑造本国在区域安全机制中的主导性,强化印尼的区域大国地位同样具有协同补充作用。首先,苏哈托执政的最后10年,印尼的外交政策渐趋积极,并逐渐构筑起相对完整的安全政策网络,即以大国平衡及安全国际化为基础,主要围绕“东盟安全共同体”这一多边框架,辅之以独立的双边安全机制及主导性的东盟外多边安全机制。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安全机制中,无论是“东盟10 +1”、 “东盟10 +3”,亦或是东盟地区论坛,南海争端都只作为其中的一项议题存在。“南海研讨会”则具有明显针对性,同时又延续了以东盟国家为一方平衡制约作为另一方的中国的均势意义,从而对印尼构筑安全机制起到重要补充。“南海研讨会”所确立的“万隆六原则”及对“南海行为准则”的探索,直接影响了1992年《东盟南海宣言》(《马尼拉宣言》)以及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进程与内容,对确立上述宣言中的合作领域、通过磋商提升互谅等方面影响明显。
其次,“南海研讨会”的运作开启了南海问题“第二轨道”建设,直接影响了东盟的“第二轨道”外交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与运行。成立于1994年的东盟地区论坛秉持协商一致与渐进性的基本原则,同样也不设置固定秘书处。1995年起设立的东盟地区论坛会间会(ISM)是“第一轨道”架构中具有信任建立措施与预防外交等专门功能的会间会,为此提供辅助支撑的则是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ASEAN-ISIS)与亚太安全理事会(CSCAP)构成的“第二轨道”,它们同样主要以研讨会方式展开活动[30]。在原则与架构之外,东盟地区论坛对自身进程的规划与对海洋安全合作的界定同样明显受到“南海研讨会”的影响,1995年通过的《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A Concept Paper)将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阶段依次规划为确立信任建立措施、发展预防性外交机制以及发展冲突解决机制三个阶段。该文件附件中对海洋安全合作领域的界定则囊括了海平面与气候变化监测、海上环境维护、探索合作性海洋科学研究等方面[31],“南海研讨会”建设重点的偏转及技术工作组的分工无疑对此产生了实际影响。因而,“南海研讨会”从进程与内容上深刻影响了东盟安全机制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对后者构成了超越被动依附的协同补充关系;即使在东盟地区论坛及东盟“第二轨道”渐趋成熟的现在,“南海研讨会”与会方仍旧肯定了其继续存在的价值。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南海研讨会”可视为印尼谋求与巩固区域大国身份并建构区域安全机制的重要工具。印尼有意塑造一种“南海研讨会模式”,以凸显本国的区域大国地位,该“模式”的基点是印尼“独立与积极”的外交理念与区域自主的区域合作观。在此基础上,印尼实质上通过以区域国家间的协商为基础,以分别牵头协调的“协调国”方式推动共同利益的增聚,并以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为政治和解的突破口,同时避免争议问题进入协商与合作的议程,谋求合作与互谅的互补,并将域外因素定位并建构为参与性与协作性的建设性力量,从而在强化信任建立措施的同时,从内外双向彰显本国的区域领导地位。首先,“南海研讨会”在成立时便得到了时任印尼外长阿拉塔斯的支持,因而它是带有官方目的的“第二轨道”。其次,印尼多次在会上强调该机制旨在实现区域所有国家的利益而非印尼的私利,印尼的作用也逐渐得到了各方的肯定[32]。再者,“非国际化”的基本原则以及域外力量被建构为参与性的建设性力量,这在南海主权争议正因美国基于霸权利益的政治和外交干涉变成东亚区域安全脆弱的根源的现状下[33],再次体现了印尼所倡导的区域抗御力、综合安全观以及区域自主;同时也彰显了印尼借引领东盟在“南海研讨会”中“对外一致”以实践本国区域领导战略的意图[34]。
最后,“南海研讨会”本身及印尼的经营确实存在诸多缺陷。就预期来说,“南海研讨会”程序上的协商一致、会议声明非强制性及其本身的“第二轨道”性质,使其抗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尤其是在确立信任建立的施力方向中无奈地忽略了主权问题这一关键议程,使其在主权争端激化时难免流于失效。就成就而言,虽然“南海研讨会”已牵头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但合作面仍过于狭窄,主要局限于海洋科研与技术合作,难以应对南海复杂多样的安全威胁。而作为主要推动力的印尼曾经尝试推动“南海研讨会”以及南海争端官方化与国际化,皆因中国与其他方面的反对而未果。在美日等国强化在东南亚的存在,建构各自主导的海上安全机制并强化与印尼关系的当前,这也为今后“南海研讨会”发展中能否坚持现行基本原则埋下了隐患。虽然印尼已在实践中通过协调国内政治、自我对区域秩序的目标、区域伙伴的态度及因应以及域外大国的认可和影响这四者间关系,实现了区域大国身份的自我认知与他者承认,但在区域间治理纷繁复杂的东南亚,印尼的区域安全领导力相较于周边大国与域外大国仍十分有限,在南海主权争端中的话语权也十分有限。这也是当前仅容纳东盟成员国与中国的“南海研讨会”的作用与影响力远不及同为“第二轨道”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的主要原因。
结论
针对南海争端而发起的“南海研讨会”是印尼谋求均势与区域自主的安全战略,构建“东盟安全共同体”与逐步提升国防实力的安全政策,推动区域合作并巩固区域大国地位的区域主义,强化综合安全能力的大国角色的重要途径。它也是印尼在实践中通过对安全行为准则、安全机制、信任建立措施三管齐下来实现上述战略与政策目标的关键一环。这一信任建立措施是印尼通过跨区域合作塑造本国区域安全管理力与保护力,弥补自己在东盟外向安全机制中领导力不足的重要举措。它在现实中发挥着对东南亚海上安全机制的协同补充作用,同时也起到了在印尼围绕以东盟为中心建构安全机制、本国独立建设的双边安全机制以外,对印尼建构区域安全机制乃至安全秩序的协同补充作用。而“南海研讨会”所倡导的基本原则,成员主要限于东盟成员国以及台海两岸,议程基于共同利益与试验性合作等这些特点以及“南海研讨会”当前存在的诸多缺陷值得我们加以利用,在化解南海争端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注 释】
[1]Sam BateMan,“Good Order at Sea in the South China Sea”,in Shicun Wu & Keyuan Zou eds.,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Regional Impl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shgate,2009.
[2]郑先武:《安全区域主义:一种批判IPE 分析视角——比约恩·赫特纳“新区域主义方法”述评》,《欧洲研究》2005年第2 期。
[3]周士新:《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 期。
[4]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5 页。
[5]陈以定:《东盟区域安全机制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6]王磊、郑先武:《国家间协调与区域安全治理:理解东盟安全机制》,《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4 期。
[7]同[4],第307 页。
[8]Ralf Emmers,“Securitization”,in Alan Collins ed.,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Third Edition,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31 -143.
[9]〈法〉夏尔-菲利普·戴维著,王忠菊译《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 -35 页。
[10]鞠海龙:《印度尼西亚海上安全政策及其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3 期。
[11]Marshall Clark,“Indonesia's Postcolonial Regional Imaginary:From a‘Neutralist’to an‘All-Directions’Foreign Policy”,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2,Issue 02,August 2011.
[12]〈印尼〉丹迪·苏森托著,鞠海龙、李皖南译《印度尼西亚新防务战略解析》,《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5 期。
[13]骆永昆: 《大选后的印尼:更加自信的地区大国》,《世界知识》2014年第17 期。
[14]Ralf Emmers,“The de-escalation of the Spratly dispute in Sino-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in Sam Bateman & Ralf Emmers eds.,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Sea:Towards a cooperative management regime,Routledge,2009,pp.135 -138.
[15] 曹云华、鞠海龙主编《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1—2012)》,时事出版社,2012年,第246 页。
[16]Hasjim Djalal,“Indonesi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nitiative”,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Vol.32,No.2,2001.
[17]Yann-Huei Song, “The South China Sea Workshop Process and Taiwan's Participation”,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Vol.41,No.3,2010.
[18]Hasjim Djalal,“Indonesi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nitiative”,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Vol.32,No.2,2001.
[19]Ibid..
[20]张良福:《历次“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非正式讨论会述评》,《国际政治研究》1995年第1 期。
[21]Hasjim Djalal,“South China Sea:Contribution of 2nd Track Diplomacy/Workshop Process to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eace and Cooperation”,http://carlospromulo.org/wp-content/uploads/2009/12/Hasjim-Djalal.pdf
[22]Hasjim Djalal,“The South China Sea:The long road towards peace and cooperation”,in Sam Bateman & Ralf Emmers eds.,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Sea:Towards a cooperative management regime,Routledge,2009,p.182.
[23]宋燕辉: 《南海地区安全战略情势之发展与现状》,载台湾“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编《亚太研究论坛》第19 期,2003年3月。
[24]《出席第十五届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心得》,载台湾《海巡双月刊》2006年19 卷。
[25]《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主编《中国海洋年鉴2010》,海洋出版社,2010年,第412 页。
[26] 中国南海研究院网站:http://www.nanhai.org.cn/index.php/Index/Survey/cooperation.html,2015 - 01-10。
[27]Ian Townsend-Gault,“Preventive Diplomacy and Pro-Activ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0,No.2,August 1998.
[28]刘复国:《当前区域性南海问题对话合作机制》,载台湾“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编《亚太研究论坛》第19 期,2003年3月。
[29]Hasjim Djalal,“The South China Sea:Cooperation for Reg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http://nghiencuubiendong.vn/en/conferences - and - seminars - /the - thi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outh -china -sea/665 -the -south-china-sea-cooperation -for -regional -security -and-development-by-hasjim-djalal,2014 -12 -02.
[30]聂文娟: 《大国因素与地区安全机制的制度化——以东盟与非盟的安全机制为例》,《外交评论》2013年第4 期。
[31]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A Concept Paper(1995),in A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 for the 20th ASEAN Regional Forum,Beijing:World Affairs Press,pp.53 -58.
[32]刘中民:《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 期。
[33]朱锋:《南海主权争议的背后》,《今日中国(中文版)》2014年第3 期。
[34]葛红亮:《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举措分析》,曹云华、鞠海龙主编《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2—2013)》,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