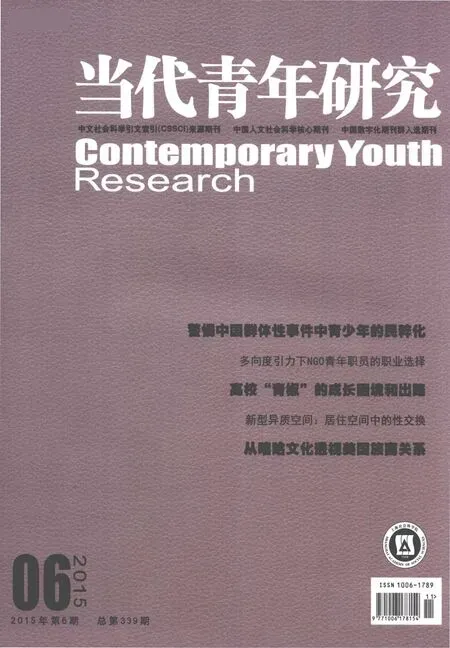新型异质空间:居住空间中的性交换——基于北京某流动人口公寓的个案研究
2015-03-29张金凯
张金凯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一、公寓空间:新型“异质空间”
“北漂”一词,形象地建构了当代一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的特征。这群特指在北京打拼的流动人群以青年人为主,他们普遍处在一种漂浮的状态。与一般意义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差异除打工地点的特殊性以外,这个群体在年龄上跨度更大,很多“70 后”“60 后”等依然漂浮着。就当前来看,很多高校大学生、研究生也成为“北漂”的一员。而“北漂”的居住情况,也是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
据调查,在住房类型上租住房屋的流动人口占65.2%,其中53.8%租住在城中村/出租屋,34.7%租住在小区商品房,3.3%租住在单位宿舍,2.8%租住在外来工公寓[1](这里的外来公寓指专门给外来工提供的政策性公寓,一般如本研究的公寓虽称“公寓”,但一般属于出租屋类别)。尤其在位于城区近郊的“城乡接合部”,在北京的五环及以外,大量分布了这类住房。与传统的农村社区相比,城乡接合部在物理空间特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耕地变得很少或者消失了,原来的传统房屋住宅区与新兴的住宅小区和工业园区、商业服务业街区混合在一起,这是城市空间扩张与城市社会结构不断协调整合的结果。[2]这类联排式或行列式的住房通过其整齐划一、最大化利用空间、无死角监控等特点成为安排流动人口的优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福柯“治理术”的实施。在公寓中,实现了对居住在其中的流动人口的身心治理。
正如福柯所言,建筑“保证人们在空间中特定的定位、移动的渠道化,以及符合化他们的共生关系。它不只被当成空间中的一个元素,而且特别地被当成一个社会关系领域中的安插”。[3]笔者所调研的这个公寓位于北京五环外,周边是成片的商业住宅区,而围绕着这个公寓,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包括宾馆、饭店、按摩店、超市、影院等一应俱全,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周边居民的日常需求,另一方面,催生了一个不同的产业——性交易。尽管从统计上说性交易的场所可存在于宾馆、家里、情色场所等,但是根据调查发现,这样的流动人口公寓逐渐形成这个年龄段青年进行性交易的场所。宾馆并不是寻欢者的固定居所,只是实施交易的平台,而家是其固定居住场所,对于人的归属感是强烈的,而公寓处在这两者之间。公寓一般并不是其长期居住空间,居住时间从数月到数年不等;公寓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缺失的“家”的归属感,让其产生寄居之感。在公寓这样的居住空间中,随着性交易的发生,居住者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同时改变了居住空间的秩序,并实现了居住者关系的再生产。
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在公寓中的房间里的居住者不仅进行了一次简单的性交易,同时进行的是一次性交换,居住者主动地将“小姐”而非其服务视为商品,在其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中完成了将人资本化的过程。对于居住者来说,公寓因为其暂存性撕扯了居住者在其中的主体地位,使得公寓既保留了宾馆的平台性,同时又具有家的归属感,但这两者因为居住者主体地位的漂浮性而混淆在一起。公寓空间因而具有一个独特功能,它们的角色,或许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即所有人类生活被区隔的所有基点)是更具幻觉性的;另一方面,它们的角色创造了一个不同的空间,另一个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示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4]公寓成为一种新型异质空间。
二、小卡片:流动人口身体交换的媒介
这一流动人口公寓位处五环外,公交或地铁到达市中心需要半个小时以上。整体为三层整栋联排式,由五排住房连接而成,占地约5000 平方米,可容纳2000 人居住。每排左右各25 间房,一边为约24 平方米的4 人间,一边为约8 平方米的单人间,由一条一米宽、两米高的幽暗过道区隔,4 个摄像头24 小时监控着过道。4 人间有3 平方米的厨房、1 平方米的卫生间以及两张上下双人床,单人间有一扇面向过道的窗户,除了卫生间、床和桌椅已经没有多少可走动的地方。在这里每个月租金为800 元,水电、网费、取暖另算。在这里居住的流动人口分布广杂,有周边店铺的员工,也有“北漂”的大学生,因为这里设施齐全,交通方便,可以短期租住,不少来京的打工者选择此地,同时其与一些企业合作,为这些企业刚来的员工提供更为便宜的租金。尽管很多居住者表示“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但并不妨碍这里很高的入住率。
(一)连接荷尔蒙与启蒙的小卡片
在幽暗的过道上、每个门口都散布着三五张名片大小的小卡片,这种小卡片与在宾馆酒店门口的卡片类似,均为提供性交易的电话号码,内容言简意赅,一个靓丽女性的照片,一个电话号码,再加上“白领、学生妹、少妇”等字样。江苏常州曾抓捕一个通过小卡片性交易的卖淫组织,其组织成员分工明确,“除2 名组织者外,这个团伙内有2 人负责散发色情广告招揽生意,1 人负责接电话,另外1 人则负责护送卖淫女” 。[5]同时,一些小卡片实为诈骗信息,不少人因为打电话而受骗。小卡片成为作为现代监视空间的异质元素。
一扇门、一扇窗阻隔了居住者的私人空间与过道的公共空间,较差的隔音效果能够清晰地听到隔壁的打喷嚏声,但听觉传播的敏感性和保密性远不及视觉传播,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人空间,门窗一般是紧紧关闭的。居室内的青年人每天除了睡觉、休息,一般的娱乐方式为打电脑、玩手机,单调的生活使得青年需要一些新鲜刺激的东西。
尽管有电脑、电话,虚拟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年的社交需求,但缺少实际接触的青年不免难耐激情。一些青年缺乏生理性满足,在雄性荷尔蒙的驱动下,将目光伸向启蒙理性的外界,以满足自己的理性选择和交往需求。他们发现有一个一举两得的方式来满足生理上的荷尔蒙与心理上的交往理性,小卡片上的女性照片诱惑着在居室里的男青年。
据统计,接受性交易的原因中“长期没有正常性生活”的比例占27%,“经不起诱惑”的占20%,“苦闷”的占15%,有46%的性交易发生在出租房内。[6]一些研究表明,多性伴性行为有可能更多的是个人社会存在的表达,或者是基于证明个人的魅力,或者是弥补个人情感的需要,它与生理因素无关。 也即,当常识上认为的男性管不住自己的生理需求或者认为自己进行性交易是基于自己的生理需求并不符合真实的情况,至少并不都是这样。今天,人们不再那么渴望家庭空间能抚慰肢体的疲劳,而更多地希望这种空间能缓解日常生活中紧张和冲突带来的情绪和心理的压力[8],当缺少家庭空间时,就需要居住空间的其他方式来填补。小卡片上靓丽女性将居住者的思维拉到了虚拟空间中的情色影视、图片和现实空间的广告、日常着装和交往生活上面,随着性的开放,居住者在居室内幻想着生活世界。居住者的痕迹留在了居室,对于私人来说,居室的幻境就是整个世界。[9]小卡片成为居室内的居住者沟通世界的媒介。
(二)小卡片开启公寓空间大门
整齐排列的房间最大化地利用了公寓空间,每个房间基本满足了居住者的日常行动,需要一个过道实现了居住者向外界的通行,过道上铺就的毯子保证了走动的安静。除了声音,外界无法探知居住者的一举一动,居住者蜗居在自己的私人空间中,以功能性存在进行机械的定时休整。流动人口白天一般都在工作单位,到了夜晚回到自己的场所,在这里进行破损零部件的修复和更新,在此基础上,生理需求、情感需求、社交需求、职业需求、娱乐需求等随之而来。而一些特定需求需要得到满足时,长期缺乏性生活、需要刺激、苦闷的居住者有时就拨打了小卡片上的电话号码。
对于提供性服务的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经济上的问题。这些人大多也是流动人口,甚至有居住在这一公寓中人。她们在工厂、单位打工,当她们发现“工厂里的工作不可能让她们有机会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更不可能为她们今后留在城市提供保障,包含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要”[10],一条走捷径的道路摆在她们面前。当她们走进公寓大门,也走进了居住空间里的生产与交换关系。
对于性服务者个人来说,性交易是一种交换关系,自己作为性服务者提供服务,居住者购买这种服务。在这里生产与交换同时发生。悬置这种关系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与影响,如果说公仆、医患、雇佣关系之间在当前对立矛盾愈演愈烈,单就居住者和性服务者在居住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而言,他们不但是非对立的,甚至是同一的。商品的拜物教使得性服务者一方面是生产者,一方面是商品,作为直接商品的工作者提供肉体满足作为消费者的居住者的需要,作为生产者的工作者一方面生产服务,包括直接性服务、心理慰藉、对话交往等,一方面与居住者共同生产一层社会关系,他们需要为这种社会关系保密,加深了社会关系的构建。在居住空间中这层社会关系从两者之间直接身体交换变成了居住者通过性服务者的身体媒介达到的与自身、外界和世界的抵达,而性服务者在这里成为物性的颠倒、完成与商品的同一外实现了居住空间的异质性表达。
在福柯看来,异质空间的异质性就在于其相对于一种真实空间的“泄露”,一方面它将真实空间的虚伪性展露无遗,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构造一个新的真实空间。当福柯拿妓院做比喻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随着资本的进化,居住空间实现了居住与妓院的合体。在这样的居住空间中不仅展现了真实空间中社会关系之间尖锐的对立矛盾,同时其试图构造一个抵消对立的空间,这种对立的空间关系在法律上是明令禁止的且是不道德的,又反衬出这种异质空间的虚构性。建筑本身并无所谓压迫或解放,并无所谓控制或自由[11],而在公寓这样的建筑中,一张小卡片打开了居住空间,居住者与性服务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异质空间,但这个异质空间并不具有反抗、解放或自由等政治意涵,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建立在消费主义之上的消磨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限以实现资本的增殖,因为当双方建立关系之后“以微乎其微的欢愉补偿我们缺失的爱、社会关系和认可。消费主义变成避风港、逃难所,对治疗孤独感和满足感缺失的需求一直在增长”[12]。随着初次性交的年龄提前、婚前同居行为的增多、不健康无规范娱乐场所的增多,以及个体职业活动自由度的提高,多性伴性行为的发展趋势恶化[13]。
(三)一个新的交换场所的诞生
随着性交换关系的表达,居住空间容许这种关系的发生,同时成为其基础。列斐伏尔认为,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它们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14]居住空间不仅具有居住的功能,同时成为性交易场所的话语。居住空间的这种特性使得我们容易误将其视为一种纯粹的异质空间,因为当其性话语被强调后,似乎这种显性特征成为其基本特征。当我们谈论宾馆时我们在谈开房,当我们谈论夜店时我们在谈论“一夜情”,而公寓,也随着这种话语的侵略而成为一种性交易场所。但是我们不应首先忘记其负载于居住空间这一基础之上。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居住空间的异质性并不纯粹,甚至这样的异质空间是一种资本逻辑所掩饰的真实空间的异质空间假象。而这才是公寓所具有的性交换场所功能表达的真实空间意义。
在深圳富士康的居住空间中,经济收入因素限制了普工对于住房空间与自由度的选择,低廉的城中村农民房因为被卷入房地产开发改造其租金也越来越高,更多的普工开始住在更便宜而密集的宿舍而不是城中村,尽管当初他们愿意花相对更多的钱住在外面的城中村里。[15]同样,像北京的这个流动人口公寓一样,其选择也是基于经济收入因素。当他们像本雅明笔下的闲逛者在北京城中漫步时,经历的是一个个不断闪动的片段,这些片段色彩鲜艳,包含着每一个在这里奋斗的人的光辉一刻,当他们享受了这激情的片刻后,不得不回到居住空间面对现实长时间段的单调与灰暗。而居住空间的异质元素在经历了将居住空间异质化之后归于平静,又回到了往日的单调与灰暗,甚至更加凸显这种单调。而消费主义的逻辑就在于通过这种不断的刺激和刺激后的空洞和饥渴来换发再一次刺激,实现需求的生产与再生产。以生产之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为取向,空间的生产发动了均质化的逻辑与重复策略。[16]
因而,流动人口公寓这种新型“异质空间”在于它表达了一种新的空间生产。不仅在于从空洞的真实空间中生发出异质空间的异质元素实现异质空间化,并且这种生发出的异质空间保持着短暂的生命力而迅速转变成更加空洞的真实空间。所以在从类似妓院的性交换场所功能中表达的异质性完成了一个颠倒,即一个纯粹的异质空间应发生“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17],而公寓中的性交换颠倒了交换与使用的顺序,造成了以假象的使用掩盖真实的支配。公寓中的居住空间成了一种后现代的异质空间,一种话语的、美学的、透过真实空间试图窥探异质空间而将自己的真实性更加“泄露”的异质空间。流动人口公寓的特殊性在于,这种马克思笔下的“住宅监狱”,通过空间剥夺导致城市雇佣工人在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中被边缘化。 他们所生产的社会空间不仅是一个短暂的仅包含他们自身和想象性世界的虚拟空间,同时这种空间会刺激他们再生产更多的虚拟空间来填补原有空间的缺失。
三、青年流动人口与性交换的空间生产
被挖掘的空间需求使得青年流动人口的时代性人格特征日益明显,他们普遍因为工作、生活等原因缺乏激情、情绪低落、苦闷空虚,这些显在的原因导致他们产生如此情绪以及采取一些相应措施。然而,正如费希尔提出的拥挤理论认为,大规模超常数量的人出现在邻近区域,造成生理和心理的过度刺激,高密集产生压力,是因为它导致了对人们“私人生活领域”的频繁侵犯。[19]高密集居住空间造成人的性格变化、心理紊乱在如富士康连环跳楼等事件中已经明显看出。而像“北漂”的这个群体在这一公寓中,他们面对着居室、公寓和小卡片,需要通过性交换来满足自己被建构的需求以外,自身在空间中成了空间的附属品。
(一)流动人口的欲望身体
性需求几乎每个人都有。像“北漂”一样的流动人口大多孤身一人在北京打拼,缺少陪伴、没有交往,然而当我们再试图挖掘其生活环境,会发现他们的需求远没有生活世界提供的性呼唤来得丰富。老陈今年30岁,来北京已经快十年,大专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漂泊,目前待业,至今未婚。从原来的工作单位辞职后在这一公寓中住了快两个月,因为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已经准备回乡了。“大专毕业就来这边了,我是河北的离得近,就想来这边找找机会,在饭馆干过,工地上也做,也坐过办公室。北京城是大,就没有你的地方。你要说住的,还好了,比住地下室、工地,睡在火车站强多了吧。就是没人搭话吧,你要是住在工地还能一起搓个牌喝点小酒,这儿谁认识谁。旁边声音都听得见的,小哥跟他女朋友吧整天哼哼唧唧的,床的声大哟,晚上觉都睡不了。不是没想过打这个电话,我以前听说有被骗的,然后来几个人说不给就喊警察,有什么法子。有时瞄那上面那女的真是漂亮,都是假的,来得丑哟,还是要看运气的。”性冲动既然是人的本能,它与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是有机融合的一体。[20]性需求有时并不是出发点,老陈这样的对于性的要求不高,但是促使他产生这一需求的不仅仅是生理性冲动,同时包含他心理上的欲望需求,包括对私人空间、对职业、对交流、对他者欲望的欲望,这些欲望通过消费主义逻辑而驱动。老陈渴望在偌大的北京有自己的天地,这片私人空间的渴望与现实的“家徒四壁”形成强烈反差,隔壁的小青年从一个他者的立场激发他对性的渴望,使得这一居住空间成为他的欲望空间,小卡片只是这个拥挤而不断膨胀的欲望空间的一个针头,一旦戳破,老陈在欲望空间打破的刹那走向新的空间,欲望空间不仅是他的出发点,同时也成为他通向幻想空间的中介。
(二)公寓中的生活策略与性的中介
在公寓中居住的流动人口对自己的居室十分熟悉,但有时会觉得很陌生。因为人通过活动建立起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图式(即主观的空间秩序),再依据这个认知图式去活动;当这个认知图式不能“同化”客观环境(客观的空间秩序)时,人就根据环境变化修改认知图式,这就是智能的本质——适应。[21]当居住空间在主观空间秩序中成为欲望空间时,如何适应只有一扇通向幽暗过道的门和一扇紧闭的窗的立方体,居住者从生活策略的角度利用各种途径来适应,通过通宵打游戏、通过夜不归宿、通过睡眠,也有通过小卡片的。小网今年24 岁,未婚,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到一家网络公司工作,这个公寓是公司安排的住处。工作一年有余,没有女朋友的他曾经选择用小卡片满足欲望。“第一次打也挺紧张的,接电话的是男的,差点直接挂掉,然后说要什么样的,在哪儿,多少钱,就答应了,其实来了个长得挺老的一个女的,做完了给了钱就走了,想想挺没劲的。找女朋友那得花多少钱,还不一定能上,还不如花点钱爽一下,还想了就再说呗。”从成本上来说,找一个女朋友比找一个性服务者花费高太多,小网选择了后者。性由其生理性而在社会化和社会交往中走向资本化、货币化[22],社交与交往成为一项货币投资行为,而生理性需求成为附属品。小网在经历了一次性交换后并没有从欲望空间中解脱出来,甚至没有窥视到他的幻想空间。本雅明所谓的“幻想居室”反而更加深刻地彰显了他的客观居室的空洞,让他在需求满足的那一刻欲望被拉回到现实,空洞的居住空间愈发需要欲望来填补。对小网来说,进行一次性交换除了肉体与金钱的交易之外,更多的是借用居住空间的中介性功能将其与幻想空间之间的关系打断,重新建构他与欲望空间的生产关系。即使社会因素的作用在总趋势上强于个体状况和个人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就一定屈从于社会,甚至愈来愈可能发挥个体的首创力[23],而个人的这种自由行为却不由自主地按照欲望空间的生产逻辑来进行,而个人的策略选择或性则成了生产的借口和消费的渠道。
(三)填满情绪与空间的生产
跟随着消费主义的生产逻辑,欲望身体采取直接的性交换行为,这是能够立刻满足欲望的需求,但过后留下更大的空缺而需要更多的欲望来填补。这种冲动感正如恩斯特•布洛赫所言,正是一种“填满情绪”:填满情绪在冲动意向上是瞬间性的,而在冲动对象方面是有准备的,在此,所谓“冲动对象”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个人所能达到的东西,而是意味着业已存在于世界中的东西。[24]如老陈、小网欲求的正是业已存在于世界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的吸引正是在居住空间中所幻想而缺失的,居室的幻想空间是标签着这些东西而使得居住者住进了欲望空间,居住者试图通过性交换这种形式从欲望空间中跳出进入到幻想空间,然而性交换的结束意味着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居室,但他们并没有回到欲望空间。相反,在欲望空间的欲望被排泄之后留下空洞的空间,需要更多的欲望来填补空间的空缺。
这种情绪在性服务者身上进一步得到强化,在性交换过程中,性服务者真实地或虚伪地成为居住者的情人及关爱和慰藉的对象,由此,性服务者在性服务中营造起属于自己的自尊空间,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自尊体验[25]。性服务者在性交换过程中通过自尊的体验获得主体地位,从而与居住者共同营造一种“幻想空间”,这一空间并不是由居室的幻想生成,而是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下,因“填满情绪”的冲动而自觉进行的空间的生产与欲望的消费过程。性服务者在居住空间内的异质性并不带有福柯意义上的揭露真实空间的虚伪性,相反,她间接地利用自己的异质性外表掩饰了真实空间而通过欲望的消费将构造出来的“幻想空间”展现在居住者面前, 这种异质性实际上成为真实空间的佐证和强化,在性交换结束后留下真实空间中被消费的欲望后的空缺,等待居住者再次填满。
因而,居住空间中的“填满情绪”在指向现成的、可求的事物的同时,一方面为空间的生产提供契机,另一方面从过程来看,空间成为中介,居住者在利用空间的工具性来填补自己的欲望,而从结果上来说,居住者将空间视为工具时空间已颠倒为目的,居住者成为实现空间的再生产的手段不断被欲望所勾引,他们冲动的对象一直是瞬间的各种欲望,在达至之后却发现欲望在更遥远处招手,冲动被利用为不断实现欲望空间向幻想空间的转化而实际上只是满足了欲望空间自身的生产,这就是由居住者与性服务者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下共同完成的空间的生产过程,而公寓的异质性正是被借以实现颠倒而表达的掩饰,以试图掩盖这一过程中真实空间(即消费主义的表达)的泄露。
将性交换置于探讨流动人口在居住空间中的生产问题牵引出消费主义的干预与控制问题。从对流动人口公寓的异质性折射出来的是空间的生产能力,而通过流动人口居住者与性服务者之间的性交换将在居住空间的生产逻辑下颠倒为空间生产的工具,而消费主义将驱动这一过程的生成。对空间的支配反映了个人与各种强势群体如何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支配空间结构与生产,以便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人占用空间的方式实施更大程度的空间。[26]马克思笔下的“住宅监狱”在今天依旧能释放其潜力,即通过空间的剥夺不仅消除了流动人口的空间生产能力,更将流动人口置于自身的生产过程而成为其生产工具,以实现其占有空间的增殖。问题在于,当我们认清如流动人口公寓这样的居住空间潜在的剥夺后,如何认清其背后消费主义的驱动,如何面对消费主义对空间的侵蚀和剥夺。
[1] 李志刚.中国大都市新移民的住房模式与影响机制[J].地理学报,2012(2):189-200.
[2] 狄雷、刘能.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过程的社会学考察[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1):71-77.
[3][4][16][17] 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36,27,51,55.
[5] 中国常州网壹新闻[OL]. http://news.cz001.com.cn.
[6] 张文卫.关于外来民工的性报告[J].中国性科学,2007(8):7-16.
[7][13] 庄渝霞.上海多性伴性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社会,2014(3):117-144.
[8][12] 布兰卡•列奥、卡塞尔.当代社会住宅的可持续性与交往空间[J].时代建筑,2011(4):62-69.
[9] 本雅明.巴黎,19 世纪的首都[M].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4-45.
[10] 张晓红.融入与隔离:从打工妹到卖淫女的角色转变[J].犯罪研究,2007(1):13-19.
[11]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6.
[14] 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M].李小科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70.
[15] 杨友仁.流动与疏离:深圳富士康工人的都市状态[J].人文地理,2013(6):36-42.
[18] 李春敏.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及启示[J].天津社会科学,2011(3):4-9.
[19] 孙逊、杨剑龙.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30.
[20] 王福民.家庭:作为生活主体存在空间之价值论旨趣[J].哲学研究,2015(4):25-30.
[21] 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5.
[22]陈荣武、曹锦清.女性性资本现象的社会转型逻辑[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4-31.
[23] 潘绥铭.社会对个人行为的作用——以“多性伴性行为”的调查分析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02(4):140-150.
[24]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M].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6.
[25] 王金玲.认识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间[J].妇女研究论丛,2012(4):11-23.
[26]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