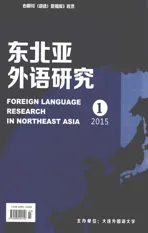美国亚裔文本中的双重“他者”书写
2015-03-29王绍平
王绍平
(大连外国语大学 公共外语部,辽宁 大连 116044)
美国亚裔文本中的双重“他者”书写
王绍平
(大连外国语大学 公共外语部,辽宁 大连 116044)
本文以跨文化视角分析具有东北亚文化血统的美国华裔、日裔、韩裔等文学文本主旨。首先,文章介绍美国亚裔研究的两个关键词“亚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感”。之后,围绕身份认同主题,从文化乡愁、历史负重与现实纠结等层面,探讨中日韩裔文本建构的双重“他者”。结论指出,研究美国亚裔文本有益于我们了解美国亚裔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东北亚文化。
东北亚文化;美国亚裔文本;双重“他者”1
作为亚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等国家同处儒学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具有很多文化相通之处(陈放 陈维新,2006)。如果将东北亚文化视为一个独特的、自主的“个体”,那么,在跨文化交流中它就成为“本群体”(in group),东北亚之外的文化则成为“他群体”(out group)。但是,这种“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改变,在具体的语境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形态。本文选取了美国亚裔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华裔、日裔、韩裔等文本,将其置于跨文化视阈下,以美国亚裔研究的批评话语为切入点,分析具有东北亚文化血统的美国文本如何表现亚裔“双重‘他者’”的认同困境,进而探讨亚裔跨文化文本的现实意义。
一、亚裔美国人与亚裔美国感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美国多元文化结构中,华裔、日裔、韩裔等同属亚裔族群。亚裔是美国四大少数族群(其他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本土印第安人)中数量增长最快、家庭收入最高、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王进军,2013)。亚裔尽管语言不同、族裔各异,但是他们共同受到美国经历的影响,与美国社会日益趋同。这里,我们首先介绍与美国亚裔研究有关的两个关键词——“亚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感”。
(一)亚裔美国人
亚裔美国人由十多个亚洲民族及其在美国出生的后裔组成,主要以华人、韩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印度人等“六大族裔”为主(曾少聪 王晓静,2009:53)。目前,亚裔美国人中最大的族群是华裔,第二大族群是日裔,第三大族群是菲律宾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较早进入北美大陆,迄今为止在北美生活了150多年。早期的亚洲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和日本,印度、菲律宾和韩国次之。从淘金时代的“金山客”,到二十世纪70年代的“模范少数民族”,到80-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一支族裔集团,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化(董娣,2001:98)。
美国亚裔作为一个族群,形成于特定的美国社会历史背景中。自1882年美国政府实施《排华法案》到1943将之废除,直至二十世纪60、70年代之前的百余年时间里,亚裔一直被称作“东方人”(Oriental),是“无法同化的异族人”(黄秀玲,2007:10),被肆意排斥和攻击,是危害美国社会的“黄祸”(the Yellow Peril)。1960年代美国社会的三大运动:反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校园运动,触发了亚裔美国人对自身权益、自身文化和自我身份的认识,促成了“亚裔美国人”称谓的提出。美国日裔社会活动家市冈裕次(Yuji Ichioka)教授创造了“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这一术语,是指所有在美国具有亚洲血统关系的人。由于这一术语的提出与使用,各个更小范围的族裔群体名称也相继出现,如美国华裔(Chinese American)、美国日裔(Japanese American)、美国韩裔(Korean American)等(张龙海,2005:41)。“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强调亚裔同样是美国人,进而否定了“东方人”等一系列带有明显贬损之意的称谓,反映了亚裔种族平等意识的新觉醒(黄际英 简明,2004)。
在美国学界,如何界定亚裔美国人一直是争议的话题之一。美国著名亚裔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她(2007:8)认为,“亚裔美国人”一词本身“极富弹性”,具有特殊的符号学地位。这是因为“它有着层层的历史积淀,而不仅仅是一个内涵固定、指涉明显的标签。它是一个符号,一个多重政治和文化力量抗争的场所。”她(2007:10)指出,亚裔美国人“由于他们不同的物质追求,政治立场的不明确,最主要是由于他们怪异的、过分成熟的‘东方’文化,使被认定其本身不具备成为完全意义上美国公民的条件。”由于在肤色、语言、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与美国的主体民族欧裔相去甚远,“在美国这所大房子里,亚裔美国人永远是客人。”(黄秀玲,2007:10)亚裔美国人所受待遇,是由美国国家意识形态需要而决定的。“当他们表现优异时(由主人来判定),就被获准为美国生活增添异国情调,甚至被捧为‘模范少数民族’以彰显美国平等理念的真实性。然而,一旦需要替罪羊时,指责他们不情愿或者不能够被同化的声音就会突显出来。”(黄秀玲,2007:10)同时指出,“亚裔美国人”一词具有“双刃剑”的本质。一方面,它有利于亚裔美国人共享处于美国主流社会边缘的少数族裔的共同经历,争取共同的族裔权利;另一方面,在接受这一称谓的同时,亚裔美国人承认了自己与“美国人”的不同,承认了“他者”地位,这对于亚裔被主流接纳非常不利(黄秀玲,2007:11)。
从历史角度看,亚裔美国人经历了从“贱民”到“楷模”的发展阶段,成为融入美国多元社会的典范。但是,种族上的生理差异和历史上的不同遭遇使亚裔群体在面对“美国”这一主体身份时,难以完全摆脱自身的“他者”意识。
(二)亚裔美国感
在美国亚裔批评话语中,“亚裔美国感”①(“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词”(浦若茜,2013:98)。这个词汇的缔造者和诠释者是亚裔“四人帮”,即“哎咦—集团”。“哎咦—集团”(“Aiiieeeee Group”)是对华裔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徐忠雄(Shawn Wong)以及日裔诗人劳森·稻田(Lawson Fusao Inada)等四位亚裔美国文学开拓者的总称。他们共同编著了具有奠基意义的亚裔美国文学选集《哎咦!亚美作家选集》(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和《大哎咦!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选集》(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1972 年,在“种族主义之爱”(“Racist Love”)一文中,“哎咦—集团”的核心成员赵健秀、陈耀光首次提出了“亚裔美国感”一词;而在出版于 1974 年的《哎咦!亚美作家选集》中,“哎咦—集团”更旗帜鲜明地以“亚裔美国感”作为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入选该文集的核心标准:“所选作品的年代、多样性、深度和质量证明了亚裔美国感及亚裔美国文化的存在,它与亚洲和白色美国(White America)相互关联但又判然有别”(转自浦若茜,2013:98)。
“亚裔美国感”内涵独特,意义非凡。赵健秀(Frank Chin)指出,“亚裔美国人并不是一个族裔,而是由华裔、日裔和菲律宾裔等几个族裔群体构成。华裔和日裔已经同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社会文化以及历史诸方面各自分离了七代和四代。他们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已经演化出了十分独特的文化与情感,它们既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特点,也有别于美国白人的特点。就连目前在美国仍然由亚裔族群使用的亚洲各种族的语言,也已经被调整和发展成为表达他们全新经历体验的独特语言。”②可以看出,“亚裔美国感”力图改变美国历史上形成的亚裔刻板形象,以接“美国地气”的方式旗帜鲜明地体现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诉求,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族群集体意识。
二、美国亚裔文本主旨
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1828-1893)指出,艺术发展受制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因素。美国亚裔文本是美国历史、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造就的文学形态,由在美国出生或后移居美国、有亚洲血统的人用英语进行的创作。从定义可以看出,亚洲文化血统/亚洲文化是美国亚裔文学与生俱来的“胎记”,是共生的关系(王绍平 邹莹,2014:79)。Gerald Haslam认为,亚裔作家深受东方文化影响,这是由于亚裔美国人和东方文化之间存在的连贯性:
……与被强迫剥离了自己文化的非洲后裔相反,亚裔美国人有一个内在的资源宝库,那便是他们的祖先所创造的伟大而复杂的文明,而在那个时候,不列颠群岛上的居民还是身上涂满油彩的原始部落。
(转自徐颖果,2012:327)
Haslam 指出的“资源宝库”即是亚洲,包括东北亚在内的文化传统,可以体现在物质、制度、行为以及心态等层面上,亚裔文本大多有着这些文化烙印。亚裔美国人因此具有了双重文化遗产和双重性格,这种“持久的内在文化资源”(转自徐颖果,2012:327)以及亚裔人口的种族特征,既给亚裔带来了几乎无法消除的“他者”文化烙印,又对他们的民族认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可以说,亚裔作家始终徘徊在东方和西方文化之间,他们塑造的人物时常“带有东方的家园情怀和美国理想寻梦的双重感受”(江宁康,2008:307)。
尽管中、日、韩裔美国人祖居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格不同,其文本中仍具有一些共同的主题,比如美国梦、边缘人及其身份、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等(吴冰,2012)。当代美国亚裔文本中的反思性叙述对美国主流文化进行了批判,同时对本民族文化的沉重包袱也进行了揭露。这些都在华裔、日裔和韩裔文本中体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出,身处亚洲的东北亚文化,在跨越了太平洋之后,在美国亚裔文本中变成了另一副“面孔”——带有“族裔性”(ethnicity)的“另类”标签,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双重“他者”的书写
(一)文化乡愁与身份探求
华人是最早来到北美的亚洲人,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不能获得美国《独立宣言》宣称的“生而平等”的权利。基于美国社会原因,早期华人多从事采矿、铁路建设、洗衣店及餐饮等职业,形成了独特的“单身汉社会”、“唐人街文化”(吴冰,2012:35-37)。华裔是遭受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少数族裔之一,1882年实施的《排华法案》直至1943年被废除,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2012年6月,美国国会就1882年《排华法案》向曾经排斥、歧视华人的做法正式道歉,成为继对日裔、非裔、本土印第安人之后的又一次“国家道歉”。
中国悠久的文化对世界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以儒家文化为根本,它包容吸收了诸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和西方文化等文化成分,显示出强大的融合性和凝聚力。作为华裔,无论到何地,他们都力图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由美国华裔创作的文本以独特视角展现了美国华裔的奋斗史和情感生活。
美国华裔文学名家辈出,是美国亚裔文学的“半壁江山”。任碧莲(Gish Jen,1955-)是华裔新“四人帮”③作家之一,出生于纽约,为第二代华裔,曾在中国山东从事过英语教学。1991年,她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Typical American),描写“二战”后来到美国的拉尔夫·张兄妹依靠自己勤奋努力追寻美国梦的移民故事。之后,她相继发表了《莫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谁是爱尔兰人?》(Who’s Irish?)、《爱妾》(The Love Wife)以及《世界与小镇》(World and Town)等作品。
“美国寻梦”是任碧莲作品的“文化母题”——“在美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带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在文学创作中经久不衰的重大主题”(江宁康,2008:314),展示了具有强烈美国特征的华裔人物。《莫娜在希望之乡》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动荡为背景,描写了女主人公张莫娜寻求自我独立与民族身份的经过,其核心情节是华裔美国人如何在美国这片“希望之乡”上解决文化认同的危机。小说围绕莫娜寻找自我身份的经历,生动地描写了当代美国文化冲突和文化协调的现实场景。比如,莫娜与父母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有差别的,她的思想和情感更多地联系着自己的出生地美国,而不像父母那样眷恋中国。尽管父母一再强调“家庭圈子”、“学校圈子”、“城市圈子”等,莫娜却以实际行动打破了父辈的“圈子”情结(“in group”和“out group”)。她结交了很多不同族群背景的朋友,认识到了美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多元族群中存在的不平等。小说中莫娜自我独立,最终选择皈依犹太教,“做犹太人”(Jen,1996:49)。莫娜这一“改宗选择”——从中华传统文化转向美国犹太文化,看似离经叛道,但却体现出主人公求新、求变的开拓精神,成为新一代美国华裔的代表形象。
(二)历史负重与认同挣扎
日裔美国人按照代际划分为一世(Issei)、二世(Nisei)和三世(Sansei)。不同于早期被美国主流视为“苦力”的华裔,日裔移民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享有较富裕的家庭生活,他们“倾向于在美国定居”、“羡慕并努力效仿美国人”(吴冰,2012:135-138)。在美国日裔历史中,二战成为对日裔影响最大的事件,是“对日裔美国人的重创”(吴冰,2012:140),约12万日裔被监禁在美国西部10个拘留营。二战也使日裔美国家庭传统结构“纷纷解体”,一世失去了“在家庭和社区的最高权威地位”,二世“独立并获得权力”(吴冰,2012:142)。这些历史使日裔美国人背负了深重的历史记忆,也使日裔文本叙述带上了沉重感。萨克文·伯科维奇(2005:593)在《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指出,“1940年以后,在日裔北美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都是唯一的一个历史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映在美国日裔文学中,作品的核心展现了“第二代日本移民的尴尬处境,他们发现自己处于父辈的文化和出生国的文化之间,被两种文化所吸引但是对两者都不精通。”
《不-不仔》(No-No Boy)(又译《不愿当兵的小子》、《说不的小子》等)再现了被二战创伤困扰的日裔群体,是日裔美国作家约翰·冈田(John Okata,1923-1971)的唯一作品。小说主人公山田一郎同其他日裔美国人一起被关押在拘留营里,在接到政府征兵令时他选择了不去军队服役,因此而入狱。战后一郎回到家乡西雅图,母亲以他为傲,因为一郎没有代表美国征战日本——母亲忠诚的故国。一郎感到深切的懊悔——在“忠诚”于出生国美国和“忠诚”于母亲(日本)之间认为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小说第一章中的一段独白体现了一郎的痛苦:
……我只是半个日本人,因为一个在美国出生、在美国被扶养成人、接受美国教育、在美国的街道上和美国的房子里、在美国人中间、说美国人的话、骂美国人的娘、喝美国人的酒、抽美国人的烟,并且按照美国方式玩耍和打架、按照美国方式看和听的人,是不可能不成为美国人,不可能不爱美国的。但是我却爱得不够,因为你仍然是我的半个母亲,我也仍然是半个日本人。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他们让我去为美国而战,我却不够坚强,不想与你作战,我不够坚强,无法与造就了这一半的痛苦去作战,我的这一半就是你,它比作为我的另一半的美国更大,实际上也比我看不见、感受不到的整个的我更大。
(转自萨克文·伯科维奇,2005:551)
一郎面对非此即彼的选择,“陷入了逻辑的困境之中”(萨克文·伯科维奇,2005:551)。残酷的现实加剧了一郎人格的分裂,也代表了日裔美国人在美国化过程中经受的痛苦。
日裔文本既有对历史阴影的回顾,也有对现实生活的描述,他们的民族叙述在亚裔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女作家盖尔·月山(Gail Tsukiyama)就是一例。她生于战后一个族群混杂的家庭,母亲是香港移民,父亲是来自夏威夷的日本人。双重文化背景成长经历为月山描写亚裔女性的故事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在第一部成名作《丝绸女子》(Women of the Silk)之后,她相继发表了小说《武士的花园》(The Samurai’s Garden)、《多梦之夜》(Night Of Many Dreams)、《织线物语》(The Language of Threads)、《梦之水》(Dreaming Water)、《万花街》(The Street of A Thousand Blossoms)和《百花齐放》(A Hundred Flowers)等。
《梦之水》以加利福尼亚为背景,描写了一位失去了日裔丈夫的意大利裔母亲凯特与患有衰老症的女儿哈娜(日译:花子)如何战胜心理痛苦、共同对抗疾病的感人经历。长期饱受衰老症折磨的哈娜只有三十八岁,可是看上去却有八十岁。六十二岁的母亲凯特在失去丈夫马克斯的悲痛中,无微不至的照顾着病情日益加重的女儿。凯特的日裔丈夫曾经被关押在怀俄明州的拘留营,凯特不畏偏见与马克斯建立了家庭,但是这个日意组合的家庭被当地社区种族主义歧视,女儿哈娜的成长也受到了影响。小说主要描写了女性生活和家庭矛盾,但是作者赋予了人物形象更多的意义,特别是歌颂了人物战胜困难的勇气和面对险境的乐观精神,展现了勇气和爱的力量,传达出生存的可贵和母爱的伟大。同时,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二战给美国日裔带来的深刻影响。
(三)现实纠结与身份失落
朝鲜半岛移民美国历史较短,人数较华裔和日裔少得多。不同于华裔、日裔和菲裔,韩朝移民来自各行各业,40%的移民是基督徒,在美国大多从事农业种植(吴冰,2012)。在美国亚裔文学中,韩裔文学占有重要一席,“令人刮目相看”(萨克文·伯科维奇,2005:653)。重要作家有姜镛讫(Younghill Kang,1903-1972),作品《草堂》(The Grass Roof)、《从东到西》(East Goes West);金兰英(Kim Ronyoung,1926-1987),代表作《泥巴墙》(Clay Walls);以及李昌瑞(Chang-Rae Lee,1956-)④,作品有《说母语的人》(Native Speaker)、《姿态生活》(A Gesture Life)、《高处不胜寒》(Aloft)、《投降者》(The Surrenderred)和《如此宽广的大海》(On Such a Full Sea)等。《说母语的人》是李昌瑞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后得到了高度赞誉。小说叙述者亨利·帕克(Henry Park)是韩裔美国人,童年随父母从韩国移民到美国,居住在纽约市白人为主的郊区。从小受韩式家庭影响,亨利性格沉默内敛。大学毕业后亨利受雇于一家侦探公司,成为一名特工。他与白人姑娘莱丽雅结婚,但是他们的混血儿子米特不幸夭折。亨利被指派监视韩裔纽约市议员约翰·康,窃取康的政治情报。莱莉雅无法忍受婚姻生活的压抑而离家出走。亨利由此陷入了自我身份与家庭生活的双重危机。
小说中,亨利“没有行动自主权,像牵线木偶般完全听凭上司的指令及要求”,“将对美国政府或者跨国公司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的人清除出去”(转自丁夏林,2014:74)。在监视康的竞选活动时,亨利“为自己是否应该出卖同为韩裔美国人而苦恼不已”(转自丁夏林,2014:74)。他的职业要求与族裔情感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从道德哲学层面看,亨利出卖同胞是符合职业道德规范的,但从族裔感情来看,它却招致自我谴责”(转自丁夏林,2014:74)。同时,亨利与妻子莱丽雅的关系也产生了严重危机。职业上的间谍角色,象征了现实中亨利的“双重生活”(Engles,1997:27)。莱丽雅无法忍受在儿子Mitt死去时亨利表现出的“明显的克制”(Engles,1997:31);对亨利处事时体现出的“情感缄默、沉默寡言”(Engles,1997:28)感到不可理喻。她将丈夫这种行为方式视为“韩国父母的文化遗传”(Engles,1997:31),是“儒家社会角色”(Engles,1997:31)的体现。亨利“情绪上的不可捉摸”(Engles,1997:31)曾经使莱丽雅着迷,但是后来却成为他们婚姻的困扰。亨利像“一条变色龙似地在各种假身份中穿梭,窃取了许多‘内部’情报,但牺牲了自己的主体性,甚至忘记了如何与妻子接吻及做爱”(转自丁夏林,2014:75)。小说中,亨利和莱丽雅曾去韩裔公公家探望。回到自己儿时生活的房子里,亨利以韩国人特有的姿势“盘腿而坐”。可在莱丽雅看来,这种坐姿像是“奇怪的类人猿”(Engles,1997:35),难以接受。
现实中,不仅亨利过着“双重生活”,第一代韩裔美国人也扮演着“双重角色”。亨利描述父亲的房子是“错层式的”,象征“追寻‘美国成功’的移民梦”的同时“坚守故国各种传统、价值和习俗”(Engles,1997:34)。父亲的房子也使亨利重新反思移民生活的真正意义。有学者指出,由于横跨两个世界(韩国和美国),亨利感到文化身份的迷失,试图寻找亚裔美国文学先驱赵健秀(Frank Chin)所谓的“亚裔美国感”。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处于“世界之间”的文化身份困境使他成为当“族裔特务”的最佳人选(转自丁夏林,2014:75)。
《说母语的人》展示了美国社会中韩裔的身份困顿,在真实与虚假的悖论中呈现了生动的现实画卷。
从以上文本分析可以看出,亚裔文本表现了亚裔的双重感受。《剑桥美国文学史》主编萨克文·伯科维奇(2005:551)指出,“亚裔美国文化的观察家们把这种痛苦的境遇称作‘双重身份’或者‘双重个性’,他们认为在亚裔美国人的内心,‘亚洲人’和‘美国人’是彼此不相容、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两个自我”。这种“两个自我”在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与协调中,形成了亚裔美国人独有的文化身份,使他们努力在美国“这所大房子里”当家做主。
当然,“他者”是相对于主体性的“自我”而存在的。没有主体自我,就没有所谓的“他者”,两者是互为共生的关系。如果我们视东北亚或者亚洲文化为一个主体,美国亚裔则可以成为“他者”之一。但是,这个“他者”却与东方有着血脉渊源,不可割断。亚裔美国文本,作为体现“亚洲的他者”的途径之一,呈现出了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图景。在这一图景中,原生的亚洲文化与异质的美国文化相遇而生,形成了具有跨文化特质的美国亚裔文化。它从特殊的视角,反映了亚裔美国人在异域他乡的生活,描述了他们的奋斗史,展现了他们丰富的情感生活,从而表现了一个独特的亚裔群体的文化心性。
已故吴冰教授(2008:20)认为,美国华裔文学可以作为“反思文学”来读。同样,美国亚裔文本也可以成为东北亚文化认识“自我”和“他者”的一面镜子,因为它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异同和冲突。这是一种“极为微妙”(胡勇,2003:序)并且带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研究视角,有利于我们和“异域”之人互为观照,启迪文明。
注释:
① 对“亚裔美国感”释义的采用以及引文出处,参见浦若茜文章“‘亚裔美国感’溯源”第98页。
② 译文引自黄际英、简明文章“论泛亚裔族群意识的觉醒——‘亚裔美国人’的文化含义”第105页。
③ 这是美国亚裔批评界对四位华裔作家的戏称:1991年,谭恩美的《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任碧莲的《典型的美国人》(Typical Americans)、李健孙的《支那崽》(China Boy)以及雷祖威的《爱的痛苦》(Pangs of Love)同时出版,评论者以此戏称四位作家为“四人帮”。新“四人帮”则是针对70年代亚裔研究始作俑者赵健秀等四人而言的。
④ 论文写作中,作者得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王胜宇先生提供的资料,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1] Engles, Tim. 1997. “Visions of Me in the Whitest Raw Light”: Assimilation and Doxic Whiteness in Chang-rae Lee’s Native Speaker[J]. Hitting Critical Mass: A 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2):27-48.
[2] Jen, Gish. 1996.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M]. New York: Vintage.
[3] 陈放 陈维新.2006.近年来东北亚文化研究概述[J].东疆学刊,(6):125-126.
[4] 丁夏林.2014.谁是“说母语者”?——解析《说母语者》中的道德伦理困境[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1):73-79.
[5] 董娣.2001.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J].外国文学动态,(7):98-101.
[6] 胡勇.2003.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7] 黄际英 简明.2004.论泛亚裔族群意识的觉醒——“亚裔美国人”的文化含义[J].长白学刊,(3):102-105.
[8] 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2007.詹乔等译.从必需到奢侈——解读亚裔美国文学 [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9] 江宁康.2008.美国当代文学与美利坚民族认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0] 浦若茜.2013.“亚裔美国感”溯源[J].外国文学研究,(4):97-106.
[11] 萨克文·伯科维奇.2005.孙宏译.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12] 王进军.2013.美国亚裔族群发展状态初探——美国观察之一[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1):120-124.
[13] 王绍平 邹莹.2014.美国华裔文学的中国元素共生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5):78-82.
[14] 吴冰.2008.关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思考[J].外国文学评论,(2):15-23.
[15] 吴冰.2012.亚裔美国文学导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6] 徐颖果主编.2012.离散族裔文学批评读本——理论研究与文本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7] 曾少聪 王晓静.2009.美国亚裔族群的认同[J].世界民族,(6):47-53.
[18] 张龙海.2005.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在中国[J].外语与外语教学,(4):41-44.
Writing the Double “Others” in Asian American Text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hematic issues of literary texts by Chinese Americans, Japanese Americans and Korean Americans with Northeast Asian descent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First, two terms “Asian American” and “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are introduced. Then, focusing on identity motif, the analyses are provid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nostalgia, historical burdens and realistic predicaments so as to present the double “Others” in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American texts. Finall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studying Asian American texts benefit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Asian Americans and Northeast Asian culture under the global context.
Northeast Asian culture; Asian American texts; double“Others”
G07
A
2095-4948(2015)01-0029-06
本文为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元素与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共生关系研究”(2012XJZD05)、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立项“英语专业亚裔美国文学课程内容改革与实践”(YJG201205)的阶段性成果。
王绍平,女,大连外国语大学公共外语部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国族裔文学、比较文学与文化、叙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