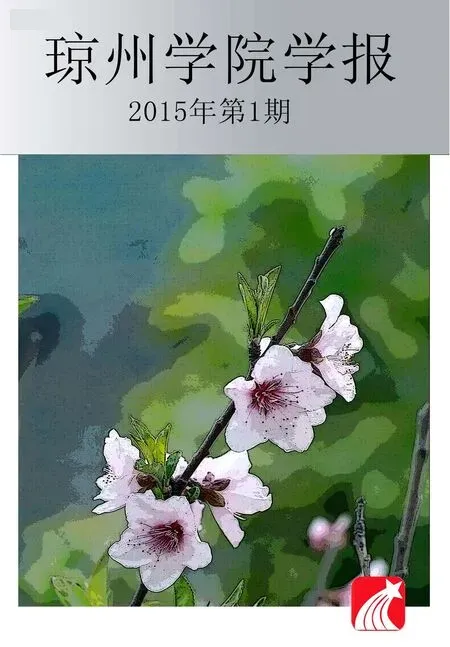拒斥与再发现:近代中国士人对基督教经典的认识
2015-03-27
(集宁师范学院 政史系,内蒙古 乌兰察布012000)
基督教在唐朝初期就已来华,被称为景教,不久唐武宗灭佛,该教受到牵连遭禁,故该教对华人社会影响甚微。元两朝时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被称为也里可温,信教者多为蒙古人,故其对华人社会亦未产生巨大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基督教又卷土重来,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推行上层路线,结交广大中国士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的科学乃至科学方法,就连乾嘉考据学派亦深受其影响。可惜后来传教士干涉中国教民生活,令禁拜孔子和祖先,不从中国之俗,到了雍正年间遂被官方禁止,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又一次来华,所到之处广行传教,势力巨大,对中国上层和下层社会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各阶层与传教运动的关系研究,以往多强调民教关系,且侧重考察民教冲突。至于中国知识阶层与基督教的关系,亦多研究其仇教的原因,对其不加入基督教的情况及其对基督教经典的认识问题则概莫能明。有鉴于此,本文旨在进一步探讨近代中国士人对基督教经典的认识这一问题,以就正于方家学者。
一、多数士人认为基督教经典各种译书文词拙劣,内容浅薄
对于基督教经典,中国传统士人皆认为其译文文词拙劣,不够驯雅。当基督教开禁之初,梁廷枬就指出明末清初以来西方传教士“所刻传书籍”“词未畅达”[1]。魏源也认为“《天学初涵》诸书,利玛窦撰文词尤拙”[2]。1860年之后,基督教传教扩大到内地,为满足传教需要虽然传教之译书不断涌现,然仍不为士人所许可。如王韬就认为其传教书籍“言语亦未能圆融”[3]122。就连赫德在华的秘书孙长也“鄙夷《圣经》的中文译本,认为翻译如此拙劣,则信仰者寥寥,就不足为奇了”[4]。
考其所译之书文词陋劣的原因,其一,基督教经典译作白话文。基督教来华早在明末清初时,其传教的策略是至上而下的,所以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衣儒服,读孔孟之书,以此扩大基督教在传统士人中的影响。虽然如此,但基督教所吸纳的多数对象还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一般来说不识字,皆少知识,所以基督教宣传其教义需浅显易懂,其经典《旧约》和《新约》多译为白话文。正缘于此,陈独秀方称:“白话文的《旧约》《新约》,没有《五经》《四书》那样古雅。”[5]
其二,从明末清初以来西方所译之书多为传教士译作,其书皆不畅达。如马建忠指出:“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6]西方传教士所译之书皆陋劣,其所译传教书籍亦然。张荫桓对此称:“中西文字各殊,西教士游华,厉吾华粗谙华文,遂举耶稣事迹附会成编,远逊佛经内典为中国文人译说耳。”[7]在华多年的美国女传教士也不讳言此事,她称:“有人曾说,撒旦创造出汉语就是为了使中国人置身于基督福音之外。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个美国成年人看来,要毫无障碍地掌握这种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使用的语言,无疑是最大的难事。”[8]
中国士人除认定传教书籍文词陋劣外,还鄙视其内容浅薄。如郭嵩焘记其友人弢公言:基督教“所传之书皆纰缪,无足观览。”[9]8冯桂芬称:“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10]曾纪泽亦称:“偶翻阅《旧约全书》,可笑之至。”[11]可见,中国士人轻视基督教教义内容。
中国士人鄙薄基督教教义内容的原因在于:
其一,士人们认定基督教言灵魂界是袭引佛教天堂、地狱之说,如清初的杨光先早就认定其“剽窃释氏天堂、地狱之唾余”[12]。郭嵩焘亦认为耶稣教“乃多取儒家之义相比驳,而袭引佛氏地狱之说”[9]33。不但中国士人有此看法,就连传教士李提摩太也称“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我才发现,佛教在其高度发展中实际上包含了基督教的一些主要教条”[13]192。可见,基督教与先入为主的佛教相比,其教义内容并没有超出佛教所说的范畴。
其二,士人认定基督教经典无甚高深哲理,遂不能满足其知识需要,读其书不免觉着乏味而无力。如王韬认定“其书理趣未能深造”[3]122。章太炎1906年7月在日本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称基督教:“就理论上说,他那缪妄可笑不合哲学之处,略有学问思想的人决定不肯信仰。”[14]基督教不适宜士人追求哲理的需要。如曾国藩称:“鄙意洋人教术本不足以惑人。”[15]
其三,士人认定基督教经典与儒家言人间世相比,亦不足观览。当时,士人们固守孔孟之道,还认为中学优然于万国之上,相反鄙视基督教教义。他们还抱乐观态度,相信“以夏变夷”的力量,令化外之国以从孔孟之道。如李元度对基督教传教的看法:“窃谓不足虑。抑且深足为喜,不惟不虑彼教夺吾孔孟之席,且喜吾孔孟之教将行于彼都,而大变其陋俗。”[16]邵作舟亦称基督教“荒诞浅陋”,而“圣人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圣人之道,彼不深知则已,苟深知则将自惭其为教之陋,而忻喜服从必矣”[17]。
总而言之,正如康有为所认识:“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18]况又没有高深的哲理,故中国士人笑其经典浅薄,不值得过目一览。如蒋敦复所称:“所论教事,荒谬浅陋,又不晓中国文义,不欲通人为之润色,开堂讲论,剌剌不休,如梦中呓,稍有知识者,闻之无不捧腹而笑。”[19]
二、少数士人挖掘基督教教义及其组织的力量,借此来改造中国
大多数中国士人笑基督教经典浅陋,质而言之,士人对西方传教士传教敌视甚深,对其经典亦少研究。如宋恕称:“基督教来禹域,士大夫憎之甚,鲜肯虚心阅其语录。”[20]615由于士人精研不深,遂笑其浅陋。其实,基督教作为世界宗教而言仍有其优势方面。
早在明末,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就有文化上的优越感,《明史》载称“其徒又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21],然而,中国士人多不相信其说。到了近代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为列强所环伺,国家岌岌可危。为挽救危亡,有识之士学习西方技术以及政治制度的同时,亦开始重视其宗教文化。梁启超就观察到“近日士夫多有因言西学,并袒西教者,慑于富强之威,而尽弃所据”[22]。1897年李提摩太亦称:“有些改革者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儒教过于功利和世俗,大胆地主张采用基督教为国教。”[13]243
这些改革者中如谭嗣同在其著作《仁学》中,亦称赞“西人之喜动,其坚忍不挠,以救世为心之耶教使然也”[23]134,又云:“耶教有民,孔教无民。”[23]94据梁启超回忆称:“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24]可见,谭嗣同于基督教确有深服之处。同时代的晚清名士宋恕,也认为“儒教及基督教最为相近”[20]616。因为相近,故其对于基督教之学说也有甚服之处。维新变法的中心人物康有为,看到了基督教教义之短,同时亦看到其教义之长。他认为基督教教义:“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谓不二法门也。”[18]
对于基督教组织,改革者和革命者亦看到其长处而加以利用。如康有为欲仿行基督教组织改造孔教,将孔教定为国教,以此对抗基督教的入侵。对于康有为此举,当时反对改革者将此条列为其罪名之一,如“湖南举人曾廉,劾有为觊觎非常,大有教皇中国之意,上孔子以开化教主神圣明王徽号,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25]当时,处于社会边缘的革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更是浚掘其力量,借此来改造中国。如孙中山,据冯自由回忆称其加入基督教,“完全出于基督教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义,为进步的及革新的,与世俗之墨守旧章思想陈腐者迥然不同”[26]。孙中山后来自己亦声称:“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27]569-570此后,孙中山擘画革命的具体方法上亦借助基督教组织形式,故冯自由称:“总理自倡导革命以来,所设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团体。其誓约均冠以当天发誓字样,是亦一种宗教宣誓的仪式,盖从基督教受洗之礼脱胎而来也。”[26]革命党中入教的不独孙中山,而是多有人在。他们从中攫取精神力量,试图改造中国。所以陆丹林称“革命党和基督教在历史上的关系,是光明的伟大的”[27]586。
结 论
近代以来,作为社会上层阶级的中国士人认为基督教经典译文文词陋劣。其文词陋劣的原因:其一,基督教经典译书多译作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当然无法与文字古雅的佛教经典相比;其二,译书多为传教士所译,而传教士多未谙熟中国语言文字。不仅基督教所译经典文辞没有吸引力,士人认为基督教经典内容与儒家言人间世相比不够精备,与佛家言灵魂界相比又不够圆满,遂认定其内容浅薄而又少有高深的哲理,所以对其经典往往视而不见,不加精研。进而言之,基督教教义不能满足中国社会上层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需要。虽然如此,基督教对于社会中下层却有吸引力。据徐珂称基督教:“有佛教之神道作用,而无空寂之弊,有回教之坚忍不屈,而与人群无忤,对于中下社会,最为适宜。”[28]换言之,基督教在中下层社会还是有发展空间的。
甲午战前,中国这一“天朝上国”虽然屡屡向西方让步,但仍能维系朝贡制度于不坠,然而经过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鲜这一主要藩属国也脱离出去,这标志着朝贡制度彻底向西方条约制度的让步。换言之,甲午战争惊醒了中国士人“天朝上国”的迷梦,遂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士人对传统的文化进一步加以反思甚至否定,对外来西方文化的认识亦进一步深化,就连以往他们所排斥的基督教也重新加以审视。那时,少数士人认识到基督教教义的普世力量,试图借助其思想及组织形式来改造中国。此后,这一思想仍然为后人所赓继。比如进入民国的冯玉祥将军,就声称:“或谓吾人信教为迷信,为媚外,实则不然,盖纯为拯救贫苦无告之平民与将亡未亡之国家计耳。”[29]换言之,冯玉祥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寄托了他改造中国的希望和理想,冯遂以基督教治军,被目为“基督将军”。又,近代中国士人阶层不加入基督教的情况及其原因还可进一步探讨,限于篇幅,本人拟另文加以研究。
[1][清]梁廷枬.海国四说[M].骆驿,刘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7.
[2][清]魏源.海国图志[M].李巨澜,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236.
[3]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传教下[M].陈恒,方银儿,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4][英]赫德.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M].傅曾仁,等,译.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380.
[5]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M]//汪中江,苑淑娅,选编.新青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400.
[6][清]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M]//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69.
[7][清]张荫桓.张荫桓日记[M].任青,马忠文,整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20.
[8][美]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往日琐事:一位美国女传教士的中国回忆[M].程麻,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21.
[9][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卷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0][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戴扬本,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09.
[11][清]曾纪泽.曾纪泽日记[M].刘志慧,点校辑注.长沙:岳麓书社,1998:1462.
[12][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M].赵春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22.
[13][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4]章太炎.演说录[N].民报,总第六号.
[15][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复倭仁[M].长沙:岳麓书社,1994:6981.
[16][清]李元度.答友人论异教书[M]//郑振铎.晚清文选.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7:129.
[17][清]邵作舟.邵氏危言[M]//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83-184.
[18]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M]//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8.
[19][清]蒋敦复.论传教[M]//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33.
[20][清]宋恕.宋恕集:上:致南条文雄书[M]//胡珠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
[21][清]张廷玉,等.明史:外国传七:意大里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460.
[22]梁启超.读西学书法[M]//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456.
[23]谭嗣同.仁学[M].印永清,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4]梁启超.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谭嗣同传[M].陈引驰,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64.
[25][清]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M]//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55.
[2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孙总理信奉耶酥教之经过[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
[27]陆丹林.革命史谭[M]//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第一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8]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56.
[29]冯玉祥.冯玉祥日记:第二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