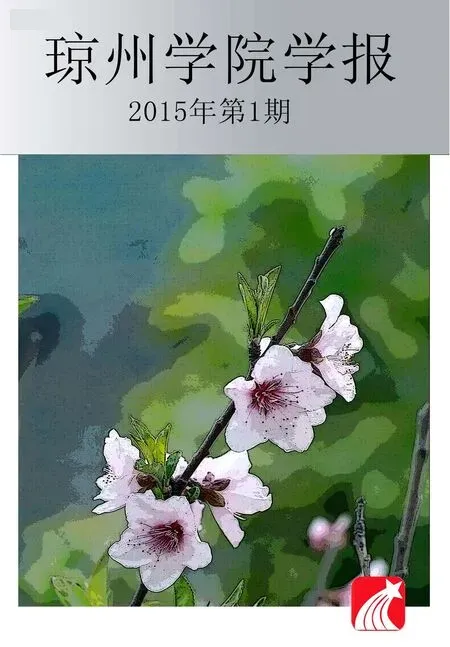论鲁迅《野草》中二元对立思维的生成及其超越意义
2015-03-27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京210097)
对于《野草》的文学价值,学术界向来有着极高的评价,自其问世以来,研究从未中断,而对于野草的解读,依旧是未竟的事业,或者可以说,《野草》的意义正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索可能。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部写于1924年至1926年鲁迅人生中最阴暗时期的作品,包含着最透彻的“鲁迅的哲学”。
一、一以贯之的二元对立思维
“二元对立”原则最早由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语言学理论,最初包括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历时(Diachronic)与共时(Synchronic)、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句段(Syntagmatic)和联想(Associative)的关系。之后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等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拓展和延伸,而这一原则也从语言分析拓展应用到诗歌以及叙事性文本分析。其中格雷马斯在他的《结构主义语义学》一书中提出了“语义方阵”的概念,对“二元对立”进行了语义与叙事结构上的阐述,他认为在任何意义的结构中,都有着一种基本的对立关系,既是语义上的对立也是叙事结构的对立。这一理论被广泛实践于文学批评之中,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元对立”原则也被用于中国文学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中。
本文提到的鲁迅的“二元对立思维”是指《野草》文本中的种种矛盾、悖论所体现的鲁迅对立式的思维特点。这一思维特点贯穿在《野草》的每一篇散文中,对当时社会国民人性的对立剖析、对自我存在的分裂态度、对生死抉择的辨证思考、对未来可能的徘徊焦灼这几个方面的深层思虑是整部《野草》的主要内容,而鲁迅对每一方面的思考方式都体现出一种极端的对立化,二元对立已经成为出现于《野草》中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造成精神上的矛盾冲突,体现着鲁迅深重的灵魂困苦。《野草》浸润着鲁迅极其深刻的生存哲学,鲁迅对于现实人生作亲历后的深度思考,对于我心灵作本我抽离式的理性剖析,对于存在本身作终极意义的灵魂叩问,在幽深的暗夜中长时踽踽独行之后,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纠缠于重重矛盾中的痛苦生命体。分析这些矛盾,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项思维对立。
(一)诅咒与悲悯
鲁迅是一个对人性看得很深很透的人,这与他早年家道中落,受尽人世炎凉的童年记忆有关,青年时走异路逃异乡的特殊经历也使他对人间的善恶有着较悲观的看法。他对人性的判断中,悲悯与诅咒并生。《失掉的好地狱》中人类带领恶鬼重新取得了地狱的统治权之后反使得原来废弛的地狱变得残酷无比,揭露出人性中的“恶”事实上比恶鬼有过之而无不及;两篇《复仇》中回荡着同一个主题,即对社会众生中麻木不仁、赏鉴无聊以致自相残杀的民族劣根的辛辣讽刺;《颓败线的颤动》中同样包含着这种对恩将仇报之不义的愤怒,如青年男女对老妇的鄙夷,孩子的“杀”;《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狗的驳诘》《立论》《求乞者》四篇,以对话和短剧的形式将人性中的多面进行具象展现,分明流露出对圆滑逢迎、趋炎附势、名利分别、敷衍塞责、卑膝求乞等卑鄙人格和社会丑态的强烈斥责,对坚守正直、真理,无分别心,直面现实等崇高品质的呼吁,而之所以怀有激烈情感的斥责和呼吁正是基于对人世的大悲悯。
而对于“恶”并非纯粹报之以诅咒,在《复仇(其二)》中并置重复了三次的“诅咒(仇恨)”与“悲悯”的话语正是鲁迅对众生相的矛盾态度。将人性的罪恶尽置于怒斥和拯救,也是鲁迅哲学,施以霹雳手段,正是出于慈悲心肠。对于有着被鲁迅所批判的人格的那些人,正如尼采哲学中的“末人”,但从“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1]178(第二卷)一句中,可看出作者非如尼采一般全然希望他们灭亡,还仍旧以悲悯的心认为他们将有前途。
(二)自爱的我与自憎的我
鲁迅曾说,他“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1]178(第三卷),《狂人日记》中,“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妹的几片肉”[1]477(第一卷)中对自己不清白的悔罪意识,也同样出现在《野草》之中。很大程度上,其中体现了“鲁迅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对于自我生命的一次深刻反省和彻底清理”[1]454。
《影的告别》向来是被评论界认为难解其中意的作品,不过该诗篇透露出来的自我决裂意图是明显的。孙玉石认为,这首散文诗是“鲁迅向‘影’所代表的消极思想的决裂”[2]47。而笔者认为正相反,“影”是鲁迅自己的投射,影与“我”作告别,离现实的人间而去,也离未来的黄金世界而去,宁愿在黑暗里,享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显然体现一种坚守自己黑暗面的执着,宁愿留守于孤独而沉着的战斗,是因为看穿了自己曾经梦想过的未来的黄金世界,因此对过去的自我作诀别。
《腊叶》可以看作是鲁迅对自我生命的珍视。他清醒地看见自己心理上消极悲观的部分,自哀为“病叶”,却仍旧不希望这病叶像与他叶子一同飘散,说明他既自憎这些阴暗面,又自爱它们,且并不视为必须剔除的人格弱点。对于“病叶”的珍藏,说明他对自己精神中阴暗面的直视,同时留恋、自爱。体现了自我与自我的分裂和矛盾。
以上可见,“自我谴责和灵魂的自我解剖,是《野草》生命焦虑的又一显著特征”[3]154。
(三)死亡与存活
死亡与存活的对立,在《题辞》中体现的极为突出,“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凭借死亡知道曾经存活的迹象,是现代哲学的一个反向辩证思维。这一思维在《野草》中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多种演绎。《死后》一文中借“死后”这一艺术技巧,以死人的眼光看出生者的社会状态,描画了人世的种种势力利益纷争。《复仇(其二)》中耶稣的死也是庸众的生的强烈反照,对比出生者的无谓。《淡淡的血痕中》对几个死者的悼念,也是为了生者更好的活。
但死亡并不是单独意义上的消亡,借死亡以知生存,正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中“向死而生”的一个命题的演化形式。生的意义从根本上体现为它的有限性,人不可能逃避的终极归宿,为生命的无限可能提供了一个敞开的空间。死是必然的归宿,但是通向这一归宿的路却有很多条,而对于道路的无数次选择和体验过程就是生存的根本意义。《死火》中徒具“炎炎的形”的死火面临着要么烧完、要么冻灭的抉择,虽然最终都不免一死,而选择死的方式也正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死火选择与其冻灭,不如烧完,这与《过客》中的不停地走的过客形象也是同一种意志的表征,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在人生的后期“拼命地做”也正是在践行他自己的哲学。
(四)绝望与希望
这一对立项是《野草》中最强烈的矛盾,也是始终横亘在鲁迅哲学世界中的精神桎梏。“发源于希望与绝望的诸多矛盾,最后归结为一个现实生存的难题——生与死的抉择,这就是《过客》《死火》和《墓碣文》中生与死的追问。”[4]145
此外,《好的故事》以《野草》中少有的温柔笔触描写了一个十分美好的梦境,然而最终梦境的幻灭也是希望的幻灭,《秋夜》中“夜半的笑声”惊醒了小粉红花的梦,使“我”退回屋内,也即意味着作者认为希望是一种虚幻的梦境,最终经不起现实的笑声。
《希望》中,鲁迅引用了裴多菲的诗歌来说明希望的虚无和欺骗性,并最终同时否定了希望和绝望的存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182(第二卷)希望与绝望的有无又引申出更深层次的一对矛盾,即类似于盘桓在叔本华和萨特的哲学中虚无和实有的矛盾。
二、佛学、尼采哲学和启蒙思想的交叉影响
《野草》中含有的极强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同时否定对立项双方的思维形式受到了禅宗思维逻辑的影响。不仅如此,佛教的世界观,尤其是悲悯情怀也深植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之中,可以说,佛学在思维形式和精神内涵这两方面都给了鲁迅极大的滋养。《野草》中流露出来对人间的怨毒、诅咒、复仇等意念则来自于尼采哲学中对末人和奴隶道德的否定。当悲悯与诅咒的矛盾内化于鲁迅自己的精神世界时,便产生了自我决裂的冲突,强化了文本中的二元对立思维。鲁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境遇使他产生对人世的绝望与生的幻灭感,而尼采哲学对虚无主义的哲学观感给了鲁迅更具超越性的认知,加之启蒙者所负载的道义责任使得他的内心仍根生着希望的火焰。《野草》中强烈的二元对立思想就是在东西方多重哲学思想影响之下回旋激荡、愈演愈烈。
“禅宗常把两个对立相反的命题放在一起,对双方都既不予以肯定,亦不予以否定,而是以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态度处之。”[5]37禅宗的这种思维形式显然很大程度上对于鲁迅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塑成作用。汪晖提出的“在”而“不属于”[6]113两个世界,也透析了鲁迅思维导向上的这种现象。汪卫东曾分析佛教的否定逻辑方式“倾向于以否定的方式来阐释自我与世界”[7]77。这种思维形式在《野草》体现得极为明显。《影的告别》中的“影”拒绝黑暗的吞并以及光明的使其消失,处于对立的抉择之中,两者都是对生命的否定,而最终“影”选择彷徨于“无地”。将具有强烈反差的矛盾双方并置,用以表达作者内心的极大的痛苦,最终和合于虚无之中予以超越,这种逻辑与禅宗思维在形式上是一致的。禅宗的思维使《野草》在艺术上有更强烈的张力,又使其在思想上更具矛盾冲突,而同时佛学本身并无二元对立的思想,它更强调的是对于一切有无的“破”,即以超越的思维来破除世间一切的辩证存在,再将“破”本身予以破除,还原世间的本体,即“如来”。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鲁迅的思维习惯产生了影响,而鲁迅以自己的方式将其进行化用,在直面人生的精神上对其二元对立思维的实现超越。
佛学的精髓在于以出世的情怀入世渡人,点化与棒杀都是方便法门,不变的是悲悯情怀,这也是成就鲁迅博大胸怀和坚韧意志的精神源泉。鲁迅由于自身的童年遭遇及当时身处的黑暗时代,更亲近于佛学中的“悲”念,即深谙于自己的痛苦,出离之后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慈悲辅成便生普度众生的大愿心。佛经认为,小悲悯观众生种种身苦、心苦,怜悯而已,不能令脱,大悲则怜悯众生苦,亦能令脱苦。迅介于小悲与大悲之间,鲁迅穷近半生都在探索救民的道路,办《莽原》等杂志,奖掖后进等,事实上早已成为青年们的精神导师。他和他的青年们对立于当时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无异于单枪匹马,所以终究“不能令脱”,但心念俱存,尽心竭力,以此为上。《颓败线的颤动》文末有“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这一句鲁迅给了“她”一个无语逼问苍天的动作,极其强烈地流露出他对这个老女人的哀悯,竟至于“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这种挣扎,更体现出极强的救赎意图。
鲁迅在《野草》中表现出来极为晦涩阴暗的思想特征,充满了对人间的诅咒、怨毒和绝望,无不透露出对于身处环境的恨意。这种恨意自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而究其思想来源,来自于尼采哲学中对于懦弱、怜悯等奴隶道德的批判,以及对肤浅自利、自我戕害、逃避现实的“末人”的审判。这样的批判与审判对外产生的是诅咒,对内则生成了自憎与自爱两种背反人格的决裂,甚至本体上的绝望与虚无感。
汪晖以“自我否定”来定义鲁迅的反传统斗争,“与‘传统’决裂的最终极的标志”[6]65体现为对自身中传统因袭的自省与否定。《秋叶》中“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这一句流露出了内心潜伏着的畏缩逡巡的意识,《狂人日记》里“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自憎,甚至对于庸众的怜悯,意志的稍许薄弱,在尼采那里都是“末人”。而“自爱”则多是出于如《腊叶》的英文译本序提到的为了“爱我者想要保存我”也存了一点自我保存的意思。如此便产生了极为强烈的自我决裂。
尼采对于虚无主义持辩证的态度,他认为“虚无主义对永恒真理的拒斥和对形而上学世界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使哲学家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从而为他们超越传统的价值立场并重估一切价值提供了可能”[8]292。鲁迅正是由于对一切希望和前途的绝望而产生了虚无的本体感受。“影”的意志是“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因为看透了人间一切求乞无赖的丑、虚伪敷衍的恶、空许哄骗的假,所以他“愿意只是虚空”,最终获得“全属于我自己的”黑暗世界。向虚空的靠近就是对一切伪价值的否决,否决之后才能做到真正的反抗与立新,进行对一切价值的重估。
价值观上虚无本质必然导致对生命的中利己成分的轻视,即对生死的达观。鲁迅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道:“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1]165(第三卷)不仅不嫌恶,还对死亡充满着“大欢喜”,借此知道存活的意义。对于生死,鲁迅吸收了尼采哲学中张扬生命本有的个性和能量诉求的部分,如《野草》中不惮于烧完自己的死火,自啮其身的死者,奇怪而高的刺向高空的枣树。但尼采哲学中将生命视为不断自我创造、超越的流变性和强力意志在鲁迅这里似乎没有明显的体现。在鲁迅那里,死是一种截止,生命是在截止之前向虚无抗战的凭借。这种思想受到了现代主义和尼采哲学的影响,但又体现出鲁迅独特的精神品质,更大程度上与存在主义“向死而生”的哲学相合。
鲁迅在《野草》中流露出来的绝望和虚无感是绝对的,但其希望其实显得毫无根据。在他的心中“未来的黄金世界”不过是圣贤牧师布道的幌子,给人暂时的麻醉。《希望》这一篇就已抹杀了一切希望的可能,所谓希望,不过是虚妄。但在鲁迅的文学作品甚至信件中,希望又是一个不断反复并上升的主题。那么这种希望又从何而来,究竟为何呢?
笔者认为《野草》写作时期,鲁迅自己的世界观中对希望是存有怀疑的,而他用以激励别人的希望,一方面是持着不能完全否决将来的“不可知”经验主义认识论;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启蒙道义而作出理性鼓舞。鲁迅曾坦言,“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1]165(第三卷),因为不愿将自己过于晦暗的思想传染给别人,因为不能确知是否果真如自己所想。而更大程度上则是因为承担着启蒙者的责任,不能给青年以消极的影响,偏要做出绝地的呐喊,来鼓舞人战斗。尽管鲁迅早期抱着进化论的观念认为孩子和未来总是好的,但经历过多重现实的碰壁,在创造《野草》时期流露出来的希望则多半出于启蒙道义。
在作《希望》不久之后,鲁迅在杂文《忽然想到三》中说道:“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1]15(第三卷)这里对于希望的语气是暧昧的,“希望”仅仅是万一的侥幸,说明鲁迅心中对于希望的信心是十分渺茫的,之所以还残留着,是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说,人不能否认未来有存在的可能,但“慰藉”一词显然透露了彼时的心虚。再则,鲁迅在给许广平的第二封信中无情地剖析了圣贤学者的“将来”无异于牧师所说的“死后”,都是叫人忍耐现实苦楚而撒的谎。但他在第八封信中却流露出了对于“希望”和“将来”的执着与渴盼:“但我总还想对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1]845(第三卷)这说明在这一时期鲁迅内心对“希望”的犹疑不决、将信将疑,可以肯定的是他仍旧没有放弃将来的希望,他仍寄望于志同道合且能并肩作战的青年,也是因为作为启蒙者“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1]63(第三卷)生于现代中国的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命运,对现实有着极强的关怀的伟大人格决定了鲁迅必然承担启蒙者的身份。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526(第四卷)。为人生,为民族而担负启蒙重则始终是鲁迅生命的意义所在。启蒙者主义实已内化为鲁迅的生命哲学。
三、鲁迅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及其价值意义
尽管《野草》中充满了二元对立的思维,但事实上这样的诸多对立并非实际上和永久性的对立。鲁迅的精神世界也并非停留于绝对的矛盾之中。鲁迅在勘破种种思维上的、现实中的对立矛盾之后,最终实现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得以实现超越乃是基于鲁迅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怀和强大的生命意志,超越不仅是对于现实中种种矛盾境遇的超越,更是对自我生命哲学困境的超越,其意义在于铸就了一位更其坚韧伟大的精神探索者和现实战士,并成就了一部饱含深邃丰盈的精神内涵和无限开放性阐释空间的经典著作。
鲁迅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剖析,前提是他对真实的社会人生有着深切的关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无可逃避地流转着整体时代的基因。《野草》不仅是内在心灵的自我剖白,更是对社会历史的理性认识的精神书写。一直在行走中的过客形象可以被看过鲁迅的精神缩影,过客与老翁和女孩构成三种人格类型,学者李天明将他们所持有的人生哲学分别归结为“存在主义、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9]83。过客既没有听从老翁的劝告,因为知道人的终极归宿是“坟”而停止对道路的探索和人生的行进,也没有像女孩一样自耽于鲜花满地的黄金世界的幻想,明知前方是“坟”,却仍旧迎刃而上,显然已经超越了希望与绝望、生与死的生存困境,在现实中实现此在的真实意义。《长明灯》中疯子要吹灭长明灯,哄他不行,打他不行,关他不行,这种种阻碍正像过客遭遇老人的苦心劝慰(前面是坟地),以及女孩子的“布施”。但疯子还是要吹灭长明灯,且要自己吹,而过客仍要走,一直走。那个使他“息不下”的那个召唤他的声音,既是现实本身,也是启蒙者所怀有的唤醒蒙昧群众的使命,超越的力量来自于对现实的不自欺,更源于对普遍世间的大悲悯。面对幻想中的静女白云,他在《一觉》中写道:“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人生在世,不可超脱的生存境遇就是“在此”,在人间的有限生命对于一个有生命力的灵魂有着不可阻挡的召唤力量,使其能够实现对重重现实矛盾、思想困境、生命限度的超越。
我们在《野草》中看到的种种由强烈的二元对立所造成的思维冲突和精神困境,事实上正是鲁迅实现其精神超越的过程:“当矛盾和抗争都达到极致的时候,生命就实现了一种精神超越。这种精神超越是通过自我的否定之否定而产生的,来自于灵魂的自我搏斗。”[10]70东西方多重思想文化以及现实的压迫在鲁迅心中形成了一个淬炼其意志的熔炉,长久的自我否定和灵魂搏斗最终熔铸了一个坚毅的精神探求者和沉勇的现实斗士。
其坚毅沉勇首先体现在不执著于启蒙战斗的手段:诅咒也是实现悲悯的手段,正如《碧岩录》中南泉斩猫的典故,“杀”也是救渡的法门;其次,超脱出自我生命的局囿,真正实现了向“超人”的迈进:“自憎”与“自爱”都是生命的呈现形式,而于生命本身的力量并不妨碍,死火选择烧完自己将“我”救出冰谷,过客听完了老翁和女孩的劝告,仍旧选择向前走,就是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摒弃了憎与爱的困局走向社会大我;再次,达到“无所待”式的精神境界:勘破了希望和绝望都是虚妄,既不会受到希望的诱惑,也不至被绝望所打击,以此进行向黑暗与虚无作持久而坚韧的战斗。
此外,作为启蒙者,鲁迅看到了超前于时代的社会追求,同时也作好了超越于现实困境的身内身外的战斗准备,他对知识阶层的解读也正是对自己的剖析:“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1]227(第八卷)他对于社会诉求的超时代性,使其超越自己身上的矛盾和人格障碍,投身于对解救时代弊病道路的精神探求更在长期的现实斗争中探明了一二门径:不能求助于宗教的“善”来解救人世间的苦,而要通过锻造自己的强力意志直面惨淡的人生,更要唤醒富有青春热血的青年来做更为广大深沉的抗争。鲁迅曾用文言翻译过尼采著名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译名为《察罗堵斯德罗绪言》。而这本书中所包含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了鲁迅的哲学。苏鲁支(查拉图斯特拉)在他的第一个伴侣死后发出了“我需要伴侣”[11]16的呐喊,也正是鲁迅在《一觉》中鲁迅对“粗暴起来”的“青年的魂灵”的号召,其中所传达出来的坚定思想,仿佛是在长久幽深的暗夜中透出了一线光明。鲁迅由于看到了在人间屹立着的愤怒而粗暴的青年而感到由衷的欢欣,这是对长久抗争的回馈,更是吹起了继续抗争的号角。这也是《野草》的终结。
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是贯穿于《野草》整部作品中较为突出的思想、艺术特征,而鲁迅在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在形而上层面体现为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也是成就其艺术价值最重要的核心意义所在。重重对立项扩大了《野草》的横向思维场域和艺术空间,而自我灵魂、现实冲突、生命哲学等多层面上的对立伸展了《野草》精神世界的纵深。察其思维对立的特点是反向的绝对对立,这种强烈的重重矛盾互相激荡思维过程使得文本充满了张力,形成思想的丰盈和逻辑紧绷。
而《野草》中多用形而上的抽象命题作为对立的思维载体,使得表层文本体现出一种歧义罗织而精神内核无所皈依的文本形态。抽象命题及其导致的歧义释放了解读的可能性,能指的表意模糊造成所指的无限延伸,以致文本呈现出一种无限开放的状态,开拓了其艺术境界。如《墓碣文》中“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类充满辩证哲思又没有确实摹状对象的语言,将《野草》的解读空间推向了极致。开放的解读空间投射在读者的阅读思维中又形成了读者心理空间上的无限延展,反过来深化了文本的精神内涵和艺术蕴藉。而最终鲁迅在文本中实现对于二元对立的超越使得文本的精神内核得以凝聚,可以算得“体露金风”,即灭却种种分别妄想之后显露出生命本体上的真实义,也是《野草》最终的精神、艺术旨归。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孙玉石.《野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7.
[3]李骞.存在的焦虑:论《野草》的生存哲学[J].文学评论,2007(6):151-155.
[4]汪卫东.《野草》的诗心[J].文学评论,2010(1):141-149.
[5]何明.试论禅宗的思维方式[J].云南学术探索,1993(4):35-37
[6]汪晖.反抗绝望[M].上海:三联书店,2008:113.
[7]汪卫东.渊默而雷声——《野草》的否定性表达与佛教论理之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1):75-88.
[8]刘放桐.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2.
[9]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83.
[10]郭翠英.矛盾与抗争:《野草》的生命意识[J].名作欣赏,2010(17):69-76.
[11][德]尼采.苏鲁支语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