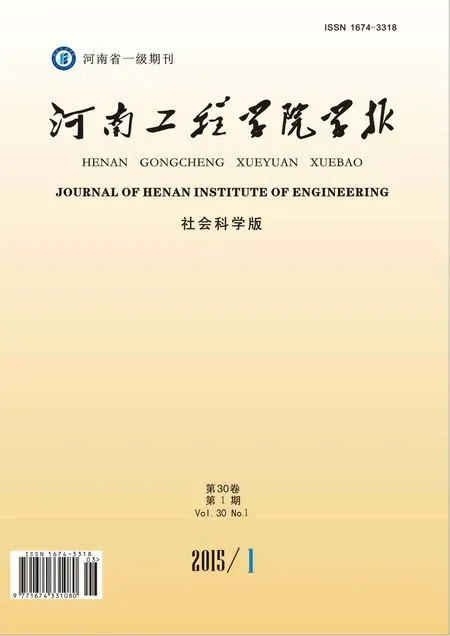“大跃进”运动研究在西方
2015-03-27李春来
李春来
(1.中共温州市委党校,浙江 温州 325038;2.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大跃进”运动研究在西方
李春来1,2
(1.中共温州市委党校,浙江 温州 325038;2.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大跃进”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历来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点。自“大跃进”运动伊始,西方学者就开始将之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经过数十年的积累,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西方学者主要运用克里姆林宫学、新制度主义、模型、定量分析以及社会史等研究方法,从“大跃进”运动的起源、失败原因、影响等方面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西方学者新颖的研究手段和开阔的研究视野值得国内学界借鉴。
关键词:“大跃进”;西方;研究范式;研究模型
“大跃进”运动作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历来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点。自“大跃进”运动伊始,西方学者就开始将之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经过数十年的积累,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西方学者的研究,无论是其主要观点还是研究方法,都有许多值得国内学界借鉴的地方。通过梳理西方学界“大跃进”运动研究的研究概况、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可以借“他山之石”,搞好我们自己的研究。
一、西方学界关于“大跃进”运动研究的基本概况
“西方人比较着重于研究‘范式’,离开了研究‘范式’,也就难以进入学术潮流,而一旦‘不入流’就有‘失范’的危险。”[1]3由于受资料来源、当时的政治事件、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学界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经历了数次转换。相应地,西方学界的“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模型(model)也不断进行调整和改变。因此,根据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式与模型的变化,可以将西方的“大跃进”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用资料主要限于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足。一些西方学者直接把苏联研究中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研究范式应用于当代中国研究,[2]强调精英“合作(consensus)”,假定一个基本上统一的领导层通过协商来制定政策,进而实现有效统治。[3]受此影响,这一阶段研究“大跃进”运动的西方学者主要采用“毛挂帅(Mao-in-command)”模型。这一模型认为: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拥有一种奇里斯玛的极权主义领导、群众的崇拜、行政管理的人员和官僚等级制的辅助。[4]这一模型的代表性著作有晁国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5]、史华慈的《极权主义巩固和中国模式》[6]等。
(二)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前期)
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暴露出的精英冲突和社会紧张使西方学者意识到“极权主义”范式的局限性,许多西方学者转而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另外,受西方社会科学兴起的“行为革命”的影响,这一时期,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开始强调政治中的精英参与者以及政治的非正式过程,把领导层冲突和各种社会群体追求政治利益看成是中国社会生活、政治事件和外交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时期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是“多元主义(pluralism)”,强调精英“冲突(conflict)”。[4]受此影响,这一阶段西方学者在“大跃进”运动研究中运用的研究模型主要有以下三种:
1.“两条路线斗争(two-line struggle)”模型
这一模型以毛主义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目标和结果的解释为依据,假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分裂成两个“司令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以不同的世界观信仰为基础,是精英在公开的世界观冲突中动员群众所造成的两极分化的产物。[4]倡导经济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大跃进”方案。而“大跃进”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派”路线战胜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派”路线的结果。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利,“右派”路线的力量增强,开始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占据上风,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被迫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这一模型的代表作有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跃进”:1958—1960》[7]等。
2.“派系(factionalism)”模型
这一模型假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不断分裂为无限数量的派系或者忠诚集团,这些派系或者忠诚集团以主从关系(patron-client)、共同的背景和其他持久的忠诚纽带为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派系或者忠诚集团将在公开的冲突和不稳定的联盟之间交替。“派系”斗争的根源是权力斗争。因此,“派系”只存在于精英之中。[4]这一模型的代表作有黎安友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的派系模型》[8]、多梅纳克(Jean-Luc Domenach)的《“大跃进”的起源:中国的一个省(1956—1958)》[9]等。
3.“循环(cycles)”模型
这一模型假定针对不同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会形成发表意见的松散的单个人的联合体——“观念集团(opinion group)”。“观念集团”背后没有“派系”那样“可支配的有组织的力量”,也不像“两条路线”的阵营那样泾渭分明,围绕不同的问题会不断形成不同的“观念集团”,“观念集团”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表达不同的利益与要求,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与权力斗争。“观念集团”之间影响的此消彼长造成了政策不断地在“左”与“右”之间摆荡、循环。[10]这一模型的代表作有张旭成(Parris H.Chang)的《中国的权力与政策》[11]、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和温克勒(Edwin A.Winckler)的《共产党中国的服从连续性:循环理论》[12]等。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
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行为革命”之后是80年代的“结构”的反革命。80年代以来,政治学兴起“结构主义”(或“新制度主义”),强调国家结构在塑造政治行为和结果中的重要性。政治结果不能仅仅解释为参与者或者参与者联盟之间竞争的利益的产物,相反,应该关注制度环境对政治冲突及其结果的影响。一些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开始注意到“多元主义”范式趋向于忽视中国的国家“结构”的作用,过多地集中于精英“参与者”。[3]因此,这一时期,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开始引入政治学的“结构主义”(或“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强调政策过程中精英与官僚机构的互动、官僚机构内部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和官僚机构的作用,开始关注精英参与者的不足,更多地注意结构对于精英行为的限制。[13]受此影响,这一阶段从事“大跃进”运动研究的西方学者主要采用“官僚政治(Bureaucracy)”模型。他们认为,随着官僚机构日渐增长的劳动分工、机构扩张,中央的监管将变得更加困难,不同的官僚机构具有对他们所控制的资源的“所有权”,政策结果部分是普遍存在的官僚机构内部竞争的产物。[14]这一模型的代表性著作有大卫·M.贝奇曼(David M.Bachman)的《中国的官僚机构、经济和领导:“大跃进”的制度起源》[15]等。
(四)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在“规范意识危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西方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没有明显的占主流的研究范式。[1]246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结构主义”(或“新制度主义”)预先假定的中国国家结构的稳定性和制度化实际上并不存在,而80年代之前的研究范式仍有一定价值。因此,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面临着如何整合“极权主义”“多元主义”“结构主义”等研究范式的挑战。[2]受此影响,这一阶段西方学者在“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中主要采用“宫廷政治(a court politics)”模型。这一模型试图将“毛挂帅”“派系”“官僚政治”等模型结合起来,把“大跃进”的主要政策变化看成是高层精英政治的产物,而“宫廷政治”就是领导层政治的支配性模式。在1955—1959年,毛泽东一直处于未受挑战的政治支配地位。各个“派系”和“官僚政治联盟”绝对地服从主席的权威,他们或者通过使主席相信他们的政策偏好来寻求促进他们的政策利益,或者通过解释主席的经常模棱两可的指示来尝试提升或保持他们的政治职位。这一模型的代表性著作有泰维斯(Frederick C.Teiwes)和孙华伦(Warren Sun)的《中国通往灾难之路:“大跃进”发动中的毛、中央政治家和省级领导人(1955—1959)》[16]、艾尔弗雷德·陈(Alfred L.Chan)的《毛的十字军:中国的“大跃进”的政治与政策执行》[17]等。
二、西方学界关于“大跃进”运动研究的主要内容
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研究经过五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西方学界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大跃进”运动的起源、失败原因、影响、评价等方面。
(一)关于“大跃进”一词的含义
西方学者对于“大跃进”一词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他们通常认为“大跃进”包括如下含义:第一,它代表了1958—1960年这段历史时期。第二,它表示一种独特的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战略。这一战略包括高投资、高生产和投资指标、分权化、工业帮助农业、自力更生、强调中小型企业。第三,从技术上讲,“大跃进”只是“三面红旗”之一。换句话说,就最狭义的意思而言,“大跃进”一词被用来指旨在永远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经济发展的大规模高潮。第四,它是指1958年初到1959年末的两年里,在中国实施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尝试。它为这样一种信念所推动,即通过极大的努力,每件事情都能立刻得到实现。通过在公社动员劳动力(并转变为资本)和大炼钢铁,不仅中国的经济结构能被改造,就连文化生活也能被重塑。第五,它主要指两样东西:一是指1958—1960年的历史时期和党统治的风格;二是指这样一种心态,即党所设定的乌托邦目标以及通过史无前例的群众动员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信念。适合这种心态的因素有:否定技术专家、紧张的思想气氛、通过斗争任何事都是可能的观念、自然法则不必然适合被灌输的人民的信念。[15]
(二)关于“大跃进”的起源
关于“大跃进”起源的研究是西方“大跃进”研究的一大热点,西方学者从各种视角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观点:
1.“毛挂帅” 说
美国学者晁国春等认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完全是“毛挂帅(Mao-in-command)”的结果。即“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集体领导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运用自身高度的组织技巧来动员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方案的事例。在“大跃进”运动当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是高度团结的,即使有分歧也是关于具体问题的,并不存在派系斗争。[5]
2.“两条路线斗争”说
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白瑞琪(Marc J.Blecher)、华人学者安炳炯(Byung-joon Ahn)等认为,在“大跃进”运动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围绕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存在着两条截然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强调自力更生、群众运动、思想激励、降低官僚政治和专业技术知识的作用、平均主义、政治挂帅的“正确的社会主义”的“左派”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强调依靠苏联、有序发展、物质刺激、重视官僚政治和专业技术知识、经济挂帅的“不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右派”路线。“两条路线斗争”具体表现为“毛主义者(Maoists)”对抗“刘主义者(Liuists)”[18]、“革命现代化者(revolutionary modernizers)”对抗“管理现代化者(managerial modernizers)”[19]、“党的口号者(Party′s sloganeers)”对抗“官僚机构的务实者(bureaucratic pragmatists)”[20]、毛泽东的“解放能量(unleashed energy)”对抗刘少奇的“有组织的动员(organized mobilization)”[7]、“农村社会主义模式(a rural model of socialism)”对抗“城市社会主义模式(an urban model of socialism)”[21]。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取决于这两条路线的相对的政治力量。当刘主义者占优势时,毛主义者在党的领导层的存在无足轻重。同样,当毛主义者发号施令时,刘主义者发现自己也靠边站了。“大跃进”运动就是毛主义者利用“一五”计划造成的普遍的不满情绪战胜刘主义者的结果。[22]在“大跃进”运动中,毛主义者完全发号施令,而“大跃进”运动以前的计划时期的刘主义者的每一个政策都被推翻。[23]
3.“派系”斗争说
美国学者哈罗德·欣顿(Harold C.Hinton)等认为,中国高层存在两大派系:以刘少奇为首的“国内”派和以周恩来为首的“国际”派。在国际事务上,刘少奇的“国内”派将中国的利益置于苏联的利益之上。在国内事务上,刘少奇的“国内”派强调思想动员、人力优先于技术、地方的小型工业优先于大工业。刘少奇的力量主要在党的机构中。与此相反,周恩来的“国际”派在外交事务上赞成更好地与苏联合作,在国内事务上偏爱正统的斯大林模式,强调技术、大工业和组织控制。周恩来的支持者主要是在政府部门。1957年,中共经历了国内和国际方面的重大危机,国内的“百花运动”和“整风运动”在政治上削弱了毛泽东的地位。国际上,赫鲁晓夫战胜了斯大林的继任者马林科夫“反党集团”。为了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危机,毛泽东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刘少奇的权力和威望,以便确保在合适的时间尽可能地实现权力的有序交接。因此,刘少奇必须发起一场能体现他如何应对当时危机的思想运动来巩固他的政治地位。“大跃进”的发动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国内”派战胜以周恩来为首的“国际”派的结果。“大跃进”的主要发动者是刘少奇而不是毛泽东。[24]
4.“循环”说
这一观点认为,“大跃进”运动只是当代中国历史上若干次循环当中的一次。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温克勒(Edwin A.Winckler)等人采用“循环模式(a model of cycles)”来分析“大跃进”运动,他们把1949年至1968年间的历史划分为八次“激进化(radicalization)”与“去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的循环,每一次循环又包括常态(normalcy)、动员(mobilization)、高潮(high tide)、恶化(deterioration)、紧缩(retrenchment)、解除动员(demobilization)六个阶段,“大跃进”运动就是其中的第五次循环。[12]澳大利亚学者比尔·布鲁格(Bill Brugger)则把1942至1973年的历史划分为九次 “激进(radicalism)”“加速激进(accelerated radicalism)”和“巩固(consolidation)”的循环。以庐山会议为分界线,庐山会议之前,“大跃进”运动属于第四次循环;庐山会议之后,“大跃进”运动属于第五次循环。[25]华人学者张旭成(Parris H.Chang)进一步分析了“循环”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在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选择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存在着“保守集团(conservative group)”(又叫“务实集团pragmatic group”)与“激进集团(radical group)”。这两大集团分别代表了“保守”(“务实”)与“激进”两种发展战略。当“激进集团”的观点占上风时,政治钟摆就摆荡到左,推动快速的革命变革的政策,强调群众动员和人的意志克服客观限制的能力。当“保守集团”的观点占上风时,政治钟摆就摆荡到右,倾向“巩固”(“撤退”),注重人的物质刺激和客观条件。[11]
5.“官僚政治”说
美国学者大卫·M.贝奇曼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权具有五大功能:资源征收、安全、经济发展、民族整合和社会改造。相应地,履行这些功能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就构成了当时中国官僚机构的五大系统:财富的征收和分配系统,即财经联盟(the financial coalition);经济改造系统,即计划与重工业联盟(the planning and heavy industry coalition);整合系统,即整合者(integrators);社会改造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安全系统,即军队和警察。其中以陈云、李先念、邓子恢等为代表的“财经联盟”,主张使用市场、价格刺激,更多地投资轻工业和农业,财政控制,摆脱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实现稳定的缓慢的增长。以李富春、薄一波为代表的“计划与重工业联盟”,支持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来发展重工业。“大跃进”运动就是李富春、薄一波“计划与重工业联盟”战胜陈云等领导的“财经联盟”的结果。[15]
6.“宫廷政治”说
澳大利亚学者泰维斯、华人学者孙华伦、美国学者拉尔夫·撒克斯顿(Ralph A.Thaxton)等认为,以往关于“大跃进”运动起源的研究过于重视领导层冲突和官僚模型,夸大了毛泽东受到的限制。相反,在分析“大跃进”运动的起源时,应该将 “毛挂帅”“派系”斗争、“官僚政治”等模型结合起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由此认为,在1955—195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确实存在着“支出联盟(sending ministries)”“协调联盟(coordinating bodies)”与支持“大跃进”的地方领导人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但是这三者之间的竞争实质上都是“向毛表忠心(display loyalty to mao)”,毛泽东一直处于“未受挑战的政治支配地位”。“大跃进”的发动不是所谓的“财经联盟”和“计划与重工业联盟”、“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斗争的产物,而是“宫廷政治(a court politics)”的产物。[16]“大跃进”运动是精英由于恐惧和信任而整体跟随毛泽东,“毛凌驾于他的同事之上,成为他们的上帝和总司令。中央的决策已经成为批准毛的想法、偏好和政策的一个仪式化的群体”,“‘大跃进’的政策过程的最显著特征是占优势的毛决心要运用他的权力,实现他个人的观点”。[17]因此,“大跃进”运动的根源在于毛泽东,“大跃进”是毛泽东决心通过依赖一个富有纪律性的列宁主义的党来迅速改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物。[26]而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运动是诸多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毛泽东本人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渴望;苏联发展模式的缺点日益凸显;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靠,转而开始重新依靠“群众”;合作化的成功让毛泽东确信,类似的群众动员可以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取得相对于资本主义阵营的比较优势;中国要赶上苏联的民族自豪感等。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毛泽东本人对1957年政治发展的理解。也就是说,“大跃进”运动的出现与毛泽东的态度变化有关。毛泽东对1957年的政治发展的理解包括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毛泽东把反“右”运动解释为社会主义改造在政治和思想战线的彻底胜利。此后,中国共产党需要真正把工作转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就消极方面而言,毛泽东把“百花运动”中党受到的严重政治挑战与反冒进的经济政策联系起来。这更加使毛泽东下决心要打破缓慢的经济增长局面。
(三)关于“大跃进”运动失败的原因
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是多方面因素的合力。英国学者杰克·格雷认为,“大跃进”运动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它的经济方面,而在于它的政治方面”,因为“大跃进”运动背后有如此出色的理论,有抗战时期“工合”的成功先例。严格地说,对于“大跃进”失败的部分解释归结于它早期的成功,这种成功创造了一种陶醉感,觉得任何事似乎都是可能的。这种陶醉感也造成另一方面的问题——许多激进分子相信“大跃进”不仅是经济上的跃进,也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跃进。在“大跃进”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渐进主义很快消失。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做的唯一一件他们知道如何去做的事是:采用“一五”计划创造的命令式配置资源的体制并把它推行到基层。结果是政治上无法忍受,经济上造成灾难。[27]美国学者阿什布鲁克(G.Ashbrook,Jr.)认为,“大跃进”失败是因为其背后的经济理论的两大原则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个原则是中国的巨大人口是经济财富。对于一个竭力突破现有农业的极限来获得食物的国家来说,这一观点错得不能再错了。由于土地和资本与人口之间的失调,所以巨大规模人口是不利条件。按照“边际效益递减”原则,将投入的劳动力翻番不会使土地的产量翻番,因为单个劳动力的劳动现在实际上被应用到相当于之前一半的土地上。第二个原则是中国的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没有充分就业,而“大跃进”运动能利用这些未利用的劳动力。这一观点同样站不住脚。首先,在宗族村落的框架内,中国的农村家庭代代相传地盛行着一种生活节奏——进行与农忙高峰期的间隔相吻合的辅助活动。村庄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它的成员进行诸如制衣、运输粮食、造屋、收集燃料、做小生意这样的传统的地方性活动,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很少。考虑到这种现实,政府任何动员表面上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的尝试都要冒打破既定的经济活动模式和损失相当多的地方经济生产的风险。其次,中国许多地区的食品消耗仅能糊口,任何增加大陆人口的能量消耗的尝试都将耗费额外的大量粮食。[28]
(四)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与国内学者一样,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大跃进”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分水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都造成深远的影响。
1.破坏了领导层的团结和统一,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伏笔
片冈铁哉认为,在毛强烈坚持下发动的“大跃进”是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分歧的分水岭,在领导“大跃进”的“长征”一代的领导干部中出现了永久的裂痕。在这个意义上,“大跃进”明确了对毛的领导的反对,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铺垫。[29]以色列学者埃利斯·约菲认为,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时候,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明显达成了普遍共识。然而,这一共识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的。“大跃进”对不同的领导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些旨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领导人,以及对苏联模式造成经济不平等而感到不满的领导人而言,“大跃进”战略可能是实现其目标的最可行途径。对于那些对苏联模式的社会影响担忧的领导人而言,“大跃进”不仅表明快速发展的前景,而且许诺给中国革命注入新的生机。为了维持领导层的共识,“大跃进”不得不实现领导人的各种各样的期望。因此,“大跃进”失败必然导致领导层共识的破裂。随后引发的一系列党内争论把“大跃进”的失败与“文化大革命”连在一起。[30]华人学者安炳炯认为,从“大跃进”及其后果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趋势使“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成为必然。当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时,党的其他领导人采取观望态度与毛暂时保持一致。因此,当时党的团结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大跃进”的实际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跃进”本身包含着无法弥合的党内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它失败的话,将进一步破坏1949年后的政策共识和领导层联盟。1958年至1959年的“大跃进”代表了毛主义的革命与发展的原型,而1959年至1962年的调整和巩固政策极大地偏离了毛主义原型,是对“大跃进”的基本构想的挑战。1962年至1966年,毛泽东坚持他珍爱的政策的努力与他的同事限制这些政策的愿望之间的不断加剧的冲突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21]美国学者理查德·桑顿(Richard C.Thornton)认为,在“大跃进”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没有两个“派系”之间斗争的特点,各个集团相互竞争。通过分而治之,毛泽东设法保持住唯一的最强大的集团的领导人和全面控制的地位。“大跃进”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高层政治的性质的根本变化,国家、军队、党以及其他的专门领导人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不断升级,最终走向两极分化。这个两极分化的过程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开始变得日益明显,最终走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31]
2.既奠定了农村改革的制度基础,又深刻影响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民抗议运动
华人学者杨大利(Dali L.Yang)认为,要理解中国改革的兴起就必须提到“大跃进”的失败。“大跃进”运动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关键节点,它的失败造成大众观念的重大变化,提供了制度革新的动力,产生了农村制度变革(例如去集体化)的要求。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个省的改革热情与它在“大跃进”饥荒期间经受的痛苦成正比。越是遭受“大跃进”饥荒严重的地区,那里的农民与干部就越是可能采取诸如以家庭为基础的耕作这样的自由化实践。从根本上说,“大跃进”饥荒是政治性的,一开始就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纠缠在一起,一旦出现大规模的饥荒,人民公社就不再具有合法性。因此,“大跃进”的长期影响正好与毛的意图相反。如果没有“大跃进”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话,中国实行集体农业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大跃进”引起的灾难深刻动摇了旧的经济发展范式——强调经济控制、计划和动员——的基础,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大跃进”饥荒敲响了埋葬集体化范式的丧钟,为新的改革范式的开启埋下了伏笔。[32]
美国学者麦宜生(Ethan Michelson)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民对农民负担的不满与抵制的根源追溯到“大跃进”时期。他认为,“大跃进”的教训使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恐惧过多的农业税。“大跃进”造成的农民对地方政权的不信任导致农民抗税“竞争的倾向(propensity for contention)”和“对抗的倾向(propensity for resistance)”的产生。在20世纪90年代,农民激烈地反对增加税收负担,他们有意无意地将其与“大跃进”的粮食征购联系起来。从农民的角度来说,后毛改革时代的税收可能类似于毛时代的“大跃进”的浮夸模式。那些受“大跃进”影响较深地区的农民似乎已经从“大跃进”中“吸取教训”,仍然害怕和不信任地方干部。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征税行为可能已经触发农民有关大饥荒的记忆。而那些受“大跃进”影响较轻的地区,这种联系则要小得多,因而农民反对税收的对抗性也较小。[33]美国学者拉尔夫·撒克斯顿指出,“大跃进”期间,毛主义者制度化、结构性的强制和腐败给农民以毁灭性打击,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以及潜在抵制的武器库。在改革时期,对地方政府行为不端的集体抵制和抗议事件的增多与这个更大范围和长期的政治遗产密不可分。[26]
3.中国共产党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巨大挫折,面临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以色列学者埃利斯·约菲指出,“大跃进”带来的灾难造成人民对政权的信心危机。在“大跃进”以前,由于头十年“统治”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政权已经积累了一大笔信心财富,当它号召人民奋斗和牺牲时,它就提取这笔财富。正如“大跃进”令人信服地表明的,人民通常愿意响应,准备竭尽全力来实现政权设定的目标。但是,“大跃进”使中国人民痛苦地发现,他们的领导人并不是绝对正确的,也会犯巨大的、代价惨重的错误。“大跃进”的失败摧毁了人民对领导层的信心。人民普遍的士气低落和不信任的心态导致了纪律的崩溃,在玩世不恭和失去信心的气氛中,个人开始为生存而奋斗,自从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以来,这种情况还不曾有过。[30]美国学者拉尔夫·撒克斯顿认为,“大跃进”期间及其后的饥荒所造成的毁灭的持续的记忆构成了这样一种方式,即村民接受寻求治理和操纵后饥荒的混乱和后毛时代的改革秩序的当权者并与之发生关系,这是饥荒后社会主义政权在短期内重建合法性面临重重困难的根源所在。[26]
4.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 “组织内卷化”过程,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消极影响,成为干部腐败问题的根源
华人学者石知余(Chih-Yu Shih)分析了“大跃进”运动对中国政治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他指出,正是“大跃进”运动把中国的道德政权(moral regime)推向极端。英明的、道德的领袖试图利用道德权威来实现现代化,通过“大跃进”运动动员所有人用他们的经济资源来支持政权的道德主张。因此,“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就使道德秩序失去了合法性,破坏了中国政治的道德共识,揭示了政权虚假的道德优越感,动摇了最高领导人的神话的根基,打破了传统上认为理所当然的中央的一致,造成了道德政权的永久性衰落,孕育了大众的道德异化感,导致干部公开的腐败。[34]华人学者吕晓波认为,“大跃进”期间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组织机构的“去规则化(deregulation)”和“去常规化(deregularization)”等革命手段来减少和补救官僚主义问题、适应经济发展。这些“革命的”方法导致“非专业化(non-professionalism)”,造成干部们普遍的政治胆怯、缺乏效率和能力,以及高度政治化。中共领导人有意的反官僚化的行动实际上导致另一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干部行动拖沓、从模棱两可的政策中揣测上级的意图、避免承担责任。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组织内卷化”过程的开始。执政党的“组织内卷化”对干部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大跃进”运动期间及其以后几十年的干部腐败问题的根源。[35]
(五)关于“大跃进”运动的评价问题
1.“大跃进”运动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美国学者沃尔特·盖伦森(Walter Galenson)、席兰(Peter Schran)等认为,“大跃进”运动是“非理性的”。沃尔特·盖伦森认为,以后院炼钢、深耕、密植以及农村公社这些不切实际方案为基础的“大跃进”运动是不负责任(irresponsibility)的行为。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会相信工农业产值能在几年之内成倍增加。一些人也许会用判断的错误、奉行意识形态或者植根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神秘的必然性的逻辑来解释经济的不断的管理不善……我们发现用一个词——非理性(irrationality)——来概括这段历史更加令人信服。[36]席兰认为,就通过本国的方法能产生奇迹般进步的效果的坚定信仰的前提而言,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农村政策能被称为“理性的”。然而这种信仰是错误的,形成这种信仰的方式看来是高度非理性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不良后果迅速显露出来。[37]
英国学者杰克·格雷、华人学者曹康等认为,“大跃进”运动是“理性的”。杰克·格雷指出,就经济方面而言,“大跃进”不是非理性的。它以中国的形式代表了当代对计划原则的普遍反应,计划原则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已经遍及全世界,在1958年,这种对计划的反应成为全世界的发展专家的常规的智慧。“大跃进”政策中的另一种在当时为世界所熟悉的想法是:有意的不平衡发展的观念。[27]曹康认为,“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本地的、小型的工厂只要更少的资本、更短的建设周期,这些工厂能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由于苏联终止贷款所导致的对进口现代设备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的限制使这些理由更加有说服力。理论上,“大跃进”方案设想的技术双重主义不是不合理的。在一个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假定在资本总额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能够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只有在这种战略实施得太过头、执行得太混乱时,才会出现资源的配置不当。[38]
2.“大跃进”运动及其造成的经济危机是否使中国“失去”了七至十年的经济发展的时间
华人学者刘大中(Ta-Chung Liu)、艾尔弗雷德·陈等认为,在1958—1968年这十年间,经济方面是“零增长”,“大跃进”运动及其造成的经济危机使中国“失去”了七至十年的经济发展的时间。刘大中指出,在1958年至1965年的七年时间里,当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和发展时,共产党中国1965年的经济停留在1958年的水平,“失去”七年时间,没有增长。[39]艾尔弗雷德·陈认为,就经济增长而言,整整八年被浪费,失去的机会的代价是巨大的。农业生产在1958年后直线下落。极力强调钢铁生产导致产量短期上升,但随后就是整个十年的下降。[17]在1949至1957年间,共产党中国的经济经历了迅速的恢复,取得巨大增长。然而,这一发展过程被1959—1962年巨大的经济危机打断。这一危机可能使这个政权付出了十年的经济增长的代价,因为1965年国民生产总值似乎没有超过1958年的水平。[40]
美国学者李皮特(Victor D.Lippit)、塞尔登等认为,所谓的“大跃进”运动使中国失去七到十年的经济增长的论断是一个“神话”。因为所谓的“大跃进”耗费了中国十年增长的论断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中国放弃“大跃进”的话,增长将自然会发生。当时存在两个选择来作为“大跃进”的替代战略。第一个选择是继续“大跃进”运动之前的政策。然而,由于这一政策使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农业部门的增长速度,这种工农业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在一定时期内能够维持,但是最终必定削弱农业支持工业的能力,农业的缓慢进步将成为制约经济全面发展的瓶颈。在1958年,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由工农业部门的不平衡增长产生的决定性的时刻,农业不能满足工业迅速增长的需要。因此,“大跃进”之前的政策尽管在“一五”计划期间使快速增长成为可能,但是不能再继续实施。这就排除了继续推行“大跃进”之前的政策的可能。第二个选择是集中资源于农业部门。因为提高农业生产率有两种主要的方式:“大跃进”的途径和通过工业部门来大量增加投资给农业部门。第一种选择寻求通过把制度重组与大力增加传统投入(尤其是劳动力投入)这二者结合起来,从而增加产出,而第二种选择意味着通过来自工业部门的现代化投入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因此,第二种方式是唯一可以替代“大跃进”运动的选择。然而,这种方式存在较大局限。首先,它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缺乏历史先例。没有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把现代化的基础建立在对农业的大规模政府投资上。其次,它未考虑到中国的工业部门为农业部门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有限的投资能力。农业现代化要求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如果没有先为经济建立一个工业基础的话,这些东西都无法提供。在缺乏这样的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将把经济增长率降到非常低的水平。因此,将投资主要用于农业现代化的第二种方案的确存在实施的可行性,但是,代价是牺牲快速的工业增长,而且随着工业部门提供必要的投资商品的能力的延缓,农业部门的长期发展将减慢,所谓的农业增长很可能只是轻微的增长。因此,“大跃进”政策没有使中国失去十年的增长,因为其他可供选择的政策也将牺牲快速增长,只有“大跃进”提供了迅速增长的希望。如果中国没有尝试“大跃进”的话,将没有尝试就已经放弃了快速增长的机会。即使“大跃进”最终没能实现它的产量目标,也仅仅只是让中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稍微落后于采用替代的政策可能已经达到的水平。因此,“大跃进”代表了一种理性的人可能选择的发展战略。“大跃进”不应该被视为牺牲了十年发展的代表,相反,应该被视为中国从能挑选的政策中选择的一次能实现十年增长的机会。[41]
三、西方学界关于“大跃进”运动的主要研究方法
(一)克里姆林宫学
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又称宣传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国家研究苏联和法西斯德国所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假定所得的资料是大量掺了水的、虚假的和空谈的。因此,学者们总是希望找到更多的材料去加以验证。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为了突破重要档案材料基本没有公开的局限,便将克里姆林宫学运用到中国问题研究当中,试图从官方公开发表的材料中找出隐含的信息。因为公开发表的材料,像讲话、社论、报纸上的文章等,都反映出中国人当时对事件的看法。尽管这些材料仅从表面上就提供了许多情况,但只要对中国领导人传递信息的手法有所了解,就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内情。中国领导人正是通过这种手法把更多的信息传递给更为老于世故的官僚机构成员的。这些方法通常被为“奥秘传播”或“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它包括:字或词按某种特殊顺序排列,强调一项政策的某个方面而略去另一方面,援引历史上的事件来指当前的某一政治准则,发表精心选择的照片以显示政治上的位置,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许多手法。[7]近年来,克里姆林宫学受到了西方学者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英国学者亚胡达(Michael Yahuda)指出,尽管克里姆林宫学所倡导的仔细的文本分析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一方法的糟糕之处在于:它没有广阔的历史的或者社会科学的框架做基础;它没有将分析置于生动的历史背景之中;它没能反映出动态的变化的环境中的决策的复杂性;它所使用的文本分析模式为了寻找隐晦的“机密通信”往往忽略文本的中心和主旨。这导致分析者脱离上下文背景而摘录出个别的词句来支撑自己的论证。这样做以后,这些词句事实上就背离了原文的中心、语气和观点,而这将严重地误导分析者。[42]
(二)新制度主义
西方的政治学自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行为主义,使传统的制度主义几乎被学者们抛弃。但是行为系统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学者们又回头来看看制度主义的分析功能,认为制度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制约人类的行为,从而可以预测其行为的结果。因此,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学者开始重新再组织再安排制度的结构,尝试探讨政府运作更新的理论,这就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新制度主义混合了传统的制度结构分析及当代的个体行为研究,将政策界定于某一制度场所内作深入的探讨,政府运作过程的重点,集中于制度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个体行为的规范在于制度之下,能充分了解政策的制度场所,我们便预知个体的运作结果。新制度主义集合了静态的制度研究与动态的个体行为分析,导致政策类型研究的兴起,有助于对政府运作过程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近年来,新制度主义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新制度主义的影响仍然不大。以中国期刊网为例,以“新制度主义”作为关键词,共检索到191篇文献。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政治学理论、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探讨新制度主义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的仅1篇。[43]因此,新制度主义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仍有提倡的必要。
(三)模型研究法
简单地说,模型就是对真实世界的某些方面的某种简化和摹画。[44]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模型是指一种关于对象结构、过程或行为的模拟结果,是人们基于想象和抽象而对某种现实的客体系统的一种简化了的映像。[45]模型建构着、聚合着而且展示着有关事物的各种关系,以简化的、抽象的、凸显的方式体现着真实的客观事实。
在西方学者“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中,体现研究模型的成果是相当多的。以“大跃进”的起源为例,西方学者提出的十余种解释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模型:“精英模型(elite model)”和“理性模型(rationality model)”。“精英模型”把“大跃进”运动的动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间权力、政策偏好、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利益等不断博弈的结果。体现“精英模型”的观点主要有“毛挂帅”说、“两条路线”斗争说、“派系”斗争说、“循环”说、“官僚政治”说、“宫廷政治”说等。而“理性模型”强调“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环境的产物。体现“理性模型”的观点主要有“一五”计划后果说、打破农业瓶颈说、独立自主发展说、解决就业说、应对危机说、第三条道路说、革命遗产说、“不断革命”说、两种发展战略说、历史传统说、综合原因说等。研究模型的重要作用在于它所具有的学理功能,即检测功能和发现功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研究模型,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科学解释系统,是对已知事实或客观原型的摹画和简化。它对已知事实或客观原型进行解释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建构某种关于事物内在的深层的结构或机制的理论论证,并将这些事实作为其必然的逻辑结论从中演绎出来。如果这一逻辑结论是已知的,则整个推演过程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就使得我们认定这一结论是一种“科学解释”;如果这一逻辑结论是过去所未知的,那么我们就认定这一结论是一种“科学预测”。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模型研究法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模型是一个静态的(static)概念,模型在适应变化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没有一个模型能够完全展现全部的历史真实。依靠模型方法绝不可能穷尽对客体的认识,因为再完美的研究模型都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认识成果。其次,模型的采用会导致过于简化的危险,“为了使它在概念上可以控制,把现实简化成了概念骨架……现象愈多样化与复杂,过分简化的危险愈大”[46]。近年来,国内学界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大力倡导建立研究模型,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国内学界在“大跃进”运动研究以至整个中共历史学的研究中,采用研究模型的著作还是不多的。鉴于中共历史学本身特有的复杂性,引入模型研究法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定量分析法
定量分析法是指依据所调查的现实资料数据,运用科学的数学推导、演算等方法,对事物之间或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数量研究的思维方法。定量分析法相对应的是定性分析法。定性分析法是为了确定认识对象的性质和类型而进行的分析,主要解决“是什么”“是不是”等问题。定量分析是为了确定认识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方面关系而进行的分析,主要解决“是多大”“有多少”等问题。认识事物,首要的是认识事物的质,亦即要进行定性分析。但是,只有把握事物的量,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事物的质。
具有强大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传统的西方学者在“大跃进”运动研究中往往更倾向于采用定量研究,运用现代数学方法来揭示有关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篇幅所限,这里试举一例。在有关“大跃进”时期粮食大幅减产的原因当中,“天灾”与“人祸”各自占多大比重?这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大热点。一些西方学者运用一整套复杂的数学公式计算了各项变量在粮食产量下降中所占的百分比,其中,从农业转移的资源所占比重为33.0%,过多的征购所占比重为28.3%,自然灾害所占比重仅为12.9%。因此,把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以及过多的征购政策是造成1958—1961年粮食产量下降最主要的原因。[47]
(五)社会史研究法
所谓社会史就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而“中国社会史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在全部历史上侧重于社会下层的社会生活部分及一些基础制度部分”。[48]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条件所限,从事“大跃进”运动研究的西方学者无法到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因此,“文化大革命”以前,西方的“大跃进”运动研究更多的是关于国家和省一级层面的决策过程以及政策执行,无法深入基层来探讨“大跃进”运动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影响。而改革开放对此的解禁令西方学者有了身临其境的机会。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秉承了欧美社会史学传统的西方学者开始把“大跃进”运动研究的重点转向对基层社会的个案研究,以“民族志”的方式叙述一个又一个乡村或者小人物的故事,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诸如“大跃进”中的新民歌、乡村的妇女解放、关于“大跃进饥荒”的回忆如何进入公共空间的讨论等“小问题”上。至于这个“故事”有没有典型意义、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大跃进”运动的全貌与真实已经不是他们所追求的。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志趣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张静如等学界前辈多年以前就提出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 但是习惯于“宏大叙事”的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往往是自上而下地审视、研讨“大跃进”运动的开展,热衷于追述和分析中共中央对“大跃进”的每一个决策的前因后果,以为中央的决策会在各地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会理所当然地决定“大跃进”的所有方面。国内的研究往往忽视了中央的文本规定在遇到地方性的抵制时会严重地变形或者妥协,过多地强调了“大跃进”运动各个方面的一致性,而忽视了“大跃进”运动所存在的多样性特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与路径各有千秋。一方面,西方的社会史研究法难以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而中共历史学中传统的“宏大叙事”又难以展现“大跃进”的历史全貌。因此,将这两种研究路径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也许不失为一种办法。
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对历史事件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差异,以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西方学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难以赞成和接受的。但是,学术上的分歧并不可怕,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分歧也就没有进步。由争论到进步的前提条件,当然是开展学术对话和交流。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之一。由于学术传统的不同,西方学者在“大跃进”研究中运用了多种比较新颖的研究方法,视野比较开阔,其分析不乏独到之处,颇值得国内学者借鉴。希望本文作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和评析西方的“大跃进”研究成果的论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笔者才疏学浅,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多的学者作更深入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1]梁怡,李向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2]HARDING H.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ntemporary China[C]//DAVID S.American S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Armonk,N.Y.: M.E.Sharpe,1993:18-34.
[3]NINA P H.Studies of Chinese pitics[C]// DAVID S.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Armonk,N.Y.: M.E.Sharpe,1993:36-125.
[4]KALLGREN J K.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irty years:An overview[M].Berkeley,Calif.: Univ.of Calif.,1979:36-38.
[5]CHAO K-C.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J].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59(321):12.
[6]SCHWARTZ B.Totalitarian consolidation and the Chinese model[J].The China Quarterly,1960(1):18-21.
[7]MACFARQUHAR 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56-522.
[8]NATHAN A.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J].China Quarterly,1973(53): 34-66.
[9]DOMENACH J-L.Aux origines du grand bond en avant[M].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1995.
[10]SCHURMANN F.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55-56.
[11]CHANG P.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M].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33.
[12]SKINNER G W,WINCKLER E A.Compliance succession in rural communist China: a cyclical theory[C]// AMITAI E.A Sociological Reader on Complex Organizations.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80:401-423.
[13]GOLDSTEIN A.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1949—1978[M].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4.
[14]LIEBERTHAL K.,OKSENBERG M.Policy making in China:Leaders,structures,and processes[M].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11.
[15]BACHMAN D.Bureaucracy,economy,and leadership in China: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2-3.
[16]TEIWES F C.,SUN W.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central politicians,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1955—1959[M].Armonk,N.Y.:M.E.Sharpe,1999:112.
[17]Chan A L.Mao′s crusade:Politic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68.
[18]BLECHER M.J.China against the tides:Restructuring through revolution,radicalism,and reform[M].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3:202.
[19]KAUTSKY J H K.Revolutionary and managerial elites in modernizing regimes[J].Comparative Politics,1969(1):22.
[20]PRYBYLA J 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t China[M].Scranton,Pa.: International Textbook Co.,1970:23.
[21]AHN B J.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Dynamics of policy processes[M].Seattle : Univ.of Washington Pr.,1976:4-31.
[22]GABRIEL S J.The structure of a post-revolutionar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The Chinese economy from the 1949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EB/OL].[2014-10-25].https://www.mtholyoke.edu/courses/sgabriel/economics/china-essays/3.html.
[23]KHOT N.Maoism in extremis,liuism in command:Economic modernization as strategy in class struggle in China[J].China Report,1979(15):12.
[24]HINTON H.C.Intra-party politics and economic policy in communist China[J].World Politics,1960 (4):5.
[25]BRUGGER B.China,lib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1942—1962[M].Totowa,N.J:Rowman & Littlefield,1981:266.
[26]THAXTON R.A.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325-327.
[27]GRAY J.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China from the 1800s to the 1980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310-314.
[28]ASHBROOK G J.Main lines of Chinese communist economic policy[C]//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U.S.Congress.An Economic Profile of Mainland China.New York: Praeger,1968:27-29.
[29]TETSUYA K.Political theor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J].Social Research,1969 (1):21.
[30]JOFFE E.Between two plenums: China′s intraleadership conflict,1959—1962[M].Ann Arbor,Mich: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5:7-24.
[31]THORNTON R C.China:The struggle for power,1917—1972[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Pr.,1973:251.
[32]YANG D L.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State,rural society,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M].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4-242.
[33]MICHELSON E.Deprivation,discontent,and disobedience in rural China:Collective learning in southeast Henan[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6.
[34]SHIH C-Y.The decline of a moral regime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in retrospect[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94 (2):12.
[35]Lu X B.Cadres and corruption:The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M].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112.
[36]GALENSON W,TAN C.Letter[N].New York Times,1969-06-17(02).
[37]SCHRAN P.Rural income policy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J].Asian Survey,1964 (7):15.
[38]CHAO K-C.Economic aftermath of the great leap in communist China[J].Asian Survey, 1964 (4):11.
[39]LIU T-C.Quantitative trends in the economy[C]//ECKSTEIN A W,GALENSON,LIU T-C.Economic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Chicago: Aldine,1968:163-167.
[40]LIU T-C.The tempo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ainland,1949—1965[C]// ECKSTEIN A W,GALENSON,LIU T-C.Economic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Chicago: Aldine,1968:6.
[41]LIPPIT V D.The greap leap forward reconsidered[J].Modern China,1975 (1):11.
[42]YAHUDA M.Kremlinology and the Chinese strategic debate,1965—1966[J].The China Quarterly,1972 (49):22.
[43]周宝龙.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与中共党史研究[J].党的建设,2009(1):74-76.
[44]KING G,KEOHANE R O,VERBA S.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49.
[45]陈波.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52.
[46]〔奥〕贝塔兰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M].秋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168.
[47]LI W,YANG D T.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5(4):22.
[48]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2-12.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318(2015)01-0025-11
作者简介:李春来(1982-),男,重庆人,中共温州市委党校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收稿日期:2014-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