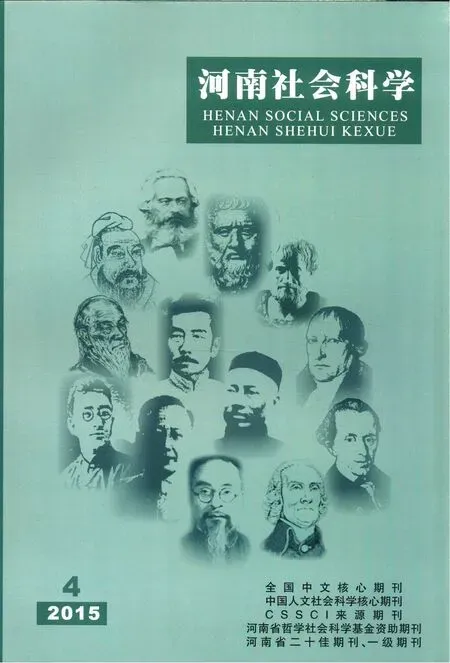埃·斯托尔的历史主义莎评探析
2015-03-27辛雅敏
辛雅敏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文所,北京 100732)
埃尔默·爱德加·斯托尔(Elmer Edgar Stoll,1874—1959),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是20世纪历史主义莎评中的一位先驱和重要代表人物。斯托尔终其一生都在为历史主义方法摇旗呐喊,观点却始终如一,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的莎评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从斯托尔等人在20世纪初开始向以布拉德雷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莎评发出诘难之后,历史主义莎评便成为莎评领域的执牛耳者,这种情况一直到意象批评乃至新批评的兴起才逐渐得到改观。
历史主义莎评来自历史学术研究对文学批评的介入。在斯托尔这样的历史主义莎评家看来,当时的莎评最大的问题在于“批评忘记了莎士比亚是在16世纪写作”[1]。于是,斯托尔主张将莎士比亚放入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与戏剧背景中去考察莎翁戏剧的创作原则,借此来阐明作者的意图,进而获得关于莎剧的真理。正如一位莎评史家所指出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莎士比亚的舞台习俗、传统、观众及剧院。假如我们是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普通观众,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2]
早在1910年左右,斯托尔就开始提出历史主义的观点,然后又分别出版了分析《奥赛罗》和《哈姆雷特》的两部小册子,但其代表作是1933年出版的《莎士比亚的艺术和技巧》(Art and Artifice in Shakespeare)一书。斯托尔在此书中阐明了他对莎剧的基本看法,然后又逐一分析了四大悲剧,尤其是《奥赛罗》和《哈姆雷特》。斯托尔的莎评覆盖范围很广,他对夏洛克和福斯塔夫这两个人物也做过比较精彩的评论,这些评论被收录在1927年出版的《莎士比亚研究:历史与比较方法》(Shakespeare Studies: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 method)一书中。我们要了解斯托尔的莎评,不妨先对他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的梳理。
一
在斯托尔看来,莎评中的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作者的意图。要理解作者意图,就要回到作者的时代;如果不把莎士比亚放回他自己的时代,莎士比亚就会变成斯温伯恩,变成布拉德雷,而不是莎士比亚自己。“批评的功能不是将诗人变为读者的同时代人,而是要将当代读者变为诗人的同时代人。批评不仅仅是像印象主义批评家那样表达自己的印象,而是要探知作者的意图,要考量作者时代的各种力量和形势。要做到这点,就必需了解作者,了解他的时代。”[1]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斯托尔所谓“了解作者的时代”,并不是后来的历史主义莎评家们所热衷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各种思想背景,而主要指的是莎士比亚所继承的文学传统和戏剧传统。斯托尔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莎士比亚关心的是艺术技巧,是故事,而不是思想,而且他认为伊朝戏剧是不受当时的思想所影响的。因此,要想真正理解莎士比亚,就要回到伊朝的戏剧舞台,去探求莎翁是如何在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创作其作品的。
在《莎士比亚的艺术和技巧》中,斯托尔开宗明义地指出,“悲剧(在这一点上包括喜剧)的核心不是人物(character),而是情境(situation);所谓的情境就是一个人物与其他人物,或者与环境的对比或冲突”[3]。情境对于生活来说是不可能的,不能用生活逻辑和心理分析去理解,其特点就是剧烈的对比和冲突。但正是这种不可能性产生了巨大的戏剧效果,才使得观众能被戏剧所吸引。“冲突越激烈,被激起的情感也越热烈;对比越强烈,效果就越大。对于天才来说,这种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挑战而已。”[3]
斯托尔认为,为了获得这样的对比和冲突,就要诉诸艺术技巧。于是,就有了伪装、误认、冒名顶替、暴政与诡计、欺骗与诽谤、偷听以及决定命运的发现(戒指、书信、手帕等等)、装死与复活、带谜的遗嘱、神谕、誓言、突然的由爱转恨、命运或超自然力、魔法、爱与复仇、大团圆等情节。所有这些情节以今天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来看,都完全不可信,但对理解莎士比亚来说,却至关重要。
对于斯托尔来说,《奥赛罗》就是这样一部“充满对比而又不可信”的悲剧,它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奥赛罗的前后变化,即一开始并不轻信他人的奥赛罗为什么会相信伊阿古?前面高贵而坚定的奥赛罗为什么后来变得如此嫉妒与狂怒?有的批评家认为是因为伊阿古的骗术很高明,而奥赛罗的天真使他成了狡猾的伊阿古的受害者,他天性中嫉妒的种子则激起了那暴风雨般的愤怒。斯托尔认为,这些说法都是从心理角度出发去解释的,但这种解释必然是说不通的。因为对于奥赛罗来说,相对于自己深爱的妻子,伊阿古毕竟要陌生得多,他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不熟悉的人而不相信自己的爱人。
在斯托尔看来,奥赛罗的这种变化是一个从文学传统和戏剧传统中继承而来的塑造人物的技巧。和其他虚构的欺骗一样,这种变化的本质是许多戏剧以及神话传说中都会出现的“关键时刻相信精心编制的恶意骗局”。这一技巧莎士比亚也使用了不止一次,比如《李尔王》中葛罗斯特相信爱德伽的骗局,《无事生非》中克劳狄奥相信唐·约翰,《辛白林》中波塞摩斯相信阿埃基摩等,都是类似技巧的重复。
同样,奥赛罗从不信到信的变化也不是现实生活中可解释的心理变化,而是由于戏剧效果的需要。什么样的戏剧效果?就是上面提到的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不是奥赛罗的高贵与伊阿古的狡猾之间的对比,而是奥赛罗自身的爱和他的恨(突如其来的恨)的对比。”[3]是奥赛罗宽宏大量的性格和他产生于嫉妒的狂怒之间的对比,而且这种对比是经过剧作家积累、压缩、简化、集中之后而形成的,所以特别能打动观众。正因为如此,斯托尔不禁问道:“如果奥赛罗的嫉妒是那么‘自然’地发生,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如此悲剧的、如此动人的效果?”[3]由此可见,莎士比亚关心的,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为了创造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的结果“是生活图景所不能给予的情感效果”[3]。
关于《奥赛罗》中的人物塑造技巧,斯托尔还有更进一步的发现。他指出,从人物的发展角度看,奥赛罗的性格变化有一种节奏,从高贵平静到嫉妒发疯,最后又归于高贵和平静。这种节奏是一种音乐的技巧,这种音乐技巧增强了幻觉的效果。而从人物关系角度看,则有一种绘画中明暗对照的技巧,正如聚光灯打在主人公身上,同样也使人物服务于戏剧幻觉。
一言以蔽之,莎士比亚戏剧作为一个整体,追求的不是现实,而是一种更高的现实,它要使观众兴奋、出神乃至不能自已。现代人要体验到这一点很难,但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感受到的则要强烈得多。
二
对于另一部重要悲剧《哈姆雷特》,斯托尔也下了一番功夫,对其做了详细的考察。他认为莎士比亚继承的是一个复仇剧传统,为了获得观众的支持,莎翁必然会屈从于当时流行的故事情节,不会有太大的创作自由。“剧作家即便倾向于做彻底的改动,也没有这个自由。……虽然可以讲得更好些,但故事一定要大体上一样,不然戏剧公司和观众都会失望;对改进的预期无疑是在风格和韵律上。”[3]虽然已经失传,但因为有基德的老剧《哈姆雷特》,所以莎士比亚接手的是一个开头和结尾都已经固定的故事,故事的开头便是鬼魂嘱咐哈姆雷特要复仇,结尾则是复仇的完成,这是不能被改变的。所以,剧作家必须要拖延戏剧的节奏才能把故事讲得够长。
从这种历史主义理解出发,斯托尔指出被浪漫主义莎评家们视为哈姆雷特性格重要证据的自我谴责其实也是一种拖延戏剧节奏的技巧。因此哈姆雷特并不是浪漫派眼中的那个病态的忧郁症患者,而是一个高贵的英雄。因为当时的观众绝不会接受一个意志薄弱、耽于思索的拖延者作为悲剧的主人公。相反,在文艺复兴复仇剧中,复仇者四处游荡而又常常自我谴责已经是一种传统,不会给人物带来负面影响,观众也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病态。
斯托尔比较了《哈姆雷特》、基德的复仇剧《西班牙悲剧》和古罗马塞内加的复仇剧,得出的结论是:“自责的功能是提供一种借口,而不是要揭露人物的缺点。”[4]也就是说,自我谴责是为叙事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性格刻画。哈姆雷特谴责自己复仇的延宕在剧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出现在第二幕结束时,另一次出现在第四幕第四场,两次自责都出现了痛下决心之类的话,这不仅是一种自我满足,更是为了使观众满足,可以进一步拖延故事情节。而从这以后之所以没有了自我谴责,也是因为国王已经采取行动,情节上不再需要由自责来拖延了。
因此,自我谴责赋予延宕以动机,它们不仅解释了延宕,也拖延了剧情,起到了暂时过渡的作用。“它们提醒观众,主要任务并没有丢,虽然延迟了,但并没有抛弃;它们展示给观众,即便在延迟,主人公也是有意识和有责任,并且始终如一的。”[4]所以哈姆雷特口中的所谓“遗忘”“怠惰”等借口都是拖延戏剧节奏的技巧;他的自我谩骂和自我抨击也都是情节和戏剧效果的要求,而不能视为对主人公的贬抑,更不能把这些作为证据,像浪漫主义莎评家那样去进行人物性格分析。
不仅如此,从这一角度解读《哈姆雷特》,也能更好地解释哈姆雷特的装疯。斯托尔认为哈姆雷特的疯言疯语的确是佯装的,不能从心理学角度过度解读。因为正如《奥赛罗》中形成的高贵的平静与嫉妒的狂怒之间的对比,哈姆雷特的装疯也在戏剧功能上形成了一种对比,即“一个高尚的王子在疯狂面具背后随意说着他想说的话,却不会被认为流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3]。这更像是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伪装技巧。因此,哈姆雷特是一个戏剧人物,是一个高贵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心理学分析的对象,也没有病态的忧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托尔断言:“心理学的、病态的、现实主义的哈姆雷特,这么说吧,完全是浪漫主义时代的发现或发明。”[4]
总之,在莎士比亚笔下,人物塑造是来自于传统并为戏剧效果服务的。莎士比亚追随的是古代戏剧家们的足迹,因而常常追求一种夸张的对比效果。他的目的是要激起观众强烈的情感,而不是去摹仿现实。莎士比亚人物的现实是戏剧内部的现实,在一个荒诞的前提下符合逻辑的发展。
三
斯托尔的莎评往往有明显的针对性,其目标是统治莎评一百余年的浪漫主义莎评。以历史主义的还原性解读为出发点,斯托尔在《莎士比亚研究:历史与比较方法》中用大量篇幅分析了夏洛克与福斯塔夫这两个人物。通过这些分析,斯托尔试图向以往的浪漫派莎评家们证明,喜剧人物不应被寄予情感,更不应该被同情。于是,夏洛克不再是浪漫派眼中值得同情的主人公,而是一个典型的喜剧反派。斯托尔认为莎士比亚至少运用了三种方式来确保观众所理解的夏洛克是一个反派角色。
首先是剧中其他人物对夏洛克的评价。斯托尔指出,除了夏洛克的好友杜伯尔之外,其他所有人对夏洛克都没有什么好的评价,这其中甚至包括夏洛克自己的仆人和女儿。相反,所有人对夏洛克的敌人巴萨尼奥和安东尼奥则都是充满赞美和褒奖之词。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剧中人物的褒奖或责难常常会“在紧要关头指导观众的判断”[5]。
其次,莎士比亚安排剧中场景顺序的方法也不利于夏洛克。斯托尔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第二幕,夏洛克的仆人朗斯洛特和女儿杰西卡被安排在夏洛克回家之前出场,并对夏洛克的吝啬进行了谴责。于是,当夏洛克在这一幕的第五场回家后抱怨朗斯洛特食量大、做事懒惰的时候,由于观众已经通过仆人和女儿的描述对夏洛特有了吝啬的基本认识,所以夏洛克对朗斯洛特的指责便显得十分可笑。这也是在当时的戏剧中非常流行、莎士比亚本人也多次使用的“第一印象”原则。
再次,从夏洛克本人的旁白和其他台词中也可以找到他是反派角色的证据。旁白往往出现在作为正面人物的主人公在场的时候。比如夏洛克这句旁白:“我恨他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可是尤其因为他是个傻子,借钱给人不取利钱,把咱们在威尼斯城里干放债这一行的利息都压低了。”(第一幕第一场)斯托尔认为在当时的舞台环境中,这样的旁白能够清楚地表明夏洛克的坏人身份。
不仅如此,斯托尔还指出,从当时的戏剧传统角度去考察,夏洛克是守财奴、高利贷者、犹太人这三种喜剧反派角色的合体,又怎么可能是一个正面人物呢?而从当时的社会思想角度去考察,犹太人面临各种歧视和迫害,在喜剧中也必然是被嘲笑的对象。
斯托尔进而试图证明,在《威尼斯商人》中,按照莎士比亚的原意,对夏洛克的同情是不应该存在的。在论证这个问题时,斯托尔提出了四个喜剧原则。首先,对戏剧乃至对所有文学作品的解读说到底是对“强调重点”(emphasis)的解读;其次,喜剧之所以区别于悲剧也正是由于这种“强调重点”或传统的“隔离状态”(isolation);再次,喜剧遵从当时的风俗和偏见;最后,夏洛克戏中有大量的外部喜剧技巧保证他不可能同时被视为既“可笑”又“可怜”[5]。这也就是说,喜剧中的反派人物是被用来嘲笑的,是绝不能被杂糅进同情的元素的。简单地讲,喜剧要确保不能激起观众的同情。
在这些原则的约束下,福斯塔夫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回归到了莫根(Morgan)对其进行感伤化解读之前的那个文艺复兴舞台上的胆小鬼。斯托尔认为,自从莫根宣称福斯塔夫不是一个懦夫,这个人物就被抽离出了具体的历史戏剧语境,成为浪漫主义莎评家们不断投入情感、并进行违反作者原意的解读的一个对象。但不管是文本中所提供的证据,还是戏剧传统和历史观念中的种种迹象,都说明福斯塔夫就应该是一个懦夫。
福斯塔夫在盖兹山被王子捉弄便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彻底的懦夫和胆小鬼,而这种对愚蠢的人的捉弄则是喜剧传统中的常用技巧。“它本身就是一个恶作剧的案例,这是一种古老的技巧,莫里哀、哥尔多尼、哥德史密斯、谢里丹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们都以此为乐,菲尔丁、斯莫利特、狄更斯以及至今还存在的闹剧也都没有将其摒弃。”[5]因此,斯托尔再次强调,莎士比亚戏剧不同于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莎剧中的情节比人物更重要。人物的性格就是人物给观众的第一印象,性格并没有任何发展。福斯塔夫一开始在盖兹山表现出的懦夫形象就是他的真实性格,而不可能是他的伪装。而从喜剧传统来说,福斯塔夫和普劳图斯笔下的“吹牛的士兵”(miles gloriosus)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传统一千多年来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所以任何感伤主义的解读都是不可取的。
四
在《莎士比亚的艺术和技巧》一书的最后两章,斯托尔把莎士比亚放在从古到今的喜剧与悲剧的对比中加以讨论,这使他的莎评上升到了一种戏剧理论的高度。斯托尔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与悲剧虽然在氛围上保留了古代传统,使二者判然有别,但在技巧上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两者都会借助阴谋诡计、乔装误认等手段获得戏剧效果,只不过喜剧中这些阴谋和误会带来的结果没有那么严重而已。斯托尔指出,在文艺复兴喜剧中,喜剧和悲剧都会用挑拨离间者。悲剧中的“恶棍只是更大胆的和更放肆的命运之神”[6];而在喜剧中,这种误解、乔装则更加常见,莎士比亚喜剧也不例外。不过莎士比亚喜剧还有一个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为了使这些外在的形式更可信,会不断地变换场所,把事情搬到更具传奇色彩的森林中,使人们更容易相信。
斯托尔认为这些戏剧技巧是从传统中得来的,是非心理的技巧。这种技巧与现代戏剧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因为现代戏剧更像生活,所以不如文艺复兴戏剧有感染力:
无论在喜剧或悲剧里,这种非心理的方法——借助于误传和误解——在效果上要比心理方法更为有力。……现代戏剧,表面上是更令人信服的,但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无论是在阅读中或在表演中,它们基本上都缺乏力量。就性格或戏剧情节来看,就人物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来看,它们都不那么感人。它们更像人生,但它们的对比没力气。[6]
文艺复兴时,不论悲剧还是喜剧,都是为了达到一种戏剧效果。“悲剧效果所需的是现实的幻象,喜剧效果所需的是讽刺或滑稽,夸大或变形:但二者都不需要抄袭生活。”[6]悲剧中要用激情和感情激起怜悯和恐惧,作家需要制造一种情境来唤起同情。喜剧则相反,要尽量避免同情,要突出受骗者和失败者,揭露他们的蠢行,使观众觉得可笑。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戏剧大师有时会糅合两种效果,比如夏洛克和福斯塔夫就被无意间糅入了同情元素,其结果就是莎剧的喜剧效果不如莫里哀等人的作品强烈,因此才导致了浪漫派莎评家的种种误解。
总的来讲,斯托尔的这种戏剧理论是建立在喜剧基础上的。他所说的技巧问题,也基本上是来自于古代喜剧的技巧,只不过他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些技巧也被用在了悲剧中。由于喜剧与悲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两者能够被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在《莎士比亚研究:历史与比较方法》一书中,斯托尔还比较了莎士比亚与莫里哀的喜剧,他认为莫里哀和琼生属于同一喜剧传统,重复是他们惯用的技巧;而莎士比亚则属于另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有可能来自普劳图斯,也有可能来自假面剧。在这方面,应该说斯托尔为莎士比亚喜剧研究奠定了一个比较文学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之一。这也是为什么《莎士比亚研究》一书的副标题是《历史的和比较方法》。
斯托尔的戏剧理论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戏剧的最终效果或作用。关于这一点,斯托尔总结道:“这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创造出一种情况而不是发展已有的某种情况,是制造一个故事情节,而不是反映自然。这不是精确地、忠实地模仿生活,而是像一切艺术那样——在媒介与传统的范围内,在习惯与想象的范围内——用某种特殊方式模仿生活,迫使我们进行思考和感受。”[6]
斯托尔进一步指出,这种戏剧的作用就是诗或文学本身的作用。这就触及了斯托尔莎评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虽然在《莎士比亚的艺术和技巧》中涉及不多,但斯托尔在《莎士比亚研究:历史与比较方法》和《从莎士比亚到乔伊斯》两部专著中反复论述了这一问题。“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品味而不是这个时代本身,这两者常常差别巨大。……文学当然不是生活,也不是历史或历史的材料,而是一个卷轴,在这个卷轴上描绘的是作者和读者无拘无束的思想——这是一个生活中的生活,奇特却与事实相冲突。”[5]文学不是对时代生活的记录,也不是对作者生活的记录,而是反映时代的品味和作者的品味,因此文学作品不是历史的记录也不是无意识的自传。在某一特定时代里,艺术与艺术之间的联系要大于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并且,艺术如果想要在观众中获得影响,就不会太超前于观众的理解力。斯托尔是站在当时的观众接受和作者意图的前提下考察戏剧功能和效果的。从这个立场出发,他与后来的历史主义批评家也有很大的分歧。因为无论是坎贝尔还是蒂利亚德,都倾向于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对当时的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斯托尔则反对这种看法,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莎剧只能被当作戏剧来看待,而且这些戏剧的目的只是为了取悦当时的普罗大众。
五、结语
文学并不一定反映现实生活,因此也不能用心理或性格分析的方法去解释。斯托尔的这一观点不仅有利于改变当时的批评风尚,肃清浪漫主义莎评的影响,为历史主义登上莎评舞台扫清道路,而且至今也仍然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毕竟我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和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人物性格的心理分析层面,我们对文艺复兴及其以前的欧洲作品也往往会按照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方式去理解。但斯托尔这样的历史主义莎评则早已证实,这样的解读是不正确的,是一种“时代错误”。
但是,斯托尔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斯托尔认为哈姆雷特的自我谴责只是在拖延戏剧节奏,但这个解释显然无法说明为何《哈姆雷特》却成为莎士比亚所有剧作中最长的一部。因此,回归文学传统的做法不仅割裂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也排除了对文本意义进一步发掘的可能;所以,当斯托尔后来又否定莎剧中存在任何象征的时候,就等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限制了对莎士比亚的进一步解读。
总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托尔的这些解读从伊朝戏剧传统出发,企图还原一个当时观众眼中的莎士比亚,这对矫正浪漫主义个人体验式批评的感伤主义错误倾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观点也暴露了斯托尔在试图还原莎剧本来面目时的矫枉过正。客观地讲,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毕竟有某种能够超越其时代的特质。斯托尔虽然也承认夏洛特和福斯塔夫比其他传统喜剧人物更复杂,但仍然坚持认为应该从传统的角度理解这些人物。因此,他的解读虽然将莎士比亚从浪漫主义的时代错误中解救出来,但同时也无视莎士比亚的伟大特质,强行将其拉回到马洛等其他文艺复兴剧作家的水平线上。这也正是包括斯托尔在内的许多历史主义批评家们所共有的局限性。
[1]Elmer Edgar Stoll.Anachronism in Shakespeare Criticism[J].Modern Philology1910,(4):557—575.
[2]Michael Taylor.ShakespeareCriticisminthe Twentieth Centu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Elmer Edgar Stoll.ArtandArtificein Shakespeare:A study in Dramatic Contrast and Illus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4
[4]ElmerEdgarStoll.Hamlet:AHistoricaland ComparativeStud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19.
[5]Elmer Edgar Stoll.Shakespeare Studies:Historical andComparativeinMethod[M].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60.
[6][美]斯托尔.莎士比亚的艺术和技巧[A].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