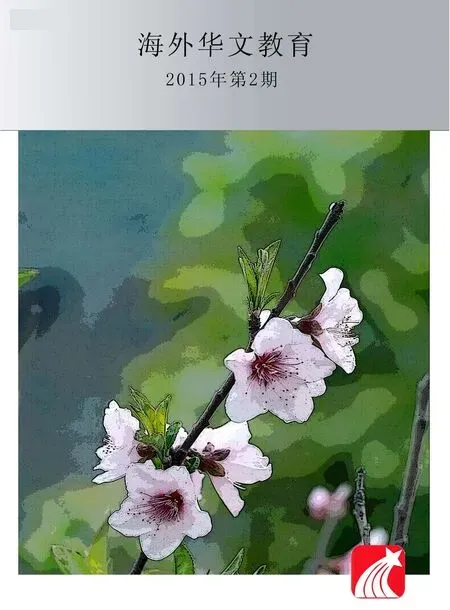论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史意识
2015-03-27宋晖
宋 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中国 北京100024)
一、引 言
我们之所以讨论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史意识问题[1]是基于许嘉璐先生对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到第二个阶段(文化平台的构建)的判断。
许嘉璐先生(2012)指出,汉语国际教育已经从第一阶段发展到了第二阶段,即从单纯的汉语教学转变为全面的文化交流。这个转化的理论基础是: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汉语和文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语言文字的本质是交际,承载着历史文化内涵。并举例“同胞”中“胞”左边是一个像月亮的“月”字,就是肉字旁,右边一个包袱的“包”。这个词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先进的哲学观念。“胞”是胎儿在母体中包在他身上的一层膜,即“衣胞”。所谓“同胞”,是说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就像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孩子。这个观点发展到宋代,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张载——又叫张横渠,因为他是陕西宝鸡横渠镇的人——用了一个词叫“民胞物与”,意思是:全天下的人都是兄弟;世上万物,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虫鱼,都是我的朋友。如果我们发出“min baowuyu”的声音,或用拼音写出来,就显示不出它的确切含义。所以,汉语和汉字是在特殊的文化载体中的一个特殊的系统和品种。特殊表现在哪里?形、音、义、词的组合,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老师如果没有讲过这类内容,或无法深入而又浅出地向学生传达,学生就只能是了解日常用语,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2]
鉴于汉语国际教育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在发展方向上的明确转向,笔者认为有必要更新固有观念或者确立崭新的教学理念,否则,我们将因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而落后于时代。要想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操不同语言的交际主体之间实现全面的文化交流,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必须具有文史意识,这里的文史意识包括两重含义,即对中华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全方位了解和对世界文史知识(或某一国别的文史)有相当的了解。尤其是在日益强调国别化教学,教材教法本土化的今天,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本身对所在国家的文史知识必须要深刻了解,因为要想有效地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得到别人的认同,就必须首先尊重别人。
二、“听不懂”难题的文化求解
(一)咖啡和油条:从“听不懂”到“听得懂”
2013年7月18日,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先生和笔者谈到了一个几十年前他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时遇到的一个问题[3]:他当年拿着西方音乐给中国人听。得到的回答是:听不懂。他注意到了“听不懂”。因为西方人听到中国的京剧或者其他戏曲形式时,会用“喜欢或不喜欢”作答。他问我这里的“听不懂”的背后反映了什么含义。本文将之归结为“听不懂”难题。笔者在后来给白先生的回信中认为,这里的“听不懂”可能有两重含义。因为对于音乐来说,无非是旋律所传递的情感和音乐本身文本的内容。第一,听不懂的是所指对象的含义,这里的含义是指音乐本身所表达的情感。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化里比较常见,对于听得懂的人来说,音乐可以杀人。对于听不懂的人来说,音乐伤害不了人,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的《碧海潮生曲》,对于周伯通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根本抗拒不了。而对于郭靖来说,就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同样,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两个弹琴的杀手弹的曲目《筝锋》也是无坚不摧。倪匡小说《六指琴魔》中的天魔琴也是杀人利器。第二,是听不懂音乐文本的内容。这里是指唱词,是文本内容的。这是由于语言差异导致的,因为音乐的旋律本身可以说是无国界的,诚如数学一样。这里的听不懂和看不懂是一样的,如果您拿法文版雨果的《悲惨世界》给我看,我肯定是不懂。但是翻译过来的作品,我想还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之所以说部分理解,是因为翻译对文本的重现是有限的。所以,异质文化沟通的首要渠道是沟通,这个沟通是在误解中不断修正,是在试错中前行的,但“前进中的问题可以在前进中解决”,总比不沟通要好。由此,我们思考“听不懂”难题必须在文化上寻解,当年的“听不懂”也许是一种拒绝,是对外来文化的排斥。
文化上的双向沟通需要咖啡也需要油条。现在的中国之于西方发生了巨变,人们即使在第二个层面上不能理解西方,也更愿意以第一种方式试图走进西方人的世界。因为文化上的接受或者异质文化间的吸引越来越有市场。这种态度反映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例如,走进国家大剧院听交响乐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用原文看美国大片的中国孩子在日益增多。同样,交流是中外双方都关注的,走进中国求学、工作甚至定居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中国通”在中国寻觅着各种交流机会。而且大家都在寻求融合,而非绝对“同一”,肯德基不仅提供咖啡,早餐也增加了油条。简而言之,“听不懂”不意味着不能沟通,“听得懂”也未必深谙其义,文化上的沟通与交流需要咖啡也需要油条,只有在和谐中寻求认同,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
(二)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深源文化观
文化平台的构建,在当下的全球语境下更需要对自身和他者的文化异同尊重和理解。这既包括对文化一致性的尊重,同时也包括对特殊性的尊重。笔者(2013)认为,汉语国际教育的本质在于文化交流。如果我们把雁雁成行、牙牙学语作为浅源目标的话,那么文化认同则是汉语国际教育的深源本质。“2005年11月16日,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中国外交学院讲演时表示:21 世纪的思想完全不同,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和谐的思想。现在法国的很多学者都主张一种复杂性思维,他们认为在政治思想方面应当能够把反面的、对立的、冲突的东西都能够纳入进来。这种思维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超越的思维,和谐的思维。而我认为,中国的古来文明为世界上和谐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4]而要想真正实现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图景,实现整个人类的和谐发展,我们认为首先在理念上需要摒弃对抗、不合作等理念。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理念来看待的话,除了关注“和”,还应该将“不同”作为中华文明的个性充分展示,也就是说“不同”与“和”在国际交往中同等重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不同的”、“民族的”、“个性化的”才是有可能在文化上更有价值的。这里可以拿新加坡的发展理念作为佐证,2012年,新加坡总人口临时数字为531 万,国土面积716 平方公里,是多种族的移民国家,也是全球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即使这样,新加坡政府还是坚持强调新加坡“在关键方面是一个亚洲社会,……尽管我们讲英语、穿衣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更长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的仿制品(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社会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5]
其实,“和”与“不同”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问题的辩证两面,过度地强调单方面都可能给我们的认识造成偏颇,使实践盲动。如何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呈现给世界,这需要首先从我做起,由于冷战思维,甚至民族或宗教的因素,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不乏负面形象或定式思维,为此,作为汉语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教师必须要打破陈规,在误解中纠偏。亓华(2007)认为必须要打破固有的,业已存在的定势。他认为,外国留学生倘若带着他们在国内预先形成的“定型观念”来看待中国,也会出现偏差,导致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误解。譬如,听到有人打招呼的时候问:“你吃了吗?”就以为中国人因吃不饱饭才如此说。有人把中国女教师不戴首饰,把小孩穿开裆裤当成是中国的贫困的现象,把中国人饭后几个人争着付钱理解为虚伪、不诚实等等,都是在同一种文化定型观念的主导下对中国的误读。……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表明,重要的不是要建立什么“定型观念”,而是要打破“定型观念”—为了让教师更好地教授学生,必须打破对外国人及外国学生的某些定型观念;为了使外国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必须打破他们从国内带来的关于中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定型观念。
(三)信息化带来的交际困惑
面对面交际中存在的“听不懂”难题,可以用深源文化观解释。但时下在语言学习中,我们遇到的难题却是由时代的进步带来的新问题,不同国家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在面对网络化的问题上,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态度,一种是乐此不疲于深居简出,将自己封闭在网络社区,经常与母语者交流,这类学习者以韩日学生为多。一种是乐此不疲于游行天下,即把网络视为交际工具,深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风土人情。所以说,线下学习如果说还是以语言学习为主的话,那么,线上学习就一定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在中国学生热衷于美剧、韩剧时,我们是否能够开发出反映中国文化要义的诸如“甄嬛传”之类的剧作;能否使我们的网络课程丰富多彩,现行的网络课程多以离线形式、简单问答式和语言学习为主,而开放课程以及课程设置都存在很大问题。如何利用好网络平台,使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学习多样有效,将成为文化平台构建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大历史观的确立
如果教者具有深源文化意识有助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话,那么,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则为学习者突破语言学习,进入文化交流打下扎实基础。可是,不无遗憾的是2007年在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包括“语言基本知识与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和“教师综合素质”等五个模块十个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课程设置中,从来就没有给予历史学科或者相关知识背景以相当的重视,可以说,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的事业中缺乏相关的历史意识。
(一)世界史:从忽视到关注
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了。而世界各国的交流在当下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地球在信息化时代成为了“村落”,历史(对于我们来说过往即历史而无论其长短)在这个村落里成为了世人敝帚自珍的稀罕宝贝。文化交流在历史语境下可以突显深度。汉语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需要历史衬托,而往往交流是多源的,以英语为例,“1066年的诺曼征服,使英国产生了奇特的双语现象:先是不同阶层说不同的语言,上层统治者亦即征服者说诺曼法语,而下层的被统治者说的是英语。地位优越的法语不需要从英语借词,而英语从法语借的只是上下层需要交际时的用语,一般是跟贵族生活有关的词语,这就在英语词汇上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如一些牲畜,它们活着时的称呼用的是源自英语的词:pig、sheep、ox 等,而一旦上了餐桌,成了佳肴,就有了个法语名字:pork、mutton、beef 等。……但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英语也从汉语中分散地借词,如从汉语借用的sampan(舢板)、chinchin(请请)、fantan(番茄)等。”[6]在这段引述中,我们看到了英法的交流,也看到英中的交往,这为彼此相互理解找到了历史上的契合点。
关注世界史的意义恰在于此,我们不仅要重视眼下的交往语境,更要重视深层次的他者语境。我们需要知道历史上我们与世界都发生了什么,而且更需要细化到我们与世界同时发生了什么。以往一遇到争端,我们总是一味追求“求同存异”,基本上是处于遇到问题搁置不管,或者遇到困难绕着走,这在短期内是有效的。汉语国际教育的第二个平台的构建之要义,我们认为是找出“同”,让我们对镜彼此;同时找出“异”,让彼此发现不同。这样的相互理解才能深刻,这样的交往才更有意义。
传统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去除有机物、营养物质和病原体等,在实际污水处理过程中,这些物质能够被持续有效地去除,但对EDCs的去除效果往往较差.因此,为减少这些具有潜在危害作用的微污染物释放到环境中,对污水处理过程中EDCs的归趋及其去除情况进行评价,对优化其处理过程十分必要.
(二)国别史:从面面俱到到个别研究
语言说到底就是交流的工具,在汉语国际教育的第一个层次学习中,语言关已经被成功逾越了,接下来学习者要用语言这把钥匙打开中华文明这扇大门。这将使得学习者不经意间发现由于本国发展史或文化的不同导致的语言差异。如“实事求是”是汉语的说法,英语说法是“铁锹就是铁锹。”(Call a spade a spade.)西班牙语是“面包就是面包,酒就是酒。”(Call bread bread and wine wine.)再如,“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是汉语的说法,英语说法是“一匙沥青坏了一桶蜜。”俄语说法是“一个苍蝇毁了一剂药膏。”[7]
但是,我们的教师是否也可以同时打开彼岸的大门呢?以往在汉语国际教育第一阶段时,我们对教师的要求是对世界文化和历史泛泛博学,强调地是知识的广博性,那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教学很少进行国别分班,而随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世界上广泛开花结果,国内派出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如果对所在国的文化历史没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将很难想象与教学对象“亲密接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一定反映历史。而深层次的语言学习会突破学话阶段,而进入到制度和习俗的对比中来,这就要求教者必须具有“原典”意识。比如中国的成语很多都是具有理据性的,如果教师只是泛泛讲“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学习者肯定会觉得枯燥无味,但如果结合《庄子·逍遥游》用故事的形式展示给学习者可能效果就会更好。再如“《圣经》的最早文本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后译成拉丁文本,再由拉丁文本译成英语《圣经》,因此《圣经》英文本反映的不仅是英国古老的文明,还有西方其他民族的文化。其中不少词语都记述了一段神奇的圣经故事。”[8]如果我们能够加以对比,或者深入研究,在文化交流中便会多一些理解力。
关于这一点,李如龙(2012)认为,在语言之外,汉语国际教育要做到在地化,主要是要适应当地的国情、民情和地情。所谓“国情”,荦荦大端自然是政治制度与文化政策。友好国家和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自然会提供汉语国际教育的必要条件。然而与语言教育关系最深的是所在国的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所谓“民情”,宗教信仰和民族情绪居其首,此外还有极其多样复杂的文化情结。汉语教育必须努力适应当地的民情,尊重当地文化,存异求同,做得好能提供教学方便,增进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做不好也可能造成更大的隔阂。语言教学一旦和文化的理解发生分离和冲突,语言教学活动就势必难以开展。所谓“地情”就是所在地区的综合性的社会特征。除了当地与所在国的政治氛围、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的不同之外,一定地域特有的地理环境、民族成分、移民来历、经济业务,与毗邻国家或地区的交往,也是构成不同地情的因素。
(三)中国史:从零散到系统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史理所当然成为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其中涉及中国语言文化史的内容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以往我们对于一些有历史理据的词语,只是注重其文化义的解读,而忽视了对其史料爬梳。如“喝墨水”一词,我们只是以知识性讲解为主告诉学习者,这个词和“读书、上学、学习文化知识有关”。进入到“第二阶段后”,我们这种已有的零散的历史知识会导致教师遇到问题时“失语”,甚至在与高层次的学习者交流时产生信息不对称。这时的讲解已经不能满足高层次的学习者需求,我们必须告诉学习者,“《隋书·礼仪志》记载,北齐规定,书绩滥劣者,饮墨水一升。”
所以,我们主张应在零散的历史知识基础上,加紧文化词库的研发。“目前,国内的中华字库等重大攻关项目纷纷启动,而对于汉语国际教育而言,词汇无疑是最直接体现文化差异的要素,但对汉语国际教育的词库或字库建设却鲜有关注。杨建国(2012)深刻提出,要研制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适合汉语国际教育的汉语文化词表,从语料库建设的角度而言,需要考虑建立两类语料库:一类是大规模的当代书面语语料库,另一类是适度规模的口语语料库。前者要考虑语料的全面性、平衡性,要能覆盖所有领域,照顾到不同文体;后者要考虑语料的真实性、自然性,要能反映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下的真实思想和心态。我们说这种文化词库建设在进行设计时必须把对象作为客户考虑,根据不同的客户,一定要实现差异化建设。教材建设已经很注重国别化了,文化词库建设也必须考虑东南亚文化圈和欧美文化圈的问题,甚至也要基于不同的国家进行设计。”[9]
四、余 论
以上,我们对许嘉璐先生提出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到第二个阶段(文化平台的构建)做出了回应。我们基本上是从师资的角度提出应具有一定的文史意识。至于如何确立应有的文史意识;是否应该在相应的课程设置中有所体现;面对第二个阶段,又会遇到哪些新问题,如高层次的学习者已经使我们应接不暇(这一定不乏已有的学习者要进一步学习中国语言或者文化),还是原有的知识体系需要调整?林林种种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调研和研究的。
在文化观上,我们之所以要强调深源文化观,是因为以往我们把文化简单化处理了,中国的文化元素是什么,有哪些,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不要一味地突显京剧、书法、武术、剪纸等技艺,而更应该深层次挖掘中国元素,这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或者他者的眼光来观测。如我们可以看看大英博物馆中展厅中的中国物件,外国人拍摄的纪录片,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白乐桑先生甚至认为,中国的晨练都是值得关注的。[10]
我们之所以强调世界史、国别史和中国史,简称“三史观”,是因为我们要提供给学习者的是一个全景化中国与区域化世界。任何的片面都会带来理解和沟通的不畅,任何的残缺都不会是继续学习的动力。
注释:
[1]本文所指的“文史意识”区别于史学上所称的“文史观”,“文史”意为“文化和历史”。
[2]详见许嘉璐,继往开来,迎接汉语国际教育的新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 期。
[3]2013年7月笔者与白乐桑先生共赴安阳考察中国文字博物馆和殷墟,返程时白先生与笔者聊及此问题,他认为,“听不懂”的回答方式似乎更反映了汉民族更关注意义。
[4]详见程麻(2012:239)《和山姆大叔对话——中美文化心理比较漫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详见[美]塞缪尔·亨廷顿(2012:295),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
[6]详见潘文国(1997:60—61),《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7][8]详见朱文俊(2000:193、416),《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9]详见宋晖,《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化语言学接口》,《国际汉语学报》,2013年第1 辑。
[10]这是笔者和白乐桑先生交谈时得知的。
[美]塞缪尔·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
程 麻:《和山姆大叔对话——中美文化心理比较漫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李如龙:《论汉语国际教育的国别化》,《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 期。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
亓 华:《汉语国际推广与文化观念的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 期。
宋 晖:《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化语言学接口》,《国际汉语学报》,2013年第1 期。
许嘉璐:《继往开来,迎接汉语国际教育的新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 期。
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