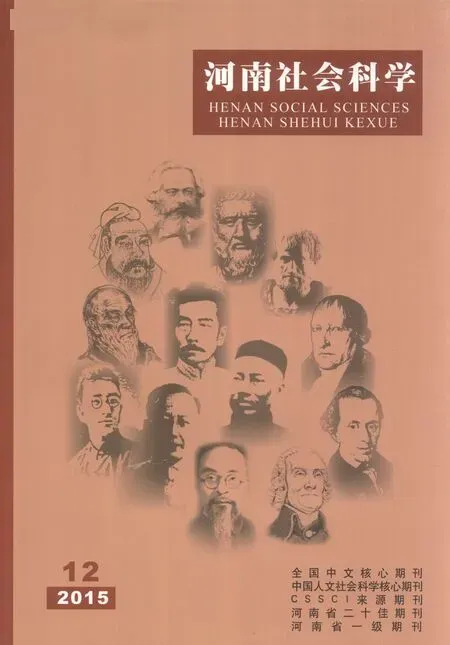论儒家思想中的价值信仰及其实践性
2015-03-26吴云
吴 云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2)
现代性“道德谋划”的失败,使得社会“伦理共契”碎片化,道德观念之一致性的丧失,成为最为深刻和危险的现代性危机。究其原因:其一,改革开放经济加速转型而导致的经济理性,其巨大的宰制作用,使得人的意义世界消退。其二,单子化的单一个体所组成的现代社会失去了可能整合的社会认可,社会阶层、贫富差距、生活方式、态度意识的“碎片化”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代性后果。其三,道德义务论者片面强调道德的内在动机性,忽视“道德心理”的相互性,“正义动机的条件性和不稳定性在无法律保障其相互性的”[1]环境下显现出来。这样在道德发生的客观外部机缘和道德主体的内部机缘的双重层面产生了危机,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中产生了“共鸣”——信仰危机、道德信仰危机。
一、儒家文化形态与价值信仰
(一)儒家文化的理性化形态
马克斯·韦伯通过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对基督教神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改造,从而生产出“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基础。而中国文化的理性化进程,它的“价值理性的建立过程,是与对天神信仰的逐渐淡化和对人间性的文化和价值的关注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它是由夏以前的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又由祭祀文化的殷商高峰而发展为周代的礼乐文化,才最终产生形成的”[2]。漫长的演变,历史的积淀,为儒家文化的产生赋予了浓厚的理性色彩。其逻辑推理缜密,思辨具体而不抽象;理论建构完整,系统而不华丽;具有实践的和实用的品格。李泽厚先生将之归纳为“实用理性”:一方面同思辨的思维模式形成对照;另一方面凸显其伦理实践。梁漱溟先生指出,儒家文化“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人”;使得“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3]。因而,不管文化形态上的“以道德代宗教”,或是在民众生活中体现的“实用理性”,都体现出儒家文化的理性化。
(二)儒家文化的超越性特征
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根源于道德理论的前提预设和德性生成的修养功夫。人性论是儒家道德理论的出发点,从探究人性之性入手,孟子认为是“人皆有之”“我固有之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对于孟子而言,人性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因此,孔孟极为强调人之性分所蕴含之仁义的绝对性、普遍性、无条件,认为此仁义作为一无条件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标准,其价值在贫富、贵贱、荣誉等一切外在的利害关系之上,甚至在人的生命之上。其终极性和超越性体现为人心的内在超越性。这种绝对价值,在宋明理学家那里进一步升格,客观化为“天理”“天道”,而通过成圣和超越自我的精神修养来体现这种绝对价值——“天道”“天理”。这样,“天理”“天道”为道德提供了本体论的根据,成为价值信仰的终极依据。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先生认为儒者之“天”与“天道”乃是具有形而上的精神、生命的绝对实在。天道既超越又内在,具有主客不二的特性,是一种和合的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4]。这就进一步把天与人、超越世界与伦理世界沟通了起来,道德便直接被赋予了超越时空的绝对性和至上的权威性,而成为康德式的道德律,价值信仰的终极理由仍被留在了现世。但是,从本源意义上又不同于西方宗教信仰,需要借助一中介——“上帝”来认识、体验和实现终极关怀,因而西方的宗教信仰成于天人分离。儒家文化的价值信仰成熟于天人合一,在儒学“天人合一”的宇宙伦理模式中,理想人格既是天人关系的中枢,又是天人关系的化身。因此,儒家文化中的“价值信仰”的完成,落实在现实理想人格的塑造上。
(三)儒者价值信仰的建立
有的学者认为,儒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士”阶层之间,发挥的作用是一种准宗教的作用。依此视界,从儒学的历史功用来看,就是对个体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确立的终极根据的寻证,并有超越的形上的关怀。这一方面是来自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为人之道,以社会内在的文化秩序和价值原则化成天下,使人们有了坚定的生活信仰;另一方面,儒者自身将生命与理想、信念融成一体,其人文理想和价值世界与敬天、法祖,上帝、皇天崇拜,对天与天命、天道的敬畏、信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救民于水火”“即世间即出世”的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担当精神、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信仰上的终极理想,与宗教徒无异。但儒者又生活在伦常之中,不离日用常行,在凡痛中体验生命、体验天道,达到高明之境[4]。而这一过程,即是儒家谓之的“修道”。
儒家修道之功夫,无论是从方法、过程还是从归宿来看,都是在客观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儒者的价值信仰便具有了鲜明的客观实践性特征。这是就价值信仰发生的客观的现世社会领域来讲的,内在的则要从修道之途径、发生机制等方面探讨。
二、儒家价值信仰的实践性
(一)修道:价值信仰之精神层面的确立
儒家从孔孟的“仁”“性”学说到宋明“天理”之说,沿袭了“性与天道通而为一”的学理架构。孔孟所强调的人之性分所蕴含之仁义以及人之践行仁义具有绝对性、普通性、无条件性的主张,后来为二程、朱熹等宋明理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文碧方,2005)。因为,孔孟认为只需“直下肯定”人性就能具有仁义,即谓“此天之所与我者”,人性通过直观即达天道。这种简陋的体道学说到宋明时期得到完善。尤其是朱陆等人解决了问题的关键——“通”以及“得道”。
在“性”与“天道”通的方式上,宋明儒学采取了一种先验性的理解形态(文碧方,2005)。在这种先验性的理解进路中,他们不仅认为性与天道相贯通,而且视性与天道为一。而二者的互证存在(天道、人道的相互呈现)关系,使得个体以人道体现天道的方式得道。这就突破了“得道体验的个体性”之局限,而以“社会性、普遍性”的天道为归宿,因而也是离不开社会实践的。
而由认同此理到实践此理,则是一个向外扩充的过程,也是一个向下落实的过程,其终点是道成肉身式的践行,它不只是主观的精神境界问题,更是客观的道体流行,是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的现实归宿处,并且,“只有当人亲身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只有当人用全部的生命领悟到了它的可信、可爱、可敬和可畏,并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托付于它,与它融为一体,才算真正得道”[5]。因此,具有神圣性、绝对性、普遍性的天道(道德律)又在于人自己去彰显、去遵从和履行。正是在这种自主的行动中,个体的道德品质得以提升,道德理想得以建立,道德人格也在人文实践中不断完整和超越。这一过程具体在行道中得以落实。
(二)行道:价值信仰之经验层面的践行
儒家的修道对个体价值信仰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从主体内在出发认同“天道”这一人生价值、存在意义的终极依据,从而达到信仰,建立价值信仰。但若停留在这个层面,儒学就无异于佛老之学,其文化气质也就转化为思辨模式。然而,儒家在确立天道之时,其中便体现了“人的社会生存的普遍价值”。从行道方面来看,修道又是行道的准备。从修道到行道,又是儒家文化的人文实践的理性化特征使然,使人在现世伦常生活中践行“道”。因而,儒者真正认同了“道”,建立了价值信仰,就必然在现世“人道”生活中体现出来。即是要在满足个体生命之安身立命需要的同时,唤醒个体自我的社会担当意识,自觉投入改造现实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去。
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儒家行道方式和坚持的原则也是不同的。在早期儒家的政治实践中,儒者以“三代之治”为理想,坚守道义,甚至以生命捍道。早期儒者的政治理想主义的特征,试图将政治秩序纳入文化秩序的治理之道。然而结果多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结果。但儒者坚定的信仰并未使其否定行道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进而选择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甚至“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心上》)的豪迈行径。
但是,礼乐崩坏的事实至少说明了社会客观上已步入一个并非仅以文化秩序即可规范整合的新阶段。因此,汉初,汉儒援法入儒,在一定程度上使儒学法家化,扭转了儒家政治实践的被动局面。汉儒对孔孟学说有一定程度上的损改,但这种改变更多的是在实践层面上,是修道所做的功夫的改造,而非道、修道的改变,具体在治民和教民两个方面实践之。
宋明之际,随着封建专制主权的巩固,皇权与纲纪、皇帝之私欲与社会之公义之间的矛盾尖锐。于是朱熹像所有的儒者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改造现有的皇帝以阻止其沿着非理性的方向独断专行,这便是“格君心之非”。朱熹坚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的儒家道义论立场,宁可死守山中。由此,不难看到,只有建立虔诚的信仰,普遍价值才能成为决定自我生命之意义的唯一绝对的标准,永远处于未决状态的生命才能获得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而只有立定道义立场,现实的价值抉择才能排除一切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从而“凡其所行无一事不得其中,而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文集》三六,《答阵同甫》八),并由此通向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之路[5]。
三、儒家价值信仰的资源性意义及不足
(一)儒家价值信仰的资源借镜
1.儒家价值信仰对个体的道德品质提升、道德人格完善以及道德理想建立的有效作用机制,尤其是由内而外的道德修养功夫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澄清,融入公民道德人格培养和道德理想的建立中,为现代公民重塑安身立命之所。
2.儒者强烈的道义担当、社会责任意识和对国家社会的义务感,在面对社会、国家的道义衰落时能挺身而出,坚守道义、公义,不失志,始终保持崇高的道德责任。社会主义公民的法权身份在《宪法》中得以保障,而在现实生活更应激发出其主人公的崇高道义感。
3.儒家价值信仰的修道、行道功夫,使修身和政事二者关联起来,使修身成为政事的必要准备,政事成为修身的功夫。在不同的阶段,二者互为体用,从而使儒者的道德人格与政治人格相统一。在社会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现代化社会,社会公民的社会角色和个体自我认同间的张力使公民人格分裂,成为现代社会对公民“异化”的另一个事实。儒家的价值信仰为弥合个体人格分裂提供了价值基础。
(二)儒家价值信仰的不足与克服
当然,儒家价值信仰的不足方面也是致命的:一是道德教化的主体定位问题。有人指出儒家文化中的精英伦理定位,其道德主体是定位了当时社会的士阶层或者是士大夫阶层的,而根本上不是对普遍大众的道德关怀。这对现代民主法治下的公民道德建设无疑是有害的。二是儒家的道德教化即修道、行道,而修道的出发点是人性,终极依据是精神的;而行道的政事活动也是“事君以道,不合则去”的原则,而即使有道义的担当也只是改造统治者违背仁义的非理性行为——“格君心之非”,即便一个皇权代替另一个皇权,儒者这种道义担当仍然不变。
因而,这种不具有社会改造力和无法创造新生活秩序的精神形态,在社会转型时期无疑无法开出新的意义系统。
在信仰理想和秩序一旦发生某种松动的时候,重塑信仰、坚定理想和整饬秩序,对文化本身的发掘是最直接的思想武器。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也指出:“一个社会每当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就会本能地转眼回顾它的起源并从那里找症结。”因而,以传统文化中优秀道德资源重整社会文化价值基础克服信仰危机、道德信仰危机,就尤为必要和紧要。同时,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人们可资利用的道德资源和走出困境的方式又是不同的。
实际上,现代儒家一直致力恢复儒家义理对公共伦理秩序的治权,它有两个方面:一是重新整合礼与乐,这在梁漱溟的“乡建运动”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是从熊十力到牟宗三的当代“新儒学”的心学复兴(刘小枫,1998)。前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方向未能成功;后者因缺乏基层社会群体的关系,无法推展其道德意识的社会功能。因而,传统儒家优秀道德资源的发掘,首先要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背景下进行;其次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为主体定位,反对传统伦理的精英定位,以培养和实现现代公民的理想道德人格为指向。
(本文为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为:AHSK11-12D229;安徽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JG12149)
[1]慈继伟.正义的两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陈来.古代宗教和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郭齐勇.儒学: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教性品格的精神形态[J].文史哲,1998,(3):36—38.
[5]赵峰.朱熹的终极关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