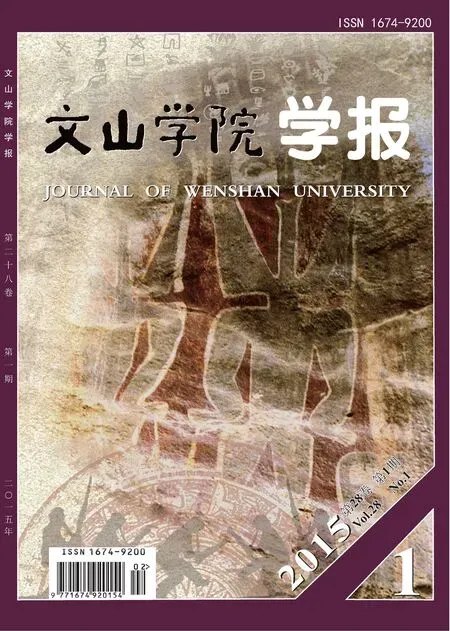一种艺术形象的两种表达
——叶梅《撒忧的龙船河》与电影《男人河》对比阅读
2015-03-21方华蓉
方华蓉
一种艺术形象的两种表达
——叶梅《撒忧的龙船河》与电影《男人河》对比阅读
方华蓉
(湖北工程学院 文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撒忧的龙船河》是著名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的中篇代表作,《男人河》是叶梅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从小说原著到影视艺术,叶梅实现的不仅是身份的转换,更是一次认识生活、理解生活的审美视角上的重新调整与定位。文章对二者作了细致而详尽的比较阅读,探究作者隐含在同一种艺术形象里面的对土家族文化的深层思考。
《撒忧的龙船河》;《男人河》;艺术形象;文化内涵
叶梅是享有盛誉的土家族女作家,奇伟瑰丽的巴楚风情和绚烂神秘的土家文化共同滋养了她独具特色的艺术生命。叶梅也有着自觉的民族意识,她的创作,根植于她爱之深思之深的土家族,通过她如神的笔墨,土家这个民族在新时期文学的艺术殿堂中散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叶梅还是一位有着多种艺术才华的作家,在这个大众传媒日益盛行,人们自觉追求视觉文化享受的时代,她亦频频“触电”,不仅主动创作影视文学剧本,而且担当编剧。她根据自己的著名中篇代表作《撒忧的龙船河》改编而成的电影《男人河》,更是取得了不俗的实绩。对叶梅而言,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艺术才华在影视界的充分展示,更重要的是,她的民族——土家族在文学界与电影银幕上的一次绚烂绽放。同一条河流,一种艺术形象,叶梅借助了小说与影视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两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反而收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
“撒忧”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土家丧葬习俗,源远流长,深刻地反映了土家人民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特生命观念与文化信仰。这种丧葬仪式,伤而不悲,狂而不邪,欢欢喜喜办丧事,热热闹闹送亡人,快快乐乐陪亲友。“撒忧”,既为逝者抚平创伤,也为生者解除忧愁。死亡,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反而是一次土家人生命最辉煌的张扬。《撒忧的龙船河》就是在这样一种耐人寻味又极有个性的民族习俗仪式中展现了土家子民别样的人生风采。小说以土家桡夫子覃老大的丧礼贯穿始终,以他与汉族女子张莲玉和土家姑娘巴茶之间几十年的情爱纷争、生死离合为主线,展现了土家族特有的文化特征,颇有诗情画意之美。全文抒情气息十分浓厚,充满了一种神秘、肃穆而略带忧伤的艺术情调。
叶梅的小说,几乎没有离开过她所熟悉的大巴山,这是她生命与艺术的源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以具有灵性的生命渗透进了叶梅独特而个性十足的“原乡”叙事中。因此,浓郁的地域特色一直是叶梅小说创作的一大亮点。长江三峡、清江流域、巴楚风情,通过她的生花妙笔,无一不散发出令人惊叹的艺术之美。奇峰、悬崖、险滩、恶水、云遮雾罩,雄奇险峻的土家民族的生存环境在奇诡绚丽又原始神秘的风情展示中弥散开来,浑厚豪放,粗犷暴虐。“那河面二十里,起源于龙船寨头一处无名山洞,沸腾泉水在苔藓密布的石洞之外积成深潭,继而跌宕出三道百丈悬崖,蜿蜒九滩十八弯,依次经过苦竹、夫妻、老鹰三峡,最后汇入长江。那河看是纤细实际奇险刁钻,河上礁石如水怪獠牙参差不齐,水流变幻莫测,时而深沉回旋织出串串漩涡,时而奔腾狂躁如一束束雪青的箭簇。”这是小说中一处典型的关于土家人日常生存环境的描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此凶险剽悍、激荡奔放的自然风貌又滋养了土家人与众不同的民族风情。浓厚的民族特色是叶梅小说最为人称道的艺术成就,《撒忧的龙船河》表现尤其出色。整部小说是以土家人的丧葬习俗贯穿其中,从而引出这个民族独特的生死观、婚嫁习俗、生活方式。读罢小说,眼前展现出的最让人回味无穷的无疑就是这个曾经幽居在深山密林的古老民族极具个性且悠远流长的文化风习,那种文化滋润出来的独特人格,以及在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碰撞所导致的分裂与融合,而这种种的艺术魅力又浓缩在小说中精心塑造的主人公覃老大这一人物身上。
覃老大是龙船寨的桡夫子,龙船河上的英雄,勇猛、剽悍、重情重义、不畏生死,他是巴山楚水滋养出来的一个传承土家道德,既有山的豪迈奔放,又有水的深情炽热的男子汉。所以,只有他能驾驭战胜龙船河,也只有他能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助他人。他在极其凶险恶劣的荒山野岭与汉族女子莲玉一夜浪漫,既是遵循了土家人的婚嫁道德,也是原始激情的冲动,从此,他一辈子陷在对莲玉的爱中不能自拔。他同时又有着土家人的道义与男人的责任感,为此又不得不与同族女子巴茶相守一生。他固执、守旧、淡泊名利,无法接受新生事物,而且迟钝、懵懂,永远无法了解由于文化的差异,也由于道德的负累,他那难以言说的爱情与婚姻的失败所导致的人生悲剧。叶梅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常为土家人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那种不被理解的劣势地位而感伤。覃老大眼中的男女性爱,无疑带有原始冲动下的生命力的飞扬,自由随性,两性愉悦,但也绝不是恣意放纵。而莲玉眼中的男女情爱,却打上了汉民族所遵循的贞洁观与伦理观。莲玉对覃老大的所谓“轻薄放荡”的不满与斥责,让这个土家男人背上了一生都难以理解的情感包袱。小说详细地描绘了在莲玉的误会与鄙视下覃老大的心理负累与愧疚,从而把两种文化的隔膜与差异,甚至是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展现出来。覃老大不爱巴茶,却又必须遵循民族习俗与之度过一生。这个土家男人在龙船寨与小城、巴茶与莲玉之间的纠缠,及在民族道德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永远无法摆脱的心灵磨难让人叹息,小说借对这个普通男人悲剧命运的展示既表现了土家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又把人的一种进退两难、左右不是,因而找不到出路的人生困境烘托到极致。米兰·昆德拉说过:“我奇怪地深信,我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有一种超过它自身的意义,都意味着某种东西,生活通过它每天发生的事在向我们讲述它自己,在逐渐揭示一个秘密,采取一个寓意必须译解的画谜的形式,我们生活中的故事构成了我们生命的神话,在这部神话书中存在着一个揭示真理和神秘的线索。”[1] 139叶梅在《撒忧的龙船河》中对普通生活的处理显然超越了它自身的限制,而具有了揭示意义的价值。因此,她的关于土家民族的小说,不是激发人们猎奇和探险的欲望,而是赋予了一种深沉的文化和人性探索的内涵,这也是叶梅能被称为“当代土家族文化小说的突出代表之一”的主要原因。
在面对文化差异的不能调和与人生悲剧的无法挽回时,《撒忧的龙船河》是忧伤的。当然,小说也表达了一种难得的历史进化中所包含的乐观精神,文化的冲突在时代的冲击与代际的转化中渐趋和缓。覃老大的孙辈们虽然还是延续着一样的人生模式,但是,走出巴楚,走出三峡,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与冲击已是土家民族的大势所趋,土家族与汉族的和谐共处和相互理解,无疑是龙船河上最美丽的旋律。叶梅以一个土家族人的身份,赋予了龙船河多重的意义:既是一个民族过去历史,也是一个民族未来前途的象征;既能真正抚平逝者的伤痛,也给生者带来永远的慰藉。
二
叶梅小说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小说故事性、动作性很强,而且具有能吸引人的言情爱恋情节,这些都使得她的小说具备了丰富的影视元素,也使得她能频繁“触电”。《男人河》是叶梅根据自己的中篇代表作《撒忧的龙船河》改编而成的一部电影,公映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甚至被评为有关长江电影的开山之作。影视是一种视听艺术,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从文学原著到影视影像,是一种从抽象的语言艺术到具体的视听艺术的转换,任何成功的改编,“归根结底是导演的再创造,是导演在对原著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影像赋予作品新的解释”[2] 249。身兼编剧的作家叶梅,将会怎样处理自己小说的改编呢?从总体的观感而言,如果说《撒忧的龙船河》像一首忧伤、多情、神秘的抒情诗,那么,电影《男人河》则充满了力量、担当、责任感的男性气质,它更像一首气势磅礴而意味深长的叙事诗。《撒忧的龙船河》精心捕捉土家族人那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习俗,而《男人河》则从高处、远处俯瞰这个民族的优缺点,因此,小说更多了一种浓郁的民族特性,而电影则更倾向于对民族本性的挖掘与探索。二者各有侧重,虽出于同一作家之手,却有一种互相补充、彼此交相辉映的艺术效果。
电影《男人河》仍旧是在巴山楚水的浓郁地域风情中展开,影像给观众带来的视觉冲击更是强烈,崇山峻岭、九曲十八弯的土家生存环境与土家族各具特色的人情风俗交相呈现,更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电影加入了很多小说没有涉及到的土家族的习俗,原始而神秘的梯玛神歌、毛古斯、跳丧、哭嫁、封舵主仪式;祖传的酿造豆干、织布技术;土家人极具个性的服饰装扮、原始巫术和生存方式都得以表现,勾勒出这个民族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影片也仍然以覃老大与汉族女子莲玉和土家姑娘巴茶之间的爱恋纠葛为主线,言情色彩很浓厚。相对于小说,《男人河》的改编有两大超越于原著的艺术创造。首先,电影放弃了小说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是以覃老大的弟弟覃老二的眼光来审视男人河,弱化了对民族传统习俗的回顾,加强了民族自省的成分,更强调了对土家族的历史命运和民族出路的思索。这着重表现在电影加强了对覃老二形象的塑造,而对小说中覃老大的形象进行了一些新的改写。原著中的覃老二与大哥生死与共,对嫂子巴茶有着欲说还休的情愫。覃老大与莲玉相好后,老二愤愤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为了实现巴茶想拥有子嗣继承家族事业的愿望,覃老二在巴茶对老大绝望而痛苦的情况下与之发生关系,这完全违背了土家族的婚嫁习俗致使覃老二背上沉重的道德负累最终做了梯玛。覃老二在小说中的分量并不重,他独特的巫师身份与土家族的文化习俗的融合,加强了小说的民族特色,但其本身的形象反而是模糊的,对提高小说的主题内涵作用并不大。《男人河》中的覃老二不再面目模糊,相反形象鲜明,电影加重了对这一人物的挖掘,这不仅仅是为了增强小说的民族特色,更是为了增添一种民族自省与探索的成分。而剧中的覃老大,身为男人河上的舵主,更多地象征着一种土家民族的守旧与权威力量。他按照民族习俗,固守男人河的秘密,既以此稳固自己的权利,也借此盘剥其他的族人。覃老大征服的男人河,不仅仅是土家人生命、死亡、力量的隐喻,更是承载着这个民族封闭、保守、自相残杀的愚昧历史。不同于在原著中作家显露出来的民族自豪感,叶梅在电影中对本民族的陋习表现出的是痛心。她既为覃老大这样的土家男人能抗拒平庸、敢爱敢恨而叫好,也为他们在长期的自我封闭中形成的自私自利、狭隘固执的民族性格而感伤。
电影中的覃老二在事业爱情上都输给了哥哥,但他是一个从不服输、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年轻人,经过多次拼搏,发现了男人河的秘密。世代男人河的舵主,为了个人权利和小集团的利益,竟然置整个民族于不顾,导致土家这个本身就很弱小的民族各自为阵,四分五裂,彼此杀伐相争。在家族利益与民族前途之间,在保守秘密与道出秘密的两难之中,覃老二做了梯玛,不同于原著中主要因为爱的受挫而不得不皈依宗教,覃老二此刻的逃遁,带有更强的反省意识,也潜伏着某种反抗。在目睹了男人河的巨大悲剧和整个民族的无谓牺牲后,覃老二意欲粉身碎骨,并以清醒的理智和巨大的勇气向族人公布了秘密。他的勇敢、无私、牺牲精神,不仅使得他最终赢得了巴茶的爱,感化了哥哥,也化解了男人河千年的冤仇。他无疑是男人河上真正的英雄。小说中并没有这一情节,电影经过改编,重新塑造人物形象,显然加强了对土家族自身弱点与命运的反省。他们抗拒平庸却固步自封,顾全大局却也自私自利,敢爱敢恨却又无所适从。男人河上固守了千年的所谓秘密,原来只不过是土家子民束缚自我、禁锢他人,以致阻碍民族走向新生的一个小把戏。令人欣慰的是,最后的男人河,终于成为了土家儿女与自然、自我、民族不断斗争、不断撕裂而最终走向生命健全和民族和解的未来之梦的象征。曾经作茧自缚的土家文化必将砸碎枷锁,卸掉历史包袱,经历凤凰涅槃般的痛楚,终将跨越历史的楚河汉界,最终走向民族新生的道路。
第二个最有特色的改编在于电影《男人河》淡化了小说中所倾重的老一代土家人与汉族人的文化冲突与隔阂,在土家人实现民族和解、团结一致的时候,土家与汉族之间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谅解。电影在表现覃老大与莲玉之间的爱情纠葛时,带有更多的温情主义和浪漫色彩。原著中的莲玉显然并不爱覃老大,他们之间的野合带有很强的偶然因素,恢复理性的莲玉有着一种读过诗书的汉族文化人对粗蛮的土家汉子的蔑视和厌恶,从来就不屑于了解覃老大,甚至在时隔多年之后还把覃老大理解成一个觊觎她美貌的淫棍。对覃老大自身而言,莲玉从来就是一个他不能理解也无法忘却的谜。他们实际上从未互相谅解过,而是始终处于一种隔阂与误会中,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碰撞在覃老大这一代人身上显然并未抚平。但电影《男人河》中的覃老大与莲玉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莲玉对覃老大,虽然不一定有着真的爱情,但却实实在在有着相当的敬佩,对土家人的生存方式和信仰也是理解的。所以,她能平静地接受已经来到她身边却因不习惯城镇生活而回归男人河的覃老大,同时她也一样能接受放弃权利而一无所有的覃老大的最终归来。土家粗蛮的桡夫子与汉族温文尔雅的文化人之间并没有紧张的冲突,原著中那种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激烈的冲撞,在电影中却以一种轻松的大团圆方式结束。小说中没有实现的爱情,在影视中都得以圆满地收尾。这种改编,虽然削弱了小说中所具有的批判与审视的锋芒,但却给影视带来了一种更具人性化的温情与浪漫色彩。
从小说《撒忧的龙船河》到电影《男人河》,从作家到编剧,叶梅实现的不仅是身份的转换,更是一次认识生活、理解生活的审美视角上的重新调整与定位。“审美视角是创作主体对生活属于自己的一种艺术发现,它是创作者主体意识和审美意象的艺术外化。”[3]这体现了作家把握生活,理解生活的方式与趣味。小说《撒忧的龙船河》更多采用了平视的叙述视角,把自我融入到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一次温情的回顾,饱含着叶梅对土家文化的认同与赞美,虽然其间也会夹杂一些非常复杂的情愫。而电影《男人河》则更多地采用了俯视的审美视角,叶梅恢复了她作为土家族知识分子的身份,隔着一定的距离理解自己民族的长处与弱点,既为族人那种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和最终跨越文明鸿沟的进步而喜悦,也为她的民族那种自私狭隘、固步自封、彼此残杀的历史文化而深深叹息,应该说,电影《男人河》更具有文化的含量和反思的深度。不同的艺术形式,都是作家对生活与人生的某种理解。叶梅借助小说和电影,以两种艺术手段,从两种视角对土家民族和她的族人进行了深层的思考和探索。两者相得益彰,共同谱写了一曲令人回味无穷的,属于土家民族的乐章。
[1] 王文初. 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 黄会林. 影视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 张德林. 审美视角与艺术深谈——小说艺术论[J].小说评论,1986(6):57-60.
(责任编辑 田景春)
Two Expressions of One Image: Commenting on Yemei's Novel Happy Dragon Boat River and Her Movie Men's River
FANG Hua-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ogan 432000, China)
Happy Dragon Boat River is a masterpiece of the famous Tu nationality writer Yemei. She adapts the novel into the fi lm Men’s River. Yemei not only changes her status, but also realizes the adjustment of aesthetic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life from the novel to the movies. The paper studies multiple cultural connotations from one signifi er by comparing two versions carefully.
Happy Dragon Boat River; Men's River; art image; cultural connotations
J905
A
1674-9200(2015)01-0058-04
2014 - 06 - 18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湖北新时期文学与影视改编”(13y089)阶段性成果。
方华蓉,湖北工程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