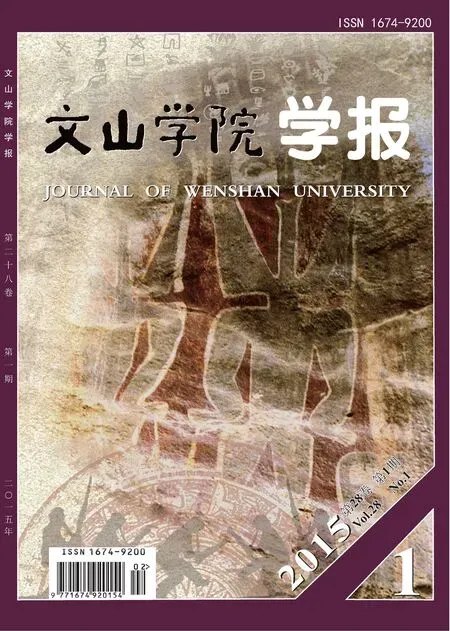儒学在滇中山区传播的文物调查个案分析
——以峨山县山区聚落发现的“字纸库”为例
2015-08-17白玉军
白玉军
儒学在滇中山区传播的文物调查个案分析
——以峨山县山区聚落发现的“字纸库”为例
白玉军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云南省内山区儒学传播与村民教化尚未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这种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文化随着区际移民的到来以不同形式在山区传播。除了传统的建文庙、兴学校、改陋俗外,移民还在山区村落修建“字纸库”“惜字亭”来传播儒学。“字纸库”在山区村落的出现,一方面加速了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文化在山区村落的传播,另一方面巩固了村民崇文重教的文化习俗。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云南山区与坝区的文化差距,进而加速了云南社会与内地的日趋一致。
区际移民;儒学传播;字纸库;峨山山区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自古以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近70%的少数民族分布在山区、半山区。随着明清时期大规模汉族移民的迁入,导致云南人口的迅速增加,汉族移民逐渐渗透至边远山区、半山区,使得云南山区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在定居云南山区的土著化过程中,汉人“逐渐获得地产,结合于土地,交融于当地民族,实现了由流徙到定居,由悬浮于土地到附着于土地,由外来客民到世居云南人的转变”[1] 146。汉人在山区“居其地、有其产、守其职、子孙世袭向土著的云南人转变”[1] 228的过程中,逐渐“反客为主”,在促进了山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文化也随着移民的到来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传播,在山区村落建造字纸库就是汉人传播儒家文化、教育村民重视文化的历史见证,进而使云南少数民族山区村落逐渐接受和采纳儒家文化的精神统治,这也是山区村落在文化教育领域不断“内地化”① ,[2] 183-190的表现之一。
本文以发现于云南峨山县山区村落的字纸库为例,在掌握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利用环境史的田野考察和人类学的社会调查方法,以字纸库为基点,细致研究山区村落的儒学传播和村民教化问题。
元明清时期云南历史进入了新阶段。清初,滇民“风气渐开,归教乡里,秉礼教、守法度”,且“子弟膺贡举成进士者接踵而起,且有好学之士,通经术,擅著作,与海内儒流颉颃”[3]299。峨山县亦如此,且在文山河流域出了个猓倮②举人③。
明清时期,峨山县称“嶍峨”县。“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立云南行中书省,置嶍峨州,隶临安路。至元二十六年降嶍峨州为嶍峨县。明洪武十五年,仍置嶍峨县,隶临安府。清沿明制。”[4]298嶍峨县作为当时的军镇,从明清伊始,就设立嶍峨县学,“在县城北,明天启七年移建,清朝康熙三十四年、雍正十三年屡修。入学额数十二名”[5](第十三卷)560。同时在乡④、村造字纸库,向众儒生和嶍峨民众宣扬儒家的学说及伦理道德。
字纸库又名“惜字亭”“惜字炉”“惜字塔”“字纸亭”“圣迹亭”“敬圣亭”等,是读书人烧毁文字纸张的地方,凡是有文字的废纸,都必须集中于字纸库烧毁,以示对知识的尊重。纸库起初以书院、文昌庙以及文人雅士所居的园林等处较为多见。到了明清时期,惜字、敬字的风俗随着汉人垦殖的脚步逐渐入移山区,一座座亭塔也陆续在山区村落各地出现。⑤,[6]峨山县山区聚落的“字纸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峨山在明清中央王朝统治时期作为军事重镇,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汉族移民源源不断。中央政府统治前期一般都会在府州县“大兴土木,除筑建城垣、衙署外,兴建学宫、明伦堂、教谕署、书院。同时,在各乡、村建造字纸库,向众儒生和民众宣扬儒家的学说及伦理道德。教化百姓尊崇孔圣人,尊崇创造汉字的仓颉。文字是圣贤心血,天地精华,所以要敬惜世间一切书籍和写过字的纸。不能亵渎字纸,不能随意丢弃践踏字纸。不能在经籍书典上乱画,也不能把书作为枕头、垫坐。凡读书人在书桌边都应置放字纸篓,将废字纸丢入篓内。对村路旁的废字纸也要拾起,把废字纸收集起来,统一送到字纸库焚烧。然后,将字纸灰送入河溪或埋至清静的山林”[7]。同时为了教化百姓敬惜字纸,还编印各类劝善书。在长期的广泛教化渲染下,敬惜字纸,尊重文化成了当地妇孺皆知、人人自觉行动的文化民俗。
笔者在峨山县槽子河流域⑥发现了两座字纸库,一座位于青龙村,一座位于双安村⑦。青龙村是峨山县岔河乡安居村委会的一个村民小组,属于山区,海拔近1600米。适宜种植烤烟、水稻、玉米等农作物,有耕地近千亩,农户88户,乡村农业人口304人(男性164人,女性140人),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为主。青龙村建置较早,笔者在其墓地里发现有“明故……”开头字样之碑文。青龙村古彝文名称“大了固”,意为迁到湾子里的村落。后以村后山峦蜿蜒起伏如“青龙”改为今名,山亦叫“青龙山”。该村主要有四姓——矣方李普,四姓分点聚居(聚族而居)构成了村寨的基本规模。村寨内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大庙,但破损已相当严重,且该大庙现已私有,成了村民圈养水牛的地方。大庙是建村以来的中心位置,村民公事亦在此处举办,大庙门前有棵万年青,已有近三百年之光阴。
青龙村的字纸库(见图1)位于村口东北方向,距离村中央⑧约500米。这座字纸库分上中下三层,层之间外标三层弧形砖,空心,顶为宝葫芦,四角,角尖为几何纹形角翘。其中层四周(除西面)均有文字,底座以青砖、石块砌垒,地基厚实稳重,屹立于今而不倒。
双安村的纸库相比于青龙村的纸库要小很多,外形相似,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该纸库没有拱门洞,亦无通烟孔。估计是“破四旧时被人给堵上了”,村民如是说。
另外,笔者和王天福老师于2013年8月23日乘车前往塔甸镇瓦哨宗⑨调查岔河乡大江村消失之谜,车上王老师就告诉我关于瓦哨宗村名的沿革史。今塔甸镇瓦哨宗村,在清朝时就称“瓦哨宗”,建村历史较早。民国时期更名为天峰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改为原名“瓦哨宗”至今。

图1 青龙村的字纸库(摄于2013年8月21日)
刚下车,王天福老师便说这个寨子的村口有个大宝贝——字纸库(见图2)。纸库位于村口,距离村寨约500米。这座塔甸镇绝无仅有保存完好的字纸库分上中下三层,层之间外标三层弧形砖,空心。顶为宝葫芦,四角,角尖为几何纹形角翘。中层两边书写有楹联,楹联内容为:“位镇丁方环绕村民镇秀气,库建南极尊崇字纸寿人文”,橫批“尊经重道”,拱门洞上缀有“寿星阁”字样。拱门洞为烧字纸处,至今尚留烟灰烧痕遗迹,旁侧置有通烟孔。下层四周雕饰动植物,清晰可见。整个纸库以青砖、石块、石灰、黄糖、糯米粉等优质材料砌建,外表以朱红粉饰,质地坚固、造型匀称,庄重玲珑。虽历经多年的风雨剥蚀,加上人为破坏,塔体斑驳,但依然雄风犹在,屹立在绿树掩映的灌木丛中,向人们展示当地人敬惜字纸、尊重文化的民俗。
峨山县字纸库在民国初期修建,主要是用来教化百姓尊崇孔圣人,尊崇创造汉字的仓颉。
岁月推移,时代进步,人们的科学意识逐步增强,至民国后期,统一收集字纸到字纸库焚烧的民俗逐渐淡化,字纸库也大多被拆毁。地处偏僻山区的峨山字纸库,在“文革”时亦被视为“四旧”,宝葫芦、角翘和塔面被砸,因其质地坚固无比,才幸免全毁而较好地保存下来。这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研究云南山区儒家文化、地方民俗的建筑艺术的珍贵遗产,亦是中央王朝对边疆山区少数民族进行传播和普及儒家思想文化的历史见证。

图2 瓦哨宗村口前的字纸库(摄于2013年8月23日)
(本研究得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的专项资助,谨表谢意。同时本文的写作是建立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之上,在实地调查中得到王天福老师的鼎力协助和当地村民的热心招待。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周琼导师的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注释:
① 这里的内地化对象主要是指边疆区域内(如云南省内)受中央集权势力影响较小的、多民族聚居的边缘山区。所以内地化还包含了边疆地区的边缘地带受到带有强烈内地化色彩的腹里地区的影响(中原内地的间接影响)。
② 猓倮,僰人种,是汉人对当地少数民族,带有歧视色彩的称呼,系今日峨山彝族古名。
③ 文献与碑刻均记载:“鲁宗孔,旹道光三十年季冬月中浣吉旦己酉科乡试中式第四十三名举人”。
④ 嶍峨县明代设10个乡,清代为9个乡。
⑤ 笔者在槽子河流域调查字纸库时多见其建筑修建于民国初期;而明清时期字纸库在两广、福建、江西、台湾等客家文化中多见。
⑥ 槽子河流域位于云南峨山县西北部,系山区彝族居住区。“槽子河” 因其形似猪槽而得名,发源于峨山黄草坝山麓的东南面,经甸中镇的西就和岔河乡的文山、安居、河外四个村委会的境内流入化念河至元江,全长20余公里。该河位于两座南北走势山脉之间的狭长地段。西边的凤窝后山属于塔甸山脉,是火成岩而成的山脉。东边的是青龙山,因其山上有个青龙村而得名。青龙山脉属于三叠纪地层。青龙山脚下有条乡道——河西路,全长21.775公里,途径河外,凤窝、文山、宝石、西就等村寨,通至甸中镇。这里的文明大都诞生于此,河流自北向南奔流而下,自古以来养育着以彝族居多的各族儿女。特别是上游修建了西就水库、白云水库、自然坝水库、茂林水库之后,槽子河的灌溉面积增加到近万亩,称她是当地的“母亲河”(当地人亦称“乳娘”) 一点不为过。
⑦ 双安村,现是文山村委会的一个彝族自然村落,属于山区,海拔1380米,有农户19户,有乡村人口56人。始建于明代,彝语名“舍觅”,意为有长田的地方。曾以河道弯曲改为“双弯”村,1932年文山人史庄周取“国泰民安”之意改为“双安”村,村落在文山河西岸,依山面水。
⑧ 村中央的古大庙为显著标志。
⑨ 今峨山县塔甸镇瓦哨宗村,在清朝时就称“瓦哨宗”,明代建村。民国时期更名为“天峰营”,1949年后又改为原名“瓦哨宗”至今。瓦哨宗村有文庙,亦有武庙,两庙间隔不足600米,这是崇文与尚武的有机结合。这种文武并祀的格局,与清代的国家祀典也有内在联系。可以说是对国家祀典的模仿,或者说是国家礼仪在乡村社会中的延伸。
[1] 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2] 周琼.清代云南内地化生态变迁后果初探——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考察[M] //杨伟兵.主编.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3] (清)王崧. 著.杜允中. 注.刘景毛. 点校.李春龙.审定.道光云南志钞[M].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1995.
[4] 玉溪市档案局(馆)编.玉溪碑刻选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5] 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 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6] 李娜.清代、民国年间惜字信仰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7] 冯锡煌,李程.客家人尊重文化的见证物——字纸库[J].源流,2013(9):60.
(责任编辑 杨永福)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Relics for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in Mountains of Yunnan Middle Areas: the "House for Burning Waste Papers with Characters" in Mountainous Villages in E'shan County
BAI Yu-jun
(Institute of Southwestern Environment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 China)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villagers in mountains of Yunnan province have not been widely studied by academic circles. Han culture, dominated by Confucianism, is spread in different forms in mountains with the advent of interregional immigrants. In addition to prospering the traditional schools, abolishing undesirable customs and building the temples, the interregional immigrants also built "House or Pavilion for Burning Waste Papers with Characters" to spread the Confucianism in villages of mountains. The emergence of "The House",on the one hand, accelerates the spread of Han culture in villages of mountains. On the other hand, it strengthens the cultural customs of worshipping culture education. It narrows the cultural gap between the basin areas and mountains in Yunnan provinc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further accelerates development consistence between Yunnan society and inland areas.
interregional immigrants; spread of Confucianism; house for burning waste papers with characters;mountains in E'shan County
B222.05
A
1674-9200(2015)01-0035-04
2014 - 07 - 02
白玉军,云南大学人文学院西南环境史研究所2012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