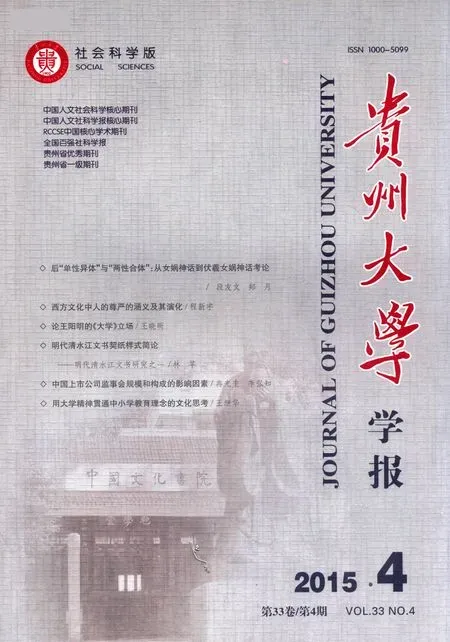论王阳明的《大学》立场
2015-03-21王晓昕
王晓昕
(贵阳学院,贵州贵阳 550000)
从严格意义上讲王阳明很难算是一位地道的经学家,在阳明心学成为显学的中晚明时代,经学甚至处于“积衰时代”[1]①除《五经臆说》(今存《五经臆说十三条》)外,阳明于龙场时期写下的与经学直接相关的著述还有《玩易窝记》《论元年春王正月》《五经臆说序》《何陋轩记》《宾阳堂记》等文。,但是由于阳明本人对经学的关注和深究,使他的经学思想和经典阐释学理论成为他整个心学思想系统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综观王阳明一身之为学为教历程,他的经学思想和经典阐释学理论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从诏狱问易、武夷卜易到龙场玩易再到以经证悟,成《五经臆说》,是阳明经学思想与经典阐释学理论的第一个方面,这个方面的思想,其主要内容是在龙场形成①除《五经臆说》(今存《五经臆说十三条》)外,阳明于龙场时期写下的与经学直接相关的著述还有《玩易窝记》《论元年春王正月》《五经臆说序》《何陋轩记》《宾阳堂记》等文。,或称为阳明早期经学思想;第二个方面,是以阳明晚年所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为代表,集中反映了阳明“经学即道学即心学”的经典阐释学理论,《传习录》中亦有数处论及。或称为阳明晚期经学思想;第三个方面,则纵贯阳明早、中、晚三个时期,是阳明历时最长、用力最多、探研最深的关于《大学》本旨的讨论,此讨论持续达20年之久,发端于龙场,揭示于南赣,直至阳明临终前一年将《大学问》稿授门人钱德洪,方成最后结论。
一、从《大学改本》到《大学章句》
《四书》作为统一的称呼,出现较晚。《唐宋注疏十三经》尚无四书之实,虽有《论》与《孟》,却无《学》与《庸》。《学》《庸》《论》《孟》合为“四书”①“四书”之名确立的具体年份,还有不同说法。,乃为南宋淳熙九年(公元1182)的事情。朱熹首次将《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并为一集,刻梓于婺,经学思想史上之“四书”一名方始出现[2]②邱汉生认为绍熙元年(公元1190)“朱熹在彰州刊刻了《四书》,为之作注,《四书》的名称从此确立”。。虽然早在北宋时,此四种著述就已引起学者重视,更有张载、二程对之大加推崇。作为“新兴经学”的“四书学”,《大学》居《四书》之首,“四书学”上升为经学,甚而越居“六经”之先,朱熹就曾主张以四书为纲,先读四书,后读六经。“四书”中,又以《大学》为纲,《大学》为先[3]。
在四书学史上,二程兄弟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二程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大学》一书的对待上,他们分别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各自作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改本”。
《大学》原为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明道称“《大学》,孔子之遗言”[4]②,伊川谓“《大学》,圣人之完书”[4]311,载于《小戴礼记》的《大学古本》由“汉河间献王后苍所传、郑康成所注”,辑于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这古本由汉至唐历经八百余年,到了北宋,掀起一阵疑古之风。疑古的实质是疑经,而疑经乃宋学之一大特点,欧阳修是提出疑经的第一人③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中说道:“疑经是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继唐人之后,宋儒对儒经也提出了大胆的怀疑,认为有的经典并非出自孔子之手。欧阳修最先著鞭,他的《易同子问》是宋人第一个大胆提出疑经问题的。他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八《易童子问》卷三,四部丛刊本。)”“欧阳修认为这些篇章,‘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是‘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尽管《易·系辞》‘繁衍丛脞’‘非圣人之作’,当是‘汉初谓之易大传’,因为当时‘学经者皆有大传’,所以也不可废去。”(第8-9页)。
《大学》之原貌如何,汉唐所传古本的字里行间,有无错简与脱衍,遂成为有宋以来儒家经典文献学中,聚讼不已的一个著名公案。针对古本《大学》怀疑之风首先由二程兄弟发起,尽管对儒家经典《学》《庸》《论》《孟》的重视,是从中唐的韩愈时代就开始的,这四书逐渐凸显为儒家经典的身份确认,的确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只是到了北宋,才越来越多地被单独拈出,被尊崇,被解释出其中的微言大意。然真正针对古本《大学》的改造,是从二程才开始的。大程子明道云:“《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小程子伊川云:“入德之门,无如《大学》”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卷二十二,《二程集》18页、277页。“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5]是他们程门立雪的学生杨时发自内腑的感叹。他们皆视《大学》为学者为学之门。由于意识到《大学》对于士子的重要性⑤徐洪兴指出:二程认为,《论语》《孟子》的重要性超过了“六经”,而《大学》《中庸》则又比《论语》《孟子》重要。,在深入研究文本的同时,二程遂提出了自己重要的发见,认为《大学古本》存在错简[6]。大程明道对古本《大学》的具体态度是:首先指出《诚意章》有错简,于是将有关段落之文字秩序作了调整,即,移“《康诰》”四条、“汤《盤》”四条、“邦畿”三条次“则近道矣”后,又移“瞻彼”、“於戏”、“听讼”三条次“节彼南山”后。载于《河南程氏经说卷第五》之《明道先生改正大学》,可目之为“大学改本”先例。紧接着兄弟程颐的态度,反映于《伊川先生改正大学》文中,则以“错简”为由,移“《康诰》曰至止于信”至“知之至也”后,移“诗云瞻彼”至“没世不忘也”后,下接“《康诰》曰惟命”至“则失之矣”,次“为天下矣”后;又以“听讼”条次“未之有也”后,“此谓知之至也”之前。此外伊川特别强调“此谓知本”四字为脱衍。
上述以错简为由所作的改正,尚属文本考据范畴,其动作也不算大。值得注意的是,伊川欲借文字注疏而开出义理之阐发,于《大学》首章“在亲民”之“亲”字下注有“当作新”三字之校勘记,实为非同小觑之举动。把“亲”释作“新”,虽未把“亲”直接迳改为“新”,却为朱熹以后迳改“亲”为“新”提供了直接依据⑥从诠释学意义上讲,加注与迳改尚不能等同。有学者查之未深,妄以为最先将“亲民”改为“新民”的,是为小程。。在二程改本的基础之上,朱熹对原《大学》之古本动手术,作出了更大更系统的动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朱熹把《大学》全文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三纲领”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部分被他称之为“经”;另一部分是余下所有文字,是对三纲领八条目的解说和论证,这一部分北他称之为“传”。“经”一章、“传”十章,朱熹将《大学》共计章分十一,称为《大学章句》。其中,《大学章句》首章对“大学之道”的诠解,又可分为四个段落:
一是关于“明明德”的诠释: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大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二是对“新民”的诠释,尤其值得注意:
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第三段解“止于至善”: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
最后一段对“三纲领”的总结:
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关于“八条目”,朱的解释是:
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谦而无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②同①。
从“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被朱熹确定为“经”,即“经一章”,以下文字皆为“传”,“其传十章”。在朱熹看来:“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
经过朱熹的这一整理,《大学》更显出有纲领有条目和有规模有节次的特点。纲举而目张,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规模是个大间架,好像一座大房子,节次就像里面的许多房间。进入房子必须有门,依次而入,不能超越。
第二个方面,朱熹认为《大学古本》不仅有错简,而且有阙文。他在研究所谓“传”的时候,发现它们基本上是按照一定次序逐条解释三纲领八条目的。但在分配《大学古本》原文时,包括经一章在内,无论怎么分配,都只能分为十一章,不多也不少。经一章从“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止,对“三纲领”“八条目”依次逐一作出解释,“三纲”加“八条”共十一目,就应有“传”十一,现在只有“传”十,少了传一章,的确是个问题。而已有的十传中,比对下来,唯独缺少对“致知在格物”的解释,朱熹他发现了这一明显的阙文,云“右传之五章,盖识格物致知之意,而今亡矣”,遂补作了“致知在格物”一章。其云: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7]
朱熹又发现,古本对“正心在诚其意”的解释也没有按照八条目应有的次序,而是出现在所谓“传”开头的地方,这就又是一处错简。“于是,朱子继承北宋儒学对《大学》本文面貌的怀疑传统,认为,解释诚意的传文没有出现在八条目中应在的位置上,这是因为‘错简’造成的;而全文中没有出现对‘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的解释则是由‘阙文’造成的。”[8]既然如此,要纠正《大学》古本错简与阙文之误,朱子以为,需有两项重要工作去做,即“移其文”、“补其传”。所谓“移其文”,朱与二程一致,通过“移文”以补古本“错简”之误,又通过“创新”而“补其传”,以弥古本“阙文”之失。《大学》古本于是由“二程改本”到“朱子章句本”,诚如后世者云:“朱子因之,更考经文,别为序次,以作章句,是为今本。”③郑珍《古本大学说序》。朱子《大学章句》乃行之于世。
在朱子目下,致使《大学》古本存暇于玉的另一原因,是所谓“经”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如此一来,朱子很“智慧”地在“经”和“传”之间划分出优劣等差,进而强化了“经”对“传”的优先性和决定性。
接下来的一个动作,则更具有颠覆的意义,朱子将《大学》“三纲领”中“在亲民”一条直接迳改为“在新民”。且辩云:“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7]3
作出这样的迳改,在朱子看来,自有经典为据。《大学》古本原有汤之《盘铭》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句、《尚书·周书·康诰》中有“作新民”、《诗·大雅·文王》中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句,朱熹称“传二章”,其中反复出现的“新”,就是迳改“亲民”为“新民”的充足理由。对于朱子的这些理由,王阳明于《传习录》首篇对此作出了回答,后文将详言。至于朱子的改动,原来古本中具有“养民”、“惠民”之民本主义浓厚色彩的“亲民”,一下子变成了“敦化”、“教化”、“革新”、“革命”等具有浓厚强权色彩的“新民”政治。过去一般只是认为朱子改“亲民”为“新民”,仅具有诠释学意义,与政治立场无关,如今看来,需要重新认识。
之后,朱子《大学章句》因具有普遍的权威性而成为最流行本子,元代更奉其为科举功令。清代学者郑珍对此作了描述:“世之童子启口即读之,于是汉传古本变而为朱子之《大学》”①郑珍《古本〈大学说〉序》。朱子提出一个严格的治学次第:先《四书》,后《五经》《四书》中又以《大学》为首。特别强调:“今且须熟读《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②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是一个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实著。”③同②。虽然如此,南宋之后的读书人从未停止过对《大学》衍本的文献学讨论,“而六七百年学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争新角异,而《大学》日多矣”④同①。,很多学者加入讨论,有的将朱子学说加以发挥而推行致用,也有的与二程意见相近者,或与朱子意见相左。一时间《大学》异本多见,遂成为一道风景。
属于第一种情形的有朱子的学生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濬的《大学衍义补》。此二书被称之为《大学》中的“帝王之学”,以为帝王要学《大学章句》,同时也是官员和士子所必读教材,以使君主与百官对于《大学》经典的研习,不只是停留在空洞的理论上,而是要能真正付诸实行。真德秀所著《大学衍义》于《大学》“八条目”只讲了前六项,于后两项“治国”与“平天下”却略而不论,认为只须作到内圣,外王之道自在其中。正因为如此,邱濬乃作《大学衍义补》,将德秀所略“治国”、“平天下”两条详加阐明,以示其全。
属于第三种情形者不在少数。长于文献考索的清代学者郑珍认为,南宋以后,明中以前,与朱子意见相左,“其最著者董文靖⑤董文靖:查无“董文靖”者,疑为“文清”之误。本也”,该本退“知止”、“近道二条合“听讼”二条为“格致传”。董还以“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一段为“致知在格物”的解释,主张勿须补传;郑济主张把经文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得”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一段合起来,作为致知格物的解释,故亦认为勿须补传;刘渍则主张把原传文第二章“诗云瞻彼淇澳”一节与“子曰听讼吾犹人”一段加在一起,作为格物致知之传,自然也认为勿须补传;还有以“诗云瞻彼淇澳”一段独立作格致之传,移于诚意章之前的。还有些改本基本上与二程接近,此勿赘言。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这样那样的改本,林林总总,正如郑珍先生所读一过的,有“宋叶丞相、王鲁斋,明车清臣、方正学、宋濂溪、蔡虚斋、王守溪、徐师曾、刘念台诸公”,真是热闹得很。郑氏也曾认为,上面提到的郑济本,“至篆书刻本行之,几几与朱子《章句》相伯仲”,确有代表性。其余改本在郑氏眼中,就未必有什么好感了,“以外崔后渠、高忠宪、李见罗、季彭山、郁文初诸改本,咸自惊独见,哄然一时,馀纷纷益不可胜记”。更有甚者,“至王顺渠古本,删而改《大学》之祸极。至丰考功伪石经出,而转成笑柄矣”。不管是以错简为因,抑或以阙文为由,抑或主阙错兼具,均主张对《大学》之古本加以改造⑥同①。。
二、王阳明的《大学》立场
在分析王阳明的《大学》立场之前,邻水甘秩斋家斌《大学说》值得一提,“其书(指古本)不别经传,分为十章。移‘瞻彼’、‘於戏’二条於‘此谓之至也’后;移‘所谓诚其意’至‘必诚其意’於‘此谓知本’后;‘所谓修身’以下章次并同朱子。”可见又一新异本。客观地说,甘氏之书“详其说,直切明易,无穿凿纠缠之私。而文颇繁冗,节裁十之五六,付其族侄两施大令刊本,成一家之言。顾念汉传古本旧矣,如先生之说,使仍就古本故次,则既不蹈董文靖后诸儒欲复古而反乱古之讥,而于文成、文贞之书,大义复不相乖忤,不尤善欤!焉得起先生而质之”,此应为有褒有贬之评判,平实客观之态度,至于谈到与阳明、李贽之书“大义不相乖忤”,也应视为基本公允之首肯。倒底阳明古本立场之“大义”究何,容后所叙。
在《章句》本成为权威和各式各样改本“哄然一时”的背景下,王阳明一反潮流,标示了其独有的《大学》立场:一是独以《古本》为正,其文本自平正、无不可通;二是坚持以为《古本》无错简,无阙文,亦无脱衍;三是对《大学》的基本文义(如“亲民”、“致知”等)作出了返本归源的全新阐释。钱德洪所撰《年谱》清楚标示了阳明主张的《大学》古本与朱子《章句》的主要不同:“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①《年谱一》,《全集》第1254页。不过,基于这一基本立场,阳明关于《大学》本旨的经学思想及经典诠释学理论的完成,却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被人怀疑到最终信服的过程。《传习录》有门人徐爱②徐爱: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杭人,王守仁的妹夫,也是王的第一位和最得意的门生,有“王门颜回”之称,曾任工部郎中,下文的“爱”即徐爱的自称。序曰: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所闻,私示同志i,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正德八年之前对守仁恢复古本立场持怀疑态度的,也不仅仅徐爱一人,爱初所表现之“始闻而骇,既而疑”的状态,也是阳明返古疑朱之论甫一披露时,学界所作之正常反映。时与阳明交往密切的,还有两位学者,一是湛若水,一位方献夫。湛、方二位最初接触阳明《大学古本》观点时,据资料分析,他们未能理解更未支持阳明立场。正德六年到七年③水野实认为是正德五年到六年,恐有小误。根据《年谱》,阳明是正德五年春离开贵州,任庐陵知县,十月离开,到北京已是年底。,阳明北京遇甘泉,极有可能在此期间向甘泉流露了自己的古本观点。但此期间,阳明多半只是口头表达己见,未见将之付诸文字。直到正德十三年七月,他发表了《古本大学旁释》,才首次将自己对《大学》的态度立场披露于世。
湛若水、方献夫与徐爱一样,都经历了一个由对阳明大学古本立场之怀疑到取信、到最终支持的过程。这从湛、方二人后来发表的文字可以看出。若水有《古本大学测》发表,献夫则有《大学原》述及。据水野实的考察,确定《古本大学测》的成书时间应在正德十三年八月(《经义考》卷159),较阳明《古本大学旁释》发表仅晚一个月。可知,甘泉的这一动作,可被看作是对阳明再次表明古本态度的一个回应。如果说阳明在北京时表明态度效果不甚明显,后在江西再次向甘泉阐明自己观点后,阳明表现出其固有的耐心。又过了一段时间,与徐曰仁一样,甘泉的态度开始起了变化。正德十年,甘泉在奔母丧返回故乡(广东增城)途中路经龙江(江西),与南赣汀彰巡抚任上的王阳明相与论学,《大学》宗旨必然又成了其中重要话题。阳明于四年后给若水的一封书简中云及:“向在龙江舟次,亦尝进其《大学》旧本及格物诸说。兄时未以为然,而仆亦遂置不复强聒者,知兄之不久自当释然于此也。乃今果获所愿,喜跃何可言。”④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四《答甘泉》。显然,根据上述可见,甘泉当初对阳明的“格物”和《古本》态度表现为“不以为然”。但是后来,甘泉的确于其《古本大学测序》中有道“甘泉子读书西樵山。于十三经,得《大学》古本焉”这一取信《大学》古本立场的心得。正德十二年十月七日,服丧之后的甘泉前往西樵,随后在给阳明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个日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考虑《大学》古本的正当性问题,不过他使用了与阳明不尽相同的理解方法。时隔不久,他终于确信了《大学》古本的正当性,并发表了他的《古本大学测》。他于《大科训规》中谈到:“《大学》古本好处,全在以修身释格物致知,使人知所谓格物者,至其理,必身至之,而非闻见想象之粗而已。”①《甘泉文集》卷六。他还于《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中有“于古本下节,以修身说格致,为无取”、“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为于学者极有力”、“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致之旨”等等表白;其于《圣学格物通序》中又云:“大学古本以修身释格致,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几乎就在同时,方献夫发表了《大学原》,至此,湛、方二人的态度已然明朗,开始支持阳明对《大学》古本立场的表彰。不过由于资料的散佚,方献夫的《大学原》及其具体言谈今已无从引征。
三、王阳明《大学》立场的发端
《传习录上》记录了徐曰仁的一段问话,这段问话虽然发生于正德七年十二月,记录的也是“与先生同舟归越,论《大学》宗旨”②《年谱》,《王阳明全集》第1235页。一事,但却反馈了三年多前的一个尤为重要的信息:阳明《大学》古本立场的发端在龙场。曰仁云:
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
“居夷三载”,也就是阳明贬谪龙场的那个时段,他在“处困养静”、“默坐澄心”后中夜大悟,他在参透本体的同时,功夫也实现了质的飞跃,“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这里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是“悟道”之后紧接着的“证道”,务必不能忽略,阳明将其中夜所“悟”“证”诸五经,其结果是,“所悟”与“所证”莫不吻合。《礼记》乃五经之一,古本《大学》为小戴《礼记》之一章,阳明不仅证诸五经,同时证诸“四子”。他得出了两种相反的结论:一方面是证诸五经莫不吻合,另一方面却于朱子之说(四子)每相抵牾。这当中显然包含了他将《大学》古本与《大学章句》两相证悟所得出的结论,而由此产生对朱子章句本的怀疑。后来钱德洪于《年谱》中证实了此事。不过当时的情况是让人能够理解的,那就是迫于当时客观情形,阳明就算有此怀疑,也断然不愿将它立即说出。其因有二,一是朱子权威在当时尚不易摇动,二是阳明自己怀疑主义思想的成熟度亦尚有待时日。如何将瞬间的直觉体悟牢牢抓住,经由悟道到证道再到体道,由更多感性成分的直觉,经由悟性上升到理性,显然需要功夫的正确运用与渐次深入,只有达到本体与功夫的高度一致性,认识与实践方能进入理想的澄明之境。然于当时,功夫不到火候,认识有待提升,阳明就连良知一语都未能说得出口。龙场,不仅是阳明《大学》古本立场的发端处,也是阳明整个良知学说的发端处。钱德洪《年谱》有关于此渊源的记载:
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③《年谱一》,《全集》1254页。
记录阳明古本立场发端于龙场的最为直接的证据,更见于阳明自著之《朱子晚年定论》,其云:
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径,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闲尝以语同志,而闻者竞相非议,目以为立异好奇。虽每痛反深抑,务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窃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为察?
阳明获龙场之悟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用儒家经典来证明己之所悟。为了证据的周全,他不仅证诸《五经》,也证诸《四子》(四书),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证诸《五经》,乃“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可证诸《四子》,却“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窃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为察”?
《年谱》中还记载了正德四年,阳明与席书的一段故事: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是年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
当时阳明以贬丞之身居龙场,尚不愿直语朱陆同异,只告席书己之所悟,其情可谅。
正德五年底阳明到了京师,在大兴隆寺与黄绾、储柴墟相识,与湛若水相以共学,于朱陆话题亦少有渋及。《年谱》云及口头上讨论晦庵、象山之学,是在正德六年辛未,阳明官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以后的事。一次回答学生提问,算是阳明口头上对朱陆之辨的首次态度。学生王舆庵读象山书有契,徐成之与辩不决。阳明答曰:
是朱非陆,天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
虽微成之之争,舆庵亦岂能遽行其说乎?[10]
这一次的回答主要渋及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辩,未渋《大学》,且徐成之仍然觉得先生的回答是“漫为含糊两解”。后也曾常常与湛若水、方献夫等于职事之暇,相与讲聚,各自砥切,时时感叹于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誇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辞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10]1234是年十二月,阳明与妹婿徐爱同舟归越,途中讨论了《大学》宗旨,爱“因旧说汨没,始闻先生之教,实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通过此番讨论,徐爱由初时的怀疑,转而为信服阳明,并以为“舍是皆旁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徐爱将当时的心情表述为“踴躍痛快”、“如狂如醒”,并且总结道:“如说格物是诚意功夫,明善是诚身功夫,穷理是尽性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约礼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诸如此类,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10]1235所谓格物是诚意功夫,亦即云道问学乃尊德性功夫,若强调尊德性与诚意为要,当然将道问学与格物置之次位了。在这一次的朱陆之辨中,阳明已明确将象山之学持之为己所张扬之立场,为几年之后公开其《大学》古本立场著了必备的铺垫。
四、王阳明《大学》立场的披露
正德八年十月,阳明于滁州督马政,学生(孟源)问“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咋办?阳明答云,头脑中如果杂虑纷扰,想要强迫禁绝是不行的;你只能就思虑萌动处去省察克治,直到天理精纯明白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这其实就是“《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10]1236阳明主张内向用功,所谓在“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显然与朱子外向功夫的“格物”而后致知、“道问学”而后“尊德性”的进路绝然不同。
离开滁州后,阳明到任南京鸿庐寺卿。于此仓居间,他将大量朱子著述阅过,以便进一步巩固已有的立场。忌于当下朱学主流形态的强势地位,阳明采取了曲折而迂回的表达方式,即将朱学判分为“中年未定之说”与“晚年既定之说”,且强化其间的自我反省。表面看来,阳明对朱子似乎有所肯定,云“予既自幸其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11],其实阳明的目的,却是要去否定朱学。他后来在南赣写下《朱子晚年定论序》,其回顾云:
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书而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11]328
正德十三年戊寅,阳明抚南赣,七月,刻《大学》古本,这时他已知,该是将自己对《大学》的立场公之于世之时了。自正德三年龙场大悟后,萌生对《大学章句》的怀疑,至七年与爱同舟讨论《大学》宗旨、八年在滁主“诚意”与“尊德性”,积蓄了多年对《章句》的不满,时机终于成熟,到了不得不发的时候。从阳明思想认知的萌生到以书面形式的表达,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他所耗费的苦心”①水野实认为:正德十一年《与陆元静》(《王文成公全书》卷四)有“所问《大学》《中庸》注,向尝略具草稿,自以所养未纯,未免务外欲速之病,寻已焚毁”,可见其著述时的苦心。。此时的王将军真可谓一面忙于指挥战斗,“出入贼垒,未暇宁居”,一面讲学论道,学生环聚于身边,每日“皆讲聚不散,至是回军休士,始得专意于朋友”,正于此时,他凝神于“日与发明《大学》本旨,指示入道之方”①。钱德洪《年谱》乃回顾云:
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至是刻录成书,傍为之释,而引以叙。[10]1254
上述,阳明在标明自己《大学》古本立场的同时,亦从如下方面对朱子《章句》提出了批评:
首先,朱子《章句》疑非圣门本旨。此疑早自阳明居黔时便已产生:“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六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之海也。……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11]28-29由此可见,阳明对朱子《章句》的怀疑由来已久,其审读亦并非意气用事。
其此,阳明主张《大学》古本“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朱子将《大学》判为“经一章”、“传十章”的作法纯属多余。主张从本意上解读古本,这在阳明看来十分重要,正德十三年七月,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古本的随意裁析,无疑使圣人的本意丢失,“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这对朱子章句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颠覆性质的判断。
再次,阳明主张“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认为朱子“因缺失而作补传”之作法实无必要。朱子于“此谓知本”至“此谓知之至也”间加了128字,称为“传之五章,释格物致知之义”,与《大学》本意已有不同。阳明认为“《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辑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①王守仁《答罗整庵少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第66页。。阳明以为,“诚意”的释文本就居于其余释文之前,“诚意”本范导“格物”与“致知”,故其于《大学古本傍释》中格外强调“惟以诚意为主,而用格物之功”。这就为“诚意功夫”②在阳明看来,格物才是诚意的功夫,“以诚意为主”,则诚意就有了本体意味。的突显寻到了经典依据。将“诗云瞻彼其澳……民之不能忘也”当作“言格物之事”,使甩掉朱子补传成为事所必然。“格致本于诚意”本可作如此理解,“诚意”不仅范导着“格致”,且对格致而言,诚意乃格致之本体;相对诚意而言,格致乃诚意之功夫。在这样一种具有辩证意蕴的解释框架下,朱子对格致的辑补就尤其显得多余和失掉意义。
正如阳明所以为,“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诚意中已内在地涵有了敬的深刻意义。曾经因为,弟子中出现只在枝叶上作功夫,而忘却根本培养以畅达生意而导致支离决裂之倾向,为“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阳明与时谐行,不失时机推出其“诚致”之意蕴功夫。阳明的功夫论与朱熹的功夫说有本质的区别。朱子曾有一整套格物功夫之罗列,归纳为四:“察之于念虑之微”、“求之于文字之中”、“察之于事为之著”、“验之于讲论之际”。在阳明看来,朱子格致功夫四条,皆求之于身心以外,四者可等量齐观,无轻重彼此之分,显然是“缺少头脑”。在阳明看来,显然应将第一条“察之于念虑之微”,作为学之主脑,并贯穿于其余三者,“念虑之微”乃知,“察之于”乃行,此正吻合于阳明“知行合一”以“致良知”的心学宗旨。这个时候,阳明“致良知”之教虽尚未正式招揭于世,其以“诚意”为《大学》古本正当性彰扬的有力推手,以“立志”、“立诚”(诚意、诚身)为学问功夫之主脑,坚定地指示“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如此一来,朱子以阙文为由,而补“格物致知”之传的作法,不啻成了画蛇添足之举。
五、王阳明《大学》立场的核心意蕴
述及小程《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一文,于“在亲民”之“亲”字下注有“当作新”,并未将“亲”迳直改为“新”。小程亦指《大学》古本存有错简,但并非以为有阙文。不过其“当作新”之注,的确为朱熹迳改“亲民”为“新民”提供了充足之理据。朱子取小程“亲”作“新”之意,作出了将之训释为自新、革新等单方面要求庻民去恶从善、弃旧图新的发挥,阳明显然是不赞同这种对《大学》古本的曲解的。
《传习录》开篇即记载了阳明与徐爱师徒二人讨论《大学》首章关于“亲民”与“新民”之别。虽说这一次的表态至多只算是小范围的私下交谈。徐曰仁《传习录上》的公开发表时间,是在他去世后的正德十三年,由陆澄与薛侃在征得先生许可后公开刊出,七月,阳明乃刻《大学》之古本,作《古本大学傍释》,又作《朱子晚年定论》随其后,紧接着八月,薛侃刻《传习录》。钱德洪《年谱》云:“侃得徐爱所遗①《年谱》:是年(正德十三年,即公元1518)爱卒,先生哭之恸,爱及门独先,闻道亦早。尝游南岳,梦一瞿昙抚其背曰:“尔与颜子同德,亦与颜子同寿。”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归,与陆澄谋耕霅上之田以俟师。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语辄伤之。《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②虔:州名。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置,以虔化水得名。治所在赣县(今赣州市)。唐辖境相当今江西赣县以南德赣江流域。南宋绍兴22年(公元1152年)改名赣州。时阳明提左佥都御史,巡按南、赣、汀、彰。终于,阳明徐爱师徒二人六年前于归省途中运河船上的那段关于《大学》宗旨的精彩对话,有了公开发表之机而告白天下。
爱请教于先生:
“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亦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回答直截了当,有理有据: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11]28-29
如何为“亲民”而非“新民”,阳明引经据典,以经证悟,或以经证误,是阳明龙场时延续下来的一贯学风。上文主旨突出且话语集中,可作如下几点训解:
其一,“作新民”之“新”,乃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不可互为诠释理据。朱子《章句》第三章(朱称“传之二章”)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尚书·康诰》“作新民”之词意,确有激励民众焕发新貌之意,但与《大学》首章之“三纲领”中“在新民”则俨然不是相同含义,以“作新民”来证诸“在新民”,在阳明看来,犯了逻辑上偷换概念之嫌而不足为凭,故“此岂足为据”?
其二,既然古本之“作新民”不得用以支撑“在新民”“新”字之改之正当性,“作”字虽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③“然非‘新’字义”:《王文成公全书》本,误作“然非‘亲’字义”。邓艾民先生《传习录注疏》认为《王文成公全书》本,新讹作亲,应据闾东本改,陈来先生于邓书序指出,“这个改正显然是正确的”。然《王阳明全集》整理者未审,故以讹传之。,那么,将“新民”还原为“亲民”,则是理所当然。因在阳明看来,“新民”与“亲民”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新民”只是单纯的教化、革新之义,而“亲民”则直接谓之以养民与惠民。朱王二者的治理立场可见一斑。阳明以经举证,列《大学》中原文论之,列“烈文”章“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又列“齐家·治国”章“如保赤子”,又列“治国·平天下”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以为己所彰显“亲民”正当性之理据,实实在在地证诸了“皆是‘亲’字意”。如说“新民”与“亲民”所呈现的皆为儒家外王之道,那么,阳明显然坚定于《大学》古本中所持有的孔孟早期儒家立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更何况,“亲民”比之“新民”,含义更为宽广,“亲民”中本已涵盖了教化之义,“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故朱子“新民”一说陷于褊狭矣。
其三,三纲领之首条“明明德”,亦即“明明德于天下”之谓,天下乃民之天下,“明明德”亦即是“亲天下之民”。“明明德”与“亲民”,二者相辅相成,本体上一脉可通,“明明德”自有“亲民”之义含于其中,失“亲民”之义亦无所谓“明明德”,非“明明德”亦无所谓“亲民”之达成。阳明举证《尧典》,云“克明俊德”即是“明明德”,云“以亲九族”以至于“平章”、“协和”,亦即是“亲民”,亦即是“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以亲天下之民,此无疑皆为早期儒家的思想与愿境,实乃圣人之意。孔子云“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之“己”,乃圣之所指大人,“修己”即是“明明德”“安百姓”即是“亲民”,己若不修,何以“安百姓”,又何以“亲民”?此非朱子“新民”之论所可比类?
最后,阳明云及“作”与“亲”,言及二者虽相对应,但“作”并非“亲”之义,文下“‘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接下来所论之“治国”、“平天下”等处,可以说都对“新”字没有涉及。
六、王阳明《大学》立场的最后总结
在经过龙场证悟、京师辩难、运河问答,以及滁州、留都、南赣之长期探索后,阳明晚年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家乡浙江,是到了对自己多年思考作出最后总结的时候了。也就是在阳明临终前一年,即将出发广西时,正式将其代表之作《大学问》发表,交与钱德洪刊录。德洪作《大学问序》云:
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德洪受而录之。①《大学问》,《全集》第967页。
阳明《大学问》设有六问:一问何以“在明明德”乎?二问何以“在亲民”乎?三问乌在其为“止至善”乎?四问“知”、“定”、“静”、“安”、“虑”、“得”,其说何也?五问物之本末,若“以新民为亲民,则本末之说亦有所未然欤?”六问“欲修其身,以至于致知在格物,其功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欤?”六问皆仅就《大学》所谓首章而设,亦可见其纲举目张,直击要害之手法。六问的核心问题,依然在于“亲民”与“新民”之立场差别。在第一问中,既然认为《大学》乃大人之学,“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阳明首先将“大人”定义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实际上就是阳明一直一来所强调和所追求的圣人、君子、求“第一等事”者,此者固能视天下犹一家,视中国犹一人。反之,“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因其心之本于仁,故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此一体之仁本然而已,此一体之仁即为大人。阳明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学之所以为大人之学,是因为大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能去其私欲之弊,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之仁心。大人之心,即是仁心;大人之学,即是心学。昔儒的大人之学属理学,于本体之外而存在;阳明的大人之学即是心学,“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在以“内”“外”对大人小人作出区分后,阳明在他的第二问中,又以“体”“用”作出对“明明德”与“亲民”的分别。明明德是体,是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用,是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按阳明一贯的主张,体用为一,不容二分,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阳明的“亲民”与程朱的“新民”的确属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阳明谓:“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只有这样,才能将明明德之体用之于天下,才能实现儒者的家齐国治天下平,是之谓尽性。如果将“亲民”更改为“新民”,“新民”必不能做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与天下父子兄弟为一家,明明德自然就成了空话。这就使体与用截然为二了。
明德为体,亲民为用,至善乃是“明德亲民之极则”。明德是粹然至善的天命之性,是灵昭不昧的本体,实际上,明德就是良知。王阳明在平辰濠之乱后提出了“致良知”,是他理论臻于成熟的标志。也就是这时候,他在对《大学》的诠释中引入了他的最新成果而使之有了全新的意义。他更加强调至善之良知的本然特性,反对议拟增损其间。他融入了《中庸》慎独思想,指至善良知乃“慎独之至”、“惟精惟一者”,存在于吾心,乃为心之本体,“后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测度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则,支离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②同①,第967-976页。此“后人”当是有所指向,因为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以私智向外揣摸测度,于是主张事事物物各有定理。阳明的这个批评是与他当年提出的“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核心主张相一致的。“盖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也,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鹜其私心于过高,是以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则二氏之流是矣。”③同②。在阳明看来,不能止于至善,即不能体现明明德,亦不能贯彻亲民:“故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这里实际上是以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来比喻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的关系,手段是末,目的是本,近似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其余三因与目的因之关系:“明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④同②。
第四问,问何为“知、定、静、安、虑、得”?在阳明看来,知求至善于吾心,方为之“定”,宋儒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不知“有一定之向”;无一定之向,则心必妄动而不能静。只有心不妄动才能静;能静,则从容闲暇而能安;能安,吾心之良知自有详审精察,而能虑;能虑,则择之无不精,处之无不当,至善于是乎就可以得到了。故在阳明看来,要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一切皆取决于吾心,根据就在于良知。至善当然也不能离开明明德。
如果说至善与明德亲民之间尚有本末之关联,而决不可将这本末关系套用于“明明德”与“亲民”之间,否则就是将本来为一物的东西肢解为二了。“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王阳明以《大学》首章所内设的此一话题发出了他的第五个问,进一步驳朱子改“亲民”为“新民”。“如子之说,以‘新民’为‘亲民’,则本末之说,亦有所未然欤?”阳明指出,本末是一物之本末,不可视之为两物;终始也是一事之终始,又怎能视之为两事?明德亲民本为一物,原为一事,谓其为一物一事之本末,是可以的。但若将“亲民”改为“新民”,是不知道明德与亲民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虽然知道本与末应为一物之本与末,却在行动上不得不将本与末分为两物了,从而导致知与行的分裂。
在第六问中,阳明强调《大学》古本的原则“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务必“先修其身”的训导,与自己的明德亲民之说显然可通。既然如此,《大学》中“修身”以外的其它条目又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功夫次第关系又如何理解?这里,王阳明基于心学的立场对此作了解答:
此正详言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功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功夫,虽亦各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①《大学问》,《全集》第967-976页。
在阳明看来,所有的功夫都是指向一件事,即明德、亲民、止至善,不分高下、不分次第。就连“身”与“心”之间也只是一件而不容二分:“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心与身只是体与用之关系,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当然心外无身。“修身”自己是不能为善去恶的,必须依赖于心的主宰:“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阳明将上述道理引导到了他心学的基本立场上,也正是此时,阳明提出了他带有总结性质的“王门四句教法”: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阳明认为,他所坚持的《大学》古本立场,才是真正儒家道统的立场:“此格、致、诚、正之说,所以阐尧舜之正传,而为孔氏之心印也。”②同①。
阳明于《大学问》中不再拘泥于词章训诂、错简脱衍之类的讨论,而是直指核心要害;也不须就《大学》全文进行疏理,而是仅就所谓首章,举纲张目,直戳“命门”。
阳明《大学问》中阐发的古本立场比之此前有了更为丰富和纵深的发展,体现在如下三点:其一,阳明将天地万物、本末、体用、本体功夫、动静、慎独、惟精惟一等大量具有思辩功能的范畴引入对自己古本立场的阐发,使得这一阐发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而达致综合而上升至形上之域。其二,他将自己多年总结出来的自己心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心即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范畴引入对自己古本立场的论证,使得这一论证在基于自己心学立场的前提下,大大丰富和提升了他的心学体系的内涵和深度。其三,正是由于上述两点,阳明对朱子改“亲民”为“新民”的批评则更加有力。
阳明之后的中晚明时期,朱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虽未曾撼动,但心学的诞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场石破惊天的大事[12]并取得了与之分庭抗礼的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
[1]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35.
[2]束景南.朱子大传[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1992:385,766.
[3]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7.
[4](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04,311.
[5](宋)杨时.杨时集(卷二十六)[M].林海权,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613.
[6]尹继佐,周山.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五)[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0.
[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8,3.
[8]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0-111.
[9]水野实.明代古本大学表彰的基础[J].中国哲学史,2010(4).
[10](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67,1234 -1236,1253 -1254.
[11]王晓昕.阳明先生集要[M].北京:中华书局 2008:28-29,328.
[12]龙冈书屋.阳明心学与贵州[J].教育文化论坛,2010(1):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