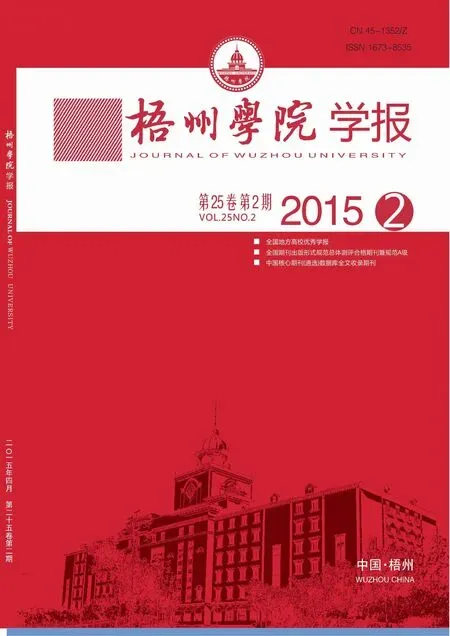试论韩少功小说创作中的悲剧意识
2015-03-21
试论韩少功小说创作中的悲剧意识
杨凯(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韩少功在其一生的文学创作历程中,作品贯穿了文革、新时期和90年代以及新世纪每一个时期,而他的作品无不充满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识,从早期的政治悲剧到后来的文化悲剧,以及新世纪人性悲剧的种种历史演变,韩少功无不在思考这种种悲剧产生的原因,该文以韩少功的3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来分析这一悲剧产生的原因和悲剧发展的过程,以期全面理解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中隐藏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韩少功;小说创作;悲剧意识;人性悲剧
一、《月兰》:特殊时代的特殊政治悲剧
张法说:“悲剧意识是悲剧性现实的反映,也是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它由相辅相成的两极所组成:悲剧意识把人类文化的困境暴露出来。这种文化困境的暴露,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同时,悲剧意识把人类文化的困境从形式上和情感上弥合起来,这种弥合也意味着对挑战的应战。”[1]在当代作家韩少功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悲剧意识从一开始就是很鲜明的,正因为韩少功的这种悲剧意识在最初小说中的显现,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壮感。
1979年《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月兰》一经刊出,便引起强烈热议和积极反响。《月兰》描写的是在特殊时代特殊背景发生的具有普遍性的悲剧性事件。月兰善良、质朴、贤惠,可她最后死了。“哦哦,月兰,我来迟了!你现在无可挽回地永远睡着了,而我刚刚醒过来……可这是怎么回事呵?到底是谁吃掉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呵?月兰!”作者悲怨而深沉的痛苦呐喊,显然带有那个时期的时代印记,这在韩少功的早期创作中也是一种自觉的创作过程。这种自觉的过程,从题材来说并没有超越同时代的题材,只是在同题材中,其作品里因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而引人注目,这应该说与韩少功早期的知青经历密不可分的,比如他的《西望茅草地》等小说,都蕴涵了政治因素带来的悲剧性结果。
月兰是长顺的女人,每天干粗活累活,照顾婆婆,孩子上学费用也得靠鸡下几个蛋来换取,可这4只鸡竟被三令五申严禁鸡鸭下田的下乡工作队放毒药毒死了。月兰的悲剧是在典型社会里发生的典型悲剧,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生命的价值,以悲壮的毁灭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而这价值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剧土壤和悲剧力量。小说在紧凑的结构布局和情节中展开,月兰的死是必然的。她被要求写检讨,写检讨还不算,每只鸡还得罚款5元,将来秋收后扣,月兰埋怨长顺,长顺喝了点酒,性起就打了月兰一耳光,月兰的心灵就在这一步步的斗争中被摧毁,月兰忍受不了大队人员对她的不公,但这就算了,月兰更忍受不了丈夫对她的不理解与这伤害自尊的一记耳光,于是月兰的悲剧发生到极致。
从韩少功的早期创作历程来分析,这种悲剧意识显然还处于最社会化的阶段,即是一种特殊时代造成的悲剧,可以说是政治性悲剧,它由于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干扰与心理因素的碰撞而产生出来巨大的能量,从而触撞禁锢已久的人们脆弱的心灵。《月兰》《西望茅草地》《火花亮在夜空》《道上人匆匆》《晨笛》等,都反映了这种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悲剧。韩少功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种极左路线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在“文革”中选择了自尽,他忍受着少年丧父的巨大痛苦和母亲的昼夜叹息,“但因父亲复杂的社会身份及其在传统家庭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他的离世给予韩少功的刺激依旧很大,有丧亲的悲苦,无所依恃的惶恐,更有阶级区隔下隐形“高墙”强加的时代精神创伤。”[3]7所以这种特殊的成长过程在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中是具有独特意义和地位的,悲剧总是伴着特殊的社会变化而产生,这一残酷的社会经历注定使得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中有着抹不去的“伤痕”色彩和“反思”色彩,悲剧意蕴也就更加浓厚和深沉了,只不过在这种悲剧阐释中,作家有时显得略单薄和无力,正如《月兰》结尾写道“支撑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赖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千千万万像海伢子妈那样的劳动妇女,她们是不应该遭受那样不幸的命运的。”这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式的呐喊和心灵式抒情,可以说这种政治性悲剧是那个刚刚告别十年浩劫时代几乎所有作家共同所有的情感基调,当然韩少功作为一个社会敏感性强烈的作家,也就深深打上了这种烙印。而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韩少功的悲剧意识更加浓厚和隐性了,也更加深刻和普遍了。
二、《爸爸爸》:看与被看的缺父式文化悲剧
韩少功在80年代中期,又开始引导新的文学创作潮流,在声势浩大的“寻根”文学中,韩少功以《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掀起了文化“寻根”的讨论,人性的弱点与阴霾得以暴露,文化是否成为悲剧的载体与依附?文化与悲剧又是怎样的关系?正如李叶所说“只有当人物身上体现出人性的光辉,当这种光辉并为阴霾所遮不见天日,而引起读者心灵上强烈的冲破阴霾的欲望时,悲剧才产生了。”[4]《爸爸爸》中的主人公“丙崽”便是这样的悲剧典型,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热议比较多的典型,有人称他为“封建原始愚昧生活方式的象征”;有人称他为“民族劣根性的代表”;有人说他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还有人说他是“一个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都不足的文学典型。”[3]646“丙崽”是一个连话也说不清的被人讥笑为“白痴”的男孩,他就会说两句话,一是“爸爸”,二是“×妈妈”,并且还伴着翻白眼的丑恶动作,让人好笑又有几分同情。丙崽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经历那么多苦难却没有死,正如韩少功自己所说“《爸爸爸》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的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5]丙崽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只会说两句不是人的人话,他就是鲁迅笔下的“被看客”,永远是“尚未摆脱被‘观看’的处境。”[6]
丙崽刚生下来后就没有了爸爸,“缺父”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现象,父亲在人的一生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父亲的缺失固然对文化的稳定性和人性的脆弱性产生影响。他是深深了解自己的身世和处境的,他一直在寻找父亲,对陌生人随口就叫出“爸爸”,仿佛丙崽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可陌生人一句“谁是你爸爸”后,他就一句“×妈妈”。丙崽始终是孤独的,是无力的,他向命运抗争,但最终只能是屈服,但还是在坚定地寻找中。这样的悲剧精神在韩少功笔下诠释得淋漓尽致。
韩少功的这种人类悲剧反省意识与他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气质是分不开的。“他当过六年知识青年和两年工作队员,在这个领域里打下了比较厚实的生活底子。而敢于正视本来千姿百态的人类社会,努力探求和揭示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尤其是人的灵魂的全部复杂性。”[7]所以丙崽不仅仅是文化的象征,更是一个复杂人性和悲剧灵魂的象征,是人类缺父寻父的悲剧缩影。韩少功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思考更深刻的就是文化因子在人性中的作用,我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里所有的深刻、神秘与痼疾,这在他80年代的《文学的根》中有过明显的探讨。当然,在韩少功的文学创作里,从政治悲剧到文化悲剧,他的这种悲剧意识也是从浅显到深刻,从简单到复杂的探索过程,在追问人类悲剧的产生与发生的同时,他还在不停地追问:人类悲剧是不是终有会结束的一天?
三、《山歌天上来》:人性悲剧是不是没有结束?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韩少功还一如既往地探索他的文学创作理念,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实现与丰富他的理念,无论是早期的政治悲剧叙述还是中期的文化寻根叙述,革命、人道、权力、乡村、人性等问题,他都在努力地思索与探求。韩少功文学作品中始终具有的悲剧意识是贯穿他作品的一个基点。《山歌天上来》主要写了“山歌”这一民间艺术的命运沉浮和3个不同的人在社会名利场中对音乐的态度和价值行为,为我们展示了一曲艺术的悲歌和人性的悲歌。民间艺术家毛三寅,他谱的曲子被人认为是“作者应该是毛三寅斯基或者毛三寅柯夫才对。”可是他去县文化馆接受培训,行为我行我素,不服老师的管教,领导认为毛三寅政治上有问题,是资产阶级音乐观。他被调回乡里后,应县山歌剧团的邀请,花了巨大的精力写了一部歌剧,却被别人抄袭而名扬海外。他受到打击然后淡泊名利,在一次意外中被老鼠咬伤,随后感染病毒,因无钱医治而不幸身亡。他只是一个简简单单清清白白的民间艺人,真诚地热情地传播着他的民间艺术。可这样的人在金钱和名誉社会面前,始终没有立足之地,他的艺术被人剽窃,他的地位被人排挤,韩少功的内心是悲凉的,信仰价值究竟有多少,信仰求索究竟值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山歌的退场和天才的陨落,不仅象征着乡村精神家园的步步沦丧,而且也成为让读者深感震动的触发点。”[8]
伪知识分子柳老师没有真正的才能,却油嘴滑舌,把艺术说得头头是道,虚伪做作,只在乎物质享受,改革开放之后,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摇身一变弃文从商。魏博士为了一时走红,竟抄袭了老寅的曲目《天大地大》,只不过是改了个名称叫《山鬼》而已,却红得发紫。人为什么在外在利益的引诱与迷惑下会变得脆弱甚至不堪一击?人性的复杂也许正是韩少功思考的原因。黑格尔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9]歌德也曾说人是一个丰富的统一体,是一种“单一的杂多”,正是这种“单一的杂多”决定了人性构成的复杂。
在韩少功的另一部作品《归去来》中,他就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与困惑。“身份认同问题是现代性的产物,尤其在80年代后,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这些问题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矛盾中成为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和苦苦追寻的问题。”[10]芹姑娘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的艺人,甚至只是一个“哭丧”的人,也像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对自己的价值与身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与否定,陷入了极度的精神苦闷与烦恼中。《山歌天上来》最后在芹姑娘说这个庆祝会害死人中嘎然而止,耐人寻味。到底是庆祝会还是追悼会?悲剧人物的内心是存在激烈冲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悲剧精神的内心冲突或性格矛盾也是悲剧精神的主观英雄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变异。”[11]异化,这便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人之异化与人性之异化最为恐慌与绝望的字眼,异化的仅仅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韩少功没有直接向读者说明,但在迄今为止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他的确清楚异化的是悲剧的人性。
从韩少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月兰》《爸爸爸》《山歌天上来》来分析其内存的悲剧意识和探讨背后的产生原因,这当然也涉及到了他的整个创作历程。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韩少功是一位具有反省意识和批判意识的思想性作家,他的这种悲剧意识不是悲观,他一直思考中国的问题,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一贯的思考批判气质使他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一种隐藏的悲剧色彩和深层的悲剧意识,他也从最初简单的政治悲剧探索到文化悲剧以及到整个人性悲剧的挖掘和认识上逐步深化,有利于思考如何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
参考文献:
[1]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7.
[2]鲁迅.再论雷锋塔的倒掉[J].语丝,1925(15).[3]廖述务.韩少功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7.[4]李叶.余华小说的悲剧性特征[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09(1).
[5]韩少功,夏云.答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问(代创作谈)[J].钟山,1987(5).
[6]张钧,韩少功.用语言挑战语言—韩少功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6).
[7]王福湘.生活思考追求—评韩少功近几年的小说创作[J].湘江文艺,1982(3).
[8]邓菡彬.对抗重复:2004年期刊中的韩少功小说[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3).
[9]黑格尔.美学: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0]张光芒.身份认同与自我的重构—重读韩少功《归去来》[J].名作欣赏,2008(19).
[11]马小朝.论中西悲剧精神的内心冲突[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1).
(责任编辑:孔文静)
On the Tragedy Consciousness in Han Shaogong’s Novels
Yang Kai(President’s Office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In Han Shaogong’s life-long creation of literature, his writing career covers every epoch ranging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to the new age, 1990’s and the new century. Each of his works is shrouded by a heavy tragic consciousness, which is embodied in political tragedy in his earlier creation, cultural tragedy in his later creation as well as the tragedy of human nature occurring in its evolution in the new century. Meanwhile, Han Shaogong never stopped pondering the underlying causes for such tragedie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Han’s three masterpieces created in different epochs so as to reveal the causes for and the process of such tragedies, attempting to obtain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loaded in Han' s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Han Shaogong; Creation of novels; Tragedy consciousness; Tragedy of human nature
[作者简介]杨凯(1986-),男,湖南临澧人,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职员,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新闻传播。
收稿日期:2015- 02- 18
[文章编号]1673-8535(2015)02-0084-04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