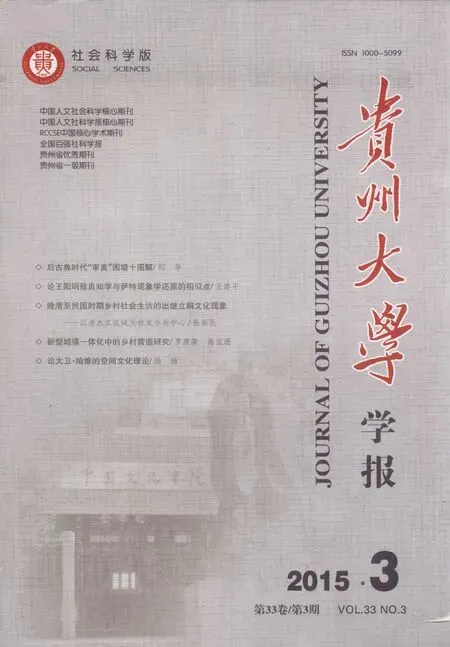苗族古歌唱者与听者探讨
2015-03-20龙仙艳
龙仙艳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苗族古歌①苗族古歌的界定按照人类学主位与客位的二分法有自称和他称之别。自称而言,苗族古歌在东部方言区称为“dut ghot dut yos”(都果都谣)、中部方言区为“hxak lul hxak ghot”(夏鲁夏个)、西部方言区为“hmongb ngoux loul”(蒙歌老)、yax lus(亚鲁)等;他称则有“苗族古歌”、“苗族史诗”、“古老话”、“苗族创世纪史话”等不同称谓。本土语境中苗族古歌多以吟诵为主,具有活态口语诗学的特性。指在苗族聚居地用苗语流传的关于开天辟地、万物起源、民族族源与迁徙等创世性题材的歌谣。从迁徙古歌到围绕土地居住权的古歌,均强调家庭、家族以及姻亲网络的聚落共同体形式[1],所以,截至当下,苗族古歌依然成为维系苗疆族源记忆、族群意识和族属认同的重要依据,并以此深远影响到椎牛、鼓藏节等宗教活动和婚丧嫁娶等生命仪式有序进行。与精英书写的文学文本不同,苗族古歌长期以来一直以口头诗学的唱本形式流传于苗族社区,较之千百年以来苗族古歌被“文本化”(被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的短时阅读而言,苗族古歌几千年以来直至当下仍然以唱本的形式在苗族民众代际之间依靠口耳相传,作为无字民族,其听觉冲击首当其冲。
苗族古歌是唱者之唱与听者之听的双向交流:从发送者的角度而言,苗族古歌在苗族社会流传的基础在于“唱”,只有通过唱者之唱苗族古歌才能得以传播;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苗族古歌的传播方式在于“听”,旋律、歌辞甚至于语境都因为听者的聆听和感受才得以完整。可见,不同于书写文本读者与作者的隔膜与疏离,苗族古歌的唱者与听者的双向交流具有情境性和现场性。正如学者所言:因为不靠文字阅读而用口耳传递,“亚鲁王”的存在和呈现就具有了集体参与和现场互动的交往特征。那样的场景异常热闹,对族群凝聚和集体认同所起的作用,实不亚于清冷的文本[2]。
可见,区别于精英书面文学的作者和读者,苗族古歌的接受主体为古歌之唱者和听者。苗族古歌的唱者包含巴兑、东郎、褒牧、理老及歌师,并非简单的传承人一说所能涵盖;从接受者(听者)角度而言,相对于书面文学单一的人类文字阅读,苗族古歌由于其歌谣听觉性从而其接受者多元,除了苗族民众作为其听众之外,世间生物、鬼神与亡灵都构成苗族古歌的听众,下文将分而论之。
一、苗族古歌之唱者
相对于精英书写的明确作者,苗族古歌由于年代久远的模糊性与其口语诗学的集体性,很难考证其源初作者。由于其口语诗学特有的“创作中的表演”之特质,从传播角度而言作者即唱者。苗族古歌与苗族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吟诵并非随意为之,多在重要仪式中演唱。在苗族社区中,古歌的唱诵并没有从苗族社会中作为一种职业而单独脱离出来,古歌之唱者与苗族其它民众一样参与生产劳动,只有在特定的场域或语境下才吟诵古歌。
苗族古歌先后5次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申报的文本中将古歌唱者概而称之为传承人,其重要性得到不断地关注: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和传递者,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贮存着、掌握着、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的技艺,他们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接力赛’中处在当代起跑点上的‘执棒者’和代表人物[3]。
事实上,由于长期的迁徙与战争等历史缘故,苗族三大方言的古歌吟唱者在不同的方言区甚至同一方言区的不同次方言在称呼和分类上亦各具特色。据笔者的田野调查,东部方言区把吟诵古老话之人称为jiangd dut(话师),这是针对jiangd sead(歌师)而言,符合东部方言区dut(话)和sead(歌)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从这一词源角度分析可知,jiangd dut(理老)并非职业称谓而是吟诵内容凸显,其具体身份可分为三种,一种即理老(bad jiangd dut),一种是理老兼歌师,此外为bax deib(巴兑)①(巴兑)即苗族东部方言区的巫师音译。。
在中部方言区,第一次将古歌传承者做出深入研究的首推杨正伟。他在《苗族古歌的传承研究》以传承为关键词,将传承者分为寨老、理老和巫师三类。
由于居住分散,西部方言区苗族古歌唱者的分类与称呼分歧较大。其中川南的古歌师分类根据其演唱场合分为houd qud(在丧葬中或祭天神中的主祭)、houd zongk(婚礼上的主礼)两类②资料来源:笔者对《四川苗族古歌》搜集者之一陶小平田野访谈的录音整理。;在麻山次方言区,以《亚鲁王》③此处所言的《亚鲁王》即包含已经出版的文字版本,又包括尚在搜集整理的民间唱本,其内容包含创世纪、亚鲁王身世以及亚鲁王子孙后裔的叙事。的唱诵为例,可分为东郎(dongb langb)和宝目(bof hmul)两类。
虽然古歌之唱者在三大方言区皆有不同称谓,但抛开称谓的表面差异,以苗族古歌的演唱功能和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宗教、法律的相关程度而言苗族古歌的唱者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强调苗族历史传承,其唱者为歌师;第二类苗族古歌偏重苗族法律制定和裁判,其唱者为理老;第三类则凸显宗教因素,其唱者为巫师。
1.歌师
东部方言区古歌以吟诵为主,仅有篇幅简短的创世古歌如《开天辟地》(Kiead qand lix jib);盘古开天、晴皓立地(Nbeax gut lix dab blab qenx haob lix dongs denb)、鸡源歌(Sead mleus ghead)等由歌师演唱。这一推断可参考在目前出版的近六部古歌集中仅有石寿贵整理的《湘西苗族巴代古歌》对sead ghot(古歌)有所搜集。事实上,jangs sead(歌师)仅仅演唱苗族古歌的一个极小分支,大多由jangd dut(理老)兼任。理老兼歌手的这类唱者由于歌的唱诵与“都”的吟诵其内容和表述分属两套不同的系统,因而身兼两职对于唱者要求较高,但又由于大多理老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故而成为理老之后如果希望成为歌师则为轻而易举之事。
据罗丹阳田野调查得知,在黔东南施秉、台江和剑河等县演唱苗族古歌之人称为ghet xiangs hx-ak(古歌师),民众对其界定有严格的标准:其一,从演述的水平上来说,古歌师需要记住大量篇幅的古歌内容,在演述的过程中不能出现差错;其二,从演述者的嗓音条件来说,古歌师的嗓音要洪亮,让受众有兴趣听下去;其三,从古歌师必须会教徒弟来说,他或她有传承苗族文化的职责;其四,除了以上三条外,古歌师还精通古歌之涵义,并能诠释 [3]9。
歌师演唱的苗族古歌偏重历史记忆,其中大量的创世题材具有“神话历史”的特征。如中部方言区的黄平、施秉与镇远一带之古歌大多由男青年游方所唱,故而演唱语境较为自由,其吟诵过程也没有太多的场景布置或禁忌。
2.理老
理老在东部方言区称为“jangs dut”(理老),由于东部方言区苗族古歌三大主题即Dut Sob(雷神之战)、Dut niex(奶夔玛媾)和果所果本(Ghot sob ghot bens)皆以dut(话)为表现形式,故而东部方言区苗族古歌之唱者以“jangs dut”(理老)吟诵为主流。
中部方言区称为“ghet lil lul”或“ghet jax”,王凤刚以流传于中部方言区丹寨县内的《苗族贾理》为例提出《贾》的历代传承人主要是理老。理老所吟诵之jax lis(中部苗族理词)或leab sead pud lis(东部苗族理词),除了创世部分与苗族古歌重叠之外,更强调以民族习惯法分析具体个案。笔者认为苗族贾理是苗族古歌世俗化的运用,随着苗族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纷争出现后,由于长期与中原文化隔离,从而除了引经据典地延伸苗族古歌之外,更有对法律案件的总结。“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不必绳以官法。”[5]14
3.巫师
巫师在中部方言区称之为xangs dliangb(鬼师);在东部方言区称之为bax deix(巴兑);西部方言区麻山次方言称之为东郎(dongb langb)和宝目(bof hmul)两类。以西部方言区麻山次方言《亚鲁王》的唱诵为例,东郎可简称为在葬礼上唱诵史诗《亚鲁王》之人,东郎的唱诵既包括创世纪,也包括亚鲁王其后代子孙身世的交代;宝目唱诵的是《亚鲁王》的创世纪部分,这个部分在生活礼仪上运用得较多。
以东部方言区的苗族古歌为例,东部大型的宗教祭祀都需要交代祭祀来源即Chat ghot(讲古)这一环节,故而讲述其巫辞起源的椎牛之椎牛古根(dut ghot niex)、椎猪之椎猪古根(dut ghot nbeat)、祀雷之祀雷古根(dut ghot sob)、还傩愿之傩神起源歌(dut nux或sead nux)等古根即苗族古歌,其吟诵除了上文提到的理老之外,更多地由巴兑来完成。
区别于歌师吟诵之古歌较少宗教语境,区别于理老之贾理强调法律分析,巫师所吟诵的苗族古歌强调宗教影响,多在丧葬仪式或祭祀活动过程中,在吟诵过程中有诸多的仪式和禁忌。
巫师之所以成为苗族古歌的唱者之一,其原因在于:对于宗教仪式而言,为了凸显仪式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故而需对仪式有一个元初的解释,所以每一堂祭祀的合理性需要从苗族古歌中找到诗学确认;对于苗族古歌而言,其演唱必须有一定的场域和语境,并非是情境性或应景性式的随意对歌,而长期以来苗族“重鬼尚巫”的传统使得大部分苗族古歌借助于祭祀活动被仪式化和凝固化,从而形成了巫师成为苗族古歌唱者的主要原因。
二、苗族古歌之听者
正如阅读使书写作品具有意义,口语诗学因为有了听众的聆听才得以完整。口承史诗的传承离不开听众。史诗的社会功能和美学价值是“潜在的功能”和“潜在的价值”,只有通过听众的接受,史诗的潜在功能才得以发挥,史诗的潜在价值才会发生效应。史诗的价值结构是史诗与听众的合成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听众是价值的主体。听众接受,史诗才得以流传,听众拒接接受,歌手演唱的再精彩,没有听众聆听,史诗就会失传,是听众使史诗获得了生命[6]264。
较之于书写文本单一的人类读者,苗族古歌或曰口语诗学的接受者更为丰富和多元。如阿尔泰乌梁部族史诗的吟诵有诸多的禁忌,其合理性解释为前来欣赏阿尔泰颂的不光是人类,还有阿尔泰山的各种神灵都在听阿尔泰颂的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7]。
可见,严格意义上的苗族古歌为“苗族”之古歌,显然是以苗族民众为主体但不仅仅限于此。换而言之,如果仅仅将其听者限定为苗族民众一维显然低估了苗族古歌,从听者而言,苗族古歌之听者不仅包括有生命的苗族民众与生物类,也包括了无生命之鬼神与亡灵类,下文将逐一论述。
1.苗族民众
正如余未人在《尊重〈亚鲁王〉史诗的口头传统》的史诗整理札记所言:我们共同做的,是《亚鲁王》由苗语口头唱诵到汉文文字的首次转化。至此,《亚鲁王》结束了上千年的纯口头唱诵,而有了一个文字的记录史诗汉文本[8]768。
通过文献查阅可知,苗族古歌被文字化最早只能追溯到1896年西方传教士克拉克的首次搜集,苗族古歌大范围地以文本形式传播则晚至1979年即田兵编著的《苗族古歌》首次公开出版。较之于百年以来短时的文字传播,苗族古歌唱本的流传则源远流长,以黔东南一带为例:《开天辟地》中关于创造宇宙的这首歌的原始框架产生时代当在汉代以前;《枫木歌》的原始框架的产生也可能早于汉初;反映吃鼓藏的苗族古歌的原始框架可能产生于在稍后的汉晋之际[9]7-15。即便以目前看来较晚定型的《苗族贾理》为例,在累经数千年的传承后大约定型在300年以前,其依据为:一是在《迁徙篇》中叙述的最后一个迁徙定居地,距今有20代约600年;二是在《村落篇》中叙述的村寨,据若干谱牒资料可确证建寨最晚有11代约310年;三是丹寨境内的一些在清雍正改土归流前存在而此后消失的村寨,《村落篇》有述,改土归流后才出现的一些移民新村寨和屯堡,《村落篇》中却无述及[5]14。
可见苗族古歌被文本化不过百年,而唱本的古歌存在至少千年以上。以东部方言区的苗族婚姻礼词(dut qub dut lanl)为例,其吟诵内容的《njout bul njout denb(历次迁徙)》等迁徙古歌,提到五宗六亲的分布是对东部方言区苗族八大姓氏七个可通婚集团的分布做出一个基本的概述。在婚礼上吟诵这则古歌,既有对民族迁徙和定居状况的情境性教育,同时也是对通婚区域和通婚方向甚至通婚对象的提醒与肯定;在最后吟诵的是dut lanl(待客礼词),则是伦理的现场教育,既有对作为新人的言传身教,也有对观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通过这样较为正式的介绍,使得新人双方的亲朋好友得到沟通和了解。
苗族古歌中神话、历史与民族的古歌之辞和创世、战争与迁徙的共时分布可知,苗族古歌在苗族地区用苗语流传与苗族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在此意义上,苗族民众成为其最为重要的听者之一。
2.世间生物
上文已论及,苗族古歌并非是精英的文字书写,它以活态的唱本形式大量寄生于民俗活动之中。鉴于此,苗族古歌之听者之二可概括为事件生物即相对于人类之外的生命体。苗族古歌之听者为生灵这一特点在中部的《贾理》尤其是创世部分十分明显,在中部方言区鼓藏节也有体现,此外在东部方言区宗教仪式中亦较为突出。
此处所言的生灵包括动物和植物,其中动物以牛、马、猪、鸡等苗族生活中关系较为密切的牲畜为例,而植物则有米草、枫树、马桑树等。相对于人作为苗族古歌之听众较为容易理解,万物生灵作为苗族古歌之听众则有待笔者进一步举例。
《祭鼓词》是苗族庞大祭祀活动的诵词,分“起鼓”、“砍鼓树”等章节,其中geid sais nix(剥牛旋)中的诵词有专门为牛吟诵的《审牛词》[10]50,63:
Bad liongk yeb牯牛哟,
……
Niangb mongx niux lol mongx hangd hot在你的身上你自己来表述
Mnongx xit nkad lol at dax dol在你的嘴上你自己来说
Xit hkieb lol at hfut nongb来哟,来我们聚会
Niangb niox hneib niul相邀来做鼓藏节
从其第二人称的重复提醒“你”可知,这段诵词显然是以牛为其拟定听众。据徐新建教授的田野民族志介绍:寨老李春荣向我们解释说:念辞(椎牛辞)的目的是告诉老人家、我们生活好了、有吃有穿,我们要来献祭你们;然后又对牛讲,不是我们要杀你,是枫树喜欢你,是刷条想赶你,让牛别伤心,安心地去侍奉老人[11]68-69。
无独有偶,东部苗族在《祀雷》时候如需要用牛祭祀,则需念《喂水牛水》:
Ghob bad mongx soub mel lot:面如生铁熟铁的雄性:
Moux lis gheax mloux dongt sead,你要侧耳倾听(我唱的)诗,
Gheax beas dongt dut(你要)侧面细听(我诵的)辞。
此处所言及的“你”即用来祭祀的水牯牛,苗族古歌之唱者通过与听者牯牛的交流得以阐释其选定其作为牺牲的缘由。麻勇斌研究员对于这一事项解释的是:之所以要牛听往古的讼理之辞,是因为牛已经要被杀来祭神了,它怨恨取它姓名的人,它会变成鬼后找害它的人的麻烦。故在他临死之前弄清原因,要让它对于死它只能责怪谁,只能找谁索命[12]273,477-478。
此外,在西部方言区麻山次方言的葬礼上,为了将亡灵灵魂驮回亚鲁王所在的故土,需要砍死一匹战马,砍马有诸多的仪式与程序,最为重要的是必需要念诵《砍马经》。从《砍马经》中了解到之所以要砍死这匹战马,是因为他“吃鲁(亚鲁)命中树,啃鲁(亚鲁)命中竹”。正是因为结怨结仇,亚鲁王当时提出要砍死亚多王(战马)偿命,亚多王则认为消除仇恨的办法并不是当时杀死它抵罪,而是以后有亡人要回祖先之地,需有战马骑着上岩石山,为此承诺可以砍死它的子孙以让亡灵顺利回归,故而对马的唱诵词中还有交代,即“你莫怨砍者,应恨你祖先,祖先亚多王,已经许了愿”。
固然按照唯物主义者而言,对于索命一说不屑一顾,那么接下来更让科学主义无法解释的是接下来要给将要刺杀的水牛喂上天的壮行酒时,在念诵以下诵词之后,不少牛温顺地舔下这碗酒水,甘愿被椎杀。在笔者2013年12月4日参加的亚鲁王祭祀大典上,被选定的战马听了《砍马经》之后,虽然马匹被砍得血淋淋,但不悲悯嘶叫,也不忍痛乱跑,而是安安静静地转圈,任由砍马师将其砍死。
生灵不仅仅是动物,还有植物,如《qet mit niongb 草卜遴选鼓藏头》[13]91-92即是为米草 而吟诵:
Niongb eb米草啊
Mongx dios daib fangb dol你原来生在大海边
Mongx daib jid fanngb faib你来自遥远的东方
Mongx bub jul hsangb huib bat sangx你阅历丰富见多识广
Mongx xangf jul bat zangs bat dliangb家神野鬼你知道端详
Nongd jef seik mongx lol niangb dangx这样才请你到屋里坐
Nongd jef wil mongx lol guf jib这样才接你来到我火塘
此外,世间生物作为苗族古歌之听众在《苗族贾理》中大量存在,仅以《创世篇·祭公祀奶》中,就逐一交代了水牛与蚂蚱、螳螂、鸡和山羊等争说要祭鼓,并对獭和鱼、鸡和野猫、虎与猪、山羊和狗、蝗与猴、老鼠和麻雀、蚂蚁和毛虫等纷争的解决从而交代其生物属性的来源。
3.鬼神
相对于有生命之人与世间生物,无生命或曰常生态之鬼神同样构成了苗族古歌听众的重要部分,下文这段古歌即为雷神吟诵:
Huad manx jox menl deb npad sob rongx sob ghunb,manx guant dab blab让你们九位龙神雷神专管天上,
Doub nex wangx jit boul guant dab doub让德能王纪专管人间。
Manx nib dab blab manx heut jid nkhed dab doub你们在天空看住世上,你们在上天专看人间。[14]50
此处的“你们”指的是雷神世家。唱者在叙述天地起源的创世神话之后,以大量的篇幅叙述雷神与皇帝战争的经过,因为这次战争以雷神胜利告终,故而重复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取悦雷神,从这一层面而言,整堂仪式的唱辞其拟定听众为雷神。
再如流传于西部方言川黔滇方言区的《祭天神》,在古歌中明确交代其祭祀对象为:
Yeuf chik nenb gud zhit shob zhit shend蚩爷兄弟竖起耳朵听
Nos dout naf dlex ndul leul daof bil draod daof dous听见大河的流水声
Yeuf chik nenb gud zhangt muas nuaf蚩爷兄弟抬头望,
Nuaf dout naf dlex ndul leuf daof dous draod daof bil看见大河从上往下的流水声[15]429-430
正是其听众为被汉族用阴谋欺骗而战败的苗族即蚩爷兄弟等众神,故而整堂仪式有禁止说汉语的禁忌,据苗族学者杨照飞的解释,一旦仪式过程中说汉语则冒犯了其祭祀对象,则整堂仪式前功尽弃。
4.亡灵
之所以将亡灵作为单独的听者加以论证,因为亡灵既不同于有生命之人与生物,又不同于无生命之鬼神。毕竟亡灵(新亡)介于阴阳之间。在苗族意识中,死亡并非生命的终极,从而新亡处于阳灵和阴魂的阈限之中:对于活人而言,新亡显然已经落气、停止呼吸,故而属于死者;对于阴魂,由于还没有经过将其魂魄送回东方故园之故,故而亡灵还没有归入祖宗行列,其模糊性类似于阈限理论之“钟摆”阶段。
正是因为将亡灵作为拟定听者,故而其吟诵的称呼对象绝对不能出现生者的名字,不然会招致不幸。正是因为苗族丧葬古歌的听者明确为亡灵,不少本土学者在对苗族丧葬古歌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在形成文本后都用模糊的名称来代替,如在《湘西苗族招魂辞》中则为“阿德”,在中部苗族的焚巾曲中则泛指为“妈妈”,西部方言川黔滇方言区的《丧事录》中,其称呼模糊为“石头大爷”:
Nat zhes,sheud zhenl nel yeuf reb el就这样,赶快起来吧,石头大爷
Nat zhes,yeuf reb sheud zhenl nel就如此,石头大爷赶快起来呢
Nat zhes sheud zhenl nel naf yeud reb el就这般,赶快起来吧,石头大爷[12]4
据过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得知,为亡灵吟诵苗族古歌为三大方言所共有。虽然称呼上有“论火把”“焚巾曲”和“指路经”或“亚鲁王”等之不同称呼,但目的都是将其魂魄送回苗族的东方故里,使其得到老祖宗的庇护,从而完成苗族特有的丧葬目的。以西部方言区麻山次方言东郎演唱的《亚鲁王》为例,在笔者采访中,田野调查者杨正江这样解释:在给死者唱诵《亚鲁王》之前,东郎有这么一个交代:“你(亡灵)生前没有人给你讲,你现在死了由我来给你讲。只有记住这段历史,你才能找到路回家,因为在老祖宗那里会有一个考官考你,你只有把老祖宗这段历史讲述得一字不漏,老祖宗才打开大门让你回家。”①资料来源:笔者对杨正江田野访谈的录音整理。杨正江:男,苗族,紫云县水塘镇人,紫云县《亚鲁王》翻译整理工作室负责人。
正是听者对象明确,故而三大方言区的丧葬礼仪中巫师唱诵苗族古歌的作用大同小异:将新亡者当着将去另一世界生活的新魂和新魄,不但将家人装殓和陪葬的衣物一一点交并教以使用方法,而且指引他们来往的路途和排除途中受阻的方法,向他们讲述民族历史,以及教导其在阴间如何处事和交往等,简直与人间指导一个新居民无异[12]309-310。
三、结语
上述对于苗族古歌唱者和听者的多维探讨是为了凸显苗族古歌不同于书面文学的口语诗学特征,一般而言,歌师和理老所吟诵的古歌其听者多为苗族民众;由巫师所吟诵的苗族古歌因为带有较多的宗教语境,故而其聆听者不限于人类一维,既有生灵万物,更有鬼神亡灵。从这一层面而言,苗族古歌的吟诵除了历史文化的传播与法律知识的灌输和文学的审美之外,更多的偏重与万物之间的沟通和聆听。这一切固然由于苗族社会万物有灵的生命观,而其深层原因还在于在苗族社会里,世间一切皆可以对话、交流,使之和谐相处,苗族古歌即灵性通达、人事化解的证明和预示。
[1]曹端波.苗族古歌中的土地与土地居住权[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3):67 -77.
[2]徐新建.生死两界送魂歌——〈亚鲁王〉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族文学研究,2014(1).
[3]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5).
[4]罗丹阳.苗族古歌传承的田野民族志[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5]王凤刚.苗族贾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学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7]海英.阿尔泰乌梁部族史诗演唱文化空间对史诗传承的约束[J].新疆大学学报,2010(11).
[8]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亚鲁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吴一文.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10]刘峰.鼓藏节[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11]徐新建.生死之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2]麻勇斌.苗族巫事[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
[13]杨元龙.祭鼓辞[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
[14]石如金.苗族创世纪史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15]杨照飞.西部苗族古歌[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