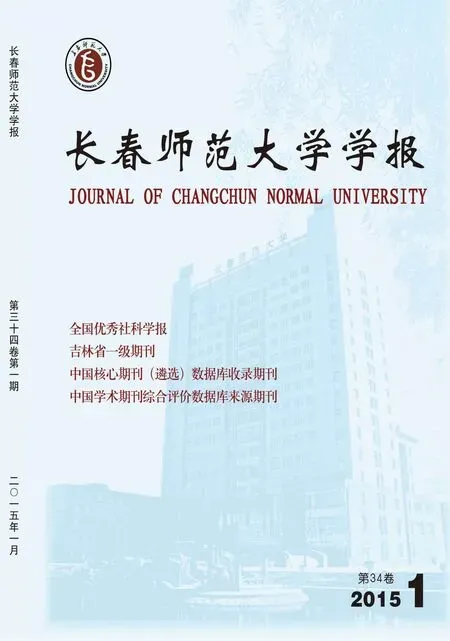淳朴直爽 清明如镜
——论《华山畿》25首的艺术特色和现实意义
2015-03-20戴从容
宋 旭,戴从容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淳朴直爽 清明如镜
——论《华山畿》25首的艺术特色和现实意义
宋 旭,戴从容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华山畿》现存25首,是南朝民歌中非常有特色的文化瑰宝。它们多出自女子之手,情绪天然质朴,幽思婉转悠扬,真诚而动人,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以及情感的真实性。《华山畿》在情节、人物和情感方面,为其他艺术形式提供了原始素材,扩展出很多改编和再创造的可能。最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单纯率性的爱情观对现代社会有很强的启示。
《华山畿》;南朝民歌;艺术特色
南朝民歌,主要包括吴歌和西曲。《乐府诗集》中,“吴声歌”最多,共收录326首,由此可印证吴歌是南朝民歌中相对比较重要的部分。《晋书·乐志》曰:“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1]639这里说的吴歌杂曲,产生于南朝四代首都建业。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吴歌也有相关论述。“‘吴声歌曲’者,为吴地的歌谣,即太湖流域的歌谣;其中充满了曼丽宛曲的情调,清辞俊语,联翩不绝,令人‘情灵摇荡’。”他认为“吴声歌曲富于家庭趣味”,大抵因为“太湖流域的人,多恋家而罕远游;且太湖里港汊虽多,而多朝发可以夕至的地方。故其生活安定而少流动性。”而“长江中流荆、楚各地,为码头所在。贾客过往极多。往往一别经年,相见不易。思妇情怀,自然要和吴地不同”,因此西曲歌中“往往具着旅游的匆促的情怀”,“富于贾人思妇的情趣。”[2]81这样的分析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南朝的吴歌,少有重大的社会主题,也少有征战徭役的痕迹。这是由于南朝由战乱纷争的时代转入了一个偏安一方的小康天地。“产生吴歌的建业、扬州、江浙、广陵都是物产丰富,商业繁盛的地方。背景不同,生活内容不同,表现出来的情景与格调也就不同了。歌中也有忧怨,但不是对社会的愤怨,而多为不能团聚的苦恼。”[3]119
《华山畿》收录的25首吴声歌曲都是真挚动人的民间情歌。胡适曾说“南方民族的文学的特别色彩是恋爱,是缠绵宛转的恋爱。”[4]68《华山畿》基本是女子的口吻,细腻婉约、悱恻单纯,围绕婚恋问题歌唱真情,有种动态的美,比吴歌中的“子夜歌”系列更加自然流畅,几乎没有文人气;也没有西曲中的娼女歌词、商人心理,是非常地道的民歌。
当时,封建礼教束缚严重,只许统治者沉浸于声色犬马,却剥夺平民百姓最基本的自由恋爱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山畿》对爱情的歌唱是对封建礼教大胆的反叛。
一、《华山畿》的外在艺术特征和手法运用
(一)句式结构
《华山畿》25首皆体制短小。《乐府诗集》中收录的《华山畿》第一首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这是结构上最完整的一首,首句三字,后四句皆五字。其他各首句式则各不相同,属于杂言民歌。三句成一首的居多,其中有的首句三个字,后两句五个字,如“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有的三句皆为五个字,如“开门枕水渚,三刀治一鱼,历乱伤杀汝”。也有四句成一首、每句五个字的,如“闻欢大养蚕,定得几许丝。所得何足言,奈何黑瘦为”。
形式上的随意恰恰证明了它们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纯正民间文学作品,没有掺杂文人创作在里面。
(二)押韵和节奏
适应本身短小的体制,《华山畿》为一、三句押韵,偶尔句句押韵。在节奏方面,由于最长是一句五言,因此每句两顿或者三顿,基本以单字结尾。
节奏的一个重要表达方式是叠音词的运用。叠音词可以帮助完善音乐结构,保证歌句节奏的自然流畅,叠音词本身便是即兴创作的痕迹之保留。另外,叠音词也可以促进感情的表达,是一种程式化的手段。如“腹中如汤灌,肝肠寸寸断,教侬底聊赖”中,“寸寸”比单字“寸”更能体现为情所苦的痛楚,我们至今读起来依然感同身受。“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中,“劳劳”强化依依惜别之意、难分难舍之感。“松上萝,愿君如行云,时时见经过”中的“时时”让人感受到希望常常见到恋人的企盼,以及愿长相守的痴情。
类似的例子在《华山畿》中还有很多,如“著处多遇罗,的的往年少,艳情何能多”;“无故相然我,路绝行人断,夜夜故望汝”;“摩可侬,巷巷相罗截,终当不置汝”;“奈何许,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腹中如乱丝,愦愦适得去,愁毒已复来”。这些叠音词使得歌咏顺畅、连贯、饱满,读起来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圆润动听,清清朗朗。
(三)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华山畿》中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并且三种手法经常结合在一起。
1.赋的运用
段宝林先生认为赋可分为三种境界,分别为直叙景事、直抒情怀、直说事理[5]172。《华山畿》中多为前两种情况。“夜相思,风吹窗帘动,言是所欢来”便是直叙景事,写女子正相思之时,风把窗帘吹动,让她以为是意中人前来。“一坐复一起,黄昏人定后,许时不来已”则呈现女子等情郎来相会,坐卧不宁、胡乱揣测的情形。“奈何许,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直接抒发一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执着情致,是典型的直抒情怀。
2.比的运用
段宝林先生把比分为明比、暗比、借比、排比、正比、反比、拟人比、谐音双关比,会意双关比等类型[5]172。《华山畿》运用的比较突出的是谐音双关比和会意双关比。由于谐音双关比和谐音辞格有关,是《华山畿》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下文会专门阐述。这里仅举例说明会意双关比。
会意双关比指利用两个词语的意义关联表达另一层意境。有时会意双关比和谐音双关比共时出现。比如“闻欢大养蚕,定得几许丝。所得何足言,奈何黑瘦为”这一首,以“丝”寓“思”,兼谐音会意于一体。“隔津叹,牵牛语织女,离泪溢河汉”不仅写牵牛织女的故事,也用来比喻自己和意中人的境遇,是单纯的会意双关比。纯粹的会意双关比再如 “啼相忆,泪如漏刻水,昼夜流不息”,以水比泪,表达相思苦;“腹中如汤灌,肝肠寸寸断,教侬底聊赖”,用汤灌腹中会意双关因爱情而肝肠寸断。
3.兴的运用
段宝林先生将兴分为有义兴和无义兴。有义兴,兴而比;无义兴,首句起兴,与后面几句只是韵脚相叶,内容并无直接联系[5]172。“松上萝,愿君如行云,时时见经过”便是无义兴,首句和后两句没有内容上的直接联系,只是“萝”和“过”押韵。而相同句式的“长鸣鸡,谁知侬念汝,独向空中啼”就是有义兴,首句不仅起到兴的作用,还和后句构成了比的关系。
《华山畿》中如有比兴手法出现,往往由三句构成,首句为上段,作为比兴句;后两句为下段,抒发情绪。
(四)谐音辞格的运用
关于谐音词格,徐中舒认为,“我国文字属于单音系,一个字只有一个音,所以同音的文字非常的多。因为音同意异的缘故,平常谈话中间,就往往引起人家的误会。此种困难,实是中国文字的缺点。但是在修辞学中,有时也能利用这种同音异字的文字,构成双关的谐音词格(“谐音词格”为徐中舒语,一作谐音辞格——引者注),谐音词格的妙处,就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这一类的修辞,在诗人的作品里很不多见,而民间的口语里,或方俗文学里,则非常的多。至于《吴声歌》里,尤为丰富。”[6]79
吴歌中常用作谐音的字词有:“芙蓉”暗指“夫容”,“莲”暗指“怜”,“藕”暗指“偶”,“丝”暗指“思”,“丝布”暗指“思夫”,“匹”含“匹配”意,“缝”暗指“逢”,“藩篱”喻指“分离”,“荻”暗指“敌”,“黄蘖”含“苦”意,“油”表示“由”,“箭”代指“见”,“梧子”暗指“吾子”,“髻”指“计”,“星”指“心”,“琴”暗指“情”,“药”暗指“约”,“关闭”之“关”双关“关联”之“关”,“题碑”谐音“啼悲”。
这些用于谐音的字,往往是当时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蚕丝”这个意象常常在《华山畿》中被用到,因为《华山畿》以女子口吻叙述,而纺织恰恰是女子本业,几乎每日不离,心中所思,见丝线布匹,便以此为比,抒发出来。另外,南朝采莲之俗盛行,虽然现存《华山畿》中几乎没有与莲相关的谐音,但用“莲藕芙蓉”来做双关之歌的例证在其他吴歌里面有很多,以此推论在《华山畿》未流传下来的那些篇中亦应不乏此类。
谐音辞格充分体现了民歌的口头性,能够灵活表达情感,亦能体现集体性特征,因为这是通俗易记的手法。表现方式的易于接受使得内容能够被传续下去。
下面阐述一些《华山畿》中谐音词格的应用例证:
以“题”为“啼”,以“碑”为“悲”,或者结合起来以“题碑”为“啼悲”的歌句比较广泛,如“将懊恼,石阙昼夜题,碑泪常不燥”;“别后常相思,顿书千丈阙,题碑无罢时”。
以“丝”为“思”,传达思念之情亦很常见,如“闻欢大养蚕,定得几许丝。所得何足言,奈何黑瘦为”;“腹中如乱丝,愦愦适得去,愁毒已复来”。
以“箭”为“见”的应用也很巧妙,如“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这种谐音词格更加隐晦,情绪更加深邃绵长。
(五)夸张手法的运用
人民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他们往往选择用夸张的手法表达浓烈的情绪。“啼著曙,泪落枕将浮,身沈被流去”,意即哭着到天明,流下的泪水不仅可以浮起枕头,还能冲走被子。用夸张手法,表现女子在感情出现问题之后的伤心。“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意为送别之时,女子泪水将长江盈满,实则是感情满溢,可见其夸张程度。
《华山畿》中的夸张难得在不浮泛,夸张得情深意重,这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无疑是成功的,同时有助于情感的宣泄和释放。
二、《华山畿》的内在情感特征以及现实意义
(一)情思单纯直接,感情炽热哀怨
王运熙先生认为吴声、西曲“艳而不荡,唯见深情”,并且引述胡应麟的话称赞它们“调存古质,至其用意之工,传情之婉,有唐人竭精殚力不能追步者”[7]73。相比其他南朝民歌,《华山畿》更为深婉缠绵、朴素深刻。
《华山畿》的每首民歌都直截了当、大胆率真,如环佩叮当、铿然作响。这是最原初的表达,洁净天然,清丽明白;又是纯粹的个人化表达,传达着生命纯然的精致状态,安康健美。
《华山畿》中有个体生命意识和独特情思的表露,能够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这是其精妙之所在。“一坐复一起,黄昏人定后,许时不来已”,这种焦急等待的心思想必很多人都能够理解,可以说是一种普世性的情感传达。“松上萝,愿君如行云,时时见经过”,以及“夜相思,风吹窗帘动,言是所欢来”等都是热烈直白的爱的宣言。
《华山畿》中的很多民歌都表达了一种凄厉哀怨之情。《乐府诗集》曰:“(清商乐)遭梁、陈亡乱,存者盖寡。及隋平陈得之,文帝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乃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1]638之所以“去其哀怨”,正是因为清商曲辞过于哀怨。《华山畿》收录在《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部分中,自然也不乏哀怨之情。这哀怨之声恰恰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体现了民间文学情感的真实性。离愁别绪、相思之苦已经足够催人心肝;男尊女卑的年代,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悲剧也不断上演,因此女子谴责情郎薄幸,表达自己的忠贞和对真挚爱情的向往的民歌便层出不穷。
爱情的不圆满使得民歌中染上一层哀痛之情。“懊恼不堪止,上床解要绳,自经屏风里”,爱情崩裂,心如死灰,以至于决然地解开床帏上的绳子上吊自尽。“不能久长离,中夜忆欢时,抱被空中啼”,长久分离,忆昔团聚之时,更觉形单影只,伶仃难耐,啼哭凄然。“未敢便相许,夜闻侬家论,不持侬与汝”,因家人反对,不能和喜欢的人结合,黯然神伤,毫无办法。对于这些歌句,读罢能够喟然长叹一声,却说不出一字,便是《华山畿》哀伤之情最动人的证明。
(二)不知缘起,留与后世之人诸多猜想,为作家文学提供原始素材
对于《华山畿》中这些坚贞的民歌,我们无法追溯到其最初的创作者;又因为其过于短小,我们无法推知具体歌唱背景,因此留给世人无尽的想象,传承意义和审美意义皆非比寻常。另外,基于对这些民歌的想象,很多文人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佳作,相关内容的影视作品也应运而生。
《华山畿》的每一首民歌都可以演绎出一段故事,故事可以多种多样,这取决于改编者、想象者的理解和意向。从这种意义上讲,《华山畿》给其他民间文学形式和作家文学提供了原始素材,提供了情感、人物、情节上的启迪。如今我们仍能在多种艺术形式中看到《华山畿》的影子。
(三)《华山畿》启示人们反思现实情感
关于《华山畿》,《古今乐录》中记载了一段传说: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1]669
华山畿的故事在元代林坤编著的《诚斋杂记·华山畿》中也有记载,前半部分的叙述和《古今乐录》中记载没有太大出入,然而末尾变为“棺应声开,女入抱之,遂活。两家相庆,配为夫妇”。化悲为喜,将其演绎成一出喜剧。
无论哪个版本的故事,都显示出对爱情的坚贞。“华山畿,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很容易让人想起《鼓吹曲辞·铙歌·上邪》里那首女子对情人抒发的誓言:“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归根结底,《华山畿》等一系列南朝民歌流传至今的最重要原因是它们反映了最真实、最直接的情意,这便是民歌的真实性。人们可以可以从中找到久违的共鸣,唤醒尘封已久的对单纯情感的审视和敬畏。《华山畿》不仅告诉人们爱情本真的模样,也在启示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态度和方式。
三、结语
《华山畿》字字珠玑,情深意长。这其中,有爱的温情和热度。爱,不仅仅是爱情,更是广义的宽泛的爱,给人们提供精神支柱,让人们在日常的奔波中体味到丝丝暖意和希望,让人们在物质生活出现变故时,依然能够坚韧淡定地生活下去,成为一个饱满的、立体的存在。
《华山畿》的意义在于它印证了民间文学的口传性、集体性、传承性、变异性以及情感的真实性,启迪和丰富了其他艺术形式,启示今人反思现代的情感质量,反思市场经济时代的爱情观,教会人们正视内心、尊重感情,告诉人们怎样对待爱情和生活才算真正活过。
[1]郭荗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张紫晨.歌谣小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4]胡适.白话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9.
[5]段宝林.民间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朱自清.中国歌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7]王运熙,王国安.国学经典导读之乐府诗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
2014-10-02
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 (09SG07)。
宋 旭(1991- ),女,吉林长春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戴从容(1971- ),女,吉林长春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I206.2
A
2095-7602(2015)01-0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