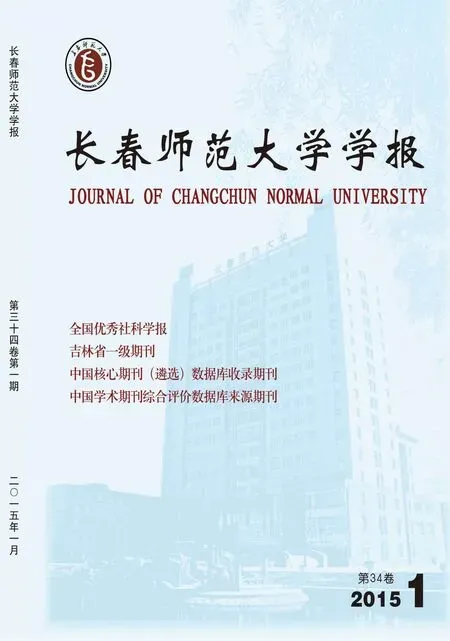翻译中的性别视角
——小说《名利场》汉译个案研究
2015-03-20陶书敏
陶书敏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理科学系,安徽 合肥 230051)
翻译中的性别视角
——小说《名利场》汉译个案研究
陶书敏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理科学系,安徽 合肥 230051)
本文基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从性别立场、性别刻板印象和双性同体三方面对比分析了小说《名利场》的译者荣如德和谢玲在翻译中的性别化处理方式,从而进一步揭示性别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
性别立场;性别刻板印象;双性同体
“社会性别”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强调人一生下来就有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作为专业术语由美国学者盖尔·卢宾首次提出,并被定义为“一种由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是性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1]。换言之,生理性别强调男女两性间的自然差异,社会性别指社会文化建构的性属差异。社会性别是由后天的社会文化环境所造成的对不同生理性别的角色定位、社会分工、心理期待和行为规范的综合表现。“社会性别”不仅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概念,还被女性主义学者广泛运用在人文、社科学术领域,发展为与各个学术领域相互兼容又自成一体的理论分析范畴,自此社会性别理论形成。
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翻译中的性别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目前,翻译中的性别研究主要从两点切入:其一,梳理和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起源、内容、代表观点以及主要翻译策略和翻译实践,如李红玉的《女性主义翻译的先锋———芭芭拉·戈达尔德》[2];其二,将西方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单独提出来,从译者的性别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国内的翻译实践,如曾文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以祝庆英〈简爱〉中译本为例》[3]。
《名利场》是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1811-1863)的代表作,小说以贝基和爱米莉两位女性人物为线索,以轻松滑稽的口吻讽刺了十九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虚伪奢侈。本文选取小说中涉及到两性关系的部分文本,选择荣如德(男)和谢玲(女)两译者的汉译本和原作进行比较,探讨翻译文本中的性别印记。
一、性别立场
在涉及到两性关系问题时,站在哪一边说话,是我们考察作者和译者性别立场的依据。作为男性作家,萨克雷在《名利场》中跨越了自身性别的藩篱,刻画了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充分展示了创作时的双性视角以及在不同性别角色间自由转换的功力。然而,以下两个例子仍显露出了作者的男性立场。
例1:We are Turks with the affections of our women...and they obey not unwillingly, and consent to remain at home as our slaves—ministering to us and doing drudgery for us.[4]185-186
荣如德译(以下简称荣译):我们象土耳其人那样对待女人的感情…….而她们也心甘情愿地服从,乖乖地待在家里当我们的奴隶——伺候我们,供我们役使[5]181。
谢玲译(以下简称谢译):对于女人的感情,我们和土耳其人一样,总是强迫她们恪守我们定下的规矩。……而这些女人,也总是心甘情愿地做男人的奴仆,呆在家里伺候大老爷们[6]207。
例2:Nor Mrs. Amelia at all above the pleasure of shopping, and bargaining, and seeing and buying pretty things. (Would any man, the most philosophic,give twopence for a woman who was?)[4]283
荣译:同样,乔治. 欧斯本太太对于逛商店、看橱窗、讨价还价、买漂亮衣服也决不是毫无兴趣。(倘若真有哪个女人对于这一切全然不屑一顾,恐怕世上任何男人——即便是最有哲学头脑的——都不愿花两便士要她。)[5]269
谢译:爱米莉娅也并不是个超凡脱俗之人,她也喜欢逛商店,讲价钱,看漂亮东西,买漂亮东西[6]307。
例1关于两性关系的论述中,男性译者荣如德秉承了原作者的性别立场,即从男性的立场出发,把“我们”(we)看作主体,“她们”看作客体。基于忠实的原则,女性译者谢玲在翻译开始也遵循这种立场,其后却将句末两个“us”分别翻译成“男人”、“大老爷们”而不是“我们”,从第一人称转向了第三人称,这一改动与简洁行文相违背,“大老爷们”的意象更属于不必要的添加。例2 原文和荣如德的译文中,都有将女性看作可供自由买卖的物品的描述,这种将女性对象化的表述激起了女性译者的强烈反抗,直接在译本中删除。女性译者在翻译中做的这些明显的改动,并非在语言理解上出了问题,也不是因为翻译技巧的差异,从性别立场上分析更为合理。在性别关系中,男女两性互为他者,绝对中立的性别立场几乎是不存在的。英语原文的表述体现了将女性视为客体、买卖“对象”的男性立场,能让男性译者自然或无意识地接受,却令女性译者焦虑。出于忠实的标准,译者的女性立场受到了压制,却又不能完全认同原作者的男性立场,只能通过改写、删除甚至重写等方式释放译者压抑的自我。
二、性别刻板印象
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是指人们对于不同的性别身份产生的固定和笼统的看法,是社会对刻板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预设。和任何固有的观念、习俗一样,性别刻板印象对人们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
例3:“Serve him right,”said Sir Pitt;[4]75
荣译:“那是这狗x的活该!”皮特爵士道[5]76。
谢译: 只见皮特爵士接着说:“活该!”[6]86
例3选自瑞蓓卡写给爱米莉娅写的信中。这句话是以瑞蓓卡的口吻模仿皮特爵士谈论一个付不起租税的老佃户,骂他活该。根据后文“‘him and his family has been cheating me on…’,Sir Pitt might have said ‘he and his family’but…”[4]75瑞蓓卡的主要目的是指出男爵(baronets)说话时的语法错误,并未说其语气粗鲁、口带脏字。与谢玲直译成“活该”不同,荣如德将原文的“Serve him right”翻译成“那是这狗x的活该”。传统汉语文化对男女两性的刻板气质作了不同的预设,女性说话举止要温柔委婉,很少口出脏字,而男性则可大大咧咧,咒骂或口出脏字是家常便饭。本例中,男性译者忽视了前后文的语境,增加了男性常用的咒骂语言,体现了汉语文化中男性的刻板印象对译者造成的影响。
例4:…and so I am tempted to think that to be despised by her sex is a very great compliment to a woman.
荣译:……因此,我情不自禁地认为,被别的女人瞧不起实在是女人的一大荣耀。
谢译:……所以我认为,同性之间的鄙视其实是一种最高的恭维与赞美[7]。
例4体现了作者对女人善妒这一刻板性别印象的接受和认同,男性译者荣如德自然地接受了这一认同,并用翻译传递下去;而女性译者谢玲显然无法默认这一偏见,所以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处理:将“善妒”这个缺点重新回归人性的缺点中。正如谢译所展示的一样,并非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妒忌同类,而是人性使然,同性相斥,相互鄙视是因为相互嫉妒。在此,女性译者谢玲跳脱出“女人善妒”这种性别刻板印象的制约,对原作品中的男性单一视角作出了公然反抗,体现了社会性别意识的觉醒。
三、双性同体(Androgyny)
“Androgyny”这个词由表示“男性”的前缀“andro”和表示女性的后缀“gyny”组合而成,源自生物学上的雌雄同株以及希腊神话中的雌雄同体现象。翻译中的双性同体指译者在翻译时具有双性视角,即译者既要摆脱自身性别限制,又能有意识地自由转换性别视角,并扮演好作者的性别角色以及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性别角色。
例1和例4是作者以第一人称作出的评论,译者扮演好作者本人的角色即可;例2 是作者以第三人称叙事后又跳脱出来以第一人称加以评论,显示了其男性立场。例3是作者以瑞蓓卡的口吻转述皮特爵士的话。在扮演作者本人角色时,荣如德坚持了原作的男性立场,而谢玲显然无法完全投入到作者本人的性别角色中,通过改写、删除改变了原作的性别立场;在反串扮演瑞蓓卡时,荣如德受到了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没有抓住瑞蓓卡转述的男性话语的重点所在,形成了超额翻译。
双性同体是文学的性别理想,是女性主义追求两性平等和谐的理想诉求,并非衡量翻译好坏的标准。翻译中的“双性同体”只是在性别维度忠实原作的策略。翻译并非原创,文学翻译的唯一标准是“忠实完整地传递原作的信息”,这也是译者的责任[8]。译者只能忠实再现原作者的单一视角,扮演好作者的性别角色。
具备了“双性同体”意识的译者,如伟大的作家一样,既意识到了男女性别差异的存在,又能克服自身性别的局限,自由进出于不同的性别角色间,成功地扮演好作者的角色和作者笔下人物的性别角色。本研究中的两位译者,无论是由于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还是出于译者自身性别意识的制约,在本文选取的几个翻译文本中,并未自觉地运用“双性同体”的策略以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作。
四、结束语
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对比分析了男性译者荣如德和女性译者谢玲对小说《名利场》涉及性别问题的文本翻译,发现性别立场、性别刻板印象均对翻译造成一定的影响。“双性同体”并非文学翻译的最终目标,而是为保证文学翻译在性别纬度上忠实于原作而对译者提出的理想诉求。
[1]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98:81.
[2]李红玉.女性主义翻译的先锋——芭芭拉·戈达尔德[J].2009(3):62-67.
[3]曾文.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以祝庆英《简爱》中译本为例[D].长沙:中南大学,2007.
[4]Thackeray. W. M. Vanity Fair[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5]荣如德,译.名利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6]谢玲,译.名利场 (上、下)[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
[7]陶书敏.翻译与性别——《名利场》翻译中的性别视角[D].合肥:安徽大学,2010.
[8]周方珠.文学翻译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4.
A Gender Perspective in Translating——A Case Study on the Chinese Versions ofVanityFair
TAO Shu-min
(Basic Department, Anhui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stitute, Hefei Anhui 230051, China)
Based on the gender theory, this thesis has analyzed the different gendered attachments between Rong Rude and Xie Ling,who are the translators of the novelVanityFair, respectivel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gender position,gender stereotype and the androgyny, so as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gender in translation.
gender position; gender stereotype; androgyny
2014-06-12
陶书敏(1982-),女,安徽舒城人,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文理科学系讲师,硕士,从事应用语言学及翻译研究。
H059
A
2095-7602(2015)01-009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