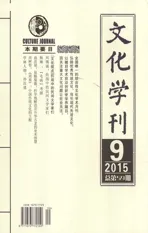从民俗语言学到语言民俗学的转向性探索
——简评曲彦斌先生的《语言民俗学概要》
2015-03-20胡正裕
胡正裕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从民俗语言学到语言民俗学的转向性探索
——简评曲彦斌先生的《语言民俗学概要》
胡正裕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曲彦斌首倡的民俗语言学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然而语言民俗学作为民俗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可谓仍处于起步阶段。学科名称的选择关联着学科定位问题,曲彦斌新作《语言民俗学》反映了作者近期关于民间语言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的最新探索。他在该领域著述颇丰,多年来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该书的出版可谓其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转变与超越。该书首次旗帜鲜明地以“语言民俗学”作为书名,具有开创性意义。全书共分八章,分别探讨了语言民俗学的分支领域:语言民俗学原理、民俗语汇、社会生活中的言语习俗、民俗语源、民间隐语、市井语言习俗、方言、古代民俗语言典籍评介等。
民俗语言学;语言民俗学;学术转向
作为民俗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语言民俗学可谓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如同时存在着“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两个学科名称,在进行语言与民俗的交叉研究时,也同时存在着“语言民俗学”与“民俗语言学”这样一对名词,所不同的是,“经过一部分学者大半个世纪的努力,语言人类学已经有了基本定位”,[1]而关于语言民俗学的概要性专著却才刚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术语之争还有“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它们研究主旨的不同。社会语言学的目的是联系社会进行语言研究,其重心是在语言上的,是为了促进对语言的解释与了解;而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却是社会学式的,语言只是被用作认识社会的一种手段,其指向不是要研究语言本身,而是语言背后的社会。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一句话:“一个新词就像是一粒新鲜的种子,播在讨论的土壤里。”[2]学科名称的选择与学科意识的关系非常紧密,是叫做“语言民俗学”还是“民俗语言学”,关联着学科定位问题。曲彦斌先生新作名为《语言民俗学概要》(大象出版社,2015),反映了作者近期关于民间语言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的最新探索。
曲先生早在30年前即已从事语言民俗或者说民俗语言的研究,著作颇丰,在该领域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本书的出版可谓其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转变与超越。如作者在序言(前言)中所述,正是多年的“心结”,促使作者完成这项事业。
出于“语言与民俗双向研究”的学术构想,曲先生先行以构建“民俗语言学”为主。他的《民俗语言学发凡》被誉为开创民俗语言学的第一篇论文。此后数十年曲先生孜孜不倦地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在《民俗语言学》初版的绪论中他说:“民俗语言学,综合运用民俗学、语言学的有关资料、观点和方法,结合两门学科的多种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及成果,对一些社会民俗事象与语言现象之间相互密切关联的本质、规律等,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科学的解释;既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民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人类文化科学的一种综合性较强、交叉度较高的双边科学。从某种意义而言,又可视之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因为,语言、民俗及民俗语言学都是人类社会的传承现象,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而社会语言学又是‘指将语言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应用于研究社会语言的学科总称’。两者是一种‘近亲’关系。”[3]曲先生同时又提出:“民俗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原则上说,同社会语言学基本相似,即主要是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4]据此,我们似乎可推知曲先生早期的研究取向是偏向于语言学的。
在《民俗语言学》(增订版)的绪论中曲先生则明确指出民俗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双向性”,并将其学术思想修正为“民俗语言学不只从语言研究民俗,从民俗研究语言,更主要的是以民俗语言文化为研究对象,因而,就难以像语言社会学属社会学分支学科、社会语言学属语言学的分支学科那样,简单地按此命名习惯将民俗语言学理解成语言学分支,认为语言民俗学是民俗学分支学科。”[5]然而,“双向取向”对于习惯了定位于某一个学科的大部分学者来说是很难获得认同的,学科取向通常只是单向的,所谓“跨学科”其实还是以某一个学科为主要阵地的。
曲先生在《民俗语言学》(增订版)中曾提到:“如今,还有一个老问题,需要重新说明。那就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名称的‘正名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北师大钟敬文先生的一位研究生向我转达钟老的意见,‘语言民俗学’才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老实讲,我一时颇感为难。因为,按照习惯说法,‘语言民俗学’是从语言学视点和语言材料研究民俗学和民俗的;‘民俗语言学’则应是从民俗学视点和民俗材料来研究语言学和语言。然而,用什么样的叫法来表示我们现实的这种双向、互动的学科呢?”[6]他在《语言民俗学概要》中重提这一十几年前的“学术心结”,并紧接着表明:“几十年来始终从事‘语言与民俗’以及‘民俗语言学与语言民俗学’的双向研究,未肯偏废。只不过,先行以构建‘民俗语言学’理论框架为主,同时也在进行‘语言民俗’和‘语言民俗学’的研究与积累。”[7]从“先行”二字可看出曲先生今日的学术转向是在规划之中的。
曲先生三十多年从事语言与民俗研究的学术路径可以归纳为:从偏向于语言学到“双向互动”再到偏向于民俗学。曲先生是语言学与民俗学进行联姻的“大红娘”,成功地完成了“学术嫁接”,其首创之功昭著。其研究方法以历时的文献资料为主,同时,以语境为取向的田野作业研究方法并未着力地使用,但这并不影响曲先生的主要功绩,因为术业有专攻,学者不可能面面俱到。
如曲先生本人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出于对学术的敏感性,便开始着眼于语言与民俗问题的钻研,迄今已有三十多年。通过不断的求索、耕耘、积累与修正,曲先生为民俗语言学这一学科构建了完整的框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乎涉及民俗语言学的所有领域”[8],其广博性无可置疑。曲先生还发表了《副语言习俗》《民间秘密语与民族文化》《隐语行话与民间文化》等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杂纂七种》(校注)《副语言习俗》《中国民间秘密语》《中国隐语行话》《神秘数——中华民族数文化》《俗语古今——中国俗语学》《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俚语隐语行话词典》《中国民俗语言学》《民俗语言文库》等著作。
学术无止境,已有的硕果不是止步的理由,花甲之后,曲先生的学术热情更是愈燃愈烈,再一次一马当先,努力完成老一代民俗学家的期待以及曲先生自己的“学术心结”,领衔撰写了《语言民俗学概要》这部让学者们眼前一亮的新著。
该书共八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阐述了语言民俗学基本原理、学术渊源和基础概念。第二章聚焦于民俗语汇研究的学术史。第三章着眼于社会生活中的言语习俗,涵盖了较为广泛的“生活世界”,分别涉及姓名、亲属称谓、绰号、禁忌与口彩、网络语言民俗、民间流行习语与社会时尚等。第四章以“措大”的民俗语源、“锦标”词系以及“保镖”词系为例,着重解析了民俗语言化石和民俗语源的问题。第五章的主题为社会方言中的民间隐语行话。第六章转为市井语言习俗例说,分别阐述了俗语雅趣、新俗语与俗语词典、“吉祥号码”与数字崇拜、市井传统商业招徕市声、饮食业的传统招徕响器(饧箫、击馋和引孩儿)、数文化中的市语、曲艺小品等。第七章关注方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保护,明确指出方言土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载体和传承工具。在第八章中,由曲先生引领的青年学者们不仅向我们推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中的十部民俗语言珍稀典籍专著,充分展示了他们对这十部典籍的研究成果,这对语言民俗学研究者颇有参考价值。
对于语言与民俗的交叉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成果,比如黄涛的《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丁石庆的《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王志清的《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等。曲先生在书中表示,期待更多的学者积极地参与构建民俗学的重要子学科——语言民俗学。该学科的繁荣,将是曲先生最大的心愿。
[1]纳日碧力戈.语言人类学[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2.
[2][英]维特根斯坦著,[芬]冯·赖特,海基·尼曼编.维特根斯坦笔记[M].许志强,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
[3][4]曲彦斌.民俗语言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15.
[5][6]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增订版)[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15.
[7]曲彦斌.语言民俗学[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
[8]刑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王 崇】
H0-05
A
1673-7725(2015)09-0247-03
2015-08-27
胡正裕(1983-),男,浙江文成人,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