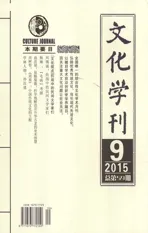莫言小说中的鬼魅形象
2015-03-20覃治华
覃治华
(吕梁学院中文系,山西 离石 033000)
莫言小说中的鬼魅形象
覃治华
(吕梁学院中文系,山西 离石 033000)
鬼魅叙事如幽灵般一再附身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宏大叙述中,并由此勾连起与之相关的种种世态,这种与现代启蒙叙事底色殊异的创作取向,无论是出于作家的理性反思,还是无意识创作,在提倡多元现代性、重视文化传统差异的今天,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本文着重就莫言小说中的鬼魅形象进行详细分析。
莫言;小说,鬼魅
在新时期作家中,莫言是一位擅长讲述鬼魅故事的作家。莫言的故乡高密离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的故乡不过几百里,谈鬼说魅的传统与原始恶劣的生存环境铸就了作家童年时期“对鬼的恐惧”。成年之后的追忆冲淡了对鬼魅的原始恐惧,而多少带有一些审美味道。正是借助鬼魅故事或回忆提供的思维方式与叙述视角,莫言在小说创作中融错觉、夸张、变形、荒诞、象征、反讽于一体,创造了天马行空而又韵味无穷的艺术世界。
莫言早期涉笔鬼魅的作品致力于一种奇幻氛围的营造,《草鞋窨子》讲述荒诞不经的奇遇、鬼故事成为乡民打发漫漫长夜的唯一方式,被压抑的年代与力比多在口头的鬼故事或实际上装神弄鬼的举动中得到释放,读来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奇遇》毋宁说是作家自己“走夜路”之恐惧情绪的释放与艺术转化,带有“志怪”的流风余韵。《夜渔》则更离奇,“我”与九叔于秋夜在一片水泽捉蟹,九叔布置好之后却变成了凝然不动、目光绿幽幽的吹哨人,“我”则在月光的照耀下,下河去追随一枝洁白的荷花,后来又遇到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年轻女人,她不仅帮我捉满两麻袋螃蟹,还留下神秘的偈子。更为神奇的是,九叔实际上却与家人彻夜都在寻找走失的“我”,而“我”二十五年后的奇遇则恰好印证了那神秘女人留下的偈子。拉美作家卡彭铁尔说过:“神奇是现实突变的必然产物,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这种现实的发现给人一种达到极点的、强烈的精神兴奋”,[1]作为作家对客观现实的突变、照亮和夸张。《夜渔》展现了物质与情感双重匮乏时代,“我”对于人间美好事物与美好感情的憧憬与渴望,而神秘的因缘际会也突出了对于无常人生的某种宿命感。
莫言在访谈中否认自己写这些神神怪怪的故事是在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就有这种神鬼的故事和恐怖体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曾对我的写作有帮助,但不在鬼怪上,而在别的方面。”莫言的这番表白可谓诚实。虽然灵魂不灭、人鬼相续的信仰已不再具有昔日的赫赫威力,但鬼魂跨越肉身及时空的界限,执著于一己爱恨情仇的偏执却一直是中国文学热衷于表现的题材,人鬼之恋与厉鬼复仇也可算是中国文学传统的母题之一。这些在莫言的小说中也是经常出现的情节。《白棉花》与《司令的女人》结尾都隐约有含冤而死的主人公化为鬼魂来惊扰威吓活人的复仇意味。《白棉花》女主人公方碧玉不仅姿色出众,且具有打抱不平、敢做敢当的侠女风范,在与乡村政治权力联姻还是忠于自己的爱情抉择中,她大胆选择后者,但最终也受到权力与世俗道德的惩罚。小说的后半部分,即方碧玉和李志高进入热恋阶段,其不祥的爱情弥漫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写得鬼气森森、阴冷袭人,既预示故事的悲剧结局,也传达方碧玉对这“非法”爱情的绝望之感。[2]遭受村支书的羞辱与李志高的抛弃之后,方碧玉死于一起清花机事故之中,死后爆料她“丑闻”的孙禾斗和铁锤子同时都遇见了沾满鲜血前来复仇的方碧玉。侠肝义胆的爱情追求在诗学正义的旗帜下击溃了人间权势的狂妄与道德惯例的残酷,作者的叙事情怀及价值取向在厉鬼复仇的情节中不言自明。不仅如此,实在不舍让方碧玉死去的叙事者,还安排另一个同样阴森但留下活路的结局:昔日工友多年后在火车上向“我”讲述了一个方碧玉掘尸诈死、远走高飞的离奇故事,并信誓旦旦声称自己在新加坡见过一个“与方碧玉一模一样”的贵妇人,开放式的结局不仅为读者留下广阔的遐想空间,也是叙事者对方碧玉精魂不死的致敬。
莫言借“鬼之化”而书写国家历史的煌煌巨著是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小说从“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的佛教教义出发,以土改中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依次轮回到人间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的经历,将1950年1月1日至 2000年年终这50年的历史变动尽收眼底,在西门闹一己的轮回中,隐约透露出作者对于历史轮回的感慨与无奈。意味深长的是,无论是地主西门闹紧追潮流的后代西门金龙、西门欢,还是长工蓝脸固守传统的后代蓝解放、蓝开放,在五十年时光的拨弄之下,都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小说中的蓝色是一种属于鬼魅幽灵的颜色,[3]“他们的肤色像是用神奇的汁液染过,闪烁着耀眼的蓝色光芒”,西门闹捡来的孤儿也是蓝脸,“左脸上有巴掌大的一块蓝痣”。他后来成为农业合作化中的最后一个单干户,像一个土地上的幽灵喜爱在月光下种地,充满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魂魄相依的隐喻色彩。其子蓝解放与其孙蓝开放不仅遗传了蓝脸的生理特征,也遗传了他抗拒历史潮流的性格特征。高贵而神秘的蓝色赋予小说超越的视角,借助这一视角,表达了作者对20世纪后50年间中国历史的反思与盲目追逐潮流的批判。
[1]阿莱霍·卡彭轶尔.这个世界的王国[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86.59.
[2]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M].秦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75.
[3]莫言,杨扬.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A].杨扬.莫言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6.
【责任编辑:周 丹】
I207.42
A
1673-7725(2015)09-0169-02
2015-06-15
覃治华(1981-)男,山西交城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