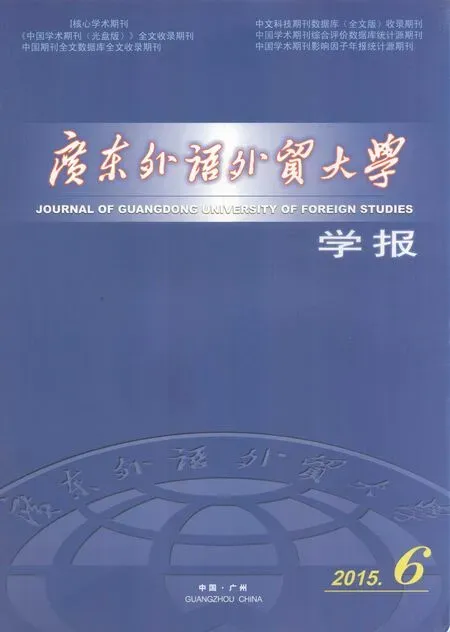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翻译论争
2015-03-20任淑坤
任淑坤
(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五四时期,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主力军。而翻译活动是他们实现理想的途径之一。在此期间,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有选择地介绍进来。据阿英统计,1917~1927年间出版译作共225种 (阿英,1981:357-360)。与晚清时期不同,五四时期的译者组织性更强,多以社团为单位,形成了多元化的译介倾向。也正因为存在诸多的“不同”和多元化,各社团之间围绕翻译曾产生了多次论争,涉及面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当属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论争。目前关于这两个社团翻译论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理论使用:如伦理学批评、操控理论;2.论争原因的分析:包括两个社团文学建设理路、翻译观、翻译方法、译者个性气质几个方面的差异和对文坛话语权的争夺等。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翻译论争的认识。但是理论使用稍有不慎就会将史实限制于理论框架之中,而遮蔽论争承载的诸多因素。又由于论争涉及团体两方,对原因的分析也多采用二元对立的格式:如为艺术和为人生、归化和异化 (尽管当时论争并未使用这样的字眼)等。发掘细读两个团体借以发声的书信、文章,缕析论争的过程和焦点,无疑会弥补一些缺憾。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翻译论争的焦点有三个。
一、翻译的功用与地位
1920年郭沫若致信《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李石岑称:“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翻译底价值,便专就文艺方面而言,只不过报告读者说:‘世界底花园中已经有了这朵花,或又开了一朵花了。受用罢!’他方面诱导读者说‘世界花园中的花便是这么样,我们也开朵出来看看吧!’所以翻译事业只在能满足人占有冲动,或诱发人创造冲动为能事,其自身别无若何积极的价值。” (郭沫若,1992:187-188)郭沫若的愤慨事出有因。1920年10月10日的《学灯》依次登载了周作人译《世界的雷》、鲁迅作《头发的故事》、郭沫若作《棠棣之花》、郑振铎译《神人》,郭沫若对编辑将自己的剧作排在周作人、鲁迅之后很不满意,便有了以上的话 (廖超慧,1997:440)。郭沫若认为,这种状况会打击作者的积极性,助长“读者 (俗人)”轻视艺术的不良趋势。他强调指出,翻译作为一种附属事业,不宜凌驾于创作、研究之上。郭沫若对翻译的这种看法,激起了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不满。
郑振铎就此信发表了回应文章——《处女与媒婆》,认为翻译的性质固然有些像媒婆,但翻译的功用却并不止于此,翻译“对于中国文学的创造,自然也很有益处。……所以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了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们对于人们的最高精神上的作用是一样的。现在不惟创作是寂寞异常,就是翻译又何尝是热闹呢?世界文学界中有多少朵鲜明美丽的花是中国人已经看见过的?”(郑振铎,1921)
郭沫若在《文学旬刊》上回信反驳,他说自己所谈的翻译界状况,不仅仅指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只是一个例子罢了,“翻译须寓有创作的精神,这句话是我所承认的,并且是我愿意极力主张。翻译绝不是容易的事情;要翻译时有创作的精神则对于作者的思想和环境须有充分的研究。”郭沫若认为“媒婆终是不可少的,只要不狂不暴,我也是极尊重的;但是在媒介以上对于翻译事业要求夸张的赞词,我却踌躇了”(郭沫若,1921)。郭沫若并不认为翻译就比创作容易,他对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流露出翻译比创作容易的意思进行了批评,也批驳了耿济之“中国人还说不到创作”的说法。
郭沫若与郑振铎的论争,涉及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翻译的媒介作用。郭沫若将翻译比作媒婆,对翻译怀有鄙夷的态度,遭到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反对。郑振铎等对郭沫若的回应中提到“翻译的性质固然有些像媒婆,但翻译的大功用却不止于此”(郑振铎,1921);(2)翻译中的创造精神。郑振铎认为翻译的作用与创作是一样的,是人类精神交流的通途。郭沫若也承认翻译中的创造性,要批判的是那些字典万能、不能坚守阵地的译者。二人的出发点可谓大相径庭;(3)翻译与创作的地位。郭沫若虽然承认翻译中具有创造性成分,但他将翻译置于创作之下。郑振铎则认为,当前翻译与创作事业一样寂寥,所以翻译活动应该继续受到重视。他强调,文艺应该包括创作文学和翻译文学,应将创作和翻译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郑振铎,1922);(4)译者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郭沫若认为,译者应该对作者的思想环境有充分的研究,不能欺人欺己,“只看书名人名大可受社会的欢迎,便急急忙忙抱着一本字典死翻,买本新书来滥译,有的连字义的对针从字典上也还甄别不出来,这如何能望他们译得不错呢!” (郭沫若,1923)对此,郑振铎并无异议,他也主张不能专捡英美杂志上最新的作品来译,“自文学在英美职业化了以后,许多作家都以维持生活的目的来写他们的作品,未免带着铜臭,且也免不了有迎合读者的心理的地方。”(郑振铎,1921)
郑、郭之间关于翻译的功用与地位的争论,以郭沫若的噤声而结束。为了消除郭沫若将翻译比作媒婆在“大力提倡‘女子解放、婚姻自由’的年代”所具有的“鄙夷的感情色彩”(陈福康,2000:258),郑振铎做了另外一个比喻,把翻译比作“奶娘”:“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是做什么‘媒婆’,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更进一步有类于‘奶娘’。……我们如果要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至少须于幽暗的中国文学的陋室里,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这种开窗的工作便是翻译者所努力做去的!”(郑振铎,1923)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其中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体现着不同的民族心理特质。民族文化中的独异性为翻译设置了障碍同时使得翻译有了存在的必要,翻译使得民族文化得以与世界文化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的功用是可以用“媒”来概括的。关于翻译为“媒”、为“诱”的说法,钱钟书就曾说过,翻译“是个居间者或者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 (钱钟书,1984:268)。钱钟书所讲翻译“媒”和“诱”的作用,与郭沫若所说的“媒婆”作用并无本质区别。所不同的是,钱钟书对这一作用十分欣赏,高度评价翻译的“媒”介作用。而郭沫若用这个比喻旨在阐明,翻译不该与创作平起平坐,甚至高于创作。
二、翻译的动机与效果
1921年6月,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上发表《盲目的翻译家》一文,认为不应追赶英美杂志的时髦。他指出,即便是“有确定价值的作品也似乎不宜乱译。在现在的时候,来译但丁的 (Dante)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韩美雷特》(Ham let),贵推 (Geothe)的《法乌斯特》(Faust)似乎也有些不经济吧。”(郑振铎,1921)郑振铎的这段话,埋下了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再起争端的种子。次年,读者万良濬致信《小说月报》,指出这些文学名著“虽产生较早,而有永久之价值者,正不妨介绍于国人。” (万良濬,1922)茅盾在同期的《小说月报》回复说,“翻译《浮士德》等书,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且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轻重缓急。”郑、茅的这一看法,激起了郭沫若的不满和反驳,也由此引发了是否应该翻译这些名著的讨论。
郭沫若发表了《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提及自己零星翻译过《浮士德》,田汉正在翻译《哈姆雷特》。在翻译活动中,介绍家指的就是译者、翻译家。郭沫若重点阐述了译者的“翻译的动机”和“翻译的效果”。翻译的动机是因为翻译家基于对作品的研究和理解,视其表现和内涵如己出,涌起创作的冲动,从而迫不得已地迻译。翻译家具有了这种动机,“他所产生出来的译品,当然能生出效果,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这种翻译家的译品,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切要的,无论对于何项读者都是经济的”(郭沫若,1959:134-139)。
茅盾发表了《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予以回应,认为郭沫若阐述的是主观的动机,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客观动机,即一件作品是否“适合一般人需要”,是否能“足救时弊”?茅盾倾向于文学的使命是“为人生”的,他从正面阐明自己的立场:“我觉得创作者若非全然和他的社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社会的同情的,他的创作自然而然不能不对社会的腐败抗议。我觉得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又从反面反驳了郭沫若:“有些作家,尤其是空想的诗人,…… (对于)扰攘的人事得失,视为蛮触之争,曾不值他一顾。……但如果大部分的其余的人,对于扰攘的人事得失感着切身的痛苦,要求文学来做诅咒反抗的工具,我想谁也没有勇气去非笑他们。”(茅盾,1922)
客观与主观的分野是相对的,细读郭沫若与茅盾的观点,虽各有侧重但其中也有重合。从翻译的动机来看,茅盾从现实社会的感受着眼,主张选择那些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郭沫若则从文本开始,选择能引起译者的共鸣与创作冲动的作品,既可以是为人生的,也可以是浪漫的。郭沫若本人当时是倾向于后者;再从翻译的效果来看,两类译者的共同观点,就是文本必须能引起译者的同情,激发作者创作的欲望。而在翻译效果上,分歧却十分明显。郭沫若强调“更进而激起其研究文学的急切的要求”,而茅盾则寄希望于文学作为“诅咒反抗的工具”,“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但不可否认,作为诅咒和反抗工具的文本同样可以具有艺术性而“激起读者研究文学的急切需要”,而激发读者文学兴趣的译本同样可以“刺激将死的人心”。茅盾所强调的客观动机与郭沫若强调的主观动机,在引起译者共鸣、激发创作冲动处汇合。
三、翻译批评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围绕翻译批评的论争有两次,一是关于文学研究会出版的唐性天译《意门湖》 (郭沫若译为《茵梦湖》)中的错误,二是关于郭沫若所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错误。
(一)关于唐性天译《意门湖》
1922年,郭沫若发表《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它》,指出唐译中某些单字译得不当,某小节“简直译得令人莫名其妙”,“是完全失败的”,“读了《意门湖》的一首译歌之外,以外的译文再也不想读下去了”。他对这首歌谣的翻译进行总结性评说:“我们相信译诗的手腕决不是在替别人翻字典,决不是如像电报局生在替别人翻电文。诗的生命在他内含的一种音乐的精神。至于俗歌民谣,尤以声律为重。……我始终相信,译诗于直译、意译之外,还有一种风韵译。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自是上乘。即使字义有失而风韵能传,当不失为佳品。若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艺坛之外了。”除了对歌谣的评论之外,他又挑出了42个唐译不妥之处 (郭沫若,1922)。以上文字并未脱离翻译批评的主旨,但郭沫若在行文中攻击“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惯用的手段是“藏名逆姓,不负责任”,“吞吞吐吐,射影含沙”,“人身攻击,自标盛德”,“挑剔人语,不立论衡”。
原本可以在心平气和状态下对译文进行的商榷,因为“投炸弹”似的言论而激化。茅盾与郑振铎在同期的《文学旬刊》分别撰文,回应郭沫若的批评。郑振铎在“通讯”栏中致信郭沫若,“你在《创造》中批评《意门湖》,很感谢。唐君的这个译本的译成,远在你们《茵梦湖》出版之前。我们手头既没有英译本,又未见注释完备的德、日对照本,所以有无错误无从知道……。你往往误会我们的‘伐异’及其他的一切,其实我们没有这种心思。我希望大家以后各自努力,不要作无谓的捣乱。批评,是应该做的工作,但应出以诚恳的态度,不谩骂,不作轻蔑的口气”(郑振铎,1922)。可以看出,翻译批评已经溢出了翻译质量本身。
(二)关于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
1924年,梁俊青致信《文学》周报,指出郭沫若所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错误问题,并说“这本书实在不能说是水平线以上,我很希望他能够再校正一些才可出版发行”(梁俊青,1924)。在下一期的《文学》周报,又登出梁俊青的来信,认为德文印刷错误太多,怕会影响读者的视听,又指出自己的一处判断错误。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说“这本书实在不能说是水平线以上”的话是不对的。
郭沫若就此致信梁俊青,对梁提出的问题作了解释,并承认书中的印刷错误的确很多,连标点在内恐怕有五百处左右。他做过两次勘误表,书局因怕影响声誉而“丢失”了。此信发表在《文学》周刊125期,同期还刊登了成仿吾就此事致梁俊青的信,认为梁俊青对郭沫若译文的批评“荒谬已极,即使他这几条的指摘完全无误,而他在篇首所列的浮词与在篇末断定这本译本不是水平线以上的翻译,实在不能说是有艺术良心之人的说话”,认为这是“艺术的良心死灭的一种表现”,是“现在这种不良教育的结果”。不但如此,他责备编辑,认为“编辑《文学》的诸君倒不能不多负一点责任,投稿总不免好丑不齐的,编辑的人当然要先检查一番,对批评一类的文章尤当注意。”(成仿吾,1924)成仿吾的言辞招致梁俊青的不满,他分别致信郭沫若和成仿吾,认为郭沫若的答复过于牵强,并继续与之展开讨论。梁俊青还公开了成仿吾给他的私信的部分内容,认为成仿吾态度一贯不好,徐志摩也因做文艺批评涉及到郭沫若的文句,遭到了成仿吾的“侮蔑”。(梁俊青,1924)成仿吾见此更加暴躁,“以骂人博有恶名的成仿吾,骂一个梁俊青还要费许多周折,还要向他赔不是么?”(成仿吾,1924)梁俊青回信,认为成仿吾的行为“完全是虚伪的做作,完全想用一种势力来压迫人。”(梁俊青,1924)
原本是梁俊青与郭沫若对翻译问题的讨论,继而转为成仿吾与梁俊青的纠缠与相互攻击,又因郭沫若致《文学》周刊编辑的一封长信转而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郭沫若在信中认为编辑的不负责任导致了“不负责任的翻译的横流”、“作家粗制滥造的倾向”和“青年的侥幸投机的心理”,认为《文学》周刊编辑不负责任、借刀杀人 (郭沫若,1924)。
这两次关于翻译批评的争论,都是以讨论翻译问题开始,以争论非翻译问题结束。对译文的讨论,反映出翻译界和读者对译文质量的关注,在客观上促使译者对译文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检查。在论辩过程中也凸显一些问题,如对待翻译批评的态度、编辑的责任等。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两个团体的宿怨使其成为一场护短与揭疮的混战。
四、论争之深层原因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关于翻译动机、翻译的地位、翻译批评的三次论争,在客观上促进了译者对翻译问题多层面的关注和思考。但我们也发现,论争往往以翻译问题发端,以纠缠于论辩双方的态度、措辞、恩怨而结束。个中原因,与创造社的精英意识不无关系。
创造社成员可谓留日学生当中的佼佼者,客观的精英地位造成了其主观的精英意识。创造社之成立与郭沫若等人的精英意识不无关联。负笈日本的郭沫若、张资平等人对中国文化生活颇为不满。郭沫若对《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的鄙夷毫不掩饰,认为那上面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张资平认为《新青年》“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因此,他们决定“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郭沫若,1979:37-38)。1921年9月,郁达夫发表《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也指出,“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象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可见,创造社在成立之初就抱有“战斗”的情怀。
创造社的成员在创业之初颇为艰难,《创造》季刊的销路也不好。鲁迅周作人等对创造社也持批评态度。初期创造社并没有得到太多喝彩声。创造社成员的精英意识与现实的边缘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处于文坛中心地位文学研究会的态度,以及从此开始的中心趋向运动。郁达夫在《艺文私见》中说: “真的文艺批评,是为常人而作的一种‘天才的赞词’。因为天才的好处,我们凡人看不出来,必待大批评家来摘发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丰城狱底,有绝世的龙泉;楚国山中,有和氏的美玉。”(郁达夫,1922:10)郭沫若也批评“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他们颇有的先入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郭沫若,1922:17)创造社的这些“举动”是向中心迈进的表现,这也决定了其与文学研究会的紧张关系。
郭沫若及其创造社成员的精英意识与中心趋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五四时期涉及创造社的几次论争。关于翻译的功用与地位、翻译的动机与目的、翻译批评的论争,其中掩盖着情绪、意气问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似关于翻译的论争会以纠缠于非翻译问题的混战而结束。这些论争客观上吸引人们对翻译问题的重视,提出了一些新的翻译观念,但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却未能深入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阿英.1981.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影印本)[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陈福康.2000.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成仿吾.1924.致郑振铎的信[N].文学周刊.1924-06-09(4).
成仿吾.1924.致梁俊青的信[N].文学周刊,1924-06-23(4).
郭沫若.1921.通讯[N].文学旬刊,1921-06-30(4).
郭沫若.1922.海外归鸿[J].创造季刊(1-1):3-19.
郭沫若.1922.《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它》[J].创造季刊(1-2):23-26.
郭沫若.1923.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J].创造季刊(2-1):33-43.
郭沫若.1924.通信[N].文学周刊,1924-07-21(2).
郭沫若.1959.沫若文集(10)[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郭沫若.1979.学生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郭沫若.1992.致李石岑[C].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廖超慧.1997.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
梁俊青.1924.致成仿吾的信[N].文学周刊,1924-07-07(4).
梁俊青.1924.评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N].文学周刊,1924-05-20(1).
梁俊青.1924.致郭沫若、致郑振铎的信[N].文学周刊,1924-06-16(4).
茅盾.1922.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N].文学旬刊,1922-08-01(2).
钱钟书.1984.林纾的翻译[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万良濬.1922.通信[N].小说月报(13-7):2.
郁达夫.1922.艺文私见[J].创造季刊(1-1):10-12.
郑振铎.1921.处女与媒婆[N].文学旬刊,1921-06-10(2).
郑振铎.1921.盲目的翻译家[N].文学旬刊,1921-06-30(2).
郑振铎.1922.本栏的旨趣与态度[N].文学旬刊,1922-05-11(3).
郑振铎.1922.通讯[N].文学旬刊,1922-09-01(4).
郑振铎.1923.翻译与创作[N].文学旬刊,1923-07-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