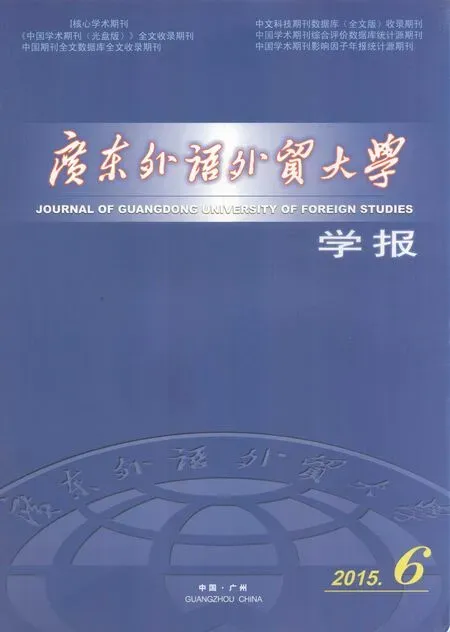阿根廷民族主义思潮对高乔诗歌研究的影响辨析
2015-03-20陈宁
陈 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广州 510420)
一、有关高乔诗歌起源及作者身份的分歧
高乔诗歌 (la poesía gauchesca)可定义为以生活在拉普拉塔河地区的高乔牧民 (los gauchos)作为主人公,描述其生活经历的叙事体诗歌。它秉承现实主义风格,着力刻画地域特色,并以模仿牧民的俚俗口语作为诗歌的语言风格。高乔诗歌出现于19世纪初期阿根廷独立革命运动前后,早期的代表作家有伊达尔戈 (Bartolomé Hidalgo),主要作品是以独立战争为题材的对话体叙事诗;30年代至50年代,即内战期间主要的诗人有阿斯卡苏比 (Hilario Ascasubi)和德尔坎波 (Estanislao del Campo),均以阿根廷草原的风土人情为描述核心。19世纪70年代,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创作了《马丁·费耶罗》 (El gaucho Martín Fierro)被认为是高乔诗歌的代表作品 (陈宁,2007)。
阿根廷文学评论界对高乔诗歌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20世纪10年代,先后有文学史家罗哈斯 (Ricardo Rojas)和诗人卢贡内斯 (Leopoldo Lugones)著文,认定高乔诗歌的代表诗人如伊达尔戈或者埃尔南德斯出生于高乔牧民,其作品是阿根廷民间八音节叙事诗的传承。20世纪30年代,博尔赫斯在《高乔诗歌》一文中指出,诗歌的创作者几乎全部出生于大地主家庭并投身于政治,是阿根廷和乌拉圭社会的精英阶层 (Borges,1932:179)。高乔诗歌是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仿拟牧民语言风格进行的创作,蕴含着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文化企图。
博尔赫斯的观点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认同。如有乌拉圭学者在《伊达尔哥全集》 (Obras completas de Bartolomé Hidalgo)的序言中指出:不应该将高乔诗歌 (poesía gauchesca)和民间诗歌 (poesía popular)混为一谈 (Praderio,1986:10)。民间诗歌及其代表格律罗曼司 (romance)由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引入,随着时间被匿名或属名的诗人们反复再创作,并且吸收印第安人的民间歌谣,其历史传统远比高乔诗歌悠久。而对于高乔诗人的身份问题,当代研究也能给予正视,承认伊达尔戈曾担任乌拉圭财政部长,埃尔南德斯不仅出生于阿根廷著名的政治世家,本人也被推举为上议院议员 (Sainz de Medrano,2010:16)。
引发这场关于高乔诗歌起源以及作者身份争论背后的动机耐人寻味:是什么令那些优秀的学者在研究中刻意忽略事实 (如诗歌作者的真实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以及身份),并且混淆文本与现实世界 (如混淆文学虚构人物与可证实或证伪的历史事件)的界限?将这类研究还原于产生它们的历史政治语境,就能理解其用心所在。
二、阿根廷民族主义思潮导致对高乔人再认识
19世纪40年代,在《法昆多》(Facundo Facundo.Civi-liza-ción y barbarie en las pampas argentinas)一书中,萨米恩托 (Faustino Domingo Sarmiento)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美洲的“文明与野蛮”论题。作品借为阿根廷地方割据军人法昆多·基罗加将军 (Facundo Quiroga)作传,运用类似文学虚构性的话语描述高乔人的游牧生活,并将其与所谓的“东方蛮族”进行类比。萨米恩托认为,高乔人是野蛮的化身,必需借欧洲文明将之同化并最终逐出阿根廷的历史舞台;同时,支撑高乔人生存的大庄园制度是野蛮的社会组织形式,必将随着工业化进程被文明的城市所取代。
萨米恩托于1858年当选为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在他的思想影响下,阿根廷模仿欧洲国家建立了民主普选制度;通过对南部印第安部落实施种族灭绝掠夺大量的土地;借助吸收欧洲移民、实施土地改革等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20世纪初期,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阿根廷成为拉美现代化和城市化最高的国家之一。高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人口结构中高比例的白人欧洲移民,使阿根廷成为最像欧洲的拉丁美洲国家。
然而,与欧洲的相似度却令阿根廷文化界开始担忧“民族性”的丧失,他们认为欧洲化正在给祖国带来灾难性的冲击,直接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困惑。民族主义者们宣称“阿根廷民族性处在危险之中 (La argentinidad estaba en peligro)”,令民族身份认同陷于危机的是“世界主义”:
我们每个人为了捍卫自己的民族,都应该与具有腐蚀性的侵略思想斗争,以传统为依托,来巩固我们尚为年轻的国家。世界主义曾经以人文哲学的形式影响了我们,它那似乎能实现的乌托邦梦想使得一些不够谨慎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眩晕。人们于是认为未来的社会就是种族的随意融合,以及未来的语言就是巴别塔之语。
所有构成民族的元素:语言、政治机构、品味和传统的观念,正深深经受着骚动。我们必须提防那些正逐渐销蚀阿根廷灵魂纯洁追求的物质焦虑。假如不以这种纯洁追求作为指引,所有国家的繁荣都建在沙砾之上。我们的传统被遗忘,这不仅仅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因为民族性也会受到威胁 (Gálvez,1944:38-39)。
这些言论的收录者贾维斯提出了“民族复兴的一代(la Generación de la Restauración)”的概念,指出生于19 世纪80年代左右的作家学者,在1910年纪念独立革命百年之际,共同致力于通过拯救传统来达到“民族复兴”伟大业绩 (Gálvez,1944:37)。在1909年出版的著作《民族复兴:教育状况报告》中,作者罗哈斯 (Ricardo Rojas)一再指出阿根廷民族正面临着外来文化的严重威胁并告诫:“我们不要再继续以那没有历史的世界主义和没有爱国精神的学校来自寻灭亡之路了”,必须“拯救”面临着异邦威胁的阿根廷的学校 (Rojas,1909:35)。
同一时代的阿根廷哲学家科恩 (Alejandro Korn)也对欧洲文明在阿根廷的影响提出质疑:“试问我们就只能将自己局限为欧洲文化的连体吗?我们还不感到厌倦吗?”;“罗哈斯曾经呼吁民族复兴,但不是简单地回归到过去或肤浅地缅怀开国元勋们,而是让蕴藏在我们民族脏腑深处的未知的力量获得新生”(Korn,1949:199)。
另一方面,阿根廷与西班牙在文化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20世纪初期西班牙的知识界也同样执着于塑造和探究“国民性 (la españolidad)”。1898美西战争的失败令西班牙失去了最后的三个海外殖民地,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同时,以英法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国家正在对传统农业国西班牙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不可阻挡的冲击。于是,哲学家乌纳穆诺 (Miguel de Unamuno)等知识分子在充满悲观的情绪中开始思索对于历史和民族性的思考。他们的观点之一是通过挽救传统来对抗“世界主义”,从而求得民族文化的更新 (regeneración)。与阿根廷知识分子通过恢复传统来复兴民族以及建构阿根廷民族性的思想相切合。一直与罗哈斯保持密切交往的乌纳穆诺在西班牙回应道:
罗哈斯所梦想的民族复兴大业,和所有的民族复兴一样——西班牙也正因为欧洲化的威胁而面临同样的问题——必须从学校开始;学校是培育阿根廷民族精神的摇篮,正如西班牙的学校是培育西班牙民族精神的摇篮一样。阿根廷恰恰是要依靠这个民族精神来寻求它的世界性 (Unamuno,1894)。
于是,当“野蛮”被“文明”消解殆尽之时,“文明”却产生了将“野蛮”奉为传统的冲动。在各种偶然或必然的因素作用下,高乔人此时成为“民族象征”,他们的精神是“民族性”的精髓所在,其习俗和历史则是传统的核心,是防止阿根廷坠入世界化和欧洲化灾难的关键。于是,几乎已经消失的畜牧业雇工变成社会精英的关注焦点,被各种历史的、文学的叙述建构成一个社会集体想象物——高乔人,并承载了诸多含义。
三、高乔诗歌研究被置于阿根廷民族主义主义思潮中
对于高乔诗歌的学术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González,2005)。1910年前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系创立,以罗哈斯和卢贡内斯为代表的学院派从一开始,就将文本研究置于纪念阿根廷立国一百周年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把两者紧密结合。对于“民族”这一概念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建构阿根廷民族的方式,它不仅决定了以何种形式书写高乔人,也影响到以何种方式解读高乔文学作品。民族复兴一代的知识分子秉承的观念认为民族是古老的、具有地域、语言文化以及血缘的统一性和传承性的共同体。他们对于高乔诗歌的评论和研究也采取了与之相对应的话语策略。
这些学者首先试图为高乔诗歌找到一个历史渊源,证明其具有悠久传统。卢贡内斯的研究著作《民歌手》(Payador)以讨论荷马史诗开篇。他宣称:荷马史诗这类古典英雄史诗传统被普罗旺斯的宫廷诗人继承,演变成赋诗比赛“tensón”,高乔人之间的对歌“payada”是这种赋诗比赛在阿根廷的延续。他以充满想象力的浪漫笔法将之描述成饱含传奇色彩的传统:闲暇时节,在乡村的杂货店兼酒馆,高乔行吟歌手之间以爱情、命运等为题展开即兴的对歌比赛,吸引四方邻里观看。为了表明牧民的对歌比赛与古希腊文明有直接的渊源,卢贡内斯试图证实“对歌”一词本身也源自古希腊语 (Lugones,1962,1153)。
从荷马史诗到普罗旺斯宫廷诗歌再到高乔诗歌,这是卢贡内斯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描绘的谱系。为了证明这个谱系的真实性,卢贡内斯以及其他意见相仿的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诗歌的格律研究。高乔诗歌惯用的八音节诗句(octosílabo)成为其史诗属性的有力证据。事实上,八音节诗句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至15世纪后被广泛使用,形成富有西班牙特色的罗曼司诗歌:一种使用八音节诗句、每小节句子数量不定,偶句押韵的诗。在卢贡内斯的论述中,“对歌”因为使用八音节诗句,被等同于罗曼司;而由于罗曼司是源自民间的诗歌,因此“对歌”也拥有史诗的性质。卢贡内斯没有对研究对象进行学术定义,而是有意无意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概念置换。一方面,他将罗曼司和英雄史诗 (poemaépico)混同 (讽刺的是,西班牙文学普遍认定的英雄史诗《熙德之歌 (Cantar de mio Cid)》并没有使用八音节诗句)。既然对歌是民间诗歌的延续,所以它既是罗曼司,也是英雄史诗。另一方面,他又将对歌和《马丁·费耶罗》统称为“高乔诗 (la poesía gaucha)”,最终得出了《马丁·费耶罗》是阿根廷的民族史诗(“Martín Fierro es un poema épico”)这样的结论 (Lugones,1962:1233)。无疑,卢贡内斯相信传统英雄史诗在族群认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也力图通过上述结论重新使用文学作品作为族群自我辨识的表述和强化族群认同的手段。所以,当阿根廷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宣布《马丁·费耶罗》是《荷马史诗》的延续、是阿根廷的民族史诗时,他们的目的在于创造出一种“本民族”的独特文化以及一个共同的族群历史。
《马丁·费耶罗》的英雄史诗地位使得阿根廷拥有独特文化似乎成为一个事实,而欲赋予这个年轻国家一个悠久的民族历史则需要更复杂的运作。和大部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阿根廷独立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是上层的欧裔美洲人阶层,他们和宗主国西班牙有着血缘和文化的紧密联系 (安德森,2003:58)。然而,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目标之一却是削弱西班牙和欧洲的影响,甚至拒绝承认与宗主国的联系。他们理想中的阿根廷民族是高乔人的传人,民族史诗也理应由他们唱诵。《马丁·费耶罗》已经被祭在史诗的圣坛上,但是作者埃尔南德斯的欧裔美洲人血统、显赫出身和政治家以及重要报业人士的身份 (Sainz de Medrano,2010:19)却并不符合评论家们心目中的史诗作者形象。精英阶层身份此时需要隐瞒,进而被语焉不详的文学话语“塑造”成民族主义所需要的形象。在卢贡内斯笔下,埃尔南德斯成为一个卑微的高乔人,因突如其来的灵感创作了《马丁·费耶罗》 (他的散文和政论著作似乎被研究者刻意遗忘)。有学者不无讥讽地说连作者的名字本身都很碍眼,假如《马丁·费耶罗》是部匿名作品,更符合人们对史诗的期望 (Peris Llorca,1997:35)。
模糊高乔诗歌作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目的在于消解文人创作和民间诗歌以及英雄史诗之间的区别。然而,无论伊达尔戈早期创作的对话体叙事诗,还是高乔诗歌代表作《马丁·费耶罗》,都无法改变它们作为虚构文本的属性。消解和混淆也只能从文学的层面出发,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建构所谓的阿根廷民族性。更多时候,它语焉不详、飘忽不定,慷慨陈词的激情大于冷静思考的理性。要达到重新建构族群历史的目标,更大胆的冒险在于越过文学虚构文本的界限,直接将《马丁·费耶罗》当作人类学著作或者史学档案来处理。秉持这一理念的人不仅包括评论家,也包括诗歌作者。埃尔南德斯在《马丁·费耶罗》的作品前言中强调自己写作的目的是“忠实地”反映高乔人的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品德等 (Hernández,2010:105)。这些言论为后来者的“误读”提供了可能:卢贡内斯曾严肃地考证诗歌主人公服兵役的地区。50年以后,在另一部以高乔人为主角、被视为“巅峰之作”的小说《堂塞贡多·松布拉》(Don Segundo Sombra)的篇首献辞中,吉拉尔德斯 (Ricardo Güiraldes)承袭了这种消解虚构与现实的手法,将小说的主人公松勃拉与包括埃尔南德斯在内的一长串历史人物,以及作者现实生活中的好友们相提,宣布将作品敬献给他们,也献给“自己内在的高乔人”(al gaucho que llevo en mí)。吉拉尔德斯和几乎所有的阿根廷文人一样,出生于大庄园主之家,游学欧洲,精通法语并对当时的先锋文学了如指掌,其经历无论如何也难以与真正意义上的高乔人相类比。吉拉尔德斯利用修辞手法将消解向前迈进了一步:他模糊“高乔人”一词的本义和象征意义,发布了一语双关的宣言,因此具有了特殊的身份,他是继承了传统精神的阿根廷人和象征意义上的高乔人;而他的作品也获得了文学虚构和历史事实的双重属性。
在似是而非的历史和文学双重叙事策略下,民族主义者按自己理想中的方式建构阿根廷历史和现实。卢贡内斯借探讨高乔诗歌的起源和《马丁·费耶罗》表达对大庄园制度的怀念。他描述了一个失落的田园世界:富有的庄园主和贫困的高乔牧民和谐相处,后者天生有服从强者的本能,心甘情愿接受纯粹的白种人为自己的保护人,承认他们世袭的权力和特殊地位。从强权和种族主义思想出发,阿根廷的独立革命运动被描述成由高乔牧民追随大庄园主为保卫田园世界而开展的战争。当革命成功并且国家日益安定后,由于拥有劣等印第安血统,高乔人无法避免消亡的命运;混血高乔人的消失又救赎了阿根廷,令民族拥有纯正的白人血统。独立革命运动被描述成高乔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战争,复杂的历史进程因此变成单线索的、因果鲜明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文学虚构式的叙述。又例如,卢贡内斯希求达到种族的同质化,他鼓吹“纯粹的白色”。在其作品中,异族以“他者”的形象呈现:黑人天生具有奴隶性格,印第安人是彻底的野蛮人,永远无法被欧洲文明教化 (Lugones,1962:1116)。他反复使用“种族 (raza)”一词,认为英雄史诗是一个种族的文明最高表现,《马丁·费耶罗》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表现了阿根廷种族的英雄精神。
独立的民族语言是另一个重要的建构企图。然而,对于语言问题的讨论和对于高乔文学一样模糊。例如,卢贡内斯将高乔牧民的口语和被文学化的高乔诗歌语言混为一谈,从语言的角度进一步消解了文学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界线。由于无法摆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他努力从词源学的角度证明高乔牧民使用的特色词汇源自拉丁语。高乔诗歌出于追求风格而频繁使用的地域性词汇以及不合语法的口语结构,此时也具备了新的意义。卢贡内斯认为这种口语化语言比正统的学院式西班牙语更加生动简洁而富有表现力。他断言,由于吸收了葡萄牙语、印第安土著语言、阿拉伯语等许多语言的词汇,《马丁·费耶罗》所使用的是一种正在形成的语言,犹如但丁的《神曲》以脱离了拉丁语而初具雏形的意大利语写成 (Lugones,1962:1252)。事实证明,高乔文学的语言并未向卢贡内斯语言的那样成为“阿根廷语”。
四、结论
阿根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一直在持续而有意识地进行对国家历史和民族的建构。在20世纪初纪念立国百年之际,这种建构与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高乔诗歌因此被利用,它的一些特点被不断地强化,成为所谓“民族文学”的代表。秉承“民族-国家”的理念,关于高乔诗歌起源的讨论和对作品的评论皆以此为出发点,文学评论也屡屡僭越界限,指涉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等领域。通过这些策略,研究者不仅试图赋予高乔诗歌以史诗属性,幻化出“一个民族创造一个文化”的虚假的血缘同质性和文化的古老和传承性;同时,在文学层面以隐喻的方式书写出一种理想中的民族历史。
矛盾之处在于,来自于欧裔美洲白人的精英阶层,由于自身的经历和教育背景,下意识地认同欧洲文化的正统性,这种思想根源与他们的诉求产生了矛盾。于是,一方面,他们以高乔诗歌为媒介,力图建构出一个能与欧洲文化和历史影响抗衡的本土文化;与此同时,又千方百计试图在高乔诗歌与古希腊文化之间建立联系以表明前者的高贵性和合理性。
从“民族-国家”的理念出发,他们罔顾阿根廷的历史事实,将“高乔人”的概念等同于“阿根廷人”,将“高乔诗歌”等同于民间诗歌以及英雄史诗,将诗歌所使用的文学语言等同于“阿根廷语”,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进行高乔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并试图以此赋予本民族一种与生俱来的古老性和合法性。同时他们又拒绝承认自己的建构行为,坚信族群的同质性、共同的传统和共同的疆域以及自己的独特语言才是构成民族的决定因素。他们的论述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两难境地。
安德森,本尼迪克特.2011.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宁.2007.孤独的牧歌:高乔诗歌[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18(2):50-53.
Borges JL.1974.Obras Completas[M].Madrid:Ultramar.
Gálvez M.1944.Recuerdos de la Vida Literaria(1900-1910):Amigos y Maestros demi Juventud[M].Buenos Aires:Guillermo Kraft.
González Ortega N.2005.Literary Nationalism and Post Colonialism in Latin America.A Show Case Study:Argentine,Martín Fierro,A Classic Epic?[J].Neolheicon XXXII(1):175-204.
Hernández J.2010.Martín Fierro[M].Madrid:Cátedra.
Hidalgo B.1986.Obra Completa[M].Montevideo:Ministerio de Educacióny Cultura.
Lugones L.1962.Prosas Completas[M].México:Aguilar.
Pagés A.1971.Unamuno y la Valoración Crítica del Martín Fierro[J].AIH.ACTAS(4):355-372.
Peris Llorca J.1997.La Construcción de un Imaginario Nacional[M].Valencia:Universitat de Valencia.
Praderio A.1986.Prólogo a Obra Completa de BartoloméHidalgo[C].Montevideo: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Sainz de Medrazo L.1979.Introducción a Martín Fierro[C].Madrid:Cáted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