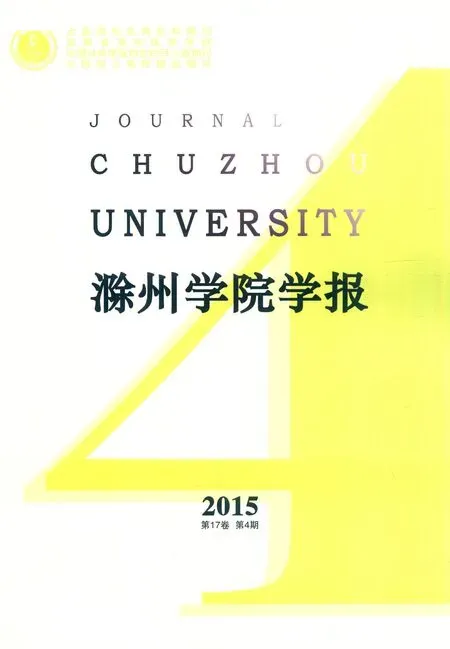苏北乡土文学创作的崛起
——评叶炜的《富矿》《后土》
2015-03-19张太兵
张太兵
苏北乡土文学创作的崛起
——评叶炜的《富矿》《后土》
张太兵
《富矿》、《后土》是新时期乡土题材创作的代表作,作品的“骨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种文明的冲突,“肉”是苏北农村的社会生活。两部作品明写农村的现代化,暗写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生活的暗流、潜流,同时书写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生活的“常”与“变”,以叶炜为代表的苏北乡土文学创作标志着新时期乡土文学创作的崛起。
《富矿》;《后土》;苏北;乡土文学;崛起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形成了两大基本叙事传统:一是乡土写实传统,从鲁迅到韩少功,以知识分子立场、文化批判形成启蒙传统;二是乡土浪漫传统,从废名、沈从文、孙犁到汪曾祺、贾平凹,以知识分子立场、人性审美形成诗化传统。[1]鲁迅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许杰、王统照、赛先艾、王鲁彦、台静农等“隐现着乡愁”的乡土作家,堪称现代乡土文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鲁迅是最早以小说的方式关照乡土的现代作家,其小说创作直接带动了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的风潮。他的小说创作多来自病态社会中疾苦不幸、 麻木不仁的人民,先将他们的病痛找出,然后暴露在阳光底下,以引起救治者的注意。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以人文主义情怀和现代意识,确立起“改造国民性”的基本主题,对封建文化作全面决绝的揭露批判。他们怀着同情、忧愤与悲悯,以理性批判的眼光展现乡村的野蛮丑陋,挖掘农民的劣根性,试图以强大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力量拯救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中乡土国民的灵魂,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后来的王鲁彦、许钦文、彭家煌、台静农是这一主题的承继者、发扬者。这种以鲁迅为标志,以知识分子立场、文化批判、启蒙主题为核心的乡土小说叙事传统,不仅成为20世纪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传统,也是 “五四”精神的主要内涵。遗憾的是,它只在20年代乡土小说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中断半个多世纪后,才在80年代中期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派小说中薪火再传。寻根派小说全都取材于乡村,以知识分子身份立场,审视比鲁迅的“未庄”还要蛮荒、古朴的乡村社会,具有明确的现代追求和对民族文化的启蒙意识。批判与继承,以现代意识省思中国传统文化,是寻根小说对待本国历史传统的基本态度。 他们省思的是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以及整个民族文化心理,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探寻,揭示这些传统的负面效应。“寻根”是对历史的一种梳理,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返照和省思。可以说,寻根小说完全切入了鲁迅传统,“在文化批判上深化了鲁迅精神”,而且“在现代叙事策略的探索方面,寻根小说也更进了一步”。[1]叶炜的创作延续了乡土写实的传统,如果说鲁迅所表现的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麻木、愚昧的的乡民,那么韩少功则是借麻木、愚昧的乡民省思中国传统文化,叶炜则是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农村现状的真实画面,塑造出一群实实在在的农民形象。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命运和遭遇、他们的生活和情绪,叶炜刻画的是社会主义当家做主的农民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在墨守“常”与应对“变”的过程中灵魂的挣扎,他们面对的时代环境是旧的伦理被抛弃,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困惑,面对复杂的现实,他们无所适从,从文本中我们仿佛可以听见她们灵魂深处的叹息。笔者认为叶炜的长篇小说《富矿》、《后土》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苏北乡土文学创作的崛起。《富矿》与《后土》创作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骨与肉
就叶炜的作品来说,《富矿》是作家以苏北生活环境为背景所创作的反映苏北民俗、苏北生活的小说。它以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为主题。“骨头”是两种文明的冲突,“肉”是苏北农村的生活。以徐州为中心的苏北大地,自古就是中国的九州之一,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风韵。这里是叶炜文学艺术的富矿。赵本夫、周梅森都是当代徐州作家的代表人物,尤其是赵本夫的小说表现出了浓郁的苏北特色。应该说叶炜的小说在民俗生活的表现上与赵本夫的小说是一脉相承的。《富矿》与《后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苏北、鲁南的农村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农民致富的进程中,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话与冲突中,农民内心的艰难、苦痛、挣扎,他们的希望与绝望、忍受与反抗、自发与自觉。麻姑是《富矿》中作家刻画最多的女性,她美丽善良而又充满情欲,麻姑和六小两小无猜,心心相映,六小和麻姑在广茂的生机勃勃的苏北大平原、在稻草垛里完成了灵魂和肉体的交融。他们的爱情生机无限、激情荡漾,又苟苟且且、隐藏于地下。但麻庄的姑娘纷纷走向煤矿去务工,这些高大健壮、精力充沛、美丽如花的姑娘走向煤矿,在麻姑的内心有意无意的荡起一阵阵涟漪,麻姑平静的内心世界惊起了波澜,最终麻姑还是没有与六小结成夫妻,由于六小的家庭遭受变故,六小的哥哥在县城工地上做活摔伤瘫痪,六小家债台高筑,麻姑嫁给了麻庄矿的蒋飞通,她很快的适应了矿上的生活,这说明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话中工业文明同化了农业文明,但是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主人公笨妮却走了与麻姑相反的道路,笨妮到煤矿工作,煤矿的所谓“现代”生活她无法适应,在煤矿期间她的肉体惨遭顾光的蹂躏,后又被矿上技术员列强奸,尤为可恨的是,是顾光将笨妮房间的钥匙交给列,唆使胡列去玩弄笨妮,顾光和胡列用笨妮的肉体打赌,他们共同践踏笨妮的灵魂、肉体与尊严。这对一个到矿上务工的村姑来说,是无法言传的不公,这些遭遇让笨妮心灵破碎,用笨妮自己的话说“我想好了,这个地方也许适合你(麻姑),但不适合我。”[2]129在这种情况下她重新回到了麻庄,回到了农村生活,回到了农业文明,麻姑和笨妮是作家极力塑造的两个女性形象,她们的选择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女性农民做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她们的选择代表了无数进城务工的农民的选择,毫无疑问她们的代表性意义在以后的岁月中将会逐步彰显出来,作家通过这两个形象记录了无数进城务工农民的心路历程,令人不能忘怀、无法忘怀,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现代化给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的农民带来了多少艰难!进城务工的农民要么适应,要么回归!这两个人物同时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度的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共同的心路历程,笨妮和麻姑将作为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两种艰难选择的永久性代表载入文学史。
二、明与暗
《富矿》与《后土》同时揭示了麻庄社会生活的“明”与“暗”,以此来影射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活。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中国由古老的农耕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转变,麻庄也在进行着这种转变。在明处,我们看见的变化太多,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高速铁路朝发夕至,铁路公路星罗棋布,开发区、新农村的楼房如雨后春笋,汽车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与之相伴的是农村的青年人越来越少;影星歌星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清正廉洁的官员越来越少;清新的天气越来越少;而雾霾越来越多,网络上惊世骇俗的新闻、图片越来越多,阴暗的角落越来越多,偷盗村、艾滋病村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包脓裹血的社会。《后土》用相当的笔墨书写了麻庄社会生活的暗流,王远是小说着力塑造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圆整”人物,如果说以曹东风和刘青松为代表的第三代村干部是农村发展的正能量,那么以王远为代表的村干部则是农村发展的负能量。明着村民看见的是王远当村干部不拿工资,将工资捐献给养老院,暗地里王远却贪污了大量劳苦村民的血汗钱,明着王远帮助如意将她的丈夫从派出所“救出来”,暗地里他却用三千元钱买下了如意的身体供自己淫欲,在现实的农村,像王远这样趁人之危、逼良为娼、落井下石,往良家妇女流血的疮口上撒盐的村干部不少。农民在致富的道路上受到了无数这样村干部的侮辱、愚弄、蹂躏、践踏。作品以平静的口气将这些暗流呈现给读者,使我们联想起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老婆与狡猾的钱文贵。穿越麻庄,中国的社会生活亦是如此,前些年国有企业改制,明着是股份制改制破产重组,暗着却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落入个人囊中,明着是进行新农村建设、开发区建设、高铁建设,暗地里却与王远一样在中饱私囊,破坏改革、破坏乡风民俗,捣毁人心。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有打着“反孔”的旗号吃“孔子饭”的人,现实生活中同样有打着“慈善”旗号吃“慈善”饭的人,打着“改革”旗号,破坏“改革”,吃“改革饭”的人。王远是新时期乡土文学中典型形象的代表,王远的形象让我们想到的太多太多,这无疑是当代文学画廊中一个与《白鹿原》中鹿子霖形象比肩的形象,一个随着时代前进将会散发出无限文学魅力的典型。《后土》虽然写了阴暗的社会生活,但作家的思想却无丝毫的阴暗,《后土》延续《富矿》的思路,表现了对农民百年命运的深切关注,以此暗喻了百年乡土中国的发展进程。小说主要写了四代村干部带领群众建设家乡的艰苦历程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斗争。第一代村干部老支书和老村长是早期农村先进人物的代表,他们为建设麻庄付出了毕生心血,但因为时代环境使然,麻庄没能摆脱贫困。第二代村干部王远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和麻庄的现实处境,在带领群众致富的过程中,也不得不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考验。以曹东风和刘青松为代表的第三代村干部更加具备改革麻庄以顺应时代要求的思想和能力。他们在带领麻庄群众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不得不与上一代思想保守的老人展开较量。而小说重点则在于展现了以大学生刘非平为代表的第四代村官的时代风采,塑造了新一代农民形象,有力地呼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王远、曹东风、刘青松、大学生刘非平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但正是这些有血有肉的平凡的小人物,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明和暗,看到了乡村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三、常与变
沈从文先生在《边城》中为我们展示了湘西世界的人性之常,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希腊小庙,作者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3]叶炜在《富矿》与《后土》中也写了一种人生形式,就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农民在致富的道路上心灵的分化,先进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对保守、充满温情甚至有些落后的乡土生活的冲击。《富矿》与《后土》对农村生活的原生态进行了叙述,更有对人性之常的展示,叶炜笔下的人性之常包括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人的嫌贫爱富、人的无法满足的欲望、人对贫乏枯燥生活的逃避、对现代文明和丰富精神生活的渴望及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对于麻姑、笨妮、翠香、六小、曹东风、刘青松、王远等人来说,农村生活是“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常,生儿育女是常,麦苗、水稻、棉花、大豆是常,猪、马、牛、羊是常,鱼塘、沟坝、桃园、荒冢是常。机器是变,矿灯、矿靴、矿服是变,漫天黑雪是变,跳舞是变,发廊卖肉是变。《后土》与《富矿》同时向人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些非常复杂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人们对罪恶的认同感,人们的欲望日益膨胀转变为恶望。比如胡列对女性的猎逐、老来对发廊老板的包养,蒋飞通与肖芳、麻姑的三角关系,李玉花和王远的私通。男盗女娼一直是我们道德上最抵触的东西,尤其是在乡土中国,但是在麻庄、麻庄矿,村民、矿工都习以为常。这折射出现代社会人们对罪恶的认同感的上升。社会越现代化人心越被掏空,在麻庄、在麻庄矿人们不再坚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正如小说中描写的“麻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时间在一点点改变她,她现在对一切都感到无所谓,她所做的一切都好像是为了打发时间。她的身体和灵魂都被生活掏空了,用文雅一点的词语来说,就是一切都忽然间变得虚无起来。”[2]129像麻姑一样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日益模糊。作家对这些“变”充满了惶惑和担忧。穿越麻庄看现实更让我们感到害怕。一个大学生毕业时,没人看中你论文写的好坏,学会了哪些东西,而看中你就业时找到了什么好工作;评价一个姑娘,不看她有多少学识、人品如何,而看她找到了多好的男朋友,看一个小伙子不去看他有多大的事业心、读了多少书做了多少事,而看重他手里捏着多大的权力、钱包里装了多少钱,这已经成为我们今天一个普遍衡量成功的标准。到了文化圈、演艺圈,作为一个演员如果没有绯闻,几乎被认为是极大的失败,还要千方百计的去制造绯闻、丑闻。而且读者、观众、包括知名人士都对此认同,这就是社会的“变”,也是叶炜忧思的“变”。这难道不是当下社会的真实状况吗?人们从对美好生活的美望变为欲望的无法自禁,由欲望的无法自禁变为充满恶望。
四、流脉与崛起
《富矿》与《后土》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乡土文学,是当代乡土小说创作的优秀代表。追溯乡土文学的历史,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早在上个世纪初叶,在鲁迅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书写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的作家。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以及以沈从文为代表性的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再到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赵本夫、叶炜为代表的当代乡土作家。乡土文学经历了长久的发展,展现出持久的强韧生命力。乡土文学作家在作品中表达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入思考和对人性的普遍拷问与关怀。鲁迅以“改造国民性”思想为目的,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4]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鲁迅的笔触在温情中带着残酷的清醒,在其描绘的乡土世界里,我们透过人物形象的纯朴看到的是鲁迅对国民“哀其不争,怒其不幸”的深深悲观与失望,是对国民劣根性深刻的剖析。与鲁迅时期不同,抗战期间乡土文学在强大的政治背景下,从以革命为脉络,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作家们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虽没有了鲁迅时期的深刻,但迎合了当时的政治诉求,得以长期存在。赵树理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由于对农民的深刻了解使他成为继鲁迅之后表现中国农民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对封建意识下的影响狭隘的农村社会关系和道德观,较同时期的作家有较深入的剖析和抨击。叶炜是中国改革开放深化期,在农村城市化进程加速期书写农民由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艰难心路历程的代表性作家。看似平静的叙述背后,力透纸背的揭示了农民离开土地时灵魂的挣扎,他们的欢乐与泪水、希望与绝望,对土地的背叛与热爱及留守农村干部的高尚与堕落,伪善与狠毒,倾轧与争斗。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在废名《竹林的故事》、沈从文《边城》的小说中,完全抹去了农村生活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表现出人性的关怀。小说用苦难对照纯真,构建了理想的人性神庙,对现代化进程中所缺失的人性美、人情美进行补充。然而,小说的隐文本却是“失乐园”母题的再现,体现作家的反思与忧患:人性美、人情美依然不能阻止悲剧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其深处潜伏的是同样的痛苦与忧伤。《后土》中关于桃源与荒冢的叙写明显可以看见废名《竹林的故事》对叶炜的影响。
[1] 白忠德.浅析中国乡土文学内涵及其叙事传统[J].作家,2010(6).
[2] 叶炜.富矿[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3]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序跋集《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4]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刘海涛
The Rise of Local Literature of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Comments onFuKuangandHouTuof Ye Wei’s Works
Zhang Taibing
FuKuangandHouTuare the master pieces of local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era. With the appearance of social life of rural areas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the works try to show the conflict between two cultures,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essence. On the surface, these two works are abou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ral areas, whilst the essence of them is about the undercurrent of social life in the rural area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Moreover, the “normalcy”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life in the modernization are also shown in these two works. Represented by Ye Wei, the local literature of Northern Jiangsu marks the rise of local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FuKuang;HouTu;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local literature; rise
张太兵,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安徽 滁州 239012)。
2015-04-19
I206.7
A
1673-1794(2015)04-0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