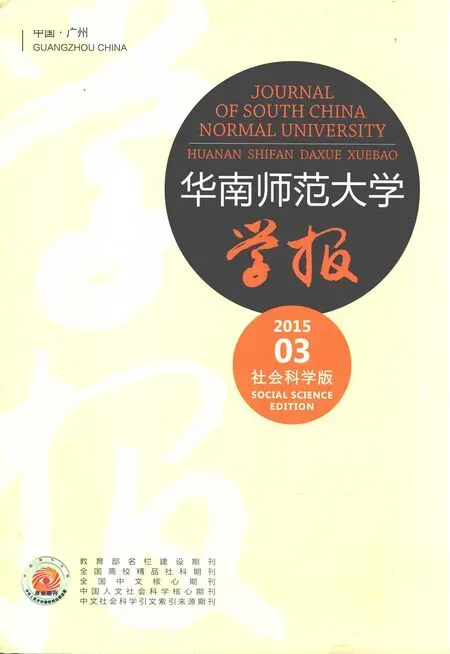秦帝国统治思想的狭隘性与局限性
2015-03-19李禹阶赵昆生
李禹阶,赵昆生
秦帝国二世而亡,除了实行商、韩法家思想,严刑峻法、苛暴虐民外,其国家统治思想及意识形态的狭隘性与单维度化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亦是一重要原因。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古代中国政治上、地域上的一统。但是,在统一六国后,秦的统治思想以及相应政策没有及时从军事轨道向和平时期转化,因此缺乏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论证以及政治思想上的建树。对于秦王朝来说,依靠刑治手段,全面秉承法家“农”“战”思想使其取得了战争的巨大成功,这也使其比较盲目地相信了强权、暴力乃至秦君臣主观作用的力量,而缺乏对于国家统治思想建构必要性的认识。因此在建立全国政权后,秦王朝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国家统治思想及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赤裸裸的刑治主义和暴力对抗,是君臣之间的利益角逐,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斗争。它所主张的政治价值与信仰、理念,亦是法家理论主张的君主专制下的刻薄寡恩、苛暴无情,由此使其在统治思想及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缺乏对于关东地区固有的宗法文化的包容与怀柔。这样,秦在统一中国后,其政治思想及强调军功、农、战的战时价值理念,就呈现出狭隘与单维度的特征,而不能适应统一后中国社会的需要。
秦帝国统治思想的狭隘性与单维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秦帝国在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对其战争力量和主观作用的深信不移和盲目夸大,以致未能及时调整“马上”与“马下”治天下的攻守异势的统治思想及其政策、策略。秦国在全国统一后,其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理论仍然停留在战争轨道上,缺乏对于全国各个阶层有效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整合。秦统一后,出于对自己战争能力和主观作用的深信不移,一味依靠刑治理念治国,没有认识到由马上取天下,而不能由马上治之的道理。这种单纯依靠刑治精神进行的社会控制,就使之成为历史上以重刑著称的朝代。它使人们重“利”、重“力”而忽略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信念,使人欲不断被膨胀、放大。这在西秦时期宗法血缘基础薄弱的军事战争轨道上是有效的,但是当它延续到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沿用在关东各国的社会整合与“文治”中,就不那么有效了。历史正是证明了这一事实。
在帝国建立之初,面临复杂的政治局面,秦王朝没有使政府权能部门迅速由战争轨道下的军事职能转变为战后恢复社会经济的和平职能,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去适应、包容关东诸国宗法血缘的社会文化、风俗,通过王朝政策的调整,达到秦、齐、楚等几大不同地域的社会整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例如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制度,但是这些制度主要是以秦国制度为标的,由此来完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全方位统一。而且十分重要的是,秦在帝国的社会控制与整合的政策措施上,仍然采取了西秦时期法家严刑苛政的国家治理思想,并将这一统治举措延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试图以此将帝国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运用到中国广大地域中去。这种对于国家政治思想及文化制度的考量,在当时纷纭复杂的政治格局和文化冲突中,是缺乏其适应性的。
事实上,秦帝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也是一个秦专制政治制度及其法家思想、刑治精神在统一战争局面下不断强化、膨胀的过程。秦的统一,一方面使秦朝君臣在主观上过分相信军事机器的强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实行统一的过程中,秦国实行的战时政策、措施强行推进、深入到帝国各个阶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西秦社会在法家思想的一统下去完成政治上、文化上的整合。尤其在秦嬴政时期军事上的摧枯拉朽,使秦帝国君臣过分相信了帝国军队与法家刑治主义的力量,所以当秦消灭了六国政权,完成国家统一后,其君主集权及官僚政治也就到达其顶点。秦始皇这种无限的自我膨胀,以及对自己战争力量和主观作用神威性的深信不移,致使他蔑视天下苍生,一切自以为是,把自己推到了孤家寡人的位置上。例如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登之罘山,就刻石称:“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义诛信行,威惮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①《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9 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大肆宣扬自己“光施文惠”“奋扬武德”“烹灭强暴”等天下苍生救世主的功绩,武断地决定以法家理论来应对一切的裁断。在秦始皇看来,专制皇权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②《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46—2547 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③《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9 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始皇不仅拥有国家最高立法权,同时亦拥有最高的思想裁断权,君主的言论、意志就是天下法律的源泉和行为的规范,由此开中国封建时代专制君主所具有的法律制定权、思想裁断权、制度施行权的先河。
始皇高高在上,俯视苍生,以自己的意志为标准进行社会分层,并强行以西秦制度来规定不同社会阶层应遵循的社会规范。他自称:“端平法度,万物之纪……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9 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按照人治社会中的君主之法,要求不同社会阶层应严格遵守该阶层的规定和规范行事,不能僭越自己所在阶层的规定。秦代法律对不同社会阶层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规范制定得非常细致和具体,其条文甚至细致到对人们具体行为方式的量上的精确规定。《秦律》现已佚失,但我们可以从“承秦制”的汉初法律中看出。如1983年至1984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 号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共有竹简527 枚,包含了27 种律和1 种令,共28 种。它的发现既完善了我们对于秦汉法律文献的认识,也看出秦法的内容包罗万象的情况。在《二年律令》里,不仅有杀人及伤人罪、经济犯罪、官员渎职及失职罪等刑事罪刑,也有以孝入律的不孝罪等伦理罪刑,还有对人口商业农业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汉初是继承秦法并且有所增删而来,因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秦代法律制定是十分完备的,其实施也是无所不入的。这样,一方面秦帝国将社会各阶层具体的一言一行都纳入了政权控制的爵制与法律框架之中,使君主极权纵深地延续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层面,表现出了君主极权的强大和无所不在。另一方面,法律条文过于具体化、细节化、生活化,除了条文自身反映的法家刑治主义的严刑峻法外,也使得各个阶层的社会行为运作缺乏余度,没有因时而变的空间和时间。尤其是在除了秦关西地域的其他中国广大土地上长期实行宗法血缘“亲亲”“尊尊”制度的社会中,其基层社会在过去往往是依靠宗法制度的族规、家法在统治,依靠祖宗血缘崇拜的精神纽带维系着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信念。这种宗法制度的存在,往往是在严酷的专制集权政治对于基层社会的压迫中起到了一个中间层次的社会压迫减震器作用,使严酷的压迫在宗法血缘的“亲”“尊”中得到部分消融。现在一旦缺失了基层宗法社会这么一个社会压迫减震器,国家的统治及严苛、刑律直接展露在民众面前,其严酷残暴的刑治精神在习惯于宗族“亲”“尊”原则及其宗法规范统治下的人民大众面前暴露无遗。所以,西秦严酷的法律规范在全国不同风俗、文化的地域的颁布实施,在基层民众社会中的延伸、深入,使广大民众处在国家极权政治和刑治精神的高压下,自然不能达到社会整合与控制的效果;而只能适得其反,引起当时楚、齐、韩、魏等各国旧贵、士人、民众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这种专制统治的政治反映。所以,陈胜、吴广等人所面临的戌边“失期”惩罚,对于长期习惯于秦国军律的西秦民众来说,应该是能够忍受的。但是对于习惯于宗族“亲”“尊”原则的关东旧六国民众而言,就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律法。所以汉初陆贾曾就“攻守异势”的问题规劝高祖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①《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第2699 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正是这种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文化特点决定了秦始皇以严刑峻法来进行社会控制的统治思想的局限性与狭隘性。
其次,是秦帝国在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上的极端功利化特征。在秦统一四海过程中,随着君主专制政体的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与权力的价值观也延伸到四海之域。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专制王权理论,随着帝国建立而逐渐推向全国。商鞅到韩非理论的演进轨迹,即是秦专制王权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发展、扩充的行进历程。从战国后期到秦帝国的统一,正是秦专制王权从理论到实践迅速演进、扩大的时期。与韩非同时代的吕不韦,曾经从政治实践中认识到专制王权乃是实现大一统的重要因素,要有效整合与控制中国古代社会,就必须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政治。他认为,“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②冀昀主编:《吕氏春秋·谨听》,第262 页,中华书局线装书局2007年版。故“国之一,在于君”,“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③冀昀主编:《吕氏春秋·执一》,第403 页,线装书局2007年版。。于是,在吕不韦等官僚、宰辅的推波助澜下,秦以君主集权和以军功显荣的权力价值论,对帝国现实地建立君主专制的官僚体制,促进官吏的选拔与流动、人才擢用都起到极大作用。同时,权力价值观的发展,使秦国士农工商各阶层打破既有的传统分工格局,无不以其军功和“技”能来获取富贵显荣。正因如此,秦国家从帝王、官吏到普通士人,其不择手段,仅为功利目的的投机思想泛起,官员政治价值观也显得十分窄化。在底层社会及民间,价值观转变更是使人目不暇接,而为官之德更加无从谈起。据史料记,当时关东陈胜、吴广起义,杰俊相立,兵至鸿门。丞相李斯见情势危急,多次欲当面向秦二世劝谏,二世不许。后来秦二世不耐烦了,对李斯加以责问说:“然则夫所贵於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贵於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柰何?”④《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53—2554,2553—2554,2539—2540 页。大意是贵有天下的帝王,岂能够像奴才一样苦形劳神,过着仆役般的生活。圣贤的帝王之有天下也,专以天下之物来满足自己的人生欲望,如果于自己身体欲望都不能满足,又将以什么来治理天下哉!因此我的人生愿望就是肆意极欲,穷尽奢侈,长享天下而无害。秦二世公开地引用韩非的话,视天下为己物,以奢侈享受为人生目的。这种治国者的政治价值观,充分体现出秦王朝上层统治者的自私、狭隘,也充分体现出秦王朝从帝王到官吏政治思维的功利性、局限性、阴暗性。正是在这种政治思维的影响下,秦二世提出了“以人徇己”或“以己徇人”的问题:“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⑤《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53—2554,2553—2554,2539—2540 页。由此发出了以严刑苛政治理社会的概叹。正是在这种极端自利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下,秦王朝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处于空前的暴戾与残酷之中。
秦帝国政治信仰的功利性狭窄化,已经成为帝国君臣上下一种普遍现象,它随时表现在朝廷官员投机性的政治价值观中。例如秦丞相李斯,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就具备十足的投机性。李斯曾经由小吏而出将入相,其心理态势则是:“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⑥《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53—2554,2553—2554,2539—2540 页。将富贵功名视为人生目的,而其富贵与尊荣均下注于君主身上,这也是封建化过程中一些官僚、士人权力价值观的发展趋势。这种权力价值观充分表现出官僚、士人对新的封建制度中仕途开放的干政激情和与此相关的对专制王权的依附性。
这种权力价值观趋向,使传统的商、韩思想延续了下来。以“强力”、军功、政绩而不以宗法统绪取富贵,已成为秦代的一种时尚。本来以军功、政绩摄取富贵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当其片面强调这个方面而忽视道德伦理的作用时,就容易使帝国上下形成一种刻薄寡恩、重刑酷法、以利相竞的风气。这种风气使得秦帝国内部的官僚机制和对于基层社会的整合、控制在帝国一统初期就存在失效的危险。例如在秦帝国宗室内部的宗法关系上,就表现出极其的刻薄寡恩、利益至上的倾向。早在秦帝国诞生的前夜,这种情况就开始出现。如秦始皇就把本家族的成员排斥在权力结构之外,不给同姓宗室子弟以政治实权。秦始皇死,秦二世就用阴谋手段夺取皇位,并且与心腹宦官赵高密谋对付宗室兄弟姊妹的策略。赵高声称:“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主张以武力和强权对待宗室兄弟姐妹。于是秦二世大开杀戒,“诛大臣及诸公子”,“六公子戮死于杜”。当时,公子将闾弟兄三人被囚禁于内宫,秦二世派人对公子将闾说:“公子不臣,罪当死。”将闾质问:“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奉旨行事。将闾仰天长号:“天乎!吾无罪!”兄弟三人拔剑自刎。这种对传统“亲亲”原则的否定,不仅使得本来就已孤独的皇帝失去了宗法、家族的人伦温馨,更使皇族内部在权力兴替上始终处于血腥的不稳定状态,形成汉初人所评价的“激秦孤立亡藩辅”而“亡秦孤立之败”的局面。
皇帝在朝廷上失去了同宗室子弟的辅佐,赵高指鹿为马的现象随即出现。这种情况,根本是秦上层统治者在窄化了政治信仰及相应的权力价值观念后,使得秦代君主专制的强权政治潜伏着异常险恶的风险与危机。本来,秦帝国的军功等级爵位是为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更好地进行社会整合而设立的,但它的政治名分与财富占有相结合的本质,又向人们披露了一个事实,即:等级越高,权力越大,土地财富的占有越多。在极端的封建君主专制下,皇帝高踞于权力金字塔顶端,俯视、监视着他的臣民;百官大臣和子民百姓则匍伏在他的膝下颤颤兢兢,诚惶诚恐地揣度着帝王的意旨,并准备承受突然降临的雷霆;君臣之间的防范、猜疑更加深了双方的冷淡,扩大了权力的距离。因此,在一个缺乏相应的社会道德伦理分野的政治局面下,对于皇帝个人来说,越是集权,越是大权在握,其所面临的来自皇室与官僚阶层的离心力就越大。这种离心力,有来自皇室内诸王对于帝位的争夺;也有来自手握军政大权的权臣对于皇权的窥视,同时亦有内臣近侍的变乱。加上帝王久居宫廷,这种离心力使等级之间距离日益扩大,加大了帝王和臣子之间的权力距离。这种扩大使君臣之间、群僚之间的宦海风波波诡云谲,并且使权力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发生转移。在秦二世执政的短短数年间,秦王朝政权由二世而赵高而子婴,几易其手,却没有受到官僚群体的集体制约与反对。所以,政治思想与信仰体系的功利性窄化与结构性缺失,是秦帝国政治整合与社会控制不能有效实行的原因之一。
再次,是秦王朝统治思想中政治哲学的低级化及单一化。秦过分崇尚武力和战争能力的结果,是使其在全国统一前夕,并没有做好统一后的理论准备,而是简单套用西秦政治思维模式以及战国时期的宗教理论,使其统治理论存在重大缺陷。
秦王朝在统一全国前后,对于当时关东国家和关西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的极大差异并没有充分重视,也缺乏足够的统一后的理论准备,这尤其表现在其理论的核心部分——政治哲学方面。从史料看,秦建立全国政权后,除了依靠法家思想治国外,其论证国家合法性以及政治等级制度的政治哲学,主要是战国时期在东方齐地流行的“五德终始”学说,和来自民间的原始宗教的山川泛灵崇拜。
“五德终始”学说是以战国时齐地思想家邹衍为代表提出的一种以自然界五种物质元素(金、木、水、火、土)来解释宇宙规律与历史发展的一种政治与文化学说。《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曰:“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以“五德终始”说解释历史演变规律,揭示朝代更替背后深层次的内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民众能够接受的一种朝代更替理论。由于时代局限,普通知识分子和百姓对社会发展、朝代更替的规律和原因不可能有深刻认识,但又迫切想知道隐含在朝代更替背后的必然性因素。自然界五种物质元素(金、木、水、火、土)作为战国以来的一种逐渐流行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一种对于宇宙与社会规律的认知工具,其五行相生相克、相互作用的道理浅显易见,因而容易被人们接受。战国时,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已在齐地广为流传。而秦相吕不韦在试图为统一后的秦帝国建立“文治”之具时,就将”五德始终“说纳入其政治视野中。《吕氏春秋·应同》篇曾记曰:“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这说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已经被《吕氏春秋》较完整地采用和保存。秦统一后,由于秦当时政治理论准备的薄弱,就采用这个现成的哲学理论来作为其政治哲学的主要基石,一方面希望从法理上解释秦朝统一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权威性,由此标示秦统一和朝代变化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为统一后的秦帝国建立一种具有理论依据的文化整合模式,来统一当时六国“不同风”局面下的文化思想,进行制度建构。据《史记·封禅书》记,当公元前221年秦刚统一六国后,立即就有人出来以“五德终始”说献计献策。“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周人之德是“火”,秦人之德是“水”,“水”克“火”,所以秦人取代周人统治了天下。“五德终始”学说虽然是东方齐地兴起的学说,但是由于“五德终始”学说在当时秦政治思想理论匮乏的情况下能够相对合理的阐明秦朝代更替的合法性,于是秦始皇毫不迟疑地把这一套拿过来,为新王朝的政治合理性服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以秦始皇之口宣布秦替周而立,其水德属性不可置疑。从文献中也可以看出,秦采用“五德终始”说作为其政治哲学的本体,并没有经过统一前后长时间的探讨、研究,而是在建国初采用了部分官僚或者士人之说。①从《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载:“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可以看出,提出这个建议的,很可能不是显官贵戚,而是普通官僚或者士人,尤其可能是东方齐地人氏。自此,秦就以“五德终始”的思想作为国家大一统的合法性论证,并且将之推向帝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层面,并以之来改正朔,易服色,完成帝国的政治与文化制度的改造大业。
秦始皇宣布采用“五德终始”说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基点后,就不仅大力神化和宣扬“五德终始”说,而且还将“五德终始”说的抽象说教进一步社会化,将其延伸到国家政治活动和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具体细微的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规范、行为来体现“五德终始”说的无所不在。例如在政治与文化制度方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黑色成为秦国崇尚的颜色,“六”成为吉祥数字。分天下三十六郡,正好是六的六倍;销毁天下兵器,铸金人十二尊,迁徙天下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皆是六的二倍;甚至“三公九卿”亦与“六”暗合。将人们崇拜并以此为生的黄河改为“德水”,将严刑苛法也与五德之数相合。由此,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体制在“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这种做法,对于统一天下习俗风尚、价值取向起到了整齐划一的作用,使人们在黑色的迷恋、“六”吉祥数的追述中体会到皇权的神圣性和秦专制统治的合理性,从而认同秦的统治。
但是,“五德终始”说又是一把双刃剑。“五德终始”可以说是秦用来建立或者弥补其政治思想及国家意识形态缺失的一种论证手段,但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学说或者一种完备的政治信念。它虽然能对秦王朝的建立和统治给予神圣、合理的解释,也同样能给人们心理上一种潜在的暗示:朝代间的更替将永远进行下去。秦取代周是合理的,因为“水”灭“火”,但“水”仍会被“土”替代。秦为了保证水德的长存与稳定,必须小心翼翼,从周的灭亡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重视实际统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秦王朝并没有记住这一点,最终被其他政治势力所取代。
在遵从“五德终始”说的同时,秦始皇还大搞多元的泛灵性山川神灵崇拜。山川神灵崇拜是一种史前原始宗教崇拜。史前对自然山川神祭祀的内容甚多,表现在天、地、日、月、山林、川谷、丘陵、星辰、寒暑诸多方面。人们可以根据不同自然现象的功能,把它视为与人的祸福相关的禁忌与预兆。《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左传》昭公元年记曰:“山川之神,则水旱厉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在位时,“顺天地子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荚”。《管子·封禅》则云伏羲、炎帝、黄帝时的封禅情形:“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其说同。伏羲、神农、黄帝封泰山未必实有其事,但它说明这些酋长兼巫师循守泛灵禁忌这一传统规则以趋福避凶的情形。这种泛灵性山川神灵崇拜自春秋战国就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当时基层社会流行的一种民间宗教信仰,并且沿用至秦。秦时,出于从思想上进行社会整合与控制的需要,帝国上下均采用了这种泛灵性山川神灵崇拜的方式。从秦朝廷来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就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三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秦始皇借向上天禀告改朝换代而要求他的臣民子孙“遵奉遗诏,永承重戒”,并且将这种训诫用封禅刻石记录下来,展示给国民,如刻石上所曰“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等等。就在这次巡行途中,秦始皇经过彭城时“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秦王政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出巡到云梦,又“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秦始皇还沿用了秦国传统的郊祀雍四畤上帝的活动来祭祀天地鬼神。秦二世时候的情形大抵也是如此。太卜官曾评论说:“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而秦帝国由于信仰的多元性与泛灵性,始终没有将国家宗教上升为一种一统国家所需要的统一神袛的一神教宗教,而是始终使其仅仅具有民间的原始宗教的山川神灵泛灵崇拜性质。这使它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统一宗教以及统一神袛的一神教宗教具有十分重大的区别。所以,秦帝国在政治信仰及社会价值观上,由于缺少其国家意识形态重新构建的基本要素,不得不用传统的自然界多神崇拜来作为其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思想信仰。这样,当世俗化的政治理论不能完成对于全国民众思想统治的功能时,宗教又处于一种在原始宗教层面的低级状态。它使秦帝国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缺乏对于各个阶层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等级次序、规范的相关论证,缺乏对于社会行为的约束和道德伦理的提倡,由此也就使完成战争功能的秦国家机器始终还在军事性的运转轨道中,各级官吏仍然依靠战争时期的刑治手段来进行社会控制,由此使秦帝国先天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结构性缺陷,这确实是十分可悲又作用有限的。
所以,由于秦王朝过分重武轻文,在全国大一统前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而在全国一统后,又没有及时调整国家政治思想理论,仅仅依靠适应于战争状态的法家刑治主义来进行和平时期的思想统治,它就使秦王朝的统一缺乏稳固的思想基础。事实上,在秦完成统一后,帝国广大官吏们的思想信仰和国家治理理念并没有转化,奉行强权政策和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路线,采取的是以刑治精神为主导的严刑峻法、刻薄寡恩的社会控制方法。这在当时社会基础与文化模式都十分不同的关东六国旧地,必然会缺乏统治的根基,并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事实上,这正是秦王朝在社会转型重建中不成熟的内敛机制与大一统社会整合中的秩序失范的必然结局。如果仅仅从时间段上看,秦对于全国统一是呈摧枯拉朽之势的。尽管秦统一六国有着长期的战争能力准备,但在具体的最后统一过程的时间段是相对较短的。秦始皇从公元前230年起,仅仅花费了10年左右时间就兼并了山东六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统一的国家政权有机体中,如何不断地修正、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秦政权社会整合与控制失效的重要亏缺就在于社会环境从战乱转型到统一安定中,没有实现统治思想与政策的调整,缺乏在和平局面下有效的自我反省和内敛机制,并且在其狭隘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下,横征暴敛、无所顾忌。这就使得一大批旧贵族以及广大士人在统一以后找不到更多获取利益的途径;而广大百姓在严刑酷法下,也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生命保障。由此观之,秦王朝的失误就在于没有完成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中政府权能及职责的及时调整,以及安宁局面下的规范化和秩序化。其结果,必然是天下汹汹,民不聊生进,进而激起全国民众的反抗。秦朝的速亡正与此有着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