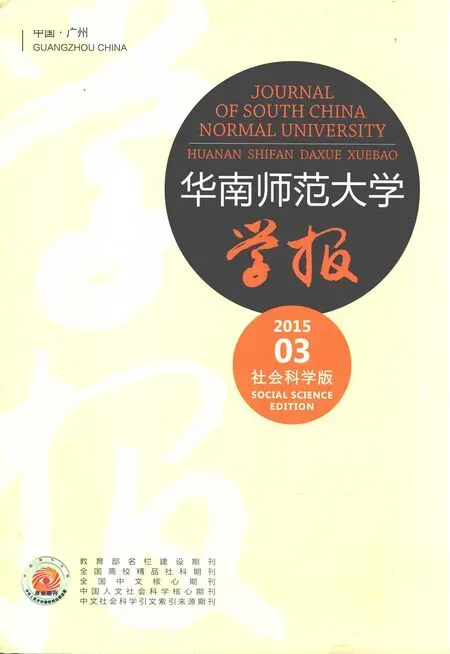自杀:五四时代的一种精神症候——《新青年》关注的两起自杀事件
2015-03-19王桂妹
王桂妹
自杀:五四时代的一种精神症候——《新青年》关注的两起自杀事件
王桂妹
【摘要】五四时期,“自杀”成为时代精神症候之一。从根本上讲,无论是清代遗臣梁济的沉湖还是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的自杀,都源自“文化激变”所带来的精神困境。新、旧两起自杀事件也引发了《新青年》同仁的关注和热议,他们对于“自杀”是非曲直的价值评判可直观地见出新青年派观念和价值的分歧。同时,由新青年的自杀也直接引发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对于新思潮的反思,成为促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向的重要契机。
【关键词】五四自杀精神症候《新青年》
【收稿日期】2015-04-15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 2015) 03-0040-06
作者简介:(王桂妹,天津静海人,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NCET-11-0202) ;吉林大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近代文学流变研究”( 2013JQ011)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两起自杀事件引起了文化界的舆论热潮:一是1918年11月10日清代遗臣梁济的沉湖自杀,一是1919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青年学生林德杨的自杀。《新青年》作为言论界翘楚,也关注到了这两起死亡事件,并引发了同仁、师生之间的讨论和论争。分析这两起自杀事件以及“新青年派”对于自杀的价值评判和意义纷争,是透视五四时代思想和精神症候的另一扇窗口。
一、“遗老”与“新青年”:剧变时代的共同精神困境
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呈日趋激越、日渐深入的演进态势,时至20世纪初终于以革命的重磅终结了数千年的王权统治,建立了共和国。然而,执政者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致使宝爱共和的知识分子转而寻求政治的根本解决,高呼“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语)。以“新青年群体”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进入新旧思潮的大激战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充满了混乱、矛盾的危机时刻。李大钊曾对这一矛盾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描述:“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这种生活,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突;这一段国民的生活史,最是可怖。”①李大钊:《新的!旧的!》,载《新青年》1918年4卷5号。鲁迅也在同一时期谈到这种矛盾的生活和思想状态:“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圣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②唐俟:《随感录五四》,载《新青年》1919年6卷3号。对于解决新旧冲突的路径,新青年同仁却有两种不同的方案。李大钊主张以“新”包容承载“旧”:“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路径,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负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
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①李大钊:《新的!旧的!》。这种新旧调和主张在五四初期只是个案,占据主流的则是弃旧图新、非此即彼的激进主张。钱玄同针对李大钊提出的以新负载旧的主张提出反对意见:“我的意思,以为要打破矛盾生活,除了征服旧的,别无他法。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似乎不必请他享新文明的幸福,尝新生活的趣味,因为他们的心理,只知道牢守那笨拙迂腐的东西,见了迅速捷便的东西,便要‘气得三尸神炸,七窍生烟’,‘狗血喷头’的骂我们改了他的老样子。”②玄同:《〈新的!旧的!〉编后》,载《新青年》1918年4卷5号。鲁迅也认定“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③唐俟:《随感录五四》,载《新青年》1919年6卷3号。而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出的“要拥护……便不得不反对”的话语方式以及“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④《通信·陈独秀答胡适》,载《新青年》1917年3卷3号。的态度,代表了新青年群体对待新旧的典型姿态。应该说,新文化倡导者们弃旧图新、水火不容的决绝态度正赋予了新思想以突围的动力,但是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姿态也进一步激化了新旧之间的矛盾,致使本以剑拔弩张的两种思想更加势不两立,新、旧两种思想在各自“唯一”的路径上也更加逼仄,愈行愈险。这即是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预言到的“过渡时代”的危险症候:“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抑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也……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线,而所争间不容发者也!”⑤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7—2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于是,“自杀”也就成为这种过渡时代必然而又自然的现象。
对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林德扬自杀,新青年同仁都意识到了这个时代所给予青年们的一种负面影响。同为北京大学学生的罗家伦,在分析林德扬自杀时即道出了一般新青年的思想和精神状况:“我以为‘五四’以后,我们青年在人生观上有了一种大大的觉悟,就是把以前的偶像,一律打破,事事发生一种怀疑的心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自然东望也不是,西望也不是,旧的人生观既然打破了,新的人生观还没有确立。学问又没有适当的人来做指导,于是消极的就流于自杀。这正是人生观将改未改的‘回旋时代’里不可免除的现象。”⑥志希:《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载《新潮》1919年2 卷2号。身为青年导师的陈独秀在针对同一事件的《自杀论》中更提出了“思想杀人”的见解:“这班现代的青年,心中充满了理想,这些理想无一样不是和现代底道德、信条、制度、习惯冲突,无一样不受社会的压迫。他们的知识又足以介绍他们和思想潮流中底危险的人生观结识,若是客观上受社会的压迫,他们还可以仗着信仰鼓起勇气和社会奋斗,不幸生在思潮剧变的时代,以前的一切信仰都失了威权,主观上自然会受悲观怀疑思想的暗示,心境深处起了人生价值上的根本疑问,转眼一看,四方八面都本来空虚、黑暗,本来没有奋斗、救济的价值,所以才自杀。象这种自杀,固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自杀,但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不算是社会杀了他,算是思想杀了他呵!”⑦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载《新青年》1920年7卷2号。新青年同仁更多地看到了新旧交战时代给这些追求新思想的“新青年们”所造成的精神困境,而没有留意到这样的时代氛围,同样给传统道德的信奉者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梁济在《敬告世人书》中有言:“今吾国人憧憧往来,虚诈惝恍,除希望侥幸便宜之外,无所用心;欲求对于职事以静心真理行之者,渺不可得。此不独为道德之害,即万事可决其无效也。”⑧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载《新青年》1919 年6卷1号。对于梁济这样以忠孝节义为人生道德支撑的人而言,世间道德如此败坏,“以死殉道”“以死救世”乃是自己的责任:“若使世事未坏到极处,我亦不必倾身救之。若世事虽坏,而辛亥与丁巳,(原作丙辰,系属笔误)或有耆儒,或有大老,表彰大节,使吾国历史旧彩不至断绝,则我亦不必引为己责。”⑨梁漱溟:《桂林梁先生遗书·年谱》,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8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梁济的自杀,也正是源于世道的败坏,而决心以死挽救道德的堕落,并以自己的殉身接续历史的“旧彩”。因此,陈寅恪悼念同样沉湖自尽的王国维的挽词,也同样适用于梁济:“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
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①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载《学衡》1928年第64期。由此可见,这两起看似性质截然相反的自杀事件,实际是同一枚时代硬币的两面。从根本上讲,都是“思想激变”的结果,一方面是旧的传统思想伦理道德被打破,丧失了权威与庇护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新思想新道德尚未确立,还不足以构成新时代的精神依托,于是“旧者”无所依,“新人”心茫然,“自杀”便成为一种带有时代症候的选择。只不过,新青年林德扬的自杀是死于一个还没有到来的新世界,而清室遗臣梁济则死于一个失去了的旧世界。
二、是与非:“自杀”的价值意义纷争
时人对于这些以“救世”为旨归的自杀者的价值评判,是对于“自杀者”最好的纪念,同时也是自杀者所追求的终极社会价值。如果说关注遗老梁济之死,只是新青年派略尽一点言论的义务,那么对于新青年林德扬的自杀进行剖析、评判则是身为新文化倡导者和思想启蒙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对这两起新旧人物的自杀事件的是非曲直评判,新青年同仁的态度和情感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梁济之死,新青年同仁固然不会像旧派和遗老界一样大肆给予赞美和褒扬乃至效仿,②梁漱溟在《桂林梁先生遗书·年谱》中记载:“都人士闻其事者莫不哀感生敬。请太傅陈公宝琛以闻于皇室,赐谕矜悼,予谥贞端。有蒙古旗人故理藩部郎中吴公宝训(字梓箴)佐彭公为《京话日报》编辑有年,因亦与公稔,感公事,后二十日投湖中继殉焉。”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90页。但是也并不像梁济在遗书中所预料的那样必遭新派人物的大骂。相反,对此事做出评判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并没有如梁济生前所预期的那样对这种“守旧”行为大加挞伐,而是绕过了“遗老”“纲常名教”“殉节”等等与新文化、新思想截然对立的范畴,转而对梁济纯洁的精神和内外一致的人格大加赞扬,发表了自己的几重感想:“第一感想,就是梁先生自杀,总算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人物。新时代的人物,虽不必学他的自杀方法,也必须有他这样真诚纯洁的精神,才能够救济社会上种种黑暗堕落。第二感想,就是梁先生主张一致,不像那班圆通派,心里相信纲常礼教,口里却赞成共和;身任民主国的职务,却开口一个纲常,闭口一个礼教。这种人比起梁先生来,在逻辑上犯了矛盾律,在道德上要发生人格问题。第三感想,就是梁先生自杀,无论是殉清不是,总算以身殉了他的主义,比那把道德礼教纲纪伦常挂在口上的旧官僚,比那把共和民权自治护法写在脸上的新官僚,到底真伪不同。第四感想,就算梁先生是单纯殉了清朝,我们虽然不赞成,然而他的几根老骨头,比那班满嘴道德,暮楚朝秦冯道式的元老,要重得几千万倍。”③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在这里,陈独秀是把梁巨川作为“以身殉主义者”给予了肯定。实际上,在其他言论中,陈独秀对这种旧式的“殉节”行为是持一贯否定态度的,认为这些“殉身者”实际也不过是牺牲品:“男子殉忠,女子殉节,都是中国、日本重要的道德,最大的荣誉;印度还有寡妇自焚的事。象这类的自杀,完全是被社会上道德习惯压迫久了,成了一种盲目的信仰。因为社会上不但设立许多陷阱似的制度,象昭忠祠、烈士墓、旌表节烈、节孝牌坊等奖励品,引诱一般男女自杀,而且拿天经地义的忠孝大义,做他们甘心自杀底暗示。这种压迫和暗示受久了,便变成一种良知,觉得殉忠殉节,真是最高的道德,不如此便问心不过。”④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载《新青年》1920年7卷2号。但无论如何,陈独秀给予梁巨川的评价是真诚而适切的。无论是把梁济放在“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旧历史链条中做纵向比较,还是把他放在现世的语境中与周围口是心非、朝秦暮楚的新、旧元老做横向比照,都凸显了梁济自杀的意义和价值;而这种“尘归尘,土归土”式的评价既体现出对于逝者的尊重,也体现出对于“殉道者”的敬重,更有对于生者——梁漱溟等遗属的安慰。同样,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虽然并没有像陈独秀那样给予死者以赞扬,但也没有实行新派对旧派应有的批评,而是从吸取教训的角度给予了温和的回应。他在回复梁漱溟为父亲自杀辩护解说的信中,首先肯定了梁漱溟在传记中所表现出来的诚恳态度以及由此所生的对于梁济老先生的敬意:“梁漱溟先生这封信,讨论他父亲巨川先生自杀的事,使人读了都很感动……使我们知道巨川先生精神生活的变迁,使我们对于他老先生不能不发生一种诚恳的敬爱心。这段文章,乃是近来传记中有数的文字。”同时,胡适也从梁漱溟为父亲申辩的矛盾处指出了“梁巨川先生的致死的原因,不在精神先衰,乃在知识思想不能调剂补助他的精神,二十年前的知识思想决不够培养他那二十年后‘老当益壮’的旧精神,所以有一种内部的冲突,所以竟致自杀。我们从这个上面可得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早点预备下一些‘精神不老丹’,方才
可望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①胡适:《通信:梁漱溟胡适〈梁巨川先生的自杀〉》,载《新青年》1919年6卷4号。总体看来,新青年同仁对于梁巨川的“殉身”是给予了充分的“了解之同情”的。
相比较对旧式人物自杀所持的一种冷静、同情乃至客气的态度,对于青年学生林德扬的自杀,新青年同仁的态度和情感显然要急切、热烈得多,对于青年自杀问题的探讨也深刻得多,并直接影响到了思想启蒙者对新思潮的警惕和反思。纵观同学、老师对于林得扬的追掉纪念文字,一个共同的情感即是对于一个青年之死的惋惜以及由此号召鼓励新青年们树立生而奋斗的人生观而非厌世自杀的人生观。但是,除了这些“人之常情”的表达,新青年同仁之间,身为启蒙者的老师和被启蒙的学生之间以及同为思想启蒙者、引导者的老师之间,对于这场死亡的态度和价值评判是有着诸多分歧的。
首先是对待“自杀”是否道德、是否有积极效用的评判。罗家伦作为死者林德扬的同学和新思想启蒙下的新青年,对于“自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早在《出世》一文中,罗家伦便从积极的角度对于“厌世”以及“因厌世而自杀”做出了高度评价:“‘厌世’同‘出世’完全是两件事。‘厌世’是很好的,我是极端赞成。我们这班青年人,第一应当奋斗,积极的去改革现状,化这可厌的世为不可厌的世,若是奋斗得精疲力尽,智绝谋穷,再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作了,而于此世仍无一丝一毫的补助,然后自杀(凡有不曾奋斗或是奋斗而不到最后一步而自杀的,还是懦夫)。像这样的自杀真是世间最有荣誉的事,惟有最高尚的人格方才可以办到,所以我更说,‘世上没有自杀决心的人什么事都办不好。’唉!自杀自杀,高谈‘出世’的人配实行你吗?”②志希:《出世》,载《新潮》1919年1卷4号。北大学生林德扬自杀后,罗家伦虽然对于林德扬没有奋斗到最后一息便自杀深感可惜,但是对这种热血青年的自杀依旧充满了赞佩:“我并不是反对厌世自杀的人,更不认自杀为不道德,我常以为中国自杀之风稀少,(匹夫匹妇自经于沟壑者不计)正是中国人心气薄弱的一种表现。”③志希:《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载《新潮》1919年2 卷2号。对于学生的这种想法,身为北大教授的蒋梦麟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认为“青年自杀,也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弱”。他不把青年自杀归罪于社会:“社会本来不能自己改良,要我们个人去改良他,社会还没有改良,我就把自己杀了,这社会还有改良的日子么?”同时,蒋梦麟对自杀提出了带有强制性的救济办法,主张从观念上、从法律上认定“自杀”为“有罪”。与蒋梦麟不同,北京大学的另一位青年导师李大钊则有着与罗家伦近似的态度和主张。他从一个更为科学的角度分析了自杀问题,把自杀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时代文明与社会制度:“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而“十九世纪末年的世界,已经充满了颓废的气氛,物质文明渐渐走入死境,所以牵着人也到死路上去。各人生活上塞满了烦闷,苦恼,疲倦,颓废,失望,怀疑。青年的神经锐敏,很容易感受刺激,所以有许多的青年,做了‘自杀’时代的牺牲。”既然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不良,李大钊主张从理解和尊重的角度去看待自杀者:“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人于不直接妨害社会,迷惑他人的范围内,有自己处决他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权。我们只能批评自杀者的人生观,说他是或非,指导一般生存的青年向人生进路的趋向,不能责备自杀者的个人,说他道德不道德,罪恶不罪恶。”作为青年导师,李大钊从理智上并不主张青年自杀,而“希望活泼泼的青年们,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但出于自身的性情,他还是忍不住对自杀的热情“礼赞”:“青年自杀的流行,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是迷乱社会,颓废时代的里的曙光一闪,我们应该认定这一道曙光的影子,努力向前冲出这个开头,再进一步,接近我们的新生活。诸君须知创造今日新俄罗斯的,是由一千八百五十年顷自杀的血泡中闯出去的青年。创造将来的新中国的,也必是由今日自杀的血泡里闯出去的青年。创造将来的新中国的,也必是由今日自杀的血泡里闯出去的青年。我悯悼这厌世自杀的青年,我不能不希望那造世不怕死的青年!我不愿青年为旧生活的逃避者,而愿青年为旧生活的反抗者!不愿青年为新生活的绝灭者,而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创造者!”④守常:《青年厌世自杀问题》,载《新潮》1919年2卷2号。众所周知,李大钊并不仅仅是一个“自杀”的言语赞美者,而实实在在是一个实践者,他最终成为一个为主义而献身的“殉道者”。
其次是对于“爱国的自杀”或“为国事殉身”的定位和褒扬问题。在对林德扬的纪念文章中,罗家伦特别提起了林德杨的爱国言行:“林君是一个热心国事的人……他有肺病,听到五四运动发生了,
他就立刻下山,抱了病来做事。”“当时他在国货维持股办事,而每天还送一篇白话文字到新闻股来。每谈国事,愤慨泣下。”“他以为救国空言无补,而认定基本计划在实业,于是筹资办第一国货店于东安市场。”在罗家伦的文字中,一个爱国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学生和导师之间显示出了明显的反差,或者说作为思想启蒙导师的新青年派对于“爱国”“为国事牺牲”“殉国”一类字眼的运用是非常慎重的。在蒋梦麟的悼念文章中只是几次提及“林君是个好人,这近乎是一个平常到空洞的定位”。陈独秀在针对这一事件而写的《自杀论》中则直接把林德杨定位为“厌世自杀者”。蔡元培在林德扬追悼会上发表的演说词中,虽然把林德扬同近代史上两位著名的自杀人士——杨笃生和姚桢相提并论,但从头到尾却只字没有提到“爱国”二字。而是从为事业奋斗的角度把林德扬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杨、姚相提并论:“这两位先生,都是因奋斗失败而自杀的。林君也因奋斗而自杀,所以同杨先生、姚先生差不多。”“他对于五四运动很出力,并且创办国货店——抵制日货根本的方法。”“所以决然自杀,要想刺激他的同志,继续去实行他的计画,所以牺牲自己一身,做发展国货的广告。”①蔡元培:《在林德扬追悼会上的演说词》,见《晨报》,1919-12-24。在纪念中,思想导师们绕过了对于林德扬的“爱国”定位转而谈其他,并非是有意贬低,而是有着更慎重的考虑和更深的用意。众所周知,“国家观念”在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以来的启蒙者诸如梁启超、章士钊、陈独秀、高一涵等人都曾在这一问题上做过详解,反复辨析、澄清现代国家观念与传统国家观念的本质性差异。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后,共和国徒存其名,新知识界痛感“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②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1916年1卷6号。。因此,新青年同仁更通过对“国家”观念的辨析进而对现有的专制统治进行批判:“近世国家之通义曰,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易词言之,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③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载《青年杂志》1915年1卷2号。可见,什么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怎样的国家才值得青年去爱乃至为之献身,这在五四时期已经不仅仅是个新旧观念问题,而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早在陈独秀为章士钊协办《甲寅》月刊时期,就以一篇极具轰动效应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提出:“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自觉心所排而去尔。”④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甲寅》1914年1卷4号。而在五四时期“共和”还是“专制”的生死较量中,高一涵更直接提出:“国家非人生之归宿。”⑤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载《青年杂志》1915年1 卷4号。陈独秀则进一步把“国家”放置在近代思潮中“黑暗的能够杀人的部分”之中,并从社会学的角度把“殉国”同“烈女殉夫”“忠臣殉君及奴仆殉主人”等归为一类,称之为“社会道德习惯上积极的压迫”⑥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载《新青年》1920年7卷2号。。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一改其在1916年《我之爱国主义》中对于殉国烈士有限度但仍热烈的赞佩。可见,在国势未明,“共和国”在专制、复辟的风潮中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评价林德扬的自杀而远离“爱国”“殉国”等容易混淆视听的概念以免给热血青年以误导,显然有着启蒙者的良苦用心。
三、迎与拒:自杀所引发的“新思潮”反思
新青年的自杀事件导致的另一重要后果是引发了新文化运动主将对于“新思潮”的警觉与反思。
陈独秀在《自杀论》中把反思的矛头直指当下流行的新思潮,提出了“思想杀人”的警示:“忠节大义的思想固然能够杀人,空观、悲观、怀疑的思想也能够杀人呵!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要注意呵!要把新思潮洗刷社会底黑暗,别把新思潮杀光明的个人加增黑暗呵!”⑦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载《新青年》1920年7卷2号。陈独秀指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思想中存在着黑暗的杀人的部分,而且这种思潮在中国的思想界还算是新的,占据着相当的势力,他列举出近代思潮中的黑暗的杀人的部分包括唯实主义、本能的、自然的、地上的、物的、全恶的、全丑的、现世的、人性与兽性同恶、科学万能、现实、唯我、客观的实验、国家的。“这种新思潮,从他扫荡古代思潮底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了他,但是要晓得他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
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呵!”①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载《新青年》1920年7卷2号。陈独秀提出救济的办法是尽快地超越这令人心生悲观、绝望的近代思潮,而以带给人希望的最近代思潮取而代之,他列出的最近思潮包括:新理想主义入新唯实主义、情感的、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生的、人的、恶中有善的、丑中有美的、现世的未来、人性比兽性进化、科学的理想万能、现实扩大、自我扩大、主观的经验、社会的非国家的。且不论陈独秀所列举的“近代思潮”和“最近代思潮”的趋势、内容是否准确,也不论陈独秀提出的“以更新救新”的方法是否适当,单从这两两相对的范畴及内涵比照中,可以明显觉察到:一些折中的、调和的、相反相成的概念已经代替了以往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概念。而从根本上讲,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主将对以往决绝姿态的一种反省。随后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中更有了对以往观念的修正性阐释。在谈到“支配中国人心底最高文化——伦理的道义”时,陈独秀一改以往对于旧道德彻底抨击、一揽子否定的态度,而是做了一分为二的区分:“同一忠、孝、节的行为,也有伦理的、情感的两种区别。情感的忠、孝、节,都是内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纯的,伦理的忠、孝、节,有时是外铄的、不自然的、虚伪的。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便更当看重。”有感于中国的文化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陈独秀主张“应当拿美与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感情”②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载《新青年》1920年7卷3号。。可见,陈独秀此一时期的见解与他在1915年所提倡“现实主义”“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与他以“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来敬告青年的主张,更与他抨击“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的态度,已不可同日而语。就陈独秀提倡以“美与宗教”来培养国民的性情而言,又和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走到了一处。
五四运动的另一领袖人物蔡元培同样是意识到了新思潮的流弊,而直接以“洪水猛兽”来做比喻:“我以为用洪水猛兽来比喻新思潮,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如何对待这俨然洪水猛兽的新思潮,蔡元培也指出不能用湮的方法,而应该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③蔡元培:《洪水与猛兽》,载《新青年》1920年7卷5号。就在林德扬自杀后不久,蔡元培又提出“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警示,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已经出现的三种流弊,其中之一直接和青年们的厌世自杀相关:“想用简单的方法,短少的时间,达他的极端的主义;经过了几次挫折,就觉得没有希望,发起厌世观,甚且自杀。”由此,他提请新文化运动诸君注意:“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以美育“引起活泼高尚的感情。”④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见《晨报副镌》,1919-12-1。蔡元培这一主张正是针对以“科学主义”为主导思想,以“实利主义”为实际导向的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一种纠偏。
实际早在鲁迅进入启蒙阵营之前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就表明了他对新文化运动后果的一种怀疑。对于他所提出的“铁屋子”的譬喻,人们更多理解为对那间“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打破的决心和愿望,而没能充分注意到鲁迅所说的对睡者唤醒的后果:“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⑤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同样,周作人的长诗《小河》,也形象地表达了自己的“忧惧”。应该说,周氏兄弟作为启蒙和革命的“过来者”,一开始就对新文化运动表达了内心的忧虑,只不过二人都是以文学寓言的方式做诗意表达,而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显然是不容易为人所领悟得了的。
固然,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所发生的大面积的、路径不同的转向以及新青年同仁的分道扬镳,有着更为复杂、更为多元、更为深广的原因,但是以林德扬为代表的“新青年自杀事件”给新文化倡导者的触动并促使启蒙者转向对新思潮的反思,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契机。
【责任编辑:王建平;实习编辑:杨孟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