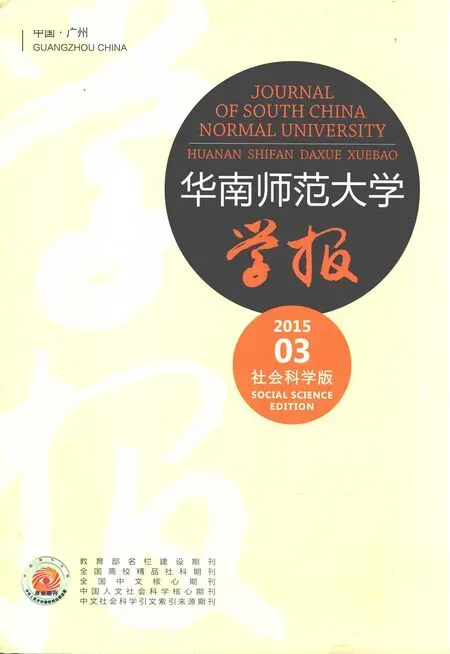黄遵宪的文化姿态与思想经验
2015-03-19左鹏军
左鹏军
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年3月28日),杰出思想家、外交家、爱国诗人黄遵宪在家乡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因肺病逝世。在他仅57年的一生中,除了在政治改革、维新变法、外交事务等方面作出的执著努力和杰出贡献外,还留下了可以代表近代中国人了解和认识日本最高水平的《日本国志》,以及收录在《人境庐诗草》与《日本杂事诗》中的1 100 多首诗歌。贯穿于黄遵宪政治活动、外交活动、学术活动、文学活动之中的,则是以颇为深邃的思考、相当广阔的视野为基础,探寻世界发展大势与西方列强及日本发达强盛的奥秘,追问清朝政治腐败、国贫民弱、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原因,求索中国走向开明法治、富裕强盛的道路。这是黄遵宪一生为之执著奋斗、无怨无悔的核心所在,也是他留下的最大精神财富。在这一艰难的精神探索、思想变革和心灵历程中,黄遵宪的文化姿态与思想成果、诗歌创作与传承变革,留下了处于时代前沿、具有深刻启发性、至今犹可深长思之的丰富思想经验。
一、当代认同与历史影响
黄遵宪一生所追求的主要并不是诗,正如他自己感慨的“穷途竟何世,馀事且诗人”①黄遵宪:《支离》,见《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八,第773 页,钱仲联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梁启超也说他“不屑以诗人自居”②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24 页,舒芜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在经过多年的外交生涯,在政治改革、维新变法上遇到失败、面临穷途末路之后,他却只能成为一个诗人。无论如何,诗,都是黄遵宪的最大成就之一,也是他倍受当时各界及后人关注和评价的一个主要方面。黄遵宪生前身后,诗名綦盛,影响及于多个方面和多个时期,可谓广泛而深远。这首先是因为人境庐诗以其广阔而深入、稳健而创新、特色而兼容的方式处于时代诗坛之高点,取得了具有突出时代性、标志性意义的思想艺术成就。与此同时,也与多位著名人物的评论赞誉从而赢得了关注、扩大了影响密切相关。在并不漫长却相当复杂的政治经历中,黄遵宪与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多位重要政治人物熟识并多受提携。又由于人境庐诗具有纵横自如、牢笼百变、大气包举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气度,从而与一般所谓同光体、中晚唐派、西昆体及其他诗人文士多有交往唱和且多受认同。黄遵宪与张荫桓、郑藻如、何如璋等多位岭南籍官员及其他人士联系密切,又曾与大河内辉声、石川英、重野安绎、冈千仞、宫岛诚一郎等多位日本诗人文士交往密切。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黄遵宪在当时国内各界、日本等地受到的关注和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同派别人士之间密切交流、互相影响的文学史事实和中国近代文坛创新发展、复杂多变的面貌。
就诗歌创作而言,黄遵宪与多位维新派政治家、文学家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深挚,这不仅仅在于诗歌主张与诗歌创作方面的一致性,而且在于政治主张、文化观念上的相通性。现有史料可以证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主张曾经直接而深刻地受到黄遵宪诗歌观念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影响启发;另一方面,梁启超的持续关注和高度评价,也对黄遵宪其人其诗广为人知、声名日隆起了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黄遵宪及其诗歌的广泛影响和地位确定,首先是从梁启超的积极鼓动、大力号召开始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并产生显著影响的《饮冰室诗话》中给予最充分评价并引为“新派诗”和“诗界革命”的同道者就是黄遵宪,这部诗话中关注最多、评价最充分的一位诗人就是黄遵宪。梁启超曾说:“公度之诗,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①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24,63 页。;“公度之诗,诗史也”②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24,63 页。。他后来还说过:“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82—83 页,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尽管梁启超对清代诗坛的整体评价在今天看来可议之处甚多,对于金和、黄遵宪和康有为的赞誉之词过多夹杂了个人好恶和主观随意色彩,但是以这些言论与评价姿态为导引,黄遵宪及其诗作受到一批政治上、文学上同道者的普遍赞扬,并对其后多年的黄遵宪研究及近代诗歌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黄遵宪其人其诗还受到其他具有相近政治倾向或文学主张的多位人士关注和赞扬。康有为说:“自是久废,无所用,益肆其力于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公度岂诗人哉?”④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见《康有为诗文选》,第101 页,舒芜、陈迩冬、王利器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不仅对黄遵宪及其人境庐诗多有理解之同情,而且融入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和文学主张,可见康有为对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认识。蒋智由也感慨说:“公才不世出,潦倒以诗名……才大世不用,此意谁能平?”⑤蒋智由:《挽黄公度京卿》,见《饮冰室诗话》,第117 页。对黄遵宪未能实现政治理想、只能以一个诗人终老而深为感慨,当然也寄托了自己的人生感受。另一位维新派人士狄葆贤也评论说:“黄公度先生,文辞斐亹,综贯百家。光绪初元随使日本,尝考其政教之废兴,风土之沿革,泐成《日本国志》一书,海内奉为环宝。由是诵说之士,抵掌而道域外之观,不致如堕五里雾中,厥功洵伟矣哉!先生雅好歌诗,为近来诗界三杰之冠。”⑥平等阁主人(狄葆贤):《平等阁诗话》卷二,第1,3 页,(上海)有正书局宣统二年版。主要从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思想政治价值、对当时中国的启发借鉴价值方面进行评价,深得黄遵宪进行日本研究并撰写研究论著及相关诗歌的主旨。他在得知黄遵宪去世消息之后作的挽诗五首同样满怀感慨同情。其一云:“竟作人间不用身,尺书重展泪沾巾。政坛法界俱沉寂,岂仅词场少一人?(近得先生正月粤中书云:‘自顾弱质残躯,不堪为世用矣。负此身世,负我知交。’不意竟成谶语。)”其二云:“悲愤年年合问谁?空馀血泪化新诗。微吟踏遍伤心地,不见黄龙上国旗。(庚子秋,余夜过威海卫,见英国兵舰云屯,电光灿烂。口占志感诗有‘灵风彻夜翻银电,不见黄龙上国旗’句。嗣见先生游香港诗,亦有‘不见黄龙上大旗’一语。)”其五云:“奇才天遣此沉沦,湘水愁予咽旧声。莫问伤心南学会,风吹雨打更何人?(先生官湘臬时,与陈佑民中丞、江建霞、徐砚父两学使,皆为南学会领袖,今诸君俱下世矣。)”⑦平等阁主人(狄葆贤):《平等阁诗话》卷二,第1,3 页,(上海)有正书局宣统二年版。将有关史实的叙述与对逝者的怀念融会于一,将个人感情与国家局势联系起来,从不同角度对黄遵宪的政治建树与伤时忧国、历史贡献与失望遗憾表达得充分而真挚,表达了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心声。黄遵宪之弟遵楷也曾指出:“其诗散见于宇内者,辄为世人所称颂。以非诗人之先生,而使天下后世,仅称为诗界革命之一人,是岂独先兄之大戚而已哉?”⑧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见《人境庐诗草》卷末,第1 页,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将黄遵宪的诗歌成就与未竟事业联系起来评价,中多感慨遗憾之音,反映了家族后人的复杂认识和深切感受。这种对黄遵宪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感慨同情影响了许多人,延续了许多年。时过多年之后,钟叔河也指出:“黄遵宪首先是一位维新运动家,一位启蒙主义者,一位日本研究专家,然后才是一位诗人。他是一位学术型的政治人物,他的诗,也主要是学术的诗,政治的诗。”⑨钟叔河:《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第29 页,(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89年版。按:钟叔河在《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说:“黄遵宪首先是一个维新运动家,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爱国的政治人物,然后才是一位诗人;他的诗,也主要是政治的诗。”第390 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黄遵宪的诗歌理论观念和创作实践中始终带有“馀事且诗人”的特点,这是认识和评价其人其诗时必须注意体会并有所践行的。
黄遵宪的文学观念和诗歌创作还深刻影响了五四一代新文学家。更准确地说,当时年轻气盛、充满激情却又内涵不丰、准备不足而又跃跃欲试的一群活动家和文学家们,从黄遵宪的文学观念与诗歌创作中找到了自己所欲鼓动倡导新文学与新文化所迫切需要的思想资源,产生了如遇前代知音的精神感受和思想认同。胡适曾从倡导白话新诗、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出发高度评价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主张,简单主观、一厢情愿甚至不惜损害论断的科学性、合理性地称之“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①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11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周作人也不止一次地表示钦佩黄遵宪的思想和见识,并从现代新诗、新文学创建的角度称赞“其特色在实行他所主张的‘我手写我口’,开中国新诗之先河”②周作人:《诗人黄公度》,见陈子善选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326 页,岳麓书社1988年版。,显然也是就其与现代新诗的相通性进行评价。郑振铎指出:“欲在古旧的诗体中而灌注以新的生命者,在当时颇不乏人,而惟黄遵宪为一个成功的作者”③郑振铎:《文学大纲》,“民国丛书”第四编五十四册,第2047 页,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并盛赞“这些山歌确是像夏晨荷叶上的露珠似的晶莹可爱”④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456 页,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朱自清也曾赞扬黄遵宪的“新诗”成就及其对五四新诗运动的启迪:“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捡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语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试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⑤朱自清:《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首,第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郑子瑜还曾专门撰文论证黄遵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⑥郑子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黄遵宪》,1989年7月郑子瑜教授寄示笔者之论文手稿复印件。按:郑子瑜先生已于2008年6月30日在新加坡去世,特记于此,以志怀念。。这些言论或观点显然都是从现代白话新诗及新文学的渊源与发生、创新性与合法性等方面进行考察并得出结论的;而且这种思考方式、评论角度和基本观点产生了至今犹在的深远影响,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成为一种话语垄断和思想霸权。从近现代诗歌变革历程与相关文献史实提供的实证可能来看,这样的认识与其说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和学术价值,不如说主要体现了这批新文学倡导者、思想家、尝试者的主观愿望和文化态度。在这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新文化思想观念的宣传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致于明显伤害了立论的可靠性和结论的允当性。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后的多种论著对于黄遵宪诗歌创作与现代白话新诗关系的解读,搀杂了过多的先验观念和主观色彩,政治性、思想性和实用性占据上风的生硬论断与相关史料、客观事实和学理判断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已经日益明显地限制和影响着近现代诗歌与文学思潮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这是研究者需要清醒明辨并注意鉴戒的。
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黄遵宪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与新文学、新文化相对或相反的方面。近现代以来,在政治理想、文化态度、文学观念上进化/发展、变革/革命观念持不同立场、相异观点的一批人士则从另外的角度对黄遵宪及其诗歌进行考察和评价,认识其诗歌创作的局限性、可商榷处,得出了一些与上述见解颇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认识。胡先骕指出:“黄公度、康更生之诗,大气磅礴则有之,然过欠剪裁,瑕累百出,殊未足称元气淋漓也。”⑦胡先骕:《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见《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第1305 页。又说:“五十年中以诗名家者甚众,决不止如胡君所推之金和、黄遵宪二人。然胡君一概抹煞,非见之偏,即学之浅,或则见闻之隘故也。黄氏本邃于旧学,其才气横溢,有足多者。然其新体诗,实与其时之政治运动有关……可见当时风气,务以新奇相尚。康有为孔子改制之说,谭嗣同之《仁学》,梁启超《时务报》《新民丛报》之论说,《新民丛报》派模仿龚定庵之诗,与黄遵宪之新体诗皆是也。黄之旧学根柢深,才气亦大,故其新体诗之价值,远在谭嗣同、梁启超诸人之上。然彼晚年,亦颇自悔,尝语陈三立:天假以年,必当敛才就范,更有进益也。”⑧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第1306 页。这显然是针对梁启超所说“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83 页。而发,可见品鉴趣味与见识的明显差异,更反映了评价角度和文化观念的明显矛盾。从黄遵宪诗歌创作及其与新派诗关系、当时诗坛状况的角度看,胡先骕所论特别启人深思的是:倍受胡适推崇②按: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这个时代之中,我只举了金和、黄遵宪两个诗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有点特别的个性,故与那一班模仿的诗人,雕琢的诗人,大不相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过:“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胡适此观点显然受到梁启超直接影响。的金和、黄遵宪在诗家众多、诗派林立的近代诗坛的合理地位与恰切评价究竟如何;所谓“新派诗”或“新体诗”的理论导向和创作实践与当时政治运动的密切关系应该如何认识评价;在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中,政治态度与文学观念、创新尝试与旧学根柢的关系及各自作用当如何体会等,都是许多论者认识不清或根本没能意识到的。徐英说得更加激烈:“金和、黄遵宪、康有为之诗,谬戾乖张,丑怪已极。而梁启超谓其元气淋漓,卓然大家,阿其所好,非通论也。”③徐英:《论近代国学》,见《人境庐诗草笺注》卷末诗话,第447 页。同样是针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有关言论而发的。通过对深受梁启超推崇的金和、黄遵宪、康有为之诗的批评,表达了持重保守的文学观念,反映了对当时总体文学与文化走向的认识,其中对以政治改革和舆论宣传为主要目标的“诗界革命”中的确存在的急躁草率、追逐新奇现象提出的严厉批评尤具启发性。这样的话虽然出自数十年以前,但对今天的近代文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治学方法、学术方式、考察角度与文化观念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从黄遵宪研究与近代诗歌变革、现代新诗倡导的理论内涵和学术史经验来看,这些与新文学和新文化立场迥然不同甚至明显对立的认识,以另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提出了近代诗歌变革中产生的新现象、出现的新问题,也是黄遵宪及其诗歌创作引起出自不同流派、具有不同观念的诗歌批评家关注并产生显著学术影响的有力证明。对于这样的声音,不应该采取有意回避或进行简单地批判,而应当从更广阔的文学与文化视野、从更深切的理论思辨和更丰富的创作实践中具体考察、深入体会,汲取其中具有启发性、前瞻性的内容。④按:关于此问题,拙文《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文学立场及其影响之省思》尝有讨论,载《文学遗产》2013年第4 期。
面对多年来黄遵宪诗歌及近代诗歌变革如此矛盾丛生、难以统一的评价,在黄遵宪研究方面用力甚勤并以《人境庐诗草笺注》享誉学界的钱仲联曾指出:“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以为疵累百出,谬戾乖张。予以为论公度诗,当着眼大处,不当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其天骨开张,大气包举者,真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抚时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至论功力之深浅,则晚清做宋人一派,尽有胜之者。公度之长处,固不在此也。”⑤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第161—162 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主要从黄遵宪诗歌评价的矛盾现象和不同结论着眼进行分析并试图寻求其中的共同点,着重强调人境庐诗在继承诗歌传统基础上着意创新的辽阔广远、雄浑遒上气象,对近代政治历史事件、国家民族命运有意纪录表现的诗史价值,颇有化解消弥以往观点分歧、融会综合见解异同的用意。但是从黄遵宪及近代诗歌研究的学术历程及其经验的角度来看,关于人境庐诗歌及相关问题评价出现的分歧,固然有着不同诗歌流派、评价角度、品鉴趣味、个人好恶等差异性、矛盾性因素,但更深刻也更值得关注的应当是这种矛盾现象所表现的关于新旧文学的不同文学观念、文化观念,所反映的关于近代以来诗歌变革、文化变迁的成败利钝及其经验教训的基本认识,也透露出中国诗歌与文学批评在中西古今、文白雅俗、新旧取舍之间探索出路、寻求可能、不断尝试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困境与艰难。这已经是一个有必要冷静面对、深刻思考并寻求合理方案与最佳可能的具有广泛思想文化意义的问题。因此,钱仲联基于深入细致的文献功夫做出的推动黄遵宪研究的有关论述,提出了引人深思的学术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但尚未真正找到会通统一黄遵宪及其诗歌评价的关键,也未从理论观念与学术变迁角度触及产生这些分歧的深层原因并将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也可以说将这一问题留给了后来的研究者。
将上述关于黄遵宪其人其诗的种种矛盾认识、不同评价视为一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现象,则应当看到,无论基于何种文学标准或文化观念,这些出自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言论都是特定思想观念、学术条件、政治环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时代和评论者个人的观念印迹,都是学术贡献与局限、思想价值与缺失共生并存的,其中的得失成败、经验教训、启发遗憾也可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史话题。从总体上看,以往对黄遵宪的研究评价在揭示若干文学史事实、得出一些有价值结论、充分显现其当世价值和历史贡献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明显的缺失或遗憾,尚待弥补纠正或丰富完善。
二、诗歌取径与诗学观念
严羽尝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①严羽:《沧浪诗话校释》,第26 页,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此语颇为流行,对明清时期许多诗人的文学观念、创作实践乃至诗歌整体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清人钟秀曾经提醒地批评说:“严仪卿曰‘诗有别才’,千古定论。又曰‘非关学也’,斯言一出,贻误后人不小,不得谓非语病。虽然,沧浪斯言亦为宋人以议论为诗者对症发药,其所谓‘非关学’者,殆谓学诗者不在着力,非谓学诗者不必读书,第恐后人误会其意,所关非浅也。”②钟秀:《观我生斋诗话》卷一,见《沧浪诗话校释》,第27页。但是,明清以降的文学史上,在诗歌创作中过多倚仗才情而轻视读书学问者大有人在,以致于形成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诗坛风尚并一直影响到近代诗坛。在这种诗坛风气之中,黄遵宪对于诗歌创作中才情与学问、感悟与读书等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显示出相当高明的见识和应对能力。他并未仅仅依靠过人才情使诗歌创作走向以情韵独胜的道路,而是保持着对创作根柢、门径、内涵的尊重,对读书、学问给予足够关注、多所用心并有意运用。从当时的诗坛状况和传统诗歌面临的文化环境而言,无论从理论观念还是从创作实际来看,这种选择路径和处理方式都显然更有合理性,从而能够在创作中将才华与学问结合得非常紧密,取得兼顾其长而兼得双美之效,由此造就了人境庐诗的独特思想深度和艺术风貌。
在许多诗人都不能不面临和处理的通俗与雅正、浅白与古奥的关系问题上,黄遵宪采取的依然是综合兼顾、取其优长的认知方式和处理方法,从中获得广阔包容的理论空间和丰富多变的创作可能。黄遵宪对中国语言文学中的通俗化、白话化传统非常熟悉,包括客家山歌民谣、浅易朴素的诗词曲、通俗小说戏曲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形态,甚至关注日本小说戏剧、民间文学中的通俗因素,从而使自己创作的一部分作品具有突出的通俗晓畅、浅白明快的思想特征和语言特点。黄遵宪文学思想与诗歌创作中的这一侧面正是被后来的多位研究者高度关注并推崇的,被认为开启了近现代文学语言通俗化、白话化的先河,甚至被认为是五四白话新诗、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这种思考方式和评价方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着主导地位,至今仍为部分研究者所坚持。从有关文学史实和学术史经验来看,不能不承认,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固有一定根据,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但是,至今可见的丰富文献史实和大量诗歌也在有力地证明,黄遵宪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中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即更多地从中国诗歌的典雅端庄传统出发,有意守护和追求渊雅正统、讲究古奥深邃的倾向。这既是黄遵宪文学修养、诗歌品位、创作能力的重要体现方式和实现途径,又是作为诗人的黄遵宪以学养功夫、创作实力获得当时由官员名士构成的主流诗人、正统派文学家及有关政治人物关注认同的必经途径。以往的研究者对融入主流诗坛之于黄遵宪诗歌创作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意义关注无多、认识不足,而经常过于片面、简单地强调其诗歌创作通俗化、浅易化倾向的意义和价值。这既不符合黄遵宪及其诗歌创作的文献史实,又不符合黄遵宪与各派诗人联系交往、与近代诗坛保持复杂关系的实际情况。这主要是不顾丰富的文学史事实,将某些既无思想深刻又无科学价值的既定主观政治观念和思想逻辑强加于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主观驾驭、强行解释的结果,从而将纷繁复杂的文学史现象引向了概念化、简单化道路,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学术研究走向了明显的非学术化方向,甚至形成了一种思想习惯、言说方式和基本认识。这是当下的黄遵宪及近代诗歌相关研究中应当充分注意并深入反思的。
从个人选择、创作态度与当时文学运动、诗歌派别、文坛风气的关系来看,黄遵宪与所谓“新派诗”和“诗界革命”在新与旧、名与实之间也留下了值得认真清理、深入反思并清醒认识的文学史和学术史经验。就与“新派诗”的关系而论,黄遵宪在早年诗作中写下的“我手写我口”①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第42 页。和在中年诗作中写下的“读我连篇新派诗”②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见《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八,第762 页。,本来只是诗歌创作中即兴的有感而发或酬答友朋时随手写下的普通诗句,并未进行过深刻的理论思考或严谨的逻辑阐述,也没有其他论述的有力支撑或明显证明,因而其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成熟的理论意识、思想内涵或倡导诗歌变革的主观意图。一系列诗歌创作也在有力地证明,黄遵宪并不反对所谓“新派诗”,还创作了若干首具有革新色彩的诗歌。但应当清醒地看到,这绝不是黄遵宪诗歌创作的全部,也不是其诗作的主导方面。颇令人觉得奇怪的是,这样两句表现出一定诗歌观念和理论意识的诗歌,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在许多研究者那里却被当成了黄遵宪主张诗歌创新变革、倡导“诗界革命”的有力证据,并进行了种种大胆分析和过度解读。而且,“新派诗”③按:与“新派诗”概念密切相关的另一概念“新学诗”的成立与否,更需要进行认真的史实文献清理并对以往的研究方式、基本认识与有关结论进行清醒反思。笔者以为,“新学诗”是一个较“新派诗”更加无根据、无法自圆其说的生造概念,相关研究中存在着更加严重的观念与方法问题。此不具论。这一概念是否能够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得以成立、它与旧派诗或传统诗歌的关系究竟如何,既尚未找到充分的文献根据,也未进行足够深入的理论阐述,许多研究或只是人云亦云、姑枉用之而已,或仍停留在对非常有限的材料进行过度阐述、强行论证的水平上,因而显得强词夺理、捉襟见肘。这是目前的黄遵宪与“诗界革命”、近代诗歌变革研究中应当认真反思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近六七十年来已经形成的近代诗歌必须朝着新诗化、通俗化、现代化的方向改革、“诗界革命”代表着近代诗歌变革发展正确方向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框架之下,黄遵宪俨然成了“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也是最成功、最具有标志性的实践者,是一面革新创造的旗帜。其实,在现有相关文献资料中,还找不到黄遵宪在理论上有意倡导、在实践上主动参与“诗界革命”的直接证据,当然也未发现他明确表示反对“诗界革命”的相关材料。结合黄遵宪的诗歌理论主张、创作实践及其与“诗界革命”鼓动倡导者梁启超等人的关系,只能说他与“诗界革命”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矜持而认同的态度。这种姿态既符合黄遵宪基于丰富的创作经验形成的文学观念和诗歌主张,也与他一贯中和稳键、朴质坚忍、务实求新的政治立场、学术文化观念、处世态度等明显相关和一致;更与梁启超1899年在《夏威夷游记》中、1902年起在《新民丛报》连载的《饮冰室诗话》中正式鼓动并积极倡导“诗界革命”之际黄遵宪的政治处境、思想转变、诗歌创作和人生经验密切相关。也就是说,黄遵宪对于“诗界革命”的真实态度和具体做法是他政治态度、思想特点、学术观念、处世原则、生活经验在文学观念、诗歌创作上的表现。黄遵宪对“诗界革命”及与此相关的舆论鼓动的态度,既不同于年轻气盛的梁启超等人的简单浪漫、焦躁冒进和急于求成,也不同于同时代更多注重延续传统、保守谨慎的主流派文人和正统派诗家,而是在因革通变、扬弃取舍之间保持着一种稳妥合和、理性持重的文学姿态与文化态度,其中蕴含着颇为深刻的世变道理和辩证智慧。就当时传统诗歌的生存处境和面临的变革来说,这种处理方式也更具有思想方法、创作原则上的建设性和启发性。从中国传统诗歌面临的中西古今选择、传承创新难题来看,这种态度也更符合近代诗歌继承优秀传统、因时而变、适当求新的发展方向。无论是从近代诗歌、近代文学研究的角度还是从近代学术、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反思,都应当看到,这也是黄遵宪留给后人值得记取的思想经验。
三、文化态度与思想调适
黄遵宪生活的晚清时期,盲目自守、闭关锁国的局面已在外国列强各种方式的强迫下、在清政府不得做出的种种应付中被愈来愈彻底地打破,代表世界文明水准、价值标准和发展方向的西方文明正在日益充分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这已经是一个不得不打开国门、无法不面对西方文化、不能不对古老的中国文化进行重新思考进而寻求出路、谋求变革的前所未有的时代。而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历经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以及英属新加坡等地的外交官僚属经历和积极考察、主动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心态及一系列诗歌创作与著述文化活动,又使黄遵宪受到日本文化、西方文化的直接冲击和巨大影响,也为他提供了深切体察、准确认识外国文化的良好机会和客观条件,可以在比较真切的中外文化关系、异同对比中思考和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显示了个人思想的先进性与时代要求的进步性之间的某种契合,也反映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变革的一个主导趋势和必然方向。
在这一几近全新的文化冲突、思想变革过程中,黄遵宪的文化心态总体上是以比较健康、积极主动的姿态去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和挑战的。这在作为他首次出国经历、出使日本期间的诸多文化感受、内心矛盾及自觉进行的自我疏导、自觉调适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在同期所著的《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及其修改过程中、在创作的《樱花歌》《西乡星歌》《不忍池晚游诗》《都踊歌》《赤穗四十七义志歌》等多首关于日本政治、历史、文化的诗歌作品中得到了集中展现;而与日本多名文学、文化与政治人士的交往对于黄遵宪日本观、世界文化观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些文学、学术、外交活动及日常生活使黄遵宪比较平稳地度过了始料未及的文化心理和价值信仰危机,积累了珍贵的文化交流经验;而且,这种丰富而亲切的日本经验成为黄遵宪接触和认识外国文化的思想基础,对于他后来出使欧美国家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后来在出使美国、英国、法国以及英属新加坡的时候,黄遵宪的内心感受、文化态度不断发生显著变化,再次经历了内心的文化困惑和思想矛盾。这一方面是由于欧美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巨大差异性、当时清政府与美国、英国、法国外交关系的复杂与艰难及其对于黄遵宪思想观念上造成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也是由于黄遵宪本人知识结构、认识能力、思想观念、内心感受所带来的明显限制,特别是对于欧美文化的明显陌生感和疏离感,造成了预想不到的内心困难与思想矛盾。这在他写下的一些诗作如《海行杂感》《纪事》《伦敦大雾行》《登巴黎铁塔》《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等作品中也有着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反映。但是,由于在日本期间已经具有丰富的对外国文化经验、形成了良好的对待外国文化、异质文明的情感态度和文化姿态,加之政治经验、文学修养、文化见识、人生阅历等的丰富提高,黄遵宪在总体上能够比较恰当地处理各种思想矛盾和现实问题,以颇为平和稳健的态度和方式比较顺利地度过各种困难。这些经历和努力,使黄遵宪在最初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外交人物当中保持着先行者的地位,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作出了积极探索和突出贡献,也积累了至今仍然值得关注并体会、汲取的文化史经验。
另一方面,黄遵宪在接触和面对外国文化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复杂深刻的内心矛盾和价值冲突,面临着难以找到正确方向、合理答案与可行出路的文化难题和价值困惑,这同样是值得充分注意的。黄遵宪也像当时的许多儒士文人一样,认为虽然西方先进文化应当学习吸收,但需要根据中国文化传统和当时的需要进行具体分辨与取舍。他在日本时曾说:“近者土风日趋于浮薄,米利坚自由之说,一倡而百和,则竟可以视君父如敝屣。所赖诸公时以忠义之说维持世教耳。”①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32 页,(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保守的思想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他还说:“形而上,孔孟之论至矣;形而下,欧米之学尽矣。论当今之事者,不可无此见解也。”②冈千仞:《观光纪游》十三,明治十七年八月一日(光绪十年六月十一日)日记,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册第五帙,第178 页,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影印本。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自上古以来,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其所发明者备矣;形而下者,则自三代以后,历汉魏晋宋金元明,犹有所未备也……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国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实有其可重者在也。中国于工艺一事,不屑讲求,所作器物,不过依样葫芦,沿袭旧式……今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法,日新月异,变而愈上。夫物穷则变,变则通。吾不可得而变革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凡关于伦常纲纪者是也;吾可得而变革者,轮舟也,铁道也,电信也,凡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③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十《工艺志》,第1—2 页,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本。他认为可以变革的方面总体上应当限定在能够直接有利于国富民强的器物、技术等物质文化层面;对于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等文化的中间层面则应当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可以学习借鉴的主要是日本、英国式的国家制度和政治体制,对于美国式的共和制度则多有批评,认为不可效法;至于一般所谓文化的最深层即道德伦理、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精神信仰等方面,则基本上不需要学习西方,也就不存在借鉴效法的问题。这种中体西用、变器而不变道的观念困扰了黄遵宪一生,也是同时代许多文人面临的最深刻的文化难题和价值困惑。①按:关于黄遵宪的政治观念和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拙文《黄遵宪晚年思想三题》(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黄遵宪的中西文化观与文化心态》(载《炎黄文化研究》第三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曾有具体讨论,此不赘述。
以明末西方传教士入华为主要标志的西学东渐思潮,在经历了清代前中期的种种艰难曲折之后,至近代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无法避免的巨大力量,西方(包括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文化对中国的渗透影响日益深入充分。虽然其间几经反复、多有波折,但西学东渐、学习西方的总体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这一空前深刻的文化变革转换历程中,中国人始终未能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中西文化的体用关系、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和适用度、中国文化传统的转化延续及其近现代价值问题。在这一思想史背景下,黄遵宪也曾深受当时颇为流行、后来仍颇受认同的西学中源论的影响。他在日本时曾说过:“余考泰西之学,墨翟之学也。尚同、兼爱、明鬼、事天,即耶稣十诫所谓‘敬事天主’‘爱人如己’”;“《韩非子》《吕氏春秋》备言墨翟之技,削鸢能飞,非机器攻战所自来乎?古以儒、墨并称,或称孔、墨,孟子且言天下之言归于墨,其纵横可知。后传于泰西,泰西之贤智者衍其绪馀,遂盛行其道矣”;“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书。第我引其端,彼竟其委,正可师其长技”②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原本第五十一首自注,光绪五年同文馆集珍版,第23—24 页。。直到晚年乡居时,西学来自中学的基本观念仍未发生转变且有所深化,认为:“旧学中能精格致学者,推沈梦溪,声、光、化、电、力、气无一不有。其使辽时,私以蜡、以泥模塑地图,即人里、鸟里之说,亦其所创也,他日必有人表而出之”③黄遵宪:《黄遵宪全集》,第434,428 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笔者对原校点有所调整并省略作者原注。。还认为:“吾读《易》,至泰、否、同人、大有四卦,而谓圣人于今日世变,由君权而政党,由政党而民主,圣人不啻先知也……而谓圣人之贵民、重文明、重大同,圣人不啻明示也(大象明之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自天佑之。系辞曰‘履信、思顺、尚贤’,非民主而何?)。所尤奇者,孔子系辞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此非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说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此非猴为人祖之说乎……达尔文悟此理于万物已成之后,孔子乃采此理于万物未成之前,不亦奇乎?”④黄遵宪:《黄遵宪全集》,第434,428 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笔者对原校点有所调整并省略作者原注。非常肯定地认为不仅西方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早已大备于中国古代典籍之中,而且西方近代社会人文科学内容、当时传入中国的新观念也早已略备于中国传统思想之中。从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当时流行一时并持续较久、包括一向被视为走向世界的先进中国人黄遵宪在内的许多文人坚信不疑的西学中源论,虽然对中西文化关系包含着明显主观故意成分的误读;但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现象,体现了中西文化接触碰撞、交流融合过程中最深层、最内在的矛盾冲突,反映了中西文化交融的沉重步伐和艰辛历程,也表明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演进与深化,有其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人文心理环境和一定的合理性,也是那一代文人弥补巨大文化失落感、消解无法消除的文化心理焦虑的一种补偿形式。
黄遵宪及其时代人士所面临的思想矛盾、价值困惑,特别是他们为解决这种前所未有的矛盾困惑所做出的积极回应、努力调整,是真切深刻且具有文化史意味的。从近代思想史的逻辑演进和近代知识分子心态调适完善的角度来看,黄遵宪那一代先进中国人未能解决的矛盾困惑,并非仅仅属于他们自己,实际上已经考验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及其他有识之士。这种文化困惑和思想矛盾是中西文化关系中一个极有深度的根本性问题,并不是黄遵宪及其同代人所能解决的(其间的缺陷和遗憾当然也不应当仅仅由他们那一代人承担),因而留给了后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更多的中国人。从文化态度、思想观念与时代氛围、文化变迁总体趋势的关系来看,黄遵宪在中西文化、古今文化之间的权衡、取舍与选择,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和突出的时代特色,留下了内容丰富、价值独具的思想史经验,直至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因为,从近代走到今天的我们,仍然在中西古今、通变扬弃、传承创新中艰难求索、奋力前行,其间留下的仍然是前景与困惑、进步与缺憾、经验与教训交织杂糅的思想历程和心灵印痕。从这一角度来看,已经逝世110 周年的黄遵宪的思想情感、理想信念与探寻中国富裕强盛、民族复兴道路的后来者们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