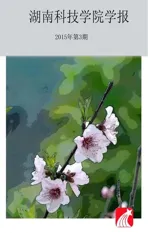论井上靖西域题材小说中中国人物形象的意义
2015-03-19李亮
李 亮
(湖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永州425199)
井上靖是一位对中国怀着友好感情的作家,虽立足于日本文化视野,却是怀着真诚的热爱与善良来理解中国文化和刻画他心目中的中国的。作为战后日本文学中最早写中国历史题材的小说家,井上靖延续了战前中岛敦、武田泰淳等作家开创的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传统。其开拓性更表现为在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在文化交流存在诸多不便的情况下,积极地以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作为小说的题材,正面地描写中国和中国人,为中日文学、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
一 奠定井上靖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基调
井上靖的西域题材小说只是他中国题材作品的一小部分,井上靖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始于1950年发表的《漆胡樽》,共创作了17部中国题材历史小说,本文中所 涉及到的几部作品可以说都是他中国题材小说创作的早期作品。井上靖在创作这些西域题材的作品时,并没有亲身来到中国西域,他所有关于中国的想象都是通过积极查阅有关的历史典籍资料在脑海中慢慢构建形成的,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加入了井上靖个人的文学艺术虚构。他西域题材小说中的中国人物形象既有真实的中国历史人物如班超、索劢,也有他虚构出来的如赵行德、朱王礼等。即便是历史真实人物,井上靖也并没有完全的按照历史记载去塑造他们,而是在史实资料记载的基础上去发挥自己的文学想象,做到了真实中包含丰富的想象,虚构中不失历史的真实。而这正好将日本文学中以森鸥外为代表的认为历史小说要尊重史实,力求再现历史原貌的创作手法和以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主张借用历史题材来表达现代主题的脱离史实的创作手法很好的统一起来,从而开辟了历史小说创作的独特的新道路。[1]井上靖在塑造西域题材人物上所运用的这一独特的创作手法,为他以后的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奠定了基调。
井上靖在之后分别于1959年、1963年、1987年先后发表了《苍狼》、《杨贵妃传》和《孔子》三篇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小说,这正好是中国历史上武人、美人和文人的代表人物,井上靖之前的有关中国人物形象的塑造,为这三部作品的完成做了很好的铺垫。《苍狼》是作家读了成吉思汗实录《元朝秘史》开章有关蒙古民族起源传说的诗后而几乎近于虚构创作产生的。蒙古民族认为蒙古的祖先是一匹苍色的狼和一只白色的牝鹿杂交产下来的,他们自命为“狼”的后代。井上靖通过艺术想象将成吉思汗虚构成尚武、黩武、不断发动战争到处寻找敌人,征战掠夺的一只“苍狼”形象。井上靖的这一虚构,在日本还引起了一场关于《苍狼》是不是历史小说的争论。井上靖笔下的战斗不息、为战而生的成吉思汗形象,正是他西域小说中武人形象的一个延续。小说《杨贵妃传》中的杨玉环,也没有被井上靖描写成如历史记载那样荒淫误国给唐代带来许多不幸与灾难的“恶”人形象。在《杨贵妃传》当中,井上靖既没有一味刻意地去赞叹杨玉环的美貌,也没有对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大加歌颂,更没有指责她是红颜祸水。作者对她的身世、性格都进行了文学虚构加工,将她改造成一个典型的“日本式”的孤独者。她身上的这种孤独气质与井上靖西域小说中的美人形象性格当中所具有的悲凉之感是一脉相承的。《孔子》是井上靖创作的最后一部有关中国题材的小说,也是他的压卷之作。井上靖没有按照传记文学的形式来写这部作品,而是在文中虚构了一个史料记载中没有的作为孔子弟子出现的人物“焉薑”,通过他的讲述,生动地描述了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如何回忆、搜集、整理其言论的情况。小说中焉薑对先师孔子的理解,当然就是作者本人对孔子的理解。小说从侧面阐释了孔子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传达了他对人生的思索和祈祷世界和平的愿望,可以说是井上靖心目中中国文人的最理想形象。由此可见,井上靖西域小说中的中国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但为其以后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奠定了基调,而且从创作手法上丰富了他小说创作的风格。
二 丰富日本文学的审美情趣
井上靖曾将人生比喻为一条冷寂的“白色的河床”,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始终可以找到一股孤独寂寞的气氛。在他的西域题材小说中不管是雄才大略的武人形象还是文弱质朴的文人形象,他们身上都具有一股孤独落寞的气质。而这种气质正是井上靖自身所具有的。日本著名评论家山本健吉就井上靖西域题材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曾如此评论:我们从作者要跟古人讲话的感情中可以看出井上氏倍感孤独的心情。他把无法对任何人讲出的感受,变成对古人诉说的语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井上氏尤其喜欢选择由于被无法诉说的热情所驱使在异域活动的人们。这些人是对自己活动的真实意义被埋没,不为任何人知道而又毫不介意的孤独者。在井上氏的作品里出现的人物,正是作者梦幻中所向往的驰骋在沙漠中的自己。[2]而《异域之人》中的班超、《敦煌》中的男主人公赵行德就是此类人物的典型吧。
在井上靖的历史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出不仅包含历史沧桑感,还有淡淡的哀伤和神秘、幽玄的独特审美感受。作为日本人,井上靖同其他许多日本作家一样,继承了日本传统的“物哀”美学思想。所谓的“物哀”即认识感知的对象与认识感知的主题,二者相互吻合一致时产生的和谐的美感。《广辞源》中将之定义为优美、细腻、沉静、直观。换句话说,物哀就是人们在同外界事物接触时,内心里不由自主所产生的某种幽深玄静的情感。因而,“物哀”不仅仅包含悲哀、悲伤、悲惨,还包含哀怜、感动、壮美的意思,不能将“物哀”美学简单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的一种,但是“悲哀”情绪却是最感人心灵的。因而大多数日本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侧重于捕捉描写“物哀”中的悲伤、悲哀美,过分强调“哀”的一面,而忽略了“物”的壮美一面,而井上靖在他的作品中很好地将日本传统“物哀”美学的悲哀一面和壮美一面统一起来。在他的西域题材历史小说中所刻画的人物往往带有孤独与哀伤的情绪,并且表现出人物悲苦的际遇、人世的不平,但他的笔触不仅仅停留于此,而是在悲哀中体现壮美。《洪水》中索劢为了部队能够顺利渡河,用自己心爱的亚夏族女子祭祀河神以及率领将士与洪水搏斗最后全军覆灭的情景充满了悲壮。而《敦煌》中的赵行德与回鹘公主的凄美爱情故事同样让人为之动容。文中如此写道“她的手的冰凉的感觉永远留在行德粗糙的手掌上”[3]。以后每当赵行德想念起回鹘女子时,“就心如刀绞,手掌还残留着执手分别时所感觉到的她的手的冰凉”[3]。这种细腻、忧伤的气氛,这种淡淡的哀伤,一定打动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在得知自己心爱的回鹘公主或许是为自己而跳下城墙殉情后,赵行德便埋头于佛经典籍之中,在乱兵中将大量珍贵经书藏入千佛洞窟中,亦不由得让人觉得悲凉壮美。还有《楼兰》中被幻想为了守护楼兰国而自杀的年轻王女,在楼兰国被侵,国民不得不举城迁移时,为了守住楼兰的魂,让后人知道楼兰的根在哪而牺牲自己性命,更使人同情流泪。其个人的命运是让人悲伤的,但将其个人命运与楼兰命运放在一起时,又是何等的壮美。其实这些人物置身于的漫漫黄沙、滚滚大漠、茫茫戈壁本身,给人们感觉的就是一副悲凉、凄美的画面。井上靖将这些人物形象置身于西域大漠中,自然也就会情景合一了。在井上靖的西域小说人物身上,我们还能找到一种神秘、宿命的佛教无常观。日本室町时期,由于禅宗的世俗化,禅的思想不仅作为宗教,而且作为文学艺术思想来接受。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镰仓以后的禅宗,一方面其寺院同政治权力结合,另一方面其思想成为文学,成为绘画,终于成为一种美的生活模式并化为独特的美的价值”[4]。佛教思想中的无常观、命运轮回同传统的“物哀”美学相结合,又发展成一种幽玄的朦胧美。井上靖笔下的中国人物形象,不论是英雄豪杰还是普通小人物,不论是男性形象还是女性形象,在荒凉的西域大漠,在宿命的历史长河中都显得如此渺小,面对命运,他们虽努力抗争,却显得如此的苍白与无奈。《异域之人》中的班超在西域为汉朝的边疆事业奋斗了三十年,耗尽自己毕生心血,最后一切却成转眼云烟。在异域的三十年生活连他自己俨然成了一个胡人。“大漠的黄尘改变了他的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孤独的岁月从他身上夺去了汉人固有的从容稳重的神情。”[5]《洪水》中那个宁可牺牲自己损失自己半数人马也绝不会用女子祭祀的方式来平息河神的愤怒的索劢,在这荒凉边疆与匈奴无休止的战斗数十年后,已然没有了当初的豪迈斗志,当再次面对洪水阻挡时,他终于还是妥协于命运,牺牲了他所钟爱的女人,希望用“祭祀女子”的方式顺利渡河,最后却还是被洪水吞噬。《敦煌》中的赵行德在见到自己钟爱的回鹘公主在西夏的阅兵式上跳楼自杀后便产生“为了超度她而保存佛经”的动机。除了这个是赵行德由一个文弱的书生到舍出性命也要保护经书的动机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动机,那便是:敦煌。作为一直处于中原地区平稳的环境下的赵行德,现在突然来到如此荒凉的大漠边疆,产生依赖于超越者的心理,寻求某种心理信仰也是非常自然的。由于敦煌作为舞台背景的作用之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敦煌》这部小说的重点并不是人,而是敦煌这个地方。井上靖缩写的不仅仅是赵行德这几个人命运,更是敦煌所承载的历史。回到现实,我们仍不清楚到底是谁留下了那些经书,其实历史也并不在乎这一点。身处宏大的历史长河中个人实在微不足道。我们关注敦煌,关注的是某个人千年前行为的结果,而并不是他本人。个人的行为有时足以改变历史走向,但历史终将吞没他。在历史面前,就像我们面对大海、大漠、星空时,会忍不住感叹自己的渺小。可见,在漫长的历史中,个人夺取功名利禄的所有努力,在最后也都会转眼成空,所有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在历史面前,人的行为的虚无,人的意志的苍白无力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井上靖小说中的这种神秘、幽玄的朦胧美,是受到日本传统文化很深的影响的。日本在中世时期,由于武士阶级崛起,战乱频繁,社会秩序崩溃,武士阶层逐渐取代贵族势力成为政权与社会文化的核心,于是一些贵族知识分子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面对现实却又无可奈何,之后慢慢发展为品味无常、享受无常的思想。这种超越无常悲感、从无常悲感的压抑下重新获得精神自由的无常思想更是因日本经常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而得以强化。这些因深感无常而发生的思想转变,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文化史的性质和特征,成为日本审美意识的准则之一。而这种无常观也沉淀到每个日本人心里,井上靖也不列外。曾在《每日新闻》社任宗教栏记者的井上靖,阅读过大量的佛教经典,对于佛教中的无常感和命运轮回的感悟一定十分深刻。
三 积极促进中日文化的交流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之间的交流十分的频繁。在古代中国的大量经典文本传入日本后,日本的贵族、文人也大多懂汉文会汉诗,并以此为荣。古代的中国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值得景仰的理想之邦,但在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之后,日本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国力也渐渐强盛起来,并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昔日令人景仰的大国,现在却屈服于自己脚下,日本国内的“大日本帝国”情绪不断高涨,而在此背景下,昔日那个令人景仰,富有、文明的中国形象在许多日本作家笔下渐渐变成一个贫穷、混乱、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而他们笔下的中国人也渐次成为愚昧、丑陋、懦弱的化身。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文学中刮起了一股“中国情趣”的热潮。在全盘西化情况下,传统的汉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被欧洲近代文学思潮所代替,但一批深受汉文学影响的日本文人、作家,仍留念心目中的那个理想之国、桃源之乡,纷纷来到中国,以自己的足之所立,目之所及,撰写了中国纪行、中国见闻或以此为题材的作品。而这些中国题材的作品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状况及这些作家、文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如国木田独步的《爱弟通信》中,清朝的北洋舰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中国人是愚昧、懦弱而贪婪的;而樱井忠温在其《肉弹》中则将中国人刻画成愚昧、肮脏、爱财如命的丑陋形象。他笔下的中国人为了钱财可以给俄军发情报当间谍,毫不关心自己国家的存亡。即便是对中国了解不多、对中国兴趣也不大的日本文学泰斗——夏目漱石,在应邀来到中国后,在其长篇游记《满韩处处》中表现出的是一个“文明人”踏入“原始部落”时的那种感受与心情。[6]在他眼中的中国人是野蛮而残酷的。还有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在当时的日本也有着广泛的阅读群。阅读这两本中国纪行,似乎也成了日本人来中国之前必做的准备。但德富苏峰在他的中国纪行中将自己目睹的中国衰弱、落后,对现实的中国及中国人的蔑视表现得毫无遮掩。而作为日本近代唯美派代表作家的谷崎润一郎从小就向往中国,阅读收藏了大量中国古典作品。谷崎润一郎也发表过许多中国题材的小说,如《麒麟》、《秘密》、《美人鱼的叹息》等,此后还根据来到中国的所见,先后写下《一个漂泊者的面影》、《支那的料理》、《苏州纪行》、《西湖之月》、《秦淮之夜》、《上海交游记》等纪行文章,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谷崎润一郎对于中国的憧憬、向往,在意识深处还是好色与享乐的结合。关于中国的传统戏剧、风俗、名胜、饮食、女人,是“食”“色”之于谷崎润一郎的极大诱惑。在他的文章中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可能更多的是现实与想象中矛盾的纠结吧。
如此多的日本作家、评论者来到中国,对中国及中国人做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当然会给从小喜欢中国古典、历史的井上靖带来极大的震动。这些前辈对中国、中国人的评价与井上靖阅读的中国历史古典而构建出的中国人物形象肯定会发生强烈冲撞。从古典文学与历史典籍中所认识、了解的中国、中国人不是如前辈们所评论的那样,于是他要塑造一系列他想象中的中国人物形象,以期对前辈们的鄙视、看不起的中国人形象进行颠覆。所以,井上靖在他的中国题材小说中,赋予了绝大部分中国人以善良、重情、积极向上、执着追求理想的美好形象。
作为战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主要开拓者,井上靖于1954年、1957年分别发表了以中日佛教交流为题材的《僧行贺的泪》和《天平之甍》,最早将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作为小说题材,也为此后日本的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奠定了基调。在井上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中,以古代西域为舞台背景的作品,可谓最有特色。他在当时无法亲历中国西域地区进行体验考察的情况下,凭借对历史资料的收集、解读,利用丰富的想象力,写出了一系列以西域为背景的小说作品,开拓了当代日本文学的一片独特天地,从而改变了千年来日本文学的岛国视野,将广袤无垠,充满沙尘和黄土味的“大陆性”引进了日本文学中。[7]西域对于井上靖来说或许存在无限的诱惑吧。“他还在京都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大概就想到中国去看一看。他说自己在大学里几乎没去上课,却埋头阅读有关西域的文章。”[7]井上靖的夫人井上芙美在《致中国读者》中如此说到。可以看出井上靖从学生时代就喜欢读关于西域的书,而关于西域他曾说过“未知、梦、迷、冒险等诸要素都集中于此地。”[8]正是由于对于西域的奇特文化的无限向往,井上靖关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更多的将舞台背景置于西域,写出了《漆胡樽》、《异域之人》、《楼兰》、《敦煌》《洪水》等等西域小说,并出版了《井上靖西域小说选集》。井上靖热情地追寻着西域之“梦”,他对于谜一般的西域的探索,都通过这些作品得到了充分显示。在这些西域小说中,井上靖塑造了雄毅英武、豪放粗犷的中国武人形象;淳朴诚实,对学问执着的中国文人形象及婀娜多姿,对爱情忠贞的中国美人形象。而这些形象在其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文学作品《苍狼》《孔子》《杨贵妃》中得到更好体现。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孔子的质朴、博学,杨贵妃的美丽可人,在井上靖的小说中得到很好的表现,而他们也正是中国武人、文人、美人最名符其实的代表。
作为战后最早写作中国历史小说又是第一个将目光投向中国西域的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西域小说中中国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颠覆前人文学作品中有关中国人负面形象,更掀起了日本国内对于中国西域,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强烈兴趣。他的许多中国题材小说被拍成电影,许多人通过观看这些电影,开始注目中国西部的这块神秘的地方。甚至有大批人把他的西域小说作为导游书,开始了西域的漫长旅程。在战后中日还没建立正常的邦交关系的背景下,井上靖关于中国西域,关于中国人的描写,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取材、访问,井上靖先后来中国三十多次,并多次任日本作家访问团团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先后同山本建吉、中野重治、司马辽太郎、福田宏年、大江健三郎等访问中国。此后,在井上靖73岁高龄时,他还担任大型记录片《丝绸之路》的艺术顾问,与日本放送协会、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摄制人员一起,再次踏上丝路古道,在大漠中追寻他的西域之梦,他向世界观众介绍丝绸之路历史变迁的愿望。在同中国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井上靖同中国的一些文人、学者也结下深厚的友谊。同巴金“把心掏出来”的三十年友情;为老舍之死执笔雪冤;还有与作家冰心、学者常书鸿的真挚友情,至今为中日两国人民乐道。作为中日两国友好的使者,井上靖向日本民众介绍了正面的积极的中国、中国人物形象,这让战后的日本人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日本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当然,井上靖的作品在中国也得到了相当全面的翻译、评论、和研究。井上靖有关中国题材的小说几乎全部被翻译成中文,为广大中国读者所喜爱。而有关井上靖的评论文章也有100余篇。总之井上靖是在中国翻译最多、评论和研究最多、影响也最大的当代日本作家之一。井上靖的中国题材小说的创作本身,就是当代中日文学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井上靖笔下的这些中国人物形象从日本传统的审美情趣来看的话都带有悲哀、伤感的感情色彩在里面,但从小说中人物的行动来看,他们又都不是悲观、消沉、逃避现实命运,而是更积极地面对现实,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同社会现实拼死斗争。井上靖西域小说中人物形象所体现的纤细、哀婉、苍凉、壮美是井上靖继承日本文学的美学传统,将中国历史典籍中的儒家色彩人物锐变成他小说中带着淡淡哀伤和佛教虚空色彩的结果,而这也正是井上靖的小说作品能为中日两国读者所认可和喜爱的原因吧。
[1]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564.
[2]井上靖.井上靖西域小说选[C].耿金声,王庆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568.
[3]井上靖.井上靖文集(第1卷)[C].郭来舜,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7073.
[4]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3.
[5]井上靖.井上靖文集(第2卷)[C].郭来舜,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35.
[6]王向远.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82.
[7]井上芙美.致中国读者[A].井上靖文集(第1卷)[C].郭来舜,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
[8]井上靖.遺跡の旅シルクロード[M].東京:新潮社,1986: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