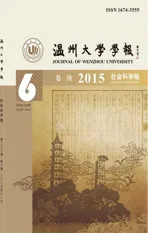清人学风影响下的南戏文献考辨简论
2015-03-18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蒋 宸(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清人学风影响下的南戏文献考辨简论
蒋宸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摘要:清代有关南戏文本文献的研究,表现出不同于前朝的学术面貌。由于受到文人情趣牵引以及当时考据学风的影响,在关于南戏的辨订中运用了不少考据学问的方法,酌古通今,旁推互证,从而使得清代的南戏研究在探索的深度与广度上均取得了不少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成就。在辨订前人有关南戏认识讹误、推动南戏文献研究由史料载录向学术研究转变、为后人提供南戏文献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关键词:清代;考据学风;南戏考辨;类比;博证
清人学术迥异前朝,自立国之初便一直依循着顾、黄诸大儒所创下的朴学实证的学风,讲求“言必有征,典必探本”[1]“酌古通今,旁推互证”[2]131,展现出一派讲考据、重实证的恢宏气象。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清代文人多热衷于针对各种典章名物、文化现象辨订正讹、考镜源流,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尚古”倾向。南戏作为传奇戏曲的直接源头,也无可回避地进入文人的考据视野,留下了不少考辨南戏史料的文献记载。这些记载,与清人的其它考证一样,表现出清人治学博证、类比的种种特征,当是受到考据学风影响的产物。故此,笔者拟以记载这类考辨文献最为集中的清人笔记为主要文献来源,考察清代学风对南戏文献考辨的影响,对这二者间的关系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清代学风的形成及其对文人情趣的牵引
由于时代、环境等因素的作用,清人的学术专注于考据,“考据之学,至乾隆中叶而极盛”[3],讲究“一字之证,博及万卷”①阮元. 王石臞先生墓志铭[C] // 闵尔昌. 碑传集补: 第39卷. 民国十二年(1923年)刊本.“实事求是,以经证经”[4],在前人基础上将考据学发展为独立的学派,并使之成为在一段时期内左右社会风气所向的学术思潮,至有“考据之学,风靡一时,不能为此学者几不得登坛坫”[5]之说。这一风气的形成,既有其政治历史的原因,也有当时文化经济等现实因素的作用。
清代雍乾以后,由于学术重心的推移以及朝廷自上而下的推崇汉学,以经学为中心的考据学风流被一时①昭梿《啸亭杂录》卷一《重经学》条载: “上(乾隆)初即位时,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 上特下诏, 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 辇至都下, 课其学之醇疵. 特拜顾栋高为祭酒, 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 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 命方侍郎苞、任宗丞启运等裒集《三礼》. 故一时耆儒夙学, 布列朝班, 而汉学始大著.”而同书卷十《书贾语》条又谓汉学昌盛之后, 儒者纷纷“株守考订, 訾议宋儒, 遂将濂、洛、关、闽之书, 束之高阁, 无读之者”, 甚至连书坊中都二十余年不贮售理学书籍, “恐其无人市易, 徒伤赀本”. 可见当时汉学、宋学之消长情势.,“成为学者社会之一般嗜好,竭生平之功力以赴之。虽境遇至为困苦者,亦不稍减其学问之欲,反以是为高尚”“当时政府及社会心理亦颇知尊重学者,故经学考证风气,充满国中”[6]439。这种考证学风,在治学方法上,比较符合后来的科学精神,“旁搜曲证”“凡考订名物,往往绘图列表,以明其真”[7],对于求学者学殖的培养与人格的树立,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其“铢积寸累,先难后获”的治学方式还具有一种特别的感召力,能使求学者“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兴奋向学”,故而当时无论硕学鸿儒还是初涉此道的求学、问学者,均以跻身朴学学林为好尚,“相与淬励精进,阘冗者尤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于是‘家家许、郑,人人贾、马’”[6]444。
同时,清代帝王十分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编订,自顺治至光绪朝,每朝均开馆修书,其中尤以康雍乾三朝为甚。据罗振玉统计,自康熙至嘉庆四朝,共计开馆修书189部(不含国史及政书等),其中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8]104-109。其数量之钜,远胜前朝各代,即便是官修著述极为宏富的宋代,在数量与规模上也均不足其十分之一。其中缘由,一方面是由于清廷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视,藉此也可以笼络一部分汉人士大夫,使他们醉心于此而不再过问政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清代物力丰阜,随着印刷业的发达,图书的流通收藏更加便利,出现了大批藏书家,因而有条件大规模地整理国故。通过这些著作馆的开设,清廷集聚了一大批学者,给以尊荣的地位与优渥待遇,让他们埋首经籍,去考订辨正、蒐古辑佚,这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当时社会集体向学的风气——“鼓箧之士,负笈之徒,皆知崇尚实学,不务空言”[2]5。当时稍有名望的学者,都以能被朝廷征召入馆修书为荣。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牵引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学风走向,其中不少文人学者把精研考据、蒐辑古佚典籍当作了舍八股科举而外可以致身荣显的途径,因而为之殚精竭力,皓首穷经。
龚自珍有诗谓:“避席畏听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②龚自珍. 《咏史》, 见: 《定盦文集》“古今体诗”上《破戒草》, 清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一语道破了乾嘉学人埋首经籍,肆力考据的两方面缘由。当时社会的文化大环境,对于求学者的成长具有培植的作用,“后辈志学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恒有先辈延主其家为课子弟,此先辈亦以子弟畜之,当奖诱增益其学”“其有外任学差或疆吏者,辄妙选名流充幕选,所至则网罗遗逸,汲引后进,而从之游者,既得以稍裕生计,亦自增其学”“其学成名著而厌仕宦者,亦到处有逢迎,或书院山长,或各省府州县修志,或大族姓修谱,或有力者刻书请鉴定,皆其职业”“有相当之报酬,又有益于学业”,即便是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富商大贾,也都附庸风雅,以此为时髦,广邀名士评鉴收藏,又重金聘请有学之士到其家坐馆,藉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治学问者受到全社会普遍的尊重,“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因而能有精力从事于更为精深的学术研究,“学乃日新”,即便寒门秀士,一时境遇困顿也不为所动,“素惯淡泊”“终其身于学”。[9]65-66很多修学者一旦厕身学林,便可以不再有衣食之忧,即使科举不第,学问优渥者,或可受荐入馆修书,从而获得进身之阶。正是由于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故而有清一代,问学考据之风特甚。
清代文人学者,多博览强记,“通训诂,考制度”“诸子百家,靡不探讨”[10],喜用笔记的形式,以“铢积寸累”的方式,“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9]62。在经学、史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乐律学、地理学、方志学、金石学、历算学等诸多领域,“讨论经史,证明掌故”[11],均有许多独到、精深的见解,“虽丛残掌录,亦必义密语详,多可启发”[12]。这类撰述,涉猎范围甚广,且多重考证,重名物制度的训释。这在清人撰著中,几乎已成了不可少的一项特色。即便是普通的文人笔记,偶谈掌故、文物,并非有意治学的,也往往考据、学问充斥其间。如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钱泳《履园丛话》这类作者用以“遣闷送日”[13]“遣愁索笑”[14]之作,也有大量如《〈新唐书〉刊削诏令》《说文系传》《古泉》《错简》《三归》《古今人表》等考证典章名物的条目充塞其中。由此足见考据问学之风对清代文人情趣的牵引。
清人的考据习气,主要体现在普通文人的笔记撰著中,虽然在名物考证等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却并非以学问为目的,因此也不可能如同经学家那样,矻矻埋首于经籍字义声韵的考索。他们更感兴趣的,往往是通过考据的方法来揭示某一种文化现象。因此,其中不少笔记的考据方法,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层面,而是通过对某一事件或事物来龙去脉的考索,以透视时事的变迁、审美趋向的差异、文化内涵的不同等等。从这个层面来说,多数清代文人的考据,实则已突破了纯粹的经史考据的范畴。
二、考据学风对南戏文献考辨的影响
由于时代风气及现实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清代文人多博学尚古,穷镜源流、蒐讨古佚已成为其日常趣味的重要一端。有人概括这一现象谓:“五尺童子,皆知剽窃定宇(惠栋)、挦撦萧客(余古农);村塾学究,莫不妄袭朏明(胡渭)、谬沿百诗(阎若璩),甚至以骨董谈经”[15],可见当时风气之烈。与此同时,清代戏曲发展极为繁盛,观剧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久已融入了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成为交游酬酢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文人学者对戏曲本身,本已持有极大的欣赏趣味,而戏曲的源流、本事乃至音律等等,又与文学、历史等密不可分,甚至可与经学、教化相通,这既引起了他们的研究兴趣,又为他们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在清代文人学者的眼中,通过这些戏曲名目,大则可以钩稽史学、音律,乃至礼乐等符合“先王之道”的宏大命题,小则可以藉以考察文化现象,怡神悦志,还可以用以与经学、文学等相发明。与伶人的场上戏曲表演大不相同,这些案头化的戏曲考据,本身也是诸多学问之一种,且综合涵括了文学、史学等各个层面,故而为不少文人学者所津津乐道。其中,有关南戏的若干命题,由于年代久远、歧说百出,特别是它在文学、史学诸方面均有极为丰富的牵连关系,因而极大地激发起文人学士的考究兴趣,在关于南戏的翫索辨订中运用了不少考据学问的方法,从而使得清代的南戏研究在探索的深度与广度上均取得了不少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成就。
清代学者考据学问的方法,一曰博证,二曰类比。主张通过广泛阅读各类典籍文献,当论证某一问题时,将平日积累的材料,加以排比组合,大量归纳例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论证问题,而后得出结论,“凡立一说,必列举古书,博采证据,然后论定”[6]518。亦即梁启超所谓的“博证”法。清初学者阎若璩尝论谓:“生千载下,而仰论千载上事,苟非典籍具存、证佐明白,固不可凭私臆度也”①阎若璩. 《潜丘札记》卷二,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道出了这一治学方法的核心要义所在——立论须以大量的文献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在清代的笔记,特别是学术札记中,每当涉及文献考证的问题,这种大量归纳例证的类比研究法便得以普遍运用,成为清代考据学风一项极为显著的特征。受此学风影响,在有关南戏文献考辨的话题中,清代文人所采用的,主要也是这种方法。
所谓博证,即是广泛阅读各类文献史料,旁推互证,而不为经史子集等人为划定的畛域所限。清代学者不比前朝,自清初诸大儒以来,便都以博洽著称,主张治学须“旁求之九流百家”[16]214,“于书无所不窥”[17]227,并训导门人弟子:“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16]219。这种博学笃实的学风在整个清代均得以传承和发扬。士人自习学之始,便被树立了博闻强记的观念,因而有清一代,多有饱学之士,即便讲求“宋学”的名儒,也一洗前朝空疏之习,文章经史并皆专通。在清人所撰读书札记中,均可见到这种博通风习的印记,如钱大昕、赵翼所著《十驾斋养新录》、《陔馀丛考》等书,其中于经史子集各类均有颇为详明的考辨研究,其考辨方式也不仅限于以经证经、以史证史,而是将各类典籍融会贯通,触手为用。
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清代文人在考察包括南戏在内的古典戏曲文献时,也一扫前人游谈之习,多引据浩繁,“于广博中求专深”[18]。明人在证说某一论题时,多由作者阅历而来,只是如同记述史实一般将之陈述出来,却极少有引用各家文献为己说提供论据支撑的表现,或是从他书直接迻录,全不考察这一说法可信与否。而清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则往往旁征罗列,博赡宏通,必求得一是而后止。如在民间影响颇广的梁祝故事,自宋元以来便被改编为各种戏曲,流传于世,其中演叙这一故事的南戏也有不少。据钱南扬先生研究,有关梁祝本事的地理位置众说纷纭,计有八处之多,莫衷一是[19]260-261。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录载其事,仅谓“梁山伯、祝英台事,自幼闻之,以其无稽,不之道也。近览《宁波志》,梁祝皆东晋人”,其后但迻录《宁波志》所载梁祝故事云云,再无片言深究。[20]而清人俞樾在其《茶香室四钞》中证说其事,则广引博征,综合前人笔记、传记、方志等多则文献,对其本事及发源地详加考证:
国朝金武祥《粟香四笔》云:小说家艳称梁山伯、祝英台事,而未知所出。《山堂肆考》亦以为俗传蝶乃梁、祝之魂为不可晓。余阅《宜兴荆溪新志》,载邵金彪《祝英台小传》云: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稽梁山伯,遂偕至义兴善权山之碧鲜岩,筑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为女子。……此东晋永和时事也。……有司为立庙于鄞,合祀梁、祝。其读书宅称碧鲜庵,齐建元间改为善权寺。今寺后有石刻,大书“祝英台读书处”。……又云:吴骞《桃溪客语》云:梁、祝事见于前载者凡数处,《宁波府志》云:梁山伯字处仁,家会稽,出而游学,道逢上虞祝英台为男妆,与共学三载,一如好友。……未几梁死,葬城西清道原。一云梁为令而死。其明年,祝适马氏,经梁墓,风雷不能前。祝知为梁墓,乃临穴哀恸,悲感路人,羡忽自启,身随以入。事闻于朝,丞相谢安请封之曰“义妇冢”。余按此视邵金彪《传》稍略,而事或转得其实。如《宁波志》所云,则梁、祝事迹固在浙东,与宜兴荆溪无涉也。邵《传》以为其读书之处在义兴善权山,则亦其读书之处,非葬处也,何以善权寺前有祝陵之名,有双蝶之异,不几并两处为一谈乎?义兴县至隋始置,谓永和时即有义兴名,亦失之不考矣。其事本属无稽,前人谓因乐府《华山畿》事而附会,然《华山畿》事无女子为男妆之说,则亦不甚合也。《粟香四笔》又引谈迁《外索》云:鄞县东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号“忠义王”。此又不知何说,殆又讹梁山伯为梁山泊,而牵合于《水浒演义》矣。[21]
按梁祝故事本属民间传说,宋代始在各家方志中广泛流传,据钱南扬先生考证,目前可见最早的出处当属唐代梁载言《十道四蕃志》(宋张津《四明图经》引)[19]248,笔者据之检索,仅得一句:“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①张津. 《(乾道)四明图经》卷二“鄞县”, 清咸丰四年刻《宋元四明六志》本.,看来传说的源头尚在梁氏撰《十道四蕃志》之前。不论其最初的源头为何,该传说在后世的传播流布之广泛,却是众所周知的,其中便牵扯出了不少故事起源地的歧说。俞氏依据前人笔记等文献所引,从语言逻辑与地名沿革的角度考察,认为本事发源地当在浙东。无论其考证是否足够严谨可信,这种广泛征引论据,从文献中爬梳剔抉,把南戏等戏曲本事考证与史地考察相结合的做法,却是清人考据所常用的手段之一。由此也可见,清代的南戏文献考辨作为考据的一个分支,无可避免地自内而外均受到博证方法的深刻影响。
所谓类比,出自梁启超的概括:“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9]47,从比较研究中归纳出见解。这是清人类比研究中最为核心的特点。清代学者多长于归纳,“属辞比事”,从众多的资料排比中总结出共通的要义。金毓黻以为清人研究学问,多采用“主题研究”,即“取古今或一代之事,析为若干主题,各个而讨论之”“就一主题”“采摭多量史料”“为殚见洽闻之讨论”[22]。这种讨论方式往往并不一定能有层层递进的深入探究,多是同一层面的列举甄别。不可否认,这种类比归纳的研究方法尽管表面看起来比较烦琐,且不如现代诸多研究方法的高屋建瓴,但在解决具体细微的问题,如文献史料的订讹正谬、祛惑存真方面却极具廓清积溷的效用,因而为清代考据学家所普遍采用。这也正是清代考据“实学”的一项重要表征。
在南戏文献考辨方面,类比研究法被运用得十分普遍,主要用于对南戏所涉本事的正讹订谬,或是以史证剧,藉助典籍记载来考证剧中关目由来。南戏题材不少都取自历代史传及民间传说,特别是早期南戏,取材于民间传说者居多,往往张冠李戴,不少剧中人物,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其事实又与剧中故事全不相类。清人治学涉猎广博,读书过程中时常寓目及相关史料,在闲暇之馀或因某些事件激发,或为消遣,每好考订史实,辨正是非,力为前人辩诬,将所见史料及前人观点用类比法作归纳,以求得一是。在这方面,争讼最为集中的大概就算是《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历来有关蔡伯喈原型的考证,歧说最多,据笔者所见,大略有王四②田艺蘅. 《留青日札》卷十九, 明万历重刻本.、唐人蔡生③邓伯羔. 《艺彀》卷下,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人邓敞④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辛部“庄岳委谈下”明万历刻本.、东晋慕容喈⑤吴骞. 《尖阳丛笔》卷二, 清钞本.、宋人蔡卞[23]等四五种说法,各家所论俱有佐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南戏文献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同样受到文人关注的还有《荆钗记》中王十朋、钱玉莲等人的原型身份问题,如梁章钜《浪迹续谈》考证《荆钗记》本事谓:
世所演《荆钗记》传奇,乃仇家故谬其词,以诬蔑王氏者。《天禄识馀》云:“玉莲乃王梅溪之女,孙汝权乃同时进士,梅溪之友,敦尚风谊,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权实惩恿之,史氏所最切齿,遂令其门客作《荆钗》传奇以蔑之。”《瓯江逸志》载王十朋年四十六,魁天下,以书报其弟梦龄、昌龄……上念二亲,而不以科名为喜;特报二弟,而不以妻子为先,孝友之意可见矣。为御史,首弹丞相史浩,乞专用张浚,上为出浩帅绍兴,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尝使之为十二牧,其謇谔如此,故史氏厚诬之。按《梅溪文集》中有《令人圹志》载:“令人贾氏,王、贾同邑,且世姻,故令人归于我,初封恭人,再封令人,卒年五十五。”又《祭令人文》云:“子归我家,今三十年。”其为世好旧姻,夫妇偕老可知,焉有入赘权门,致妻投江之事?《圹志》又云:“女二人,长嫁国学进士钱万全。”盖即钱玉莲(钱当为王)也。撰传奇者谬悠其说,以诬大贤,实为可恨。施愚山《短斋杂记》亦详辨之。[24]
文中多方引证《天禄识馀》《瓯江逸志》,以及王龟龄《梅溪文集》中所收圹志与祭文等所涉及的相关史料,证明《荆钗记》中所演王十朋另赘权门事为人所诬,并引施闰章《短斋杂记》来证实己说。同样的论题,在梁氏之前,清人翟灏《通俗编》卷三十七已有考证,征引《鹤林玉露》《天禄志馀》《杨升庵外集》等多则材料进行类比互证,以此来为历史上的王龟龄辩诬①翟灏. 《通俗编》卷三十七, 清乾隆十六年翟氏无不宜斋刻本.。而其后平步青《霞外攈屑》又引《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谓“卷首姓氏‘永嘉贾氏岩老下诰案’,梅溪有《送贾岩老自闽还乡》诗,乃其妻弟也。是忠文娶于贾,非钱,传奇之诬妄可证”,且为此则材料大感得意,“惜晴江(翟灏)不及引”。②平步青. 《霞外攈屑》卷九《小栖霞说稗》, 民国六年刻香雪崦丛书本.叠床架屋,于前人已有考证基础上不断引证、发明,并且将之视作兴趣激发的一大快事,可见这类类比研究,不仅是清人研究学问的一种方法,也早已内化成为其性情的一部分,因此,于南戏文献考辨中运用类比法进行研究,实则也是面对同类话题不自觉而采用的做法。类比研究之所以能在包括南戏研究在内的清人考据中被普遍采用,大放异彩,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处还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无论《琵琶记》或《荆钗记》等,这类关涉书生负心的南戏剧作,清人多极力辨明其为诬指。尽管从今天的学术视野来看,这类剧作不过是借古人字号演绎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其创作之初,并不一定存在有意诬指古人的意图。然而清人这种即使对待戏曲小说这类多虚妄之言的作品,都不轻轻放过,认真剔抉辨识其本事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清人治学风气对文人学者精神状态的影响之大。
三、考据学风影响下南戏文献考辨的贡献
由于时代风气的牵动,在宏博邃密的考据学风影响下,清人有关南戏文献的考证辨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对南戏研究贡献颇大。总的说来,清人关于南戏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辨订正讹、廓清积溷,针对前人在有关南戏的理解上的讹误,在大量文献佐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合乎事实的新见解。如关于南戏渊源的考索,在这方面,自明中叶以来已多有论说,如祝允明《猥谈》所称“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25]225,徐渭《南词叙录》所谓“南戏始于宋光宗朝”[26]等,均以为南戏始于宋代。经南戏专家钱南扬先生的研究,也确证了这一说法的可靠性。然而,有关南戏与北曲杂剧的年代先后问题,明代以至清初诸家,或不言先后,或误以为南戏系承北曲杂剧之后而出,如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宋元以来,因金人北曲,变为南戏”③王圻. 《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乐考》, 明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 按: 清代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十八《乐考》“俗部乐”条所谓“宋元以来, 因金之北曲, 变为南戏”, 系袭自王氏《续通考》.,清初纳兰容若《渌水亭杂识》亦谓:“元曲起而词废,南曲起而北曲又废”[27]。实则,据前引《猥谈》所言及史玄《旧京遗事》:“院本杂剧肇于金元全盛之时”[28],即可知南戏年代当早于北曲杂剧。但历朝以来无人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直至乾隆初年,清人翟灏著《通俗编》,通过史料排比研究,方才首先提出了“南戏肇始,实在北戏之先”的观点:
【南戏】祝允明《猥谈》:“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有赵闳榜禁,颇著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后日增,今遂遍满四方,辗转改益,盖已略无音律腔调。愚人蠢工,徇意更变妄名,如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趁逐悠扬,杜撰百端,真胡说耳。”叶子奇《草木子》:“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识者曰:‘若见永嘉人作相,宋当亡。’及宋将亡,乃永嘉陈宜中作相。其后元朝,南戏尚盛行,及当乱,北院本特盛,南戏遂绝。”《庄岳委谈》:“今《王魁》本不传而传《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为今南曲首。然叶当国初,著书而云‘南戏绝’,岂《琵琶》尚未行世耶?”按:南戏肇始,实在北戏之先。而《王魁》不传,胡氏乃以王、关《西厢》为戏文祖耳。今戏曲合用南北腔调,又始于杭人沈和甫,见钟氏《点鬼簿》①翟灏. 《通俗编》卷三十一, 清乾隆十六年翟氏无不宜斋刻本.。
翟氏这节文字,后为李调元全文照录入其于乾隆四十九年刊刻的《函海》本《雨村剧话》,由于《雨村剧话》作为古代戏曲论著专书,在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在1959年被中国戏曲研究院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书而影响广泛,遂致戏曲研究者多以为“南戏肇始,实在北戏之先”的卓见为李调元首次提出,实则雨村不过剿袭翟氏成说而已。真正首次提出这一见解的,当为翟灏于乾隆十六年刊行的《通俗编》,早于李氏三十多年。
二是推动南戏文本文献研究由史料载录向学术研究的转变。有关南戏史料的记载,目前所见者,虽然早在元末明初叶子奇的《草木子》已现其端,其后祝允明《猥谈》、徐渭《南词叙录》等屡有述及,但实际上,这些载录多是依据见闻记录史料,或是针对南戏曲词文本的评点,而少有穷搜检讨式的研究。究其原因,明代距宋元之世不远,且“依腔传字,腔格相对固定”的南戏,其创作、传播一直持续到明中叶嘉靖年间[29],“以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为界”[30],因而明人不仅能有亲身接触南戏的机会,有较为直观的感受,同时口耳相承流传下来的有关南戏的史料也较为可信。因是口耳可见可闻,并非必须借助寻绎典籍载存方可得知,故明代的文人大多没有对南戏相关问题蒐佚检讨的意识,而只是依着文人的意趣,“饱食之暇,偶录记忆”[31],“时作杂记,聊以消闲”[32],以记述笔法记载下有关南戏的史料,或是以评论的口吻议说曲词、曲调的得失,如“南戏出于宣和之末、南渡之际,……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25]225,“谓则成元本止《书馆相逢》,又谓《赏月》、《扫松》二阕为朱教谕所补,亦好奇之谈,非实录也”[33],“传奇词调俊逸推《琵琶记》,事迹委曲推《荆钗记》;《香囊》词调不逮《琵琶》而事迹过之,事迹不逮《荆钗》而词调过之,可并存也”[34]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与文人风习的引导下产生的结果,有其出现的历史与现实的依据。即便如胡应麟所作《少室山房笔丛》,论说颇有引证,却也多是仅限于援引一两则文献以证明自己言之有据,绝少有像清人那样的博证文字。相较而言,清代文人在面对有关南戏文本文献的论题时,态度则要严谨的多。由于清代距离宋元南戏盛行之时年代已颇久远,而南戏也在戏曲本身的演进过程中经蜕变而以传奇的面貌出现,清人失去了明代那种可以亲身接触南戏的感受,口耳相传的有关南戏的见闻也多因转述过多而悠缪难据。清代文人一方面受到时代风气的牵引,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现实依据的缺乏,因而其关于南戏的探索,往往只能从文献出发,围绕某一论题,通过多则文献史料的比照参证,抉微发覆,以求得一是。如前文所引有关梁祝题材南戏本事的考证、关于《荆钗记》本事原型的考证,以及清人探讨兴趣极大的关于《琵琶记》人物本事的考证等,均是在引证大量相同或相近题材的文献资料,反复比照、推研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见解。可以说,正是由于现实条件的转变、考据学风的濡染等多重因素的作用,清人关于南戏文献的考辨才洗脱了前人多随兴漫笔、以述为主的面貌,善考索,重博证,从而获得与诸子杂史等考证相埒的地位,由史料载述、评点转向学术研究的路线。
三是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式法的关于南戏文本文献的研究方法。清人的治学方法,据罗振玉归纳,概括为征经、释词、释例、审音、类考、攈佚六类[8]133-135。所谓征经,即征引经籍,证明己说;释词即杂考词源,疏释词义,辨明句旨;释例,即彰显异同,以例明之;审音即辨明韵节,协和平仄;类考,即以类归摄,考流溯源;攈佚,即蒐罗子史,攈拾佚典。这六类方法,在清人学术中往往并非单独运用,而是彼此依存、互为发明、融为一体的,它们有的是具体的研究形式,如释词、释例、审音、攈佚等,有的则是具有统摄意义的研究法门,如征经和类考,也即我们前文所称的博证和类比研究,在前四种方法(或曰形式)中,经常有赖于它们来完成研究论题。
在清代以来的南戏文本文献的研究中,这些方法也均得到了很充分的运用,其中释词、释例、审音诸类,如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所收《也啰》,袁栋《书影丛说》卷十三所收《乐调》,《在园杂志》卷三《歌曲》条,《乐府传声》之《源流》《句韵必清》条,《香研居词麈》之《论〈九宫合谱〉之误》《论南北曲之分》条,况周颐《眉庐丛话》之《“齣”字辨误》条,以及梁廷柟《曲话》中有关《九宫谱定》的条目等,均从一字一音入手,详明例释,博采众典,其明辨缕析的细密功夫,实与清儒考辨小学文字音韵一般无异。
而关于征经、类考两种,即博证与类比的研究方法,虽然在清人学术中得到了及广泛的运用,却并非清人的发明。据笔者考察,其最早当始于汉代的经学笺疏,后由经学拓展至史学、文学诸领域。又经由清初顾炎武等人的提倡推衍,这种治学研究的方法在清儒手中被发扬光大到了极致,几近成为当时学界定为一尊的圭臬。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在清代学界获得普遍的认同与发扬,乃在于它契合了近世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即先确立研究的问题,而后广泛搜求与此问题相同或相近的文献资料,“罗列比较以研究之”,从比较研究中渐次归纳出自己的观点,最后再根据自己的观点,从各个角度搜求文献资料加以印证,“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9]62。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科学精神”,清儒所治之学问,大多均立言有据,不易为后人所推翻。在南戏研究中,清代虽然仍保留了不少前人所流传下来的史料载述、评点等方式,但其最为核心、最见特色的文献考据部分,如前文所引《茶香室四钞》考“梁祝”本事、《浪迹续谈》考《荆钗记》本事等,均是采用博证、类比这两种方法进行抉微发覆式的考索,并且这种言必有据的“科学精神”与治学方式,一直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研究包括南戏在内的古典戏曲文本文献的方法路线,已成为被普遍认同、遵循的学术准则。
四、结 语
清代文人所载录的南戏史料范围颇广,其中最具有清代时代特色的内容,首推对南戏文献进行考证辨订的条目。由于受到清代特定政治经济环境下治学风气的影响,清儒研治经史的考据学风牵引着文人的治学兴趣,并渗透到文人笔记、诗文等多方面的撰著中,影响及其中关涉戏曲、南戏的部分,从而使得清人研究中出现了前人有过的专门针对南戏与戏曲史问题的深入探索与考辨。尽管由于时代局限,其中的一些考辨在今天看来有的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但正是在这些考证以及溯源的基础上,我们今天对待戏曲史以及南戏的认知才更加明晰与准确。在清人笔记关涉南戏文献考辨的内容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其大量地征引文献用以证明己说的类比、博证的研究方法,这与清儒研治经学、史学、文字训诂学等专门学问时所采用的讲究“一字之证,博及万卷”①阮元. 王石臞先生墓志铭[C] // 闵尔昌. 碑传集补: 卷三十九. 民国十二年刊本.“六艺百氏,旁推交通”[35]“于书无所不窥”[17]227的方法如出一辙,不仅典型地证明了清人针对南戏文献的考辨与清儒治学精神、学风之间,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为我们后人的南戏文本文献研究留下了可资式法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对之进行认真且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永瑢, 陆锡熊, 孙士毅, 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上册[M]. 整理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566.
[2] 江藩. 国朝汉学师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 徐世昌. 苏斋学案[C] // 徐世昌. 清儒学案: 第4册. 沈芝盈, 梁运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3585.
[4] 徐世昌. 朴斋学案[C] // 徐世昌. 清儒学案: 第4册. 沈芝盈, 梁运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3749.
[5] 铢庵. 人物风俗制度丛谈[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8: 204.
[6] 萧一山. 清代通史: 第2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7] 徐世昌. 让堂学案[C] // 徐世昌. 清儒学案: 第4册. 沈芝盈, 梁运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3183.
[8] 罗振玉. 清代学术源流考[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9] 朱维铮. 《清代学术概论》导读[C] //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0] 徐世昌. 钓台学案[C] // 徐世昌. 清儒学案: 第3册. 沈芝盈, 梁运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093.
[11] 徐世昌. 谢山学案上[C] // 徐世昌. 清儒学案: 第3册. 沈芝盈, 梁运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649.
[12] 徐世昌. 南江学案[C] // 徐世昌. 清儒学案: 第4册. 沈芝盈, 梁运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3973.
[13] 王士禛. 古夫于亭杂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5.
[14] 钱泳. 履园丛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
[15] 沈粹芬, 黄人, 王文濡, 等. 清文汇: 中册[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6: 1766.
[16] 全祖望.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C] // 全祖望.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上册. 朱铸禹, 汇校集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7] 全祖望. 亭林先生神道表[C] // 全祖望.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上册. 朱铸禹, 汇校集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8] 赵兴勤. 赵翼评传[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120.
[19] 钱南扬. 梁祝戏剧辑存[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20] 陆容. 菽园杂记[C] // 俞为民, 洪振宁. 南戏大典·资料编: 明代卷.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 13.
[21] 俞樾. 茶香室丛钞: 第4册[M]. 贞凡, 顾馨, 徐敏霞,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1526-1528.
[22] 金毓黻. 中国史学史[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346.
[23] 梁绍壬. 两般秋雨盦随笔[C] // 俞为民, 洪振宁. 南戏大典·资料编: 清代卷.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 337.
[24] 梁章钜. 浪迹续谈[C] // 梁章钜.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87-288.
[25] 祝允明. 猥谈[C] // 俞为民, 孙蓉蓉. 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 第1集[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225.
[26] 徐渭. 南词叙录[C] // 俞为民, 孙蓉蓉. 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 第1集[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482.
[27] 纳兰性德. 渌水亭杂识[C] // 阙名. 笔记小说大观·二编: 第7册. 景印本. 台北: 新兴书局有限公司, 1988: 4238. [28] 史玄. 旧京遗事[C] // 阙名. 笔记小说大观·九编: 第8册. 景印本. 台北: 新兴书局有限公司, 1988: 5125.
[29] 吴新雷. 论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的界说[C] // 吴新雷. 昆曲研究新集. 台北: 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191.
[30] 俞为民. 宋元南戏文本考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273.
[31] 段成式. 酉阳杂俎[C]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557.
[32]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373.
[33] 王世贞. 艺苑卮言[C] // 俞为民, 洪振宁. 南戏大典·资料编: 明代卷.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 68.
[34] 张凤翼. 谭辂[C] // 俞为民, 洪振宁. 南戏大典·资料编: 明代卷.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 85.
[35] 陶澍. 《蛾术编》序[C] // 王鸣盛. 蛾术编: 上册. 上海: 上海书店, 2012: 2.
(编辑:刘慧青)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Style of Stud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anxi Theory
JIANG C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325035)
Abstract:The Nanxi (Southern drama南戏) text literature of Qing Dynasty, showed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academic outlook. Due to the literati taste traction and affected the textual research style, on the South Wan cord identified in using the method of a lot of research learning, action of ancient today, next to push each other, which makes the study of Qing Dynasty Nanxi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all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of the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the previous incorrect understanding o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Nanxiliterature historical data recorded by the south to academic research,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to provide local people and other aspect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Key words:Qing Dynasty; Textual Research Style; Textual Research of Nanxi(Southern Drama南戏); Analogy; Extensive Demonstration
作者简介:蒋宸(1982- ),男,江苏南京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戏曲史,中国古代小说,清代文学
基金项目: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4jd19)
收稿日期:2015-04-30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6.004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6-00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