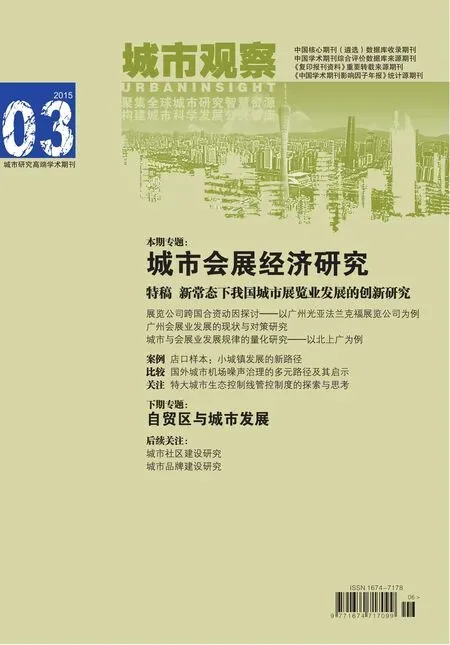书展——一场价值观的竞赛
2015-03-18布莱恩莫兰
◎ [丹] 布莱恩·莫兰
基于对法兰克福书展和伦敦书展的深入实地调查①,本文介绍了国际书展在出版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了书展如何通过将不同的参与者聚集到一个结构化的环境中展开短暂的面对面交流,来明确和重申构成整个出版领域的经济性、社会性与象征性价值观。
在许多方面,国际书展与Arjun Appadurai题为“价值的竞赛”的开创性论述中所设定的标准是一致的。他认为,书展是:
在文化定义上远离日常经济生活的周期性综合活动。参与这些活动……既是掌权者的一种特权,也是他们相互间进行身份地位竞赛的一种手段。这种竞赛的通货……也是通过已达成共识的文化符号来区分的……我们要讨论解决的并不仅仅是参与者的地位、排行、名望或声誉,而是所讨论的社会核心价值的体现,尽管这种价值竞赛是在特定时间和场所发生的,但它们的形式和结果最终还是会对日常生活的能力与价值的普遍现实产生间接影响(1986: 21)。
虽然Appadurai关于价值竞赛典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美拉尼西亚库拉圈(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群岛东南部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交易制度——译者注),但他已明确指出,当代工业化社会中存在“一种与日常的经济行为的风气形成鲜明对比争胜式、浪漫的、利己的、类游戏风气”(Appadurai 1986: 50)。为了进一步深化对Appadurai提出的“‘竞赛’经济的构成模式”(1986: 50)的研究,笔者在前人研究(Moeran 1993: 87)的基础上提出,价值的竞赛还包括:
巴黎、伦敦、米兰、纽约和东京举办的各类高级女装及成衣时装秀;索斯比、佳士得及其他艺术品拍卖行组织的带有宣传性质的拍卖活动;大型年度传媒活动如世界小姐和环球小姐等选美竞赛、欧洲歌唱大赛、格莱美音乐奖、电影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艺术展和电影节(戛纳、威尼斯等);当然,还有诺贝尔奖(Moeran 1993: 93)。
不少学者对以上内容作过研究,如时装秀和贸易展(Entwistle & Rocamora 2006;参见Skov 2006)、格莱美奖(Anand &Watson 2004)、布克文学奖(Anand & Jones 2008)、奥运会(Glynn 2008)以及各类电影节(Barbato & Mio 2007; Evans 2007; Mazza& Strandgaard Pedersen 2008)。虽然这些学者最初都会以提及“礼制竞赛”的形式承认Appadurai对他们理论论述的贡献(参见Anand & Watson 2004),但近来的研究更倾向于向制度社会学靠拢,即认为价值竞赛是一种“领域配置活动”(Lampel & Meyer 2008)。本文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和制度社会学对国际书展进行分析,建议Appadurai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应得到更充分重视,而不是像现在被断章取义。
出版业
书籍能够传递知识与想法,通过这种传递,书籍刻画出一个社会的文化,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书籍印刷成册的形式使其相较其他传播媒介拥有独特的优势:外观吸引、相对廉价、容易获取、长久保存、使用方便(参见Clark 2001: 2)。
出版是指将图书置于公共领域的商业活动(Feather 2006 [1988]: 1),出版社则是“获取内容和承担风险、以生产特定文化商品为目的的机构”(Thompson 2005: 15)。出版社吸引一大批不同类型、有意传播其想法并因此而出名的作者。与其他文化或“创意产业”(Caves 2000)相比,出版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每年推出的新产品的数量无可比拟:仅英语图书就有25万种,还有上百万种正在发售。
新产品大多是未经实验或测试的,因此它们成功与否——换言之,收益会有多少——是难以预测的。出版社面临的主要难题,一是获取内容,二是实现增长。它们一方面要培育作者,同时为了能出版作者的书稿,还要预先支付编辑、生产和印刷费用,作者的预付款自然也不在话下。一般要到几个月(往往是半年)以后这些成本才能收回——并期望进一步通过图书销售来创造利润。②所以说出版带有高风险的决策。没有资金,出版商就无法提高每年新增出版物的数量——这就意味着,为了发展,它要么设法出版一部畅销书,要么就得以某种方式筹措资金。
出版商不仅仅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它们委托作者创作书稿、并对生产、推广和销售进行投资。在此过程中,它们对作者的作品授权并添加附加值(Clark 2001: 3)。John Thompson运用了三种分析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学术出版业的组织构成。第一是出版流程,指一部图书从书稿签约到成品所经历的(通常是四个)阶段,通过定价、印数、库存、再版、绝版等决策实现。出版流程可分为两季,对大多数出版商而言即将出版的书单——即上一年度新发行的出版物——它们起着为生产开支提供资金的作用。一般20%的图书能提供80%的收入(Thompson 2005:16-20)。但出版商还要制定一份库存书籍目录,即出版首年后继续销售的书目。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收入,支撑出版商的发展(包括承担新书的风险)。
第二是出版产业链,指参与出版、销售、分销图书的相互关联的机构,互相提供对方所需的服务。因此出版产业链既是供应链,也是价值链。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增加价值,还可以利用中介(如文稿代理人和图书包装商)创造内容。出版商的核心活动是获取(和开发)内容并拟定一份出版清单;进行投资并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评估文本质量以确保其达到有关标准;图书的销售与推广(Thompson 2005: 20-6)。
第三是出版领域,由“不同的出版商、代理和其他机构各司其职的结构化空间”构成(Thompson 2005: 16)。事实上,它是由一系列相互重叠的(子)领域组成的,因为不同类型的出版物(教科书、大众读物、学术出版物等)由于要展现不同的语言、空间和技术属性,其制作过程也各有特点。
Thompson认为,出版商拥有四种资源,一是经济资本,来自金融资本的原始积累;二是人力资本,即出版社雇员和他们的知识体系;三是象征资本,由出版商在扮演文化中介和质量品味的裁决人角色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威望、声誉、受敬成都等构成,有助于出版商吸引、定位和提升新书和获取作者。象征资本同时也是由作者自己创造的,因此它是出版领域信任关系的基础(Thompson 2005: 33);四是出版商积累的知识资本(其所拥有或控制的知识产权)。“出版商获取、开发并转化为以图书为主的可交易商品的知识内容的权益总和”表现为出版社掌握的与作者签订的合同(Thompson 2005: 34)。事实上,一个出版商的主要金融资产存在于它以合同形式所获取和控制的知识产权——笔者将在本文结论部分继续对此作论述。
书展
书展只是众多展会中的其中一种,它是由出版界各方参与的获取内容和承担经济风险的过程。书展是全球出版产业的重要节点,在产业链中有特定的层次定位——图书类型(儿童、饮食、旅游等)、市场细分(贸易、学术、古文物等)、产业的地理分布(印度作曲家、香港画家等)(参见Skov 2006: 765)。作为日常销售活动的一部分,学术出版商通过参加学术会议与(潜在的)作者会面,从而获取编辑内容,同时销售其产品;参加专业培训类会议(尤其是有关电子系统开发的);参加图书馆人会议(从中了解图书馆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完善和向其推销专用电子平台);用户群以及类似的论坛(如独立出版商行业大会),让出版商能与出版产业链的其他同行分享和交流经验。
国际书展对于出版产业的组织架构尤为重要。尽管每年全球各地都会举办不同类型的书展,其中两大国际书展与图书的出版周期是吻合的,分别是每年4月份的伦敦书展和10月份的法兰克福书展。出版商都希望在上一年度的秋季推销它们来年春季的书目,而在春季书展上推销其秋季书目(Owen 2006 [1991]: 86)。
书展将出版产业中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所有参与者都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特定场合。书展还为出版领域提供了一个有形的架构,使不同出版商所掌握的各类资源(经济、人力、象征和知识资本)得以在它们运行的结构化空间中受到关注。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书展是在二战后出现的,首先在莱比锡(1946年)、然后在法兰克福(1949年)重办一项可追溯至12至13世纪的年度展会(Flood 2007; Weidhaas 2007)。从那以后,世界各地的国际书展犹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56年的华沙书展是首次在德国境外举办的书展,之后是1957年分别在贝尔格莱德和多伦多举行的书展以及1964年的博洛尼亚儿童书展。1972年,伦敦书展创办;197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书展。20世纪80年代更是书展过剩,1981年巴黎图书博览会、1982年伊斯坦布尔书展、1985年哥德堡书展、1987年瓜达拉哈拉书展、1988年德黑兰书展。到了90年代,这种趋势蔓延到中东和亚洲,1991年阿布扎比书展、1990年香港书展、1994年东京书展和1995年北京书展,到了新世纪的头十年,还有2003年曼谷书展、2006年布加勒斯特、开普敦、塞萨洛尼基书展、2008年吉隆坡和维也纳书展,等等。书展如今已成为一座城市作为出版产业“全球化中的一员及其年度时间表中的一个节点”的国际性展会(Weller 2008:111),中世纪时各个展会之间的竞争关系,时至今日仍可见一斑(参见Flood 2007: 8)。
在众多书展当中,由德国书商和出版商协会下属一家公司负责筹办的法兰克福书展无疑是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其举办地位于该市的会展场所(法兰克福展览馆),占据了所有12座场馆,时间为每年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从周三到周日)。2006年,来自113个国家的7272个参展商带来了38.24万种出版物,其中包括11.19万种新书。展会期间举办各类活动共2700场次,来自66个国家的1.1万名注册记者对书展进行了报道。③参展总人数达到28.66万人次,其中18.3万为商旅游客。④
与其他大型国际书展一样,法兰克福书展是一项商业展会,而非作者们的节日。它是国际出版发行权、版权费及其他相关合同方面全球公认地位最高的书展。与许多其他书展相似,法兰克福书展也是发行新书和宣布行业新闻的一个重要推广场所,同时也为书展参与者开展市场调研提供了契机。价值供应链的所有成员都会参与其中——包括出版商、代理、书商、图书馆员、学术人士、插画师、服务提供商、电影制片人、翻译、印刷厂、专业贸易协会、艺术家、作者、古文物研究者、软件与多媒体提供商等。⑤
不少书展都是由有国际展览机构筹办的。法兰克福书展本身就积极在世界各地举办书展,譬如,2006年伦敦书展迁址码头区遭受重创后,阿布扎比和开普敦的书展似有超越之势。另一个展会组织机构是励展博览集团,集团旗下拥有500多项全球贸易展览,服务涵盖47个关键产业,涉及航空航天、珠宝、能源、电子、体育、休闲、保健、旅游、图书与出版等。该公司(从1986年起至今)一直举办伦敦书展、美国图书博览会、加拿大图书博览会、巴黎图书沙龙、东京国际书展以及现在的维也纳国际图书展(自2008年起),与贸易协会、城市管理机构、政府或半政府组织(如每年在伦敦书展上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共同组织年度国家论坛)。
尽管法兰克福书展偶尔也会积极推动这些展会的举办,但它们绝不会照搬法兰克福书展的模式。有些书展——如博洛尼亚、伦敦和瓜达拉哈拉书展尝试成为国际版权展会,而另外一些——如华沙、北京和德黑兰书展则是国家性的,针对本地市场,往往包括公众参与。还有一些——如美国图书博览会——几乎只关注版权经销权。因此,出版商与其他参展商对各类书展的评级也大不相同,取决于它们各自的需求。通常来说,从国际性而言,法兰克福书展是公认排名第一的,紧随其后的是伦敦书展,然后要么是博洛尼亚(儿童书展),要么是瓜达拉哈拉(西班牙语图书版权展)。法兰克福书展优于其他书展,因为它有专设的贸易展区;地方政府自身有投资,这点伦敦书展没有;并且法兰克福书展组织架构相当成熟。
书展上的日常活动
那么书展上的情况是怎样的,人们为什么要去书展,又为何使书展成为一种价值观的竞赛呢?显然,书展为参展商和参观者提供了高度灵活、成本划算的环境,可以达成一系列销售与推广目标——从获取潜在的畅销书出版权,到出售电影版权,手段包括指定新的销售代表、建立品牌形象、了解竞争对手的现状、甚至是出版社转让。最重要的是,书展为参与者提供了面对面交流以建立客户关系的机会。
法兰克福书展让你能够鸟瞰出版界——各家公司的现状,以及哪家公司被出售,等等。书展是面对面交流的唯一机会,在介绍公司业务情况时,有些事靠发电子邮件是解释不清楚的。
在展会上还能建立人脉,虽然这可能不会直接创造利润,也可能是为别人创造了利润。因此,有些人脉关系需要在展会后跟进(Naveen Kishore, 海鸥出版社总经理)。
展会让你将人与名字对上号。在法兰克福书展和伦敦书展上,你会遇到新客户。我在Berg出版公司这三年就开拓了20到30个客户,这要感谢我在书展上遇到的贵客。所有订单——如今每年价值达到5万英镑——需要在书展后的三个月内通过熟人搭熟人的方式不断跟进。比如你在新加坡的联络人告诉你,纪伊国屋书屋要在迪拜开一家新店,那么你就可以开拓那边的业务。开拓人脉在任何书展上都是至关重要的(Veruschka Selbach,Berg学术出版公司前任销售经理)。
书展之所以重要,在于许多版权业务都是基于人脉关系的,需要长期维系,才能最终让你的联络人在找业务时第一个就想到你。要了解客户的品位,打比方说,你马上就能够知道应该将新书的意大利语翻译权指派给谁……
电子邮件是无法替代书展的,因为在书展上你有机会坐下来面对面聊上半个钟头(Lynette Owen,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前任版权总监)。
书展上的交流是双向的,它也为参与者提供了信息:
书展为我们带来新的资讯,而电子邮件要往往滞后一两个月才能获取信息。人们之所以更愿意交谈,是因为聊天不会像书信那般正式。在谈判中这就很关键,双方都不愿意在电子邮件中将所有事情都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因为那便就等同于作出承诺,而大家都不愿意那样做……。因此我们通过交谈展开谈判或解决问题。书展就是用来干这个的(Fanny Thépot, Berg学术出版公司系统经理)。
有多少人参加书展,就有多少经验可供分享,因此我们无法对书展或人们为何去书展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有一些——像出版商——或多或少都要驻扎在摊位上,虽然他们也会拜访其他出版商,譬如商讨联合出版或经销的可能性。另一些——像版权交易商——他们的摊位上只有几张桌椅而已。还有一些——像销售代表、经销商和书店——它们没有固定摊位,到处走动。最后一类——包括服务提供商——它们虽然有自己的摊位,但也会四处走动拜访出版商以推销各种服务。
书展的选择有很多,全球几乎每个月都有书展在举办……但应该如何参加书展?是有自己的摊位,还是与他人共用摊位?是作为参展商的一员,还是在展馆溜达?自己有摊位的好处是有一个存放图书的大本营,随时方便向参观者展示。而如果你想给自己公司的书目打开市场,那么去拜访别的摊位也许效果更好(Lynette Owen)。
各家出版商派往书展的工作人员数目大相径庭。有些大型出版公司摊位面积大,会派大量职员与潜在客户坐下来交谈(内容主要包括翻译权、电影权、媒体权等)。另一些小型的独立出版商可能只有一位工作人员负责解答问题。出于成本因素考虑,本地出版商派出的工作人员往往比外地出版商要多。
在书展上,不同的工作人员由于具备应对不同谈判的专业和知识体系,会参加不同的会议。因此,出版公司的总经理可能要参加好几个会议,探讨公司当前和潜在的境外经销状况,如哪些国家在销售、付款和折扣方面存在问题。他可能要与两三家美国的高校出版社探讨联合出版某些新书目,甚至还要与来自阿根廷或意大利等国家的、对其公司书单感兴趣的出版商就某本畅销期刊作版权买卖谈判。而来自国外的出版商也会向这位总经理推销他们带来的书单的翻译权。后者还要与为高校提供期刊检索与存档服务的公司、数据转换、数字软件提供商、系统开发等公司的负责人会面。最后,他还可能要与两到三位亚洲经销商探讨某隔壁即将开展的项目(如筹划一本百科全书)。书展结束后一周,这位总经理要撰写一份(长达10页的)翔实报告抄送给公司同事,汇报他参加书展这三天内所参加的二三十次会议的内容,并指派有关人员跟进后续工作。
销售推广经理在为期五天的书展上可能要参加50多次会议,每次大概半小时,从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这些会议基本是预先安排的,偶尔也会插进一两个临时安排的会议。销售推广经理主要关注图书的销售和版权,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经销商、销售代表和书店经理会面,推销今年秋季和来年春季将要出版的新书。
在会面中销售推广经理可能了解到各种有用或无用的信息——向阿根廷的学生销售图书的潜在可能性,俄罗斯方面想要投资一家独立出版社,等等。她可能会遇到诸如一本在中东国家销售的书籍含有裸体插画的问题。她可能会与斯洛文尼亚、巴西或白俄罗斯的出版商商讨某本期刊的翻译权问题。她还可能了解到曼谷或迪拜开了几家大型新书店;怎样充分利用图书馆的预算;在日本对于采购20万日元以上的图书产品要如何追加预算并获得委员会同意;与另一家英国学术出版商共同承担聘用一位驻美国的专职代表的费用的可能性;立陶宛图书市场的焦点;等等。同样,在法兰克福书展结束后一周,她会向同事发出一份长达10至12页的报告。
偶尔有一两个会议会当场下单(有时一位客户采购图书的订单金额在5000到1万英镑之间),但大多数情况只是口头表示有采购意向。因此,尽管我们普遍认为书展能带来新的生意,但几乎不可能准确地说一次书展能带来多少生意。版权一般是打包出售的,因此很容易计算出翻译权、电影权、商品权等的销量分别由多少。⑥不过,版权合同不一定在书展上就能签订落实:
大的版权合同一般不会在法兰克福书展或伦敦书展上签订,而是展前一两周就签好了,等到书展开幕后再公开对外宣布(Malcolm Campbell,地球观察出版社负责人)。⑦
谈到计算书展的成本收益,销售与版权大不相同。耐人寻味的是,在励展博览集团和法兰克福书展网站上公布的有关书展的海量数据中,偏偏这一项是没有的。
书展带来的收益很难量化,尤其是当它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项目,不排除那些在书展前一周就签好订单的情况。因此,像法兰克福书展这样的场合,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会面和寻找新商机的平台(Veruschka Selbach)。
总之,书展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与长期合作伙伴进行业务谈判、通过市场信息交换获取知识、开拓和维系人脉关系的机会(参见Skov 2006: 770)。参与者还可以从中观察竞争对手的展销情况。这有助于出版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纵向融合,以及出版行业范围内各家出版企业的横向交流(参见Maskell, Bathelt & Malmberg 2006:1001-2)。不过与Maskell等人所述不同的是,实际交易本身并没有被边缘化(参见Skov 2006: 770)。
受关注度
商品展销会就像一座城市,将各种陌生人聚集到一起,他们之间的交流并无统一的脚本可循。而是更像实地考察工作者,“带有个人目的的各式参与者沿着相互交织的不同轨迹,在参展商的陈列之上创造出一种景象(Skov 2006: 773)。”像舞台剧或时装秀一样,书展在某些方面转移其所展示景象的注意力。它们将“地理上分散的、社会上内嵌的、文化上蔓延的公司聚集到一个中立的地方,重新制定一种内在的抽象关系结构(Skov 2006: 768)”。作为这种内在结构重构的一部分,受关注度对于那些书展的参展商和参与者而言都是一个主要目标。展会的时间和地点、你的摊位在什么位置、摊位面积有多大、是否位列展会目录中、做成了几单生意、举办或参与了几场活动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关键。
我们首先考察书展的时间、地点和框架。伦敦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这两大国际书展举办的时间就是为了配合每年3月和10月的出版季。法兰克福书展的时间与这一条件吻合,但目前的伦敦书展并没有,因为它是在4月份举办的,所以对于出版商签订合同来说有点晚,大多数合同都是在伦敦书展前就定下来了。以儿童图书为例,本地出版商需要5到6个月时间解决翻译权问题,进行翻译、付印、9月份将成书在书店上架才赶得上圣诞节的销售。如果伦敦书展在4月份举办,那么出版周期就会大大缩短。过去有17届伦敦书展是在奥林匹亚举办,那时书展的规模较小,在3月份举办,时间较好。进入21世纪后,伦敦书展的规模愈发扩大,奥林匹亚已不能满足,需要寻找新的场地。伯爵宫展览中心能为其提供场所,但要求是伦敦书展不能在3月份举办,因为那里届时要举办理想家居展,该展会已有上百年历史,其展览日期都是刻在石碑上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6年,励展博览集团将伦敦书展从伯爵宫展览中心迁至公司拥有部分股权的位于码头区Excel展览馆⑧。几大主要参展商都表示赞成,伦敦书展得以重新在3月份举办。然而书展开幕后,大家又开始抱怨。原来Excel展览馆“位置比较荒凉”,不仅交通不便,场馆周边也没有上档次的用餐场所。励展无奈只能重新将伦敦书展迁回伯爵宫展览中心,在4月份举办。所以,伦敦书展无论是地点和时间都有所改变。⑨
这一切都与受关注度有关,因为伦敦书展是英国出版界“自己的地盘”,有关方面希望让外国来宾看到最好的一面:
人们希望留在伯爵宫展览中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地位和受关注度。因为这是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举办的展览,英国出版商希望能面面俱到。他们很在意外国来宾的看法……也就是说场馆附近得有上流的餐馆和酒吧。这就是迁址码头区失败的原因所在(Emma Lowe,励展博览集团伦敦书展销售经理)。
然后再看一下摊位的位置和大小。参展商摊位的位置和大小就能反映出其在出版界的受关注度。从这个角度说,书展就像一幅“图表”,记录了出版商和其他参与者在抽象空间中的相对位置(Skov 2006: 768)。
我们的工作是确保大家摊位的位置都能被看到,这就要求各参展商的挡板不应太长,没有太多东西阻挡人们的视线。比如说我们会限定高度不能超过4米。想要超过这个高度限制必须办理一系列复杂费时的手续,还得缴纳相应费用(Emma Lowe)。
摊位的位置和受关注度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定价机制看出,四面开展位最贵,三面开次之,两面开再次之,单面开最便宜,⑩摊位摆放的桌椅有档次不同的套餐可供租用,如果加上一些电子设备,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租金价格从158欧元到642欧元不等。
另一个感觉就是越来越多的参展商自建展位。去年,大约有900平方米的摊位面积——占整个书展摊位总面积的6到7成——是由参展商自建的(虽然在我做建筑师的先生看来,他们的设计根本不够得体!)这表明外观与差异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励展通过为微软等境外参展商提供定制设计套餐牟利,参展商只需提前与预定,到时直接飞过来参加展会便可,完全不用担心布展细节的问题(Emma Lowe)。
这里,受关注度实际上是指一种“任性”消费,有实力的大型出版集团斥巨资设计独特的摊位。这种开支唯一的好处是参展商可以在其参加的其他展会上再利用同样的设计与装备,至少在展会常客们看来,它们建立起一种“品牌识别”。这种相似的背景布置导致了不同公司间的直接比较,即Lise Skov所说的“相似性条件”。她指出,书展让出版商:
看似摆脱了历史、地理和社会背景;所有生产的痕迹都从展品中移除了。在摊位上可见的只有企业本身相对于其他公司的市场定位。一家公司想要名声在外,就必须靠标准化的标识来实现。
摊位标识显示出竞争对手之间的实力关系,不仅是出版领域本身的,还包括出版商与其他相关领域之间的(参见Entwistle& Rocamora 2006: 744)。因此,大型出版集团对于在哪里参展有着明确的偏好。
那年(2008年)整个展览都围绕阿歇特出版公司,因为它们是最先预定特定形状和大小的摊位的——从主入口进来半边主通道上的三排区域。然后兰登书屋也想预订三排区域,但出于各种原因,它们不希望与阿歇特出版公司在主通道上正对,而是想与其在通道的同一边。还好柯林斯公司看中了阿歇特出版公司对面的空展位,但我们也要事先与阿歇特出版公司商量。其实挺麻烦的,因为阿歇特出版公司旗下还有一堆子公司一同参展,必须一个个征求意见,确保没有任何冲突了,我们才能与柯林斯签协议。整件事大概花了三个星期才摆平。弄完这个我们才有时间处理其他大客户的细节问题(Emma Lowe)。
既然摊位的可溢价空间如此之大,那么它们是如何分配的呢?Emma Lowe继续道:
我们在分配摊位给参展商时采用积分制。它们的参展年限和参展面积各占50%。很难做到绝对公平,我们只能尽力而为,而这也是唯一的办法。对于有怨言的参展商,我们请他们提出替代方案,但至今还没有收到比较可行的方案。对于忠实客户我们是有回馈的。所以关键不是参展商卖了多少图书或版权,而是它们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或伦敦书展的年限有多长。
基本上是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问题的是如果有公司想扩张摊位,比如威力出版社想在明年将它那片展区剩下的位置包下来,那就意味着原先在那个位置的默多克出版社要移到别的摊位。也就是说我得开始挤走旁边的人。这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有些搞促销的参展商喜欢抱团,但有些出版服务型企业,比如DHL、UPS等货运代理,则宁愿各摆各的。
大家都怕对手抢了自己的客源,或者抢先一步践行了他们的好点子。因此我常常会被问道“某某公司的摊位在哪儿?”,问的人往往是希望或不希望自己的摊位跟某某公司挨着。这里面的内幕可不少,我的意思是,早在他们正式对外宣布以前,我就知道培生收购企鹅出版社的事情了,因为下届伦敦书展时,合并后的新公司摊位是要连在一起,并且它们会选定新的位置和设计。
这里就出现了受关注度的反面:不受关注度。有些公司希望受到关注,但又不是公开性的关注。
书展上受关注度的第三个方面是参展目录(或《官方指南》),它就像一部出版界的《圣经》,告诉你哪家企业在哪个位置,因此所有企业都希望被列入。《指南》以参展商名的首字母顺序罗列,每个条目内容包括公司名、摊位号、公司联系方式、5行左右的企业介绍以及最多3位联系人的联系方式。还会列出所有海外参展商的名录,并按产品类型分类(计算机/环保生态/烹饪术,等等)。因此每个企业都至少会被提到两次。
第四,在书展上达成的图书或其他与出版产业相关的交易。这些交易的消息除了在出版产业的不同部门间流传外,书展的每日快讯还会对其细节进行报道,让外界了解出版行业的动态。在伦敦书展期间,读者通过《书展快讯》可获悉某某出版企业并购、某小说被翻拍成电影、海外的版权交易、手机阅读、出版行业奖项、数字化创新等的新闻。
最后是各种活动。书展参与者经常会受邀参加某参展商组织的活动——如新书发布会、出版社百年庆典(Mills & Boon出版社)等。这种活动的重要性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放松的交流环境,并且让出版界的各界人士有露脸的机会,因为这些活动本身就代表了“行内人”的分类(参见Entwistle & Rocamora 2006: 741)。励展博览集团的Emma Lowe对此是这样表述的:
大家都想露脸,但光靠一两次是不够的,所以很有必要参加各种活动——无论是展期内的活动还是平时的活动……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参加这类活动有助于我了解整个行业,因为在觥筹交错之间,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几年前我们迁址码头区Excel场馆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里没有喝酒的地方。不会喝酒对出版界的人来说,绝对是职场天花板。
结论
经济人类学家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事物是如何被注入某种品质,使其价值无法单纯地用物质必需品或等值货币来衡量(Bell & Werner 2004: xi)。这一点能推动我们接下来的讨论。
关于价值观的研究一直都是人类学理论中无法绕开的话题,但David Graeber(2001)却认为,价值观往往极少被系统地对待。其中一个例外是Clyde Kluckhohn,他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新墨西哥州的5个印第安人社区展开了价值观的比较研究。Kluckhohn的中心假设是,价值观是“合意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个体在不同行为之间的抉择(Kluckhohn 1951: 395)。因此,价值观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判断行为的合理性和是否值得的标准(Graeber 2001: 3)。而这也是会展的核心。
回到本文的开头部分,笔者曾建议追溯过去几十年的人类学分析,并用“价值观”替代Appadurai所用的“价值”一词。书展便是一个价值观的竞赛,因为所有参与者在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乃至任何其他书展(或商品展销会)上的各种行动轨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相反,如前所述,出版界是以四种资源为特征的。不同的价值观——或曰价值(Hyde 1983: 60)——正是由经济、社会(或人)、象征和知识资本的不同形式所创造、竞争和维系在书展上的。参与者们都表示,强化社会关系是书展的一个关键功能。他们也受到了摊位位置、布置、规模,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交流的渠道达成交易,会展期间参与或听闻的活动等象征性的影响。最后,出版商还要就作者的知识资产——或曰创作力——进行交易谈判。正是社会性、象征性和创作力(赏识)价值观的结合,将无价的“价值”转化为价格或经济价值。书展恰恰是这一方程的体现。
正是参与者认为出版界是什么样的,他们能从中获取什么,才造就了世界各地的书展。社会性、象征性和创造性价值观只有在这一社会关系网中才能存在并有效运行。因此,经济价值在本质上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只有与其他价值观相比较或相联系才具有意义(Saussure 1983 [1916]:116-18),还可能包括物品的物质/技术和实用性属性。与提到的其他价值观一道,它们构成了一个价值观的域,其竞争与议价构成了(商品交换)价值本身(Moeran 2004: 266-70)。
其次,国际书展——与时装周、格莱美奖等一样——明确地界定了一个特定领域(出版、时装、音乐)。尽管它们的实现方式可能并不一致,因为每个“价值观的竞赛”都会强调某一些价值观,而忽略另外一些。例如,书展体现出的某些仪式行为元素,并不一定适用于奥斯卡颁奖典礼(Faulkner & Anderson 1987;Levy 1987:269)。虽然法兰克福书展上也会颁布两项文学奖——德国书业和平奖和德国图书奖——并且诺贝尔文学奖或多或少会与法兰克福书展的举办重合,但总体来说,主流文学奖项一般和书展无关。这些奖项为某些人带来特权,使他们在出版领域构筑起声望等级,而且还可能对小说销售和未来的预付款和合同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不如格莱美奖或布克文学奖在商业性、吸引大众口味、乃至创造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方面的影响力深远(参见Anand &Jones 2008; Watson & Anand 2006)。
无论如何,书展在许多其他方面都符合Appadurai所定义的价值观的竞争。这其中又有象征性、社会性和创造性起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发生的综合的周期性事件。它们是“礼节性的特殊事件”,是在时间、地点、布置和道具方面都有“固定场所”的一场“表演秀”(Baudrillard 1981: 116; Malinowski 1922: 85; Smith 1989: 108-9)。在封闭无窗的建筑物内,以特定的摊位构造和摆设,展厅将书展与外界隔离开来。如前所述,它们对出版领域的大客户(各家出版机构、版权出售方、服务提供商、代理、媒体)作出空间上的定位(参见Entwistle &Rocamora 2006: 736)。与时装秀一样,只有那些在出版领域拥有一席之地的人才能有幸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大型国际书展。因此,书展的封闭性是其神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书展还具有将出版业定义为一个社群(更普遍的说法是一个“大家庭”)的作用,因为书展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践空间,在那里受关注度和互相认可能带来归属感(Entwistle & Rocamora 2006:743, 749)。书展包含了社群成员身份的问题,管理着参与者的人际间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在其他“行内人”作一系列展示时约束他们的行为(包括行业用语和着装规范)(参见Smith 1989: 51)。
虽然书展不在日常经济生活之列,但书展上发生的事情(版权买卖,代理、销售代表和分销商的任命等)会对出版界整体的日常运行产生影响。价值观竞赛的特点是它们使用的是一种并非货币形式的“通货”。譬如在时装秀中,“系列”便是衡量设计师本季出品的通货。书展的“通货”则是从版权中衍生出来的知识产权资产,因为它们是出版者拥有的价值核心。版权并不一定遵循供求法则,因为它们依赖于个人口味(故版权代理需要长年培养人脉关系和了解买家的品位)。版权本身与作者和出版社的地位、等级、名望和声誉有关,也与具体买卖版权的双方有关(因此,英国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前任版权总监莱内特·欧文女士常被人称作“版权女王”)。然而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作者有没有能力写出一本或一系列畅销书。
版权无疑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版权除了具有法律和经济影响外,还有更多的内涵。在探讨Mauss关于礼品的著名文章时,Maurice Godelier (2004: 19)区分了出售的商品(可让渡和被让渡的)、礼品(不可让渡但被让渡的)以及自留的圣物(不可让渡和未被让渡的)。例如,在美拉尼西亚的一些地方,有些物品在库拉圈上发布、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以前,是属于一个家族或某个人的。但即便在转以后,这种物品仍旧属于原所有者,他们理论上可以要求临时保管人将物品归还。换言之,物品的主人将使用权割让从而产生了礼品,但并没有给出所有权 (Godelier 2004: 15) 。因此有些贵重物品虽然被让渡了,但它们仍然是原所有者的不可让渡的财产。
版权显然符合这一逻辑。当一位作者将他或她的精神权注入一部作品时,意味着创作力包含了一个人(或曰创作者)将其内在融入一个物品(创作作品)——这便是版权法所支撑的内涵(参见Feather 2006 [1988]: 162)。一位作者与一家出版社签订版权合同,允许后者在限定的时间内复制其作品,出版社将这一权利及其附属权利(删减、改编、电影化、系列化)传递到出版产业链的其他有关各方。通常这些权利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归到出版社进而回归到作者,直至作者逝世后50年,届时其作品变为“可让渡的”——即可以在公共领域免费流通。版权是一种持有时便获得的东西(Weiner 1992)。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书展上“出售”版权并没有完全将物与人分离,而是带有一种给予的性质,因为创作者的某些东西仍然保留在所交换的创作作品之中。因此,版权及其相关财产权处在“礼品与商品之间一个微妙的中间地带”;它们能够满足个体致富的欲望,同时也能满足社会的需求(Hyde 1983: 81 fn)。
这里还有一个较为讽刺的现象。在许多方面,国际书展引起公众对创作作品版权买卖注意。但在此过程中,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通常作者或编辑都不会参加书展,尽管他们才是出版产业中参与创作过程最多的人。相反,参加书展的都是那些负责版权流通的销售和推广人员。假设“商品必须在独立领域间相互流通”(Hyde 1983: 201),书展似乎就是为了显示图书的商品性可见,而隐藏其礼品性即持有即获得的不可让渡性。图书这种商品便是在其隐藏的礼品属性下被创造、发行、售卖和阅读的。在这个前提下,书展参与者如此重视展会期间的社会关系便不足为奇了。他们处在礼品交换的核心(Mauss 1966):通过礼品交换,空间上的接近(书展)造就了一种社会生活(出版领域)。正如Lewis Hyde所说:“礼物代表关系”(1983: 69)。
总结:书展是价值观的竞赛,因为它是在特定场所、使用特定道具、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发生的一项周期性事件。它与外界隔离,将关键代理商和机构在出版领域的空间位置具体化。通过提供一个具体的实践空间,由受关注度产生和维系的归属感,书展将出版产业定义为一个社群(或曰:“大家庭”)。同时,与其他价值观竞赛一样,书展使用特殊的通货:版权,将作者和出版机构的地位与声望联系起来。版权与金钱本身是分离的,因为一位作者的创作力——被让渡但不可让渡的——被认为是图书这种商品的内在属性。书展正是在版权法“持有即获得”的属性背景下才产生。
注释:
①笔者在2007年法兰克福书展和2008年伦敦书展上对书展参与者进行了为期3天的观察,旁听了Berg出版社与来访的销售代表、分销商、出版商等的会谈。并于2008年2月的某一天前往里士满拜访了励展博览集团,与负责伦敦书展的职员交谈。在得到该公司许可的情况下,笔者有幸在开展前一天跟随职员进入伯爵宫展览中心,观察他们的布展情况。笔者还与法兰克福书展的布展负责人有过交流。
②期刊是出版商的一项重要资产,因为订户预付的费用可以提供现金流。各种支付方式的引入,如按次计费,使得该项收入分散到全年。
③贸易展览和节庆活动中的媒体参与对这些事件的宣传报道和营造正面形象通常都会起到关键作用(Mossberg & Getz 2006: 321)。
④书展只在周末向公众开放。这类数据以及书展的声望是书展的潜在参与者是否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参考标准(参见Berne & García-Uceda 2008: 567)。
⑤出版领域中唯一一类基本不参加书展的人便是编辑。作者一般也很少参加书展。一位知情人士是这样形容的:“让作者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就好比牵着一头牛去参观史密斯菲尔德食品有限公司(美国最大的猪肉和肉制品公司)”。
⑥Owen (2006 [1991])列举了各种可以议价的项目,但学术图书的版权买卖中一个基本的经验法则是,出版商定价的10%乘以印数。
⑦Entwistle and Rocamora (2006: 742)指出,尽管时装秀从表面上看是在卖衣服,但其实大多数交易在时装秀开幕前就已经达成,因为等到时装秀开始再谈的话,衣服早就过季了。
⑧很多节庆活动都没有自己的场馆(Mossberg & Getz 2006: 319)。
⑨励展现已成功租到伯爵宫展览中心的第二座场馆,因此场地问题没有那么紧张,参与者也比较满意。
[1]Anand, N. & B. Jones 2008. Tournament rituals, category dynamics, and field configuration: the case of the Booker Priz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5, 1036-60.
[2]——& M. Watson 2004. Tournament rituals in the evolution of fields: the case of the Grammy Award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 59-80.
[3]Appadurai, A. 1986. Introduction.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ed.) A. Appadurai, 1-72.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4]Barbato, M. & C. Mio 2007. Accoun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control in the cultural sphere: the case of the Venice Biennale. Accounting, Business and Financial History 17, 187-208.
[5]Baudrillard, J. 198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rans. C. Levin). St Louis, Mo: Telos.
[6]Bell, D. & C. Werner (eds) 2004. Values and valuables: from the sacred to the symbolic.Walnut Creek,Calif.: AltaMira.
[7]Berne, C. & M.E. Garciá-Uceda 2008. Criteria involved in evaluation of trade shows to visit.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37, 565-79.
[8]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9]Caves,R. 2000.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Clark, G. 2001. Inside book publishing (Thi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1]Entwistle, J. & A. Rocamora 2006. The field of fashion materialized: a study of London Fashion Week.Sociology 40, 735-51.
[12]Evans, O. 2007. Border exchanges: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film festiv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15, 23-33.
[13]Faulkner, R. & A. Anderson 1987. Short-term projects and emergent careers: evidence from Hollywoo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879-909.
[14]Feather, J. 2006 [1988]. A history of British publishing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5]Flood, J. 2007. ‘Omnium totius orbis emporiorum compendium’: the Frankfurt fair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n Fairs, markets and the itinerant book trade (eds) R. Myers, M. Harris & G. Mandelbrote, 1-42.Delaware: Oak Knoll Pres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6]Glynn, M. 2008. Configuring the field of play: how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impacts civic commun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5, 1117-46.
[17]Godelier, M. 2004. What Mauss did not say: things you give, things you sell, and things that must be kept.In Values and valuables: from the sacred to the symbolic (eds) C. Werner & D. Bell, 3-20.Walnut Creek,Calif.: AltaMira.
[18]Graeber, D. 2001. 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New York: Palgrave.
[19]Hyde,L. 1983. The gift: imagination and the erotic life of property. New York: Vintage.
[20]Kluckhohn, C. 1951. Values and value-orient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an exploration in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eds) T. Parsons & E. Shils, 388-433.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Lampel, J. & A. Meyer 2008. Field-configuring events as structuring mechanisms: how conferences,ceremonies, and trade shows constitute new technologies, industries, and marke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5, 1025-35.
[22]Levy, E. 1987. And the winner is ...: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Oscar awards. New York: Ungar.
[23]Malinowski, B.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24]Maskell, P.,H. Bathelt & A. Malmberg 2006. Building global knowledge pipelines: the role of temporary cluster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4, 997-1013.
[25]Mauss, M. 1966. 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London: Cohen & West.
[26]Mazza, C. & J. Strandgaard Pedersen 2008.Who’s last? Challenges and advantages for late adopt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eld. ?reative Encounters Working Paper 16,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27]Moeran, B. 1993. A tournament of value: strategies of presentation in Japanese advertising. Ethnos 58, 73-94.
[28]——2004.Women’s fashion magazines: people, things, and values. In Values and valuables: from the sacred to the symbolic (eds) C. Werner & D. Bell, 257-81.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29]Mossberg, L. & D. Getz 2006. Stakeholder in?uences on the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of festival brand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6, 308-26.
[30]Owen, L. 2006 [1991]. Selling rights (Fif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31]Powell, W. 1985. Getting into print: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scholarly publishing. Chicago:University Press.
[32]Saussure, F. de 1983 [191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R. Harris). London: Duckworth.
[33]Skov, L. 2006. The role of trade fairs in the global fashion business. Current Sociology 54, 764-83.
[34]Smith, C. 1989. Auctio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alue.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35]Thompson, J. 2005. Books in the digital age. Cambridge: Polity.
[36]Watson, M. & N. Anand 2006. Award ceremony as an arbiter of commerce and canon in the popular music industry. Popular Music 25, 41-56.
[37]Weidhaas, P. 2007.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Toronto: Dundurn.
[38]Weiner, A. 1992. Inalienable possessions: the paradox of giving-while-keep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9]Weller, S. 2008. Beyo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ustralian Fashion Week’s trans-sectoral synergies. Growth and Change 39: 1, 1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