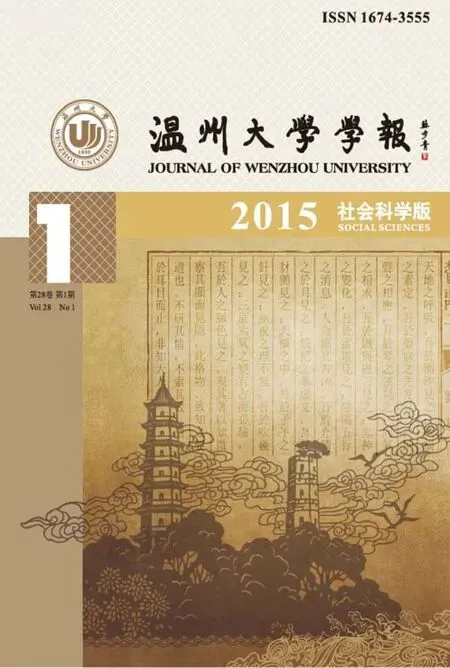好莱坞模式的移置与潜入—— 电影《特洛伊》对《荷马史诗》的改写
2015-03-17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3
张 磊(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3)
好莱坞模式的移置与潜入—— 电影《特洛伊》对《荷马史诗》的改写
张磊
(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3)
摘要:电影《特洛伊》是对经典文本《荷马史诗》的重述,它的改写体现了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典型模式,在多个电影版本的比较视域下,其叙述策略更加清晰,这种策略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强调自由主义英雄,神彻底隐退;二是戏说爱情,以其浪漫唯美面目取悦大众;三是进行存在主义的现代阐释,减弱了史诗故事的历史感。好莱坞模式已悄然移置和潜入经典之中,它不是历史电影,而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制造出的虚假幻象。
关键词:《特洛伊》;《荷马史诗》;好莱坞模式;叙述策略
古希腊时代的特洛伊战争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到了荷马口中,荷马已通过他精妙的谋篇布局为我们呈现出浩荡的战争场面、跌宕的故事情节和动人心魄的人物形象,为我们剥离出经典的叙述结构,成为西方文学的经典,而这些特质也使它成为电影艺术的宠儿。近二十年来,用镜头语言来叙述特洛伊的故事,在欧美国家出现了各种版本,如:1997年安德烈·康察洛夫斯基(Andrey Konchalovskiy)导演的《奥德赛》(The Odyssey),2003年约翰·肯特·哈里森(John Kent Harrison )导演的《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又译《新木马屠城记》),2004年由美国好莱坞华纳兄弟影业公司(Warner Bro. Pictures)出品的沃尔夫冈·彼得森(Wolfgang Petersen)导演的《特洛伊》(Troy),以及2008年泰瑞·英格莱姆(Terry Ingram)导演的《奥德赛与迷雾之岛》(Odyssey: The isles of Mists)。以上这些影片中,好莱坞的《特洛伊》投资最多,1.75亿美元,从画面到音质再到特效,制作精良,营销成功,票房最高,全球票房累计达54.3亿美元,成功地践行了好莱坞电影高投入高回报的生产运营模式。
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的电影《特洛伊》对《荷马史诗》做出了大胆的现代诠释,它在片尾字幕中声明只是得到荷马《伊利亚特》的启发(“Inspired by Homer’s ‘THE ILIAD’”),从而为编剧的再创造留下了充分的空间,运用各种电影技术手段对荷马原作加以改造、重述,体现出好莱坞电影模式的典型特征。它是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合格产品,达到了商业上的营利目的,但艺术性却大受其害,本文力图在多个电影版本的比较视域下,研究好莱坞电影《特洛伊》的叙述策略,剖析好莱坞电影模式中隐含的产业化手段对其艺术性的影响。
一、自由主义式英雄
电影《特洛伊》中神的隐退向来是评论的焦点。所谓“神的隐退”是与《荷马史诗》比照而言的。在《荷马史诗》中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呼风唤雨,左右着人类的命运和战争的结局,荷马生动细致地展现了众神的姿容、神态、动作、对话及心理活动,这样的描述达到过半的篇幅。在荷马那里,特洛伊战争既是凡人之间的斗争,也是神与神、神与凡人之间的斗争,而与凡人同形同性的神不过是对人自身的观照,是否展现和如何展现神的形象关系到是否贴近荷马的原作和精神。同题材的几部欧洲电影中都以各种方式展现了神的形象和力量。1997年的《奥德赛》剧情十分忠实于荷马原作,众多神祗现身,飘忽来去,悬在空中,背后有光晕,面容或圣洁或威武,掌握着人物的命运。2003年的《新木马屠城记》中,三位女神将帕里斯引入缥缈幻境,女神阿芙洛狄忒施展神力为帕里斯和海伦展现幻象,冥冥中促成了二者的爱情,神明确参与和构织了剧情。2008年的《奥德赛与迷雾之岛》中,雅典娜也飘临奥德修斯面前给予他重要的指示。在这些影片中,神都现出真身,以其话语启示和指引人,影响了人物的命运并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而在电影《特洛伊》中,神的种种形象皆被隐藏,只有冰冷的神的塑像不断闪回,唯一出场的一位女神——阿基琉斯的母亲忒提斯,完全以普通人的形象出现,身周既无光晕,也未在空中飘荡,而是立足水边,皱纹丛生,额际一抹白发,宛若一位人间慈母。对一般观众而言,倘无《荷马史诗》的阅读背景,定然无法确切了解她作为海洋女神的身份和威力。重要的是神的旨意与安排全然不见,一切都落实到尘世中来,信神的,不见神助,不信神的,也未见神的报复。
《特洛伊》在情节上不但消隐了神的形象,还添置了阿基琉斯挥剑斩断太阳神阿波罗头像一节。阿波罗在电影中不过是一尊金色的塑像,他的头颅被阿基琉斯无情地斩下,无力地躺在地上,在阿基琉斯眼里,只有敌人,没有神,而攻城后,特洛伊王宫中所有的神像悉数倒下,这样对于神的公开的侮辱和挑衅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也并非荷马《伊利亚特》中的情节,但对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就毫无所谓了。《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的死本为阿波罗的报复所致,在电影中却毫无交代,而是改编成死于帕里斯的箭下。电影展现和强调了人对神的不屑和侮辱,却隐藏了神对人的报复,于是神的力量变弱了,观众对神的敬畏感也随之减弱。对于后现代语境中的观众而言,一切权威、中心和意义皆可颠覆和逆反,神的退场也易于接受。
《荷马史诗》中的古希腊时代是人神共生的时代。古希腊人认为神的旨意不可违抗,但在与神的对抗中体现出的人的价值与尊严是可贵的,《荷马史诗》彰显的正是这种反抗精神。正因为神的强大,才显出敢于反抗神的人的伟大。当神隐退,人的反抗精神也随之削弱。《伊利亚特》中的主角是阿基琉斯和赫克托尔,他们是在神的强大意志下展开抗争的,他们对抗的是神意安排的命运,当《特洛伊》中的神迹消隐之后,他们通过英勇的战斗来维护自我尊严、证明自我价值的精神犹存,但他们反抗的目标已变成专制强权与俗世观念,他们也由此成为直面现实积极抗争的英雄,这更接近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更易为现代人理解。
作为人神之子的阿基琉斯,在荷马口中是“神样的”“捷足的”[1]6,荷马多次强调他是“宙斯宠爱的”“女神的儿子”[1]368,对他的神性血统毫不掩饰,他的母亲可以为他向宙斯求情,为他请赫淮斯托斯打造黄金战甲。到了《特洛伊》中,阿基琉斯的神性血统被淡化,他从未请求过母亲帮忙,也从不看重自己的出身,而他对阿伽门农的无畏反叛、对帕特洛克罗斯的手足情谊和对普里阿摩斯的悲悯情怀均十分忠实于原作精神。电影中的阿基琉斯宽厚待人,尊重下属,尊重勇敢的敌人,也尊重勇敢的女俘,唯独憎厌高高在上的阿伽门农,阿基琉斯明确表示自己“不为国王而战”,认为为一个蠢国王赔上一条命是不值得的,他也不为希腊而战,当希腊军队溃败的时候,他并不十分忧虑,他不是一名只会服从的战士,他还会深入思考战争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他乃是为了不朽的声名而战,只为自己而战,不受任何人控制,他为之奋斗的是个体而非集体的荣誉,甚至他的傲慢、愤怒和任气使性也是他坚持自我的方式,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行为方式使阿基琉斯成为一位反强权反体制的现代英雄,而对于自由的寻求、对于体制的反叛正是渗透在电影中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在阿基琉斯的反叛精神上,好莱坞与几千年前的荷马找到了契合点。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阿基琉斯的一段话:“众神羡慕我们,因为我们有一天会死,每一刻都可能是最后一刻,所以一切都变得更美好,现在就是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候,因为它永不再来。”这段哲理化言说是编剧对原作的现代阐释,明确表达了作为人的美好,作为神的局限,这一观念指向的是对神的蔑视,而非对神的崇拜,这也成为整部影片人反抗神的哲学基础。
另一得到凸显的人物是赫克托尔,他讲求公义,为他所热爱的国家、父兄、妻儿而苦战,明知不敌阿基琉斯,仍然勇于担当,为家国和自己的荣誉而战斗,其精神与荷马原作是一致的。荷马称赫克托尔同样是“宙斯宠爱的”[1]142,而《特洛伊》中的赫克托尔是其父兄、妻子、人民所一致认可的,当特洛伊的君臣们不切实际地幻想着神的相助,只有赫克托尔能够冷静地分析战争形势,他明白神是不会替他们打仗的,而唯有相信自身的力量,他这种不依赖于神的心灵的勇猛与雄伟,与阿基琉斯是一致的。
二、战争背景下的理想爱情
战争与爱情是文学与电影表现的永恒母题。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展现了战争中的英雄精神以及帕里斯与海伦的悲剧爱情。同样的母题,在电影中衍生出的主题是多样化的。《新木马屠城记》着眼于表现战争中人的野心与欲望及人的命运起伏,在同类电影中对战争本质的揭示最为深刻。影片末尾通过音乐、灯光、布景合力表现战争的结局,对战争进行反思,具有厚重的历史感,犹如一场战争悲剧。至于《特洛伊》,它用远景镜头展现了战争的宏大场面,用近景镜头呈现了勇士们贴身肉搏的惨烈景象,辅以电脑特效,以强大的影像冲击力来震撼观众,该片的导演沃尔夫冈·彼得森致力于打造一种完美的视觉效果,给观众以真实感,将观众带入故事中,以消除几千年来人们心灵上的距离,战争场景仅在这一层面上显示出意义,战争仅仅作为景观存在,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和舞台,导演无意于揭示战争的本质这一严肃而沉重的主题。
《特洛伊》开场即用旁白明示主题:战斗的勇气、不朽的荣誉、热烈的爱情,这三个方面有一个隐含的共同的定语,就是“个人的”。战争不过是阿基琉斯追求名誉、施展才能的舞台,不过是赫克托尔捍卫家国、担当责任的路径。由帕里斯、海伦的爱情点燃的战争,成为个体寻求真爱的背景,正因战争的存在,更显出爱的坚持和爱的激情。影片聚焦于爱为何物,可以让人不惜触发战争,背负耻辱与骂名,乃至付出生命。原本英武年轻的墨涅拉俄斯在电影中变得老气横秋、粗鲁野蛮,且是好色之徒,不懂得爱惜海伦,而帕里斯却是风流倜傥、俊美潇洒,爱情将海伦从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中唤醒,更让帕里斯由风流成性变得认真、专情,这些都为帕里斯与海伦的私通铺垫了种种合理性,编剧甚至没有安排帕里斯的死(古希腊神话中帕里斯死于神箭手菲罗克忒忒斯的箭下),而是让他与海伦在特洛伊陷落后逃出生天,反让海伦的前夫墨涅拉俄斯在决斗中意外死于赫克托尔之手(荷马原作中墨涅拉俄斯在攻城后与海伦重逢)。特洛伊沦陷了,爱情却存活下来,电影将这一爱情演绎得唯美而浪漫,大大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伊利亚特》的结局原是悲剧性的城市陷落,英雄惨死,爱情毁灭,由此凸显出与悲剧命运相抗争过程的精彩与壮丽,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抗争精神乃是史诗的核心。而《特洛伊》保留了城市陷落与英雄惨死,却让帕里斯与海伦的爱情存活,使原作一悲到底的悲剧结局有所缓冲,也使观众的悲悯情绪得到慰藉,同时影片的悲剧精神大为削弱。影片这一媚俗式的剧情改编,虽取悦了观众,却降低了电影的文化品位。
电影中另一对年轻人阿基琉斯与布里塞伊斯的爱情,则完全是编剧的铺陈演绎。布里塞伊斯这一人物确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出现,她的丈夫被阿基琉斯杀死,阿基琉斯“辛辛苦苦从吕尔涅索斯把她抢到手”[1]51,此后她成为阿基琉斯的女俘。对于二人的感情,荷马用语不多,阿基琉斯曾说,布里塞伊斯是“我心爱的侍妾”“我从心里喜爱她,尽管她是女俘。”[1]200荷马称布里塞伊斯是阿基琉斯的“伴侣”,当布里塞伊斯被阿伽门农抢走时,布里塞伊斯“不愿意”,而阿基琉斯则“流泪”并到海边向母亲哭诉,请求母亲帮助。即便在古希腊神话中,对此也只做了简单描述:“姑娘怏怏不乐。她已经爱上了宽厚温良的主人。”[2]352到了电影《特洛伊》,编剧首先为布里塞伊斯杜撰出贵族身份,使其成为帕里斯的表妹,王室的成员,又编织出阿基琉斯与布里塞伊斯相处中的心灵沟通,阿基琉斯将她从士兵的凌辱中救出,二人倾心交谈,在对彼此的赞赏中生出情愫,阿基琉斯甚至因她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产生了退出战争的想法,攻城后阿基琉斯又舍命维护并因此丧生,由此他们的爱情成为由战争催生、推动并毁灭的有始有终的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荷马作品和古希腊神话中聊胜于无的情节在这里被大肆敷衍成整部影片的核心故事,弥补了男主角情感生活的空白,使爱情故事更加丰富多彩。
通过对两场爱情细致而理想地描摹,导演试图为观众搭建通向古希腊的桥梁。在《特洛伊》的国际版预告片中,导演就将帕里斯对海伦的爱情阐释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激情”(a passion for one woman),这样的阐述也意在通过男女之爱这种人类最普遍的情感来沟通古人与今人。影片淋漓尽致地演绎了爱情故事的经典模式:才子佳人模式(帕里斯与海伦相恋)、三角恋模式(墨涅拉俄斯、帕里斯与海伦)、红颜祸水模式(因海伦引发特洛伊战争并致帕里斯国破家亡)、英雄救美模式(阿基琉斯搭救布里塞伊斯)。其中,才子佳人模式、三角恋模式和红颜祸水模式是原作中暗含的,而阿基琉斯与布里塞伊斯之间的英雄救美模式就是典型的过度诠释。古人与今人的情感是相通的,正是通过爱情,影片消除了观众对于古人的距离感,抓住了观众的心。
暴力、血腥、爱情、肉体,是好莱坞电影产业必备的要素,在各种题材中好莱坞都进行了机械复制,《特洛伊》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在这些要素的引导下,战争成为暴力和血腥的舞台,爱情成为叙述的主线,明星肉体的裸露成为引人眼球的看点。《特洛伊》为我们展示了爱情的美好与理想,爱情对于双方自我的净化与升华,以此触碰观众的心灵,满足观众的娱乐心态,不像《新木马屠城记》那么残酷与沉重。正像电影史学家托马斯·沙兹指出的,电影变得“越来越以剧情为驱动,越来越成为本能的、运动的和快节奏的,越来越倚重特效,越来越离奇古怪(因而也就全然无关政治),并且越来越集中地针对更年轻的观众群体”[3]7。
三、存在主义的现代阐释
“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4]233福柯的这一论断提醒我们应当注意电影制作发行的年代。后现代语境的浸润,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当下电影自身所带有的企业性和商业性都必然对电影的制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化的两大发源之一,与美国是同质文化,隔膜的仅仅是三千年漫长的时间距离,好莱坞的产业化运营自然要考虑现代观众的接受程度。好莱坞并不着意于反映古希腊人的历史故事,而更倾向于藉此建构自己的价值观,以赢得公众和票房,美国一面大力推销自己的文化工业产品,一面借助于电影这种大众媒介来实现其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阐释不可避免,重要的是如何阐释和阐释出了什么。《特洛伊》的编剧是大卫·贝尼奥夫(David Benioff),他在《荷马史诗》的启发下进行的改写属于对经典的重述。经典重述必然产生经典文本与重述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带来意义的增殖,增加审美快感,为观众带来更多想象的空间。好莱坞电影改写经典文学作品不胜枚举,它主要考虑票房价值,以及能否迎合观众的情趣。好莱坞由此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但它在商业利润驱使下和意识形态渗透下做出的阐释和重述,我们也理应对其提出质疑。
电影无论怎样阐释经典,都难逃其“前文本”《荷马史诗》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引发“影响的焦虑”,也自然会形成卡洛儿所称的双层交流体系——坦率明朗的故事呈现给普通观众,而电影对原作的互文性和指涉性则留给影迷和专业人士探究[3]11。阐释是多样化的,《新木马屠城记》中以墨涅拉俄斯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墨涅拉俄斯以见证者身份试图还原历史真相,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故事讲得完整而贴切,但在后现代语境下试图讲述真相的观念明显有违时宜了。因为任何真相都只是一种叙述。其实,美国华纳兄弟公司早在1956年就出品了由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导演的《木马屠城记》(Helen of Troy),这部最早以《伊利亚特》为题材的电影因时代所限,大量情节如同室内剧,多采用定镜拍摄,背景音乐夸张而激越,以海伦和帕里斯的爱情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主要人物阿基琉斯和赫克托尔却不突出。48年后,《特洛伊》以全新面貌登上银幕,给予经典故事以崭新的现代阐释。
《特洛伊》的阐释是建筑在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阿基琉斯已成为一位看清了世界的荒诞本质并勇敢地反抗的存在主义者。参战前母亲告诉他摆在面前的两条路:要么英勇战斗、千古留名但命不长久,要么默默无名、平安一生,阿基琉斯义无返顾地进行了自由选择,只因自己天生就是战士。当布里塞伊斯欲刺杀他时,他说:“人都难逃一死,今天死跟五十年后死有什么差别?”如同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在小说《局外人》中的表述,主人公默尔索觉得:“世人都知道,活着不胜其烦,颇不值得。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区别不大……”[5]57二者的话如出一辙。阿基琉斯看透了战争的实质,不过是阿伽门农个人权力欲望的膨胀,也知自己注定短命,但他依然参战,用自己英勇搏杀的行动赋予战争以价值,以奋斗的过程反抗荒诞的现实,以过程的充实反抗必死的结局。阿基琉斯的死亦是一场偶然的荒诞事件,骁勇善战、千夫莫敌的阿基琉斯竟死于自私懦弱的帕里斯箭下,只因一时儿女情长便令帕里斯有机可乘,这与原作中被太阳神阿波罗射中大相径庭,却令世事的无常荒诞感陡增。
赫克托尔也是一位存在主义者。阿基琉斯参战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赫克托尔则是被“抛到”战争中来的。他深爱妻子,渴望陪伴儿子长大,从内心深处厌战,渴望和平,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走上战场,存在即荒诞。他的先知姐姐卡珊德拉已预言了他的死亡,但他依然选择勇敢地担当,明知死亡在前方等待着,依然向死而生,这是他自己做出的自由选择,这就是他意识中认为应当做的,如萨特所言,“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绝对的责任不是从别处接受的,它仅仅是我们的自由的结果的逻辑要求。”[6]708所以自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当意识到自由的那一刻,重担和责任也随即而来。赫克托尔最终悲壮地死在战场上,却赢得对手的尊敬,以自由无畏的死抗拒了世界的荒诞。
如上所述,《特洛伊》在表现阿基琉斯和赫克托尔时,都突出了他们生命中的二难选择情境,这样的演绎,首先在于古希腊文学精神与存在主义哲学的相通。荷马是以人对神的反抗来凸显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萨特的行动哲学也同此理,萨特从人的行动来解释人,把人的唯一希望诉诸人的行动,强调以自由选择决定人的本质,“每个人都是对自我的绝对选择”[6]710。纵然反抗是徒劳的,却在反抗中确立了自我。同时史诗中以阿基琉斯和赫克托尔为代表的人对神的反抗的悲剧性结局,都显现为对于“死亡”本身的关注和对其意义的探讨,而“死亡”正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在”的展开,“亲在”的存在状态。阿基琉斯和赫克托尔敢于正视死亡,能够果断地心甘情愿地选择死亡,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谓的人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只有自由地为死而在,才给亲在以绝对目标并将存在推入其有限性中。”[7]782
《特洛伊》的存在主义阐释亲近了当代人的心灵,也带上了戏说的随意,使得史诗本身的严肃格调大为弱化,笼罩在经典史诗上的“光晕”也黯淡下来,影像虽斑斓,但来自经典的底蕴和历史感却大为减弱。因此,《特洛伊》虽是关乎历史的,却只是生产出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影像供观众消费,而并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正如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谈及后现代主义文化时提到的,彩色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它是不真实的,没有历史感,把过去变成了过去的形象,“它带给人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过去,我们只有些关于过去的形象,而不是过去本身。”[8]205《特洛伊》因取自古代题材而戴上了经典史诗大片的华丽面具,面具下仍是一以贯之的好莱坞模式,是电影工业制造出的又一虚假幻象,其消费娱乐性乃是其本质,其形象和意识都已和工业生产及商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 荷马.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M]. 罗念生, 王焕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6.
[2] 古斯塔夫·施瓦布. 希腊古典神话[M]. 曹乃云,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 352.
[3] 大卫·波德维尔. 好莱坞的叙事方法[M]. 白可,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7.
[4] 戴锦华. 电影理论与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33.
[5] 阿尔贝·加缪. 局外人[C] // 柳鸣九, 沈志明, 主编. 加缪全集. 柳鸣九,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57.
[6] 让-保尔·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708.
[7] 全增嘏. 西方哲学史: 下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782.
[8] 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唐小兵, 译. 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05.
(编辑:刘慧青)
The Hollywood Model Has Permeated the Classics—— Troy as Restatement of Homer’s Epic
ZHANG Lei
(School of Literature, Qilu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China250013)
Abstract:The Hollywood movie Troy restates the classical Homer’s Epic, which manifests the typical model of the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In terms of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film versions, Troy’s narrative strategies are more distinct, which can be reflected from three aspects blow: Firstly, it is focus on the liberal heroes, but completely hides the thearchies; Secondly, romantic narrative and aesthetic frames are created to cater and please the audience; Thirdly, the historical sense from Homer’s Epic is weakened by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existentialism. Therefor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Hollywood model has permeated the classics, which produces a false illusion instead of the real historical movie.
Key words:Troy;Homer’s Epic;Hollywood Model;Narrative Strategies
作者简介:张磊(1979- ),女,山东泰安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与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0CWYZ12)
收稿日期:2014-08-07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4.01.017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1-01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