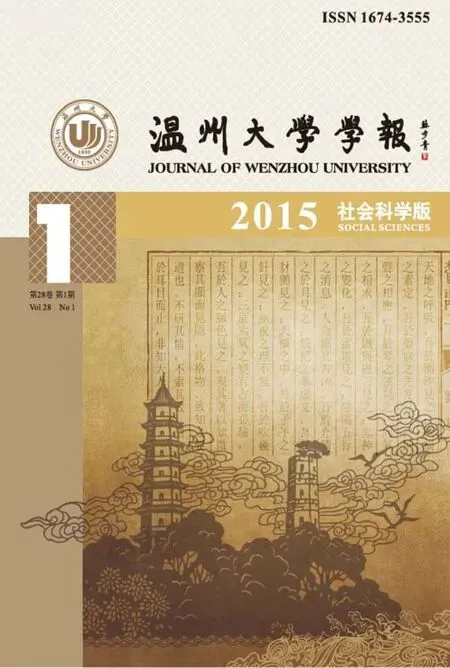传统社会春节禁忌的利益取向及功能
2015-03-17李国江山东东营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山东东营257091
李国江(山东东营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山东东营 257091)
传统社会春节禁忌的利益取向及功能
李国江
(山东东营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山东东营257091)
摘要:传统社会春节禁忌在很大程度上是巫术交感原理在年节庆典中为满足民众春节生活需求,尤其是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而被民众享用的一种生活文化。春节禁忌因其在民众观念层面特有的约束力,以及关照对象的利益取向,在构建和维护民众节期生活秩序方面具有特殊功能。
关键词:传统社会;春节;禁忌;利益取向;功能
春节是中国民众最为关注的岁时转换节点,它也成为民众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在春节这一岁时过渡礼仪中,人们以盛大的仪式和热情,除旧布新、祭祝祈年、敦亲祀祖、娱乐狂欢,同时又遵奉诸多禁忌。民众俗信的春节禁忌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且是年节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在年节期间的各项仪式和丰富的节俗活动之中,民众遵奉诸多禁忌,以此来构建维护年节生活秩序。
一、春节禁忌
禁忌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现象。民俗学意义上的禁忌,是指民众从自身的功利目的出发,在生产生活中对俗信神圣的、不洁的、危险的事物所持有的态度而形成的禁制行为。在中国,禁忌很早就广泛地存在于民众生活中,其中先秦文献《礼记·曲礼》中便有“入境而问禁”之语。作为被民众信奉享用的世俗性信仰文化,禁忌在其传承过程中,为人们严格的遵循和恪守,有的成为牢固的文化通则,代代流传。
中国春节禁忌是就春节节俗生活中的禁忌而言的。具体来讲,是指民众在春节节俗生活中,围绕着春节的节日内涵,对认为能够危害年节生活秩序的神圣的、不洁的、危险的事物采取的规避行为。春节是自然时序和人文活动转换的重要节点,是中华民族具备认同传统最隆重的岁时节日。辞旧迎新,酬报祈福是春节的根本主题。在春节节期里,人们以盛大的仪式和热情,祈愿新的好预兆。人们俗信,在新旧交替的年节,诸多事项具有了“非常日”的灵力,对他们的触犯将预示着不期的恶果。而谨遵禁忌,新年会有好的开始,会实现自己的祈愿。这种趋吉避凶的心理,使得民众在辞旧迎新的节点上更将禁忌作为顺利度过这一岁时过渡仪礼的重要手段。年节期间,民众对那些俗信蕴含灵力的语言、行为、饮食等加以规避,被时时告诫“别这样做,以免发生什么什么事。”[1]19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曾指出巫术交感原理是“联想的错误应用”[1]16,就此而言,传统社会春节禁忌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巫术交感原理在年节庆典中为满足民众春节生活需求,尤其是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而被民众享用的一种生活文化。
二、春节禁忌的利益取向
禁忌的利益取向是指民众的禁忌行为所指向的关照对象。根据禁忌关照对象的不同,禁忌的利益取向可分为两种,一是集体利益取向;一是个体利益取向。
(一)集体利益取向
集体利益取向是指禁忌行为所关照的对象是集体,通过遵从禁忌,能对集体产生影响。这里的集体是指两人以上的群体,包括家庭中成员群体组合、家庭、村落或更大的社区。具有这类取向的禁忌的实施者可以是集体中的每一个人,也可以是某一专门的人。当然,不论遵守禁忌的实施者是谁,也不论数量多寡,凡需要求遵守禁忌的实施者都必须遵守,否则整个集体利益将受到威胁,进而威胁到个人的利益,这时遭受谴责或惩罚的将是整个集体中的人。因此,凡是此类取向的禁忌,一般具有很强的约束力。马凌诺斯基(Bronislw Kaspar Malinowski)《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描述了在“库拉”活动期间,其留守的妻子必须严守贞操,如有不轨,将导致航船的失事或整个“库拉”的失败[2]。弗雷泽在《金枝》中讲到在新几内亚西南的凯伊群岛上,一旦一只驶向远方港口的帆船处于航行期间,挑选三四个年轻的姑娘和船员们保持所谓心灵上的联系,用它们的行动来为航行的安全和成功做贡献。她们必须遵守一些禁忌:
“一律不许她们离开给她们指定的屋子,更甚者,只要那只船被认为还在海上,她们就必须绝对保持静止的姿态,两手夹在膝间,卷曲地躺在席子上。他们不得向左或向右摆头,或做其他诸如此类的动作。如若她们做了,就会使船颠簸摇晃;她们也不得吃带粘性的东西,比如可可奶粥,因为食物的粘性将堵塞船在水上的航道。只有当水手们被认为已抵达目的地以后,这种严格的规定才可以多少放松一点。但直到航行结束之前,这些姑娘们都被禁止吃带刺或尖骨头的鱼类,比如榎鱼,否则她们在海上的朋友就将因此而陷于尖锐险峻的困难境地。”[1]24
由此可见,不管是为“库拉”的禁忌还是为一次远航的禁忌,这类禁忌都为一个集体来服务,此时集体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在家留守的妻子遵守的禁忌和选拔的姑娘谨守的禁忌,都是为了整个远航船队的整体利益。如若违犯,将严重影响整体利益,从而其本人亦将遭受惩罚。故此,禁忌的实施者会严格地遵守。
(二)个体利益取向
个体利益取向是指禁忌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为某个体,通过遵从禁忌,只能对个体产生影响。这类取向的禁忌,其实施者是某个体,关照的也是某个体,禁忌最终关照的个体可以是自己(当禁忌的实施者和受施者合二为一时),也可以是他人。但最终的利益取向都是个体。由于禁忌行为直接关照个体利益,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其产生的约束力一般较强。
弗雷泽在《金枝》中也描述了很多此类的禁忌。例如在沙捞越班丁地方的“沿海达雅克人”那里,男人们外出作战时,女人们必须严格遵守很多的禁忌。其中一些规定是:
“女人们必须很早就起床,天一亮就立即打开窗户,否则她们在远方的丈夫将睡过了头;女人们不得油头发,否则男人们将滑到;女人们不得在白天睡觉或打盹,否则男人们将在行军之时发困;……”[1]25
女人在其丈夫出征期间,为其出征的丈夫谨遵禁忌,其利益取向是其丈夫,不关乎他人。但是也因为个体利益取向禁忌的关照对象为个体,因此,其约束力有时显得不像以集体利益取向时那样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遵守禁忌与否,仅仅关系到个人利益,缺少一种集体力量的约束,在此种情况下,别人也无从干涉,不会受谴责或惩罚。另一方面,有些个体对禁忌的认识较淡漠,以致不会严格遵守禁忌。出于以上考虑,故会出现约束力有时相对较弱的现象。
中国春节是以家庭为内核空间的节日,人们在年节里合家团圆、敦亲祀祖。如果离开家庭空间,春节的民俗文化将会失去其传承的基础。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春节是一种典型的“家庭节日”。正是基于此,春节禁忌的利益取向在具有上述两种利益取向共性的同时,又体现出其鲜明的特点。
一是春节禁忌的利益取向更多的是关照群体对象。春节一般是将家庭或家族作为其节俗活动整合的范畴,它所聚合的是全部家庭成员,有时则是全部家族成员,节期中的活动多是以家庭或家族作为参与单位。节日庆典便以家庭或家族的群体利益作为目标,对群体利益进行最大限度的争取和扩大。因此,在春节这一家庭节日中对群体利益的最大化诉求,使得春节禁忌的利益取向于群体。传统春节中祭灶、年初一禁止向外倾倒垃圾等较普遍存在的节俗,以及类似“忌门”等在特定地域内传承的习俗中所包含的禁忌,无一不是考虑到家庭或家族的群体利益而为之。春节禁忌相对于对群体对象的较多关照,对于个体对象的利益关照则相对较少。
二是从利益取向的角度来看,春节禁忌的约束力强弱有别,主要体现为春节禁忌的群体利益取向所表现的约束力强于个体利益取向所产生的约束力。就禁忌利益取向与禁忌约束力关系的一般情况而言,个体利益取向的禁忌,个体可能会根据其对禁忌的认识和态度可以不遵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不会遭到其他群体成员的谴责或惩罚。而集体利益取向的禁忌一般要求全体成员都必须遵守,集体成员都作为禁忌的实施者,犯忌会对整个集体带来损害,因此在集体中,违犯禁忌的个体将会遭到集体里其他成员的谴责,甚至严厉的惩罚。从这一角度来讲,作为以家庭或家族为集体关照对象的春节禁忌,其利益取向所表现出的禁忌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大多要强于以个体利益取向的禁忌所产生的约束力。当然,在现代春节生活中,有些春节禁忌习俗已经消失,有些禁忌已不为人们严格遵奉,春节禁忌的利益取向与春节禁忌约束力之间的关系,也应结合社会变迁及民众价值观的变化对其加以关注。
三、春节禁忌的功能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春节是人们根据自然节律安排人文活动的重要节点,它不仅是自然时序的转换点,而且也是人文活动的转换点。春节节期随之成为二者结合而成的重要转换期。在这一转换期中,人们由一种“常日”的生活状态进入到“非常日”时段,从而使得春节节期体现出反结构性、过渡性和凸显福祸二元思维观念的鲜明特色。
在一般意义上,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利用禁忌限制和约束某些言行,规避不希望发生的某些事情,从而消除消极的情感影响,营造积极的情感取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禁忌构建和维护正常生活秩序。从这一角度来讲,春节禁忌也在维护民众节期生活秩序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
(一)构建反结构性的节期生活
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通过结构与反结构的分析进一步发展了范杰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仪式过程研究。他推论:对于个人和群体来说,社会生活是一个辨证的过程,其中涉及高位与地位、交融与结构、同质与异质、平等与不平等的承接过程[3]97。基于此,他认为在仪式过程中,存在一个对日常生活结构设定的阐明和挑战阶段,在该阶段,通过含有颠覆社会性和逆反仪式性的行为,日常生活规范受到了最为首要的对抗[3]序一。维克多·特纳将其看作是一种交融,是一种反结构。以此观点分析,春节构建了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秩序的生活领域。民众将从春节这一领域通过,这一领域不具有或很少具有以前日常生活的状况,当然,也很少具有通过这一领域之后的未来生活的状况,这是一个在年度期内相对特殊的时空领域。民众用几乎同样的心情,共享着同一种气氛,生活程序极具模式性。此时,民众已进入了一个模式化了的时空,不论高位与地位、富有与贫穷几乎都被融进这一模式之中。
人们在构建这一反结构生活中,积极的巫术是通过积极主动的形式去驱邪避灾,服务于民众生活,参与这一反结构的构建。而禁忌则是通过消极规避,去实现希冀的愿望。法术的“为”和禁忌的“不为”作为两种手段,在春节这一特殊的领域内共同构建了不同于日常生活秩序的反结构秩序。其中禁忌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在这一领域内,处处都被禁忌所围拢,尽管有些在平时是可以随意可为的,不能算作禁忌的言行,在这一时段,却只能遵从和恪守。在这种异于日常的生活结构中,对于禁忌,没有哪一个人能视其于不顾,去触犯禁忌。相反,人们都是在谨小慎微地履行着禁忌,人们抛弃了平日生活中的等级、身份观念,都不约而同地在遵守着所有的禁忌。这一时期内,禁忌对民众发挥着更大的威力,显现出一种无形的世俗权威,规范着民众应适合这一时期的生活,人们都震慑于这一世俗的权威,为自己、为他人,从而为整个春节生活构建稳定的秩序,营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因此,春节禁忌在很大程度上是构建春节这一反结构性生活的主要力量,它在维护这一反结构性生活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保障过渡性的岁时通过仪式
按照范热内普的界定,“过渡礼仪模式”本身不但包含人生过渡礼仪,而且也包括了岁时节庆等所有适合该模式的礼仪。从这一角度来讲,春节作为一种岁时节庆,自然也纳入过渡仪礼的范畴。
范热内普指出过渡礼仪由分隔、边缘、聚合三个阶段组成,就中国传统春节而言,其节期从过渡礼仪的角度来看也适用于上述三阶段。一般意义上讲,传统春节通常是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开始,包含这一仪式的节点被称为“小年”,自此便进入到年节生活阶段,直至狂欢庆典的“元宵节”结束,民众才结束年节生活状态,回到常日的生活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民众通过主动礼仪和被动礼仪确保春节过渡礼仪的顺利通过。范热内普指出,主动礼仪即将意志转化为行动;被动礼仪被称为禁忌。禁忌即为禁止,是“不许做”或“不许行动”之命令。从心理学角度看,此类行动是对被动意志之回应,正如主动礼仪是对主动意志之呼应一样,换言之,禁忌也转化为一种意志,是主观行动,而不是主观行动之否定[4]。但在整个过渡礼仪中,范热内普认为禁忌是一种依附礼仪,一个禁忌不能自成体系,它必须与某主动礼仪相辅相生。因此,禁忌只有与“主动”礼仪相互对立地共存于一个仪礼中,其意义才能被理解。事实上,在春节过渡礼仪中,民众在思维深层总是在对这一过渡期进行二元认识。一是辞旧和迎新的二元对立,一是求福和避祸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相互对立的认识中,民众能将自己的意志主动地转化为行动,即采取主动礼仪积极地迎新求福。同时,还辅以被动礼仪,即采取禁忌,以消极被动地迎新求福。但是此时的消极,从民众主观层面来看,仍然是积极的。因此,春节过渡仪式中的禁忌与主动礼仪,二者相互依存,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共同满足民众的需求。
从过渡礼仪的角度来看,民众在春节期间遵奉禁忌,其实质是将人们与日常生活暂时分隔,将其聚合入非常日的神圣的仪式时空,以利于顺利完成过渡。传统社会春节诸多仪式大都离不开禁忌这种被动礼仪的参与,就传统年节守岁仪式中的“忌早睡”习俗来说,该禁忌将民众的作息与常日隔离,使得民众进入一种通宵达旦的守岁状态,处于一种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将来的阈限期。民众认为阈限期的行为具有象征意义,除夕守岁有“惜阴”之意,谨遵该禁忌可以在岁时交接的节点上避祸求福,待阈限期过后,禁忌才得以结束,人们重又回归常日生活状态。在这里,是禁忌在助益民众通过该仪式。
可见,在春节过渡礼仪中,主动礼仪毋庸置疑地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作为被动礼仪的禁忌,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通过春节禁忌,限制和约束自己的生活,从而在岁时通过仪式中保障人们在“不为”中达到趋吉避祸的心理需求。
(三)强化趋吉避凶的民俗观念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尽管社会文化现象非常复杂、多样,甚至极度的无序,但在其中却蕴含着某种深层的统一和系统性,只有极少的关键原则在起作用。这些原则是一种基本的关系,反应的是文化在深层内涵上的对立统一,是一种共生共存但又互相冲突的关联[5]。春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其仪式繁多,节俗众多,但是民众在纷繁的仪式和众多的节俗中,始终以求吉纳祥、避祸祛凶的民俗心理行事,从而形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趋吉避凶的民俗观念,该观念深蕴在春节文化之中,并且支配着民众的节期生活。
在岁时转换的关键节点,民众趋吉避凶的民俗观念较之日常尤为凸显。民众普遍认为,春节是求吉避祸的关键节点,人们希冀在新年伊始,能求得一个好的开端,以期将来得福走运。人们也更相信,在此节点因自身言行不忌所致的祸患将可能延及来年的生活。基于此种认识,人们在春节期间一方面主动求福,凡是有好的预兆之事都积极去做;同时,也不忘积极避祸,在言行上规避兆凶的不好事物,对它们敬而远之,不说、不触、不吃,通过诸多禁忌将祸凶的兆示降到最低,从而满足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
由此可见,春节禁忌是福、祸二元观念这一文化深层结构的一种外化,它不但是民众在年节用来避祸求福的重要手段,而且它在满足民众对该观念心理需求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地强化着民众趋吉避凶的节期观念。
四、结 论
传统社会春节禁忌是民众在传统岁时转换期中为满足生活需要,尤其是心理安全需要而创造和传承的一种民俗信仰。它凭借其在民众观念层面特有的约束力,以其关照对象的利益取向,在营造节日氛围,构建和维护民众节日生活秩序方面发挥着有益的作用,并成为了传统春节节俗的重要内容。春节禁忌是深刻着传统社会时代烙印的生活文化,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段中民众的世界观。随着社会的发展,春节禁忌在传承中经历着变迁,在现代春节生活中,很多传统春节禁忌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禁忌自身的顽固性及种种社会原因,有的传统春节禁忌在现代春节生活中却仍有传承。因此,关注传统春节禁忌利益取向和功能,一方面可以认识禁忌在传统社会民众年节生活中的特有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考察传统社会民众年节心理的视角,而且也能为春节禁忌在现代社会中的民俗内涵、功能等的变迁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金枝[M]. 徐育新, 汪培基, 张泽石, 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2] 马凌诺斯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 梁永佳, 李绍明,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201.
[3]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 柳博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4]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 过渡礼仪[M]. 张举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8.
[5] 庄孔韶. 人类学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72.
(编辑:刘慧青)
Benefit Orient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Spring Festival Taboo in Traditional Society
LI Guojiang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Department, Dongying Vocational College, Dongying, China257091)
Abstract:n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Spring Festival taboo, as the life culture, is enjoyed by people. To a large extent, the Spring Festival taboo uses the witchcraft of sympathetic principle, meeting people’s life demand, especially the mental demand for tending towards luck and avoiding fierce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Because of the specific binding of folk’s ideology and benefit orientation, the Spring Festival taboo has special function in the aspects of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people’s life order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Key words:Traditional Society; Spring Festival; Taboo; Benefit Orientation; Function
作者简介:李国江(1973- ),男,山东东营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遗产
收稿日期:2014-01-17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1.014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K8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1-008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