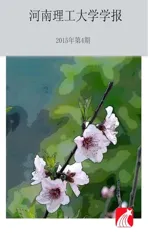言论自由与保障名誉的博弈:网络反腐视角下诽谤罪的再认定
2015-03-17胡安琪
行 江,胡安琪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言论自由与保障名誉的博弈:网络反腐视角下诽谤罪的再认定
行江,胡安琪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E-mail:444826786@qq.com
摘要:在网络反腐的进程中,公民的言论自由及宪法监督权与被举报人的名誉权均为法律所重点保护的权利,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为保证公民言论自由和监督权的广泛行使以及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热情,对网络反腐中举报人的“诽官”行为应当以最谦抑的刑法手段进行预防和惩戒。本着这个理念,在网络反腐视角下对网络诽谤的入罪标准应重新给予审慎思考,不能轻易降低诽谤罪的入罪门槛、扩大刑法的适用范围,对网络诽谤的构成要件应进行谨慎认定,以充分、合理地在打击网络诽谤犯罪的同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关键词:网络反腐;网络诽谤;诽谤罪;构成要件;谦抑性
一、网络反腐中言论自由与保护名誉的冲突
当前,民众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网络反腐的热情日渐高涨。网络反腐较制度反腐相比,更具隐匿性,有利于保护举报人,信息传播速度快,容易形成社会舆论压力,有利于降低反腐成本[1]。原陕西省安监局局长“表哥”杨达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等一批落马高官接连成为网民反腐成功的代表人物,网络反腐日渐成为新时代打击腐败犯罪的有效途径。然而,在网络反腐风生水起的同时,部分民众却恰恰利用了网络反腐的特性,恶意捏造被举报人的虚假事实并在网络进行散布,给被举报人的人格尊严、生活乃至工作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网络反腐本身是被宪法赋予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基础的。宪法第41条赋予中国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检举的权利。公民监督权的行使则须通过言论的表达,到目前为止,新中国历史上共有四部宪法都明确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然而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法律赋予公民行使权利的自由,但自由不是无边界的,正如孟德斯鸠的经典名言:“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在网络反腐的今天,这句话的意义更显深刻。法律赋予举报人言论自由和宪法监督权,但是另一方面被举报者本身亦有人格尊严即名誉权,自由的边界是义务,即不触犯被举报人权利的义务,若超出这个边界,举报人则将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就向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在网络反腐的背景之下应当如何协调举报人言论自由与被举报人名誉权的难题。
二、网络反腐中言论自由与保护名誉的协调
苏力教授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将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冲突理解为权利的相互性,若侧重于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就须提高诽谤罪的入罪门槛,但该入罪标准则对名誉权的保护有不利之虞;如果侧重于保护名誉权,则须降低诽谤罪的入罪标准,但会阻碍公民言论自由的表达[2]。苏力教授认为从社会权利的制度化配置方式来看,无论在普通法还是大陆法国家,言论自由都被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具有优先性,在美国,言论自由从1940年以后就被视为“优先的自由”,即便在表达言论自由时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也更多采用民事侵权的方式予以制裁而鲜用刑罚权。然而于志刚教授则认为:“结合我国网络诽谤行为的现状以及民主、法治的发展水平,妄言向表达自由权与名誉权某一方倾斜恐怕言之过早,而是必须在两种价值观念的平衡中,寻找刑法介入的空间与界限。”[3]
在这里笔者暂且不论名誉权与表达自由孰轻孰重,但是在网络反腐的背景之下,网络诽谤的对象是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在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直接对抗当中,普通公民作为弱势一方的力量是相当脆弱的。然而公民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民主与宪政发展的基础, 刑法若想介入必须慎之又慎。并且,言论自由与民主思想密切相关,只有保障公民充分表达对政府及官员批评、建议和检举的言论,才能形成对抗和制约公权力的强大公民力量,防止公权力走向腐败。换言之,对于公职人员的检举揭发属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由于政府越来越发觉现今社会环境的复杂,单单依靠政府一己之力已无法顺利地达成政策目标,这便需要政府借助其他力量来进行直接管理”,即通过与社会公众合作来解决,政府在管理过程中予以监督和指导即可[4]。而司法机关若对涉嫌“诽官”案件降低诽谤罪的入罪门槛,则会引起公众“公器私用”和“官官相护”的质疑。故而对于政府公职人员的监督言论,各部门法须给予最大程度的包容和保护,尤其是刑法作为最严苛的部门法,将有关监督公权力的言行入罪应当慎之又慎,方是合理的司法选择。
网络诽谤与一般诽谤的区别仅在于诽谤行为发生的领域和空间不同,两者的法律定性并无不同,对网络诽谤行为仍应当以诽谤罪来规制。但是伴随着网络反腐工作的展开,网络诽谤行为也产生了有别于一般诽谤的新特性,需要我们以不同于一般规制诽谤罪的思路来处理。按照上述平衡权利价值的理念,从刑法层面上来说,就是要对举报人在网络反腐下的“诽官”行为,以最谦抑的刑法手段来处理,谨慎界定诽谤罪的入罪门槛,对网络诽谤的构成要件重新进行刑法分析,以寻找刑法介入的空间与界限。
三、网络反腐下诽谤罪构成要件认定
犯罪构成是违法有责类型,而构成要件的机能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机能,故一个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才表明其具有社会危害性与应受惩罚性,才符合刑法规定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客观要件[5]。因此,在运用刑事手段规制网络反腐案件中的诽谤行为时,应严格坚守犯罪构成要件的底线,审慎地对某种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的犯罪成立条件进行认定。
(一)客观方面
(1)就危害行为来说,对于网络反腐中的“诽官”行为不宜扩大。刑法第246条规定的诽谤罪的客观方面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故诽谤罪的客观方面包括两种危害行为,一是“捏造”,二是“散布”。所谓“捏造事实”是指凭空编造虚假的事实;所谓“散布”是指向特定人或不特定多数人传播谣言的行为。“捏造”与“散布”行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可能同时具备,也可能只发生其中之一。这就对诽谤罪到底是单一行为还是复数行为产生了分歧。从法条文义上看,诽谤罪是复数行为,只有“故意捏造并且散布”虚构的事实才成立诽谤罪的客观方面:如果仅仅只有“捏造”一个行为,而未对捏造的虚假信息对外传播则不可能侵犯他人的名誉权,从而不能成立诽谤罪;若只有“散布”的行为而未对该信息进行捏造,亦不构成诽谤罪的客观方面。这也是中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6][7]。但张明楷教授则认为即使刑法分则条文在两个行为动词之间使用了“并且”也不一定意味着该罪是复数行为,诽谤罪条文虽然从文义上表述为“捏造并散布”,但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先捏造、后诽谤[8]。2013 年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也采用了与通说相反的解释,从实体法上看,该解释的规定无疑扩大了诽谤罪的适用范围。
不论通说和司法解释如何认定诽谤行为的单一性和复数性问题,笔者认为,在网络反腐过程当中,不宜将网络举报所引发的诽谤行为做扩大化认定,即对“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行为”不能以诽谤罪论处。首先,这种解释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是打着“法律拟制”旗号的类推解释。单纯恶意散布谣言的行为本身并不能直接等价于诽谤,否则就会超出诽谤罪语义的射程范围,有违国民预测可能性,使得民众不敢轻易行使宪法监督权,不利于打击腐败犯罪。其次,尽管民众对政府或官员行为的表述可能存在过激的情况,但跟帖、转帖行为仍是围绕政府或官员言行本身的“评论”范畴,这正是民众行使自己宪法监督权的正当途径, 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理念亦强调政府权力的民主监督,就是建立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多渠道、多层次的网络监督模式,发挥监督的整体效应[9]。虽然对网络谣言的转发可能会加快谣言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法律并非禁止一切侵害法律的行为,需要刑法介入规制的是超过法律容忍限度的危险行为。民众对政府官员工作和生活作风的批评、议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名誉权造成侵害风险,“但这种风险是任何承认并保障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所必然要面临的风险,是民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言论自由的附随物”,在网络反腐的背景下,该风险并没有超过刑法所可以容忍的限度[10]。除此之外,随着微博、微信使用率的日渐高涨,随意在网络上发布的一条信息都可能得到民众少则上百、多则几十万的浏览、评论或转发,网络已经成为民众自由发表言论、进行交流讨论的平台。在网络反腐案件中,如果对所有恶意转发行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则会导致打击范围过广,有失法律的正当性和谦抑性。刑法的严厉性要求其必须保持谦抑性,就是要尽可能缩小刑法的打击面而不是肆意扩大,在对捏造并散布者进行刑法规制就能起到抑止诽谤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的作用时,刑法就不应过度介入打击转发、跟帖的行为,否则就会溢出刑罚的必要限度,造成刑罚权的滥用[11]。除非能够证明捏造者与散布者具有共同故意,才有成立诽谤罪之共同犯罪的余地。
(2)就诽谤罪的行为对象来说,刑法分则将诽谤罪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一章之中,即刑法只保护侵犯自然人名誉权的行为,对侵犯法人名誉权的行为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当中,曾有司法机关对诽谤罪行为对象认识错误而导致错判的先例。最典型的如2007年发生的鄂尔多斯吴保全案,吴保全因在网上发帖诽谤鄂尔多斯市政府强行征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农民的承诺完全没有兑现,被东胜区法院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若行为人故意举报虚假事实来诽谤某国家机关,则必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而不能以诽谤罪论处;只能作为侵犯法人名誉权的违法行为,追究其民事侵权责任,而绝不可因诽谤的对象是国家机关而基于有关部门和上级领导的压力而对行为人突破罪刑法定的底线以刑法进行严厉打击。十八大以来,国家对于以微博反腐为代表的网络反腐声音采取倾听和更加包容的态度,在人权问题得到日益重视的今天,不应当以诽谤罪为借口实现钳制公民举报腐败的目的,地方政府也不应该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惜以公权力扼杀民众运用网络进行监督政府的权利。
(3)诽谤捏造的内容必须确证为完全虚假或存在重大虚假内容,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要构成网络诽谤犯罪,该谣言必须经过有关机关深入实地调查,在完全确定为虚假的情况之下才能考虑诽谤罪的入罪问题,绝不能在真伪不明时,未经证实就将该言论认定为网络谣言。特别在网络反腐过程当中,由于是普通民众对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检举揭发,政府及官员的腐败证据对普通民众来说难以完整的收集,并且我们不能要求一名普通民众用规范用语表述官员腐败的事实及程度,甚至民众可能只是对政府或官员的行为发表自己的评价而出现语言过激的现象,故在监督腐败的过程当中难免夸大部分内容而出现虚假的成分。故我们应当严格对该虚假部分进行调查,以最谨慎的态度认定该部分内容的虚假性。在捏造的内容存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之下,应本着“事实存疑时有利于行为人”的原则来处理;若行为人未对特定自然人进行诽谤,而只是针对政府或官员所为的事实发表看法,即使出现语言过激而内容过于夸大的现象,也不应轻易动用诽谤罪来打击。
(4)网络谣言散布的对象不一定针对在公开场合的不特定多数人,还包括特定的少数人。若在私下里向特定的少数人散布谣言,则只要该特定的少数人符合“传播性理论”的情形,也应当认定该行为符合诽谤罪的客观方面[12]。但若只是通过不公开的途径将捏造的信息传播给特定的人,就不应以诽谤罪论处。如2009年10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开通的举报网站就是如此,举报人可以通过署名或匿名举报的方式上传举报信息,但该举报信息不向社会公众公开,若想查询则只能通过输入举报之后生成的查询码。也就是说,只有知道查询码的人才可以得知举报信息,而该查询码一般也只有举报人本人知晓,故不能将故意捏造谣言在该网站上进行举报的情形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公开散布谣言,不能构成诽谤罪。
(二)客体要件
刑法将诽谤罪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一章当中,故诽谤罪侵犯的法益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即名誉权,而非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诽谤行为严重侵犯到社会公共秩序或国家利益时,只是能对该案提起公诉的条件,而不是诽谤罪本身成立的构成要件。在上文所述的“吴保全案”中,东胜区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吴保全在网上发帖举报政府的行为危害了本地区作为全国先进市区的社会发展秩序,给本地区造成恶劣影响,故成立诽谤罪。并且当地警方也以此为原因对吴保全提起拘留、逮捕,检察机关也主动提起公诉,这是不合理的。
(1)诽谤罪是自诉案件,公权力若想要介入,必须在诽谤行为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况之下。诽谤地方政府或政府官员固然有损公务人员及国家机关自身的名誉权,但并不能因其属于国家性质的机关和工作人员,就随意认定其危害了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利益。在处理网络反腐过程中的网络诽谤行为时,应特别谨慎对待提起公诉的条件,不能轻易将案件认定为“严重危害社护秩序和国家利益”而由检察机关主动提起公诉,这样容易引起民众对国家机关公权私用的质疑,并严重侵害公民的言论自由从而不敢轻易发表言论引起“寒蝉效应”,更会严重挫伤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一般说来,若以国家领导人为网络诽谤对象,可以认定其诽谤行为严重危害到国家利益而作为公诉案件来处理[13]。但“对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但书的范围,应当作严格解释,将诽谤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情形排除在外”[14]。
(2)即使对诽谤罪提起公诉也应当以行为符合诽谤罪的成立要件为前提,然而在此案中,吴保全的行为并没有侵犯特定公民的名誉权,司法机关误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作为诽谤罪的客体,不符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就更谈不上主动对其拘留、逮捕和提起公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在网络上检举揭发国家工作人员腐败行为有失真实时,很容易被司法机关错误认定为严重侵犯国家利益而予以诽谤罪处理,这是完全混淆了诽谤罪的成立要件与对其提起公诉条件的表现。
(三)主观方面
网络谣言的制造者往往出于侵犯被害人名誉权的故意,在明知自己的诽谤行为会造成他人名誉权受损的情况下,仍然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故意捏造与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此时行为人所持的是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主观恶性较强。犯罪客观方面具有犯罪故意的规制机能,故意犯的主观方面必须认识到客观方面的所有要素(客观的超过要素除外)。故民众在网络上举报腐败现象时,在有关部门公布调查结果前,公众很难明辨信息的真伪,难免会出现举报内容不实的客观现象,这样就导致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实。但是只要该虚假内容不是行为人出于明知的故意所追求发生的,就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过失犯不能成立网络诽谤犯罪。
除此之外,间接故意也可以成为网络诽谤的主观方面。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行为人往往并未百分百把握自己传播的信息到底真伪如何,是否会给他人的名誉权造成损害,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放任的心理态度,也应当为刑法所规制。但这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弱,并且普通网民在网络平台上发表反腐言论时,对某条信息需要检验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所负担的注意义务程度也相对较小,我们不能苛求一个普通公民能用规范的眼光检索信息的真伪,故在网络反腐过程中若出现反腐言论与事实不符时,应慎重对行为人主观方面进行认定以免打击范围过宽。
(四)主体要件
(1)单纯跟帖、转载、回复评论者主体的认定。近年来,因在网络上转载、跟帖回复评论而以诽谤罪受到刑事强制措施和刑法处罚的人不在少数,如“严小玲轮奸致死案”中福州三网民因转帖内容涉及诽谤罪而获刑、彭洪转发打黑漫画被劳教两年、孟祥存转发检举腐败的内容而被法院认定为诽谤罪,都是由于网络信息的受众转发原始的诽谤信息而被认定为涉嫌诽谤。笔者认为,在网络反腐的背景下,通常转载、回复者不应轻易认定为网络诽谤的犯罪主体。
联系上文的“危害行为”来说,当回复者、转发者明知是虚假的、有损他人名誉权的信息却仍然给予肯定甚至宣扬时,通常是在他人观点的基础之上加以自我评判,一方面包含了评论者基于自我评判而对虚假事实产生的认同,另一方面可能掺加了评论者在原观点之外捏造出的虚假事实。评论与一般谣言相异的地方在于评论是依附其他谣言进行表达的,缺乏制造虚假信息的主动性和本源性,因而对被评论言论的真伪不负有审慎检验的义务,若增加公民过多的“检阅”任务,必然会限制公民监督言论的表达。同时,单纯评论比主动捏造并散布谣言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应受惩罚性都要小,并且评论是言论自由权的应有之义和必然延伸,因而刑法对评论行为应当持有更加宽容的态度而不应当随意介入。所以,单纯转载者即便附加了自己的评论、看法,只要该行为没有捏造新的虚假信息就不能以犯罪论处。但是在跟帖回复的过程中,行为人若故意虚构新的事实并加以散布,其行为本身已经超出刑法所可以容许的风险范畴,则应当为刑法所规制。
(2)网络服务提供者主体的认定。这主要是涉及网络谣言犯罪的不作为犯,笔者认为,网络谣言犯罪可以以不作为的形式来实施。这里的不作为犯一般是对网络谣言的发布及扩散负有一定监督管理义务的个人或单位,一般来说主要是指网络服务的提供者、管理者和网络平台的负责人。因为若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不负责任,特别是在网络反腐的过程当中,明知是虚假信息而出于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放任诽谤结果继续发生,则会导致网络谣言进一步扩散,给被举报人的名誉权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故可以追究相关不作为的个人和单位的刑事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虽然对于其所管理的网络空间具有监督言行的义务,但并不是说一旦行为人将诽谤信息在网上散布,网络平台负责人没有及时发现并处理就构成犯罪,而是若被害人已经对网站负责人提出申诉,并提供了初步的证据足以证实该谣言的虚假性,而网站负责人明知不删除谣言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继续散布从而产生更为恶劣的影响,但仍然不予处理,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这时才可能动用刑罚权予以制裁。
四、结语
在网络反腐的进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守宪法至上的原则,最大化地保障公民的宪法监督权和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实现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另一方面,举报人在表达言论之时仍应当坚守权利的边界,对举报人恶意诽谤被举报人的行为应给予严厉否定。需要注意的是,刑罚是“最后的手段”,动用刑罚一定要慎之又慎。当权利发生冲突时,刑法不应轻易介入。在网络反腐的过程中,将举报人的“诽官”行为入罪,应坚守犯罪成立条件的法律底线,对网络诽谤的构成要件认定应保持谦抑的态度,以保证在合理限制刑法处罚范围的同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出现“寒蝉效应”,在不当表达网络反腐言论与侵犯他人名誉权之间留下缓冲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刘细良,黄胜波. 微博反腐:双刃剑效应与路径选择[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8(1):139-140.
[2]苏力.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92.
[3]于志刚. 表达自由权与名誉权需平衡[EB/OL].(2011-12-22)[2015-08-07].http://www.chinalawedu.com/new/21605a23310aa2011/20111222qinlu17153.shtml.
[4]齐嘉霖.政府与民众关系视角下我国公共利益界定的困境探析[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15(3): 262.
[5]张明楷. 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4-125.
[6]马克昌.刑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7]刘宪权.刑法学(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574.
[8]张明楷.单一行为与复数行为的区分[J].人民检察,2011, 56(1): 7.
[9]李颖.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探析[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14(3) : 268.
[10] 唐煜枫.刑法中言论的行为性辨析——以言论自由的界限为视角[J].法学评论,2006, 27(3): 31.
[11] 吉米·边沁.立法理论[M].李贵方,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180.
[12] 韩玉胜,胡杰. 诽谤罪中散布行为的界定[J].人民检察,2014, 59(5):9.
[13] 曲新久. 惩治网络诽谤的三个刑法问题[J].人民检察,2013, 58(9): 9.
[14] 赵秉志, 彭新林.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范围如何确定[J]. 法学评论, 2009, 30(5):130.
[责任编辑位雪燕]
The Game of Free Speech and Reputation Protection: Reaffirming Crime of
Defa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Anti-corruption
XING Jiang, HU Anqi
(SchoolofLaw,AnhuiUniversity,Hefei230601,Anhui,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anti-corruption on the Internet, citizens’free speech, supervisory right of constitution and informer’s reputation are important rights protected by law. When they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in order to ensure citizens’ right of free speech and supervision, and their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and social affair management, Criminal Law should keep modest to fight against defaming officials on the network. In line with this philosophy, we should give careful thought to standards of internet defa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anti-corruption, not easily reduce the threshold of defamation and expand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Criminal Law. In addition, elements of internet defamation should be carefully identified to fully and rationally fight against the crime of internet defamation and ensure citizens’ basic rights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network anti-corruption; internet defamation; crime of defamation; elements of crime; modest and restraining principle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79(2015)04-0402-06
作者简介:行江(1977—),男,陕西合阳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