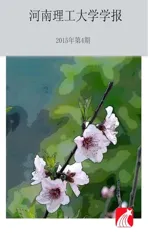论《一点慈悲》对美国例外论神话的质疑
2015-03-17常剑若
常剑若
(河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论《一点慈悲》对美国例外论神话的质疑
常剑若
(河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E-mail:changjianruo@hpu.edu.cn
摘要:托妮·莫里森的近作《一点慈悲》回顾了美利坚民族起源,再现了美利坚民族萌芽阶段发生在蛮荒的北美大陆的宗教、文化冲突与种族、阶级隔阂。小说通过讲述来自不同种族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物经历的生存困境、精神困顿与挣扎,对基于二元分离原则的例外论神话在美国文化中的潜在逻辑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指出了这一原则的荒谬与危害。《一点慈悲》对美国例外论神话的质疑和解构对于来自不同种族与文化群体的人们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和谐共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一点慈悲》;美国例外论;二元分离
一、序言
美国非裔女作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取材于非裔美国人生活,“再现了本族群个人和群体的奋争以及主体身份建构的艰辛与诉求”[1]212。其作品蕴含的对于历史灾难的批判,对于宽容和理解、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于族群和谐、国族和谐乃至世界和谐的思考,使其“具有超越了种族范畴的普遍意义”[1]216。她的第九部小说《一点慈悲》(AMercy)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并被《纽约时报书评》列为“2008年度十大最佳图书”之一。中外论者对这部小说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进行了多方位解读,认为这部小说“诗意地再现了一个处于原生状态、充满纷争的殖民地世界”,是莫里森“对奴役本质和自由的思考”[2]46和“揭露蓄奴制之罪恶以及作为非裔美国人之艰辛的崇高而又必需的课题之一”[3]2,“从超越种族的视角彰显了她对社会、历史和人心的深刻洞察”[4]35。笔者在研读这部作品时发现,《一点慈悲》一方面延续了莫里森对美国非裔民族命运的关怀,再现了美利坚民族萌芽阶段发生在北美蛮荒大陆的宗教文化冲突和种族阶级隔阂,同时对基于“上帝的选民”与“弃民”之二元分离原则的例外论神话在美国文化中的潜在逻辑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故而本文拟从小说对美国例外论的视角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以进一步挖掘莫里森小说蕴含的深邃思想及深切的人文关怀。
二、例外论神话在美国的认同与质疑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都具有与众不同的例外性,例外论在美国却融入了尤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 又译作“美国卓异论”,意指美利坚合众国因其独一无二之地缘特征、国家起源、文教背景、历史进展、政治经济体系与宗教体制,和其他国家相比有“质的不同”(qualitatively different)[5]18。例外论在美国白人文化中具有深刻的宗教和历史根源。从第一批清教徒踏上前往北美新大陆的征程到美国独立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美国牢固树立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历史名人把这个国度比作“山巅(闪耀)之城”、“自由帝国”和“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上帝拣选的民族”、“救世国家”,例外论也成为美国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潜在现代理论基础之一。
然而在今天生态危机加剧、全球反恐、世界多元化、多极化的历史语境下,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地位受到其他崛起大国的挑战而逐渐式微;其国内外出现了众多问题,美国人引以为荣的例外论神话也受到一批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的质疑。“水门事件”后Bell宣称:“不再有天定命运或者使命。我们也没有对腐败权利的免疫力。我们并不例外。”[6]197Lipset把例外论的影响比作“一把双刃剑”[4]。更有学者认为鉴于美国充满血腥的西进与南进扩张史,美国例外论毫无神圣可言,它不过是美国白人在历史上制造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的“胜利文化背后的暴力潜规则”[7]38;它导致美国不遵从国际道德和法律准则制约,为自己开出一系列“自我豁免清单”[8]53。
美国当代小说家也对美国例外论这一意识形态对其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其中托马斯·品钦的小说《梅森与迪克逊》围绕着著名的梅森——杰克逊线的划定,“关注新世界确立的基本原则,矛头指向美国例外论这一美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伦理底线,揭示社会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9]65。而在小说《一点慈悲》中,莫里森从非裔美国作家的视角,通过讲述北美殖民地早期一群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背景和社会阶层的人们各自的生存困境、精神困顿与挣扎,追溯了美利坚民族萌芽阶段、蓄奴制发生之前奴役的根源,同时揭示了美国例外论“上帝选民”与“弃民”之二元分离原则的荒谬与危害。
三、“我是一个另类”:被例外化者之痛与自我救赎
莫里森在一次访谈中说:“种族主义……是一种病症……它分裂欧洲,将其变为异类,使欧洲人成为奴隶主,使他们变得疯狂。”[10]178在《一点慈悲》中,莫里森通过讲述北美殖民地早期来自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的人物的人生际遇,试图揭示这一病症的根源:基于新大陆与旧世界、欧洲白人殖民者与土著民、白人与有色人种、奴隶主与奴隶、“上帝选民”与“弃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分离原则之上的美国例外论,同时再现了例外论所隔离的双方各自经历的精神困顿与挣扎。
小说主人公弗洛伦斯是生活在北美蛮荒大陆的年轻黑人女奴,一生充满了“被例外化者”遭受的痛苦与坎坷。幼时她并未意识到作为黑人女奴的、被排除在上帝救赎之外的悲惨身份,充满了对爱与被爱的渴望。不谙世事的她“生就一双奴隶的手,却长着一双葡萄牙贵妇的脚”,因为“始终都无法忍受打赤脚”,“总是在乞求一双鞋子”[11] 2,充满了对被选择、认可的希冀和爱与被爱的渴望。然而这一愿望却被母亲认为是堕落的、危险的,因为她发现了白人奴隶主望向女儿日渐膨起的胸脯的贪婪目光。八岁那年,母亲为了使女儿免受自己曾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痛苦,忍痛请求主人的债主雅克布把女儿带走抵债,使她初尝了被抛弃的痛苦。后来她被患了水痘的女主人差往铁匠处求助,途中在白人寡妇伊玲家里借宿,次日却碰到社区一群上门来“预审”其女儿简的白人基督徒。为了霸占伊玲家的牧场,他们谣传天生一只眼睛斜视的简是有人声称看到过的“黑魔鬼”。双方争执不下时,弗洛伦斯走进房间。她迥异的肤色和长相令他们震惊骇怪,使她成为又一个被冷酷审判的对象。他们认为被吓哭的小女孩的哭声预示 “黑魔鬼就在我们当中”,而弗洛伦斯就是“黑魔鬼的奴仆”[11]111。一些女人强迫她脱光衣服,像审视一头怪兽一样检查她的身体,搜索她不属于人类的证据。在弗洛伦斯看来,那些盯着她身子看的眼神“不是憎恨,不是恐惧……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认可。猪仔从食槽中抬起头看我时,都带着更多的认同”,那些眼神剥夺了她的人类属性,使她怀疑“我是一个另类”[10]111,几乎粉碎了她支离破碎的自我。
女奴莉娜是被例外化的土著人代表。幼年时瘟疫吞噬了整个村庄,她被长老会收留。但是长老会的慈悲是有条件的:他们称莉娜家族的毁灭是“上帝不悦的第一个标志”,是“对懒散且不敬神的人的惩罚”,所以莉娜“只得承认自己是不信教的野蛮人,听凭自己被那些大人物净化”[11]47。然而,她根深蒂固的本族文化信仰和生活习惯使长老会认为她野性难驯、终难教化,不久再次抛弃了她。
经过深思不难发现,弗洛伦斯和莉娜的痛苦根源正是基于“上帝选民”与“弃民”之二元分离逻辑的宗教和文化例外论。例外论使基督徒变得狭隘多疑、冷酷无情,“在成为上帝的选民和救世这一人类的普遍天性的问题上义无反顾地背离了自己的弟兄”[11]33。如小说中丽贝卡所言,“她们(浸礼会教徒)对上帝喜好的定义甚至比她的父母更窄,”认为“除了他们自己,以及那些赞同他们,与他们同属一类的人之外,就再没有人得到(上帝的)救赎”[11]32。再洗礼派教徒则认为“罪分等级,民族有优劣之分。例如,土著人和非洲人可以获得宽恕,但不能进入天堂——一个他们熟悉得如自家花园的天堂”[11]98。同时,例外论深深毒害了被例外化者的灵魂,迫使其遵从例外论的“二元分离”逻辑,认同“上帝弃民”身份,最终失去构建完整自我的机会和能力。
所幸并非所有被例外化者都屈从自己“上帝弃民”之命运。他们中的勇者通过各种方式与之抗衡,使自己强大,构建独立自我,成为“披着驴皮的狮子”,即“比自由人还自由的奴隶”[11]160。弗洛伦斯是一个从奴役到解放的典型。被母亲的抛弃重创后她在与自由黑人铁匠的爱情滋润下重构破碎的自我,虽然因嫉妒误伤了铁匠领养的小男孩而遭受铁匠的选择性拒绝,却在伤痛之后勇敢地站起来,最终摆脱了爱情、肤色与例外论的多重奴役,在书写对爱人、对世界的自白书中自省自悟,成功构建了独立的自我。莉娜是“被例外化者”浴火重生的另一个典范。为抗衡失去家人、又被当作异教徒抛弃的无比孤独与伤痛,她创造性地把母亲生前传给她的民族信仰和习俗的碎片与从基督徒那里学来的知识相结合,“回忆或者创造出蕴含于事物当中的含义”,“找到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方式”,她通过“与鸟儿交谈……给奶牛唱歌,向落雨张开嘴巴”自我疗伤,通过“把敢于回忆的内容都分类贮存,而把其余的都清除掉”[11]48重塑身心,最终摆脱了充满灾难与伤痛的过往,全身心地融入农场劳动。她坚韧自强,不亢不卑,固守着自己的信仰和道德底线,“她的自我创造已臻于完美”[11]51。这些被例外化者的抗争与自我救赎既成功颠覆了例外论神话,同时给其他被形形色色的例外论所隔离的人们以深刻启示,激励他们自尊、自爱、自强,构建完整自我,为他们从容自信、以平等身份融入主流社会提供了借鉴意义。
四、“披着狮子皮的驴”:例外论者之殇与自我毁灭
在《一点慈悲》中,白人农场主夫妇雅克布与丽贝卡夫妇可以被看作美利坚民族萌芽阶段例外论神话的创造者和持有者。他们被刻画成洋溢着丰富、淳厚人性色彩的美国版亚当与夏娃形象,同时兼具美国白人推崇并引以为荣的拓荒者精神。雅克布热爱自然,孤儿出身使他深谙被排斥、被抛弃的痛苦,因而对孤儿和无家可归者充满悲天悯人之情。更重要的是,他从一个落魄的孤儿,依靠一点运气(一位从未谋面的叔父留给他的120英亩休闲地),经过努力耕种与自我奋斗,崛起成为集强烈的独立精神、鲜明的道德原则和事业成功于一身的农场主。他的创业史与悲天悯人之心使他成为未来美国主流文化奉为经典的“美国梦”的完美化身和理想化的美利坚民族自我形象的代表。他的妻子丽贝卡则是深具拓荒者精神与美德的女性代表。她“体态丰盈,容貌秀丽,吃苦耐劳”,“不属于任何教会,有文化但不骄傲、独立又有教养”[11]20。她厌恶发生在家乡的、打着上帝的虔诚信徒旗号实施的、对于宗教异端、异派的残忍行径,很高兴作为“邮购新娘”离开欧洲旧世界的腐朽,来到充满冒险与刺激的新大陆这一亟待开发的处女地。她对丈夫关爱有加,“在一片对她而言完全陌生的土地上热情洋溢又充满创新地干着家常杂务,快活得像一只蓝知更鸟”[11]20。她和来自不同种族与宗教文化背景的女奴莉娜、弗洛伦斯和“悲哀”和谐共处,共同劳作,带领她们与农场白人契约工一起,帮丈夫建立了一个多种族杂居的伊甸园般的农场。
然而,雅克布夫妇虽然是“美国梦”的完美化身和缔造美国例外论的中坚力量,自身却并未远离例外论的排挤与伤害,甚至深陷例外论的悖论怪圈而不可自拔,走上自我毁灭之途。雅克布是一个具有典型两面性的美国例外论者。他一方面厌恶当地上层社会天主教徒的“放荡、虚浮与狡猾”[11]14,自诩不必牺牲自己的道德原则,即“血肉之躯不是他的商品”[11]22,依靠自己的辛勤努力也能够积累大地主德·奥尔特加所持有的财富和地位;同时又对被排除在上流社会之外耿耿于怀,对被他深深鄙视的德·奥尔特加的华丽住宅羡慕不已。二人的会见使他厌倦了小农场主的闭塞和一成不变,虚荣心和对财富积累的欲望使他最终突破了自己设定的道德底线,找到了自欺欺人的借口:“在朱伯里奥庄园与黑奴的亲密无间和远在巴巴多斯的劳动力之间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差异”[11]35,心安理得地参与到蔗糖和朗姆酒生意及黑奴买卖中而免受良心的谴责。于是,他从一个集强烈的独立精神、自食其力、具有良知和慈悲之心的农场主蜕变成和被他鄙视的大地主一样的物质的奴隶,一个持有双重标准、充满悖论的美国例外论缔造者和践行者。他疯狂经商赚钱,狂热地投入到巨宅建设中,最终却耗尽心力,死在新宅豪华厅堂的地板上,只留灵魂在那里游荡。丽贝卡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她的吃苦耐劳、自力更生、与人为善等美德并未得到教区再洗礼派教徒的认可。他们固执地认为自己的信仰更合上帝心意,而其他人都不配得到上帝救赎。他们允许丽贝卡到教堂礼拜,却拒绝为她的孩子举行洗礼,使得丽贝卡在孩子们接连夭亡时几度精神崩溃。然而丈夫死后,大病初愈的丽贝卡却似乎忘记了宗教例外论曾经给她的伤害。她对农场劳动的激情消失殆尽,频频出入教堂寻求精神安慰,同时把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害加诸与她曾经同舟共济的战友。她再也不和颜悦色地对待在她病危时忠心耿耿守护她的女奴和劳工,甚至谋划要卖掉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请回铁匠救治病危的她的弗洛伦斯。丈夫离世后的丽贝卡变得判若两人,和雅克布一样背离了自己的道德原则。她的苛刻使得农场劳工共同建造的伊甸园般的家摇摇欲坠,随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雅克布夫妇虽然享有人身自由,“内心的枯萎”却使他们为财富、欲望和虚荣所奴役,成了如铁匠所说的“披着狮子皮的驴”[11]160,也即美国例外论的充满矛盾色彩与讽刺意味的另类牺牲品。
五、“质的不同”与“量的卓异”——美国例外论之辩
这部小说另一个充满隐喻色彩、发人深思之处是“孤儿”被遗弃或者放逐之意象的反复出现。弗洛伦斯不知其父是谁,被母亲与铁匠两度抛弃;雅克布幼年被父亲抛弃,饱尝了弃儿的辛酸与窘迫;被他收留的混血女奴“悲哀”是死去的葡萄牙船长的遗孤;丽贝卡是被父母为了“免除养育她的责任”而“出售”给任何一个人的“邮购新娘”[11]75;莉娜全族死于瘟疫,被长老会教派收留后,因为拒绝皈依又被卖给雅克布;用莉娜的话说,“他们是孤儿,一个不差全是”[11]59。
通过反复出现的“孤儿”和“遗弃”之意象,莫里森展示了早期北美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全貌。这些孤儿或者被父母遗弃,或者背弃了本族文化,或者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或者被亲族放逐……他们聚居在北美新大陆,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当地粗粝的生活,成为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在Lipset的美国例外论那里,美利坚民族与其他国族相比,不是“量的卓异” (quantitatively better),而是“质的不同” (qualitatively different)[5]18,然而在莫里森的《一点慈悲》中,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和社会阶层的人们虽然在“量”的方面——肤色之深浅、财产之多寡、地位之高低、文化之先进和相对落后等方面迥然各异,在“质”的方面即人类的天性本质方面却是如此相似:他们都是人,都具有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受到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某种羁绊与奴役:“他们都是孤儿,一个不差地全都是”[11]59,因而都需要“一点慈悲”,“不是上帝赐予的慈悲,而是一个人给予的慈悲”[11]167,是人类在面临共同的生存困境时相互给予彼此的不可多得而弥足珍贵的慈悲、慰藉与温暖。
通过再现美利坚民族萌芽阶段发生在北美蛮荒大陆的宗教文化冲突和阶级种族隔阂,《一点慈悲》追溯了美国例外论诞生的宗教和历史根源,揭露了基于“上帝选民”与“弃民”之二元分离原则的美国例外论的荒谬和危害,同时折射出莫里森对当代美国民族身份和充满悖论的美国例外论这一神话的深入思考。美国真的曾经是、依然是、永远都会是一个“例外”的国家吗?我们不妨听听Roger Cohen的质问吧:“当你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恐怖主义袭击到核武扩散……都需要合作行动的时候,你又能有多么例外呢?”[12]当全人类都面临环境恶化、能源危机、恐怖袭击等生存困境,人与人、国族与国族之间只有求同存异、齐心协力应对人类面对的种种危机,摒弃“自我”与“他者”之二元对立逻辑,关键时刻彼此施以援手,给予彼此“一点慈悲”,人类才能有更好的明天。因而,托妮·莫里森的《一点慈悲》给我们的最终启示是:到了宣告美国例外论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例外论的终结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常剑若. 托尼·莫里森对语言的后现代思考[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2):212-216.
[2]FRYKHOLM AMY. A Mercy [J]. Christian Century,2009, 24 (2): 46-49.
[3]UPDIKE JOHN. Dreamy Wilderness: Unmastered Women in Colonial Virginia [J]. The New Yorker, 2008,11(3):2.
[4]王守仁,吴新云.超越种族——莫里森小说《慈悲》中的“奴役”解析[J].当代外国文学,2009,30(2):35-44.
[5]LIPSET S M.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96:18.
[6]BELL D.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J].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197.
[7]ZINN H.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492 to Present [M]. Harper & Row, 1980:59.
[8]霍华德·齐恩.美国例外主义的神话[J].民主与科学,2005(6):49-53.
[9]王建平.《梅森与迪克逊》:托马斯·品钦对美国例外论的批判[J].国外文学,2009(1):65-71.
[10] MARCUS J. This Side of Paradise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EB/OL].(1998-01-10)[2015-06-07]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tg/feature/-/7651/.
[11] MORRISON T. A Mercy[M]. New York: Knopf, 2008.
[12] COHEN R. Palin’s American Exception [N]. The New York Times, 2008-10-25.
[责任编辑位雪燕]
AMercy: A Query Against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CHANG Jianruo
(SchoolofForeignStudies,HenanPolytechnicUniversity,Jiaozuo454000,Henan,China)
Abstract:Toni Morrison’s novel A Mercy traces the origin of American nation, and depicts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onflicts, racial and class separation that occurred in the barren New World at the embryonic stage of the American nation.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 survival predicament and spiritual dilemma of the people from diverse races, cultur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the novel deconstructs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by demonstrating the absurdity and danger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t principle of pernicious binary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hosen” and “its Others”, which provides significant reference to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ons and cultures in today’s multicultural world.
Key words:Toni Morrison; A Mercy;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binary separation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79(2015)04-0439-05
作者简介:常剑若(1972—),女,河南偃师人,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