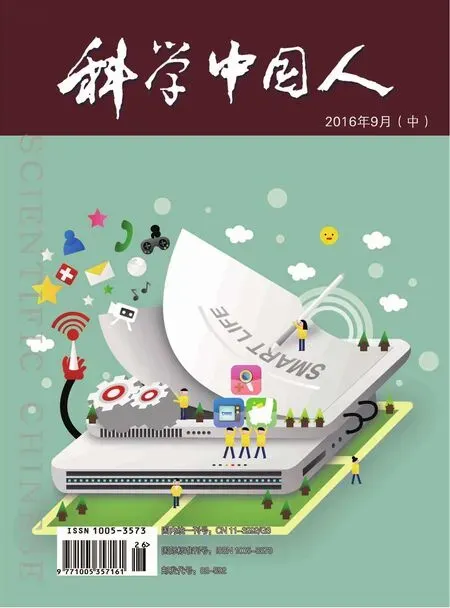刑事辩护制度的价值
2015-03-12刘映江
刘映江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
“刑事辩护制度”是各国所普遍承认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理论和实际意义重大,对各国法治建设影响极深。刑事辩护制度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以尊重人的尊严为思想基础,主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定程序审判而定罪前,应被推定为无罪而得自行或委托他人进行辩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查阅案卷材料、调查取证或进行其他行之有效的方式对控诉人的控诉、证据、程序等提出合理的质疑,以达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之目的。
在我国的法制长河中,“重实体,轻程序”向来是一个习惯。尽管近代以来我们开始引进刑事辩 护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也一直不断地加强有关刑事辩护方面的立法但是依然难遂人意。由于受到阅卷权、会见权等多方限制,辩护人很难进行充分合理之辩护。因此进行刑事辩护制度研究有助于破除传统的“辩护虚无主义”,改变国人的诉讼观念。
1 刑事辩护制度的外在价值
1.1 辩护制度的案件事实查明作用
刑事辩护制度是当今世界通行的一项制度,其中的一项意图就在于通过控辩对抗来发现事真像。案件事实的发现归根结底是认识论上的问题,因为时间具有一维性,所以谁也无法还原历史,只能尽可能去认识它。马克思认为认识事物必须去抓住矛盾的本质,而矛盾分析法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规律。所以不能任意听信一面之词搞片面化、绝对化。而辩护制度的引入使得裁判者能获得控辩双方在各自立场上的陈述。
不仅如此辩护制度还有利于增强证据收集的全面性。现代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同时又规定公诉方既要收集有罪或罪重的证据又要收集无罪或罪轻的证据。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侦查、检察机关会基于自己的控诉立场以及先入为主的心理活动所影响在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上有所怠慢或已收集到而不提供。而被告人所聘请之辩护人则会竭尽所能寻找有利于其当事人的证据。新刑诉扩大了律师的权利,律师可以更大限度的调查取证,补充控诉方有意无意遗漏的证据,使得能在法院呈现的证据数量和种类更加充分、完善。辩护律师亦可依据法律赋予之阅卷、会见权,从有关案件材料中和当事人处了解情况。如若发现疑点,例如从某些蛛丝马迹推知公诉方未提供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时,便可帮助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要求公诉机关提供证据,从而有利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当然此案件事实应为法院于庭审中所认定之事实,而不应为人所推测或臆断之事实。
1.2 对正确判决的作用
法院的多数判决为法官独立作出,缺乏公开性、透明性。大多数当事人又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无法辨别法院判决的合理性。辩护制度的引入使得律师这类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能够充当辩护人对整个诉讼过程在实体上和程序上提出质疑。社会大众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案件情况,这样社会就能够更好的监督司法,达到抑制法官的乱作为。法官在作出的判决时就不得不在理性的基础上综合全面的考虑案件情况慎重的作出判决,当作出判决存在缺陷时,辩护人能够帮助被告人申请上诉获要求重审。使案件结果经过反复推敲。最终获得最能为人所接受的结果。
再者如前文所言刑事辩护制度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而判决结果的作出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性怀疑。当辩护制度使得事实清楚时,所作出的判决的正确性便得到了提升。因此辩护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努力就可以充分的促进判决的正确作出。
2 刑事辩护制度的内在价值
2.1 对控辩平等的保障作用
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具有权力的天性——扩张性。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作为公诉方的检察机关难免会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者由于双方力量以及法律认知方面的对比严重失衡。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劣势,其人权处于一种被侵犯的态势不利于维护其合法权益。为保障司法公正,就必须首先保证控辩平等,使被告人不受制于公诉机关之权势,能够并且敢于据理力争。然而天然的差距却又使得被告人无法充分行使权利,造成不平等。这时我们就需要介入第三方力量,来重新平衡二者之间的天平。此时,辩护人的介入便很好的充当了该平衡者,帮助被告人为有关诉讼行为,使得控辩关系不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固定的公平的“三角形”里。
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就是使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相互对抗,法官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裁判。从而使裁判结果更能体现各方之意志。辩护制度的平等性就在于控辩力量的平等和证明机会的平等。被告人如果没有具有专业知识的律师提供帮助便无法与控诉方在诉讼地位上实现实质的平等。我们所倡导的之人人平等便会成为“空头支票”。因此国家必须保障被告人能有力的行使辩护权自行辩护或委托律师代为辩护,不仅如此在被告人因经济原因而无力聘请律师时,国家还应为其解决辩护人问题。因为辩护人的出现平衡了控辩之间的实力差距,所以辩护制度有保障控辩平等之功能。
2.2 对诉讼民主的维护作用
现代诉讼理论认为刑事诉讼的中心应是被告人,被告人应享有进行诉讼的权利或为诉讼行为的自由。但当刑事诉讼不允许被告人为辩护或要求其自证其罪时,被告人就会陷入有理无处诉的境地。久而久之,一种压抑引起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心态持续发酵。被告人会走向“爆发”或“灭亡”的极端。“或破罐破摔或沉默寡言”而不是积极地参与到诉讼中来。反之当被告人被赋予沉默权和辩护权时,他们可以畅所欲言的为自己辩护时,便会积极地参与进来,通过自身与辩护人的共同努力使自己的意志尽可能多的反应到诉讼中。让尽量多的意志体现出来而这就是民主。唯有公平有效辩护制度才能保障被指控人的诉讼权利,鼓励他积极进行诉讼。
此外,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程序。应体现“看的见的公正”这一特点。在对行使“国家权利”的指控人和为维护“公民权利”的被指控方的立场上应当然的体现其作为程序正义的核心——“保护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体现在辩护制度中就是“控、审分离”和“控、辩对抗”,使国家权利内部相互制衡和权利制约权力。艾伦·德肖微茨教授层板指出“认真负责,积极热心的辩护律师是自由的最后堡垒——是抵抗气势汹汹的政府欺负她的子民的最后防线。他们的任务就是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挑战,使掌权者在对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作出行动前三思而行,考虑可能引起的后果”。辩护制度的建立就是要从制度上使每一个被指控者对公诉机关的违反辩护制度的行径提出质疑,社会对公诉机关的进行监督于法有据。要求指控者改正自己的不当行为或向裁判者表达指控者的不当行为以为裁判依据。而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制约是民主价值的重要体现。
3 刑事辩护制度的效益价值
3.1 能有效提高司法效率
诉讼效率的提高即以更少的诉讼投入换取更高的诉讼回报。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等于非正义”。当佘祥林拿着无罪判决沉冤得雪时,可知他已付出了十余载的青春。陈朴生教授在其书《刑事经济学》中写道“刑事诉讼之机能在于维护公共福祉,保障基本人权,不计程序之繁琐,进行之迟缓,亦属于个人无益,与国家有损。”可见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性。
就刑事诉讼而言,辩护制度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使得案件的判决结果做到“事实清楚”,于证据方面,辩护制度又可增强证据收集的全面性和充分性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当事实更为清楚,证据更为充分之时,判决的正确性会大大提高。且当被指控人充分行使辩护权,积极参与到诉讼之中时,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会大大增强。如此一来,可以大大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这样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有效成果会大大提高。诉讼效率也就因此提高了。
3.2 司法成本的节约
不少人认为,引入刑事辩护制度会使诉讼过程变长,诉讼过程会更为复杂,由此产生的诉讼成本也会更多。其实不然,辩护制度可以从三个方面降低诉讼成本。
刑事诉讼包含了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而每一过程都需要国家和当事人为大量准备,由此便会花费国家和当事人大量的物力财力。当刑事犯罪发生后,国家为惩罚犯罪往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侦查案件,收集与案件有关的线索,但如果此时犯罪嫌疑人在咨询其律师后了解其行为之性质和争取投案自首之好处,在辩护律师的劝导下,嫌疑人的自首几率会大大增加。如果犯罪嫌疑人成功自首,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在犯罪嫌疑人的帮助下刑事诉讼的侦查成本会大量节约下来,投入到更有益的地方去。
如果刑事诉讼中不介入辩护制度,法院就只能听信控方一面之词,采信控方一面之证,如此势必会造成更多的冤假错案。冤假错案发生后,为维护司法公正,势必要纠正冤假错案。之前为解决此案投入时间金钱不算。法院还需要为被枉判而受有不利益之当事人赔偿因受冤狱所造成之损失。如在2013年重审的“张氏叔侄案”,杭州中院不得不为张辉张高平两叔侄赔偿损失二百余万元。当司法机关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无辜之人身上时就会贻误破案时机,而真正的凶手就会逍遥法外继续威胁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于因错误审判而造成的错误执行,要回复其原有状态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如“张氏叔侄”“佘祥林”者尚可为些许补救,而如“聂树斌”案者,则只能给社会留下悔恨与悲伤。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不管怎样,于受害者的亲属或于社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一次次的冤假错案上演,势必会对国家和当事人造成巨大的损失。于普通公民来说而言,当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含冤而死,当毫不相关的人锒铛入狱。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会严重影响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多数人会采取冷漠的态度行事,致使社会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国家而言,持续的冤假错案产生会使司法公信力大大受损。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存在的前提,当司法公信力丧失时,国家管理社会所赖以依存的法律将会失去其作用。国家也会因此而不稳定。当刑事辩护制度能够保证裁判做出的正确性时。司法活动不会因走错路而徒添成本,司法成本得以被节约。司法权威会大大得到维护,使得法制思想蔚然成风社会安更加定结。
4 结语
一般来说公正的辩护程序会产生公正的辩护结果,公正的辩护结果需要公正的辩护程序,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有时候公正的辩护程序不必然产生公正的结果,公正的结果也可以通过不公正的程序来实现。如果过分的强调控辩平等,真正有罪之人就有可能会利用辩护人来逃避法律的追究,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刑事诉讼的效率,不给予被告人充足的时间聘请辩护人、准备辩护、调查取证等就有可能容易造成司法迫害,不仅不利于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现代法理学主张的“以权力为本位思想”背道而驰,还不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
匈牙利学者阿尔培德·欧德曾说“在我们当今的时代里,几乎所有刑事司法程序都有两个目的:一是发现一种实施迅速、成功和简便的新方式、新途径,换言之,是刑事诉讼活动更有效率;二是确保刑事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这与公正的要求密切相联。”笔者认为,要协调处理他们的关系,应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基础上追求实体正义和诉讼效率之提高,以内在、外在、效益为序,追求价值之实现。平等的机制是人权实现的基础,设立辩护制度的目的就在于实现实体正义,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我们应当允许任何人发言,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