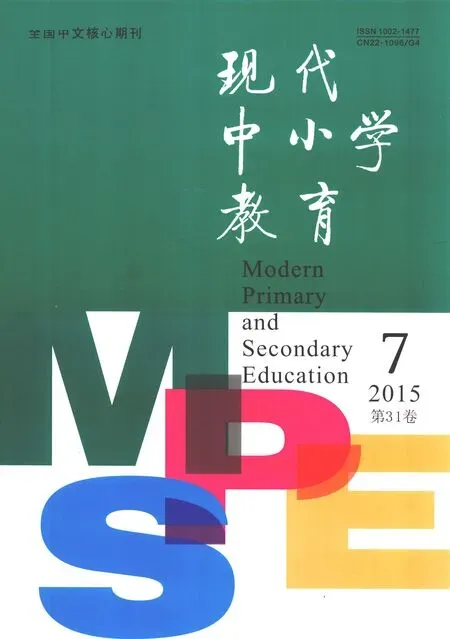后结构主义视角下我国课程话语的西学东鉴
2015-03-01李晓玉杨道宇
李晓玉 杨道宇
(渤海大学教育学院,辽宁锦州121000)
课程研究
后结构主义视角下我国课程话语的西学东鉴
李晓玉 杨道宇
(渤海大学教育学院,辽宁锦州121000)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后结构主义思潮蔓延于西方思想学界,并与文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融合,对教育课程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展现后结构主义的产生背景、主要特征,揭示其蕴含的课程观念,旨在把握后结构主义课程研究的话语脉络及风格,拓宽我国本土课程话语的研究视域,引发该课程话语对中国本土课程话语的相关思考。
后结构主义;课程;话语权;西学东鉴
后结构主义课程话语是一种以“恰当距离”“文本”“解构”“语境”等为主题,倡导课程流变性和动态建构性,认为教学是对课程文本不断解构的一种西方崭新的话语观念。不同地域孕育着不同意味的课程话语,而课程话语的脉络及观念也会因地域之差而呈现不同的课程效用。结合当下中国课程研究发展现状,借鉴西方后结构主义课程话语,汲取与本国课程话语共通、契合的课程精华。
一、后结构主义课程话语的背景、特征及局限
后结构主义流传至今,对教育的影响日益扩大,其课程话语与后结构主义密切相关,它对教育领域的影响集中在教育的研究方法、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诸多方面,但研究这些问题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后结构主义的前提下进行。
1.后结构主义的产生背景
人类的知识视角或范式不存在一蹴而就的裂转,新旧范式的变迁皆充斥着持续不断的论辩,甚至是流血的科学革命。依库恩所言,崭新的范式不可能是知识的单向堆砌,而是对无法契合特定社会与时代需求的旧知识范式的一种质的革新。“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这一更迭正是这一点的鲜明印证。
(1)从“主体”滑向“结构”。20世纪30—50年代,法国学术界长期由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主体哲学引领着。其中,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存在主义最受瞩目,他一度成为当时法国人心中的膜拜对象。萨特所倡导的“人拥有自由的本质”是其存在主义哲学的一大旨观;他还以现象学方法为基础探讨人在面对空虚、憎恨、恐惧、绝望等情绪时的处境问题[1],这一境遇感的剖析恰恰契合了二战期间流离失所之人的内心感受,激起了阵阵强烈的情感波澜。以此为基点,萨特又进一步对人的尊严与价值予以褒扬,这无疑为饱受残忍战争伤痛、企图寻求解脱出路的人们带来了一剂心灵慰藉。但这种感性胜于理性的主义终究无法回应人们对其自身和世界真理探寻的种种疑问,现实生活的诸多现象和问题皆环卷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而找不到突破的出口。
由此,先验主体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各学科并轨发展的冲击下,因其自身局限性消解其效用而谢幕于法国思想舞台。在接下来的短短十年里,法国学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翻版,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主导的结构主义迅速占领学术高地。其实,结构化思维方式并非列维·斯特劳斯之首创,瑞士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才是运用结构化思想的第一人。这不足为奇,因为任何一种思想都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才能打磨成真正建构完备体系的伟人。索绪尔逝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学生将其在日内瓦大学的授课内容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并于1916年出版。[2]《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思想不断向东传播,率先影响了俄国诗界重要学者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使其在音位学领域有所突破。雅各布森移居美国,于哈佛大学任教期间,又将结构主义思维火种传递给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他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方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通过建构具体逻辑体系来组织世界,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方法的高度共鸣。20世纪60年代,许多富有影响力的学科竞相与结构主义接轨,由此轰轰烈烈地迎来了结构主义的巅峰时代。
(2)从“结构”滑向“解构”。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运用新锐犀利的结构化方法批判四十年代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主体哲学话语、并取而代之的年代。那个年代,结构主义确实对人文社会科学激荡出浩大的波澜,凭借其独有的思维优势,引导人们走出意识形态的偏激。但就在结构主义扮演法国思想界的主角之时,其理论内部的矛盾与不足日益凸显,导致“阵营”内部分裂,同时附带“五月风暴”的推波助澜,一股以“解构”为流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于对结构主义的延续与声讨中应运而生。相对结构主义来说,后结构主义既是一种思维模式,又是一派创造性的哲学风格。该思潮以福柯、德里达等人为代表,严厉批判传统结构主义对固定结构的“执念”,瓦解主体,主张非中心化,重视多元性、动态性、不确定性,提倡真理相对性。[1]由此可见,一个“后”字将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划清了界限,一个“后”字意味着蕴含“主体优先”立场的全部谢幕。
综上,后结构主义就是在以上背景下产生的一种颇具前位性色彩的方法论思潮。
2.后结构主义课程话语的主要特征
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一个学派,抑或是一种思想运动,加之其对多元性的热衷,注定了其跨学科的命运,使其自身包含许多潜藏区别,但其中又包含相关性的分支。教育领域受后结构主义影响深刻,而话语问题是该思潮关注的焦点,其课程话语是将后结构主义要义渗透到课程研究中所形成的话语体系,呈现一种全新的知识话语观。其特征主要有四点:第一,强调课程具有流变性和相对性。课程并非是僵化统一、亘古不变的,学生身心各方面存在差异,课程应以其自身的动态性和建构性不断契合学生的个体差异,以崭新的多元开放取代传统的整齐划一。第二,提出教学是对课程文本的解构和增值。[1]通过拆解和断裂课程文本的核心结构框架,冲散其原有的定势意义,再通过多维度、多向度地解读文本、游戏文本,活跃文本等多元因素,实现文本意义的开放增值。第三,强调解构课程话语背后的权利关系。课程身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其本质承载着当权者的利益。因此,利益的变化必然带动课程话语的动态生成,通过解构其话语背后的权利意涵,把握课程与利益之间的比重,规避课程专家对课程结构稳定性的幻想,鼓励以动态、反思的视角指导并建构课程。第四,重视多元性、差异性。跳出结构僵化束缚,认识异质性课程文化和多元的课程文化价值取向,予以边缘文化应有的地位,以差异离心式的“变色龙”风格颠覆绝对僵化式的“堡垒”格调。
3.后结构主义课程话语的局限性
各国课程话语都是各自课程文化土壤孕育出的产物,受不同风格的政治观念、思维方式、道德伦理的调和,话语的表征方式也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因此,将西方课程话语简单平移到中国课程话语中,势必会造成课程话语重心偏移,影响中西方课程文化的共通感。在借鉴西方后结构主义课程话语的精华之时,也要意识到其与本国课程文化的冲突之处,适时予以话语转换。同时,在接受后结构主义课程话语的颇多启示时,也要明晰其自身的局限性,对其进行合理的扬弃:第一,过分对话语予以重视,解构课程文本,力求将课程、知识、权利等元素排除在客观世界之外,这就导致课程文本会失去国家政治、伦理等所提供的参照作用,且在现实情况下,课程是无法脱离权利、利益等元素而成为一种纯粹文本的,或者说把握课程与权利的绝对平衡是很难的,因为它是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织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第二,强调课程意义的相对性、流变性和暂时性,[3]如若把握不好,则容易片面夸大其性质的相对性,抹杀其确定性,陷入真理的相对主义,从而导致从根本上否定其客观存在;亦如戴格瑙特将“定义”理解为众多线的汇聚,而画线人却既找不到画线的具体位置,对自己到底处于哪条线亦是含混不清,这就容易因尺度把握的不到位而迈向真理的相对主义。第三,后结构主义课程研究揭示了广泛应用的课程研究范式,如“泰勒原理”和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论等理论具有封闭性、确定性,对其进行解构,但该课程话语所提供的对于解构之后的建构方案,缺乏相应的建设性和切实的可行性。
二、后结构主义对我国课程话语的建构启示
1.课程话语权的持有者可随学科类型、教学情境而变化
美国课程论学者古德莱德(J.I.Goodlad)曾将课程按不同阶段分为理想的课程、正式的课程、领悟的课程、操作的课程和经验的课程。[4]从教师角度来看,教师主要能够参与的是领悟的课程和操作的课程两个阶段。领悟的课程是教师对上一阶段正式的课程形成的一种解读,由于教师无法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理想课程和正式课程的决策中去,导致教师经解读所呈现出来的领悟课程与专家定制的理想课程和正式课程会有一定的距离,尽管教师在操作课程中会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学生的差异特点进行调整,但其教学成效还是会与课程专家、教育部门制定的课程初衷有一定的距离。从学生角度来看,自新课改以来,学生最主要能够参与的是操作的课程和经验的课程。操作的课程中,教师会根据学生的学习差异对课程实施的模式和进程做适当调整,学生在课程运行中,较传统课程也能得到一定的课堂话语机会;而经验课程是学生通过亲身经历而积淀下来的学习经历或体验,这个阶段会因学生对课程实际理解的风格差异而有所区别,是被个体个性化了的课程。只有在经验课程当中,学生的课程话语权才得到了最纯粹的发挥。从五阶段课程中师生课程话语的参与程度来看,由课程开发制定到最后的学生课程经历,其参与者很大程度上是固定的、局限的,变动性较小。
后结构主义课程观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变”,人的经验亦瞬时变幻,因此,对于知识,更不可能具有解决一切问题的普适性质,由此不禁引申:持课程话语权的主体,可能适合于一种或多种课程情景,但他不可能在所有情景中都奏效,掌握课程话语权的主体应随课程性质、情境的不同而变化。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人一旦适应了一种结构,主观上就难以适应其他结构了,处于一种抵制改变的状态,教育领域亦是如此。教师已形成了承接上级定制的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习惯,学生亦适应了一个教师、一本教材、一种教法、一次考试、一个答案的固定结构,长此以往,不论教学成效如何,这种结构已形成了一种不言对错的定势。其实,学生和教师作为课程资源的组成部分,二者皆处于课程的流变生成状态之中,对于课程目标定制、课程文本开发、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不应仅局限于课程专家、教育工作者,而应将其权利视情景、视课程性质、视学科类型分享给学生,为学生赋权予能。教育是面向学生的教育,学生的需要是教育最值得思考的元素,只有不断变换、调整课程话语主体,才能将课程建构成一种多维精华凝练的契合性文本。这种状态下的课程话语才能既符合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对人才的需要,又契合学生的渴望,同时也能够超越家长对自己孩子充分发展的期望额度。
2.教学组织形式应转变为师生之间的循环式对话沟通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校教育一直维系着传统“主客鲜明”的课堂关系,显现学生主体性的教学模式常居于表面[5],教师因自身担负着上级规定的教学任务,行为与话语必须以国家意志和社会价值取向为导向,以致有: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常将自己游离于“学生-教学-教材”之外,扮演着忠实的知识传输的角色,实则却是被赋予话语权的制度下的产物,这是所谓的“灌输”型教师;部分教师凭借社会赋予的“合法”教学权,利用其自身学科专业知识把握的优势,将话语权转化为对学生的一种霸权控制,经时间的推移积淀为一种权威运作,这种所谓的说教型教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授着专业性极强的抽象内容,忽视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对出现错误的学生施予过度训诫;部分教师习惯于以提问学生的方式检查教学成效,这种模式直接造成学生一味忙于准备教师提出的问题,提问时间大大占据本属于学生自身主动拓展学习内容的时间,同时也给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负担。这些教师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剥夺着学生的话语权。一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难发现,随着学生日益成长,他们越来越不愿主动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对于异于自己头脑的思想也是得过且过的对待,生活的热情和思考每天都被大量机械的知识所占据,导致幼儿时期自信地站在人前背三字经、百家姓的我们祖国的花朵,现在都“羞涩”得不善言谈了。这一系列的教师与学生话语权的异化现象充分说明我们的教育在话语权的均衡配置上出现了问题。
事实上,课堂是通过师生情感对话交流、话语角色转换逐步推进教学活动的,真正的好课堂应该以后结构主义的动态多元话语模式替换传统的僵化权威“主客”模式,让学生有机会真正言说自己的内心话语,而不是一味地接受教师的知识灌输,导致大量的知识堆砌,严严实实地掩盖住了学生内心的真实声音。教师虽对专业领域知识脉络的把握较学生更为深刻,但学生思维开放敏捷,在许多领域有着个人超群、独到的见解,常常为教师所不及,学生是可以对知识进行细节裁剪与动态修正的,教师应重视并利用学生自身趋于完善的可能性,在课堂上充分鼓励并尊重学生话语权的发挥。这份尊重虽然会释放一定的教师话语权,但收获的是学生由心而发的探索内驱力,内驱力促动学生对教师教学精华和教师指导活动的需求与渴望。教师权力表面上虽弱化了,但权力的弱化换来的是极佳的教学效果,这种效果则反过来增加了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此时的这种影响力并非传统课堂上的那种话语控制力,而是指导学生成长的权威性。这种话语转化是循环往复的,在话语权的“释放—收获”过程中真正僭越了错位陈旧的单一传授制和权威控制式教学关系,真正实现了教师与学生的双主体互动对话,以此来建构并保持一种新型互惠的对话关系,规避控制、强制,建构“互联”式、对话式教育教学关系,通过师生双方情感与知识的相互激荡,实现其共同学习的理想。
3.调整课程话语,适时视情境走近多元化,实现“波位”课程领悟
随着当代众多学科的日益成长与壮大,课程内容选择的专业性剂量日益加码,其话语在选择和组织上也日趋专业化、学术化,课程话语的表述愈加偏向对言语逻辑性和学术深度的把握,导致课程话语顺其惯性滑入艰深晦涩的言语表达范式,新词、怪述不断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和耳膜。从师生层面看,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一线教师和学生在领悟、实施、学习课程之时无法对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话语的本真意味达到透彻、一致的理解,有时甚至和课程专家的编制主旨背道而驰,这无疑为学生在不断完善自身、趋近国家人才培养标准的进程中增设了一系列障碍。但从课程编制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们习惯于在国家权威文献政策中找寻准确而有深度的阐释课程教学规律的专业术语,这种专业术语极富权威学术表现力,满载专家们对课程学术问题的复杂情感交锋和心理境况,经过对每一个术语精确性的推敲与斟酌,课程专家希望能够将其所阐述的课程理念被一线教师完全接受,以此准确地传达给学生。
当课程话语无法在其本真含义上被正确理解并使用时,它就不能够发挥其在课程沟通上的原始工具效用了,而是转变为以话语自身作为其终极目的。[6]鉴于后结构主义倡导的以差异多元替代整体划一、解构“中心”的时代创新理念,超越学术话语的简单平移,对课程话语进行提萃,剥离课程话语晦涩难懂的面纱,将其逐步调整为“亲民”的、通俗易懂的、多元开放的形式,能够直观地、毫无异议地将课程话语的最本质要义呈现出来,一线教师再以该内涵基质为起点,不断对其进行适时、视情境的多元拓展,譬如向水中抛出一颗石子,石子在接触水面的一刹那,水面上会以石子和水的接触点为圆心,向四周荡起圈圈波纹,将此时的圆心比做教师,波纹比做教师对课程要义的多维拓展,这一拓展顺应了学生的学习风格差异,学生在掌握课程基本要义的同时,会在教师施予的不同维度的拓展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波位”。这样,既消解了长期浸润于教学实践的一线教师错意课程理论专家理想目标理念的困扰,又使学生的差异风格得到关照,拉近了课程专家、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的话语距离,规避了“教师难解专家义,学生难懂教师言”的“话语”错位阻塞现象。
总之,后结构主义思潮对思想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动作用,它批判性地继承了结构主义思想,推进整体划一向多元差异转变,促使确定向流变转型。虽然后结构课程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局限,或略带稚气,但其开创性的思想势必对课程研究的纵深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1]李克健.追寻教育研究之道——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方法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41,134-135,174.
[2]赵一凡.结构主义[J].外国文学,2002,(1):3-9.
[3]汪霞.后结构主义课程研究的发展与评价[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3(1):20-24.
[4]李定仁,徐继存.课程论研究二十年(1979—1999)[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5-6.
[5]曾贞.论学生主体性实践中的话语价值[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3(12):29-31.
[6]杨晓奇.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育话语冲突及其融通[J].教育科学,2011,27(3):29-33.
[责任编辑:黄晓娜]
G423.04
A
1002-1477(2015)07-0024-04
10.16165/j.cnki.22-1096/g4.2015.07.006
2014-12-25
辽宁省社科联项目(2014lslktzijy-06)。
李晓玉(1989-),女,辽宁辽阳人,硕士研究生;杨道宇(1978-),男,河南商丘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