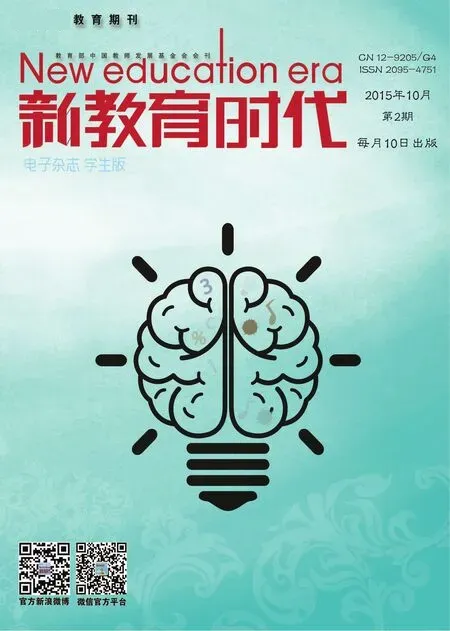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异质性分析
2015-02-28姜其沅
姜其沅
(山东省莱州市委党校 山东莱州 261400)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异质性分析
姜其沅
(山东省莱州市委党校 山东莱州 261400)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发展而成的具有同构异质关系的两种民主形式,两者既存在本质的不同,又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 差异分析
一、发展动力不同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具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为了弥补自由主义理论主导下的选举民主的弊端。西方的竞选民主仅仅关注选票结果,这样便造成一种“多数原则悖论”现象,竞选人过分关注选票的多少,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重视甚至出现被忽略的情况,这就大大降低了民主的质量和实效性。同时,竞选民主强调竞争忽视合作,造成政治冲突不断,政局不稳。最为重要的是,竞选民主将政治权力的授予权赋予了间隔性的政治选举,在选举期间每位选民的个体偏好简单地聚合成集体选择,但当政治选举结束后,人民便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很难再对政治政策产生实质性、持久性的影响,人民没法再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不能对政策的选择产生实际的影响。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兴起的另一原因在于“为了回应西方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多元文化社会潜藏的深刻而持久的道德冲突,以及种族文化团体之间认知资源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等方面的问题。”简而言之也就是应对多元社会、多元价值的冲突。多元社会的出现使社会矛盾更加负责,原先简单地两个阶级的对抗变成了社会多元力量的冲突,原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各种社会力量渴望发声的要求,因而更具包容性的政治结构的产生是社会多元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
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内生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当中的,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理论指导,也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更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的成果。从三三制政权、统一战线、群众路线、政治协商会议等形式,所有的这些协商实践形式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以团结包容为主要特征的三三制政权、统一战线等形式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而建国后的政治协商会议更是在旧政协的失败以及社会各阶级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中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产生的。因而可以说,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是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最大动力。
二、理论来源不同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更多的是古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复兴,在古代雅典城邦民主的实践中就存在着丰富的协商元素,例如古希腊人创立的公民大会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对影响国家政策的议程施加影响,政策的制定以及领导权利的授予都要经过协商讨论的方式来决定,伯里克里曾说:“我们不认为讨论会妨碍行动,相反,我们认为讨论是任何明智行动不可或缺的条件,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尚未对结果进行适当的公开讨论之前就贸然采取行动。”虽然古代雅典民主只是针对具有公民身份的人的民主,但他们的思想中包含了公平、协商的民主思想,是后世的民主建设发展的源泉。
而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来源则更为丰富。首先是我国传统的“和合”思想契合了协商民主的发展要求,符合其要求合作、寻求共识的价值观念。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多党合作思想坚持了合作共赢、协商发展的观点。马恩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有必要与其他团体党派合作,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汲取中国传统的协商合作的文化精华以及马恩的多党合作思想,通过广泛与各民主党派、各革命阶级的广泛合作,构建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建国后的多党合作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更是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合作协商的执政思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共产党这个群体一直保持着活跃的开放性,不论实在革命时期还是执政建设时期,都以宽阔的胸怀吸纳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允许他们提出意见、参与政权建设,这是共产党的先锋队属性决定的。
三、参与主体不同
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主要有公民大会、公民陪审团、市镇会议等,从其发挥作用的范围来看,主要是针对基层协商领域,协商内容通常是非常具体的地方事务,参与主体主要是与地方事务涉及的利益直接相关的地方民众。在这种基层的协商实践中,公民有资格、有途径直接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直接民主形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则不仅仅局限于基层领域,而是在国家层面、政党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基层甚至虚拟的网络空间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实践形式。我国的多党合作以及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形式的典型代表,中国共产党充分借助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平台,通过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各种形式的协商办法,就大政方针、国家领导人选的确定与民主党派进行深刻的协商交流。党际协商亦是我国协商民主重要的实践形式。党际协商顾名思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以及共产党内部的协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的关系,不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这种协商地位上的平等赋予了党际协商的真实性与可能性。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协商更是近年来中央大力倡导和鼓励的,民主集中制与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体制为协商民主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社会层面中的政府机关的行政协商,例如立法听证会、网络问政等形式促进了信息公开、决策优化,为我国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民主质量的提供了保障。最后我国基层形式多样的协商实践形式更像是一颗颗璀璨明星照亮我国民主实践的康庄大道。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包含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既有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以及各界别政协委员的间接协商,也有直接的基层协商,既有不同团体、界别、职业、地域、民族的代表的精英式协商,也有直接以个体身份参与的基层协商。与西方协商民主相比而言,显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广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