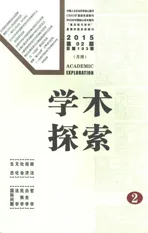向死而乐:丧葬仪式中戏谑的调适功能
——以元谋凉山乡彝族丧葬仪式为个案
2015-02-26侯小纳
侯小纳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向死而乐:丧葬仪式中戏谑的调适功能
——以元谋凉山乡彝族丧葬仪式为个案
侯小纳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丧葬礼仪是人类最后的通过仪式与重要的文化现象。元谋凉山乡彝族的丧葬礼仪过程既表达出对已逝者的安抚与哀悼,同时也表现出生者在丧葬仪式中对待死亡的一种调侃、戏谑、娱乐的态度。这种在丧葬仪式中呈现出来的调侃、戏谑的态度可以填补因亲人逝去而带来的巨大心灵空白。本文试图说明元谋凉山乡彝族在丧礼仪式过程中,通过戏谑、娱乐的方式来调适生与死、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及对待生死的乐观态度。
葬礼;戏谑;调适;凉山乡;彝族
丧葬仪式的举行宣示了个人与此岸世界的最后联系的断裂。在葬礼中,吊唁人群向逝者表达最为沉痛的哀悼,在整个丧葬仪式过程中,弥漫着严肃、悲痛的气氛。但是,作为元谋凉山乡彝族的葬礼仪式过程则表现出一种戏谑、娱乐的成分:吊唁队伍与逝者家属相互夸耀本家的英雄业绩,借此以贬低对方的家支力量,这样的情况看似不合人情常理,但其中又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透露出元谋凉山乡彝族在生与死、自我与他者之间有效的调适能力。
一、丧葬仪式中的喇叭调
在元谋凉山乡彝族当中,喇叭匠(喇叭吹奏者)不属于一种固定的人群,吹奏喇叭也算不上一种固定的职业,喇叭吹奏者甚至会受到本族群内部成员的轻视,但是,他们可以称得上是平日生活中的多才多艺者,在平时生活中与普通人并无二致,只是在有人去世时,受逝者亲属的邀请才吹奏喇叭。在当地彝族族群中,吹喇叭是很被人瞧不起的一项活动,喇叭匠一般都是当地与彝族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他民族人员来担纲。不过,随着观念的变化,现在元谋凉山彝族族群中也有人在丧礼上吹奏喇叭。在人生的各个重要过渡阶段,元谋凉山乡彝族唯有在丧礼仪式中才会延请喇叭匠,并且在该族群中,平时一般不会吹奏喇叭、燃放鞭炮,这与当地汉族有着明显的不同:当地汉族群众婚礼仪式中也吹奏喇叭,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活跃婚庆场面非常好的方式。
在元谋凉山乡彝族族群中,不同年龄的人过世有着不同的丧葬仪式方式,现以老人去世为例证展开论述(属自然死亡,非自然死亡则有不同的丧葬仪式)。丧葬仪式是彝族最为重要、最为盛大的仪式活动之一。一般来讲,人去世后都要选在祖坟旁边安葬,形式则采用火葬。但是,也有另选风水地点的(此处不做展开)。老人去世之后,要安排几个人到亲属朋友所住村子的高山上大声通知某某不在了,并大声询问亲属朋友听到与否,直到有人应答说听见为止(非常忌讳直接到其家中通知)。之后,家人要给死者洗脸、换上新的民族服装,并且要在堂屋正中央搭上一尺多高的平台,按照女左男右侧身睡好,身上盖上新衣服以及羊毛制作的千层披毡,两旁放好凳子,给前来吊唁的亲属朋友做好准备,吊唁而来的亲属大部分为女性。一般来讲,只要前来吊唁的亲属朋友至少都会带上一瓶白酒。女人都会哭丧(男人一般不哭丧),并且一天要哭好几次,直到逝者的遗体被抬上山为止。逝者遗体停放好,相关亲属到齐之后,就要安排人员通知喇叭匠。当老人去世后,逝者家属要请一对喇叭匠,从亲人去世开始,一直吹奏至把遗体抬上山结束为止。主人家请来的喇叭队由去请的亲属来安排并陪同就餐,如安排座位、饮酒吃饭等等。这期间要求不停地吹奏,等到客人(指女婿家及女婿带来的吊唁亲属)的喇叭队到来的时候,无论客人家有几队喇叭,都要吹赢,不能服输。要吹奏出各种调式,吹出对方无法应对或者从没听过的调子,这样主人家才会喜欢。
丧葬仪式过程中,吹喇叭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娱乐性质,它是在哭丧间歇时候给人以稍许的放松,在汉族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在大部分的汉族地区,喇叭匠只是主人家聘请,前来吊唁的人并不会带来喇叭匠)。但是,死者家属与吊唁队伍同时宴请喇叭匠,两队喇叭匠(逝者家属与吊唁人群)以对方不熟悉的音高与曲调来表现自己的“优势”,并以比赛的形式来决定输赢,借此向外界宣示本家的势力,这是元谋凉山乡彝族较为独特的地方。这种在严肃的丧葬仪式场合中表现出来的戏谑、娱乐,打破了人们平日里对死亡的恐惧,把肃穆与欢愉并置在一起。严肃性与娱乐性就像“雅努斯的硬币”是一体两面的,在对逝者离开此岸世界的哀悼中,其实也有对其进入彼岸世界的庆贺和歌颂。这种“对待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双重认识角度,在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存在,有严肃的(就其组织方式和音调气氛而言)祭祀活动同时还有嘲笑和亵渎神灵的诙谐性祭祀活动(‘仪式游戏’)”[1](P6~7)。死者家属与吊唁队伍在喇叭匠吹奏乐调的“竞赛”当中,表达了生者对逝者的安抚与缅怀,他们不强调一味地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一则因为这种悲痛是无济于事的;二则是通过这种带有娱乐形式的“竞赛”,很好地弥合了生死之间的巨大裂缝。“进入国家阶段之后,凯旋仪式几乎对等地既有对胜利者的歌颂,又有对胜利者的戏弄,而丧葬仪式,也是既有对死者的哀悼(歌颂),也有对死者的戏弄。”[1](P7)这种寓褒贬于一身、把生死相等同的做法与看法,是同当下对待生与死、严肃与诙谐的观点磗格不入的,强调一极(生、严肃的一极)而排斥另一极(死、诙谐的一极)是进入国家阶段之后才出现的事情,元谋凉山彝族丧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竞赛”、娱乐成分,可以更好地弥补因丧失亲人产生的心灵缺憾,可以重新调整与周围亲人的社会关系。
二、相互夸耀的出殡队伍
除了在喇叭队伍中出现的“竞赛”场面,在庞大的出殡队伍中同样有夸耀自己、贬损对方以使本家支“脸上有光”的情况出现。老人过世之后,要安排专门的人员来煮饭以招待吊唁者,吊唁亲属人数少则杀羊,多则杀牛,每天如此,一直到女儿家的人到来之后才另作安排。正亲(直系亲属)及儿女到齐后,就要安排两名总管,主要负责叫人、接收吊唁人群所带的白酒(现在有带钱的也一起收管并进行记录)。另外,有带纸烟、毛毯、衣服之类的也一起登记并给交主人家。一般的亲戚朋友只会带一小瓶白酒,关系较近的亲属则带上披毡之类的吊唁品,有的逝者家属一次会收到上百条披毡。吃饭问题都归“厨师”统管(家族中较会做饭的),他们会安排妇女煮饭、收拾碗筷并负责所有人用餐问题,以保证任何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赶到都能够吃上饭。主人家还要安排采购人员买米、买菜,缺什么就买什么。重要的是白布,白布的数量要提前计算好,要求在场人员中所有的晚辈都要戴孝,尤其是随女婿到来的客人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随后就要找一个懂风水的人看好墓地,大部分都选在祖坟旁边,(但也有例外:有的是自己以前就已经看好并且已经倒酒祭拜过的,有的是自己不愿意去的,还有的就是非正常死亡或者没有子嗣传承家支血脉的,这些情况都不能葬至祖坟)出殡日期的选择很有讲究,不能选择对家里人不好的时间,一般是要选择属虎的某天。除较近的亲属外,大部分人一般会在出殡前一天晚上到场。女儿家前来吊唁的亲属,他们要组织少则几十人多至上百人的吊唁队伍,这支吊唁人群要由女婿来组织,因为女儿已经在老人病重或垂危时就已经在老人身边陪护着,伤感未尽不能回家,只能在婆家提前商定组织吊唁队伍的事宜。在出殡前一天上午要杀牛或宰羊隆重款待自己的客人,安排一至两人牵牛走在队伍的前面,然后需要安排几个耍刀人披上披毡,头戴包头,手提大刀——现在都用木刀,口中说着盘古开天辟地如何强大,自己属于什么家支,今天如何威风、辛劳地来参加这次丧葬活动等等。主人家跟随在牛后,也会以同样的耍刀队伍来迎接并引导吊唁人群到逝者遗体旁,然后各自夸耀自己、贬损对方后方才收场。如果逝者家属有好几个女婿,那么送丧场面则会表现出更多的娱乐气氛:这些女婿之间也会互相竞争、夸耀自己的家支力量的强大以及自己的祖先比起其他几个女婿的先祖是怎样的英雄了得,并且女婿们在一起很会“结盟”,即联合其他的几家以排斥另一家,在场的其他吊唁人群就会像看喜剧一样,喝彩鼓劲。这样大闹一场之后,方才收场。这种“各自夸耀自己、贬损对方”方才收场的出殡活动,在表面看来,或许给人一种不尊重逝者的感觉,甚至会产生一种将死亡当儿戏的印象,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丧葬仪式中夸耀本家支的英雄事迹、贬损甚至辱骂对方的做法是一种刻意的贬低化、降格,这种贬低化与降格具有一种再生的积极因素。“贬低化,在这里就意味着世俗化,就是靠拢作为吸纳因素而同时又是生育因素的大地:贬低化同时既是埋葬,又是播种,置于死地,就是为了更好更多地重新生育”。[1](P25~26)
在元谋小凉山彝族的整个丧葬仪式中,彝族丧葬形式过程中的“戏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贬低化”,但这种“贬低化”同样直接的讽刺、挖苦,而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再生。正是在这种对自己的夸耀与对他人的贬低,打破了平时严肃的以社会地位为基础的论资排辈。与此同时,送丧队伍、场面的大小已经成为其家支地位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象征,它成为本家族向外界展示实力的机会,因此,即使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在所不惜,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似乎宣扬了一种浪费的奢靡之风,其实它蕴含着巨大的解构力量:对日常生活中贵生轻死的脱冕与降格。
三、女性的哭丧
在元谋小凉山彝族丧葬仪式过程中,除了要请喇叭队,还要请来很多好的铜枪炮手,他们装好火药(并不填充子弹),每到一个村子就要朝天开上几枪,用意在于表示队伍已经出发,另一方面是昭告半路加入的人员,这样一直走到能看到逝者村子的地方就休息下来,但是要打一阵铜炮枪,其用意是告知逝者家属吊唁队伍已经到达,请其做好准备。此时,主人家也会同样用铜炮枪来响应,表示欢迎或者知道吊唁队伍的到来(现在没有铜炮枪则用鞭炮来替代)。吊唁队伍后面跟随的是穿着民族盛装的妇女,她们大部分都会披上一件披毡,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跟进。女人是要去哭丧的,后面就是庞大的男性队伍。吊唁队伍到主人家门前时,妇女们会逐个进门哭丧,哭丧的内容根据每个人的身份以及与逝者关系亲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表达对逝者的不舍与追思,希望逝者能够在另一世界过得美满。男人们则不会马上进门,一般也不用哭丧,他们要在门外由姑爷找个空地坐下,然后,大舅哥(或小舅子)就会出来迎接妹夫(或姐夫),逝者家属会分别给女婿和牛挂红(以此证明牛是女儿、女婿敬献的),并找几个兄弟(或堂兄弟)端酒给姑爷,由女婿向自己吊唁队伍的所有成员一一敬酒,表示感谢,敬酒的过程中,女婿会带着夸耀的语气,逐一介绍前来吊唁的每一个家支关系及家支势力,以彰显自己的权力关系。逝者家属要很客气礼貌地招待女婿及吊唁人群,否则,吊唁队伍便不会进入主人家门,以此来拖延主人家用餐的时间,这一过程仍然具有很强的娱乐成分。等主客双方相互推让一番之后,吊唁人群才进入主人家,这时院子里要燃放大量的鞭炮,一般要持续一个小时左右,鞭炮燃放过后就是逝者家属与吊唁队伍一起用餐。老人过世后,无论白天晚上都有人在哭(基本上限于女性),但在晚上一般是懂得民族古调的老人按照师徒教授的方式进行讲唱(有的是讲,有的则是唱),有给逝者指明认祖归宗路径的,有吟唱阴阳两界故事的,有讲述神话传说以及古礼的,甚至有胡编乱造的等等。这种老人去世之后在夜晚讲述的神话传说、民谣古礼平时并不会轻易讲述,除了让后辈子孙了解本族群文化历史,其实还是一种调节哀伤氛围的手段,与“喇叭匠”有着相似的功能。元谋凉山彝族丧葬仪式中的哭丧现象,在很多民族的丧葬仪式中亦不同程度地存在,其哭丧内容几乎都是表达对逝者的追思与缅怀,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专业的哭丧人员(他们在丧葬仪式中被雇佣,负责引发吊唁人群的哀悼情绪),在元谋小凉山彝族丧葬仪式中,男性在哭丧队伍中并不占据主体,这可能与此一族群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有关。在老人过世后的头几天,哭丧是每天必需的一项“工作”,即使哭丧者已经没有了悲伤的情绪,还是要维持着这样一种哀痛的感情,甚至以至于使这种吊唁形式成为一种程式。这种长时段哭丧已经超越了吊唁的最初动机(表达哀伤),从更加深刻的意涵方面来说,它不仅仅是表达一种失去亲人的痛苦,同时也展现了错综复杂的家支关系。
在丧葬仪式过程中,表现出“娱乐”的吊唁场面并不是没有出现过,《百夷传》中的傣族丧葬就有记载:“父母亡,不用僧道,祭则用妇人,祝于尸前。诸亲戚邻人,各持酒物于丧家,聚少年百数人,饮酒作乐,歌舞达旦,谓之娱尸。”此种元谋凉山乡彝族丧葬礼仪过程中的“娱尸”行为,在其他民族中的祭祀歌舞中也多有存在。“居住在罗平县的彝族有‘闹丧’的习俗,村人齐集丧家舞龙耍狮,并要戴上孙悟空、猪八戒、大头和尚等面具互相嬉戏打逗,还要由数人挑着酒桶来‘闹酒’,即挑着酒忽左忽右、忽前忽后、摇摇晃晃地在人群中穿行,引来一阵阵欢笑声。丧礼中‘喜’的成分似乎还要多于悲的成分。”[2](P145)可见,虽然丧葬仪式过程是人的整个生命仪式中最为神圣、隆重的礼仪之一,但是,以一种娱乐的形式来表达对逝去亲属的哀思,这是对在世者的抚慰,同时也是对已逝者的祈愿:在他们看来,彼岸世界是一个极乐的福地。这样的对待生死的看法,对于调整因亲属去世而带来的巨大悲痛有很好的补偿作用。
结 语
在元谋小凉山彝族的丧葬仪式过程中,通过吊唁人群与逝者家属相互之间的“竞赛”“夸耀自己”“贬损对方”以及几乎成为程式的“哭丧”,可以看出相对于哀伤、严肃的丧葬仪式中的另一内涵:相对于死亡的新生、相对于痛哭的笑谑与相对于加冕的脱冕。“贬低被骂者,即把他发落到绝对地形学的肉体下部去,发落到生育、生殖器官部位,即肉体墓穴(或肉体地狱)中去,让他归于消灭而再生。”[1](P33~34)无论是在相互的竞赛与夸耀当中,还是在夸张的哭丧过程中,都不含有绝对否定意义上的侮辱与降格,正是在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丧葬仪式应该具有的严肃性的地方,这种元谋小凉山乡彝族丧葬仪式中的笑谑、娱乐性,展现了他们对待死亡的乐观态度,并且帮助我们“摆脱看世界的正统观点,摆脱各种陈规虚礼,摆脱通行的真理,摆脱普通的、习见的、众所公认的观点,使之能以新的方式看世界,感受到一切现存的事物的相对性和出现完全改观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1](P40~41)。
[1]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和少英.逝者的庆典:云南民族丧葬[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3]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M].白春仁,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简·艾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M].刘宗迪,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6]巴莫阿依.彝族祖灵信仰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7]夏之乾.中国少数民族丧葬[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
[8]李玉洁.先秦丧葬制度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9]赵泽洪.魂归人间:普洱地区少数民族丧葬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10]徐吉军.长江流域的丧葬[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1]李如森.汉代丧葬礼俗[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
[12]林富士.礼俗与宗教[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Facing Death Happily:the Function of Adjustment of Banter in Funeral Ceremony——A Case Study of Yi Peop le′s Funeral Ceremony of Liangshan,Yuanmou County
HOU Xiao-na
(School of Humanit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Funeral Ceremony is the final rites of passage and an important cultural phenomenon of human beings.Yi people′s funeral ceremony in Liangshan town,Yuanmou county expresses not only conciliation and mourning for the dead but also the liv ing′s attitude towards death of ridicule,banter and entertainment.This attitude can fill in the huge blank in soul from the rela tives′death.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at the Yi people in Liangshan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and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bymeans of banter and entertainment,which also shows their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 death.
funeral;banter,adjustment;Liangshan town
C955
A
:1006-723X(2015)02-0090-04
〔责任编辑:左安嵩〕
侯小纳,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