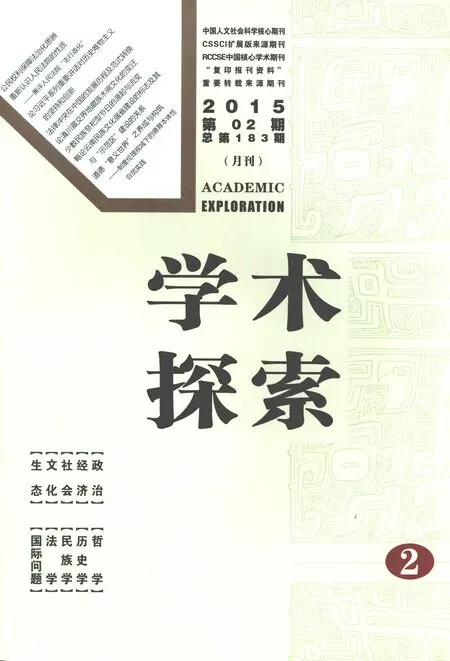少数民族祭祀型节日的源起与流变
2015-02-26何马玉涓
何马玉涓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少数民族祭祀型节日的源起与流变
何马玉涓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祭祀型节日可以被看作少数民族文化的“活态”文本,节日仪式、节日功能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复合、变异,但依然能从行为实践中推演出民族的产生、发展及其生存状态。溯源的目的不仅是寻找节日产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找到那些隐藏在言语行为背后的民族历史与民族精神,这关乎着仪式存在的真正价值。
少数民族;节日源起;流变
节日文化,是民族文化众多子系统之一,是民族和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及表现系统。对节日、祭祀的研究,历来为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民间文艺学所垂青,这正是由它的“文化集约丛”或“文化焦点”的地位决定的。[1]传统节日按照性质差异大致分为祭天(祖)节日、农事祭祀节日、交游节日、集贸节日,随着社会变迁的需要,以上几类节日逐渐综合演化而形成文化内核多重的复合型节日。其中,祭祀型节日的内涵深邃复杂,远古生存的追忆、民众的虔诚与怀疑、无畏地牺牲与功利性的渴望都集合在祭祀型节日当中,并通过神圣时空的复演表现出来。这种神圣化是建立在与生境相匹配的信仰之上,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社会群体相互接触,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内部结构难以继续与仪式解释系统相应和的时候,节日便在一次次复演中产生出新的形式与意义。
一、源起:生存的解释
一年当中由种种传承线路形成的固定或不完全固定的活动时间,开展特定主题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日[2]被定义为节日。“传承路线”“固定或不完全固定”“特定主题”“约定俗成”等语汇背后是一个庞杂系统,建构出神圣与世俗的时空,并受宗教祭祀、农事生产和历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有全民性、集体性和传统性表征的民族节日。
关于节日仪式的研究从一开始便与神话的解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却两者发生时间这一问题,二者早已被视为一个相互交融的体系。当我们谈到民族节日,尤其是祭祀型节日的时候,信仰与仪式便成为最基本的范畴。信仰是观点的表达,而仪式则是一切确定的行为模式[3]。信仰外化为具象的节日仪式,节日仪式存在的根本则是人类内在信仰。自然界是充斥信仰的,自然界的山川河流不仅仅是“自然的”,它们总是洋溢着宗教的价值。[4]世界的一切现象都存在自我的模式,而原始人类最先发现了世界呈现出来的神圣模式,这种神圣模式的产生在于特定时空下人类对其生存的解释。这种生存的解释便是节日仪式产生的根源。
原始人类将世界看成是诸神灵创造的业绩,这种神圣的创造总是固守着它的可被理解的品质,也即是说,它能本能地揭示神圣的众多方面。比如,天空直接地、“自然地”揭示了自己的无限高远,揭示了神性的超验性。
天空高远的、无限的、永恒的和强有力的存在揭示出它的超验、力量和永恒,因此构成原始初民对神圣最直接的感受,由此有了“天神”。这种认识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在西方人类学田野笔记中,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原住民的至上神名大多意为“高的”“向上的”“天空的居住者(主人)”等。这些称呼恰恰反映出原初的哲学观念。
当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相对应的哲学观念也随之改变。人类绝不会永久地守护着某一特定的神灵。正如我们早先已经说过的那样,一块圣石之所以受到崇拜正因为它是神圣的,而不是它是一块石头,正是通过石头存在的模式而表现出的神圣性,揭示了这块石头的真正本质。农业的发现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经济,而且相应地改变了神圣体系,人们看到了更多具体的力量——性行为与生育能力、女性与自然世界。同时,更多更丰富的后世文化逐渐内化到前知识体系当中,此时,神灵出现隐退与涌现,集合各种力量的“天神”逐渐远离人类,取而代之的是各司其职的、被人类所亲近的男女众神形象。当然,此时的“天神”仍然会作为最后的求助对象,但更多的时候,祭祀当中被留有位置的是能有效发挥不同功能的各类神癨。诸如,“天神”沦为逊位神,祖先神、其他力量神癨乃至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涌现到祭祀空间,神话解释系统构成的祭辞也在不断地被改造,试图令节日祭祀具备合理性。
作为人类学百科全书的《金枝》,弗雷泽用鸿篇长卷记录下世界范围内早期人类社群及原始部落大量的风俗、仪式、信仰。作者依托进化学派的观点与方法,阐述了巫术、宗教与科学的起源,明确了“巫术先于宗教”,并进一步推论到,当人类用巫术去解释、控制神秘的自然界力不从心后,又创立了宗教祈求神的仪式(节日),被现实证实无效后,人类才探寻到科学,以此揭示生存世界的奥秘。不难看出,对生存世界、生存本身的解释是原始人类致力的追求,在实践中产生相应的祭祀仪式,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获得重新解读。
祭祀仪式中的实践主体将形式各异的交感巫术与模拟巫术置放于祭祀节日中,与后世文化不断融合,最终形成文化残留与文化变异。将不同区域的傈僳族刀杆节的祭祀仪式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自然崇拜——农事诉求——保护神敬畏成为该节日内涵的演变过程,是线性发展也是多元文化渗透的结果。怒江泸水地区傈僳族刀杆节的祭祀仪式具有明显的原始信仰残留,外化于民众心理上对自然神灵作用的信服。该地区傈僳族尼帕①尼帕,全称为“阿塔德尼帕”,巫师,汉语称为“香通”。们用以“上刀山”的刀杆架由被称为“金柱”和“银柱”的两根木杆以及36把长刀组成。“金柱”,即为公柱,代表阳间;“银柱”,即为母柱,代表阴间。两木平放间隔32厘米,从上到下设三根横木,以中横木为界,至下横木之间表示阳界,至上横木之间表示阴间。刀杆顶用竹片将“金柱”和“银柱”连接起来围成半圆,称其“天门”,并以红布缠绕,半圆中间拴一根铁链,用锁锁住,表示锁“天门”,并配以一个装有36枚币的“红包”。
尼帕们在“上刀杆下火海”之前都必须完成一系列繁复的祭祀仪式,所祭祀神灵众多,且以自然神灵为主,每位神灵各司其职,维护着神圣与世俗世界的秩序。其中,龙神、水神被认为是尼帕“下火海”的保护神,傈僳族认为只要顺利将龙神、水神请来,下火海的时候尼帕便如同置身于水塘之中,不会有烫的感觉。除此之外,尼帕们在上刀山之前,需要一一完成祭山神、请龙神及其他自然神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香、纸钱、以公鸡和公猪为主的牺牲、酒为祭祀的必需品,而尼帕们则伴着锣鼓节奏完成鞠躬、磕头,进入癫狂式的忘我状态。此时的音乐、癫狂动作与祭辞成了仪式实践,以此表达着请神、祈神的目的,彰显出“祭祀”的本质。
“我请我的老祖宗和保护神,我的保护神一般是大蟒蛇、青蛇,还有天上飞的老雕、老鹰,把它们请下来保护我们上刀山。那两根刀杆架平常看是木头、钢管,其实(代表)是金柱和银柱,一般大蟒蛇和青蛇就绕在刀杆上。上刀杆前都要用双手用力摇晃刀杆,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摇晃驱逐作怪的飞禽,目的之二是将刀杆两边的蟒蛇摇清醒,使它们能专心一致地为我们保驾。”
这是怒江泸水刀杆掌师对上刀杆之前仪式行为的解释,映射出其心理对神秘力量的诚服与推崇。尼帕们各自的保护神虽不尽相同,但在完成仪式实践的过程中都遵循类似的规则。
如果说节日的源起依托于原始人类对生存世界的解读,那么在此心理基础之上构建出来的神圣时间与世俗世界、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便构成节日的存在。一方面,在时间的长河中存在着神圣时间的间隔,存在着节日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有着世俗的时间,普遍的时间持续,在这种世俗的时间之中,不存在有任何宗教意义的行为。[4]
祭祀型节日源起问题最终具化到三大功能的把握上,一是心理范畴的再生性功能:饱含崇拜情感的原始宗教节日及其仪式通过神话的解释(祭辞的演绎)重复过往,表示着对一个发生在神话中的过去、发生在“世界开端”的神圣事件的再次实现化。对世界生成、族群生成的神话吟诵仪式暗示出了对民族原初时间的重现,神圣时间每隔一年被重新产生,仪式让节日参与主体进入到神圣时间,完成新生;二是物质范畴的社会功能:节日不仅是某一群体的符号性行为方式,它还需超越观念,强化实践,达成现实中族人共同发展的目的,因此遵循自然满足功利性诉求是节日源起的又一重要特征。通过逐步获得的自然节律认知,随自然时序而动,表现出人与自然顺应与改造的关系,发挥着利于农事及生活的作用,保障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实践行动与庄严神圣的祭祀让节日参与主体代系相承最终成为一套完整的生存法则;三是历史进程的整合功能:节日祭祀自身的演化、其他民族如汉文化及其节日形态的传播使得节日成为多元文化的整合场。纵向来看,祭祀的节日渊源、母体或前身随着人类节日文化生境的断裂而重组,各种巫术、仪式初步形成不完全固态的节日特征。横向来看,文化传播让更多民族节日文化得以交流,于是在整合中衍生出节日观念和形式上的变异。
二、祭祀节日的类型及特征
少数民族节日类型主要包括祭祀型节日、交游型节日、集贸型节日以及综合性节日,其中祭祀型节日历史久远,最易推演出文明发展的初始形态与原始文化内涵,但由于此类节日的变异性与复合性,在进行节日类型划分的时候通常会出现重合的现象。
(一)神灵祭祀
祭天、祭祖和祭各种保护神都属于神灵祭祀的范畴。神灵从自然形象到半人半兽再到人格化的确定是人类对世界解释体系认知上的历时性发展。最初的原始人类面对生存,为协调自身所处的生境,形成了一套对宇宙、世界、社会、人生、心灵、情感的实用解释系统。这个解释系统基于原始思维,为人类提供了超出日常经验知识解释能力之外的现象问题的答案,于是随之产生崇拜的自然神灵、崇拜的鬼神、崇拜的祖先、崇拜的保护神(英雄)。取悦无法驾驭的强大对象产生了天、山、水崇拜;寻求难以探寻的生命源起产生了图腾。梦境、昏迷、死亡等生命现象让原始人类获得了灵魂与肉体分离的观念,并与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结合,产生出原始宗教观念。而少数民族祭祀类节日就是建立在原始宗教观念之上,根据各族的生境、历史,产生出丰富多样的神灵形象,并被配以一套完整的信仰习俗。这种信仰被看作是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引导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文化交流。
现存的云南少数民族神灵祭祀节日主要有祭天、祭祖、祭保护神。祭天节有:佤族拉木鼓节、哈尼族苦扎扎、拉祜族祭太阳节、独龙族卡雀哇、怒族祭天、景颇族目瑙纵歌。祭祖节有:纳西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等民族的祭祖节、阿昌族阿露窝罗节、彝族祭大、纳西族三朵节。祭保护神节有:傈僳族刀杆节、祭山神。神灵祭祀仪式几乎都有神话解释系统与之对应,只是有些神话在历史长河中消逝了,有些则承继下来。诸如,农历一月纳西族祭天习俗与《祭天古歌》;农历十二月独龙族的卡雀哇与《创世纪》;农历二月阿昌族的阿露窝罗节与《遮米麻与遮帕麻》;苗族的鼓社祭与《苗族古歌》;哈尼族的昂玛突与《哈尼阿陪聪坡坡》等。神话具有原始宗教、原始信仰的性质,它为宗教信仰及其实践提供了理由与依据。各少数民族的神话叙述活动与祭祀型节日密不可分,关涉着人类对世界万物和自身存在的思考。神话与祭祀之间的合理性解释与具体操演再次证明祭祀型节日的源起来自于人们内心的需要,即需要对人类生存进行解释。由生活的状态引出相关信仰,接着又依托于这些信仰通过功利性的一系列活动达成自己的目的。
通常,这种类型的祭祀节日是集合众人力量而共同完成的,民族文化集成者、神秘力量习得者与广大民众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共同作用于节日仪式当中,从而发挥各自的作用。例如,勐连彝族现存祭祀型节日除了家庭岁时祭祀节日,就是影响力更大的村寨集体祭祀仪式。家庭岁时祭祀节日包括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六月初六献田头、火把节、七月半、八月八尝新节、九月祭土黄、杀年猪;[5]村寨集体祭祀仪式包括正月初一祭土主、农历二月初一祭猎神、农历三月二十八祭土主、祭龙、祭山神。
“土主”存在于许多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中,各族称谓略有不同,但都被看作地方保护神。由于“山神”亦有类似作用,某些民族与地区将山神与土主融合为一体,行同一祭祀之礼。一般以村寨为单位建有土主庙,土主的形象也不尽相同。作为主管一方之神,功能稍微繁杂,管农业丰歉、人畜瘟疫、生死更替等,需集合村寨力量进行祭祀,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
猎神主管山林的猎物,狩猎的成功与否需仰仗猎神;龙神司雨水,雨水充沛是庄稼丰收的保证。这些职能明确的神灵的产生映射出的是其区域历史上经济生活方式。随着经济生活、观念认知的改变,有关此类神灵的祭祀节日逐渐减少。
(二)农事祭祀
农事祭祀节日建立于中国的岁时文化。“岁”是上古社会的一种斧类砍削工具,卜辞中将杀牲称为“岁”。“时”,指自然季节。时从日,时的变化与日有关。“岁时”的词意逐渐发生变化,但其根本仍基于农事节奏,以周期性祭祀活动对应每一季节段落中人们的诉求。[6]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云南少数民族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结构,大致包括四个类型:山地耕牧型、刀耕火种型、梯田稻作型和坝区稻作型。这种经济模式成为制约民族节日形态的重要因素。部分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特有的历法,诸如藏历、傣历、彝族的十月太阳历、苗历、哈尼族等民族的物候历,属于自然历法,通常是根据所处环境气候特点,借助山花的开放凋谢,山鸟的啼鸣,草木的枯荣,降雨降雪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作为判断节令的物候。诸如,傈僳族传统的“花鸟历”,将一年四季分为干、湿两大季,并确立10个节令作为安排生产活动的标尺:花开月(3月):“自白勒”鸟叫,开始翻晒土地;鸟叫月(4月):布谷鸟叫,开始播种;烧火山月(5月):“瓜卷双卷”鸟叫,结束播种;饥饿月(6月):“哦嘟嘟”鸟叫,节令已过,不能再下种;采集月(7、8月):采集野果、香菌、木耳及各种块茎植物;收获月(9、10月):庄稼成熟,收割庄稼;煮酒月(11月):家家户户煮酒,享受收获的喜悦;狩猎月(12月):男子到山上狩猎,女子织布;过年月(1月):男女老少都以请客、做客及对歌跳舞和玩各种传统体育活动来欢度傈僳年;盖房月(2月):雨水较少,也没有农活,家家户户忙盖新房和翻盖旧房。傈僳族对节令的划分因地区差异而略有不同。贡山一带傈僳族是根据月亮圆缺来划分月份并安排农事和家事:春耕月,种植月,薅锄月,撒荞月,秋收月,狩猎月,煮酒月,过年月。福贡的则划分为:织布月,新生月,雷雨月,布谷鸟叫月,砍火山月,烧火山月,栽秧月,盖房月,撒荞月,收割月,煮酒月和过年月。
围绕农业生产这一核心,少数民族创造出了一些内涵各异但却服从于农耕需要的农事祭祀节日。诸如哈尼族的“求丰收”“捉虫节”“牛纳纳”“祭谷王”“祭仓神”“新米节”;白族的“开社”“打春牛”“祭五谷神”“三月节”“祭牛王”;彝族的“请雨水”“叫五谷魂”“叫饭魂”“祭牛节”;基诺族的“鸟古欧”“祭水塘”“社祭节”“烧地祭”“插种祭”;瑶族的“开年节”“端午节”“尝新节”;蒙古族的“祭地母”;布依族的“烧虫节”“祈雨祭”;阿昌族的“撒种节”“吃新谷”等。
这种为着农耕生活方式而存在的节日大都发生于自然界中不同季节和年轮转变的关键时期,并依据时令和节日安排自己的生产与生活。[7]祭祀仪式成为其节日程式的核心,围绕不同时节的农事生产进程产生出相对应的祭祀仪式,从祭祀对象到祭祀操演之丰富体现出来的却是各民族面对生存的同一心理诉求。诸如,布依族传统节日“祭青苗节”,一般在农历四月中旬举行。耕牛不下田,并给予新鲜的米饭以示慰劳,同时民众需要祭祀稻谷神,旨在祈求稻神保佑新插的秧苗能够茁壮成长,为秋季的丰收奠定基础。以一年为时间节点,“撒谷节”为的是春天播种的顺利;“保苗会”为的是驱魔除害,祈求丰收;“尝新节”祭献谷神、祖先及为人类带来谷种的狗,以感谢神灵的赐予,祈求来年更好的收成等,各族的祭祀仪式最终的目的是农耕文化所追求的族群利益,关于族群的生存、繁衍与发展。
在文化交融过程中,与汉族产生互动较多的少数民族受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除了过本民族的年节之外,同样过汉族的春节,当然由于地域不同、影响力不同、春节习俗各异。
傈僳族的阔时节被看作岁首,以驱旧迎新为主,集合多种形式的综合性节日,依照传统习俗庆祝新年,亦称其为年节。年节与岁时相联系,同样与农业生产周期有关。
三、祭祀节日的流变
(一)从“神圣”到“世俗”
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祭祀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定期或不定期的祭祀仪式在整个神圣操演中主题清晰、目的明确,围绕“祭”凸显着人与自然、神话原型与讲演、操作仪式与习俗之间的关系。当这种特定文化语境逐渐消失的时候,念词、讲演、仪式习俗等随之走下神坛,演化为众人眼中的节日。在这种节日变迁过程中,民众除保留传统心理模式之外,生成更多的体悟,包括对现代节日演绎的认同、现代生活方式、娱乐方式的观念。最终,节日文化特征悄然完成了从“祭”到“节”、从“神圣”到“世俗”的过程。通过对不同少数民族祭祀仪式演化过程的梳理,不难看出现代节日仪式中,本受推崇的神秘力量习得者的主导力量逐渐旁落,娱神与敬畏之心向娱人与集体狂欢转变,一种原本与民族生存生活相关的神圣事项走向世俗,成为民族艺术的代表,成为民族文化符号。“节日”以强大的容纳空间,涵盖了更多的节日文化构成、节日观念构成和节日的功能。
此处,我们不妨再以傈僳族刀杆节为个案来说明有关的节日变迁问题。“上刀山下火海”的仪式在历史上并非傈僳族专属,山地民族都有这种仪式的遗存。现在,这种仪式常见于云南各地傈僳族中,并定为傈僳族特有的传统节日“刀杆节”,但区域差异使得傈僳族刀杆节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怒江傈僳族的祭祀仪式依然带有明显的原始信仰,从其祭祀对象及祭祀程式中不难推演出上刀山下火海源自于山地自然崇拜,以及与山地刀耕火种经济方式息息相关的对铁制生产生活用具的崇拜。最初,民族生存过程中对自然环境与生产方式功利性的祈愿成就了这一套原始祭祀仪式。但后世出现了民族迁徙、文化交融,祭祀中自然神灵的强大作用逐渐被民族关系下民众的需求所取代,基于此,腾冲傈僳族刀杆节最终依附于明代将领王骥将军的传说,以王骥的传说为其民族的深层心理制约和文化心理定式,并以由此形成的惯性支配为基础,展现出由祭祀原始崇拜发展为兼具祭祀、纪念民族英雄功能的纪念性节日的演变过程。
怒江与腾冲傈僳族对刀杆节认知的差异形成了一组难能可贵的对比关系,我们可以从横向的比较中看到节日本身纵向的发展脉络。当代刀杆节的最初恢复是民众自发与政府干预的共同作用。如,1981年,腾冲傈僳族民众要求恢复刀杆,意在通过刀杆节的举行祈福禳灾。1997年,怒江泸水成立刀杆队,恢复刀杆节。至今,刀杆节仪式艺术的内涵和外延日益扩大。时间、空间以及节日流程都标识上了现代节日属性。同时,民众滋生出对“节”性质转变的心理认可,并加速了节日观念、节日属性的转变,最终演化为一个“节”的概念。
这种节日变迁及其变迁带来的节日文化现代性特征逐渐让祭祀类节日从“神圣时空”走到了“世俗时空”。在现代节日文化的重构中,民族艺术、技艺等文化因子被看作民族文化标签不断被强化,并展现于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
(二)从“单一”到“复合”
节日及其显性特征反映出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这是一个最直观、最庞大的系统,勾连着民族内核与外部环境。两者产生变异的时候,往往最先表现于节日构成中。祭祀类节日的构成同样呈现出从“单一”到“复合”的发展态势。这种复合性包含了民众节日心理、节日程式和节日功能的复合。敬畏到娱神再到娱人的心理变化、节日与旅游业的对接都集中体现出节日的复合性特征,最后凝结于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娱乐等多重功能中。
景颇族“目瑙”的“合理性”有着完整的解释系统,即神话中讲述的民族生存史与迁徙史,民众相信人间的目瑙历经“占目瑙”“鸟目瑙”而神圣崇高①景颇族民间传说的目瑙纵歌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天上的目瑙(占目瑙);鸟类目瑙(鸟目瑙);人类目瑙(神京目瑙)。。最初山官家对目脑纵的独权也影射出经济平衡的需要,传统的仪式流程为:竖立目瑙示栋(包括太阳神、木代神的祭台)——“迷推”②迷推,景颇语,大董萨,即为能沟通神人的巫师。占卜备祭品——杀牲祭献——请神祭神③斋瓦、瑙双、瑙巴、董萨共同祭祀“木代神”,斋瓦念迎神的祭词《目瑙斋娃》;瑙双充当木代神儿女,舞蹈娱神;董萨与“迷推”先后净场禳灾。——目脑纵——谢神④斋瓦谢神,念祭词《种旱谷》和《找祭木代之牛》。,传统民族精英是仪式过程中的主导力量,目脑纵以娱神祈愿为典型的原始宗教仪式,虔诚的整套祭祀是其重心,节日显得单一而不亵。
中断、恢复、重构,原始宗教仪典的单一性逐渐被现代节日的复合特征所替代。2014年德宏景颇族国际目瑙纵歌节体现为多种文化结合的复合性节庆,时间从2月8日延续到2月16日,其中核心节日仪式历时3天(2月13日至2月15日),传统仪式:剽牛仪式——竖目瑙示栋(供神钵)仪式——目瑙纵歌绶冠仪式——万人之舞“目瑙纵歌”。与此同时,衍生出更为丰富的节日内容:《绿叶宴——景颇族八大系列名菜》及其他文化产品首发仪式;微电影《大舞之魂》开机仪式;景颇族传统绿叶团结自助餐暨民乐展演以及其他13个节日活动。①其余活动以经济活动为主。传统仪式、现代展演和其他经济文化事项共同复合为如“目瑙纵歌”这般祭祀类节日的现代面貌。
在当下的节日文化重构中,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各民族受到了现代文化影响并产生出“现代”文化自觉,最终通过具体操演,淡化了节日中的原始信仰,注入更多的现代主流意识,节日仪式被扩展为核心部分、衍生部分,产生出多重意义与功能。
余 论
回顾有关节日源起的论述,鲜有专门的研究。通常是在论述原始宗教、原始信仰与农事生活的时候简单概述。当下的研究者们更加关注社会转型期中少数民族的节日文化变迁问题,涉及文化适应、功能转变、节日与经济、节日与旅游等。事实上,追根溯源才能具备谈论“变迁”二字的基础。少数民族节日的功能一般作为节日类型划分的依据,而功能恰恰说明节日产生、存在的必要,与节日源起交织。祭祀型节日则俨然成为一个通过神话与实践集合了民族历史、心理、生存与发展的活态文本。“活态”所要表达的意思就在于那些系统的祭祀仪式依然在变异中折射出我们想要去关注的那些过往。
在研究节日文化的时候,丰富的个案搜集是寻找共性、发现差异的基础。以“祈福”为例,若仅将其当作一个节日程式语汇运用,不过是一个关联节日功能的基本步骤。但“祈福”二字背后是复杂、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同一节日“刀杆节”为例,区域差异下的巫师们如何演绎“祈福”。傈僳族尼帕在登上刀杆顶后都肩负祈福的责任,但具体实践却相去甚远。怒江泸水的傈僳族尼帕祈福步骤:第一个到达刀杆顶的尼帕,需把天门锁打开,并解下红布披挂在身上,称为“挂红”,意为打破了人神界线;第二个尼帕需要承担娱神的任务,呼喊或舞动;第三个尼帕要从刀杆顶上撒下粑粑、五谷等物品,称为“撒五谷”,意在为四面八方的百姓祈福。腾冲傈僳族尼帕的祈福则以一人之力完成。刀杆顶上备好五面旗子,香通将旗子向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一一掷下,如果旗子能顺利插入地下并竖立的话就代表这一方向的民众来年清吉平安,如果旗子倒下的话就代表这一方来年会发生一些灾祸。两种不同的“祈福”方式,不同的侧重点,影射着民族文化中的生境差异、异质特征。
祭祀型节日形态的异质特征是根植于不同民族乃至同一民族的生境与文化差异。当我们通过大量案例推演出祭祀型节日源起的心理需要、心理契合,梳理出祭祀神灵从自然形态到半人半兽再到人格化神癨的过程,解读出神话背后的民族历史、生境等共同特征的时候,面对文化交流日益增强,更应该重视节日文化的“同质化”问题。如何让民族节日在现代延展过程中保存异质性将是下一步思考的问题。
[1]黄泽.西南民族节日文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2]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大连: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3]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理论的知识谱系[J].民俗研究,2003,(2).
[4]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5]杨甫旺.民族学视野中的勐连彝村[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6]海上.中国人的岁时文化[M].长沙:岳麓书社,2005.
[7]施惟达.云南民族文化概说[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Origination and Rheology of Ethnic Sacrificial Festivals
He-Mayu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Yunnna 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In this paper,sacrificial ethnic festival can be regarded as the text of the“living state”.Festival ceremony and function will compound and vary alongwith social development,but natioalemergence,development and survival can still be de duced from behavioral practice.The purpose of trace is not only to find the cause of the festival emergence,butmore important is to find those national history and spirithidden behind words and action,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true value of ceremony.
Ethnics;festival origin;rheology
C951
:A
:1006-723X(2015)02-0084-06
〔责任编辑:左安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YXZ2010005)
何马玉涓,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①傈僳族目前通用的文字是由传教士傅能仁在传教之余,以拉丁字母制作傈僳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