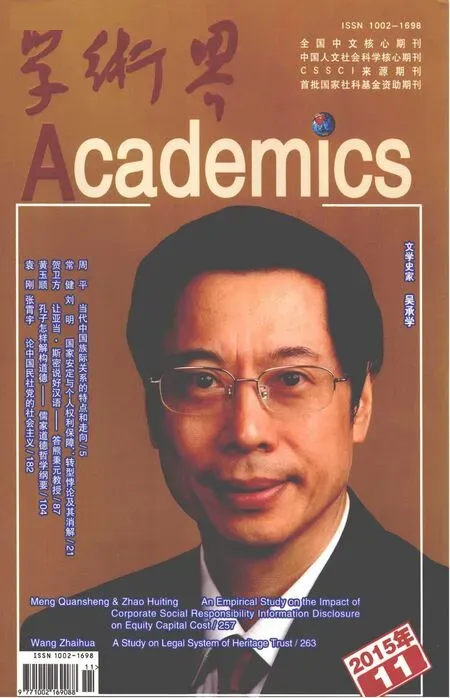《牟子理惑论》:儒释道三教辨通思路的初建
2015-02-26解兴华
○解兴华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牟子理惑论》,亦称《理惑论》、《牟子》、《牟子理惑》。它是否为佛教入华后的第一篇中国佛教论文,这个问题在学界至今尚无定论。因为有关《牟子理惑论》的真伪,自明末胡应麟对此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以来,争论十分激烈。主伪派以梁启超、吕澄和日本学者常盘大定为代表,认为此论成书较晚,大致为晋宋时期的作品。主真派以胡适、汤用彤、法国马思伯乐(H.Maspero)、伯希和(P.Pellion)与日本福井康顺为代表,主张该论成书于汉魏时期。双方各有理据,其理据亦均可被辩驳。因此,在此论未被确定证伪之前,本文仍依照《牟子传》自身的说法,支持主真派学者的意见,并由此获得推论:《理惑论》应为现存的佛教入华后中国人所撰写的第一篇佛教著述。
《理惑论》前有序,为作者牟子的略传及写作《理惑论》的缘起;后有跋,说明牟子论文体例的依据;中有本论三十七章,均采取问答形式,从佛教的立场,对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所引起的种种疑难和非议,分别进行了辩护,其中涉及到佛经体例、夷夏之别、鬼神、孝道、戒律等三教论争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描述牟子所见的佛教与儒、道等本土文化的对立,以及东汉末年的牟子提出的消解这些对立的三教辨通观念,并指出此观念是儒释道三教辨通思路的初建,为后世的三教辨通提供了基础哲学框架。
一、佛教与礼教的观念对立及其消解的思路
佛教初传中国,首先遇到作为本土主要意识形态——礼教的观念抵制。在《理惑论》中,这些抵制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佛教沙门毁伤身体,不合“孝子之道”。
所谓“毁伤身体”,是指沙门剃头,此为佛教出家相之一。《理惑论》第九章问者说:“《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没,‘启予手启予足。’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1〕此处两处用典:一者用《孝经》中的《开宗明义章》之言;二者引《论语·泰伯》载“曾子有疾”篇。总的来说,礼法之制,认为身体发肤,是父母所生,保持从父母而来的身体完好无损,即是作为家族一份子的个人履行孝道的基本要求。然而,同样以“立身行道”者自居的佛教沙门,却从剃发开始自身的修行。在本土观念看来,这是两种绝对对立、不可调和的教化。因此,如果站在礼教立场上,佛教即是必须抵制的文化。
第二,佛教沙门辞亲出家,违背“福孝之行”。
在礼教看来,出家者放弃了家族传承的责任,放弃由姓氏、名字、爵禄标识出来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责任,放弃了延续与彰表家族之德的任务,更放弃了圣人之道,放弃了对礼乐文化知识的学习与传承。礼教通过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塑造了个人,而佛教却表达了对礼教个人彻底否定的教义,这无疑也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三,佛教沙门仪礼简陋,乖离“貌服之制”。
无论是黄帝“垂衣裳、制服饰”,还是《尚书·洪范》立貌、言、视、听、思为君子修身五事,抑或孔子以服、言、行为先王之三德,〔2〕礼教对“貌服之制”、“礼仪容止”的要求历来严谨。佛教沙门“剃头发,披赤布,见人无跪起之礼,无盘旋之容止”〔3〕,明显乖违礼制。
按照佛教本身的教义,沙门剃头是破憍慢法之一。《大智度论》卷四十九载:“剃头着染衣,持钵乞食,此是破憍慢法。”〔4〕憍慢,指自高傲物的心态,属于佛教沙门修行中应该破除的众多烦恼之一。而从根本上说,憍慢是“我执”的表现之一。剃除须发,可以“舍弃饰好”〔5〕,避免世俗之虚饰,由此促进“破憍慢”、“破我执”的具体实践。而关于出家,《萨婆多毗尼毗婆沙》云:“家者是烦恼因缘,是故宜应极远离也。”〔6〕声闻乘佛教认为,家是产生烦恼的因缘,佛教以舍却烦恼,涅槃清净为人生目标,当然应该远离“为爱等诸烦恼所没”的家庭生活。大乘佛教虽然反对拘泥于出家之形服的小乘教,提倡以发菩提心及修利他行为出家之要谛,但同时也指出,在家行道极难。如《大智度论》卷十三载:“居家生业种种事务,若欲专心道法,家业则废,若欲专修家业,道事则废,不取不舍乃应行法,是名为难。若出家离俗,绝诸纷乱,一向专心行道为易。复次,居家愦闹多事多务,结使之根,众恶之府,是为甚难。”〔7〕如不是因缘具足,奉佛者在五浊恶世中修持佛道,还是应取辞亲出家之行。至于礼仪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佛教亦有自己的威仪。所谓威仪,是指举止善合规矩,言行举止不失方正,以塑造令人见之能起崇仰畏敬之念的仪容。如《菩萨善戒经》卷五谓身有四威仪:“一者行,二者住,三者坐,四者卧。”〔8〕日常生活起居皆有与其相应的作法、观念与祈愿,不能造次,从而达到清净增上的作用。仅就敬礼而言,《大智度论》卷十云:“有下中上礼,下者揖,中者跪,上者稽首,头面礼足是上供养。”〔9〕《大唐西域记》中则记载了九种敬礼:“致敬之式,其仪九等:一发言慰问,二俯首示敬,三举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长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轮俱屈,九五体投地。”《华严经随疏演义钞》载,凡礼敬三宝时,必须五体投地,藉此以折伏憍慢。也就是说,佛教虽有种种威仪礼拜,但却不对世俗人施行,而只是用来恭敬佛法僧三宝的。
依照以上教理,佛教似乎就是对礼教的直接反动,二者矛盾根本不可调和。而牟子却提出了以下消解对立思路:
礼教包含着“至德要道”与“下德”小节两个层面,佛教虽然在“下德”小节上有违礼教,但在“至德要道”上却与礼教保持一致。牟子指出,即使在礼教内部,“至德要道”与“下德”小节也会发生对立的情况。如周太王长子泰伯为了让天下于更有德行的三子季历,情愿避居江南,来到有“断发纹身”习俗的地域。此行虽然违背了《孝经》“身体发肤”之义,却被孔子赞为“至德”矣。〔10〕儒家认为,在“大德”与“小德”发生冲突时,应该采取孔子所言的“权”的办法。权,即称量、权衡。儒家认为,“权者,道之变也”,“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预设,尤至难者也”〔11〕。要在具体情况中权衡轻重,取“反经合道”之途,这是至难的。在牟子看来,对沙门之行进行评价时也可使用“权”的准则,即沙门之行虽违背了礼教的“下德”,却成就了真正的“至德要道”。
问题在于,牟子所指的佛教可与礼教会同的“至德要道”究竟是什么呢?相关篇章并未明确阐述,但关于“至德要道”之用,牟子一再强调,成就佛家之道或礼教之道,我们都可以获得类似的益处,即善事父母以成大孝,宰国致太平以成大仁。这里隐含着一个危险的推论:基于佛、礼同一的论点,只要我们清除佛、礼对立的妄见,佛教完全可以代替礼教成为国家意志。但反过来说,礼教亦可拒绝佛教在本土文化中的生存价值。
二、佛学与儒学的思想对立及其圆融的思路
儒学是礼教的阐释者与维护者。在《牟子理惑论》中,问者站在儒学的立场,提出佛教存在着如经典浩瀚〔12〕、教理繁琐〔13〕、布施浪费〔14〕等多种不当之处,本文捡取其中关乎佛道思想对立问题的紧要之处加以分析。
第一,“道生死以乱志”。
儒家很少接受关于生死问题讨论的合法性。如“问者”所言,儒家所志,不在理会“生死之事”、“鬼神之务”,而在“修世事”。佛教却明言以“了生死”为目的。它解释生死的实相,亦立特有的“死后更生”的轮回之说。这在儒家看来,均为“乱志”之教。那么,何以谈论“生死之实”就会乱“修世事”之志呢?后儒的两点意见值得注意:首先,“鬼神及死事难明,语之无益”〔15〕。其次,妨碍礼教的执行。《说苑·辨物》载:“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16〕以讨论死后有无心知的问题为例,正反两方面的回答都会引发违背礼教的意愿,制造妨碍礼教的可能。
第二,夷狄之教。
夷夏之别以及不能用夷为夏,是先秦以来由儒家大力倡导并为世人普遍接受的时代精神之主导方面之一。因佛教为夷狄之教而对其加以反对,亦属当时流行的反佛观念之一。
第三,“自毕于世”。
问者指出:“沙门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何聊之有?”〔17〕所谓“六情”,按汉班固《白虎通·情性》言,“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德论篇》则论人之性情:“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18〕《礼记·乐记》载:“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19〕王充《论衡》言:“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发。情接于物然者也,出形于外。”〔20〕人之性情由作为宇宙本体的阴阳而来,因此生而便满怀五性六情。性与情的不同之处在于,性是逻辑在先,即对人生而然之质的一种观念表达。不过,绝对孤立的“性”显然并不存在,因为人自出生便必然“感于物而动”,从而将自己的“性”表达为“情”,即“性情相应”。由此可以推知,人的“六情”必然伴随着人的生存过程。“情”的良好表达,即实现儒者所谓“动而处其中”的中庸之道。
相较而言,佛家对儒家的“六情”却有特殊的解释。六情大致属于佛教的心所有法,即心主体活动时所产生的各种精神现象。这些精神现象,在佛教看来,都是属于世间的心理要素,于众生来说,都是“我执”。作为不自在的精神根源,它们都是应该出离的对象。然而,“闭六情”、“自毕于世”的思想,在儒家看来,是违背人安身立命的自然性情的,故问者言“何聊之有”。
针对以上佛教的诸多由儒家观念展示出来的不当之处,牟子提出:
第一,佛教的生死鬼神之说,填补了儒家学说的空白。《理惑论》第十二章载:“‘人临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复呼谁?’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还则生。不还,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榖之根叶,魂神如五榖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已?得道身灭耳。’”〔21〕礼教的设计,主要针对养生、送死、祭祀三件大事。牟子此处所言,大致可见《礼记·礼运》载如何送死的礼仪:“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饭用生稻之米,故云饭腥。古丧礼中将生米填入死者口中)而苴孰(草包熟肉准备随葬),故天望(孔颖达疏:‘天望,谓始死望天而招魂。’)而地藏(葬)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皆从其初”。〔22〕儒家对生死问题极为慎重,汉晋时期,儒家成为统治思想,礼乐隆重,社会对养生送死祭祀等大事极为重视。庐山慧远法师,在讲经说法之余,还专门开设了外典的丧服学,此事件即可折射当时的文化氛围。
在礼教养生送死祭祀三个问题中,送死和祭祀逻辑地蕴含了“鬼神”的概念。也就是说,鬼神观念本身就是儒学必须阐明或处理的观念。而从文献事实上看,孔子虽明言不说“鬼神之余事”,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儒家典籍中对生死鬼神话题只言片语的阐述。《孝经》“鬼神享祭”,《易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等思想,都不约而同地表明了儒者对生死的关注,并暗示了“魂神不死”的观念,而它们的意义在于,表彰儒学所倡之大道的价值,亦即通过合乎道的行为来获得福果。因此,关注生死鬼神问题,承认“魂神不死”,并不违背儒学,相反,作为我们在实践“至道”(“为道”)时的理论需求,它是一种必要的言说(“至道之要,实贵寂寞,佛家岂好言耳……不得不对耳”〔23〕)。
第二,“用夷变夏”的非法性并不适用于佛教。孔孟之道,主张“夷夏之别”。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便有了难以消除的“原罪”。对此,牟子大量用典,列举在华夏之地也会有如瞽叟(舜的父亲)、管蔡(周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鲜与蔡叔度,于武王死后策动叛乱)等顽嚚昏悖之人出现,孔子、孟轲等人在中原遇到排斥,西羌、西狄这样的边远之地也会出现如大禹、由余等圣哲之人,故孔子言“九夷”之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24〕此一切无非说明:夷夏的区别不在于地域,而在于此地域所承载的文化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夷夏之别的精神实质,是“有道”与“无道”两种文化的差异;而“用夷变夏”的非法性则在于以野蛮驱逐文明的悖乱,“尊王攘夷”的合法性即在于维护王的文明(“王道”)。以此逻辑,孔子所言“夷狄虽然有君,仍不如华夏之无君”,恰恰指出了夷狄即便设立了王权及社会等级制度,如若其中并未贯彻道,即“有君”亦不代表有道,则无道之有君还不如有道之无君。因此,牟子表明,问者质疑的症结是“见礼制之华,闇道德之实”〔25〕。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佛教是否属于无道的野蛮文化呢?毫无疑问,牟子持否定意见。“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26〕,佛教教导了最普遍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佛教传递了“大道”。故此,佛教与礼教的冲突在牟子眼中,不再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仅仅是本土与外来的地域差别。由此,用夷夏之别来对抗佛教的合理性就消失了。
第三,佛教“自毕于世”的苦行是合乎儒家对待富贵之欲的道德教条的。牟子指出,儒家信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27〕。当问者提出儒家重视作为人之性情本然的乐生之欲时,牟子却指明了儒家思想中所蕴涵的另一个超越性的规范,即对道的服从。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都必须与道相应,才能获得存在或消除的合理性。佛教的“自毕于世”正是为了追求道的实现。然而,这里隐含着危险的问题:佛教所求之道,与儒家所言之道是否一致呢?如果一致的话,未能将自苦以求道作为修养之普遍教条的儒家,与佛家相较,在道的实践上究竟孰优孰劣呢?对此,牟子并未明确解说。
我们完全可以发现,牟子为礼教与儒家思想构筑了一个最高精神内涵——“道”。这个被明确构筑出来的“道”亦可被归属于佛教。在“道”的立场上,佛教对礼教与儒家的一切反动,都可被视为教条性的、枝末性的。
三、佛学与“为道者”的思想对立及其解决的方式
“为道者”,在《理惑论》的问者眼中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为道家;二为道教。
对于佛教来说,道家所提出的形而上的抽象之“道”无疑为其进入本土思想提供了说服力。事实上,在解答“何为佛道”的问题时,牟子说:“道之言导也,导人至于无为。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28〕;“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29〕。在这里,佛道,与道家之道似乎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它们都具有三个特点:(一)抽象性。道妙于万物,是无形无象无体。(二)普遍有效性。道遍在万物,周行不殆,且规定着万物的变化规律与总体趋势。道的运行即是可被称为“自然”的东西。(三)实践性。道是修养的依据,其最终的目的是“无为而无不为”,即于居家、宰国、独立三个方面皆成其用。
道教,在《理惑论》中亦被表述为“为道者”,或称“神仙辟谷长生之术”。如汤用彤先生所言:“两汉之世,鬼神祭祀、服食修炼,托始于黄帝老子,采用阴阳五行之说,成一大综合,而渐演为后来之道教。浮屠虽外来之宗教,而亦容纳为此大综合之一部分。”〔30〕然而,在《理惑论》中,以“问者”为代表的本土人士却开始发现道教与佛教的重大区别。站在道教立场上,佛教教义存在着以下荒谬之处:第一,佛教食谷而以酒肉为上戒。第二,佛教有病而进针药。第三,佛教讪神仙,不信不死之道。
对此,牟子的回应是:
首先,必须严格区分道家与道教。当问者言“为道者,或辟谷不食而饮酒啖肉,亦云老氏之术”时,牟子提出,“众道丛残,凡有九十六种……吾观老氏上下篇,闻其禁五味之戒,未睹其绝五谷之语”〔31〕。为道者繁杂,共有96种。而作为道家经典的《老子》从未有过辟谷之说。通过大量征引《道德经》的文字,牟子明确了道家与神仙辟谷之术的分别。
其次,在价值上,牟子认为,道家高于道教。问者言:“道皆无为,一也。子何以分别罗列,云其异乎!”〔32〕“为道者”所追求的都是无为,为何我们要分别它们的高下呢?而牟子则明确,“同类殊性,万物皆然”,如果混淆了老氏之道与神仙方术之道,正如“玉石同匮”,“朱紫相夺”,“众阴蔽日月”,“众私掩其公”。那么,道教之言为何不可取呢?牟子的理由是:神仙辟谷之术,虽然“洋洋盈耳”,但“数千百术,行之无效,为之无征”〔33〕。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轮回报应,以及在修行实践理论中所承诺的“涅槃”、“神通”等独特境界,于中土人士看来,也是无可验证的。如何避免受到类似的指责的呢?事实上,《理惑论》除了言及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及“魂神不灭”外,对佛教中其它的在中土人士看来具有“神怪”特征的内容几乎没有涉及。至于佛陀的相好,我们则能找到儒道二家中宣扬尧舜孔老等圣人天生异相的附会资源。〔34〕
最后,由于以上两个观点的确立,问者的三个质疑不再具备有效性。因为,在牟子的辩论中,道教被彻底地贬斥了,同时,由于牟子宣示了佛老同归,所以,所有来自以神仙辟谷之术为主要内容的道教的批评,不仅仅针对佛教,也可被视为是对老氏之道的反动。无论是辟谷不食,还是不进针药、不信不死之道,在儒道二家那里,都不具有合法性。而佛教戒酒肉,承认自然生命过程的现实性,却与本土圣哲省欲去奢、生死自然的言论没有出入。
综上所述,儒释道三教辨通模式的观念初建便是如下的路子:将以“自苦解脱”为根本目的的佛教描述为以发现及实践“道”之真理为根本目的的佛教。同时,澄清“德”、“权”、“让”、“无为”等礼、儒、道等本土观念,指出在抽象而无具体内容的“道”之原则上,佛教、礼教、道家与儒家是根本一致的,而佛教与其余三者在孝道、服制、夷夏观、生死观、鬼神观、性情观等诸多观念的对立都可被归属为枝末性的、形而下的,即在最高的形而上的原则中,佛教对儒家孝、礼等等的一切反动具有了合法性,三教一致的观念便由此而建立。
然而,正如唐代韩愈在《原道》中所作的廓清:“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35〕。儒家的最高精神是具有确定含义的“仁”与“义”,并非抽象而空洞的“道”与“德”。同理,佛教亦有自身具体而独特的理论。事实上,为了保证三教一致理念的成立,即便在论证的过程中触及了佛教的独特观念,《牟子》也避开了对它们的有效阐述。如《牟子》第十五章言佛教“度世”之用。所谓“度世”,即指众生自苦解脱的涅槃境界。这是佛家之宗,其中所含摄的佛性哲学、心性观、修行实践论等思想远不是礼教儒家的人伦日用,以及道家归志质朴、体道自然等观念能够比附说明的。同时,如果佛教之“道”被《牟子》阐释为“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36〕,那么,佛教之用与礼教、儒家“修世事”之用,以及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之用似乎不再有什么差别了。
从思想史上看,牟子的儒释道三教辨通思路成为后世学者论证三教一致理念时所广泛使用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不仅为佛教提供将儒、道思想摄纳进来的可能性,亦可令佛教教义合理地渗入儒、道的思想系统中,引起儒、道本土思想的佛学化。古代中国佛教史中围绕儒释道三教辨通的根本思路即是把儒释道三教的最高目的都归属于“道”的发现与成就,共同的最高宗旨为儒释道三教的并行不悖、互渗互补提供了合法性。在这一思路的轨范下,历代学者于儒释道三教的辨通中或谓“道”即是“理”,或谓“道”即是“性”,或谓“道”即是“心”,宋明理学与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心性哲学即是由此而开展出来的。
注释:
〔1〕〔梁〕僧佑著:《弘明集》,载《大正藏》第52册,第3页下。
〔2〕《牟子理惑论》第十一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3页上。
〔3〕《弘明集》,载《大正藏》第52册,第3页上。
〔4〕〔7〕〔9〕〔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载《大正藏》第25册,第412页下、第161页上、第131页上。
〔5〕〔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载《大正藏》第3册,第633页下。
〔6〕失译《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载《大正藏》第23册,第512页下。
〔8〕〔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菩萨善戒经》,载《大正藏》第30册,第986页上。
〔10〕《牟子理惑论》第九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2页下。
〔11〕皇侃著:《论语义疏》,转引自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09页。
〔12〕《牟子理惑论》第四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2页上。
〔13〕《牟子理惑论》第四、五、十八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1页下、第2页中、第4页中。
〔14〕《牟子理惑论》第十六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4页上。
〔15〕刘宝楠著:《论语正义·先进》,载《诸子集成》第1册,第243页。
〔16〕转引自方立天:《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中华书局,1990年第1版,第257页。
〔17〕〔27〕《牟子理惑论》第十九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4页下。
〔18〕〔19〕〔20〕转引自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25页。
〔21〕《牟子理惑论》第十二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3页中。
〔22〕〔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1版,第594页。
〔23〕《牟子理惑论》第十三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3页下。
〔24〕〔25〕〔26〕《牟子理惑论》第十四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3页下。
〔28〕〔29〕〔36〕《牟子理惑论》第三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1页下。
〔30〕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31〕《牟子理惑论》第二十九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6页上。
〔32〕《牟子理惑论》第三十三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6页中。
〔33〕《牟子理惑论》第三十一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6页上。
〔34〕《牟子理惑论》第八章,载《大正藏》第52册,第2页下。
〔35〕韩愈:《原道》,载《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