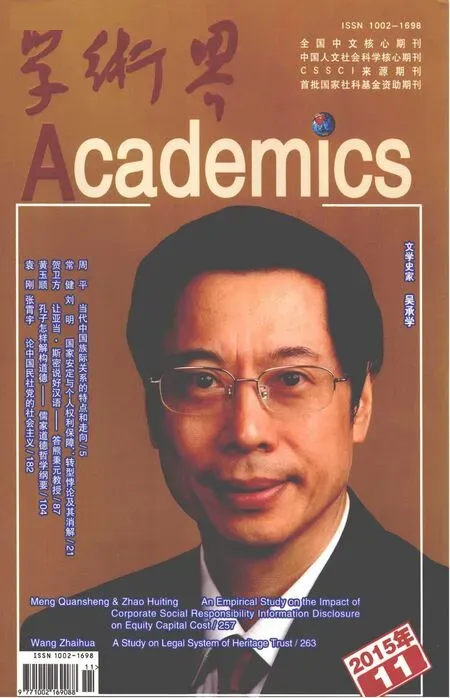最低保障与个人自由——哈耶克是否自相矛盾
2015-02-26王建勋
○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2249)
哈耶克(F.A.Hayek)无疑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classical liberal)之一。他毕生致力于批判计划经济和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阐释和发展自由社会的法政原理,堪称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集大成者。熟谙权力的威胁和危害,哈耶克始终对政府和国家怀抱高度怵惕之心,总是不遗余力地捍卫个人自由。然而,在对待社会保障的问题上,哈耶克的态度有些令人费解。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福利国家,反对再分配,反对以满足人们特定收入水平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由国家对那些无以为继的人们提供最低保障,确保其获得最低收入,保障其基本生活得以维持。值得追问的是,为何哈耶克提出这样的主张?他的理由和论证能否站得住脚?他的看法是否自相矛盾?最低收入保障究竟是否会伤害个人自由?其与一个自由社会相容吗?进一步,古典自由主义者该如何对待社会保障?为什么?这些问题的探究,无论对于解决这个“哈耶克式困惑”(Hayekian puzzle)还是对于廓清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地回答,以期抛砖引玉。
一、为何哈耶克支持最低收入保障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保障(economic security):一种是“有限保障”(limited security),一种是“绝对保障”(absolute security)。前者意味着保障人们免受严重的贫困,确保所有的人都能最低限度地维持生计,或者,说得更加简洁明了,保障(人们的)最低收入(security of minimum income);后者意味着保障(人们)获得特定的收入(security of the particular income),确保(人们)达到特定的生活水准。〔1〕哈耶克认为,有限保障可以提供给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因而不是一项特权(privilege),而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愿望目标(legitimate object of desire);而绝对保障无法提供给所有的人,因此难免成为一些人的特权,只是保障特定的人获得特定的好处。〔2〕他还指出,前者不涉及福利国家的问题,而后者则与福利国家密切相关,因为它反映的是一种利用政府权力确保对物品的更加平均或者公正的分配。〔3〕在他看来,有限保障的提供是对市场的补充,而绝对保障的提供只能通过控制或者废除市场得以实现。〔4〕
基于这种区分,哈耶克主张,自由社会中的政府应当提供有限保障——最低收入保障,而不应当提供绝对保障——特定收入保障。在其《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兼美国社会主义党全国主席克鲁格(Maynard C.Krueger)问哈耶克:“你如何看待对食物、衣服和居所的最低保障(minimum guarantee)?这是否违反了你对适当计划(proper planning)的定义?”哈耶克回答说:“‘最低保障’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在说,我支持保障这个国家中每个人的最低收入(minimum income)。”此时,当著名政治学家梅利亚姆(Charles E.Merriam)提醒哈耶克,他自己曾经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用过这样的表达时,哈耶克说:“我将用我的方式重新表述,我的意思是,保障每个人都可仰赖的最低收入。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失业保险。”〔5〕
在哈耶克看来,为那些无法维持生计的人提供最低保障,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一个自由社会所必需的。他说:“保障每一个人特定的最低收入,或者保障一种底线(floor)——确保任何人都不会处于该底线以下,即使当他不能维持生计时——似乎不但是一种防范所有人都面临之风险的完全正当的保护,而且是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必需组成部分,在此种社会中,个人不再对他生于其中的特定小群体成员有具体的索取权。当那些原先享受其好处的人发现,在并非他们自己过错的情况下,他们谋生的能力消失而无助时,一种意在诱导大量成员离开基于小群体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之相对保障的体制,可能不久就会招致强烈不满和暴力反抗。”〔6〕
问题在于,哈耶克支持最低收入保障的理由是什么?能否站得住脚?基于英美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他的第一个理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足以给每个生活困顿的人提供最低的收入保障,以满足其衣、食、住等方面的需求。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这样写道:“在一个已经达到了像我们社会的总体富裕水平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理由不应该保证向所有人提供第一种保障,而这不会致整个社会的自由(general freedom)于险境。”〔7〕
这不过是说,既然这些国家已经足够富裕,就应当为那些无法维持生计的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社会的总体富裕状况可以成为国家为一些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理由?一个社会的总体富裕程度难道不是反映在每个公民的富裕程度上?在自由世界,一个社会总体上的富裕状况总是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社会成员的财富上,而不是说这样的社会从民间攫取了更多的财富——国家更加富有,藏富于民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富裕社会,相反,国家富有而民间贫穷的社会不是一个富裕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总体富裕程度不过意味着其社会成员的财富所有状况,那么,这跟国家是否有权力对无法维持生计者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没有任何关联。在自由世界,虽然一个社会总体上十分富裕,但其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可能捉襟见肘,它拿什么来提供最低收入保障?还有,到底一个社会多富裕才应提供哈耶克式的最低收入保障?如何确定这种标准?
与此相关,哈耶克注意到,现代社会中的政府都为其社会成员提供了某种社会保障,这或许增加了他提议由政府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信心。他在1944年时说:“对于英格兰相当多的人口而言,这种保障(最低收入保障)早已得以实现。”〔8〕后来,他又指出:“所有现代政府都为穷困的、不幸的以及残疾的人提供了保障,关心健康问题和知识传播。随着财富的总体性增加,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纯粹性服务活动的规模不应该扩大。”〔9〕这似乎在说,既然所有的现代政府都提供了最低收入保障,我们就不应该拒绝它。问题在于,即使所有的政府都提供了最低收入保障,难道就能证明其正当性?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福利国家,难道就意味着福利国家具有正当性?哈耶克自己恐怕也不会赞成这样的推论,但他自己的论证的确存在着让人如此质疑的漏洞。
哈耶克的第二个理由是,由于一个社会的成员面临一些共同的风险,单个人无法抵御,只有集体行动才能满足这种共同的需要,而这意味着应当由国家来提供帮助。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指出:“也没有理由认为,国家不应当帮助个人,为其生活中的共同风险提供保障,由于这些风险的不确定性,个人几乎不可能提供充分的保障。正如在生病或者遇到意外事故时一样,只要政府提供的帮助原则上既不会削弱避免这种灾难的愿望也不会削弱克服其后果的努力,简而言之,只要我们处理的是真正可以保险的风险,由国家帮助组织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险体系的理由就非常强烈。……凡是在共同行动能够减轻个人既无法防御也无法承受其后果的灾难时,无疑就应当采取这种共同行动。”〔10〕后来,他在《自由宪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有一些共同的需要,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满足,因而能在不限制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得以保障。几乎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变得更加富裕时,社会总是为那些不能维持生计者所提供的生存保障——这种保障可在市场之外提供——将会逐渐提高,或者,政府可以有益而无害地在这些努力中伸出援助之手甚至起领导作用。没有理由认为政府不应当也在诸如社会保险和教育领域扮演某种角色甚至起带头作用,或者临时地补贴特定的试验发展。在此,我们的难题与其说是政府行动的目标,不如说是它的方法。”〔11〕
无疑,哈耶克的论证并不复杂。在他看来,既然人类社会中存在一些共同的风险或者共同的需要,而个人无法抵御这种共同风险或者满足这种共同需要,所以需要集体行动,而这意味着由政府插手——提供帮助或者发挥领导作用。这样的说法看似顺理成章,仔细考虑之后不难发现其中的逻辑和推理问题。我们承认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共同的风险或者需要,我们也承认这种风险或者需要个人难以应付,因而需要集体行动,但为什么这样的集体行动就要求政府介入呢?为什么人们不可以通过自治的方式实现这种集体行动呢?为什么人们不可以依赖市场或者公民社会(NGO)完成这种集体行动呢?难道由政府介入比依赖市场和公民社会具有更多的优势?遗憾的是,哈耶克没有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而是径直认为集体行动要求政府介入——无论是提供帮助还是发挥领导作用。
实际上,对于抵御人们共同的风险和满足人们共同的需要,并不必需政府介入,因为市场和公民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至少就哈耶克所提到的共同风险和共同需要而言。譬如,就救济穷人而言,家庭、宗族、教会等组织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就抵御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难的风险而言,各种各样的商业保险或者私人保险都可胜任;至于教育、医疗等领域,私立学校和医院的表现几乎在任何自由社会都比公立学校和医院更加出色。认为集体行动必然需要政府介入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大量的集体行动都是在市场上和公民社会中完成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对灌溉、地下水、森林、渔场等共有资源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人们是能够自治的,是能够通过自治的方式实现集体行动的。〔12〕虽然早期的集体行动理论家们——诸如奥尔森(Mancur Olson)〔13〕和哈丁(Garrett Hardin)〔14〕——对于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努力有些悲观,但奥斯特罗姆及其同仁的大量研究告诉我们,人是具有自组织和自治能力的动物,根基于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虽然这需要特定的制度安排、社会资本等。
哈耶克支持最低收入保障的最后一个理由是,确保不幸的人获得最低收入保障,符合所有人利益,帮助那些存在生计困难的人或许是一项道德义务。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他写道:“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没有理由认为政府不应当以保障最低收入的形式或者划定一个任何人都不会降至其下的底线,确保所有的人免受严重的匮乏。确立此种免受极端不幸的保障很可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或者,在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里,帮助那些不能自立的人或许是所有人的一项明确的道德义务(moral duty)。”〔15〕哈耶克的说法令人诧异,令人困惑的是,他怎么知道最低收入保障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如果拿一些人的钱为另一些人提供此种保障,也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如何证明这符合为此种保障支付成本者的利益?除非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愿,否则,恐怕很难证明这符合他们的利益。
还有,即使承认帮助他人是一项道德义务,但这种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legal duty)也存在着根本区别,前者不可强制执行,而后者是可以强制执行的。那么,如何将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转化为一种法律义务?在法律上一个人(一些人)有义务帮助另一个人(另一些人)吗?可以在法律上要求一些人必须帮助另一些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见,如果哈耶克主张由国家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就必须将为此支付成本界定为一项法律义务,否则,它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根本无法强制执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强行将一项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后果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要求人们做那些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如同立法要求父母必须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必须常回家看看父母。这样的立法看似强化了道德义务,实际上是专断的、暴虐的、不道德的。
二、最低收入保障与个人自由相容吗
作为个人自由的最有力鼓吹者之一,哈耶克如何看待其最低收入保障提议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呢?仔细阅读其从《通往奴役之路》到《法律、立法与自由》的主要著作之后,不难发现,他不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不认为最低收入保障会限制或者侵犯个人自由。虽然他承认最低收入保障可能会削弱竞争,但他认为,原则上,由国家提供这种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是相容的。〔16〕他还曾指出:“只要这种普遍的最低收入在市场之外提供给所有那些无论由于何种原因而不能在市场上充分自足的人,这不必然导致对自由的限制或者与法治冲突。”〔17〕也就是说,在哈耶克看来,只要这种最低收入保障是提供给所有需要保障者的,只要它不歧视任何需要保障者,或者说,只要它平等地对待所有需要保障者,它就不会限制个人自由。
值得拷问的是,哈耶克在这里似乎曲解了平等原则,背离了他自己对平等的释义。他曾经反复强调,平等仅仅意味着一般性法律规则的平等,或者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只有这种平等才与一个自由社会相容。在《自由宪章》专门讨论平等的一章中,他指出:“一般性法律与行为规则的平等(equality of the general rules of law and conduct)是唯一有益于自由的平等,是在不摧毁自由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获得的唯一一种平等。自由不仅与其他任何类型的平等无关,而且它们注定要在许多方面制造不平等。”〔18〕显然,平等地对待所有需要最低收入保障者,与一般性法律和行为规则的平等或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完全不是一回事。平等地对待所有需要最低收入保障者,不过是说,所有的人在满足特定条件时都可以享受最低收入保障而已,无关乎一般性法律和行为规则。这种平等不过是需要最低收入保障者之间的平等,其根本在于,确保需要最低收入保障者平等地享有福利特权。这种平等违反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因为它并没有考虑谁为这种最低收入保障买单,并没有将为最低收入保障支付成本者包括进来,因而只是一些人之间的平等,对另一些人构成了歧视。这种平等的倡导者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凭什么让一些人为另一些人享受最低收入保障而支付成本?这不是对前者的歧视吗?一般性法律和行为规则的平等允许这样的歧视吗?
在哈耶克看来,虽然一个人可以为政府不应当提供任何社会保障进行合情合理地辩护,但这种辩护跟自由没什么关系,或者说,根本不涉及到自由的问题。他说:“一旦政府完全不应该涉足这样的事务(社会保障)之顽固立场——一种可以自圆其说但与自由无关的立场——被抛弃,自由的卫士便普遍发现,福利国家的方案包含许多同样正当合理和毋庸置疑的内容。譬如,如果他们承认他们不反对纯净食品法,这被理解为,他们不应当反对推动一个可欲目标的任何政府行动。因而,那些企图根据目标而非方法厘定政府职能的人时常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种不得不反对似乎只有可欲结果的国家行动,或者,不得不承认,他们没有一般性的规则可以用来作为反对尽管可有效实现特定目的但总体上将摧毁一个自由社会之手段的根基。”〔19〕为什么政府不应提供任何社会保障的辩护与自由无关?哈耶克没有解释。他一方面强调福利国家中的大量做法具有正当性,另一方面主张根据方法而不是目标来界定政府的职能。问题在于,如何辨析并且根据什么标准来辨析福利国家中的哪些内容是具有正当性的?只要手段合理就不应对其目标进行拷问?政府的目标存在边界吗?什么样的目标政府不应当追求?如何判断政府采用的方法是否具有正当性?……
对于论证最低收入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相容性,哈耶克主要给出了两个理由。一个是,国家不仅是一个强制性的机器,而且是一个服务性的机构;虽然国家的强制性一面对个人自由是一个威胁,但其服务性一面则对个人自由没有坏处;因此,一个自由社会只需要限制国家强制性的措施,而不需要限制其服务性的行动。他这样写道:“尽管国家不应当介入那些与维持法律和秩序无关的事务之看法似乎合乎逻辑——只要我们仅仅把国家看成一个强制性机器(coercive apparatus),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服务性机构(service agency),它可以在不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帮助实现一些可欲的目标,否则,这些目标也许无法实现。那么,政府的许多新型福利活动之所以对自由构成威胁,是因为尽管它们以纯粹服务性活动的面目出现,但它们的确构成了政府强制性权力的运用,并且,在特定领域依赖于政府声称拥有的排他性权力。”〔20〕他又说:“尽管少数理论家要求政府的活动应当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但这样的立场无法被自由之原则证明具有正当性。只有政府的强制性手段需要被严格限制。我们已经(在第十五章中)看到,存在一个不可否认的、广大的非强制性政府活动领域,并且,明显地需要通过税收资助它们。”〔21〕
哈耶克提出了一个看似有说服力的理由,但问题是,其强制性活动和服务性活动的区分能否站得住脚?这两种活动真的可以区分开来吗?哈耶克将国家职能区分为强制性的和服务性的,是因为在他看来,存在着两种独立的、不同性质或者类型的、可以完全分开的国家活动,一些是需要直接动用强制性手段(暴力手段)才能完成的活动,一些是不需要直接动用强制性手段即可完成的活动,后者就是他所谓的服务性活动,诸如救济穷人等。这种区分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是建立在对“服务”一词的狭义理解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哈耶克没有看到其所谓服务性职能背后的强制性后盾。
如果我们对“服务”一词进行广义理解的话,可以将国家的所有职能都理解为服务性的,包括那些需要动用强制手段的活动,因为强制无论如何都不是国家的目的,或者说,不是人们设立国家的目的,其强制性措施总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因而,可以说,国家的所有活动都(应)是服务性的。譬如,如果一个人被证实实施了犯罪行为,国家会对他(她)采取强制措施,而这种强制性活动是为了服务于秩序,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国家的强制机关,诸如军队、警察、监狱等都不是为了强制而存在,而是为了提供安全、秩序以及保护人们的权利和自由之类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哈耶克将国家的职能区分为强制性活动和服务性活动似乎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更加重要的是,哈耶克对国家两种职能的区分没有认识到其所谓服务性活动背后的强制性后盾。毋庸置疑,国家所提供的所有服务都离不开税收的支撑,而征税总是以强制或者暴力作为后盾的。根本而言,国家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纳税人,它是一个税收最大化机器,也是一个最大、最具有浪费性的消费机器。既然如此,国家提供的所有服务,或者说,国家从事的所有活动——不论性质与类型,都是建立在以强制性手段作为后盾的税收基础之上的。没有税收,没有税收的强制性后盾,国家是无法提供任何服务的。这是国家提供服务与市场、公民社会提供服务的根本性区别之一。最低收入保障的本质不过是国家强制一些人缴税来保障另一些人的最低收入而已,在国家提供保障的那一刻看似没有强制任何人,而只是向一些人提供了服务——最低收入,但它在提供这种服务之前已经实施了强制或者可能实施强制,迫使另一些人缴纳了税。只要存在这种强制,它便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这完全符合哈耶克本人对自由的界定和理解。〔22〕
不能不说,哈耶克对征税权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缺乏必要的警惕。公关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布坎南(James M.Buchanan)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民主社会里,征税权也很容易被滥用,很容易沦为一些人侵犯另一些人财产权的工具,往往成为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之一。〔23〕构建有限政府的关键步骤之一,就是限制国家的征税权,既要防止政府以征税的名义直接侵犯私人财产权,也要防止政府通过多数暴政的方式进行再分配。如果征税权得不到有效地制约,私人财产权则不会安全,个人自由便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为财产权是个人获得独立、人格、尊严的前提,是个人自由的基石。〔24〕马歇尔(John Marshall)大法官曾言:“征税的权力包含有毁灭的力量。”〔25〕
哈耶克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如果说国家的服务性职能不会伤害自由,那么,他为何认为福利国家对个人自由有极大的威胁呢?从国家承担服务性职能的角度来讲,福利国家与哈耶克式最低收入保障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提供更多、范围更广的服务,而后者提供更少、范围更窄的服务,既然只有服务多与少的区别,应该都不会对自由构成伤害。然而,奇怪的是,哈耶克认为福利国家对个人自由构成伤害,而最低收入保障则不然。既然都是提供服务,难道提供服务多了会伤害自由,而提供服务少了则对自由无害?还有,如果国家的服务性职能不会伤害自由,那么,哪些服务应该由国家来提供?哪些服务不应该由国家来提供?或者说,国家提供服务的边界在哪里?如果说国家应该提供最低收入保障,为何它不应该提供高于最低收入的保障?为何它不应该提供福利国家所提供的所有服务?哈耶克对强制性职能与服务性职能的区分及其对服务性职能的理解,使其难以回答这些问题。
哈耶克论证最低收入保障不会伤害自由的第二个理由是,虽然最低收入保障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再分配和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有着很大不同,因为前者意味着能够自立的多数同意帮助那些不能自立的少数,而后者意味着多数因少数拥有更多财富而强行抢劫。在《自由宪章》中,他这样写道:“当然,即使对那些不能自立的人提供统一的最低收入保障也确实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收入再分配。但是,在对那些不能在正常发挥作用的市场上赚取收入维持生计者提供这种最低收入保障和旨在于所有较重要职业中确立‘公正’报酬的再分配之间,即在一种绝大多数解决温饱的人同意给予那些不能维持生计的人这样的再分配,与大多数人因少数人拥有更多财富因而从其手中抢夺的再分配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保存了非人格化的调整方法(impersonal method of adjustment),人们在其中可以选择他们的职业;而后者则将我们带至一个愈来愈接近人们被当局命令做什么的体制。”〔26〕
这段话表明,在讨论最低收入保障时,哈耶克有些想当然。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他怎么知道,在最低收入保障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自愿同意为那些不能维持生计者提供此种保障?这种同意是如何形成的?经过了什么样的程序?可以假定它天然存在吗?它不需要明确而清晰地表达吗?为何哈耶克认为存在着这种同意?无论是最低收入保障还是福利国家,就财富转移而言,二者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吗?为何哈耶克将前者界定为“同意”,而将后者界定为“抢劫”?抢劫一美元与抢劫一百美元在性质上存在根本区别吗?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认为,最低收入保障的提供意味着支付成本者是自愿同意的。“同意”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程序基础之上,必须是自愿的,必须是当事人明确清晰的意思表示。在一个共同体中,除非一些成员自愿、明确表示愿意为另一些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否则,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假定这样的同意当然存在。至于最低收入保障和福利国家在财富转移性质上的共同性,恐怕哈耶克也很难提出反驳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哈耶克式的最低收入保障不是无条件地提供给所有的人,而是要求获得最低收入保障的人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需要,证明自己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不能提供此种证明的人,是不能获得最低收入保障的。〔27〕问题在于,一个人如何证明自己无法维持生计?如何证明自己没有维持生活的收入?提供工资或者纳税记录?提供存款证明或者银行帐单?如何判断以及谁来判断当事人提供的这种证明是真实、可靠的?如果当事人隐藏收入怎么办?如何避免当事人撒谎或者欺诈的道德风险?如果真实可靠的证明要求政府对当事人的生活和家庭进行调查,如何避免侵犯其隐私权和其他权利?还有,如果当事人由于挥霍或者酗酒等行为导致自己不能维持生计,是否同样应该得到最低收入保障?如果他屡次因为挥霍或者酗酒等致使自己无法维持生计,他是否还应该继续得到最低收入保障?如何避免懒汉精神?
其实,哈耶克也意识到了由国家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但是他并没有详细讨论这些危险究竟是什么,也没有评估这些危险的危害性到底有多大,是否对个人自由构成严重的威胁等,而是近乎不假思索地认为,这些危险并不构成反对最低收入保障的理由。他这样写道:“对于应当保障的准确标准存在一些困难的问题;尤其重要的问题是,那些依赖社会(最低收入保障)的人应否无限期地享有像其他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一样的全部自由。对这些问题的不谨慎处理,很可能导致严重甚至也许危险的政治难题;但是,毋庸质疑,某种最低限度的、足以维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住保障,可以提供给每一个人。”〔28〕
如果考虑到由国家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可行性,这些难题就不应该被淡化。比如,就保障的具体标准而言,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标准?这样的标准根据什么来确立?这种标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确立这样的标准是否需要考虑人与人之间、地域之间的差别等?什么样的保障构成“足以维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住保障”?举例而言,假设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里,有的人需要每月500美元满足衣食住要求,而有的人则需要600美元,还有的人需要800美元,该以哪些人的需要为依据来确立保障的标准?由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不同,人们很难有共同的看法,也难以找到客观的标准。任何标准都难免是任意的、武断的,反映的不过都是标准制定者的看法,而不是需要保障者的看法。还有,不同的人对“健康”和“工作能力”的判断和看法不同,因而对于什么样的保障能够维持健康和工作能力也就不可能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该以哪些人的意见为准?再者,很多自力更生的人——包括大量的富人——可能都是通过健康换来的收入或者财富,他们拼命工作,精神压力巨大,凭什么让他们拿出钱来保障其他人的所谓健康和工作能力?正当性何在?
值得玩味的是,当哈耶克说“那些依赖社会(最低收入保障)的人应否无限期地享有像其他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一样的全部自由”时,他究竟意味着什么?莫非他是在建议,那些靠最低收入保障过活的人之(部分)自由应当受到限制或者被褫夺?若果真如此,他们的哪些自由应当被限制或者褫夺?是否要对此种限制或者褫夺设定期限?进一步,限制或者褫夺其自由的理由或者依据是什么?一部分人因为享受最低收入保障而丧失(部分)自由,是否意味着最低收入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存在龃龉?一部分人的(部分)自由的丧失,是否意味着整个社会自由的减少?如果哈耶克主张一些人的(部分)自由因为享受最低收入保障而受到限制或者被褫夺,这无疑意味着他承认最低收入保障和个人自由之间存在冲突,承认个人自由是一个人享受最低收入保障所应付出的代价,而这与他所谓最低收入保障与个人自由相容的看法显然是矛盾的。福利国家的实践也表明,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经常要付出牺牲(部分)自由或者权利的代价,比如,享受福利者被迫进行毒品检验、部分隐私公开等。
哈耶克还承认,由国家提供社会保险可能会使竞争多多少少失效,但他仍然认为最低收入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是可以相容的。〔29〕他没有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保障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竞争失效?这种失效对于市场的有效运转是否具有致命性?如果说社会保障致使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失效了,市场如何发挥作用?如果市场不能发挥作用,替代它的除了计划和命令之外,还能有什么?哈耶克深谙竞争和市场的重要性,因而才对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进行了开创性地批判,指出消除竞争和市场的经济体制必然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最后,哈耶克也意识到了由国家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可能对国际关系和移民的影响,但他没有对此进行分析和讨论。在《通往奴役之路》的一个注释中,他写道:“如果仅仅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赋予人们比其它国家高的生活水准权利,严重的国际关系问题也将出现,这不应该被轻描淡写地抛至脑后。”〔30〕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准高于另一个国家,移民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由此而带来的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问题恐怕不容忽视。譬如,如果一个国家提供了最低收入保障,而另一个国家没有提供,那么,后者的公民就很可能想方设法移入前者,尤其是对于邻国而言,像墨西哥和美国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阻止新的移民还是完全放开移民?如果一些移民是通过合法的方式进入的,他们应否(立即)享受最低收入保障?如果一些移民是通过非法的方式进入的,他们的子女应否(立即)享受最低收入保障?如果完全阻止新的移民,不仅不现实,而且与自由迁徙的理念不符;如果完全放开新的移民,则可能使一国财政不堪重负。欧美不少福利国家严重的移民问题令那里的政府头疼不已,迄今也未找到合适的对策。
三、古典自由主义者该如何对待社会保障
对待社会保障或者福利国家的态度,常常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和其他流派理论家的重大分歧之一。虽然哈耶克支持最低收入保障多多少少有些让人意外,但他并非唯一一位支持社会保障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布坎南(James M.Buchanan)、穆雷(Charles Murray)等一流的理论家也赞成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保障。譬如,弗里德曼提议征收所谓的“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即收入达不到一定标准的人不仅不需要交税,而且还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一定数额的补贴,以确保所有人的净收入不低于一个底线,从而实现减轻贫困的目的。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有助于直接缓解贫困,以现金帮助最有用,具有普遍适用性,成本明确地由整个社会负担,在市场之外运作;虽然它也像所有其他缓解贫困的措施一样会削弱那些获得帮助的人自救的动机,但作为一种补充收入至一定最低限度的制度安排,不会完全根除这种动机。〔31〕
但是,弗里德曼也认识到了其负所得税提议的潜在危险,但他认为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第十二章中,他这样写道:“我提议的负所得税的主要缺陷在于其政治后果。它确立的是一种强制一些人交税来补贴另一些人的制度。很可能,受到补贴的人有投票权。如果不是绝大多数人自愿交税帮助不幸的少数人,总是有转变为多数人为了自利而强制不情愿的少数人交税之危险。因为这个提议致使一些人交税补贴另一些人的过程如此明确,这种危险也许比其他措施更大。对这个问题,我看没什么解决办法,除非依赖选民的自制和善意。”〔32〕并且,他似乎对这种自制和善意还比较乐观。他指出,英国的养老金制度虽然也是用一些人的税收来补贴另一些人,但这并未摧毁英国的自由或者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还出现了选民自制的迹象。〔33〕然而,自弗里德曼写作此书的196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演进和困境告诉我们,他过于乐观了。福利国家的现状是,福利只能螺旋式上升,民众都渴望获得更多的福利,一旦福利减少,全国就发生大罢工之类的抗议。
虽然与弗里德曼不同,但另一位获得诺奖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布坎南也认为由民主国家提供普遍性福利(general welfare)并无不妥,只要这种福利是建立在比例制单一税(flat tax)的基础之上,并且政策没有歧视性,福利支付给所有公民。〔34〕问题在于,即使是通过单一税提供福利,也带有歧视性,因为一些人交的税多,而另一些人交的税少,还有一些人可能不交税。如果说用这种单一税提供那些必需的公共物品——如国防、司法、治安等——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的话,那么用它来提供福利则不可取,因为它也是一种再分配。
还有,著名古典自由主义学者穆雷(Charles Murray)则提出,为了与福利国家支持者妥协,应当赞成由国家给每个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guaranteed minimum income),作为福利国家的替代性选择。〔35〕问题是,为何要与福利国家支持者进行妥协?即使牺牲原则也要实现此种妥协吗?而且,最低收入保障真的能替代福利国家吗?其可行性如何?实际上,福利国家支持者大多不满足于当下的福利项目,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全面的福利。由政府来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结果很可能是,既没有废除现有福利项目,又增加了新的福利,结局更糟。
那么,古典自由主义者该如何对待最低收入保障?或者说,古典自由主义者该如何在一般意义上对待社会保障?什么样的态度才与古典自由者力倡的个人自由相容?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人们设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或者,用洛克的话说,保护自己的财产权。〔36〕既然如此,政府的任何行动都应当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所有其他行动都超越了政府的边界,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提供社会保障。任何类型的社会保障都会导致再分配,都会导致一些人侵犯另一些人的财产权,而这根本就违反了设立政府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自由主义者应当反对任何类型的社会保障,回到诺齐克(Robert Nozick)主张的“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将国家的行动严格限制在防止盗窃、抢劫、欺诈以及其他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害上,只负责提供治安、司法、国防之类的公共物品,其他所有的事务都留给市场和公民社会。〔37〕只有这种最小国家才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容,才与个人自由相容。
很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可能认为,这种主张不现实,因为现在的国家已经远远超越了诺齐克意义上的最小国家,承担着很多不应该履行的职能,回归最小国家恐怕没有可行性。其实,这种看法是基于现状不可改变的认识,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国家现在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很多福利甚至只是二战之后才出现的。譬如,仅仅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民主党总统的执政理念与今天的民主党总统还大相径庭。1887年,德克萨斯州几个县因为干旱而颗粒无收,国会起草了《德克萨斯种子法案》,意在对遭受旱灾的农民进行救济,但时任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President Grover Cleveland)否决了该法案。在其著名的否决声明中,他重申了美国国父们开创的有限政府理念:“我在美国宪法中找不到动用公帑进行救济的理由,我不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和义务应该扩至对遭受灾害的个人进行救济的情形——这与公共服务或者公共利益没有适当关联。我认为,无视联邦政府权力和义务有限使命的普遍倾向应被坚决抵制,以实现该教训应被时刻牢记的目的——尽管人民供养政府,但政府决不应供养人民。我们总是可以仰赖民众的友爱和慈善来救济其不幸的同胞。这一点是反复且最近刚刚证明过的。这种情况下的联邦资助鼓励人们指望政府的家长式关怀,削弱我们刚毅的国民性,抑制我们民众之间那种互助友善的情感与行动——而这有助于加强手足之情的纽带。”〔38〕
这段话告诉我们,慈善和救济根本不是政府的职能,而是民间或者公民社会的事务,政府介入不仅没有好处,反而还有坏处。它只需要政府减少税收,藏富于民,民众之间自然会相互帮助、和衷共济。由政府提供救济的假设是,政府比同胞公民更具有爱心,更懂得生活窘迫的人们需要什么。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政府里面的每一个公务员都来自社会,都不比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更具有爱心,因而政府不可能比民间更关爱需要帮助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一个受难者的邻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比政府更了解当事人,更知道当事人需要什么等。经验也表明,在提供慈善和救济事务上,民间比政府更公开、更透明、更负责。一些国家的民间慈善事业不发达,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没有爱心,而是因为那里助推民间慈善的制度安排不合理,比如没有结社自由因而不能成立慈善组织,没有税收优惠因而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等。
四、结 语
无论如何,哈耶克支持最低收入保障的理由都经不起推敲,对最低收入保障与个人自由的论证都缺乏说服力。对最低收入保障所可能带来的诸多挑战和威胁,他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有意无意地回避,要么有很多想当然的成分。就他自己所构建的理论体系而言,就其概念和逻辑的自洽性而言,最低收入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的龃龉是显而易见的。作为20世纪倡导个人自由的最卓越人物之一,他极力反对福利国家但又支持最低收入保障的看法,是令人费解的,或许是在其面临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汹涌思潮时所做的思想上的妥协。作为力倡个人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应当拒绝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因为这根本不是国家的正当职能。古典自由主义者应当回归诺齐克的“最小国家”,只赋予政府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职能,救济和慈善事务应当留给市场和公民社会。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比民间更具有爱心,也没有理由相信政府从事慈善比民间更加公开、透明、负责。为了根除当下的福利国家或者与福利国家支持者进行妥协而支持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尤其是最低收入保障),不仅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原则,而且牺牲了理论的一致性,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
注释:
〔1〕〔2〕Hayek,Friedrich A.,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pp.119-120;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72,pp.259-260,259.
〔4〕〔7〕〔8〕〔10〕〔16〕〔28〕〔29〕〔30〕Hayek,Friedrich A.,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pp.120,120,120,120-121,121,120,121,Footnote1,120.
〔3〕〔9〕〔11〕〔18〕〔19〕〔20〕〔21〕〔22〕〔26〕〔27〕Hayek,Friedrich A.,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72,pp.259,257,257-258,85,258,258,257,11-21;133-147,303,303.
〔5〕Hayek,F.A.,Hayek on Hayek: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ed.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London:Routledge.1994,p.101.
〔6〕Hayek,F.A.,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Vol.3: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London:Routledge,1982,p.55.
〔12〕Ostrom,Elinor.,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3〕Olson,Mancur.,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4〕Hardin,Garrett.,The Tragedy of Commons,Science,1968,162(No.3859),pp.1243-1248.
〔15〕〔17〕Hayek,F.A.,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Vol.2: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London:Routledge,1982,pp.87,87.
〔23〕Brennan,Geoffrey and James M.Buchanan,The Power to Tax: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a Fiscal Constitution(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M.Buchanan,Vol.9).Indianapolis,IN:Liberty Fund,2000.
〔24〕Pipes,Richard.,Property and Freedom.New York:Vintage,1999.
〔25〕McCulloch v.Maryland,17U.S.316(1819).
〔31〕〔32〕〔33〕Friedman,Milton.,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Phoenix Books.1963,pp.192,194,194-195.
〔34〕Buchanan,James M.,Can Democracy 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Social Philosophy & Policy,1997,Vol.14,No.2,pp.165-179.
〔35〕Murray,Charles.,In Our Hands:A Plan to Replace the Welfare State.Washington,DC:AEI Press,2006.
〔36〕Locke,John.,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Ed.Thomas Cook.New York: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1947.
〔37〕Nozick,Robert.,Anarchy,State,and Utopia.New York:Basic Books,1974.
〔38〕Cleveland,Grover.,“Cleveland’s Veto of the Texas Seed Bill,”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Grover Cleveland.New York:Cassell Publishing Co.1892,p.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