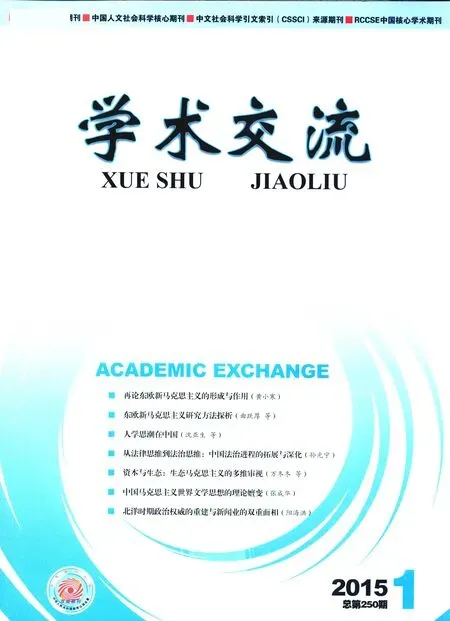无主动产之先占取得
2015-02-25李迪昕
李迪昕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沈阳 110034)
法学研究
无主动产之先占取得
李迪昕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沈阳 110034)
无主动产能否先占取得,这不仅是制度解释问题,更具有制度构建意义。中国现行《民法通则》《继承法》《物权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等就所有人不明的、无人认领的、无继承人的无主财产等归属问题皆做出了归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规定,引发理论界争议不断。不论从立法抑或实践层面而言,既然先占取得在我国以社会习惯的方式获得了国家的默许,立法应肯认发现人、拾得人有条件地先占取得无主动产所有权。与此同时,亦应将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明定禁止先占的动产以及无人承受的动产遗产排除在先占行列之外。
无主动产;先占取得;公共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现行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等就所有人不明的、无人认领的、无继承人的无主动产归属作出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之规定,但这种规定有失合理。我国之所以在历史上存在无主动产归先占者所有之立法规定,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未曾提及,并非因立法者的立法疏忽所致,而是有意为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立法者认为确定无主动产归先占者所有不仅是对所有权人权利的侵害,同时违背了立法欲使公权力主体成为当然所有人的倾向。但是笔者认为,立法之所以允许国家干涉私权,其目的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若不分无主动产是否涉及公共利益而一律使国家或集体成为其当然所有者,丧失立论基础。纵使无主动产与公共利益存在关联,也应该在其他法律制度中体现,而非在具有私权属性的民法中加以规定。足见,立法将无主动产一律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亦主要是基于其具有公权力主体之身份,但此种规定有失合理,原因如下:首先,将一切无主动产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与法理不符。从法理角度而言,民法遵循的基本理念是权利义务之对等,立法规范任意将公权力进行扩大化,使公权力主体在未负有任何义务的前提下就享有作为无主动产当然所有者之权利,这显然不符合法理。其次,将一切无主动产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事实上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从现实角度而言,若将无主动产统一归公权力主体所有,在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加重了国家负担。详言之,本可由拾荒者捡拾之无主动产,若否认其取得所有权,将会出现两种极端现象,部分人因丧失了利益的驱动而逐渐对无主动产视而不见、任其灭失,不捡拾不利用;另一部分人捡拾后藏之匿之,不使用亦不上交,无论从哪种结果来看,殊途同归地导致无法循环利用大量可回收的财产,因而减少了社会财富。
此外因抛弃产生的无主动产,形态品种各异,公权力主体亦无可能设置机构代替拾荒者。倘若国家为了便于管理,耗资设置各种机构,耗资甚巨却得利甚微。足见若将无主动产一律纳入国库,尚不论因无人利用造成的浪费,对国家亦是不小的财政负担。可见,立法规范将无主动产一律收归公权力主体所有,造成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悖离。换言之,倘若否认无主动产先占取得亦是与社会现实不符,在生活中常见人们采花垂钓以及众多儿歌如“采蘑菇的小姑娘”等,若按此立法规定确定归属,岂不是对公共财物的侵占以及对违法乱纪行为的公开宣扬。立法赋予公权力主体成为无主动产的当然所有者,既影响了社会风气,不利于资源的循环利用,亦是无权利无必要的,如此规定只会造成与现实的脱节,与事实的悖离。
二、无主动产先占取得之理论分析
先占作为一种原始财产最重要的取得方式起源于罗马法,并在罗马时期成为一项公认原则。罗马法中的先占即是以据为己有的意图获取或是占有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物①在罗马人眼中,占有是对物的事实控制,占有关系是伴随人类对无主物第一次占有事实发生时开始的。对无主物这种事实上的占据(或占有,罗马人即是这样理解这个词)被法律承认为合法占据,鉴于物本身是无主的,不会因此侵害任何人。先占是自然法方式的典型代表,查士丁尼曾在“民法总论”中说,自然理性要求最先占有者享有无主物。([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51.)。随着成文法时代的到来,近代无主动产先占取得之理论基础源于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诺其克承袭了洛克观点,并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表示,判断先占取得无主动产是否正义的标准即在于,此先占是否使他人福利有所减等,应在“不对他人利益造成任何损害的前提下”为人们提供自我完善的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尽管新中国立法未规定无主动产之先占取得,但并不能否认“其作为一种确认无主动产归属的重要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物权法》只字未提并非代表其无存在之价值,理论界关于无主动产是否可以先占取得,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持反对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其一,作为早期游牧民族财产取得方式的先占制度在当今社会已丧失重要性,暂不论无主动产量少而价菲②有学者认为,在特定的法律制度调整之外的无主财产范围是很小的,价值亦是有限的,主要是废弃之物。(魏振瀛.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1.),若予以认可,则违背中国提倡的拾金不昧等道德行为准则。其二,无主动产先占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对原权利人权利的一种侵害,也不利于中国竭力扩张国家利益的倾向,物权法既有关于无主动产归属的规定,即表明其意欲通过立法阻断私人成为无主动产所有者,使国家或集体成为其当然所有者。其三,有学者认为,所有权不能因先占的事实而取得,即便对自然物可先占取得,而劳动产品所有权亦不可能先占取得[1]。持肯定观点学者则认为,无主动产先占制度设计的首要价值在于实现物之归属,诚如梅因先生所言,先占的真正基础在于此制度长期存在而发生的一种推定,每一个物件应当有一个所有人。
笔者基于三点理由,肯认先占取得无主动产。第一,不论从自然角度还是社会角度,嗣后无主财产③无主财产包括“自始无主财产”和“嗣后无主财产”两大类。自始无主的财产,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49条规定的反面解释,凡是法律未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动植物资源就不属于国家所有也不属于集体所有,这样的野生动植物即处于法律上的“无主”状态。就嗣后无主的财产而言,凡所有人不明的或经法定程序而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埋藏物、隐藏物、漂流物、无人继承的遗产等,都属于嗣后无主财产。的数量都是有增无减。如近两年内中国先后经历了汶川和玉树两次大地震,这样的天灾地变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同时,势必造成大量无主财产的出现。无主财产包括无主动产、无主不动产,而这些财产的价值都是可大可小的。传统观点认为无主财产价值不大,更多的是就无主动产而言。即便单就无主动产而言,事实也并非如此,若说无主的一只矿泉水瓶价值很小,那么同为动产而无主的一只金戒指就价值不菲。更遑论不论是无主还是有主的不动产,根本就不存在因“有主”还是“无主”的价值差别问题。第二,适用先占制度的首要前提为此财产系无主财产,既然为无主财产,侵害权利人利益之说则不攻自破。第三,立法将无主财产全纳入国家或集体所有范畴既不利于公共利益,也不利于实现物尽其用,而先占制度之确立,承认先占取得无主动产所有权,不仅可以定纷止争,同时亦可达到对物回收利用之目的,继而充分发挥物的效用[2]。有鉴于此,作为所有权制度中重要内容的先占取得不仅在域外民法中有较为详尽的规定,其在社会生活中亦是屡见不鲜。现行法未予规定是成文法与习惯的脱节,也是所有权制度不完善之体现。无主财产问题在本质上属财产法这一大的研究范畴中的所有权问题。由现行的所有权制度现状决定,我国关于无主财产归属在借鉴大多数国家二元主义的基础上应有所变通,肯认无主动产归先占人所有。
三、无主动产先占取得之规则构建
(一)先占之主体
在对先占人的范围界定前,首先应确定先占行为的性质,通过对先占行为性质的研究而解决哪些先占人能取得所有权的问题。在理论界,关于先占的法律性质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是法律行为说,既然法律要求成立先占必须以所有的意思对无主动产实施占有,而“所有的意思”为所有权取得之效果意思。笔者认为,法律行为说将“先占人所有的意思”与“效果意思”进行了混同。二是准法律行为说,先占乃“以所有意思为要素准法律行为中的非表现行为”,若具备意思表示即可对所有权进行确认。但准法律行为说忽略了大量没有意思表示而先占的事实。三是,事实行为说,所有的意思并非是效果意思,而是事实上完全支配管领意思,行为人基于对无主动产占有的事实而获得法律保护继而实现所有权取得之效果[2]381。通说认为,先占法律性质为事实行为,先占取得无主动产是通过先占的事实实现对所有权的取得,其与取得时效中所有的意思一样,是事实上管领支配之意思,尽管要求“以所有的意思”占有标的物,但并未要求将此意思表示于外,不要求先占主体具有行为能力。
笔者认为,与社会公共利益无紧密联系的无主动产,一般民事主体可以先占取得,鉴于先占行为是事实行为,无论主体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是否被剥夺人身自由或政治权利,皆可成为先占人。详言之,根据无主动产是否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联系而进行细分,立法应肯认一般民事主体先占取得与社会公共利益无紧密联系的无主动产;但不能先占取得与社会公共利益存在紧密联系的无主动产,但立法对占有人的权利予以充分保障,尽管其不能取得所有权,国家会以一定的对价进行赎买。如此规定既调动一般民事主体积极保护无主动产的积极性,同时亦避免因无人管理无主动产造成的资源浪费。
(二)先占之对象
无主动产存在已从习惯法层面得到证成,但应以当前制定法中关于动产归属之规定为进路判定先占人先占的对象。易言之,在制定法的框架中运用解释性技术寻找空间。我国立法尽管没有明定国家取得无主不动产所有权,鉴于我国实行“不动产尤其是土地”以国家和集体享有所有权为基础,足见其否认一般民事主体先占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因此,将先占的对象限定为动产。
详言之,对于自始未设定权利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在对《物权法》及《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条和第3条进行反面解释得出,凡是属于非珍贵非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并非有益的,无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不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既不属于公有,那就代表可以私有,鉴于私有的主体是多数主体,在未对此动产归属作出明确界定前,在法律上这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处于“无主”状态,可以成为“先占”的对象。确定上述归属实行先占自由主义即谁先基于所有的意思实行占有就承认其取得所有权,世界各国以及我国理论界对于自始无主的动植物资源通常承认先占取得。以上是从立法层面可以推出自始未设定权利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可以先占取得。从现实层面而言,在我国,尽管国家和集体享有土地所有权,但生活在国有或集体土地周围的人们生存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供给。概言之,可以先占取得的自始无主动产主要是指野生动植物资源。嗣后无主动产除了抛弃物外,还包括所有权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漂流物、无人认领的遗失物等。下文将在先占自由主义框架下“对典型无主动产归属之规则构建”进行详细阐述。
1.自始无主的野生动植物、抛弃物、捕获的野生动物或驯服的野生动物恢复自然状态后、逃出蜂箱的蜜蜂在其恢复自然状态后,归先占人所有①对于此条归属之设计主要参见罗马法,在罗马法中,野生动物、敌人的物品、海洋中产生的岛屿皆可以归先占人所有。。
2.所有权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属之确定[3]。发现人在自己所有的财产中发现埋藏物、隐藏物,则埋藏物、隐藏物的所有权归发现人自己所有;若发现人在他人所有的财产中发现埋藏物、隐藏物,可以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处理,公安等有关部门收到后应发出6个月的招领公告。在招领期限内有权利人前来认领,不论埋藏物、隐藏物是否具有文物价值,都应扣除必要保管费用后归权利人所有;在招领期限内无权利人前来认领,埋藏物、隐藏物如果具有特殊价值主要是指文物价值,《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则发现者不能基于先占取得,在扣除必要保管费用后由国家取得所有权,但发现人可以获得相应奖金;无人认领的埋藏物、隐藏物如不具有特殊价值,在扣除必要保管费用后由发现人基于先占取得1/2埋藏物隐藏物的价值,剩下1/2价值归财产所有权人所有②此条归属之设计主要参见域外法以及我国古代立法之规定。如《法国民法典》于其第716条对埋藏物进行立法解释,隐匿或是埋藏之物件,在无法证明其所有者且属于偶然发现之物,若在自己所有之土地内发现的埋藏物则归发现人,此时发现人与土地所有者乃同一人;若在他人所有土地内发现埋藏物,则发现人与土地所有者各取半数。《意大利民法典》传承了古罗马法的使命于其第832条在对埋藏物进行定义的同时亦确定了所有权人不明埋藏物的归属,在自己所有土地内发现埋藏物归自己所有,在别人所有土地内发现埋藏物,土地所有者与发现者各取一半。若埋藏物发现于他人所有动产中亦适用上述规定。此外《瑞士民法典》于其第724条对于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物或自然物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即由发现地的州取得所有权。不仅域外立法对所有权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属作出了明确规定,我国古代也殊途同归地作出了相似规定。《唐律疏议·杂律》中规定,在他人土地内发现宿藏物,按照规定应当与土地所有者各取一半,不送还给土地所有者即自己藏匿起来企图独占的,构成犯罪。足见,域外法与我国唐律中关于埋藏物归属之确定有异曲同工之效。但遗憾的是,我国现行法未传承此种归属确定之方式,而将所有权人不明的或经法定程序无人认领的埋藏物、隐藏物一律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对此很多学者不敢苟同,不论是柳经纬教授所言,倘若国家成为无主动产的当然所有者,那么拾荒者每天从事活动都是对国家动产的侵占;抑或是李显东教授主张,对于类似挖奇石或采蘑菇,并没有听说国家取得这些物品的所有权。有鉴于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在对无人认领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属进行设计时应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并结合国情确定无人认领埋藏物、隐藏物归属之应有规则。。
3.无人认领遗失物归属之确定。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后可以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处理,公安等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后可以发出6个月的招领公告或者在当地广泛流通的报纸上发出3次寻找失主的公告,每次间隔时间为30天,对于价值不超过100元的遗失物只需公告1次。倘若遗失物具有易腐易坏或保管费用昂贵的特性,拾得人可以在向公安等有关部门报告后进行公开拍卖并由公安等有关部门对拍卖所得的价金进行公告,招领公告应当载明遗失物的数量、种类、拾得日期、拾得地点,在招领公告期限内或自报纸上最后发出公告起3个月内无权利人前来认领的,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则于期限届满时由拾得人在支付公安等有关部门必要保管费用后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或是拾得人亦可以主张对遗失物进行拍卖并在扣除必要保管费用后获得剩余的价金。倘若依照上述规定有权获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拾得人向公安等有关部门表示放弃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在招领公告期届满或自最后公告之日起3个月届满为起点2年内没有主张权利的,遗失物的所有权抑或拍卖所得的价金由国家取得③此条归属之设计主要参见我国古代法关于无人认领遗失物归属之规定。遗失物并非无主动产,但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属于嗣后无主动产,归属问题历朝历代不论是推行法治抑或德治皆对此进行了规定。从最早西周、秦汉时期的“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发展到以晋代为起点直至元代的“拾得人仅负有还主交公的义务且拾得人不能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再从元代的规定继而演变成明清律典中规定的“在公示期限届满拾得人按先占原则取得所有权”。引起这一系列变化之原因,第一次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第二次则是伴随着私权观念的发达。尽管后来清廷在受日耳曼法影响之下被迫进行法律的修订,却殊途同归地做出与明清律法相吻合的规定。可惜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并未延续此历史发展之脉络,在民法典的起草中乃至后来的《民法通则》《物权法》皆似乎回归到了晋代关于无人认领遗失物归属之规定,即对于公示期限届满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属做出收归国家所有的规定。但笔者认为,不论是明清律典抑或是德日民法典皆殊途同归地肯认,公示期限届满无人认领时拾得人可以按照先占原则取得遗失物所有权,对此就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巧合。之所以作出相同规定其背后一定暗藏合理之处。。
(三)先占之构成要件
立法对与社会公共利益无紧密联系的无主动产采“先占自由主义”,就应明晰先占人取得所有权的条件,即先占取得的构成要件。在参考域外法即日、德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无主动产先占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首先,先占的主观要件是指先占人需要以所有的意思实施占有。先占人是否为所有意思的判断标准,可综合考虑先占人对无主动产实际管领状态同时结合心理因素、先占对象等内容进行判断。诚如王利明与梁慧星教授认为无主财产的先占应当是基于所有的意思而先于他人占有,若非基于所有的意思占有则不能取得所有权。其次,先占的客观要件包括标的物为“非法律禁止先占的无主动产”、不对他人独占先占权构成侵犯。并非所有无主动产皆可先占取得,若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立法否认一般民事主体先占取得,不仅先占行为无效,还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此外,一些无主动产尽管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但因属于立法明定禁止先占之财产,亦被排除先占的行列。
“法律禁止先占之物”具体包括:
1.立法明定为国家所有的动产。如环境保护法或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禁止采集或捕获的植物、动物;公共设施;文物保护法禁止流通的、具有考古或其他研究价值的文物;具有研究价值的陨石。
2.自然人的尸体。按照社会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并参照现代民法相关规定,自然人的尸体不能作为先占客体,其所有权原则上应由其亲属取得。对于被人抛弃或是无人认领的尸体,国家应该按照符合公序良俗的方式妥善处理,此外自然人的器官亦同。对于近亲属不明或不存在的无主尸体,所有权可例外归“公”,但绝不能基于先占取得,这主要是基于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考量,使善良民族传统得到传承。若不确定无主尸体归属,则有伤社会风化,同时也构成对善良习俗的破坏,更为严重的是会扰乱社会秩序。综上,对无法确定所有者的尸体可比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无主财产认领之规定,由公安机关先行侦查并发布认尸公告,在侦查结束后公告期间届满时,仍无人认领的尸体,直接按照殡葬制度由侦查机关交给民政部门火化处理。
3.法律明定禁止公民持有或流通的动产。
笔者认为,不可先占取得的无主动产,除包括上述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抑或立法明定禁止先占之动产外,还应包括无人承受的动产遗产。此类继承人不确定的动产遗产需要在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申请后,在公告期届满无人认领情形下才能将其认定为无主财产并判决确定归属。在确定归属时,若按一般无主动产归属确定原则实行先占自由主义,由利害关系人包括被继承人生前所在的单位、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抑或债权人等取得所有权,不仅无法理依据而且此种归属之确定会导致更多人为取得无人承受遗产所有权纷纷以利害关系的身份向法院提出申请,不仅造成司法资源浪费,亦会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之维系。有鉴于此,对此类特殊无主动产归属之确定既不实行先占自由主义也不实行国家先占主义,而是对无人承受的动产遗产与无主不动产一样由法院判归公,此无主财产将被无主财产公益基金进行托管,并服务于公益事业。
[1]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3.
[2]钱明星.物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82.
[3]荀峰.村民发现埋藏乌木相关法律问题探讨[J].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12,(78):98.
〔责任编辑:张 毫〕
D923.2
A
1000-8284(2015)01-0100-05
2014-01-10
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2015lslktzdian-23)
李迪昕(1984-),女,辽宁沈阳人,讲师,博士,从事中国民法学、外国民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