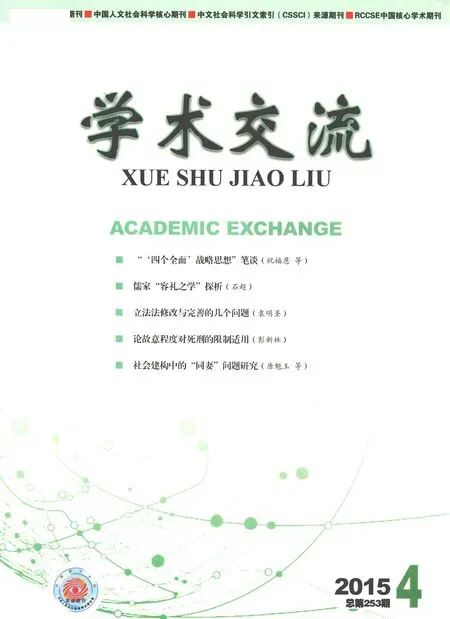自我与他者的跨文化认知
——论史景迁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2015-02-25谭旭虎
谭旭虎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上海 200030)
自我与他者的跨文化认知
——论史景迁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谭旭虎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上海 200030)
中西文化交流一直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研究重点,这部分内容在他的中国研究中不仅占据了很大比重,同时也是其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史景迁通过对跨越中西文化的个案及群体分析,试图重构多个世纪以来两种文化间的历史交流与碰撞。通过考察史景迁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我们既能对其中国研究有更全面的认识,同时亦能获取对当代历史文化语境中文化交互的有益启示与经验。
史景迁;跨文化认知;中西文化交流
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价值传递及相互间的跨文化认知既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也是对异质文化交互会通的探索。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不仅认为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线索”,更“花了40多年的时间用不同的方式探索着这一主题”[1]。学者朱政惠也曾评论史景迁“对中外文化密切交流和促进这种交流的期待是非常真诚的,胸襟可谓博大”[2]。但目前学界对史景迁的这一重要研究内容往往泛泛提及,并未作出整体分析与深入探索。本文拟对史景迁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作以具体分析,一方面厘清史景迁对中国研究的全貌,另一方面也借此深入探索其研究对于当下历史语境中异质文化交互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西游:困惑与疯癫
黄嘉略与胡若望是两位18世纪前往欧洲的中国人,而他们也成为史景迁中西文化交流与研究视野中的“西游”先行者。黄嘉略是有历史记载最早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之一,史景迁对黄嘉略的开拓性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均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特别指出:黄嘉略与弗莱雷(Nicolas Fréret)、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等法国汉学奠基人在历史、语言、哲学等一系列方面展开合作,并取得了可观进展,对法国汉学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黄嘉略还成为当时巴黎社会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大部分人都想从黄嘉略那里了解有关他祖国的信息”[3]18。其中甚至包括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我们知道,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从亚洲人视角来观照欧洲的著作。史景迁认为,尽管该书是通过“波斯人”之眼进行的文化观察,但黄嘉略至少是那个波斯质询者的原型之一,他向孟德斯鸠提出的种种看似天真的问题,将欧洲的虚饰与做作揭露得淋漓尽致。史景迁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有关中国的论述也给予了细致考察。他认为孟德斯鸠重新审视了耶稣会士的资料,从全新的角度作出了具有世界视野的分析,在他的分析中,中国被首次放置在了否定的一面[4]48-51。史景迁指出,在孟德斯鸠命名为“地理学”的读书笔记中,与黄嘉略的谈话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不难推断黄嘉略在孟德斯鸠对中国的思考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3]18。总体来说,对黄嘉略的勇气与开拓精神,以及他为中法文化交流带来的实质进展,史景迁对他均持有肯定立场。在他看来,黄嘉略不但富于冒险精神,而且聪敏、勤奋、诚恳,在面对接踵而至的困难时具有极大的耐力与坚持[3]18。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尽管这场早期文化交往看上去卓有成效,然而史景迁对黄嘉略的叙事基调却笼罩着凄惨与悲悯,灰暗的基调从开局贯穿至收梢,给受众留下了一种压抑、困厄之感:“黄嘉略曾经热切寄望他的女儿玛丽能够活下去,替他实现沟通融合中法文化,增进双方彼此了解的梦想。但就在他去世后几个月,女儿也死了。黄嘉略所梦想的中西交流新纪元就像夜空中一点闪烁的微光,也随之熄灭。”[3]24黄嘉略在巴黎短暂困顿的一生都在试图让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国,但他的努力在史景迁的叙事中指向了一种徒劳而悲凄的结局。不仅如此,史景迁对异质文化之间是否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也表示出疑虑,他认为孟德斯鸠在“地理学”读书笔记中流露出了更真实的想法:“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中国人。”[3]20
史景迁所关注的另一“西游”先行者胡若望则传达出异质文化彼此认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极大“困惑”。胡若望是广州圣公会的看门人,略通文墨,1722年跟随著名传教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前往法国担任中文文书工作。到欧洲后,胡若望却表现出“疯癫”的言行举止:他对出现在身边的任何女性都极端反感,他自制小鼓和旗帜,上书“男女有别”,在巴黎大街上用汉语宣讲其道德价值观,而他本该为神父做的文书工作却毫无进展。傅圣泽一筹莫展,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这个中国人已经坠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失衡状态。”[5]100而后胡若望被送往沙琅东(Charenton)精神病收容所,被关押近两年后才释放归国。有论者认为胡若望的怪异行径是由东方人的文化适应与胡若望自身天主教信仰的奇异混合所致[6]。有的论者则将胡若望的混乱归因于环境的复杂变化导致精神紧张,而语言上的无法正常交流又使其紧张加剧,于是日益失去自制[7]。史景迁对此则表现出一种不置可否的暧昧态度:“没有人真的知道胡若望是疯子还是正常人。”[5]116-117福柯将人们对疯癫的接受划分为三个阶段:中世纪末至文艺复兴时期(15—16世纪)、古典时期(17—18世纪)、现代时期(19——20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用“疯人船”放逐疯人,在这一时期,疯癫甚至带有浪漫和神圣化的味道。但到了古典时期,如监牢一般的精神病院取代了“疯人船”,疯癫成了栅栏后的展示对象,受到理性的监督。疯癫和非理性在经过了一系列异化程序之后,被视作“社会的他者”被圈禁起来。疯癫在此时甚至开始具备演出与展示的特征:就在关押胡若望的沙琅东收容所,曾经组织过一些著名的疯人表演,疯子不但是演员而且也是观众,疯癫成为了一种景观,成为了理性世界的一种消遣[8]。实际上在进入沙琅东之前,胡若望就已经成为了巴黎的景观:“他摆姿势,扮小丑,唱圣歌……怪诞的、异国的、混乱颠倒的人物被人群包围着,欢呼着,叫喊着,大笑着。”[5]96不同文化体系均有各自界定客体对象的方式,对那些无法嵌入到正常分类秩序中的人或物,文化主体则往往将之界定为异类,并予以排斥。胡若望即是这样一个无法嵌入异质文化分类图式的极端案例,他无法获得异质文化的认同并取得合法的文化身份,因而被排除出了正常的社会体系之外。胡若望与黄嘉略这两个“西游”先行者在史景迁那里呈现出了相似的叙事逻辑,他们的历史经历“给人的印象是,到西方去的中国人注定是要失败的”[7]。
二、东行:改变中国的个体与群像
相对于东方文化对西方的渗透,史景迁更注重探讨西方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中西交流史上的先驱利玛窦成为史景迁选择进行微观探索的个体,而16位自1620至1960年代陆续来到中国,在各个领域内发挥着影响力的西方顾问则是他选择进行宏观把握的群像。
相对其他学者,史景迁研究视野中的利玛窦呈现出一种全球史视野与特殊历史叙述方式的精妙结合。史景迁将利玛窦放置于16世纪晚期航海大发现后欧洲殖民扩张及反宗教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这样才能使利玛窦的意义得以凸显。史景迁并没有详尽地探讨利玛窦究竟是如何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调和与适应的,他更关注的是利玛窦文化适应策略背后是如何受到其西方文化源流的影响。史景迁将自己从编年式的传统历史叙事方式中解放出来,在16世纪的全球图景中自由穿梭,我们看到的不是按线性时序呈现的利玛窦,而是一个与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反宗教改革等西方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丰富历史人物。叙事焦点在中西之间、历史背景与个人事件之间来回切换:“史景迁将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与因素并置在一起,使得它们令人信服地汇聚起来。”[9]不仅如此,相较于其他对利玛窦的研究,史景迁所揭示的利玛窦去除了许多宏大叙事的外衣,呈现出非常人性化的一面。利玛窦对传教事业虽然信念坚定,但对于困境同样敏感、迷茫,更多的时候,在异乡经常充满敌意与戒备的环境中,他充满了失败与挫折感,而且不得不孤独地承受,这也导致他对中国的看法充满了矛盾与暧昧。史景迁非常赞赏利玛窦取得的历史成就及其个人的卓越品质:“利玛窦不是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但他当之无愧是最有智慧的文化交流使者。”[4]17但史景迁的利玛窦叙事仍然体现出多多少少的悲观倾向,这种悲观常常以种种隐喻式细节得以表现:利玛窦刚到韶州就遭遇中国人的暴力袭击,留下了终身腿伤,“只要他一走远路,伤痛就会折磨着他,使他只能跛行”[10]58。在私人通信中,利玛窦流露出绝望、消沉的情绪。他称中国为“贫瘠之地”,而他在中国人之间的感受则是“被抛弃”或“被放逐”[10]56。在史景迁看来,无论利玛窦怎样努力地将基督教与儒家、古罗马与明代中国进行调和,如果他传教的终极目的收效甚微,那么利玛窦的挫败感就不可避免:“在利玛窦表面的成功和日益深化的投入之下,实际潜藏着巨大的个人痛苦与精神烦恼。”[3]47
自1620至1960年代相继来到中国的16位西方顾问是史景迁在《改变中国——中国的西方顾问》一书中聚焦的“东行者”群像。这场持续数个世纪的“改变中国”进程涉及了宗教、经济、教育、医学、军事等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经历着类似的激动与危险,怀抱着同样的希望,也学会了承受同样的失望与挫败。”[11]Introduction16位西方顾问在改变中国的方式策略上各不相同,但史景迁认为他们在中国的历史经验均包含着各种危机:
首先是技术本身带来的危机。在史景迁看来,技术对西方顾问来说如同双刃剑,既是有利工具,也是最大障碍。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寄望用天文数理等近代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高层统治者,达到从上而下“改变中国”的目的。但史景迁认为他们只是被中国宫廷当作技术工匠使用,即使受到上层喜爱,中国的皈依也依然遥不可及:“作为天文官员的汤若望将他作为一名上帝使者的身份挤到了一旁。”[11]2219世纪基督教福音派教士伯驾(Peter Parker)选择用医学技术接近中国,但繁重忙碌的医务工作也极大地阻碍了伯驾的“灵魂工程”:“伯驾试图让中国通过上帝的荣光而获得自由,结果最终反被他自己的技术所奴役,并不可抑制地遭受到他本意眷爱的人民的怨怒。”[11]56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等人也都是由于对中国有着特定技术价值而进入中国历史,他们大多数最终均被自己的“技术”所淹没,而他们所预期的实质性转变并未发生。
其次是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与赫德(Robert Hart)作为被中国政府雇佣管理海关的西方人,在史景迁看来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危机:“李泰国究竟代表谁?或者说,他认为他代表谁?”[11]103史景迁认为李泰国所扮演的角色之间包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的外国雇员,体验着中国安抚远夷的做法,同时又遭受着来自英国的批评,认为他执行海关法规过于严苛,“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李泰国的继任者赫德虽然在很多方面吸取了李泰国的教训,但同样被英国认为他在帮助中国危害英国利益;而中国方面也对他抱有怀疑:“他是一个处在两种文明夹缝之间的人,他必须做出平衡,使两方面在他的思想中都保持恰当的关系。”[11]120尽管赫德权重一时,但史景迁并不认为他比其他西方顾问更成功,他所做的努力却并未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基础结构,多年的努力最后也毁于一旦[11]128。
史景迁将西方人“改变中国”的失败归因于其技术包装下的意识形态内核,以及过于自恃的道德优越感。西方人对其技术优势过于自信,将西方的改变理所当然地视作不可抵挡的世界潮流:“中国人反抗这一改变潮流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就如同潮汐涨落、日月光辉一般是不证自明的。”[11]292史景迁在对这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作出否定评价的同时,更冷静地作出判断:“中国从来就不是美国可以失去的,也不是天主教欧洲的,也不是英国的或者苏俄的”[11]290。史景迁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与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使得西方顾问们在改变中国的道路上屡屡受挫。
三、想象中国:被建构的形象
除了跨越中西之间的历史个体与群像外,史景迁还通过《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一书讨论了13至20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建构主题。在他看来,西方对中国的种种认知与考量均可用“观测”(sighting)一词加以描述和概括。史景迁共选择了从1253至1985年间48种包括历史、文学文本在内各种形态的中国“观测”,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到过中国,与中国有过真实交往经历的西方探险者、军人、传教士等人群的写实性“观测”,如马可波罗、利玛窦、马嘎尔尼、尼克松、斯诺等;第二类是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中对中国的虚构类“观测”,如庞德的诗歌,福楼拜、杰克伦敦、卡夫卡、卡尔维诺的小说,奥尼尔的戏剧及一些西方电影中的中国呈现等;第三类则是西方思想者、理论家们对中国所作的体系化价值评判,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以及韦伯、亚当斯密、魏特夫等人对中国的理论判断类“观测”。
通过对以上三类“观测”的分析,史景迁指出,西方的中国形象认知与建构始终包含着相互矛盾、复杂多样的观点与看法,时而是真实知识与回忆,时而是漫无边际的想象与虚构。重要的是,这种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交织纠葛、缠杂含混,正如史景迁所说:“我们很难搞清楚真实和虚构是在哪里混淆起来的,又是在哪里分离开来的。”[4]56而且,中国在西方的影响力与西方人实际的中国经验或原本事实之间也并无必然联系[12]xiii。中国不过是西方用于反视、思考自身的文化参照物,西方在中国发现的客观真实有多少,他们所虚构出来的发现就有多少[13]。这种真幻层叠交错的奇特认知方式也正是西方在建构中国形象以及文化“他性”(otherness)时的重要特点之一。同时,史景迁指出西方对中国“他性”建构呈现的另一大特点是对“他者”奇观化的期待与欣赏,如西方对所谓“异国情调”(exoticism)的追寻与猎奇正是绝佳例证。法国文学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作品在史景迁看来无疑最能体现19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中国情调特质。史景迁挑选了谢阁兰在小说《雷奈利》(RenéLeys)中对一位东方侍妾的外貌描绘,认为这就体现出了典型白人男性凝视视角之下对东方女性的呈现,而作品中刻意使用许多省略号来断句的写作方式则营造出一种夏日夜晚般的“中国风情”。事实上,正如有论者所分析的,这种富含性意味的“中国情调”正是文学作品中帝国主义叙事的体现,东方被表征为女性,是阴性、芬芳、衰颓和过于成熟的,而西方则被表征为男性,是统治的、具有男子气和刚猛的[14]。对“中国情调”的猎奇式心态背后是西方对于中国文化一整套定型化、程式化的努力,是西方根据自身需要而不断创造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而其本质则是用刻板、抽象化的概念与形象掩盖民族国家与文化的真实特质。
美国学者哈罗德(Harold Isaacs)曾在20世纪50年代用访谈形式对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认知与情感倾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的中国认知呈现出自相矛盾、甚至彼此对立的复杂面貌,有时候中国是世外桃源般令人倾羡的国度,中国人被视作优等民族,有着众多先贤哲人,中国人民也勤劳勇敢、受人敬重;而有时中国则如同人间地狱而令人生畏,人民是野蛮无情、阴险狡诈的,统治者则都是虐待狂和刽子手[15]。史景迁在《大汗之国》中所提供的48种中国“观测”与哈罗德的调查结果几乎一致,西方认知建构的中国形象如同钟摆一般在正面积极和负面否定间来回摆动,相互矛盾的对立观点常常混杂纠葛,呈现出复杂多样、难以界定的面貌,且随着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而凸显出不同侧面,如同舞台上的光线,人们只关注光线所及之处。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之所以与中国的真实历史进程相关甚少,史景迁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大部分时候西方都是为了解决自己内部的文化需要和问题而“观测”中国、理解中国,是为了平衡自身文化内部话语权的矛盾而刻意找寻的镜像参照物[4]144-145。学者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也认为: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现实并无关联,它只与那些将中国视作一个大的文化“他者”的声称相关。而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中国形象也都是与西方主流权威观念以及当时的政府需求相一致,而不是相反[16]。这也正是史景迁所说的“文化利用”(culture use)问题,中国作为巨大的文化“他者”,成为了西方批判、反观、思考自身文化的重要参照物:“中国如此遥远,与西方的差异如此巨大,它最大的作用就在于让西方在其身上投射自身的所有想象。”[14]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的中国形象如同“变色龙”一般闪烁跳跃、矛盾极端。因为这条“变色龙”无论鲜明还是黯淡,都并不是指向中国本身,而是指向西方的问题与需要。中国已成了西方反观审视自身的文化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与早期在胡若望、黄嘉略、利玛窦历史叙事上体现出的悲观倾向不同,史景迁在《大汗之国》中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谨慎乐观,以及对异质文化间最终能够达成彼此理解的信念:尽管早期的中国“观测”常常视野模糊、晦暗不明,且与真实相去甚远,并常常因外界影响发生偏差误读,但“观测”中国依然值得尝试[12]xviii。
四、结论
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是史景迁最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当被问及不同文化、文明之间如何达成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沟通时,史景迁笑言:“我一生的工作都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17]不论是对胡若望、黄嘉略、利玛窦这样具有中西交汇历史经验的个体考察,还是《改变中国》中对怀有激情与向往的西方顾问群像呈现,以及《大汗之国》中西方对中国整体视野下的文化态度审视,史景迁的目标都是希望获取有益于当下异质文化间沟通交往的思路与启示。
对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史景迁起初表现得并不乐观,命定般的挫败与沮丧在《改变中国》的16位西方顾问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黄嘉略、利玛窦尽管取得了沟通中西文化的辉煌成就,却也都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中陷入窘境,胡若望更是被异质文化定义为“疯癫”而直接排除于体系之外。但到了写作于90年代的《大汗之国》中,史景迁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转变,他开始流露出审慎的乐观,以及对中西之间和谐共处、相互补益的信心。这显然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具体历史语境的发展演进,异质文化间不断增长的交互会通密切相关。当时间来到21世纪,史景迁则从审慎乐观走向了对异质文化间智识、思想交汇的积极正面倡导。2010年,史景迁获得美国联邦政府颁发的人文学科最高荣誉“杰斐逊讲席”,而史景迁为此作的演讲正是以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为主题。史景迁指出,17世纪的中国人沈福宗在欧洲与英国科学家海德(Thomas Hyde)及波义耳(Robert Boyle)之间的文化碰撞、学术交流体现出了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交流概念,是真正的“思想交汇”(meeting of minds),而这种异质文化间的“思想交汇”则正是当下我们需要不断追寻并加以实践的,因为“思想交汇的理念能够成为探索与改变的真正动力,同时也是文化间和谐与适应的驱动力量”[18]。不仅如此,针对西方在与中国的现实文化交往中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价值观强加于中国的做法,史景迁表示出明确的反对,他指出这样的做法很多时候是西方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这样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实际上是用国际压力试图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价值体系,而达不到真正的文化交汇目的[1]。
史景迁自身对中西文化交流从悲观走向积极乐观的转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异质文化间相互审视、参照的正面范例,他的研究经历与情感态度转变让我们确信,当异质文化彼此间思想、智识的交汇变得日益频繁深入的时候,“会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小”[19],一种积极、正面的异质文化间互动关系终将得以建立。
[1]Jim Leach.The China Scholar[J].Humanities,2012,31(3):11-13,50-54.
[2]朱政惠.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在耶鲁大学拜访史景迁教授[J].探索与争鸣,2004,(5):8-10.
[3]Jonathan Spence.Chinese Roundabout: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M].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2.
[4][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Jonathan Spence.The Question of Hu[M].New York:Vintage,1988.
[6]John Updike.Chinese Disharmonies[J].New Yorker,1989,65(7):109-115.
[7]Nicolas Standaert.Review the Question of Hu[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0,49(1):136-137.
[8][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林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19.
[9]Timothy Brook.Review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6,45(4):831-833.
[10]Jonathan Spence.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M].New York:Viking Penguin,1984.
[11]Jonathan Spence.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M].3rd ed.New York:Penguin Books,2002.
[12]Jonathan Spence.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China in Western Minds[M].New York:W.W.Norton &Company,1998.
[13]Jonathan Porter.Asia[J].History:Reviews of New Books,1999,27(3):133-134.
[14]Ian Buruma.Two Cheers for Orientalism[J].The New Republic,1999,221(1/2):29-32.
[15][美]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M].于殿利,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43.
[16]Colin 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M].Oxford:Oxford Univ Press,1989:263.
[17]张润芝.史景迁:中国近代史课本不该从屈辱开始[N].时代周报,2011-12-01.
[18]Jonathan Spence.When Minds Met: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EB/OL].http://www.neh.gov/about/awards/jefferson-lecture/jonathan-spence-lecture,2010-05-20.
[19]李宇宏.读懂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3.
〔责任编辑:崔家善 李彬琳〕
K207.8;G115
A
1000-8284(2015)04-0214-05
2015-03-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史景迁的中国形象研究”(11CZW04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比较文化视野下的史景迁研究”(10YJC751078)
谭旭虎(1980-),女,湖南湘潭人,讲师,博士,从事跨文化传播与国际汉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