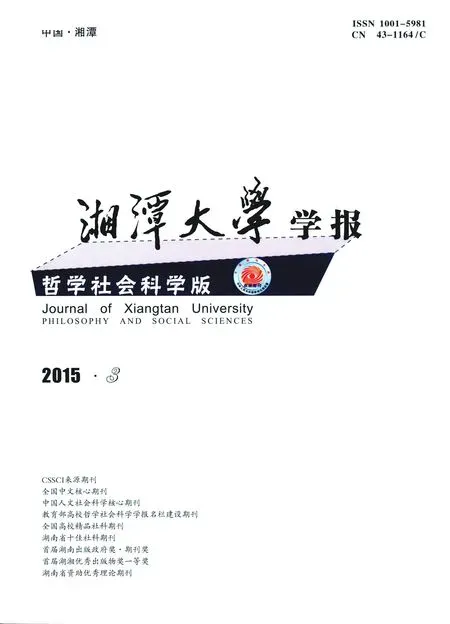彩礼返还纠纷司法裁判的“法”与“理”*
2015-02-23黄小筝
黄小筝
(1.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2.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彩礼返还纠纷司法裁判的“法”与“理”*
黄小筝
(1.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2.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我国当前彩礼返还纠纷司法裁判的混乱、同案异判等现象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作为裁判“法据”的彩礼返还法律规则粗糙含混,与民间习俗不一致。法官不得不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作为裁判“理据”的法律原则。但因为法官对各法律原则的理解与优位排序不同,又因为与彩礼密切相关的婚约制度的缺位,法官常在裁判中加入诸多权衡,从而加剧了彩礼返还纠纷裁判依据不明、裁判尺度不一的现象。应重建婚约制度,特别是婚约解除损害赔偿制度。
彩礼返还纠纷;司法裁判;婚约制度
我国彩礼返还司法裁判同案异判的现象常见不鲜,彩礼返还的比例从完全不返还至返还100%不等;甚至同一法院同一法庭的判决也出现相差悬殊的返还比例,如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2001年以来,判决返还礼金最低的比例为32%,最高的比例为100%,判决返还彩礼的比例相差68%。[1]16彩礼返还裁判司法主观主义严重,常示人以“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之直观印象,甚至被指为“法官之治”。彩礼返还纠纷司法裁判混乱、同案异判、上诉多、执行难等现象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彩礼返还纠纷的法律问题兼跨实体与程序,司法裁判中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应否返还,返还内容、范围和比例的确定,以及诉讼主体、诉讼时效的程序设计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如何界定“彩礼”,即涉诉财物的性质、返还的根据与基础。但是,目前我国彩礼返还纠纷裁判的法律规则粗略含混,与民间习俗也极不一致。
(一)“彩礼”的界定语焉不详
2004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法释二”)第10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按照此规定,立法者处理彩礼问题的基本思路显然是以是否登记结婚,即所诉争之财物是否基于婚姻目的而发生并且是否将婚姻目的落到实处作为彩礼返还规则。
按照法释二第10条第一句话的字面意思,即“按照习俗给付的”才能成为彩礼,才能成为返还之诉的对象根据。那么,究竟是以当地是否存在订婚送彩礼的习俗,还是以涉诉财物是否基于婚姻目的而赠与为界定彩礼的标准呢?有学者专家指出: “关于两者的区分,《解释(二)》未作说明,按照最高法院对该条的阐释,要看当事人所在地有无给付彩礼的风俗,如果有,那么一方婚前给付另一方的财物可以认定为彩礼,在满足《解释(二)》第10条规定的三种情形时可以要求返还。至于没有这种风俗的地方,以防止那些本来没有彩礼风俗,自愿给付对方财物的人也以此条为依据起诉要求返还财物。”从这一角度而言,要牢牢地把本地区是否有此种风俗习惯作为能否认定给付具有彩礼性质的根本、重要的判断标准。
但是,审判实务却非如此。2014年2月初,某电视相亲节目男嘉宾诉女嘉宾返还宝马车一案中,被告女嘉宾在答辩状中就是如此论辩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彩礼应当严格限制在按照当地习俗给付的彩礼,彩礼的受益人应当是女方的父母,而北京是大都市,没有婚前给付彩礼的习俗,宝马车并非彩礼。并且,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属于限制婚姻自主权,在法律上不受保护。”[2]而一审法院却将判断标准聚焦于赠与是否基于结婚之目的,而非当地是否存在结婚赠送彩礼的习俗。“节目本身系为男女双方寻求合适的结婚对象而举办的电视栏目,节目的参加者一般都抱着成就姻缘的心态,原告与被告在参加此节目期间相识,并很快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可以表明双方交往之初具有缔结婚姻的意图——双方在确立恋爱关系后很快表露出缔结婚姻的意愿。在此基础上,原告通过其母汇款为被告出资购买近三十万元的宝马车,应属贵重物品,与在恋爱期间的男女朋友为促进情感、表达心意而赠送的一般性礼物是有区别的,结合中国传统的习俗、现代社会的人情因素以及宝马车的价值等综合分析,此宝马车具备彩礼性质。”[2]
那么,到底如何界定诉争财物是否属于“彩礼”?仅按风俗给付的才是彩礼?或者只要男女双方是基于婚姻目的赠受的就属于彩礼?此外,还有按财物的贵重程度、赠受的时间等标准界定彩礼,即价值高的才是彩礼,或者登记结婚前给付的才是彩礼。总之,对“彩礼”的界定语焉不详,所诉争的财物是否应该返还就难以把握,彩礼返还的条件、内容、范围、比例也就无法确定。
(二)彩礼的法律性质定性不清
学界目前对彩礼的法律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为一般赠与说。即婚约完全是男女双方的意思自治,赠与物一旦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赠与人不得以婚约解除为由请求返还财物。二为附条件的赠与说。反对将彩礼视为附条件之赠与的论者认为,彩礼所附条件使受赠人产生结婚义务负担,有悖婚姻自由理念,并助长借婚姻索取财物之不良风气。然而,民事法律行为所附之条件有义务与事实之分,彩礼给付所附“以后结婚”之条件并不是要求对方将来履行的“义务”,而是双方拟制的一种将来的“事实”。这种约定的结婚事件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说都只是一种期待权,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双方都不能要求对方因彩礼给付行为而把“以后结婚”当成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
最高院并没有明确支持哪一种观点,只承认彩礼的赠付,是以基于婚姻之目的。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就蕴含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如果没有结成婚,其目的落空,此时彩礼如仍归对方所有,与其当初给付时的本意明显背离。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彩礼问题的处理,一定要视双方最终的现实结果而定。法释二对彩礼的法律性质避而不谈,只规定以是否登记结婚作为是否支持返还彩礼的基本原则,使得审判实务中法官在彩礼返还的内容、范围、比例等的裁判尺度上也是各依己见,随意性很大。
(三)“共同生活”、“生活困难”等言之不确
法释二第10条规定“双方结婚后确未共同生活的”应当返还彩礼,即对 “结婚”作出了目的性扩张。按照最高院的解释,作出如此规定,是因为“给付彩礼后,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双方并未真正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对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进行保护。双方登记结婚后,在法律上已经形成合法的夫妻关系。不过,如果一直没有共同生活的话,也就没有夫妻之间相互扶助、共同生活经历。所以,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虽已成立,但实质意义上真正的共同生活还远没有开始。”[3]103这本无可厚非,因为“夫妻生活持续期间短暂,事实上的夫妻协同体没有成立,参照婚约不履行加以处理,受领方应负担返还义务”。但对于那种已经共同生活多年、形成事实夫妻协同体多年甚至已共同生育儿女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婚约当事人,法释二第10条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而此种情形,在我国当前的广大农村,恰恰是最常见不鲜的现实。
那么,何为“共同生活”?除了共同的住所易于界定与认定之外,该如何理解“夫妻”共同的性生活、共同的家庭扶助义务与精神慰藉,以及“共同生活”的时间而尚且不管证据效力与证明责任的问题?如何理解“生活困难”,是绝对困难还是相对困难?除了考虑彩礼赠与人的困难之外,是否也应考虑彩礼受赠方(实际就是女方)的物质、精神方面的困难与痛苦,如女方家庭的物质匮乏,女方因怀孕、流产、生育等所遭受的人身诘难与精神痛苦等方面。
正由于以上所述彩礼返还的法律规则,即主要以为裁判断案之“法据”的粗略含混、晦涩不明,使裁判者不得不将目光更多地转向多元宽泛的的法律原则,将其作为裁判的“理据”,“自由”地解释彩礼返还的法律规则。“当一项正式法律文献表现出可能会产生两种解释的模棱两可性和不确定性——事实往往如此——的时候”,[4]430或者当完全适用某个或某项规范性的法律规则作为司法裁判的形式依据会产生不正义、不公平的情形下,那些“上帝在创世之时就放在人们心里的正义的律法”、不言自明的正义标准、介于理性与经验之间的推理、源于事物本质性规律的法则、基于普遍正义与个体正义之间的衡平法、特定时期的公共政策、基本的道德信念、具体社会阶段的思维倾向与习惯法等体现公平正义之法律精神的非正式法律渊源,就内化到“法律原则”中,成为躲藏在“无知之幕”背后的左右裁判结果的实质依据,亦即让法官认为能够使裁判合法又合理之“理据”。
具体而言,彩礼返还纠纷裁判中法官所考量的“理据”包括公平正义、法益价值均衡、意思自治、婚姻自由、行为自负、信赖利益保护、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尊重习俗,以及是否考虑过错责任。
(一)公平正义与法益均衡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公平”是最基本的道德评价标准,是“正义”的首要之义。公平正义之理是司法活动所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是彩礼返还裁判的“总理据”。民事活动中的公平正义主要是指应当以民事法律关系人的权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以权衡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是否合理得当。在解决彩礼返还纠纷时,既应当保护彩礼赠与方的利益,又应当根据具体案情的事实和情境进行利益的平衡,权衡选择、优位排序立法目的、法律精神、原则规范等,充分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一方违反婚约毕竟会造成另一方机会丧失与可选择范围的缩小及致信赖婚约之精神上的伤害,根据特定的案情、以法律规范为基础,裁定彩礼全部返还或酌情返还,符合私法公平原则之精义。
(二)意思自治、婚姻自由、行为自负与信赖利益保护
婚姻自由、行为自负、信赖保护是意思自治的应有之义。行为人完全具有订婚与不订婚、结婚与不结婚的意思自治,当然也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订婚与恋爱不同,订婚使当事人产生很大的信赖利益,信赖“将来会结婚”,为此当事人会在财产、身体和精神等方面有更深的投入,更深入为对方贡献财产、精力、身体等。故一些执法者认为,法律对恋爱、一般的男女同居与婚约之态度应当区分开来,法律可以把恋爱、一般的男女同居而产生的赠与问题让位于道德来调整,但对婚约、对基于婚约而生的彩礼返还问题应予以规制。在婚约制度、特别是婚约解除的损害赔偿制度缺失的情形下,执法者很容易把彩礼返还当成这些问题的救济途径,在彩礼返还的裁判中权衡这些因素。不过,由于缺乏较统一明确的法律规范,即使是基于同样的司法理据,却也有可能作出相反的裁决。比如根据行为自负之理,有的法官认为订婚有可能避免了没有对象的孤独、忧虑和不安,给自己心理带来一定程度的快乐感和安定感,此可视为订婚带来的利益。婚约解除后,违约方应对受害方基于此婚约而信赖的利益,进行补偿。而有的法官则认为,不能只享受权益不付出代价,既然选择了订婚,便应为此承担婚约解除后失去所给付或所收受的彩礼与身体、声誉或精神方面的损害之风险,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婚约不同于一般的契约,结婚了尚且可以离婚,在彩礼返还纠纷裁判中加入救济甚至替代婚约解除引发的损害之考量,会削弱法律的权威、增加司法的混乱。又如,如果只强调契约的意思自治与婚姻的自由,可以订婚也可以随意毁婚而不追究其过错,那么,这并不是真正的婚姻自由。对违约者作出失去所赠或所受赠之彩礼,恰恰是对自由的适当限制,使其不得滥用自由而损害他人的自由。由此,不同的法官会结合案情作出全部返还、酌情返还、不返还的千差万别的裁决。
(三)男女平等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是男女平等原则的重要补充,是实现男女两性从法律上、形式上的平等向实际生活中的实质平等过渡的有力保障。审理彩礼返还纠纷秉持男女平等之理,这也是婚姻法男女平等原则的延伸。因此,有执法者认为,法释二规定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这一规定明显对妇女权利的保护十分不利。[5]81这种立法目的虽然考虑了广大农村举全家之力给付以结婚为目的之彩礼的现状,因而当彩礼给付之结婚目的没有达成时,应予以返还。但却忽略了另外的现实,一是在农村,订婚或举行婚礼的“仪式婚”无论是在形式效力(向邻人宣示)还是实质效力(共同生活)上,都并不逊色于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法律婚”;二是,忽视了男女两性的区别,使基于婚约而发生的同居行为、“共同生活”而导致的怀孕、流产、生育等损害由女性独自承担。这并非真正的两性平等,也并不符合公平正义之理。因此,有的法官在现行法律没有明确界定 “共同生活”的标准、过错责任等问题的情形下,各自选择其所偏好的公平正义之理,比如尊重传统习俗。
(四)尊重习俗
传统习惯认可的是男方要求解除婚约,则无权请求女方返还彩礼;如果是女家悔婚,则要退还所收受的彩礼。这种延续千百年的习惯风俗早已根深蒂固,也确实是保护妇女权益的善良风俗。并且,根据我国农村的风俗习惯,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的确定并不是完全依据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同时男女的结合是否得到了双方父母和亲属朋友的认可并举办了在一定范围内为人所知的仪式也是一种男女取得婚姻关系的方式。此种方式在广大农村地区甚至比结婚登记更深入人心。事实上我国农村大量存在着男女双方共同生活了多年而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现象,女方基于婚约与婚礼等仪式在男方外出务工时,一直在“婆家”居住、帮工、甚至已生育孩子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法院仍然不折不扣地以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彩礼返还的判断原则,这对于女方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也是不尊重传统习俗与现实情况的。
(五)过错责任
在彩礼返还问题中讨论过错责任,实质上涉及的是婚约。举凡对婚约有法律规定的国家、地区,均规定婚约赠与返还无须考虑主观过错,但在婚约制度里规定了婚约解除受害方、弱势方的救济途径。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亲属法规定,当一方无正当理由违反婚约时,应赔偿他方因此所受的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即受害方可提出精神赔偿,前提是受害方没有过失。我国的婚姻法没有关于婚约的规定,因此,对婚约解除有无主观过错便成为彩礼返还裁判中一些法官心照不宣的重要的权衡标准,倾向于救济与补偿婚约解除受害方的权益与损害。
综上,由于相关的婚约法律法规缺位,彩礼返还法律规则粗糙含混、意义模糊,并且与习俗冲突,不同法官对不同法律原则的优位排序不同,使彩礼纠纷裁判中“应否返”、“返什么”、“返多少”、“由谁返”等问题难以界定。彩礼返还纠纷司法裁判成为法官在不同的、模糊的、相互冲突的、各自偏好的法律规则与原则之间选择与权衡的过程,也是法官各依其所秉持的价值立场与公平正义之理“自由”解释法律规则的“法”“理”权衡过程。因此,实践中除了提高法官职业共同体的水平,特别是提高法律推理水平与规范“法官造法”、改进判决书的风格以充分展现法律推理过程及裁判理由之外,最根本的是应在立法上重建婚约制度,将彩礼返还纠纷纳入婚约财产纠纷规范,特别是要建立婚约解除损害赔偿制度。
[1]汤建国,高其才.习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的实践[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
[2]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朝民初字第16873号,以及起诉书、答辩书.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
[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5]李洪祥.彩礼返还之规定的社会性别分析[J].法学杂志,2005(3).
责任编辑:饶娣清
Law and Reason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Concerning Engagement Gifts Restitution
HUANG Xiao-zheng
(LawSchool,Guangxi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Naning,Guangxi530000;LawSchool,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Currently the law decides whether to return the betrothal gift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marriage is registered. There are no clarific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trothal gifts, no rules on the scope, content and amount of the restitution. The practice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tradition. Lack of regulation of engagement, the simplicity and vagueness of rules on the restitution of betrothal gifts make the judgment in this area a dialectical reasoning according to common sense and legal principle instead of law. It is very common that sometimes cases with generally same issues are decided very differently.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ules on the restitution of betrothal gifts shall be adopted as a part of engagement regime.
engagement gifts restitution; justice;engagement regime
2014-11-22
黄小筝(1980-),女,广西贵港人,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DFO-052
A
1001-5981(2015)03-00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