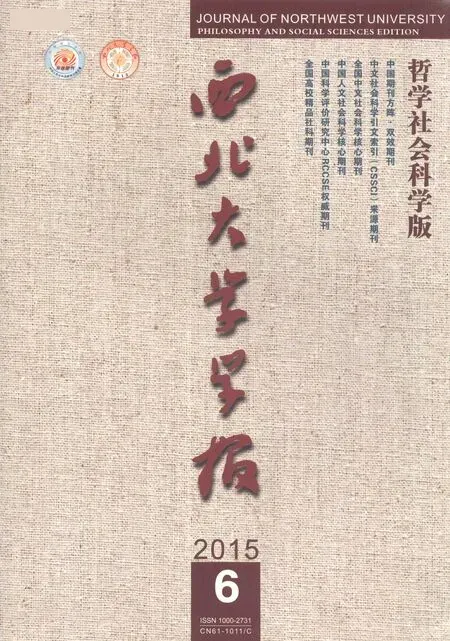近代社会中心-边缘结构视角中的异化问题
2015-02-22刘吉发
刘吉发,肖 涵
(长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近代社会中心-边缘结构视角中的异化问题
刘吉发,肖涵
(长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4)
摘要:关于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分析,学界存在着争论,却都不自觉地引向隐藏至深的社会结构问题。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在农业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哲学基元不同,近代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在组织化进程中以自我与他人异化关系为基础不断扩张。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不仅自身发生着异化——构成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且在组织结构中的扩张也带来了异化——构成承认、普遍竞争与个人认同的伪共在。如果从近代的社会结构去探寻异化的根源和土壤,不仅有助于从总体性视角理解异化问题,也有助于寻找到扬弃异化的实践途径。
关键词:中心-边缘结构;社会异化;近代社会;自我与他人;组织化
马克思(Karl Marx)对近代异化问题有着关注,后人对此的解读也络绎不绝,尤其是对马克思有关此的思考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的问题上。有人认为马克思有关异化的思考前后存在转折关系,这种观点以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批判为论据,然殊不知马克思批判和放弃的并不是对异化问题的关注,而是古典哲学中惯用的抽象方法,从而将异化问题置于现实中。还有人认为马克思有关异化的思考前后不存在转折关系,这种观点从逻辑上分析了分工与异化是否具有必然关系,无意间也触碰到现实结构的问题。我们发现异化问题的关键在于近代形成的社会结构——中心-边缘结构上,这份结构决定了异化的发生,而无关分工或者其他微观因素本身。从哲学视角可以看到这份结构以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为基础(自我在近代社会一直居于中心地位),在近代组织化过程中扩散,形成伪共在现象,可以说这份结构的形成发展就是异化发生本身,如果我们抓到这份结构并致力于解构它,异化的问题可能随之而解。当然,我们从马克思的异化分析出发引出中心-边缘结构,并不是说将这份结构追溯到马克思那里,更不是说马克思在有关异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中心-边缘结构。总之,我们希望区别于细枝末节的视角而从中心-边缘结构观察异化,这既是中心-边缘结构为异化问题提供了视角,也是说明中心-边缘结构即为异化本身,而且是动态的。
一、异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下文皆以《手稿》《形态》指代)被视为分析异化问题的理论丰碑。围绕异化问题,学界存在着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手稿》和《形态》形成的异化思想存在转折关系,另一种则认为他们之间没有转折关系。在这两种观点的分析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结构才是异化问题的关键所在,虽然他们都未自觉且深入分析。这里的社会结构就是中心-边缘结构。
第一种观点将马克思对黑格尔(Hegel)和费尔巴哈(Feuerbach)的批判视为其与分析异化问题的决裂,其实这是不成立的。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对异化的认识停留在“人自身”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即抽象人的本质去判断一切。这也是德国古典哲学惯用的伎俩——“绝对精神”,认为一切异于此的就是发生了“异化”。这种因“物质生活方式的局限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1](P29)“绝对精神”是一种以“普遍利益”形式出现的个人利益的异化。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放弃和决裂的并不是对异化的分析,而是以往对异化分析的出发点和抽象方法,也就是说人和异化都要放入现实生活、社会结构中去理解。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能因为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向分工的关注点转变就以为其思想呈现转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原因,但不能反推,即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不是互为因果,但马克思在《形态》中又提到“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原因。有人解释简单看是因为在原版著作中私有财产和私有制是同一个德文,更进一步看是存在“分工-私有制-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逻辑关系。第二种观点指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和分工与私有制的关系并不是一回事,这不能简单地归于私有财产与私有制内涵的不同,而是分工与私有制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分工所带来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异化概念的引申意义上说的,分工是否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平等是要斟酌的。那么就不能将异化劳动向分工的转变看成马克思异化思考的转折。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阐述这几方观点,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现实生活”“社会关系”,分析第二种观点中存在的一份论证方法,是想提出造成异化的不是分工或者其他因素,而是这些因素在社会结构中发生了异化,造成了社会结构本身的异化,“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实际上是人的社会空间*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存在物”和“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一来为自身而存在,二来是类存在物,前者是在自然空间中开展的,后者是在社会空间进行的,也就是张康之教授所说的“当人从纯粹自然中走出来并构成了社会的时候,社会空间也就同时生成了”。这层空间里,社会关系是基本组成部分,剩下的无论是以物化形式出现还是以心理、思想等精神形式出现的都是其中的要素。与人的分离和对立。而一切异化的消除,又都是包含在社会空间的改造过程中的”[2]。隐藏在异化背后的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中心-边缘结构。
中心-边缘结构是一个分析框架和批判工具。劳尔·普雷维什(Roal Prebish)是较早引入“中心-边缘”思想的学者(可参见1949年《拉美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一文),在拉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经历了30年代的国际经济危机阵痛后,其独立反思提出“中心-边缘”思想用以解释国际中心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揭露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存在着一个事实上不平等的结构;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可以极其轻易地把发展中国家所创造的财富窃为己有;而发达国家自身所产生的危机,也可以在这个结构中轻易地就转嫁给发展中国家”[3]。当然,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相对来说是粗糙的,主要针对经济领域并携带局限性,对“中心-边缘”结构进行更细致全面分析的是加尔通(Johan Caltung)。在加尔通这里,不仅是国际社会,一国之内照样存在“中心-边缘”结构,从而描绘了一幅“中心-边缘”结构网。
以上我们似乎发现这个社会结构是静态的而非一个行动框架,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结构的价值将不尽如人意。我们可以发掘有关中心-边缘结构的更丰富内容而不停留在加尔通那里,这首先取决于清晰了解近代社会中心-边缘结构形成的哲学基元与发展。当然,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并不能将中心-边缘结构思想溯源到马克思那里*“在马克思全部理论著述中所包含的一个基本思想内核是他的辩证法,即使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看到的也是无处不呈现着用辩证逻辑去安排经济事实的叙述方式。对于辩证法而言,普遍联系、相互影响和朝着对立面的运动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路径,或者说,辩证法是不允许在形式上做出一种静态的‘中心-边缘’划分的……当然,在辩证法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中也包含着一个历史维度,这样一来,属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因素即使共存于同一个历史断面上,代表了旧的历史时期的因素虽然还现实地存在着,却被辩证法认为是失去了历史合理性的现象,是需要加以扬弃的因素……当然,‘中心-边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也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因为包括普雷维什在内的这些来自于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受到了《资本论》的影响,而且在他们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去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国际关系时,有着明显的试图扩展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追求。”(参见张康之,张桐.论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关于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平等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04).),只是在马克思所处的以及其后所处的时代中,如今的我们都可以概括出中心-边缘结构,我们也能看到具有这个特征的社会现实——支配控制。总之,我们并不是说马克思的理论中具有甚至提出了中心-边缘结构思想,也不是想用中心-边缘结构去取代马克思理论中的异化阐述,而是用中心-边缘结构这一框架去分析马克思关注的、存在于近代社会的异化问题,从而发现一个新的视角,便于解决这个固有的问题。拿捏中心-边缘结构是把握异化问题的关键所在,而掌握其在近代社会的哲学基元及发展历程又是拿捏该结构的基础。
二、近代社会中心-边缘结构的哲学基元与发展
中心-边缘结构是亘古存在的, 不过近代社会中这一结构因基元不同而区别于农业社会: 近代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以自我与他人这对关系为基础, 而农业社会并非如此, 在农业社会并没有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以近代意义上的权利为基础的, 在农业社会根本谈不上个人权利,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部分取决于自然意义上, 没有个体意识可言。 农业社会的确也存在用等级去区别人们, 但总体上看,处在等级顶端的是王权, 它是社会结构的中心, 所以农业社会存在的中心-边缘结构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 而非近代意义上建立在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基础上。 在近代, 自我出现并一直处于中心地位, 而他人话语虽占有一席之地却难与其抗衡而处于边缘, 自我与他人之间就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
近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的发展,自我意识浮出水面。18世纪是一道明显的人告别“类特性”的分界线,即近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开始生成,每个人都有了作为“人是万物尺度”的自我坐标。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并非像启蒙思想家构想的“人与人生而平等”,18世纪之后的很长时间,自我保持着中心地位支配着他人这一边缘。黑格尔以“主人-奴隶”的关系总结了自我意识的生成逻辑:“主人是自为存在着的意识,但已不仅是自为存在的概念,而是自为存在的意识,这个意识是通过另一个意识而自己与自己结合。”这里的“另一个意识”“其本质即在于隶属于一个独立的存在……主人既然有力量支配他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又有力量支配他的对象(奴隶)”[4](P102-103)这就很明显地说明了自我的中心地位,而他人只是附属物。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更是从自我去推演法权概念从而建立法治共同体的:“理性存在者这样设定其发挥自由效用性的能力,就设定并规定了一个在自身之外的感性世界。”[5](P24)即从作为主客同一体的自我推演出一个由法权规律支配的感性世界,从自我推演出有限理性者及其在感性世界中的必然联系。其实,19世纪开始,自我意识充斥在整个社会,可谓大行其道。
自启蒙运动之后,自我意识作为主流思想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他人话语也在生成。具有犹太教解经地位的《塔木德》包含着犹太教的他人哲学,体现了犹太教对“他人”的敬重:触犯他人就要请求他人的宽恕,这是道德的回归。勒维纳斯(E.Levinas)更是指出“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质”[6](P182),“人类在他们的本质上不仅是‘为己者’,而且是‘为他者’”[7](P182)。从而开启了他人话语的微弱历程。同样,如果从自我与他人的视角去解读“精神分析学”和“现象学”,也能看出他人话语的一些理论端倪。“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Freud)并不满意黑格尔从静态角度对自我意识生成逻辑的总结,而赋予了自我意识以动力机制,即“是他在策动我”,这种转向就是揭示了背后存在的他人话语。现象学是以“存在”为研究对象,在传统哲学中一直就存在着一对概念——“存在”与“本质”,“存在”是与自我意识相对立的,传统哲学追求本质,现象学意味着从自我意识向他人话语的研究转变。
他人话语的出现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自我与他人之间建构起来的中心-边缘结构。表面看来,由于他人地位的提升,自我更加依赖于他人,自我与他人之间获得了可以协调的“融洽”关系,其实他人对于自我而言是一种工具,一种获得承认的工具,进而也带来了近代社会出现的异化:人沦为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自然状态”所讲的狼间的斗争。处在支配环境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在近代社会并没有消解,而是以更合法化的方式存在了下来,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被多数人认为以近代组织为基本理论范式的韦伯(Max Weber),其实也都是为了给统治、支配以合法性。“韦伯的研究究其根本,并不能够被单纯地看作是一种管理理论或组织理论,而是一种以科学化、技术化面目出现的统治术,所探讨的是如何让统治获得合法性的技术。”[8](P138)正如一旦一种理念或者理论获得载体就能更强有力地发展,自我与他人的这种中心与边缘关系被结构化。
同时,在19世纪末的近代社会,伴随着社会的组织化进程*农业社会并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组织,近代组织是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等级结构固然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在农业中,分工因土地的小块耕作而受到阻碍,与这种耕作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工业中,各业手工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业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也是非常少的。”所以,在农业社会背景下去探讨组织甚或组织化的问题是不恰当的。,组织随即成为他人话语的载体。在一切与组织相关的活动中,自我就不再具有原先的“自由”了,因为在协作过程中如果自我不“承认”他人或组织,他是无法生存下去的,随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社会风险日益增多,自我依赖他人和组织获得安全感(学术上我们应该采用“确定性”这一概念)。那种原本存在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就被带到了组织之中,并且组织赋予了这种结构以合法性。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组织本身也成了一个大型的自我,与其他组织以及环境之间也形成了这种中心-边缘结构。所以近代社会,伴随着组织化的进程,以自我与他人为基元的中心-边缘结构开始向更大范畴扩散,也可以说自我与他人这对基元找到了载体而获得更大范畴的发展。
三、中心-边缘结构发展中的多层异化
我们发现,近代社会自我与他人之间发生了异化,自我居于中心地位不下;组织化现象的发生伴随着异化的进一步深化,成员资格的承认异化为组织的封闭,同时组织中令人不舒坦的竞争关系长期存在也由中心-边缘结构给予了合法性,个体与组织的关系异化为同一性*简单来说,同一性就是形式上的统一性,个人并没有将组织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有别于农业社会家园共同体的同质性。,构成近代社会特有的承认、竞争和个人认同的伪共在,这种局面都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上发生、存在的,即为异化。在这发展过程中,我们能看到区别于普雷维什“中心-边缘”思想的行动结构,即动态的。
从马克思的阐述中我们也能发现产生异化的社会结构(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创造中心-边缘结构的概念,我们也不能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追溯中心-边缘结构,只是拥有与之同等性质——支配性质的社会结构——的论述),马克思指出“要使这三个因素(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笔者注)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8](P9)。其实,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里所讲的分工并非单纯是分工本身,而是放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去理解的。在这种社会结构视域下,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是分工造成的还是社会结构(在马克思那里可以理解为所有制)造成的,是首先要分析清楚的。现代经济学家给所有制定性为“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8](P9),即造成不平等结果的分工而产生的所有制,是一种支配控制性质的结构,我们将它称为中心-边缘结构。在这种中心-边缘结构的维度下,微观之处的手段(分工)与宏观之处的所有制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即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状态。
具体来说就是,近代社会以自我与他人二者关系为基元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及其在组织化中的扩散,也就是说,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着异化,以其为基元的组织(间)也发生着异化,而这双重异化都可以称为中心-边缘结构。换言之,异化的发生造成了中心-边缘结构,中心-边缘结构即为异化。如果我们抓住中心-边缘结构,而不是无休止地观察异化现象、争论影响异化的微观因素,将有利于总体性解决异化问题。近代社会拥有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环境,即社会结构完全可以从组织结构的层面去理解,接下来我们就要具体分析在组织(近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中有着怎样的异化形态,这里就不是普雷维什所阐述的静态结构而是动态的。
在组织化演进过程中,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就不像原先那么简单,而是变得更为复杂,自我与他人的那种“承认”关系在组织中异化为组织认同,所谓组织认同简单来说就是组织对个体的认同。我们提到过,他人变成了自我获得“承认”的工具而发生了异化,在组织中也同样,核心概念就是成员资格,近代社会人们能够“团结”的基础是获得组织的成员资格,获得组织的认同,否则“合作”无从谈起。由于这种认同异化,造成了组织本身的封闭,封闭就是组织的第一层异化(这就是为何近代组织系统理论、权变理论等一直强调“开放”的重要性,却未能使组织摆脱“边界”概念,未能实现充分开放的原因),这种异化也就是组织内外部你和我的中心-边缘结构,也是组织之间你和我的中心-边缘结构。围绕组织认同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生成,一切都在异化过程之中结构化,这种被结构化的异化的认同关系在组织中也存在竞争,或者说认同竟然与竞争“共在”,这其实又是一层异化。
竞争不同于斗争,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斗争多以暴力和血腥的方式出现;而在近代社会,人们的关系多表现在竞争上,竞争是由承认关系异化产生的,也就是说竞争和承认“共在”,为什么能够这样?根源于中心-边缘结构这份异化。自我与他人的异化关系扩散到组织后,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关系更为复杂,人们之间并不仅仅满足于以往自我与他人的承认关系,而多了份竞争关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近代社会的文明成果——法制,就从大的范畴给了竞争以合法性,只要不逾越底线受到惩罚;同等意义上,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也给予由承认异化带来的结果——普遍竞争以结构化和合法性。也就是说,发生在中心-边缘结构上的承认和竞争的主体并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业已形成的这份异化结构给予了竞争合法性。这种由自我与他人之间“承认”关系异化所带来的竞争,进入组织后就表现出了表面的“平衡”状态,即承认和普遍竞争的伪共在,这种伪共在就是一种异化,是中心-边缘结构,在组织中就形成了封闭性,从而也扩展到组织之间。
竞争在组织结构中得以稳定和发展,同时也给组织结构带来更大层面意义上的异化,但是近代社会中产生的组织结构都是类似的,都是中心-边缘结构,所以它逃脱不了竞争的纠缠。竞争关系就是以组织化为载体的近代社会的基础关系,而组织中的中心-边缘结构与竞争之间互相依赖,不打破这种组织结构就无法釜底抽薪般地改变竞争这层关系,也就无法真正扬弃异化。
当然,早期自我与他人的这种关系潜移到组织中时并不是没有产生矛盾,虽然组织结构给予了自我意识、承认关系和普遍竞争得以平衡的空间,但自此组织认同与自我认同之间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可以理解到近代思潮中有关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二者关系的争论:近代社会,个体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依靠组织中的他人,同时,组织为了得到更好的认同也给自己打上了共同利益的标签。其实,随着承认关系的异化和竞争关系的普遍化,个体与组织间的异质性不断增多,个体仅在形式上与组织目标同一。问题根源于近代组织结构:存在于组织结构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是支配性质的,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必然有着巨大的隔阂,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尽管竞争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它却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使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8](P23)。这也是近代社会中组织的同一性问题,在组织中的个人已经失去了很多称其为人的本质的东西,也就是人在组织中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要求相反的东西,就等于要求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不要有竞争,或者说,就等于要求各个人从头脑中抛掉他们作为被孤立的人所无法控制的那些关系。”[8](P23)从我们分析的视角来看,存在于异化背后的“那些关系”是中心-边缘结构,要消解近代社会的异化就是要从这份结构入手,在近代社会就集中表现为组织化中的承认、普遍竞争和个人认同的伪共在,从组织结构入手进行变革才能改变社会基础关系,进而构建合作的新型社会关系和结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张康之.基于人的活动的三重空间:马克思人学理论中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历史空间[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4).
[3] 张康之,张桐.论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关于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平等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4).
[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先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M].谢地坤,程志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 埃玛纽埃尔·勒维纳斯.塔木德四讲[M].关宝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7] 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8]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陈萍]
【公共管理研究】
Discussion on the Alienation in the Social View
of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in the Recent Times
LIU JI-fa, XIAO Han
(SchoolofPoliticsandAdministration,Chang′anUniversity,Xi′an710064,China)
Abstract:There are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analysis of alienation by Marx in academic circles, resulted by the hidden social structure problem on a deeper level behind the alien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human development history,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shows differences between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modern society, and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in modern society continuously expands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in the organizational process. In this expanding process,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not only alienates itself but also brings alienation 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hose recognition, dominance and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are being-together. If the root and soil of alienation are explored from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it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reat alienation in an overall angle, but to look for practical methods to discard alienation.
Key words:Core-periphery Structure; alienation; modern society; self and others; systematization
作者简介:韩奇,男,陕西西安人,博士,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KS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310811155001);长安大学创新团队项目(310811151009)
收稿日期:2015-04-13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6-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