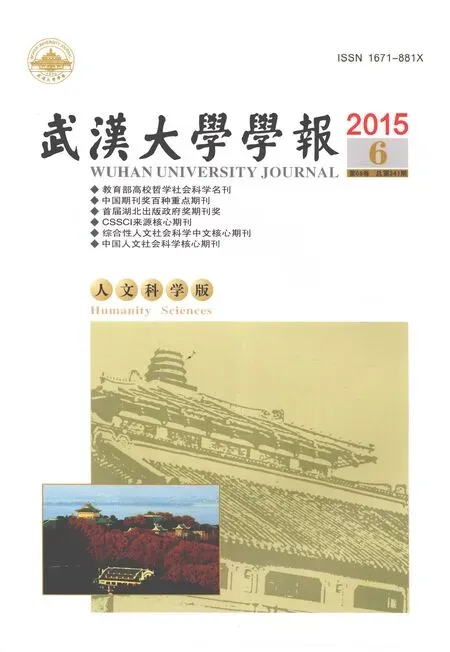罗莎·卢森堡——意象杂陈*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722013JC003)
2015-02-21
罗莎·卢森堡——意象杂陈*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722013JC003)
熊敏
一、 从策兰*保罗·策兰,原名安切尔,1920年生于奥地利一个讲德语的犹太血统家庭,全家在纳粹统治时期被关进集中营,仅他自己脱难,并于战后定居巴黎。他以《死亡赋格》一诗成名,震动诗坛。1970年自杀。的两首诗谈起
策兰曾经写过一首晦涩难懂的诗歌《你躺在》:
你躺在巨大的耳廓中,/被灌木围绕,被雪。/去普韦尔,去哈韦尔河,/去看屠夫的钩子,/那红色的被钉住的苹果/来自瑞典——/现在满载礼物的桌子拉近了,/它围绕着一个伊甸园——/那男人现在成了筛子,那女人/母猪,不得不在水中挣扎,/为她自己,不为任何人,为每一个人——/护城河不会溅出任何声音。/没有什么/停下脚步。
这里要强调的是,最后两段实际上是对一段历史细节的真实再现:1919年1月15日,带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左翼政治家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杀害。在当年对凶手的所谓“审判”中,当法官问及李卜克内西是否已死了时,证人的回答是“李卜克内西已被子弹洞穿得像一道筛子”;当问及罗莎·卢森堡时,凶手之一、一个名叫荣格的士兵(正是他在“伊甸园”旅馆里开枪击中罗莎·卢森堡,并和同伙一起把她的尸体抛向护城河)这样回答:“这个老母猪已经在河里游了。”
诗人直接把刽子手的语言如“母猪”之类用在诗中,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冲击力。“读了这首诗,最刺伤我们的,也正是那在护城河中上下挣扎的‘母猪’这个意象。它永远留在我们读者的视野中了。”*王家新:《在你的晚脸前》,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84~85页。事实上,这首诗是对德国右翼一连串残忍谋杀行为和德国人对此保持沉默的悲观的评论。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策兰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生前的那个时代,却深知类似时代的残酷和身处其间的苦楚,否则卢森堡的形象不会数次出现在他的哀歌中。他认定这两个相隔不远的时代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为之深感无力和沉痛。而这种联系亦已为历史学家们一再确认:“所有历史都具有开放性,因为,以1918年的视角来看,1933-1945年降临到德国、欧洲和全世界头上的灾难是无法避免的。”*雷塔拉克:《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王莹、方长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2页。“霍亨索伦王朝下的德意志帝国在她的被暗杀中庆贺了它的最后一次胜利,而对于纳粹德国而言,则是它的第一次胜利。”*张亮、熊婴:《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1页。
与卢森堡相关联的还有一首更早的《凝结》:
还有你的/伤口,罗莎。/而你的罗马尼亚野牛的/犄角的光/替代了那颗星/在沙床上,在/滔滔不绝的,红色——/灰烬般强劲的/枪托中。
在这首诗中,触目的伤口、野蛮的枪托和她在书简中曾经提到的受难的动物凝结在一起,肉体的毁灭与精神的光芒交相映现。与前诗相比,除了具有同样的难言的悲愤,又似乎多了些对人性的期许和希望,这期许和希望恰恰是卢森堡的人格力量所带来的。
总体上,策兰的这两首诗为我们呈现出的意象是,罗莎·卢森堡作为革命的犹太知识分子和作为理想个人,既为现实世界所驱逐,同时又为它带来人性的微光。
二、 孤独的异邦人*学者林贤治曾写作《嗜血的红色罗莎》,并收入到《孤独的异邦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一书。笔者在此借用这一用语。
策兰的两首诗都涉及罗莎·卢森堡的悲剧性死亡,但她的命运不是纯粹个体的,而是与她相类的同一犹太族群共同遭受的命运,无论是在1919年还是在1933年。从十月革命爆发不久后当时欧美政治家们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义愤填膺地指证犹太民族与革命原罪的密切关联。例如,在1920年2月《星期日先驱报》一篇题为《犹太复国主义对阵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中,丘吉尔写道:“犹太人发起的运动早已屡见不鲜。从斯巴达克斯—魏斯豪普特到卡尔·马克思,再到(俄罗斯的)托洛茨基、(匈牙利的)库恩·贝拉、(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美国的)艾玛·戈德曼……他们一直阴谋在全世界推翻文明,以发展受阻、嫉妒的恶意和不可能实现的平等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胡溦编译:《丘吉尔另一面:曾想信奉伊斯兰教 赞赏希特勒侵略》,载http://www.cankaoxiaoxi.com/mil/20150128/643194.shtml,2015-01-28。从此,犹太革命家与阴谋家的形象根深蒂固地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同时演化为一个几乎无法打破的诅咒。而且即至今日,在许多欧洲人的脑海里仍然存有这样的印象。王昭阳在他的旅欧札记中,“慢慢发现有些不便随意触碰的话题”,“某些久远的、隐忍的、深入骨髓的憎恨,开始冒出污黄色的气泡。不是完全针对解体了的苏联,或是消散了的红色意识形态,更多更主要的,是针对托洛茨基和罗莎共同的种族。”“不止一个人悄悄地告诉我,欧洲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千万人无辜死亡的大灾难,总归与‘他们’有关。不论是金融大亨,还是赤色激进分子,‘他们’总是要破坏和瓦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最习惯的生存方式,是悄悄寄生于另一个国家。”*王昭阳:《与故土一拍两散》,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06~107页。
与刻骨而褊狭的族群仇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汉娜·阿伦特与伊萨克·多伊彻从正面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阿伦特在其关于卢森堡的书评中,十分赞赏内特尔提炼的波兰犹太人“同龄群体”概念,认为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能够卓尔不群,恰恰是源于“同龄群体”对她的无条件支持,而卢森堡本人也对这个“同龄群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页。。在《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游荡的犹太人》一文中,伊萨克·多伊彻将卢森堡等人界定为行走于边界,既在犹太人之中、又在犹太人之外的那类伟大的革命者,并这样阐释他们与革命之间的关联:“作为犹太人,他们仔细地研究不同的文化、宗教与民族文化的界限,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先天优越的。他们在不同的时代的界限中出生和长大,他们的思想在最丰富的文化影响相互交结与哺育的地方成熟起来,他们生活在他们尊敬的民族的边缘或者每个角落。他们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但是又不在社会中,他们是社会中的人,但又不是社会中的人。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超出他们的社会、超出他们的国家、超出他们的时代与同代人而在思想上崛起,并从精神上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而且深深地影响到未来。”*张亮、熊婴:《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6~237页。伊萨克的这个分析相当精辟,也的确适用于罗莎·卢森堡本人。从个人经历来看,卢森堡从幼年起即身处波、俄、德三种文化的交互浸淫之中,却又始终与它们保持疏离。波兰是她名义上的祖国,却将她驱逐出境;她因参与1905年的俄国革命而遭被捕,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时她正深陷牢狱,却富有远见地阐发了她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遭到扭曲的担忧;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身心俱疲,并以与之决裂告终。正因如此,“所有这些伟大的革命家极易受到攻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作为犹太人是无根的;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又是那么的唯一,因为他们在思想传统和他们时代的最高贵的志向上又有着最深层的根源。然而,只要宗教的不宽容或民族主义情绪方兴未艾,只要教条主义的狭隘思想和狂热获胜时,他们就是第一批受害者”*张亮、熊婴:《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第241页。。
然而,阿伦特和伊萨克所描述的只是专属于某类犹太人的特质吗?或许从广义上来看,它同时也是大多数开创者和革命者的一般特质。
三、 丰满的革命者
有些人的意义主要存在于他们给世界增添的作品之中,而不在于他们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罗莎·卢森堡 则不同。历史于她而言绝不仅仅是必不可少的背景;相反,它就像一道白光从卢森堡这面棱镜中穿越和折射,在随之而来的光谱中,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和世界*部分语出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28~29页,但有改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但凡言及卢森堡,必然会强调其犯有错误却又语焉不详,必然会将她置于以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为衡量标准的参照系对她加以贬抑。这时,卢森堡只能被呈现为一个扁平的纸人,人们完全看不到她内心的丰富。然而,“在任何时候人都应该活得丰满”*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傅惟慈等译,花城出版社2007年,第86页。,因此当她在狱中将青山雀的叫声当作一种甜蜜的慰藉时,当她为拯救了一只将死的大孔雀蝶而兴奋不已时,当她为罗马尼亚水牛受虐而流泪时,她就不再是一个单面的符号,而成为我们心中一个亲近的人。诚如林贤治所言,仅仅阅读她的政论,哪怕是一度遭禁的《论俄国革命》,也并不代表理解了她的全部;只有结合她的《狱中书简》,她作为革命者的形象才是大致完整的,因为她在《论俄国革命》中的立论“必与她对鸟儿,土蜂,蓬草的情感相关联”*筱敏:《捕蝶者》,花城出版社2007年,第83页。,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整体中,我们才能讶异于“一个一刻也离不开现实斗争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古典,一个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安静,一个坚强如钢、宁折不变的人是如此地喜欢柔美,一个以激烈不妥协著称的人是如此地博爱、宽容!——这就是“嗜血的‘红色罗莎’”!”*林贤治:《孤独的异邦人》,第166~167页。而如此呈现出来的卢森堡,不但具有明确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则,而且富于同情心、人性和丰饶的诗意。
卢森堡呈现给我们的革命者形象显然是非典型甚至是“颠覆性”的,但也是最丰满和真实的。她最初只是要“做个好人,意味着必要时快乐地将自己的生命投入‘死亡的怀抱’,而与此同时,醉心于每一个明亮的日子,每一朵美丽的云彩”*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第70页。。
四、 永生者
“‘柏林秩序井然!’你们这些麻木不仁的刽子手!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明天革命就将‘隆隆地再次冲天而起’,吹着军号,令你们胆战心惊地宣告:我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依然这样!”*《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78页。这是卢森堡生前写下的最后文字,其后如她所希望的,死在了战斗岗位上。
然而,她真的死去了吗?如同她在文章中宣告的革命永续,卢森堡的思想和精神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延续。
委内瑞拉已故前总统查韦斯曾引述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阐发,声称“批评能够保障社会主义在实现过程中所需要的流畅:如果批评被信条所取代,社会主义就将不可避免地停滞”。“因此,我们欢迎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验进行批评讨论的所有空间。”*乌戈·查韦斯:《从第一行开始:查韦斯随笔》,刘波、范蕾、王帅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94页。卢森堡在世时,她的资本积累理论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内部阵营中亦少有人认同,在半个世纪后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赞誉,他认为“在马克思之后的时代里,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改进和完善马克思的分析,罗莎·卢森堡便是其中之一”*萨缪尔森:《中间道路经济学》,何宝玉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4页。。她也活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誓言中:“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指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董桥:《英华沉浮录》第6册,海豚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更为重要的,她活在越来越多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的心中,敦促人们对一切“固定的东西”进行反思。
阿伦特所期待的“对罗莎生平和事迹的姗姗来迟的承认”*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49页。早已实现,但仅仅承认,还只是停留于与历史的“清结”*这一说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海姆佩尔首先提出来,并广为接受,它意味着与过去达成协议,与历史做出了断,而不是真正彻底的清算。参见王家新:《在你的晚脸前》,第83页。。也许更好的方式是,让她成为我们脚下的“绊脚石”*德国艺术家冈特·戴姆尼于1996年发起“绊脚石”项目。这些地砖作为小型纪念碑,铺在纳粹时期受难者(通常是犹太人)生前居所的门前,以纪念他们并警醒人们牢记这段历史。,成为我们永志不忘、哀伤而甜蜜的记忆!